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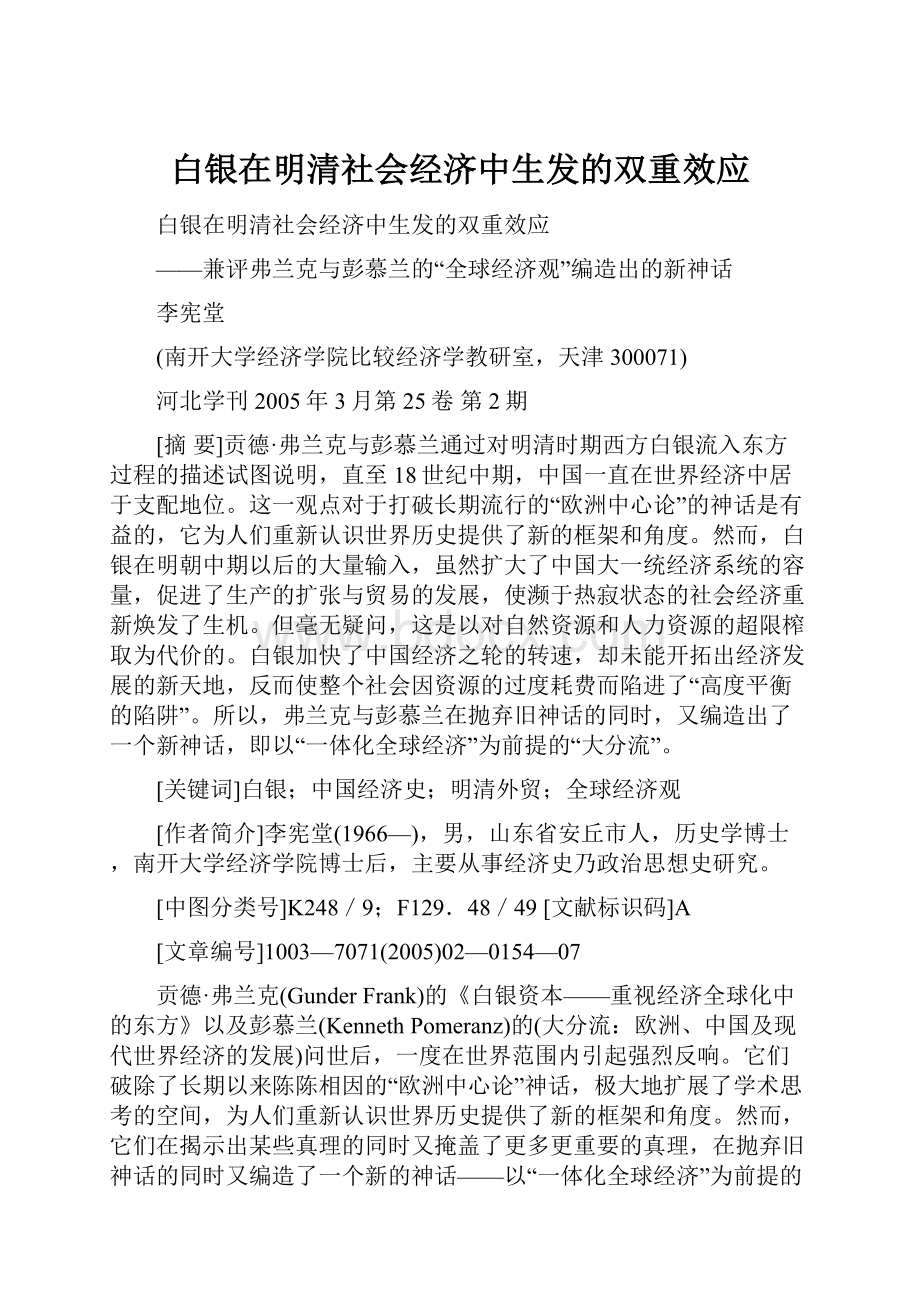
在他们看来,似乎中、西双方的命运在一个神秘的时刻突然发生相反的转向。
通过对白银在国际市场间流转过程的描述,通过强调中国“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1](《前言》),弗兰克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
“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
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
”[1](《前言》)他还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列车的火车头。
而彭慕兰则谨慎得多,他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指出直到18世纪中期,欧洲和亚洲的核心区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与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两者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2](《前言》)。
正如他们自己所标榜的,两人都是从“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经济史的,但遗憾的是,他们进行的还是一种平面上或表面上的比较,在“证明”了亚洲或者说中国拥有至少同样的生产力水平和商业规模后,只能把欧洲扬镳而去的原因归结为海外殖民地的开发、煤矿恰好坐落于工业中心这样的单个事实或偶然机遇,不能解释为什么当欧洲人前仆后继地从事探索新世界的冒险事业、坚忍不拔地敲击天朝上国紧锁的国门而导致民族国家间争战海上的宏伟活剧拉开序幕之时,中国的统治者依然沉湎在大一统残山剩水的迷梦里;
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当西方资本主义横行世界之时,中华帝国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下行的螺旋”。
他们以数据材料证明了东方与西方这两匹马跑得同样快,也曾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却没有发现一也就无从解释一它们跑的方向从一开始就不同。
我的观点是,西方向东方输入白银,从客观效果来看,如同把水流注入油井①,采出来的是更宝贵的原油——物质财富。
当流水一样滚滚而来的白银流人中国后,运出去的却是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
如此绝对出超的外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病态的标志。
在这种看似无比合算的交易开始之时,东西方之间的对决便输赢已定了。
因为西方通过交易得到的是培育社会机能的营养——中国民众的超额劳动甚至生命价值,而东方(中国)得到的只是维持生命活力的血液。
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扩大了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
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
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
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①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
①这个比喻受到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监雅恩·
皮特森·
科恩的启发。
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他得意地宜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从事的豪华贸易几乎是一种无本买卖:
“只要有了船,我们就有了最重要的香料。
那么会失去什么呢?
毫无所失,只要有些船.再用一点水注入水泵引动。
”[1](P378)
一、白银的输入促进了生产的扩张和贸易的发展,为明清两朝的经济赋予了生机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依据一个农民的理想确立了国家制度的规模和气质——简陋、保守,毫无想象力,没有为经济的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
政府把小农经济作为立国之本,既限制大产业的形成,更抑制工商业的发展。
从洪武直到正德,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像一个勤勤恳恳的农夫,一心一意地经营着自给自足的小康之世,对传说中的两宋繁华毫不热心。
然而,至迟到明武宗(1506——1521年在位)时期,由于人口增加、吏治败坏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社会矛盾加剧,朱元璋设计的那种空前保守的小农经济体系濒于崩溃。
据《明史·
武宗本纪》载,正德四年(1509年),“两广、江西、湖广、陕西、四川并盗起”;
正德七年(1512年),“自畿辅迄江、淮、楚、蜀,盗贼杀官吏,山东尤甚,至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绝”。
《明史》的作者是这样评价当时形势的:
“准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几危宗社。
”[3](列传第197)嘉靖朝则更属艰难时世,由于统治者坚持禁止民间通商海外的蒙昧政策,导致东南沿海民不聊生,纷纷下海为盗,“倭患”蔓延二十余年,几乎动摇朝廷根本。
此后,明朝的各代帝王可谓一蟹不如一蟹,全都是昏庸暗昧之徒,但明政权危而不倒,并且社会出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繁荣局面,所依赖的正是白银的力量。
明朝开国之初,统治者出于垄断财富的需要,推行纸钞,禁用金银,但实际上一直禁而不止。
这首先是因为维持禁令的成本太高;
其次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运作实际上已经离不开金银了。
早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政府就将部分税粮折为白银征取;
正统元年(1436年),十万两“金花银”的征收更成为与明朝相始终的定例。
正统二年(1437年),朝廷被迫宣布“弛用银之禁”,于是“朝野率用银,其小者乃用钱”[3](《食货五·
钱钞》)。
社会对白银的渴求也日益强烈。
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批准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请,“准贩东西二洋”,白银开始大规模流入中国②,孕育了明朝中后期被现代许多史学家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之表现的工商业的高度繁荣。
明朝经济的规模迅速扩大,社会的形象和风气也为之一变,“舍本逐末”成为时尚,金钱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宰。
明人何良俊在《四方斋丛说》中称:
余谓正德(1506---1521)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嘉靖)四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
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十倍于前矣。
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
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
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
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的何乔远在其所著《名山藏·
食货》中,记载当时有个叫马一龙的,在一次乡饮酒礼上“集耆老言五十年前事”。
与会的二十四位老人异口同词,表达的都是沧海桑田、人心不古的伤感和无奈。
其中有一个是这样说的:
当时人皆食力,市廛之民,布在田野,妇织男耕,儿女辈亦携筐拾路遗,挑野菜。
而今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廛,奔竞无赖,张拳鼓舌,诡遇博货,诮胼胝为愚矣。
马一龙于天启二年(1622年)战死,主要活动年代在万历末年,即1610年前后,上推五十年,当在1560年左右,即嘉靖末隆庆初。
另外,范濂(云间据目钞)亦称:
吾松(指松江府——作者注)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之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伦教荡然,纲常已矣。
这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严重冲击了旧有秩序的经济和文化基础。
①用这个概念来表述当时原始手工业的繁荣局面,已是一种约定俗成,姑且用之。
②据萧清《中国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在公元1601—1620年间.东印度公司运往东方的银条和银币,用英镑计价,达548090镑,这些白银中大多流入中国;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
自隆庆五年(1571年)马尼拉开港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问,经由菲律宾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6000万披索以上,约合4000多万库平两。
另外,弗兰克综合了不同研究者的观点,认为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美洲和日本总共生产了大约3.8万吨白银,最终流入中国的为7000~10000吨,占1/3到1/4;
而倘若把时间拉长到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中国获得的白银大约有6万多吨,占世界总产量13.7万吨的将近一半[1](P208—210)。
以上所引的作者都是南方人(何良俊是华亭人,何乔远是晋江人),所反映的基本都是南方的情况。
南方商品经济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对外通商的便利。
特别是其中的珠江三角洲、福建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是外国白银直接灌溉的地区。
美国学者Robert·
B·
Marks指出,到1600年,对外贸易“造成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1](P225)。
事实上,在白银的刺激下,不仅珠江与长江三角洲成了中国经济的吸引力中心,包括东北、四川等以前比较独立的经济单元在内的广大内陆地区也都被纳入了雏形乍现的国民经济体系之内,形成了以市场为机制的全国性专业分工和资源协作网络。
首先,它表现在专业化生产程度的提高。
在苏州府的许多市镇,越来越多的农户“以机为田,以梭为耒”[4](《风俗》),“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3](卷4),摆脱了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
其中有些经营好的机户脱颖而出,成为剥削雇用劳动的小作坊、小工场主。
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技术工人也日益增多。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应天巡抚曹时聘在给皇帝的上奏中,提到了苏州纺织业雇用劳动的情况:
浮食奇民,朝不谋夕。
得业则生,失业则死。
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
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6](卷361)。
其次,表现在商业资本的壮大和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
万历三十年(1602年)进士、曾任广西巡抚的谢肇沏在其所著<
五杂俎)中,提到当时商人财力的雄厚:
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富裕的商业资本开始向生产领域渗透,大商人直接投资手工业生产的现象越来越多。
如在徽、杭等地,有些商人不仅从事生丝、绸缎和棉花、布匹贩卖,而且还开设纺织厂、染坊、踹房等从事生产经营。
还有一种形式是商人通过给予手工业者提供原料或同时提供生产工具、收买成品,参与生产过程。
如在丝、棉纺织业中,有的商人“代料”给机户,机户将织成的绸缎布匹送给经销商,领取工钱。
在农副业领域也是这样。
许多商人租佃山场或购买土地,雇用工人从事商业性的农业经营,并且外地人投资的情况很常见,甚至出现了期货性质的“包买”方式。
例如,在广东、福建等地的槟榔、荔枝、龙眼贸易中,包买商人经常是在果树刚开花或结实的时候,通过经纪人整园预买;
到水果收获期,商人雇用民工采摘,并设厂加工,分检、装箱、打包、运输等各个环节都是由专业工人进行的。
再次,表现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不仅出现了专门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许多仰赖于粮食进口的专业经营区域。
如江南的苏、杭、嘉、湖和广州的近郊地区,农民大都以种桑养蚕为业,以至于粮食不能自给(原来是著名的粮仓),需要从安徽、河南以及长江中上游地区运进①;
华北地区生产的棉花、生丝大部分运到了南方,经过加工后最终进入了国际市场;
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通过种植甘蔗加工制成的蔗糖换取华北、华中地区的棉花和外围地区的稻米,把经过加工的棉织品出口到南洋,换回白银;
东南沿海的许多地方则仰仗甘蔗为生,如《福建通志》载:
“泉州枕山负海……负山之民,垦辟硗确,植蔗煮糖。
地狭人稠,仰粟于外。
”
还有,就是表现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的增加。
如福建的一些瓷器工场、珠江及长江三角洲的一些丝绸作坊,就是专为欧洲人加工生产的。
商品经济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广泛渗透,极大地拓展了资源运作的空间,扩大了社会财富的总量。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指标上:
一是耕地面积的增加。
据统计,明朝耕地面积在1578年是701397628亩,1602年达到了1161894881亩”[7]。
不论数据是否精确,土地垦辟面积迅速大量增加却是事实。
二是人口的增长。
人口史学家何炳棣在对大量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1600年的人口达到了1.5亿左右②。
我们知道,明朝自开国后人口数基本上呈缓慢增长趋势,但在正德以前,增长曲线一直没有大的起伏,从嘉靖末年开始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据万历年间《杭州府志》卷十九所记,杭州在嘉靖(1522—1566)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有狐兔为群者”,“近民居栉比,鸡犬相闻,极为富庶”。
明人范廉的《云间据目钞》也有这样的记载:
“余年十五(在公元1554年),避倭入城,城多荆榛草莽。
隆(治)万(历)以来,生齿浩繁。
居民稠密。
”而江苏吴江县在弘治(1488—1505)前只有三市四镇,嘉靖(1522>
—1566)中期以后则增为十市四镇[8](P287)。
可见正是白银的大量涌入,激发了劳动力和土地的潜能,从而支持了商业、手工业的扩容,扩大了小农经济体系的人口承载能力。
三是土地利用率的提高。
不论是路边舍畔还是田间地头,都尽可能地得到了开发利用,如桑树和茶树等经济树木的种植达到了见缝插针,随处即是;
珠江流域的农民以边缘的丘陵地生产的红薯和玉米为生,而把水田出产的大米顺流而下运往珠江三角洲,等等。
①例如,万历《嘉定县志》载:
“其民托命于木棉,因而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舶舻相衔也。
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向背相望也。
②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如M·
K·
贝内特估计,1600年的人口为1.4亿,到1650年才达到1.5亿[1](p236):
赵文林、谢淑君认为。
明代峰值人口为一亿左右(参见《中国人口史》,第357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清朝所以能在改朝换代几十年后迅速地恢复元气,经济规模和水平迅速超过明朝①,与统:
冶者采取了较为开明的工商政策是大有关系的。
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即宣布“除豁直省匠籍”,将工匠编入民籍,宮府需王役则出银雇募,工匠可以自由从事手工业生产或经营。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在海疆敌对势力的威胁解除后,就开放了海禁,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分设海关,管理对外贸易。
这正是海外白银流入的高峰期。
这时,沿海居民赴南洋诸岛贸易的人空前增多了。
据《清朝文献通考·
市籴二》记载,康熙南巡至苏州时,见该地“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赉银面归”。
与欧洲各国的交易规模也扩大了很多。
乾隆朝前期,西方来华商船为每年二十艘左右,到乾隆末年,则增加到五六十艘[9](P49)。
西方人同中国人交易的主要货物就是北美生产的白银。
可以说,真正支持康乾盛世之繁荣的,是白银而不是其他。
二、加剧了对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榨取,过度消耗了民族经济自我成长的机能
为什么一个曾经拥有了全世界白银储存量一半、劳动生产率一度居全球之冠的庞大经济体,会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一败涂地,最终沦入贫困和耻辱的深渊?
像彭慕兰和弗兰克那样,用纯外部因素导致的“大分流”和突然“转向”来解释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
当时中国和西欧之间的经济差异不是数量上的,而是性质上的,是方向上的不同。
它们就像两棵树,一棵正处在成长的早期阶段,生机勃勃;
另一棵在白银资本的灌溉之下一度繁花似锦,但已经渐染秋霜。
历史运行的际遇使它们碰到了一起,它们通过贸易进行的能量交换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但贸易对于双方的意义完全不同:
中国获得的是刺激经济运行的动力,西方获得的是培育社会机能的营养。
如果把白银的获取看作成功的标志,那么可以说,中国的成功就是其最终失败的开始,而西方的失败则为他们筑下了未来成功的阶梯。
彭慕兰、弗兰克之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因为他们想当然地把白银直接认同为“财富”,而没有意识到这种经济壮阳药的严重副作用。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不同性质的输入品对于社会经济的意义是不同的。
所以,有必要首先对外贸商品进行分类②。
关于分类的标准,向来不外乎劳动价值说与效用价值说两种。
一个强调的是价值的客观基础,另一个强调的是价值的主管偏好,看起来像两种不同的语言一样圆凿方枘。
但两者还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就像可以把不问语种归结为同一个语系——只要能找到共同的语法规则。
①据《清史稿·
世宗本纪》记载,雍正元年(1723年),国家田赋收入即达三千零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三两,盐课银四百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三万两。
这差不多是明朝的最高收入水平。
②在这个问题上,向来有大同小异的不同观点,如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
盂(ThomasMum)将外贸商品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为自然财富的、国民节省下来的生活必需品;
另一类是人为财富.指出口的工业制造品;
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F·
Quensnay)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农产品和工业品两类四种;
英国古典学派的巴尔木(NicholasBarbon)分为自然品、人工品;
20世纪美国经济学家I.B.克拉维斯则分为可获得性商品和不可获得性商品。
前者指一个国家能以有利条件进行生产的商品,后者是指一个国家绝对无法生产或虽然能够生产但成本过于高昂的商品。
这些分类部属二分法,强调的是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农林产品与工业品的不同。
它们反映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后盾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外贸观念,用来解释全球性经贸规象则过于狭隘。
价值既不是对象物的属性,也不纯粹是一种主观判断,它是对人和物之间某种关系的认定,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世界因为有了人而有了价值,人在通过劳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了对象物,也创造了自己的需求。
对象物凭自己的自在自足性满足人的某种需求的能力,就是它的价值。
所以,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是价值的表现。
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设定一个基本的“需求”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就像确定海平面作为测量地表高度的基准一样。
在国际贸易中,这个标准就是“国际平均生活水平”,是以主要交易国内社会大众的生活水平加权平均得出的结果。
在这个水平之下,出于维持生存目的而输出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密集型商品可称为“绝对价值商品”,因为在交易中出卖的是本来用于维持平均生活水平的劳动——可以理解为生命价值的让度,如手工生产的粮食和布匹之类生活必需品、棉花与生丝等原料性半成品、绸缎与瓷器及茶叶之类资源成本高昂的高档消费品、以及以低于国内价格出售的工业制造品,等等;
达到平均国际生活水平之后输出的制造品可以看作维持平均生活水平之后剩余劳动的产物,是“剩余价值商品”①,如采用大机器技术生产的农产品及工业制品等;
基于特产性的自然禀赋型产品可称为“相对价值商品”,如珠宝、象牙、贵金属、贵重皮毛、香料等奢侈品,其价值主要是由脱离了基本需求的精神性需求所决定的。
精神性需求的基础是消费物的稀缺性,而稀缺性可以理解为要得到这种商品,必须付出更多的人类劳动,甚至是风险性劳动。
为这种劳动支付的价格是维持奢侈生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通过以上分类,我们就会直观地领会这样的道理:
贵金属(货币)并不等同于财富,因为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稀缺性所决定的,具有很强的边际倾向性;
而作为交换手段和价值符号的货币,只代表着一种兑现财富的能力。
所以,一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获取贵金属,并不一定获得真正的利益,特别是在必须为此输出社会大众的基本生存资源时。
其实,古典经济学家们早就指出并强调过两者的区别,只是现代社会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使我们忽略了这些朴素的真理②。
由此,我们可以洞悉明清时期中西贸易的不平衡性。
中国输出的是绝对价值商品,这类商品的生产是以资源的高耗费为前提的,其中既有当代人的生命价值补贴(劳动力),也包含着后代人权益的透支(自然资源);
而西方输出的是贵金属,并且这些贵金属是在殖民地高压统治下以超经济剥夺的方式取得的,西方人并没有为此支付应有的成本——没有为此耗费自己的生存资源。
并且,当它们被运来中国时,占相当大一部分的还是没有接受商品经济洗礼的自然物,其价值只相当于它们的使用价值,但却以货币的形式支付给中国——小农经济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对货币产生了强烈的需求,为自然物白银赋予了额外的价值③。
这同样加剧了对中国的剥夺。
这意味着白银流入越多,中国民众赖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资源流失越多④,中国基层民众往贫困的深渊里陷得就越深——正是白银使中国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陷入了赤贫之境。
①当然,这里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与马克思的概念不同,姑目用之。
②如法国重农学派的领军人物魁奈认为:
一国财富并非它所保有的货币,而是它所保有的货源与消费货物,货币是一种交换手段,而不是交换的目的。
德国19世纪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List)认为,一国的盛衰荣枯.是由其财富量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其货币量所决定。
一国货币量增多后,人民生活并不能因此而改善,因为货币与财富是处在对立的地位,二者的比例,即是一般物价水准(参见姚贤镐、漆长华《国际贸易学说》,第66页,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出版)。
亚当·
斯密也强调:
“所谓利益或利得,我的解释,不是金银量的增加,而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增加,或是国居民收入的增加。
”(参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61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出版).
③贵金属作为货币的价值是在反复交易的过程中得到确立的,大于其作为自然物的价值。
约翰·
罗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说:
“白银作为金属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有用处。
这种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相对供给量而言对作为金属的白银的需求量。
白银被当作货币以后增加的价值……取决于白银被当作货币以后需求的增加量。
”(参见《论货币和贸易》,第6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
④我们不要忘了,正是马尔代夫群岛的贝壳,摧毁了非洲大陆的经济。
白银只是比贝壳更迷人一些罢了。
其实,当它们被窖藏于地下时,也没什么不同。
货币经济是强者的经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是它的基本机制。
当农民被迫以白银缴纳赋税和地租时,当技术工人仰赖于市场谋取衣食时,他们便丧失了对自己的劳动的支配权,陷进“凶荒之年无以为生.丰收之年谷贱民穷”的困境——“天下之银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
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
”[10](《田制三》)社会大众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疲于应付,无可奈何地陷入了货币为榨取劳动设置的圈套,陷入自我消耗的恶性循环:
付出的劳动越多,就越是贫困;
越拼命挣扎,代表财富的白银就离去得越远。
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