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气为主Word格式.docx
《文以气为主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以气为主Word格式.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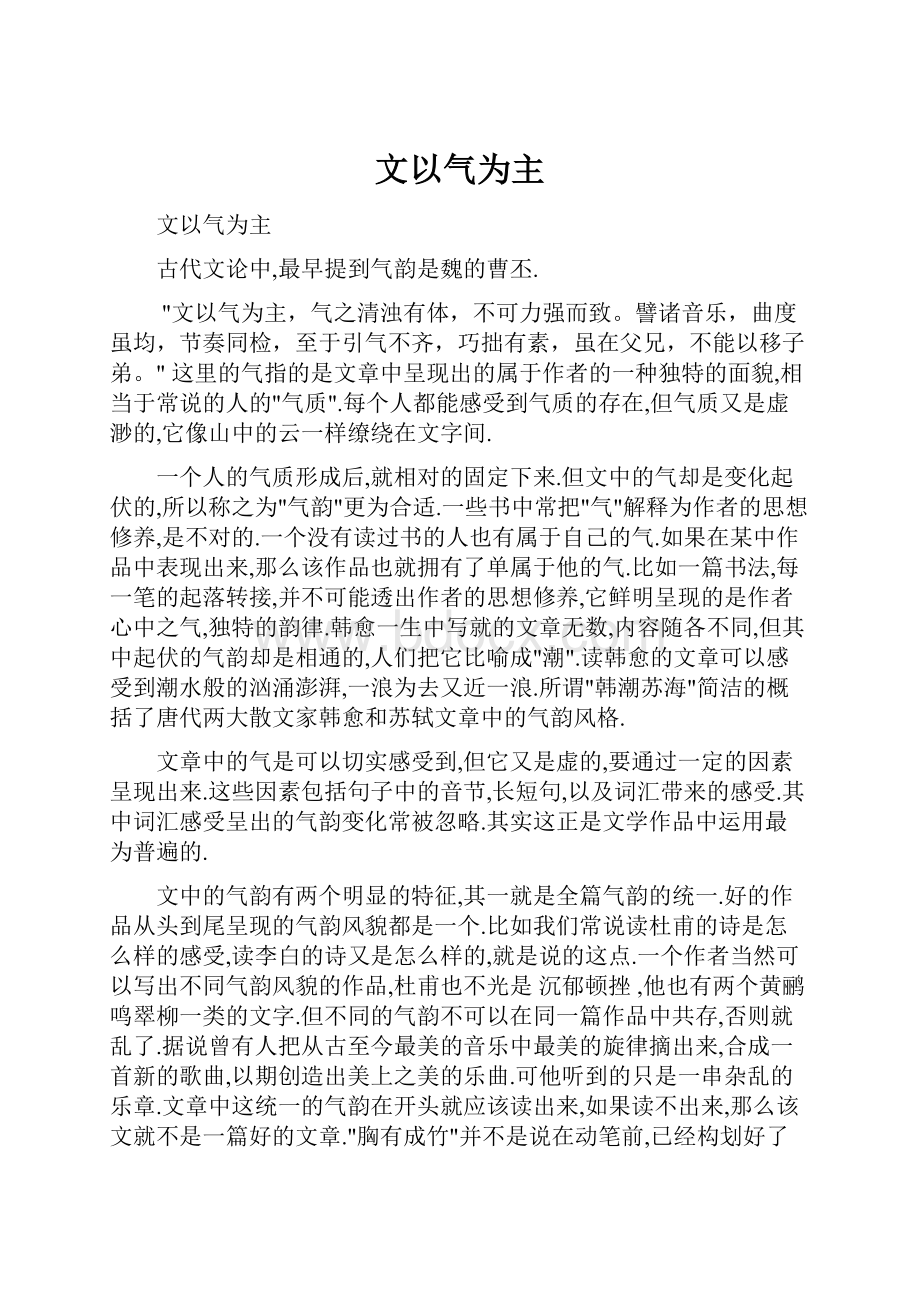
《左传》所谓“诗以言志”意思是“赋诗言志”,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的某种政教怀抱。
《尧典》的“诗言志”,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
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
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负,这从《论语》中孔子要观其弟子之志就可看出来。
而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
《离骚》中所说“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这个“志”的内容虽仍然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显然也包括了因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激之情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内。
至于他在《怀沙》中所说“抚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
”。
这里的“志”实际上指的是他内心的整个思想、意愿、感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诗言志”的内容是有发展变化的。
到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
《毛诗序》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情志并提,两相联系,比较中肯而客观。
主要内容
“诗言志”的内涵十分丰富,各人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本文认为“诗言志”主要是指诗应当表达人们的志向与愿望。
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所以人们在诗中所反映的志愿也不一样。
诗言志,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通过象征手法来表现自己的心曲,都应该遵循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寓志于形象之中。
(改善生活,渴望爱情,实现人生价值。
)
诗六义
当代释义
指《诗经》的“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
这些名称在先秦时就已经出现。
《周礼·
春官》:
“大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毛诗序》明确提出“六义”说:
“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对于“六义”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
在唐以前,并没有把“风”、“雅”、“颂”作为《诗经》的三种体裁,“赋”、“比”、“兴”作为《诗经》的三种表现方法。
如《毛诗序》解释“风”就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就是既把“风”作为诗体同时也作为诗法,是体、法并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在解释“比”、“兴”时也是把二者即作为表现方法又作为诗体,如说“比体云构”,“毛诗述传,独标兴体”,“起情故兴体以立”。
这表明在唐以前所谓《诗经》“六义”是既指六种体裁,又指六种表现方法。
近人章炳麟曾考证作为六种诗体,古代曾以入乐与不入乐加以区别。
“风”、“雅”、“颂”是入乐的;
“赋”、“比”、“兴”,则“不被管弦”,“不入声乐”,所以后来在孔子录诗时被删去。
把“六义”严格划分为三体三法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比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
”这种解释被普遍采用。
古文释义
毛诗·
大序》(节录)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长声)歌之,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反常);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莫过)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使夫妇之道正常),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上以风化(教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谲谏(用委婉的言辞劝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指衰世中的风、雅之作)作矣。
国史(王室的史官)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
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诗六义”的意义
诗六义的组合与定位,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内涵与形式做了最早的分类。
诗经作为一部早期的诗歌典籍,利用不同手法、不同笔韵将一个时代文化融合在一起,利用不同风格的比对,体现了一个诗歌文化中的“雅与俗”的品味,将生活与时代做了一个细致深入的描写。
一个诗书的时代,为后期诗词歌赋的全面发展做了最早的归类。
风雅颂简介
一般认为风、雅、颂是按不同乐调的分类;
赋、比、兴是按不同表现手法的分类。
郑樵云:
“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通志序》)
风
“风”本是乐曲的统称。
《国风》即各地区的民歌——地方风土之音。
一共有15组,但15组国风并不是15个国家的乐曲,而是十几个地区的乐曲,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的乐歌,共160篇。
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带有地方色彩。
从内容上说,大多数是民歌。
作者大多是民间歌手,但是也有个别贵族。
主要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雅
对于“雅”的认识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即中央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
也有人说“雅”与“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
还有观点认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乐。
郑樵显然是赞同第一种观点。
《雅》共105篇,分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
《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贵族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歌。
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
只有几首表达个人感情的诗。
但是没有情诗。
颂
“颂”,即祭祀和颂圣的乐曲,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
作用是“美圣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
其中《周颂》31篇,认为可能是西周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
《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
《商颂》则认为是春秋以前宋国的作品。
赋比兴简介
“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陈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
“比”是打比方,用一个事物比喻另一个事物。
“兴”是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另外一件事物。
“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毛诗序》说: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王国维说:
“颂之声较风、雅为缓。
”(《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
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
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
《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
《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兴
“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
“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
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
例卫风·
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
.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
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
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
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赋比兴”的观念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先由《周礼·
春官·
大师》总结:
“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
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
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兴观群怨
兴观群怨,来自孔子对诗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是对诗的美学作用和社会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
出自《论语·
阳货》: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说明了诗歌欣赏的心理特征与诗歌艺术的社会作用。
孔子说:
“同学们怎么不学<
诗经>
呢?
<
可以激抒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与自然,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讽谏怨刺不平之事。
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
”
这是对诗歌社会作用最高度的赞颂。
现代诗歌批评所津津乐道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在孔子的这段话里实际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简直就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
所以,圣人不仅以诗礼传家,要求儿子孔鲤学诗学礼,而且在这里又一次号召所有的学生都好好地去学诗。
正是由于孔子的大力提倡并亲自删削编定,《诗三百》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了《诗经》,成为儒学的重要经典之一。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毛诗序》那一段著名的更为热情洋溢的颂词: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
总括来说,“兴观群怨”对文艺的社会功能作了全面概括,即根据文艺的特点,指出了文艺具有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
但孔子的目的是为了“事父”、“事君”,有其鲜明的阶级局限性。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从司马迁到王夫之,历代许多理论家都承扬这一思想,都给予高度评价。
王夫之曾说:
“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
”认为孔子这一观点把诗的所有内容都说全了,这种评阅虽为过分,但确实指出了“兴观群怨”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兴”指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感发情感,引起联想、想象活动,在感情的涌动中获得审美享受。
“观”是说通过诗歌可以了解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感情状态。
“群”是指诗歌可以使社会人群交流思想感情,统一认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团结。
“怨”是强调诗歌可以表达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不满与批判。
“兴”、“观”、“群”、“怨”这四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
其中“兴”是前提,它包含了孔子对诗的整体作用的概括,所以“观”、“群”、“怨”离不开“兴”。
而且将“兴”置于首位,充分注意到了艺术的感发作用。
这一思想表明,孔子已认识到艺术的社会作用只能通过美感的心理活动来实现。
兴、观、群、怨以外,诗还可以事父、事君,并且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在孔子以前,人们已经大致上认识到诗歌的美刺、言志和观风俗、知民情的作用,但讲得比较零碎而不全面。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把前人的意见进行概括,对诗的作用作了较有系统的理论的表述,对后世的诗论很有影响。
(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集解》引孔安国注:
“兴,引譬连类。
”朱熹《四书集注》:
“感发志意。
”这是说诗对读者的思想感情有启发和陶冶的作用。
观
《集解》引郑玄注:
“观风俗之盛衰。
”朱熹注:
“考见得失。
”这是说诗能够帮助读者认识风俗的盛衰和社会的中得失。
群
“群居相切磋。
“和而不流。
”这是说诗能够帮助人们互相切磋砥砺,提高修养。
怨
“怨刺上政。
”这是说诗可以用来批评政治,表达民情
所谓“兴”,就是“引譬连类”(孔安国说),并可用以“感发志意”(朱熹说);
所谓“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郑玄说),旁人可以从中“考见得失”(朱熹说);
所谓“群”,就是“群居相切磋”(孔安国说);
所谓“怨”,就是“怨刺上政”(孔安国说)。
孔子把诗歌作为从政和教育的工具,通过对作品的钻研,考察诗歌的政治作用,看到了文学的社会价值,但他随后有把文学的作用归结到了“事父、事君”上去,则又表现出了利用文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用心。
(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
阳货》)。
这是孔子对诗的作用的分析,实际上可说是包含着对一切艺术作用的分析。
在孔子之前,还没有人提出过这样明确全面的看法。
在这个十分简括的规定里,总结了从远古到孔子漫长历史年代里人们对艺术认识的美学内容。
所谓“兴”,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朱熹注为“感发志意”,两注都是……符合孔子思想的精神,并且可以互相补充。
“引譬连类”,指的是通过某一个别的、形象的譬喻,使人们通过联想的作用,领会到同这一譬喻相关的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关于社会人生的道理。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通过个别显示一般,达到一般。
这种不是用抽象的、一般的概念,而是用个别的、形象的譬喻来使人们趋向于领会某一普遍性道理的作法,正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形象思维”的开始。
如果个别的、形象的譬喻不是说明某一普遍性道理的例证和手段,而是同普遍性的道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并且通过直观、联想的作用而诉之于个体的社会性情感,作用于人的个性和心理,这时“引譬连类”所得到的结果就是审美的。
孔子虽然也把诗作为说明某一普遍道理的例证,但由于他强调艺术诉之于人们的社会性情感,唤起个性向善的自觉,也就是朱熹所谓“感发志意”的作用,所以“引譬连类”就不是单纯的说理教训,而是要求用艺术的形象去陶冶、发展、完成人性。
换句话说,由于孔子十分强调艺术对个体心理的感染作用,把启发高扬个体的社会性情感(“仁”)看作是艺术的本质,这就使得“引譬连类”不是导向诉诸理智的抽象的说理,而是导向诉诸情感的形象的艺术。
“引譬连类”与“感发志意”两者在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之中构成孔子所谓“诗可以兴”的理论。
前者指出了艺术的特征是借助于个别的、形象的东西,通过联想的作用,使人领会感受一般的、普遍的东西;
后者则使这种“引譬连类”的最终目的不是说理教训,而是用艺术的形象去感染人、教育人。
“兴”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诗(艺术)应以个别的、有限的形象自由的、主动的引起人们比这形象本身更为广泛的联想,并使人们在情感心理上受到感染和教育。
“譬”与“类”通过想象、联想(“连”)的作用而交融统一,从而以“引譬连类”为其特殊方式的“兴”,在实际上就是通由想象、联想,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和客观化,表现为一个可以直观到的个别现象。
可以证明,“兴”开始包含着对艺术形象的个别与普遍、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理解,对想象、联想、情感认识诸因素在艺术中作用的探索,对审美和艺术欣赏过程中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重要意义的理解。
虽然所有这些理解还处于一种萌芽的、含混的状态中,但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孔子提出“兴”这个总括的概念,播下了一颗有着极大发展可能性的种子,后世中国美学关于艺术特征的理论是从这颗种子逐渐生长起来的大树。
所谓“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基本上符合孔子的意思,但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论语》一书中用“观”字的地方不少,有些地方,“观”即是考察、观察的意思。
如“听起言而观其行”、“观其所以,视其所由”都是考察、视察的意思,并且是以一种理智的、冷静的态度去进行的。
但由于孔子仁学是以情理结合的实际理性为基本精神,就在这理智的、冷静的考察中也仍然伴随有感情的态度。
仅就郑玄的“观风俗之盛衰”的说法来看,在看到风俗之盛时会生出赞美的情感;
相反,回生出嫌恶的感情。
实际上,《论语》中有些地方“观”字的用法,明显地表现了同风俗之盛衰相连的不同的情感态度。
如孔子说: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八佾》)这个“观”字显然同强烈的情感态度相连,意为我怎么会愿意看它,喜欢它呢?
相反,在回想起那已过去的尧的时代的风俗之盛时,孔子却发出了热烈的赞叹:
“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
惟天为大,惟尧则之。
”“荡荡乎!
民无能名焉。
其有成功也。
焕乎!
其有文章。
”(《泰伯》)这种“观”不是充满了热烈的赞美感情吗?
所以,孔子所说的“诗可以观”的“观”不只是单纯理智上的冷静观察,而是带有情感好恶特征的。
孔子在现实生活中看到“风俗之盛衰”的不同表现时即引起了赞美和嫌恶两种不同的感情,在诗中看到这种表现时当然更会引起审美上的不同感受,因为诗中的表现会比现实生活本身更集中、更鲜明。
可见,孔子认为诗可以“观”并不是强调对于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详尽描写,而是强调去“观”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定社会国家的人民的道德感情和心理状态。
孔子认为社会风俗的盛衰和人民的情感心理状态密切相关,所以“观风俗之盛衰”主要是“观”人们的道德精神心理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他称赞《诗》三百篇的好处最根本的在于“思无邪”(《为政》),又称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都是从诗中所表现的人的道德精神心理状态去“观”的。
……所有上述这些说法,包含着一个深刻的思想,那就是要从艺术去看一个社会的状态,主要是看表现在艺术中的这个社会的人们的精神情感心理的状态。
这是把握住了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根本特征的。
因为一定社会时代的人们的精神情感心理状态,正是在艺术中才得到具体可感的表现,并且显示出它的全部的丰富性、多面性、复杂性。
孔子的诗“可以观”的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使中国美学注重审美和艺术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不把审美和艺术看作是同社会无关的东西,能够从社会历史的观点去观察审美和艺术的发展变化,并且把艺术看作一定时代人们的道德精神心理状态的表现,重视艺术与社会的精神和心理的重要关系,形成一个良好的传统。
所谓“群”,孔安国注为“群居相切磋”,朱熹注为“和而不流”,虽然也是从对《论语》的体会得来的,但尚未抓住最本质的东西。
要了解孔子所说的“诗可以群”的含义,首先要了解孔子对于“群”的看法。
孔子所谓的“群”,指的是人生活于为氏族血缘所决定的社会伦理关系之中,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
在孔子看来,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
所以,如在前面已指出过的,孔子反对人脱离社会,与鸟兽同群。
孔安国在解释孔子的意思时说:
“吾自当与人同群,安能去人同鸟兽居乎?
”这是符合孔子的思想的。
孔子在特定的历史形态下认识到了人的社会性,充分肯定了人的社会性。
这是孔子的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
此外,孔子所说的“群”是同他所说的“仁”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他看来,真正的“群”应当建立在人们的互爱互助的基础之上。
孔子认为“君子群而不党”(《卫灵公》),这就是说,君子的“群”是以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