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表演艺术中演员魅力的三种基本类型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论表演艺术中演员魅力的三种基本类型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表演艺术中演员魅力的三种基本类型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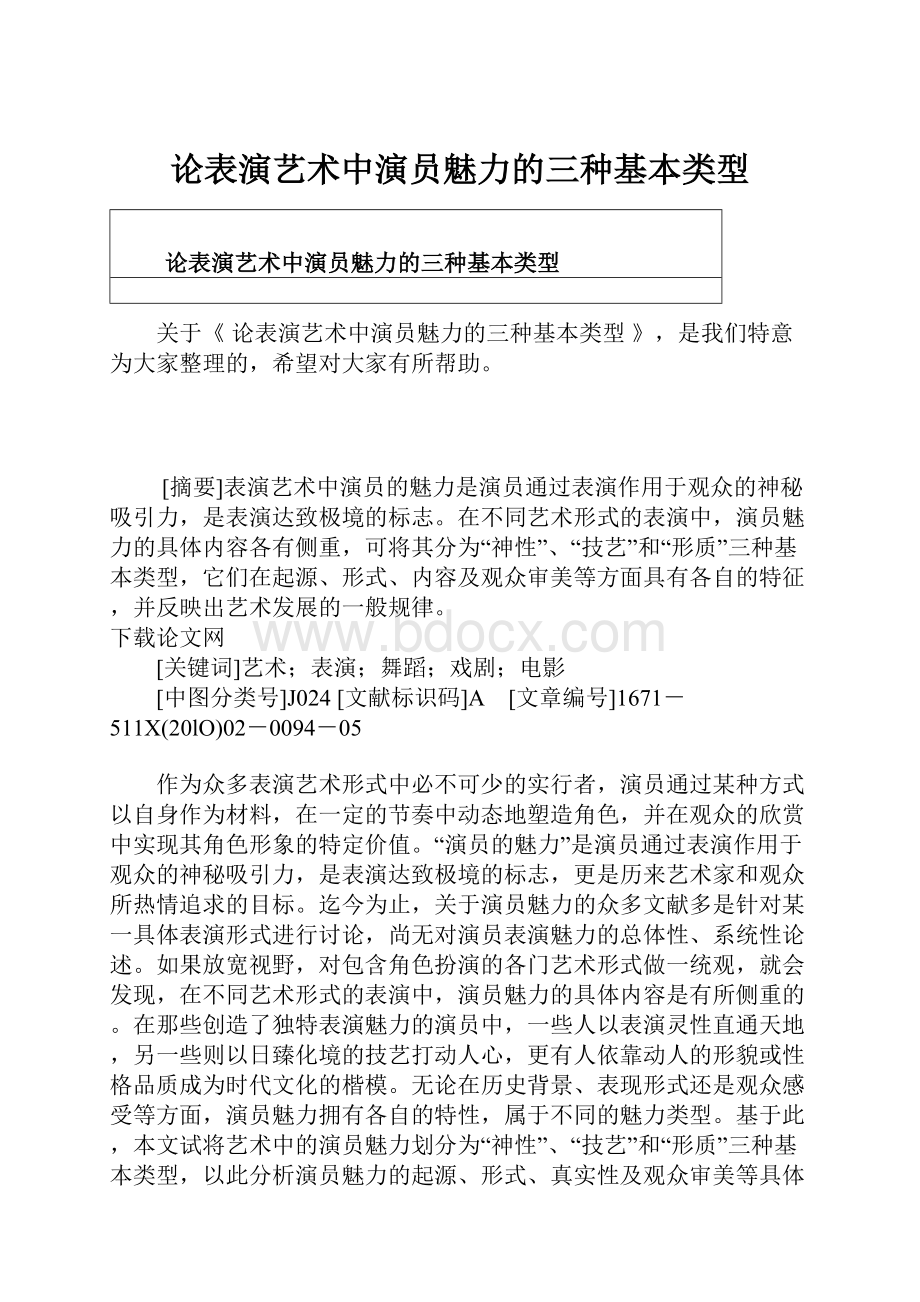
演员以一种直透生命本质的表演方式,成为能与天地沟通的人或某神灵的化身;
观众从演员的表演中汲取到生命原发的力量并受到某种超越凡俗的精神性召唤。
这种魅力类型可谓是人类史前阶段和文明初期的产物。
在原始社会的主要宗教活动中,巫觋通过“咒语”和“降神仪式”象征性地实现祈求、招魂或驱鬼的“超人”的力量。
这包括人与神之间的双向沟通,巫觋或作为人的代表向神祈祷,或是代表神鬼发言,给众人以启示。
这后一种“代表神鬼发言”基本可看作一种代言体的化身表演形式。
如果巫觋被视为最初的“演员”,那么他们的表演吸引力与其被赋予的“角色”密切相关。
在观众眼里,表演者是世上少有的通灵者,他们所扮演的神的“角色”更是充满了魔力,这让原始先民产生一种真实的敬意心理,可谓“神性魅力”。
在今天,古代传统代言神鬼的仪式即便没有完全消失,也在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向娱乐方向转变或者发展为戏曲形式了。
然而,原始的神性魅力却并未因此消失。
据《说文解字》,巫觋是以“以舞降神”的方式脱离凡人身体和世俗生活的。
这说明,舞蹈是“通灵”的最为原始和有效的方式。
我们发现,在现代的某些舞蹈表演形式中所展现的正是原始宗教仪典形式中这最为精髓的部分。
只不过“通灵”的概念已被逐渐泛化,神性魅力的所指已不再是演员对神鬼的代言身份,而是一种与天地自然沟通的“人的神性”。
现代意义的“神性魅力”更加典型地表现为演员的生命表现力,并极少地存在于一些伟大的演员身上。
充满神性的表演往往依托于神话传说、原始仪典等题材,传达出诸如生命、时间、死亡、两性关系等原始而宏大的抽象概念。
例如,在德国舞蹈家皮娜?
鲍什编排的舞剧《春之祭》中,一位少女在古代原始部落的献祭仪式中被选为祭祀春天的祭品,她由麻木、静止转为奔走求助至疯狂的自我舞蹈,她身上单薄的红衣早已在癫狂中脱落,舞者以其裸露的肉体对抗着命运,在斯特拉文斯基的狂野音乐中,整个场景弥漫出一股既神圣又暴力的气息,其中的核心则是女性以一种超越人性极致的恐惧为动力,对暴力的反抗;
台湾舞蹈家樊洁兮则融合古老的敦煌舞姿、中国武术和日本能剧的表现方式,扮演中国沿海地区的守护女神妈祖;
杨丽萍编创的《云南的响声》是直接关于繁衍生息的舞剧,她所扮演的孕妇在鼓乐声中分娩,表现出新生所必经的苦痛与挣扎。
以上种种包含着深沉的情感和博大的精神,解答着人对生命基本问题的疑问。
在形式上,神性演员具有一种模糊、神秘、难以用“语言”概括的原生态的身体符号。
无论是外形还是动作,神性表演所展现的都是以自由和天性为主的身体,绝不追求社会化的身体形态。
演员热烈地展现性、生殖和死亡,却拒绝低俗的情调。
尤其在女性身体方面,其姿态与现代男性意识中的欲望对象相距甚远,例如上文中皮娜?
鲍什虽以裸体示人,但其表演却丝毫不具色情的暗示。
神性表演所追求的是一种抽象的,能够与天地对话的生命形式。
正如现代舞先驱邓肯所言,舞者“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惟有和大自然的韵律取得一致并和它产生共鸣,才能变得又灵敏又活跃。
”她的表演直接从自然界的生命现象中汲取灵感,花朵的开放、海水的波动、鸟儿的飞翔等动作都成为舞蹈律动的启示。
比起刺激神经的直线形和棱角的刺激,这种律动遵循一种自发式的节奏,不需要过多外在节奏的激励,自然也不受其约束。
这种境界在中国古琴艺术中有所体现:
古琴曲不像任何其他乐曲拥有固定的节拍.它可能一强两弱、三弱、四弱、五弱、乃至半强半弱式毫无规律地任意交替。
同一琴曲,到了不同琴家手上,强弱对比或音符时值常常会大相径庭。
但这恰恰构成了古琴的境界,正如琴人郑觐文所言:
“(古琴)板拍不固定,正是其妙处……点明拍子反倒不能尽情发挥,各极其妙,这正是琴曲的伟大、玄妙之处,其他诸种琴曲何所及?
”琴曲乃心声,这突破了机械性固定节拍束缚的抑扬顿挫和起承转合,正是琴人涤净心灵,在大地自然间呼应“天籁”所成的生命律动。
杨丽萍在《雀之灵》中的表演充分地展示出这种生命的节奏,通过添加新的肢体动作,她成功地将傣族民间的孔雀舞转化为自我生命的释放。
伴随表演的是一首缓慢而轻柔的小提琴曲,鲜有突出的节奏点,但舞者却用身体和手臂依照自我的内在节奏发展着动作,她的手指、腕、臂、胸、腰、髋等关节流水般地运动着,她用修长、柔韧的臂膀和灵活自如的手指形态变幻,神奇地塑造出一个超然而灵动的艺术形象。
这充满神性的表演显示出一种波浪式的节奏,是“上升的、扩展的、有其自身的冲动和后继动作的节奏,它前后呼应,在融会贯通中达到无限的程度”。
而这盎然的生命力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自然。
从未受过专业舞蹈训练的杨丽萍正是通过观察“蚂蚁交尾、孔雀开屏、树叶在风中摆动”这类自然现象而获得了表演的节奏。
在神性表演中,演员对角色的扮演包含着一种“自足的真实”。
这是说,演员与角色不是“描摹”与“被描摹”的关系,两者不作区分,在每一次角色扮演中,演员都重又将自我“燃烧”一遍。
同时,演员也不特意迎合观众对角色的心理期待,只求完成自我能量的释放,这种生命的必须才是其表演的目的。
这与形质表演方式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有着本质的差别,后者以实现观众期待的最大真实为目的。
神性表演根本是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表演,它虽然以基本的技能为依托,但演员获得技能的方式往往不是来源于历史的传承,而是个体得自自然的灵感创造,并且更深入地进入无意识领域.不过分展露人造的形式。
观众看到具有神性魅力的表演,保持着一种信仰的态度并感到身心被引至某种超脱凡俗的境界。
然而,这种欣赏是有条件的。
由于神性表演外在节奏性的缺场,观众不可能借由外在的线索寻找到详细而具体的节奏刻度,只有通过直观感受做出浑朴的把握,“神会”到表演的内在节奏。
欧阳修曾谓:
“乐之道深矣,故工于善者,必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
听之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以意,不可得而言也”(《书梅圣俞稿后》)。
这正是神性观演关系的恰当表述。
因此,对神性表演的欣赏要求观众较高的审美层次和感悟能力,只有充满生命力并真正清洁的心灵才能让神性魅力的实现成为可能。
归根结底,演员生命的原初动力形式构成了神性魅力的核心。
神性魅力包括忘我的姿态、长期修炼的身体、表演内容的精神纯粹性、原始性和抽象性;
它展示出表演者自身的内在生命节奏,带给观众超越凡俗的感受。
二
演员的“技艺”魅力可定义为:
演员以一种非凡的姿态展示其千锤百炼的技能,并在游刃有余的角色展示中渗透出个人风格;
观众感受到演员的艺术,对其在表演中所显示的伟力感到由衷的赞叹。
这种魅力类型起源自“娱人”、“取乐”的技能表演,从事这类表演的演员必须通过严格的训练达到超越常人的技能以博得认可。
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某些技能表演形式得到了持续而精深的发展,形成较为固定的艺术表演模式,培养了代代相传的专门演员。
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包括中国戏曲、日本歌舞伎、狂言、西方芭蕾舞剧、歌剧、哑剧等等。
掌握这些传承悠久的技艺,既需要演员过人的天资,更少不了超强度的训练,这两者共同建筑了表演者的“伟力”。
这种以人的伟力成就的技艺在观众那里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人称“炫技”大师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至今仍代表着一种特别的魅力。
他以灵活的运弓、惊人的速度、精确的音准和双音拉奏的泛音等超越时代的技巧,令当时的观众意乱神迷,并传说他是“魔鬼”的化身。
然而,“炫技”二字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机械化展示。
虽然技艺的修炼是身体的规训化过程,但技艺魅力的基础却仍旧是演员的个别天性。
京剧四大名旦都唱《玉堂春》,但他们依不同禀赋各自有所创造,梅兰芳典雅、尚小云刚健、程砚秋委婉、荀慧生俏丽,韵味不同却各具魅力。
可以说,只有在融入了演员有机天性的基础上,技艺才可能具有生命力;
而技艺魅力的关键就在于演员能够在技艺规则中自如地渗透出个人风格来。
有别于神性表演,技艺表演往往不求深刻内容,展现的是处于社会生活矛盾冲突中的类型化人物。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表演内容已转化为展示演技的载体。
因此,传统的经典剧目反复上演,却常演常新,令观众百看不厌。
在任何时候,歌剧《图兰朵》中观众所期待的高潮都是卡拉夫那段考验男高音的咏叹调《今夜无人人睡》。
在形式上,与技艺表演最为密切的是“程式”二字。
程式是某种艺术形式的规则,是艺术家所创造的基于生活而又有别于生活的表现手法,遵循“出之贵实,用之贵虚”(王骥德《曲律》)的原则。
技艺演员需要以“程式”作为标准和尺度进行表演。
首先在外形上,技艺表演展示的就是一种规训化的身体。
芭蕾舞演员立在足尖上的“阿拉贝斯克”、狂言演员弯曲而稳定的身姿、戏曲演员出台亮相的身段和“眼风”……这一招一式往往蕴含着十几甚至几十代艺术家的珍贵艺术经验,也离不开演员常年的修习和创造。
技艺的自如展示是以外在的规定性为依托的,演员的每一个动作、表情、唱腔或念白都遵循着属于某种艺术规则的特定节奏。
例如在京剧中,隐于幕后的现场伴奏者用京胡、月琴、锣鼓等乐器细致地跟随着演员唱念做打中的每一细微而流转;
演员无论是疯癫还是幽怨,痛哭还是欢笑,哪怕是情绪变化中的一个眼神,也都是在一定的锣鼓点中完成的。
技艺的展示必须在具体的节奏中按照程式的规定顺利行进并最终完成,才有可能使观众获得满足。
在芭蕾舞剧《天鹅湖》中,按照惯例,黑天鹅在诱惑王子得逞后会以连续32个“挥鞭转”表示得意的心情。
当演员贴合音乐的节拍,以饱满的情绪完成一个又一个叹为观止的旋转,稳健而自如地将表演推向那最后一转的高潮时,观众席间的默数声早已转为热情的欢呼。
可见,技艺魅力的基本形式是一种精彩的、有把握的变化。
技艺演员扮演角色的真实性可称为“表现的真实”。
演员的“第一自我”与角色之间留有距离,其表演的目的不是“成为”角色,而是为观众诠释角色,强调“表演”的自觉。
这是与神性表演大异其趣的。
演员本人的生命和样貌并不是表演的核心,其所负载的技艺表现形式才是关键所在,这在演员浓烈的面部化妆和服饰装扮中就能窥见一二。
而且,对于通过外部程式描摹角色情态的技艺演员来说,自身与角色的距离并不成为表演的障碍,演员与角色在形貌、性格、年龄甚至性别的差距有时反而让表演者获得了更强的敏感度。
鲜有醉酒经验的梅兰芳能够在《贵妃醉酒》中将醉态表现得非常传神,其原因就在于“醒眼看醉人,看得更清楚,而醉人自己倒未必知道他在醉中是些什么样子”。
而美轮美奂的性别倒错表演则是以性别的距离造就的艺术。
当代日本歌舞伎“女形”演员坂东玉三郎在其著名剧目《京鹿子娘道成寺》中,扮演一位美丽的青楼舞女,他在拍子木、三味线和人声的伴奏呼哨中翩翩起舞,就像一只活跃的牵线木偶,在狭小的空间里挥洒其技艺的自由,细致而明晰地展示出女人的形态,并显示出一种虚幻妖冶的超现实美感。
有意思的是,“女形”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细腻和生动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女性所能达到的美的境界。
这正是因为“女形”演员对女性的观看是以一种有距离的男性视角进行的,这往往比身在其中的女性自身更加敏感和细心;
在表演上,亦会更加强调女性的特质。
坂东玉三郎说:
“在台上,我不是呈现一个女性,而是指示出一个女性的精髓之处。
”(纪录片《WrittenFace》,1995)对此,罗兰?
巴特曾有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女形”演出“不是复制女性,而是意指女性……女性特质被表现出来以供品味,而不是观看。
”这段话不仅概括出技艺表演重“表现”的特性,同时指明,对于观众来说,欣赏技艺表演是一种品味的过程。
事实上,“男人扮演女人”与“女人扮演女人”在观众的审美中是大异其趣的,前者是一种模仿的技艺,而后者则带有更多的天然成分,在两者的审美上。
就存在着些许“品味”与“观看”的差异。
而只有那些熟悉审美对象艺术形式的观众,才能真正“品味”技艺表演的魅力。
总之,演员以其一己之力所生动展现的艺术形式是技艺魅力的核心。
技艺演员以“表现的真实”为目的,通过在节奏中对艺术程式的自如把握。
对人情世态进行生动的描摹;
观众则通过对表演的“品味”,使演员的魅力得到实现。
三
演员的“形质”魅力可定义为:
演员以某种不露痕迹的表演方式,展示角色的身体形态和性格品质;
观众的焦点集中在演员身体、姿态、情绪和感受上,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贴近感,并引发出爱慕、亲密、认同、憎恨、同情等情绪。
在漫长的西方戏剧史中,每个时代都有令人铭记的、能够精彩呈现出人物形貌品质的伟大演员,如莎士比亚时代的勃贝奇,18世纪的大卫?
加里克、西登斯夫人,19世纪的埃德蒙?
基恩、爱利奥诺拉?
杜丝、萨拉?
贝恩哈特,20世纪的约翰?
巴里摩尔、劳伦斯?
奥利弗、马龙?
白兰度等。
而相比戏剧舞台,自20世纪蓬勃发展的电影则令演员的形质魅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从玛丽莲?
梦露到奥黛丽?
赫本,从克拉克?
盖博到亨弗莱?
鲍嘉,从杰克?
尼克尔森到西恩?
潘,从梅丽尔?
斯特里普到凯特?
温丝莱特……事实上,电影演员那前所未有的巨大魅力与电影的形式特性是分不开的。
第一,通过摄影的技巧化处理,电影银幕上的演员在外形上不仅能够达到完美,还能借光影效果增加神秘感;
通过剪辑和蒙太奇,则可以塑造完美的表演。
第二,相比戏剧舞台,电影能够自由变化拍摄的角度和距离。
根据人类学学者霍尔所提出的人际交往心理的“距离模式”理论,电影中相当于私人距离的特写镜头能够将观演双方拉至亲密的关系中,令观众十分容易对演员产生亲近感。
第三,由于屏幕隔开了现实,电影演员的不在场使得这种特殊的亲密感恰恰以观众“单相思”的方式完成,从而为遥不可及的演员增添了魅力所需的神秘感。
第四,电影的自由时空和放大屏幕令演员在银幕中的表演内容既丰富开放又具体细腻,角色的各种情态得以多元地展示出来,从而满足了观众多元的心理期待。
第五,从传播角度看,由于印刻在胶片中的演员数量稀少,演员的表演可被看做德波所谓“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的一种“炫示”。
在视觉文化的今天,这“炫示”的范围已扩展至全球。
以上这些无疑帮助塑造了电影明星的巨大魅力,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虚构的成分。
事实上,英语中“魅力”的对应词“glamour”就包含着“人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带有虚构假想成分的美”这层意思。
与技艺表演不同,形质表演是为戏剧内容服务的,演员的基本任务就是全身心地塑造剧作中的性格化人物形象。
一个具有魅力的人物形象往往包含着角色与演员的双重魅力,且两者可以互为增色:
演员将自身的魅力带人角色,而角色的文学魅力则会令演员呈现的形质更加动人。
在电影《重庆森林》里,王菲将其生活中直率又飘忽的现代青年形象未加更动地带入角色“阿菲”的形象,而“阿菲”追逐爱情和梦想的纯真而古怪的方式,则让王菲本人的灵动形质更得凸显。
谁都无法区分生活中的王菲和电影中的“阿菲”,同时,谁也无法否认“阿菲”形象的独特魅力。
在形式上,形质演员以极为自然和具体的方式呈现角色。
生活中任何一种身体形态、人类最为细腻的表情动作都可能成为形质表演的内容。
形质演员必须经得起仔细而具体的“观看”。
这方面的典范之一是影响1930年代的电影演员葛丽泰?
嘉宝,她以一系列神秘而高贵的女性形象展示出优雅的举止、修长的身材和完美的容貌,她的嘴唇、睫毛、“像受伤的蝴蝶般”瘦削的双肩,情绪起伏所带来的“像一连串涟漪掠过她脸部”的丰富表情都令人铭记。
演员自然形质所赋予角色的“适合”、“美”或“吸引力”是人物形象魅力的根本内容。
形质表演遵循着人在生活中的自然反应节奏,其形态却又不同于一般生活。
这种由演员掌控的节奏是“自由”与“控制”的结合,既需要“自然”,又要求“生动有力”。
优秀的演员能够灵敏地赋予一般生活以富有活力的节奏,天然而生动地描摹人的形态。
例如美国演员梅丽尔?
斯特里普就可以自如地在各种角色间穿梭,塑造各具形质的典型形象。
无论是专横干练的老总、粗犷坚强的女工、隐忍沉默的主妇、严肃古板的修女,还是醉生梦死的艺术家或活泼的“舞蹈女皇”,都被这位伟大的演员赋予了自然而生动的艺术生命。
形质表演追求“再现的真实”。
演员与角色间是一种身心结合的关系。
演员表演的目的就是在规定的戏剧情境中无限拉近与角色的距离,使自己“成为”角色。
实现这一目标的表演方法则并不是固定的。
当代的表演主要倾向于演员在假定的环境中进入角色,遵循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其后继者创立的“由内向外”的表演法;
它注重演员个体独一无二的情感体验,让角色的种子扎根于心,靠个人的养料使其自然长成角色的形象。
另一种表演方法则是以英国古典主义表演派为代表的“由外向内”法。
英国演员深受莎士比亚戏剧锻炼,讲求通过观察生活、搜集人物外部特征获得表演素材,并通过发音、动作、方言、击剑、舞蹈、身体控制等方面的训练完成表演。
正如这一派的杰出代表劳伦斯?
奥利弗所言:
“演员的第一特性就是适应性,演员的身体像乐器一样,必须精细地调音,并经常的演奏。
演员应该能够从头到脚控制全身。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像奥利弗这样的优秀演员在其所塑造的典型形质中具有技术的控制力,但是其表演的结果仍然落在角色形象的“自然”和“真实”上,使表演看起来不像在“表演”。
这种再现式的表演使演员与观众的关系极为密切。
在演员塑造的角色形象身上,不仅有来自演员自身的形质吸引力,还具有前述电影形式所赋予的虚幻性,更可能带有角色所包含的理想化内容。
这十分容易契合观众的心理原型,使其获得自然的审美愉悦和特殊的欲望满足。
观众感觉表演者既亲切又遥远,拥有亲近、喜爱、羡慕、陌生等复杂感觉。
概言之,形质魅力是演员自身形象气质、修养、性格等因素在与角色形象的交融过程中的自然流露,它与人的魅力直接相关,又特别得益于表演形式和表演产品的塑造,是产生最现代,观众在心理上最亲近的一种魅力类型。
四、结语
按起源时间而排序的“神性”、“技艺”和“形质”三种演员魅力,各自对应主要的代表艺术形式:
“神性”魅力与某些舞蹈形式对应;
“技艺”魅力在传统戏曲、歌舞伎、舞剧、哑剧等中生发;
“形质”魅力则主要是西方戏剧舞台与电影的产物。
当然,界限不是绝对的。
任何门类的演员都有可能实现某几种魅力的混合。
例如像玛利亚?
卡拉斯这样的歌剧女高音,她前所未有地将个人特质有机地融入歌剧角色,其魅力既包含“技艺”,也包含着“形质”。
文中的分类是为研究所作的理想分类。
三种魅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在表演内容上,神性表演依托神话传说、原始仪典等题材,传达原始而宏大的抽象概念;
技艺表演则不做抽象内容,以简单而激烈的内容为载体,展示艺术程式;
与二者不同,形质表演则依循多样而具体的戏剧内容进行。
可以看到,演员是从一个抽象化的生命原点转至类型化的人物,再转化为具体的性格化人物。
第二,在演员与角色的关系上,神性表演不似技艺表演中“描摹与被描摹”的关系,也不追求形质表演那样好似日常生活的真实感,而是根本从大地而生,只求生命的自我燃烧。
三者有着“自足”、“表现”与“再现”的区分。
体现在表演方式上,技艺表演包含了人类共同创造的艺术成就;
神性表演虽然以基本的技能为依托,但相比技艺表演,演员获得技能的方式往往不是来源于历史的传承,而是个体得自自然的灵感创造;
形质表演虽然也依靠基本的技能,却要实现“非表演”的表演,最终落在性格化的形象上。
这是演员从灵性向伟力,再至个性的变化过程。
“神性”魅力包含着脱离社会的自由身体,不迎合观众;
“技艺”魅力则包含着规训化的身体和满足观众的表演“自觉”;
“形质”魅力则最大程度地通过天然的人物形质契合观众的心理期待。
第三,在审美上,观众通过“神会”沉浸在神性魅力中;
通过“品味”获得对技艺的审美把握;
通过“观看”得到形质的真谛。
可见,魅力的实现是从神秘的人性本质走向神秘的观演方式,观众从感知天地的境界转向艺术的审美,再转至原型和欲求的满足。
就此,我们可以总结说,按起源先后排列的三种魅力是从清澈的生命之源转向人类的文化创造,再转向个体形态的过程,也是从精神性走向世俗化,或从形而上转至形而下的过程。
它揭示出表演艺术的一种步入平凡化、大众化的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艺术史的发展进程。
然而,虽然三种魅力有其各自的成因,但却拥有相同的根本。
“生命活动的过程,既包括低等级的形而下也包括高等级的形而上。
一切受思维支配的行动过程,最终都是追求完美为指归的……”也就是说,尽管其形式和内容有所差异,三种魅力却都标志着“完美指归”的境界。
而对演员来说,魅力的共同根本是什么呢?
正如学者所回答的,艺术的魅力正是一种“真实生命之内充”,也就是说,无论是“神性”“技艺”还是“形质”魅力,都意味着演员已然能够做到无所挂碍的浑然天成和自如,在充盈着演员个人生命力的表演中显示出各具内容且韵味无穷的境界。
这就是演员的魅力。
本文三种魅力的排列并没有任何重要程度的意涵在内,它们一样具有欣赏价值,是艺术史中的珍贵内容。
对于艺术中演员的魅力,本文还只停留在提出问题阶段,最终的结论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