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陈平原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陈平原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陈平原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3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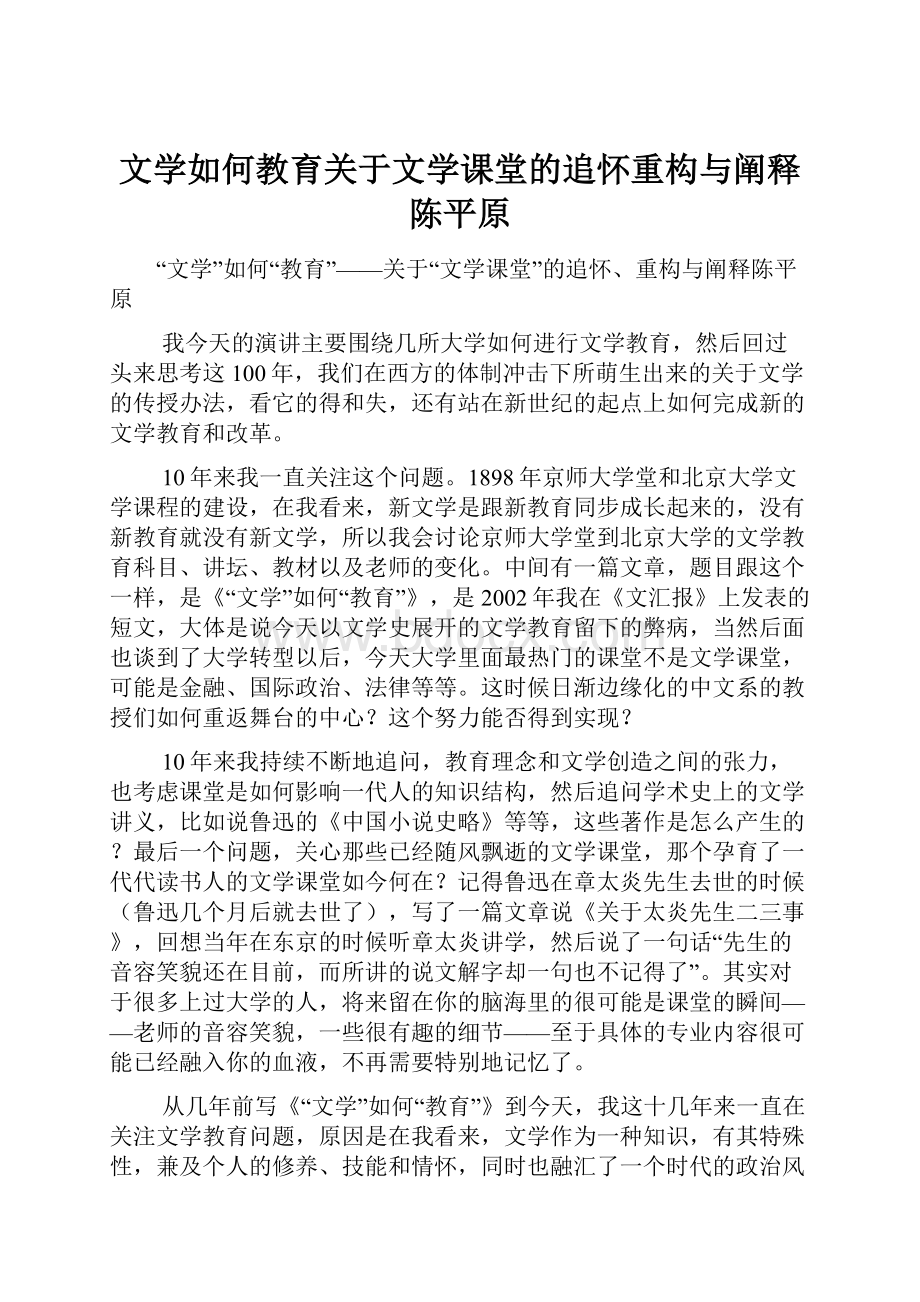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学档案馆里面的资料,也可以看到各种出版的著作,但惟有第三者——文学课堂,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不要说没有录音录像设备,即使有也没有办法形神兼备。
因为在我看来不存在标准的教学——没有标准的老师,没有标准的教案,也没有标准的课堂。
好的老师每次讲课都不一样,除非你拿着讲稿念,如果不是的话,大环境、小环境,个人心境、今天的心境,以及才情、听众都影响到你这一堂课的表述,所以说课堂基本上没有办法固定下来。
这正是课堂的魅力所在。
课堂一如舞台,好的大学老师讲课是根据学生的需求而进行的一场文学表演,理想状态是有教案能发挥,没教案随口说的那叫脱口秀,不叫大学课堂。
第二个是不限于具体知识传播。
讲文学的往往不限于文学,同样道理,讲哲学、讲历史都是这样的,一般在课堂里面隐含了其他内容,比如说对社会的关怀、个人的道德情操,还有对时间的感触等等,都在课堂里展现。
第三是关于学术上的前瞻性。
好的大学教授会把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他对未来学术发展的倾向、考虑放到课堂上展现。
在北大讲课,基本上都是讲我还没有出书的,出了就不讲,也就是说我在做什么,思考什么,希望我的学生跟我一起思考,这样的话才有前瞻性。
如果拿一份已经出版的讲稿来讲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第四,讲课必须兼及老师的能力与学生的趣味。
老师各有专长,一般来说,小学、中学要求有标准教案,大学里面没有,大学里面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加以发挥,但问题是现在很多老师不考虑学生的趣味,讲课很难跟学生对话。
当然我说了,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二者结合才是一个理想的课堂。
讲课是一门艺术,我会想到一本书,《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里面提到了美国的大物理学家费恩曼,他好几年连续地自告奋勇地给大学新生讲课,那个传记里面有这么一段描述非常精彩:
“对于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结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焰火,无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研究生,还是普通民众,他都能做到谈吐自如。
”这时候每一场演讲都是一场表演,就像舞台的乐手、舞者、歌唱家一样。
物理学家做得到的,文学家也应该做得到;
物理学课堂能够做到这点,文学课堂也应该能够做到这点。
今天我就想谈这个问题,围绕下面9个问题,来谈关于文学课堂应该怎样呈现曾经有过的迷人的风采,以及留下来的遗憾。
第一个是讨论学生们的追忆而呈现出的文学历史,而不是档案里面出来的。
第二个是学科化之前,就是文学学科建立之前的文学教育。
诸位知道,晚清以前,中国人当然也有文学教育,但跟今天文学系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的课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另外一种文学教育,等下我会提到。
第三个是讲课堂内外的笑声,是讲1920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略》那个课堂。
第四个是新文学之学院化。
1929年当“清华学堂”变为“清华大学”的时候,朱自清开的一门课——“中国新文学研究”——留下的故事。
第五个是教授们的诗意人生,是讲当年国民党建都南京以后,南京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当年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他们的教授(比如黄侃、吴梅)怎么做学问。
第六个是创作到底能不能教,讨论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这么一个作家进入大学教创作碰到的障碍。
第七个是史家的诗,讲1949年钱穆在香港建立新亚书院,那时候他们开的文学课程。
第八个是文学史家的情怀。
1946年台静农应邀到台湾大学教书,而后20年,他当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建立起中国文学史课程,那个课程里面隐含了什么样的情怀。
第九个是倒过来的文学教育,就是1958年中国国内开展教育革命,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55级学生,他们如何起来响应教育革命的号召,编写文学史,留下了一大堆的故事,而过了50年以后,这些人年纪大了,反过来反省当年走过的道路,然后来看一下文学教育怎么样才是比较理想的。
第一个,因追怀而获得的“历史”。
我说被发现、而且被阐释的传统才有生命力,否则的话它是一个古董。
这种被发现、被阐释的传统介入当下的教育改革,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我的追忆里面涉及到具体的人物、事件,而不是一般的档案、一般的资料,比起档案、表格、数字来说,这样有温情,可感触。
表格那样的东西很重要,但只有专家才解读。
而今天我想讲的各种各样的追忆,各种各样的关于文学教育的故事,很难被一般大众理解,而且我以为被叙述,以及被遗忘的那些故事,可能包含的内容比档案馆里面的数字更重要。
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于前辈的追忆,我们才能理解那段历史,如果没有王瑶先生整理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或者说没有程千帆对原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师长的诗意人生的追怀,没有汪曾祺对沈从文教育方式的追忆,没有余英时对钱穆和新亚书院的追忆,就没有今天关于文学教育的一系列的五彩缤纷的场面。
可以这么说,从1998年到今天,十几年间,我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出版了这些讲大学的书。
今天我的专业除了文学史、学术史之外,大学的研究可能是比较受关注的,包括今年初的《陈平原大学三书》都是我谈大学的。
我谈大学的策略跟一般的教育学院的研究者不太一样,就是上面标的那句话“不避雅俗,兼及文史,在叙事和论述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因此我的大学研究接受的面会比较广一点。
下面我举三篇文章说明一下,比如说讲清华国学院的时候,专门强调弟子的位置。
所有的大学,其实是靠弟子追忆出来的,老师做出成绩,假如没有弟子追忆的话,老师会被历史所遗忘,弟子的追忆是构成学术传统的关键一环。
弟子的追忆是将所有的学问变得可触可感可亲可爱的关键。
所以我说,在学术史上谈大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因素考虑进来。
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是大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互动,学生的专业成绩贡献,还有他们的追怀是构成学术传统的关键。
还有一篇文章《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我讲钱钟书的《围城》里面的三闾大学,还有鹿桥描写西南联大的《未央歌》,还有杨沫的《青春之歌》,以及《青春之歌》里面的那个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张中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大出风头,写了很多文章,结集为《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这三本书,这三本书里面最精彩的就是讲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以及北京的其他大学学者们的风采,而这个风采和《青春之歌》的革命想象构成一个对弈,革命的北大是北大,学问的北大也是北大,而两个北大之间是互相矛盾的,在这中间需要我们考虑几十年来意识形态的渲染,使我们对大学的想象发生偏差。
所以我想通过清理几十年间讲大学的小说、散文、诗歌,以及其他作品,来看我们怎么讲述大学的故事。
其实我最早写的还是《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我们怎么进行文学教育?
前面有一段话:
“文学教育作为一种知识生产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教育理念变了,知识体系就必须变,知识体系变了,文学史场景也必须变,大学里的课堂和讲授,跟社会上的文学潮流,表面上没有关系,其实关系很密切,对文学史的叙述和讲授,直接地影响了当下的文学创造。
”胡适说白话文学是正宗,周作人又介绍欧洲文学潮流,鲁迅讲小说史,吴梅讲戏曲等等,所有课堂上的课程变化很快体现在社会上文学潮流的变化中。
从这个意义上,课堂连着社会,文学讲授连着整个文学创造。
这是前面我的研究。
今天主要讨论的问题是用各种历史记忆讨论20世纪诸多大学的文学课堂,思考现在的文学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可能采取的突围的策略,表面上是讲故事,勾及历史,背后是隐藏了我对文学教育的可能性的思考。
本来文学教育必须涉及到课程与演说、讲义与著述,还有意识形态对于大学课堂的控制,但一些问题暂时讲不了,我先从文学课堂入手,来呈现大学在1910年代到1960年代的文学课堂的情况,这里面涉及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东京、广州、昆明、香港、台北等等,涉及到各种各样的文学趣味和政治立场的学者,他们怎么在课堂上表演他们的人生。
第一组人讲的是在受西学影响建立起学科化之前的文学教育,举的是康有为和章太炎的故事。
传统中国当然有文学教育,但这个文学教育和今天的课堂讲授完全不一样,最大的特点是,大都是只言片语,很精彩,但不是文章。
今天的大学里面教授的两个小时演讲就是一篇文章,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都是文章,我们必须围绕一个主题,给一个题目,包括我今天来会报一个题目,中间还有几个章节,这都是现代学术进来以后才有的。
古代不是这么讲学问的,等一下我会讲到。
那时的文学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满天星斗、点到为止,我会举一段给大家听。
文字这么简练,思路这么跳跃,除非我们都是朝夕相处的师徒,我才可以那么讲。
今天诸位进这个课堂之前,对我毫无了解,所以我要那么讲的话,是不行的,如果是跟了我七八年的学生,我只要讲上半句,他就知道下半句。
古代的书院就是这么讲出来的。
这里有口述者的随意发挥,记录者的刻意选择等等,留在今天,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文学课堂只有结论,没有论证过程,就是一句话,一个判断。
先说康有为,1891年到1897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这时期的学生后来很有名,包括陈千秋、梁启超、麦梦华、徐勤、梁启勋等人,都是他的得意弟子。
万木草堂当时留下来的记录稿,是他的学生们大家一起记,晚上一起拼,重新把它整理出来的。
目前的记录稿有两种,一种在中大图书馆,一种在北大图书馆,由北大的教授楼宇烈整理,20年前出版了其中的一部分。
这个书《长兴学记》、《桂学答问》比较少,后面主要是《万木草堂口说》,就是当年在万木草堂,康有为讲课的记录稿。
当然在没有录入设备之前,记录可能是简要的,但是这个简要也让你明白当年的讲课是什么样的。
梁启超日后写《南海康先生传》,里面说到他讲课的特点是:
每论一学、论一事,上下古今,究其沿革得失,引欧美以比较,进退古今之间,思想之由日益发达,我一辈子的学问从那儿出来。
这里的“引欧美以比较,随时上下古今”,不是一个一般性的论述,是真的这样,等下我们看他的讲稿就知道。
他的弟弟梁启勋写《万木草堂回忆》也说到这点。
“每论一事,上下古今”,他最喜欢讲的是学术源流,包括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等九流的学说,也包括文学中的诗、书、画、诗词等等。
比如说他讲唐诗的李、杜,会讲李、杜以前怎么样,李、杜以后怎么样,这个讲课的办法,特别像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就是前面的学术源流更像哲学史,后来的文学研究大体上接近我们的文学史,等一下我会举例说明他是怎么讲的。
有一个细节,另外一个学生说,当年康有为讲课的时候没有书本,讲席上只有茶壶茶杯,讲到一半还要吃点心,因为一下子要讲两三个小时,太累了,耗气太大,必须吃一点东西。
讲什么?
讲学术源流,当然也会讲八股。
因为在科举废除之前,主要是讲学问,偶及八股,对学生有一点好处。
我讲里面的文学部分,找了一章,这里的“/”表明是一句话,本来是断开来的,我这里抄两页给大家看,讲到文学部分:
“古人言语文章无别/六经皆孔子文章/《易经》多工夫。
/吾之微谓人皆死,唯文不死,古来瞬间豪杰皆死,唯有文可以不死/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文有自然之法,有创造之法。
/《诗》,词章之祖,李斯词章亦佳。
/《书》,开记事之体(《尚书》是记事的体制的变化)/后望至六朝/韩愈一人独唱古文,当时未之有,跟他的只有柳宗元等几个人(从之者柳宗元及其徒数人而已。
)(韩愈的文章况为有宋一代,本朝,也就是清代只有三个,就是清初三家,龚定庵是晚清的。
)/能追周秦以上文/唐以前之文,简腴厚曲,唐以后之文,长枯薄直。
”就这么讲下来,诸位,如果今天我们在课堂上这么讲,学生肯定抗议,说你上一句和下一句没有关系,上一句是一个判断,下一句也是一个判断,而且每一句话都跳跃,可是这是一个读书人一辈子的心得。
今天我们做博士论文,可能就照里面抄几句,然后就开始论证、找材料,最后是敷衍成篇。
刚才我说了,古代的书院教文学,书是自己读,老师的任务是点拨。
而今天教文学的办法完全不一样,今天再这么讲,学生们肯定抗议。
还有一个学者是章太炎。
章太炎在1906年到1910年在东京,他1903年被关起来,1906年出来,孙中山请他到日本主持《民报》,同时讲学,草创“国学讲习会”,以及在大成中学讲,以及后来在民报社有一个“八人小班”,其中包括鲁迅、周作人等人,所以特别有名。
当年他一边干革命,一边做学问,做学问除了写作还要教书,带着一批学生,既有成规模的演讲,也有小范围的讲学,这使得我们今天留下很多回忆资料,让我们了解章太炎在东京的讲学情况。
有一点我们知道,他主要讲《说文解字》,同时讲《史记》、《庄子》等等,各家说法不太一样。
我举几个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是任鸿隽说:
当年在大成中学讲学,先讲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再讲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再讲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再讲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一周一次讲了两三年。
接下来还讲诸子,讲《庄子》。
据任鸿隽说,后来还专门讲了一次中国文学史,怎么讲也不知道,因为没有材料留下来,这是几十年后的回忆,不太可靠。
但是现在国家图书馆藏了另外一个跟了他很多年的学生朱希祖(后来在北大历史系当主任)的日记稿本,根据那个稿本,章太炎确实在大成中学每周讲两次课,后来讲《庄子》、《楚辞》、《尔雅》,而且还和钱玄同、许寿裳、鲁迅、周作人等8人组成小班,在《明报》讲课。
后来这个小班很有名,因为8个人都是日后的名人,尤其鲁迅、周作人特别有名,他们的追忆文章又非常精彩。
但有一点,他们只听了《说文解字》,听《说文解字》不是为了做小学研究,而是为了写文章。
周氏兄弟当时立志要做文学,然后从小学入手做文学研究。
看看他们的上课情况:
“听他讲课是零八到零九年,大概听了一年,一个桌子,先生坐一边,学生三名围坐,讲《说文解字》。
太炎先生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对年轻学生很好,而且夏天不穿上衣,穿一件背心,留着小胡子,笑嘻嘻地讲述庄谐杂出,好像庙里的菩萨一样。
”这样的章太炎我们日后不能想象,他就是这样在东京跟几位学生讲学,讲什么?
《说文解字》之外,其实还讲别的,第二学期讲《楚辞》,但鲁迅、周作人已经离开了,没再听。
日后他的《说文解字》笔记,包括钱玄同、朱希祖、鲁迅的合在一起,现在已经刊行了。
我当时就说,可惜了,他的其他课程,《诸子学》、《庄子》、《楚辞》、《中国文学史》没有留下笔记,要是有的话会更精彩。
当然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做了一次系列的演讲,那个演讲后来出版了,叫做《国学概论》,有三种版本,一种是《申报》的记者记录下来发表的,一种是张冥飞记录发表的,还有一种是曹聚仁发表的。
章太炎说曹聚仁的可以,另外两种是胡说八道,不能信。
为什么?
我先说一下听课情况,因为章太炎的名气太大了,1922年第一次讲课有1000人来听,后来只剩下几十个。
公众是来看名人的,章太炎说的他们听不懂,他讲的是经学、哲学、文学的演变。
为什么别的人记录不好,只有曹聚仁记得好?
有两个道理:
因为章太炎先生的学问,别人没读过他的书根本听不懂;
第二个,章太炎先生的余杭话只有曹聚仁听得懂,很多在座的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所以我看记录稿,第一讲有大纲,三本差不多,从第二讲开始就乱了,尤其是张冥飞先生胆子特别大,听不懂,然后自己发挥,所以说出来的都不知道是谁说的。
章太炎非常生气地说只有曹聚仁的可以。
曹聚仁是浙江一师的学生,在此之前已经读过他的书,加上是老乡,所以他知道他说什么,现在他这个版本被接受。
这个本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国学研究分成经学、哲学、文学。
经学是传统的说法,哲学、文学不是传统的说法,在晚清之前没有哲学、文学这样的说法,学科的分类已经受到西学的影响,我们没办法再回到国学的范围内来谈文学了。
刚才我想描述一个梗概,就是说在现代大学建立之前,在书院向现代大学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学者如何讲授文学。
下面我讲的是1898年北京大学开始创建,此前还有苏州大学、东吴大学的教会学校的一些课程。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个体制完全确立,我们今天所有的课堂讲授办法是从那个时候延续下来的。
这里面文学是什么?
文学被分成若干个分支,文体问题、时代问题、风格问题一个个分下来。
我讲一个人的课程情况,那就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的课程、课堂的情况。
当年鲁迅是教育部的官员,在北京大学兼课,所以称为讲师。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有一个领导露怯了说“北大很厉害,鲁迅才只是讲师”,他不知道那个讲师是兼职的意思。
周作人是教授,鲁迅是讲师,是因为鲁迅的正职是教育部的官员,而且鲁迅不仅在北京大学讲课,还在别的学校讲课。
第一个请鲁迅讲课的是北京大学,时间非常准确,因为鲁迅的日记记下来了,1920年8月6日,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代表校长蔡元培送了聘书,第一次到学堂讲课是1920年12月24日,讲中国小说史,一直讲到1926年。
讲课的讲稿先是油印,后来铅印,到1923年初,上册正式出版,1924年出下册的本子。
今天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那个本子基础上略作修改,可以说就是北大讲义。
除了北大讲义以外,1921年他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是后来的北师大讲课。
1923年到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也就是女师大,当国文系小说科的教员。
另外还在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小说史,在集成国际语言学校讲了7次课,讲什么不知道,因为到现在为止考证不出来,日记里面只提到到哪里讲课。
在黎明中学讲高中的文科、讲小说。
在大中公学讲新文艺,在中国大学讲小说。
我们可以说,教育部的官员鲁迅先生在北京风尘仆仆,城南城北到处兼课,我统计了一下,最多的时候是1925年的11月,他居然同时在6所学校兼课,一个星期他讲6所学校,主要讲小说史。
当然课不用备,可以用北大的讲义,但是中间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件是女师大的风潮,“三·
一八惨案”。
所有在中国念过书的人大体上都知道“三·
一八”,以及《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因为进入了中学教材。
1926年形势紧张,张作霖打到北京来,通缉的名单上有鲁迅,鲁迅跟许广平一同南下,他到厦门大学教了一个学期,然后转广州,这个过程大家都熟悉。
在北京讲课的鲁迅风格如何?
鲁迅不同时期的照片大家都不陌生,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在课堂上的风格。
其实图像很说明问题,我后来说他是“冷幽默”,诸位大致有一个想象。
他的兄弟不一样,周作人不会讲课,他的文章写得很好,讲课就是照本宣科。
他的演讲,据说第二排以后的都听不到,第二天看了报纸才知道他昨天讲了什么。
鲁迅不一样,他很会讲课,教学效果极佳,在北大的课堂上经常是人山人海,窗户外还有人在听课,有很多追忆和赞叹。
当然你可以说鲁迅日后成为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别人回忆的时候总是多溢美之词。
诸位都知道,所有的回忆都必须略打折扣,今天回忆起汪精卫,肯定说他一看就是奸相,回忆起鲁迅肯定说早就知道他是好人,都是这样的。
回忆会有一些偏差,但大致能够说明问题,我挑了几个学生的回忆,看看他们怎么讲鲁迅的讲课。
我每回略带一点解释,告诉你为什么这么看。
曾经在鲁迅指导下写作的董秋芳,回忆他当年在北大英语系念书,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
中国小说史是国文系的课程,就是中文系的课程。
当时的情况是,1917年以后,北京大学实行选科制,必修课以外,可以随便选,所以国文系的课程,各个系都可以修。
这个英文系的学生董秋芳修了这门课以后说:
“(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意味深长地加入了很多幽默的讽刺的话,使听者忘记疲倦,这样我才能去看他,看他的神态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师。
”日后成为著名小说家的王鲁彦,当年只是在北大旁听,老北大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除了正规修课的学生之外,可以注册旁听,还有一种就是偷听,根本连注册都没有,只要有位置就坐下来。
到今天为止,北大还是这样,但是会影响到正科生的位置,因为真正修课的学生往往来得比较晚,偷听的、旁听的坐在前面,所以变成前面几排都不是自己的学生,后面才是,这是个很尴尬的状态。
现在我们努力在改变,但是我觉得这是北大的好传统。
他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可是日后满腔热情地追忆北大,而且说的都是好话,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对于北大的声誉来说,旁听生和偷听生日后的贡献以及他们的追忆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许钦文、王鲁彦都是这种。
王鲁彦不是北大的正式学生,他经常听鲁迅的课,回忆说:
“鲁迅讲话声音很平缓,没有抑扬顿挫,没有慷慨激昂,两只手拿着粉笔和讲义,从来没有表情来帮助他说话,脸上老是那么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的,不动声色地叙述着极为平常的中国小说史略。
极平常的语句,不赞誉也不褒贬,可是突然间教室里会爆发出一阵笑声,他会停下来,等你笑完了继续讲,还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这么讲下来能吸引人吗?
为什么能吸引人,下面我会跟大家说。
从内容而言,日后成为著名史学家的尚钺,当年进的是北大英文系,追随鲁迅学习写作。
他1939年就写文章回忆说:
“当年鲁迅课堂吸引无数的学生,我一下子连听鲁迅三年的课。
”诸位,鲁迅在北大就开一门课——中国小说史,没有开别的课,但是这门课一讲再讲,这个人说他修了3年,后面冯至说他修了4年。
这门课一年一年地讲,但每一年都不一样。
就像我刚才说的,好的教授讲课,是表演,每一年的舞台表演都不一样的。
所以鲁迅讲了3年,他听了3年,他记得小说史略之外还有一个《苦闷的象征》,那是什么意思?
其实那个记忆有一点差错,鲁迅没有讲过文学理论,鲁迅在北大的课堂上只有一门课就是中国小说史略,但是1923年、1924年《中国小说史略》的上卷、下卷出版了。
鲁迅怎么办?
当时鲁迅正在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就把《苦闷的象征》加到中国小说史里面来了。
所以讲的是中国小说史,中间包含人生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