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的思想体系Word文件下载.docx
《庄子哲学的思想体系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庄子哲学的思想体系Word文件下载.docx(2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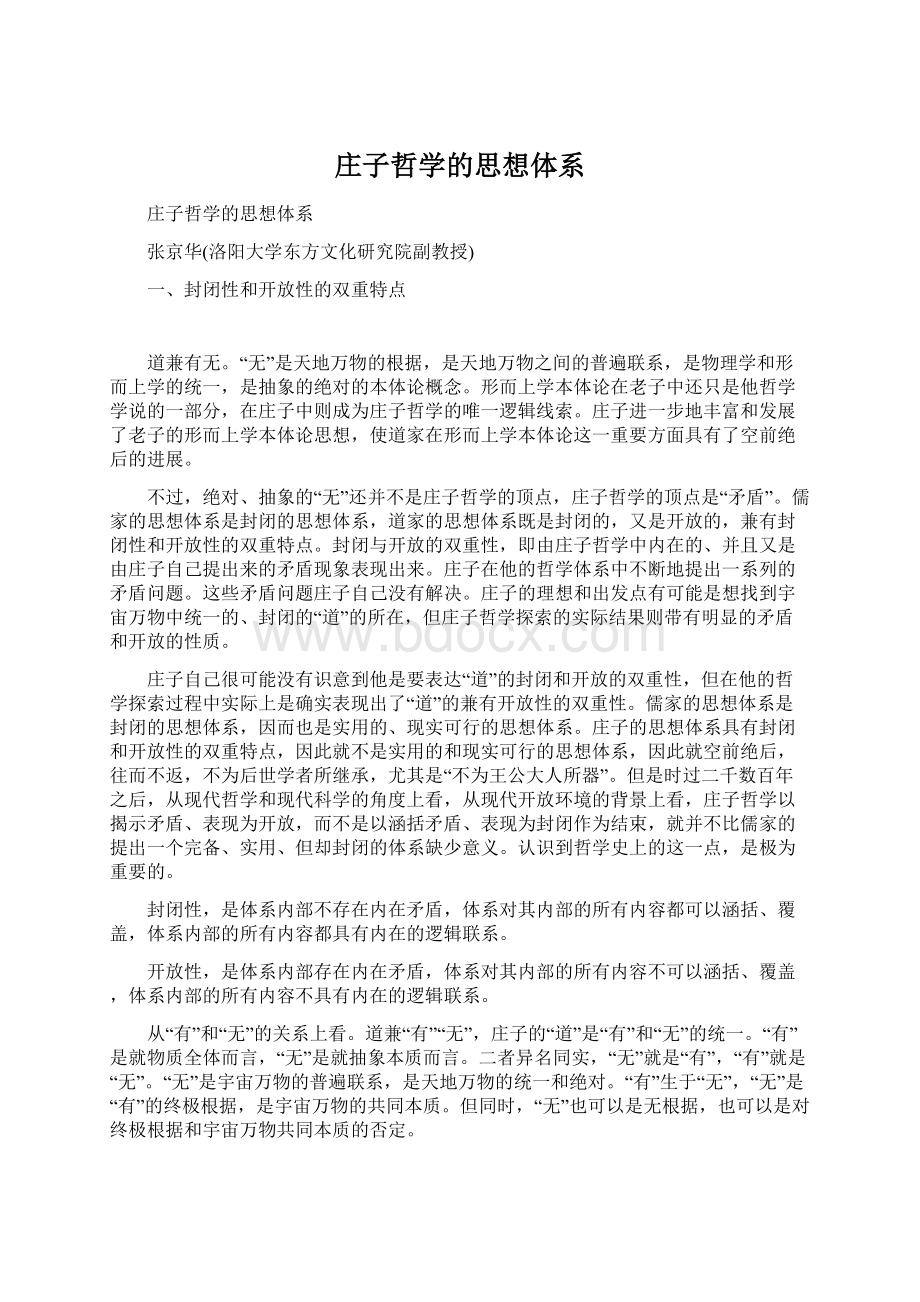
但是在“道”的认识和描述上,“道”非常道,非常名。
“道”不可闻,闻而非也。
“道”不可见,见而非也。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之为不知,不知乃知之。
所以,如果庄子知“道”,就应该抱一自守,对“道”不加论述;
如果庄子对“道”屡有论述,著书十余万言,申之无已,这个“道”就应该不是真实的“道”。
道家学说的最主要特点就是认为有“道”,以“道”为精,以“道”为本,叫作“主之以太一”(《庄子·
天下》)。
庄子继关尹、老聃之后十分认真地坚持了“道”的绝对性、一元性,力求建立道论的封闭体系。
但在庄子坚求乎“道”的过程中,却因为同时出现了“道”自身内部的矛盾现象,从而使道论导向了开放。
一方面“道”是统一的,不统一就不是“道”,“道”只能是统一的;
另一方面,“道”实际上并不统一,还存在着内在矛盾,包含着它所不能包含的因素。
既然“道”是统一的,也就不必要有人类对于“道”的追求探索;
既然“道”并不统一,也就不能先验地称之为“道”。
在学术界已经有很多人分析了庄子哲学中的矛盾现象,认为这是庄子哲学体系的缺陷。
比如周勃《论庄子的自由观与人生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一期。
)指出人生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在庄子思想中的深刻对立,刘笑敢《庄子人生哲学中的矛盾》(载《文史哲》1985年第二期。
)指出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在庄子人生哲学中的根本矛盾,等等。
但是这种对庄子哲学中矛盾现象的分析对于庄子哲学并不具有实际意义,所谓的指出矛盾也并没有涉及到庄子哲学的实质,因此也不能以此作为评判庄子哲学性质和衡量庄子哲学水平的标准。
庄子道论中的矛盾问题,是在庄子道论的阐述过程中内在出现的,而且是由庄子自己首先意识到和积极总结出来的。
恰恰是由庄子哲学中的矛盾问题,展现出了庄子哲学体系中封闭性和开放性的双重特点,而这也正是庄子哲学在思维水平上高于封闭体系的儒家哲学,发展了老子哲学,使道家一派无愧于儒家而与之并称,虽然有空前绝后的不幸,而又能够超越时代,超越古代,直接与现代哲学中的许多重要原则相吻合的关键所在。
在老子的道论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内在而根本的矛盾之处。
比如第一,老子认为“道”是绝对统一的,但同时老子又认为现实中存在着不合于“道”的事物,如“仁”、“义”、“礼”,如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道”,如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第二,认为“道”无名但又强为之名曰“大”,字之曰“道”,著书五千言以讲“道”。
不过和庄子相比,老子中的这些矛盾问题是隐微的,而且也与老子本质上有为的、作为政治理论一家之言的目的相同步,从而实际上也就本无所谓内在的矛盾与不矛盾。
庄子执着于道的统一,又困苦于道的开放。
《庄子·
天下》:
“天下大乱,道德不一。
悲夫!
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
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
”庄子沉痛百家的“往而不返”,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只往不来。
一得一失,一失一得。
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百家蔽于人而不知天。
知天而困于天,知人而困于人。
既封闭,又开放,这一双重特点自始至终遍在于庄子哲学的各部分,成为贯穿庄子哲学体系的、与道论的主线相对称的又一条重要线索。
在庄子哲学中由庄子自己所提出的矛盾问题分八组略述于下。
(一)
《齐物论》: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
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
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
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
木处则惴栗惧,猿猴然乎哉?
三者孰知正处?
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此一事物、彼一事物与他一事物各有自己的原则和本质。
每一事物都自以为是对的、正确的,但每一事物实际上都不一定是对的、正确的,因为各事物相互之间都不能互证。
而且,对于每一事物既然不能证明其是、其正确,也就同样不能证明其非、其不正确。
所以:
啮缺问乎王倪曰: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
“吾恶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然则物无知邪?
虽然,尝试言之。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
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
”
啮缺问:
“你知道事物都是正确的吗?
王倪说:
“我哪里知道。
“你知道你不知道吗?
“那么所有人都没有知吗?
不过,我试着问你:
你怎么能知道我所说的知道不是不知道?
你怎么能知道我所说的不知道不是知道?
(二)
同是感觉和认识的主体,在不同的环境下就会有不同的情况。
《徐无鬼》:
濡需者,豕虱是也。
择疏鬣自以为广宫大囿,奎蹄曲隈,乳间股脚,自以为安室利处。
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己与豕俱焦也。
囿于行迹者,就像猪身上的虱子。
猪身上的虱子选择了猪毛稀疏的地方,自己以为是宽广的宫殿苑囿。
选择了猪的两股之间,两胯之内,两排乳之间或脚弯之处,自己以为是平安有利的居室住处,却不知道杀猪的人有一天动起手来,布草点火,把自己和猪一起烧焦。
《达生》: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
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迕物而不折。
喝酒醉了的人从车上摔下来,车跑得很快人也不会摔死。
醉了的人骨骼与常人相同,但受到的损伤却与常人不同,这是因为醉了的人神智完全,乘了车也不自知,摔下来也不自知,面临死亡心中也不惊惧,所以本应受到损伤却不会有损伤。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
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
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
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我怎么知道热爱生活不是迷惑?
怎么知道怕死的人不是像人小时候从家里走散,长大了就不再想回家乡那样?
丽姬本是丽戎国艾地看守封疆的小官的女儿。
晋国带走她的时候,她哭得那么厉害,等到到了晋王的宫中,和晋王一起睡在大床上,吃的是肉食,就后悔开始的哭泣了。
我怎么知道已经死了的人不后悔他当初的祈求活下来?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
梦哭泣者,旦而田猎。
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
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
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
丘也与汝,皆梦也。
予谓汝梦,亦梦也。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
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
胡蝶之梦为周与?
梦中饮酒的人,醒了以后在哭泣。
梦中哭泣的人,醒了以后去畋猎。
梦之中又有梦,而且在梦中时并不自知是在做梦。
愚笨的人梦醒之后自以为知道是做了一个梦,但却不知他仍然是在一个大梦之中。
我和你都是梦,我告诉你我和你都是梦,也是一个梦。
庄周做梦,在梦中成为了一只蝴蝶,成为蝴蝶以后感觉身心都很便当,并没有什么不适,飞起来真是一只蝴蝶。
梦醒了,就又还是庄周,觉得作为庄周身心也很适应。
不知道庄周在梦中成为蝴蝶了呢?
还是蝴蝶在梦中成为了现在的庄周呢?
(三)
《骈拇》:
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
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
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
且夫骈于拇者,决之则泣。
枝于手者,齕之则啼。
二者或有余于数,或不足于数,其于忧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
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
野鸭的脖子短,如要接长它就会给野鸭带来忧患。
鹤的脖子长,如要截短它就会给鹤带来忧患。
天性本就长的不能截短,天性本就短的不能接长。
或长或短,天性如此,本没有忧患,截短了,接长了,反而会成为忧患。
想来仁义是不合于人的天性吧?
为什么讲求仁义的人都怀着那样多的忧患呢?
脚趾连在一起长的,把它分开就有痛苦。
手指多长出来的,把它咬断就有痛苦。
这两种情况一是比正常的五指有余,一是比正常的五趾不足,但它们都是天然的,要变动它们,无论是使之增加还是使之减少,都会产生痛苦。
人世间的仁人,焦急地忧患于人世,而不讲仁义的人,顺其天性寻求欢乐,谋取富贵。
想来仁义应该是不符合人的天性吧?
自从夏商周三代有了仁义以来,为什么天下这样乱?
庄子的疑问在于,天道应该是通达顺畅的,不论是比一般情况多出来一些,还是比一般情况少出来一些,只要是合于天性,就应该是快乐适意的,不会有痛苦忧患。
而讲求仁义的人自己总是怀着很深重的痛苦和忧患,那么仁义就应该是不合于天道了吧?
这里所说的仁义,可以代指一切人文创造和人道作为。
由此就产生出了天和人的矛盾。
(四)
《在宥》:
何谓道?
有天道,有人道。
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
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但天道与人道的分别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到底是真,还是假?
庄子是怀着疑问,两难回避的。
《大宗师》:
古之真人,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其一与天为徒。
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
道通为一。
其分也,成也。
其成也,毁也。
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之成。
果且有成与亏乎哉?
果且无成与亏乎哉?
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
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若是而可谓成乎?
虽我亦成也。
若是而不可谓成乎?
物与我无成也。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
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
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
古时候的“真人”,有作为是与天道同一,没有作为也是与天道同一。
与天道同一是与天道同一,与天道不同一也是与天道同一。
与天道同一是与天道相伴随,与天道不同一是与人世相伴随。
天道和人世是同一的,谁也不比谁多,谁也不比谁少,这叫作“真人”。
“道”是把所有的一切都包涵覆盖,通融为一。
事物有了独立的性质和自己的本位,事物之间有了区分,叫作“成”。
有了“成”同时也就有了“毁”。
对每一事物自己来说是“成”,对所有的事物共同本原的“道”来说是“毁”。
一切事物都无所谓“成”,无所谓“毁”,不论“成”或“毁”又都由“道”包涵覆盖,通达为一。
“道”本应是无所不包,无一例外的。
最初的“道”就是万物都包融在一起,没有是非的分别。
后来有了是非的分别,是非显出来了,“道”就亏损了。
“道”的亏损,就是个性的建立。
到底是有个性的建立和“道”的亏损呢,还是没有个性的建立和“道”的亏损呢?
有建立和亏损,所以昭文在鼓琴;
没有建立和亏损,所以昭文不在鼓琴,是这样吗?
如果这样就叫作个性的建立,随便你怎样也可以有所建立了。
如果这样不能叫作个性的建立,我和其他事物无论怎样也都不能有个性的建立。
天地与我包融为一,万物与我通达为一。
既然已经为一,还可以再有所表述吗?
既然已经说过“为一”的话了,还能够算作是没有表述吗?
为一是“一”,加上表述就成了“二”,已经有了“二”,再讲天地万物的同一,就又成了“三”。
这样加下去,最擅于算数的人也算不过来,何况一般的人?
从“无”到“有”已经是这样了,更何况从“有”到“有”呢?
(五)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
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
百骸、九窍、六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
汝皆说之乎?
其有私焉?
如是皆有为臣妾乎?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其递相为君臣乎?
其有真君存焉?
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
人谓之不死,奚益?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人之生也,固若是盲乎?
其我独盲,而人亦有不盲者乎?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
有之,愚者与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
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果有言邪?
其未尝有言邪?
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辨乎,其无辨乎?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
言恶乎隐而有是非?
道恶乎往而不存?
言恶乎存而不可?
没有“他”就不会产生我,没有我“他”也无从展现,相互间的关系是很近了,但却不知道“他”是谁。
好像是有“真宰”,但偏又不能看到他。
“他”有情可证,有信可验,但看不见他的形貌。
有情,却没有形。
人的身体有百骸、九窍、六脏,说它繁多,它又各有作用;
说它简单,它又十分完备。
恰当而完备。
我和谁有亲缘,以至于此?
是他泛爱万物?
还是他独有私情?
如果是独有私情,那么他是把人类都当作他的臣妾了吗?
如果是这些“臣妾”不足以自为,为什么在这些“臣妾”之中又分贵贱,为什么这些“臣妾”要轮换着做君臣呢?
还是应该有一个“真宰”吧?
但不论人类是依循了他,还是不依循他,都不会妨碍他。
而人却从一开始降生,有了形体,就念念不忘着一个信念,一直到死,一生都与物质利益相追随,做起来如同驾车奔驰一样,从来不知道停下来,这不可悲吗?
人的一生都是在被动地为谁去做,只知道做,却见不到任何成就,到人老时一身疲惫,仍然连死后归身何处都不知道,这不可哀吗?
即使人活着,没有死去,比死去了又有什么不同?
人死了,人的情感、意志、愿望也随之而去,身心俱灭,这不是最可悲哀的吗?
人生就是这样的盲目无意义吗?
是我一个人盲目,还是有谁不盲目呢?
如果按照人自己的意志去做,谁会没有自己的想法呢?
为什么还要在自己的意志之外寻找依据呢?
人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连愚笨的人也有自己的意志。
如果说人只是依循天道而没有自己的意志,但却各有是非,那就如同说“今天去越国昨天到”一样是错误的了,那就如同说本没有而又有。
没有而又有,就是有超常智慧的夏禹来了,也不能够弄懂,我又能够怎么办呢?
人类的语言和吹起的风不同。
风不论吹到哪里都是真实的,而语言是否真实确切却不一定。
说话的人倒是把话说出来了,但从实质上看他是说了呢,还是不曾说过什么呢?
说话的人认为他所说的话和小鸟的叫声不同,是有不同呢,还是并无不同?
道的真伪隐于何处?
言语的是非隐于何处?
道为什么总是离开而留不住?
言语为什么总是留下来而不真实?
这里的第一段,是庄子对天道也就是宇宙万物统一性的存在与否,提出疑问。
又《庄子·
大宗师》:
“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
子舆曰:
‘子桑殆病矣!
’裹饭而往食之。
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
‘父邪!
母邪!
天乎!
’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
子舆入,曰:
‘子之歌诗,何故若是?
’曰: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
父母岂欲吾贫哉?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
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
天运》:
“天其运乎?
地其处乎?
日月其争于所乎?
孰主张是?
孰维纲是?
孰居无事推而行是?
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
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
云者为雨乎?
雨者为云乎?
孰隆施是?
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
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
孰居无事而披拂是?
敢问何故?
子桑的歌哭和《天运》篇中的提问都不是针对着饥饿和云雨的具体原因,而是针对着人生和现实自然的最终原因。
子桑歌哭,为的是要知道造成现实的是父,是母?
是天,是人?
求之而不得,所以且歌且哭。
人既然有身心、才智、情趣,可以鼓琴而歌,得造物者之宠爱,为什么同时又遭逢苦难,有疾病和饥饿呢?
造成现实的如果是父母,父母生育子女,会是要他们遭受贫寒吗?
造成现实的如果是天道,天道公平无私,为什么还要使人蒙受苦难?
子桑所哭的不在于自己,而在于整个人类;
不在于一时的饥苦,而在于全部的生的原因、生的目的。
难道使人类逢此两难的,是不可能为人类所理解的“命”吗?
天是运转的吗?
地是静止的吗?
日月各自在争夺哪一处地方吗?
谁推动它们?
谁牵制它们?
是谁闲着没事来操纵它们,还是它们受机械的控制,一发而不能自止?
云是为了雨,还是雨是为了云?
谁造成了雨和云?
是谁无聊地促成了云雨?
风从北方吹来,又往西方和东方吹去,又盘旋而上?
是谁在那里呼吸鼓荡?
是谁闲着没事在那里煽动?
最终的原因和目的何在?
在这几处地方,庄子对“道”的存在与不存在,“道”的“德”(即不私)与不德,以及人的独立本性,人的宇宙位置,人的认识能力,提出疑问。
在第二段中,庄子指出了天道与人道的矛盾。
“若是而可谓成乎?
若是而不可谓成乎?
”或者万物都有“成”,或者万物都无“成”。
如果万物有成,人以人的成心作为依据,那么就不需要在人的成心之外再有一个天道,但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人人各师其成心,因而没有愚智之分,没有判别是非的标准,宇宙万物失去统一性。
如果万物无成,没有人的成心,人就应该以天道取代自己的独立本性,以天道为宇宙万物的共同归旨,但是实际上却又存在着人类各自不同的是非分歧。
认为宇宙万物有统一的“道”,如同以无有为有一样,面临矛盾。
在第三段中,庄子从认识的角度,提出天道与人道的矛盾,统一仍然难以判定。
道往而不存,言存而不可,人类的语言和知识是在本质上与道对立的,因而不能真实地认识道,对道的统一或不统一两难判别。
又《庄子·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
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
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虽然,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
所谓人之非天乎?
懂得天,就是到了知识的极限了。
但是懂得天的人一定是由天产生出来的人,只有“真人”才是这样的人。
懂得人的人,只懂得人而不懂得天,但他可以用他所懂得的来弥补他所不懂得的,用他对自己的知识弥补他对天的知识。
这样的人能够避免祸灾,终其天年,能做到这一步,也就是知识到了比较丰富的阶段了。
不过还是有缺陷。
因为知识是要表达事物的本质,而事物的本质如何还不确定。
有天道,有人道,我怎么知道所谓的天道不是照应在人身上?
我怎么知道所谓的人道不是代表了天道?
总之,在庄子看来,天道均平、公正、同一。
人道则是非淆乱,损不足以奉有余,人心险于山川,人情排下而进上,人事始作简而将毕巨,迂回、不平衡、不可逆反。
天道和人道的关系究竟怎样?
是同一,还是互相矛盾?
如果天道和人道是矛盾的,那么天道实际上就不是同一的,就是不存在的。
如果天道和人道合一,那么究竟是天道合在人道上,还是人道合在天道上?
如果天道合在人道上,那么人人师从自己的成心,不论愚笨、智慧,人人都有各自的一个“天道”,就成为无限多元和绝对意志自由,因而实际上就没有天道。
如果人道合在天道上,人道为什么实际上与天道不同,而人类对此又迷而不觉?
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上,都存在着一个天道与人道的矛盾对立。
(六)
庄子对于所谓人道与天道的不符有着十分深切的感触。
缮性》:
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
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
《天道》:
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此皆顺比于岁,不物于易者也。
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
《庚桑楚》:
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
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天下》:
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七)
在天道与人道的矛盾状态下,庄子哲学中因而就出现了这种何去何从、进退两难的情况。
《田子方》:
吾何以过人哉!
吾以其来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
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
我何以过人哉!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其在彼邪?
亡乎我;
在我邪?
亡乎彼。
方将踌躇,方将四顾,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
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
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
《人间世》: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
“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
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
吾甚之。
子常语诸梁也曰:
‘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
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
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
今吾朝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