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林每月点评微小说佳作5Word下载.docx
《李春林每月点评微小说佳作5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李春林每月点评微小说佳作5Word下载.docx(3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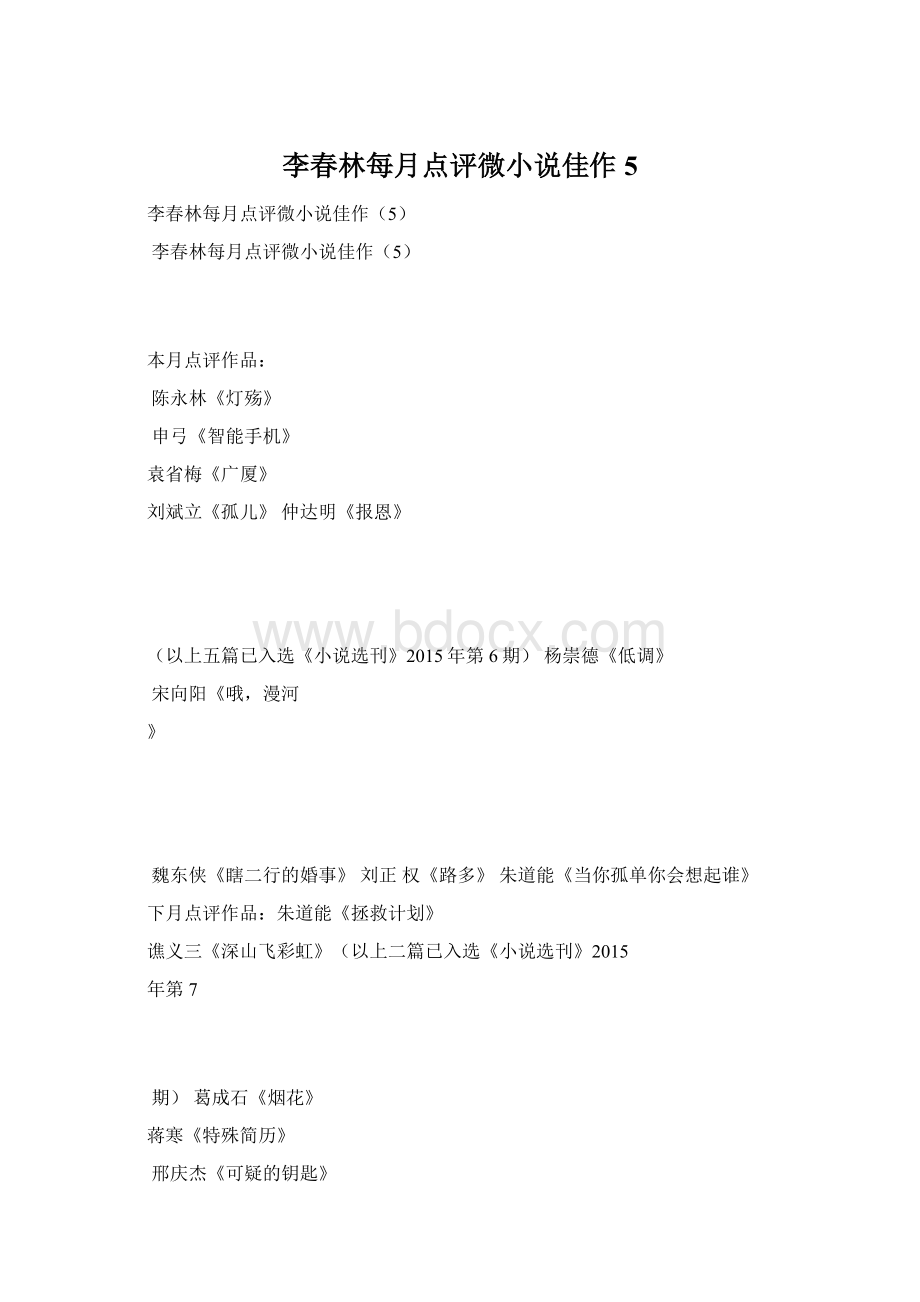
原来发了财的春生,用一百元钱一个灯笼收买了人心,使这传统灯笼变了味,失去了“口碑”的含金量,没有了价值,村长便把历年收存的灯笼一把火烧毁,把奶奶和小孩送的那盏电子明灯高挂村口,大道光明直行。
故事演绎的是真实的现实生活,诠释了奶奶们留下的优良传统,虽一时会被“钱迷了心窍”的爸妈一辈误失,而得益于有了路走的新一辈孩子终不会忘记开路的人。
村长为民敬业带来的优良传统,永是一盏不灭的红灯。
作品以灯和路造境,气息生动,抑扬顿挫,言近旨远,耐人寻味,值得一读。
小说内文:
这天晚上,六根对女人说:
“再过几天就中秋了。
你明天去买十斤月饼,三斤糖块,三十挂小鞭炮……烟我已买了。
”每年的中秋晚上,许多村里人都在六根家挂一盏灯笼。
鄱阳湖一带有这种风俗,一到中秋这晚,村里人便在德高望重的人门前挂盏灯笼,表达自己的敬意。
这几年,六根门前挂的灯笼最多。
村里人在哪家门前挂灯笼,哪家就得放鞭炮迎接。
大人敬烟,小孩散糖,女人吃月饼。
六根的女人有点不愿意:
“每年花一百多块钱换几十只灯笼,一点也不值。
那些灯笼既当不得衣服穿,又顶不得饭吃。
”六根沉了脸,骂:
“你懂个屁!
这灯笼拿多少钱也买不到的。
别人想自己门前多挂几个灯笼还想不到呢。
这是村里人对我的信任,对我工作的肯定。
”女人说:
“钱呢?
”六根问:
“家里一百多块钱也没有?
“儿子前几天上学,把家里的三千块钱全带走了。
”六根就翻口袋,口袋翻尽了,才翻出五十多块钱。
六根说:
“要不,你明天提一只母鸡去卖。
”女人小声嘟囔:
“哪有你这个当村长的!
别人当村长,家里要啥有啥,可你每年只得几十只灯笼。
”六根再懒得搭理女人了,想,如自己当村长不廉洁,那他门前每年咋挂几十只灯笼?
六根把这看得很重,每年村里人挂的灯笼,他都没扔,都堆放在一间房里。
中秋节这天,六根早早吃过了晚饭。
女人买来的糖块、月饼也摆放在桌上。
鞭炮拆了封。
只等提灯笼的人一来,就放鞭炮。
月饼样的圆月好不容易从鄱阳湖里爬起来了,一些小孩已在月光下疯闹了。
六根坐在门前悠然地吸着烟,眼光却不时往路边上掠。
终于来了一个红红的灯笼,六根兴奋地站起来,喊女人:
“快拿鞭炮放,灯笼来了。
”鞭炮劈里啪啦地响了。
可是灯笼并没进他家,而是进了春生的家。
六根气得骂女人:
“谁叫你这么早放鞭炮?
”女人不敢辩,反而安慰六根:
“急啥?
等会儿,灯笼不就都来了?
”六根的气才消了一些。
又来了一只灯笼。
拎灯笼的是谷子。
六根喊:
“谷子,这么早来了?
”可是谷子没听见样径直往前走。
片刻春生家响起欢欢悦悦的鞭炮声。
六根惊得傻傻地立在那。
往年,谷子每回给他送灯笼。
今年却把灯笼送给了那个发了横财的春生。
六根气得大骂:
“这世道变了。
人都被金钱蒙住了眼。
”六根的女儿劝道:
“爹犯得着生气吗?
春生早在村里传出话,谁送他一盏灯笼,他就给谁一百块钱。
”六根还是生气:
“春生是啥货色?
他怎么配村里人送灯笼?
他的钱不是靠坑蒙拐骗来的吗?
”六根说的是实话,春生先是在城里办了个皮包公司,骗了一些单位的货款却不给货,只给单位的头送些钱。
春生有了钱,就在村里办了个罐头厂,钱大把大把地进。
可交税时却说厂子亏损。
春生办了厂后,村里人都想进他的厂,村里人给春生的笑容越来越多,看春生的目光越来越谄媚了。
“唉——”六根就长长地叹气。
六根掏出枝烟,点了,狠狠地吸。
烟雾整个裹住了六根满是阴云的脸。
春生家的鞭炮劈里啪啦地响个不停,春生门前已挂了二十几个红灯笼了。
可六根门前还一只灯笼都没挂。
六根感到极难过。
自己当了十几年村长,爱村,敬业,没为自己多捞一根柴火,没做一件昧良心的事。
可在村里人眼里竟不如一个损人利己赚到了钱的春生。
一只只大红灯笼从六根眼前飘走了,进了春生的家。
女人把六根拉进屋:
“犯得着生气吗?
别气坏了身体。
”女人关紧门,可劈里啪啦的鞭炮声仍是那么刺耳。
女人就开了电视机,有多大声开多大的声。
女儿说:
“爹,村里人送的灯笼已没点价值。
我们给自己家挂个灯笼吧。
”六根骂:
“别丢人现眼。
”
此时,门被拍得砰砰响。
六根开了门,一个小孩举着一盏灯,灯后跟着十几个活蹦乱跳的小学生。
小孩齐声说:
“村长,我们给您送灯来了。
”六根的眼睛竟湿了。
六根忙放鞭炮,又不住地给小孩散糖。
一小孩说:
“六根叔你别生气。
奶奶告诉我们,爸妈被钱迷了心窍,心都被狗吃了,他们分不清好坏,为得一百块钱给春生送灯笼。
春生用钱买通大家送灯笼,这灯笼没啥好看的。
今日我们送您一盏电子照路明灯,奶奶说这灯很进步,亮多了,又安全,您开山修了路,让我们上学有路走……”六根听到这里,接下灯,眼一涩,脸上竟有两条小虫子爬。
六根把三十挂小鞭炮全放了。
六根又喊女人与女儿:
“你们把房里的旧灯笼全拿来。
”几百只灯笼很快堆了一地。
六根拿出打火机,点了火。
片刻,灯笼全着火了。
一小孩问:
“六根叔,你咋烧灯笼?
”六根说:
“这些旧灯笼也没啥好看的了,没有什么用途,烧了。
”片刻,几百只灯笼就化为一堆过眼的火红。
六根把那盏电子照路明灯挂在村口。
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夜来灯亮,大道直行,风吹雨淋,不失光明。
作者简介:
陈永林,1970年代生于江西都昌,中学毕业后拉过人力车、烧过锅炉、开过出租车、当过兵。
现为《微型小说选刊》主编。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江西省作协理事、滕王阁文学院合同制专业作家。
已出版《我要是个女人多好》《上学的路有多远》等20余部小说集。
智能手机
申弓
《小说界》2015年4月增刊号
入选《小说选刊》2015年第6期
作品以质朴而睿智的语言,写了一个生活小故事,一对恩爱夫妻,因了感情交流的载体越来越科技化,两心相悦的情感则越来越产生猜忌、误会和疏离。
且不写没有电话时,书信恋爱的字字爱、句句情,都由心生;
有了电话后,妻子只记丈夫的电话“就记住了全世界的了”;
黑白手机时代,兼用本子记电话号码,号码便是爱人的记忆;
智能手机一用,便不用脑子记电话了,代表爱人的号码也忘记了,“将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夫妻感情由此不断惹祸。
作品引发人们思考因科技进步而带来与传统文化相悖的种种社会现象,诸如依赖电脑,人脑健忘;
电脑换笔,传统书法后退;
甚至有了机器人的服务,还会失去老人临终的亲情抚慰。
传统情感文化应如何同科技进步,与时俱进呢?
作品最后一老清华高才生的发言——“厚德载物”,言简意赅,清晰明朗,形象地将答案摆在读者面前,令人深思。
作品的艺术情趣和理性思维融合一起,以小见大地记录了新时期科技进步与人文活动发展的轨迹。
值得一读。
老婆说,全世界的电话,她就只记住一个,那就是我的。
比如有一次,她在被小人困扰时,就拨了我的电话,五分钟后我就来到了身旁,为她解了困。
再比如一次,她在出差的旅途中,匆匆忙忙给我打回了电话,说找不到联系人的电话了。
不到一分钟,她便收到了我提供的电话号码。
老婆是聪明的,记住了我的电话,就等于记住了全世界的了。
那时的手机还是黑白时代,大家都在使用手机的同时,外加一个小本本,记录着朋友的或常用的电话。
每次拨出都要念上一串的数字,打得多了,自然也就能记住了。
记得有一次朋友聚会,我们还搞了一个活动,那就是比赛谁记的电话多。
冠军的奖品是一只钦州泥兴工艺品高鼓花樽。
我一口气报出了100个,力拔头筹,在众目众目睽睽之下捧走了奖品。
后来,手机换代了。
我将所有朋友的电话都输入了手机的电话本上,这样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再也不用为中间是三个7或者四个7而苦恼,也不再为11位或10位数字而绞尽脑汁,什么时候要打谁的电话,只需在键盘上按上一个姓氏,那电话就能准确无误地拨出去。
是谁的电话打进来,一看也就一目了然,再也用不着问:
请问你是哪位了。
一天,老婆的手机欠了费,打不出去了,让我帮她充100元的话费。
我一口答应了,不就是100元吗?
一会便可以马到功成。
不想来到收费处,却想不起她的号码来。
偏偏来得急,忘了带手机,便只好又跑了回来。
老婆一见我,就责备说,怎么舍不得100元?
我说没有的事,我跟你,谁是谁啊。
是忘了号码了。
什么?
你将我的电话号码给忘了?
我说是的,到了交费处,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你到底怎么了?
竟然连我的号码都忘了!
我可一辈子都没有忘记你的啊。
是啊,你听我解释,自从用上了这智能手机……
你不用解释,算我白痴了,我全世界的电话就只记住你的,而你却将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不是将你忘,是忘了电话……号码也没丢,还存在电脑、手机里……
那不是一样?
我的号码就是我,那是我的代号,你竟然给忘了,说明我在你的心中已经没有位置了,我的位置只存在你的电脑、手机里……
你跟电话是两个概念,老婆你言重了……
一点都不重,算我白痴了。
由是,老婆整天眼皮耷着,脸色阴着,一天比一天忧郁起来,还跟我打起了冷战,家里失去了原有的融和,变得像冰窖,更严重的是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吃饭不同一个桌,睡觉背对着背。
我明白,都是手机惹的祸。
相当初书信热恋,白纸黑字,书法艺术,字字爱,句句情,力透纸背,心心相印……
进而我的行动也开始受到了监视,比如说我的电话响了,她就要走到最近的地方听着我的对话;
我的短信来了,她也要用冷冷的眼光来扫描。
每当我外出,后边总有个影子不即不离地跟着。
特别是有作者来访,要是男的,她就不管,要是女的,无论是年长年幼,高矮胖瘦,黑白俊丑,她都要左右不离前后的一直陪着。
我十分明白,那是手机惹的祸。
我也十分清楚,任何解释都多余的。
不过,这种瓜田李下的生活,也真让人厌烦。
这天,我看见她在满世界找手机。
当我打开洗衣机,却发现给洗坏了。
原来丢魂走魄的她,竟然在洗衣时,连手机也忘了掏出来。
我想,也好,这手机用了好几年了,也该换换了。
便请缨去帮她选购了一个3G智能的。
回来教会她发短信、上网、上Q、上微博、照相、玩游戏等,还帮她建立了电话簿,将一批常用的电话号码都输了进去,还特别建立了一个快拨电话,将联系最密切的电话输入,我的自然排在第一,需要给我打电话,就只拨一下快捷键就可以了。
老婆学会了这些,还乐滋滋地使用起来。
对我的态度好像也慢慢改善了。
不到半个月,她便用得得心应手了。
我心里想,别看这个老婆,平时工作忙碌,容易丢三忘四的,可在使用智能手机上,一点也不落后,有时甚至还超越我这个师傅呢,比如没过几天,她居然会使用了微信,我至今还不会用呢。
大约过了半年,中秋节的晚上,儿子和女儿早早地将一个圆桌摆到了离月亮最近的天台上,还请来了老外婆,一家子在一起吃月饼赏月。
突然想到要做一个游戏,外婆将大家的手机收起暂为保管着,然后比赛看谁能说出所有家里人和亲戚的电话号码。
奖品是我手指上的金戒子。
结果,我们四个拥有手机的,谁也说不出来。
还是外婆厉害,等到我们都停了下来,她竟然一个不拉地报出了在座所有人和不在座的所有亲戚的电话号码,外婆得到了最高奖赏,由我亲手将那金灿灿的戒子戴到了她的手指上。
老婆在沉思,又望着我,怎么了?
老婆说:
“老公,对不起了,以前错怪你了。
老外婆接着发表得奖感言:
“是的,你们是错了。
有了电脑工作,可不要忘了脑力劳动;
有了智能手机,可不要丢了善良心机;
有了机器人的服务,可不要‘久病床前无孝子’;
科学发展,自强不息,世道人心,还是厚德载物,金光闪闪……”
老外婆一顿一挫的发言令我们全家激动得拥抱在一起,清风满月,光明无际,老外婆不愧是老清华的高才生,使我们高山仰止。
申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广西人,1986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1971年参加工作,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十多部小说集。
孤儿
刘斌立
《文艺报》2015年4月3日
作品写的是资源枯竭的矿山,“因为矿场倒了,几万员工和十几万的家属顿时都没有了生计。
而这个大山里的小城市,哪里能承载得了这个负担呢?
”四位矿山员工只好离别妻儿奔赴有17个小时车程的省城打工,以寻求生计。
小说只写了清早4点钟四人告别家人赶上长途汽车,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开始播音,这短时间发生的故事,通过情景细节描写、回忆、倒叙,最后诗一般地营造了一个意境:
“清晨,那些星罗棋布的灯火,只是那个城市里还没有断息的活力。
只是离世界越远,就越像一个孤儿,即将被永远地遗忘在大山里了。
”作品艺术而真实地反映了下岗职工的生活疾苦,像失去了母亲般的“孤儿”,旨在引发应对“资源枯竭”的经济决策者的关注,颇具现实意义。
秦浩又查看了一下打包的行李,确定无误了才去厨房。
他妻子4点就起来煮了红薯粥,他看了看那半锅粥,舀了一碗,又倒进锅里一小半。
妻子并没有注意到,但仍旧习惯性地提醒他“早饭要吃饱”。
秦浩进星子只看了一眼孩子,没敢亲她:
小家伙睡的浅,弄醒了,知道爸爸要走,必然哭天喊地。
一个大背包上了肩,手里还有一个大尼龙面子灰突突的行李包,秦浩看着妻子,没有再说话,只是下巴抬了抬。
妻子知道其中的含义“我走了,家里靠你了!
这只是秦浩每年里都要经历的分离,可能大家都已习惯了。
走下楼,秦浩就看见路灯底下已经有两个同伴在那儿抽烟等他了。
他们手里都有一个大大的尼龙面子的行李包,在路灯下,包上“锡山矿务局”的印字特别显眼。
那几个字也印人了秦浩的眼睛,他手里也有一个。
“锡山矿务局”那几个字在他心里狠狠地戳了一下。
曾经锡山矿每局是这个域市最好的单位,不管是工资、福利,甚至是秦浩背后的那片家属楼,都曾经是这个城市最让人羡慕的。
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城市就是因为有了锡山矿务局,才建设起来。
他们手里这个大行李包,就是某年单位组织外出考察学习时,每个员工发的福利品。
而如今,秦浩还得用这个包装起自己的衣衫琐碎,颇为讽刺的是,现在他们都是离开矿务局家属区,而出去打工的。
三个人相互看了看,点了点头,一起朝矿区大门而去。
黑黢黢的矿区内,似乎空无一人。
路灯已没几盏好的。
三个人抽着烟,倒是烟头一亮一亮的,显出了几分活力。
大门口的铁门虚关着,他们发现耶儿还站看一个人。
“广路,你怎么叉来了?
”秦浩先发问的。
卫广路把烟头掐了,狠狠用脚踩着,边碾脚边说:
“我把娃娃交给我妹妹了,这儿不可能找得到工作,我必须出去打工。
“你走了,你蛙儿不是成孤儿了,要不得哦。
”另一个声音说。
秦浩赶紧用手止住那人,但是昏暗的灯光中,已看见广路眼神瞬间黯然了。
“算了算了,走,挣到钱再打算。
”一只胳膊拉起广路。
秦浩看了一眼大伙儿,边走边说:
“也好,又是我们四个一起,互相有个照顾。
卫路广和秦浩他们一起在外面打工两年了,可是在家的妻子一直到肝部疼痛到无法忍受才去医院,确诊是肝癌晚期,广路赶回家不到三天,妻子就去世了。
这个矿区里,很多职工
都死于这个疾病。
大家其实都知道,有些工种因为当年缺少劳动保护,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侵害。
本来有一年大家还准备上访争取一些基本权利,但是就在那年,矿区停产了,接着被宣布为资源枯竭。
秦浩他们坐上了早班长途车,他们接下来的两天都会在路上。
长途车要走4个小时,把他们带到省城,他们要换火车北上17个小时,到达北方的一个省会城币。
秦浩是第一批走出去的锡山矿务局的工人,他当年是负责矿区锅炉班的班长,锅炉班负责整个矿区的热水供应,三班倒24小时从不停歇。
当年矿场停业,秦浩整整一年都无法在这个城市找到工作,因为矿场倒了,几万员工和十几万的家属顿时都没有了生计。
秦浩北上之路,经历了三个城市,最终找到了现在的工作,为一个小区的供暖站负责整个冬季烧锅炉。
他站稳脚跟后,陆续把自己锅炉班的一帮弟兄都介绍了过来。
工作从每年的深秋囤煤开始干起,到次年春天的3月停止。
每个冬天,秦浩能挣到一份相当辛苦但至少能让家人温饱一年的收入。
而家乡那个城市对他来说,就是永远十分想念,但却没有希望的地方。
长途车上,司机开了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已经开始播音了。
第一个让秦浩他们打开话匣子的话题是,播音员说为了响应中央关于节能的号召,今年北方城普遍延后了开始供暖的时间,同时供暖的温度会下降。
节能意味着烧炉工工作量减小,虽然只是延后三天,但是秦浩他们似乎已经感觉到今年能拿到手的收入一定会减少了。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但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明年春天烧炉的工作一结束,必须得留在当地再找找工作,争取多挣点钱再回家。
秦浩没有参与讨论,因为他又听到另外一则新闻。
播音员正念着一串城市的名字,那是国家公布的第二批“资源枯竭性城市”名单。
秦浩听到了熟悉的那个名字。
长途汽车已经盘山走了一段,秦浩回过身去,从车窗回望着已经在大山深处的城市。
清晨,那些星罗棋布的灯火,只是那个城市里还没有断息的活力。
只是离世界越远,就越像
一个孤儿,即将被永远地遗忘在大山里了。
刘斌立,1978年出生于重庆,现居北京。
发表《多伦多的外科医生》、《老人与马》、《相亲》、《夜袭》等诸多优秀微型小说作品,入选国内外微型小说选本。
出版有《那一刻的仲夏》、《忐忑》、《时光交汇的地方》等微型小说专集。
广厦
袁省梅
《小说界》2015年4月第2期
作品写进城建房农民工大高的妻子秀来探望,住不进旅社宾馆,只好住在工地未竣工的楼体内。
故事写得真实细腻,情景交融,情节虽少,却释放出诸多耐人思考的信息:
主人公“转眼想自己建了那么多的楼房,竟然没有一间房子让秀住,就有些落寞”,这是“泥瓦匠,住草房”的现实写照;
“秀说,跟你在一起,住哪儿都是最好的”,这是农民工爱情的真挚体现;
住工地楼时几个水泥袋子,铺在草席子下,大高说,“这就是咱的五星级。
秀说,这就是咱的席梦思。
大高说,跟宾馆差个啥?
……眼睛却湿了”,这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意境。
小说刻画的是深化改革的劳动者形象,一座座“广厦”是他们双手创造的改革成果,他们只知向“广厦”奉献,不知向“广厦”索取。
他们“席梦思”上的中国梦是乐观,艰苦,敬业,友善,其价值可歌可泣。
秀找到大高的工地宿舍时,天已快黑了。
大高刚从工地上回来,见到秀,先是惊喜,然后,就责怪秀不提前说一声,也没个准备。
嘴里一个劲地怪着,眼里的笑呢,却藏不住,采蜜的蝴蝶般,在秀的脸上绕。
小别胜新婚,何况,他们还是新婚。
结婚一个月,秀就去了县城的商场打工,大高呢,也跟着工程队走了。
算算,他们已经分别八个月零六天了。
怎么会不高兴呢?
秀抿着嘴笑,乜他一眼,没说话,从包里给工友们掏红枣,掏炒豆子和花生,叫大家吃,说都是自家地里的,豆子也是自己炒的。
说笑了一阵,队长说不早了,叫大高领着秀去城里住去。
大家也都叫大高得让秀住宾馆,五星级,最高级的,说媳妇好不容易来一趟。
大高看秀一眼,嘿嘿笑,说那是肯定了。
大高和秀从工地出来,走了好长一截了,宿舍那团亮的灯光渐渐地远了,工友们的说笑声也渐渐地听不分明了,大高不走了。
他前后看看没人,一下搂住秀。
他们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街,渐渐地,走进了城区。
他们的手紧紧地牵着,没有松开一下,好像是手一松开,对方就跑了。
秀说,真去住宾馆?
大高说,当然。
秀说,那找个便宜的。
大高不依,说,要住就住最好的,不能让你受屈。
秀说,跟你在一起,住哪儿都是最好的,住哪儿我都高兴。
大高的心潮一下就荡漾开来,春风拂面,又柔软,又温暖,是美好了。
他轻轻地把秀的一双手都抓握在自己的手心里,是想说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只一下一下地摩挲着秀的手。
大高没想到看得上的宾馆,一晚上就要好几百,终于选定了一家,要登记时,却发现没有带身份证。
身份证前几天叫队长拿去办银行卡了。
大高叫秀拿她的身份证登记,秀在包里找了半天,竟也忘带了。
他们,只好又走到了大街上。
正是吃晚饭的时间,附近小区的高楼低楼都亮起了灯。
灯光璀璨,富丽堂皇。
一盏灯就是一个家。
大高看着楼房上亮的窗户,繁星般看得眼花,告诉秀说这个小区也是他们建的。
走到一个小区边,又说,这个小区也是他们建的。
转眼想自己建了那么多的楼房,竟然没有一间房子让秀住,就有些落寞,也伤感,把秀的手捏了又捏。
秀呵呵笑,说没啥的,有啥呢?
不住省钱,咱也正好看看城里的夜景。
大高问秀在大街上走一晚上?
秀说,走一晚上就走一晚上。
大高突然想起了他们工地的楼房,那里,有好几十栋的高楼,楼体已建成,只差外包装和内粉刷了。
大高说,要不,咱回工地?
秀说,好。
他们,又回到了工地。
宿舍已没了灯光,唯有门房前的灯静静地亮着。
月亮挂在半空,是个满月,硕大,明亮,把工地照得亮亮的。
大高牵着秀的手,叫秀轻点,不要吵醒了门房老刘的狗。
秀听说有狗,心里一紧,就把大高的手抓得更紧了。
通过门房时,那条黄狗倏地从暗处跳了出来,对着他们“汪”地咬叫了一声。
大高忙说,老黄是我,不要乱咬好好睡你的。
叫老黄的狗看了一眼大高,“咻咻”地低声哼了哼,又钻到黑里去了。
大高带着秀走进一栋高楼,说是那几天下雨,宿舍里漏雨,他们好多人就扯了凉席,睡到这楼里。
大高说,这栋楼的上水下水都齐了,电线也到位了,接个灯泡,屋里就亮了。
他们在里面玩牌洗衣服,老赵还把他买的电视机抱来,把天线扯来,看电视。
秀说,你的生活倒好,有滋有味。
大高说,没你,哪好?
秀乐了,悄悄地掐他一把。
大高问秀想住几楼。
大高说,你想住几楼就住几楼,今晚,这栋楼都是你的。
大高说这话时,好像他是这栋楼的主人,也豪迈,也气派。
秀看一眼晦明里的大高,笑得咯咯的,说,当然要住最高楼。
大高说,好咧。
说着,就背起了秀。
六层楼,大高一直把秀背了上去。
这是一个大房子。
房里并不昏暗,皎洁的月光透过洞开的窗户,给地上照下一块一块水样的亮。
地上的沙子水泥灰点砖头,都看得清楚。
大高领着秀看了客厅,看了卧室厨房卫生间。
有个房间里,竟然铺着一领草席子。
大高说,肯定是谁睡了没带走。
秀说,是给咱准备的。
大高说,就是。
秀咯咯笑着,拉着大高挨个房间看,刚说睡在最小的房间,转眼,又说还是大房间好。
大高说,要住就住最好的。
秀乐了,大高也乐了。
他们捡了个水泥袋子,清扫了地面,又在楼下的房间找来几个水泥袋子,铺在草席子下。
大高拍拍草席子,说,这就是咱的五星级。
秀说,就是呢,还不用掏钱。
大高说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