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视野中的《平凡的世界》Word下载.docx
《当代文学史视野中的《平凡的世界》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当代文学史视野中的《平凡的世界》Word下载.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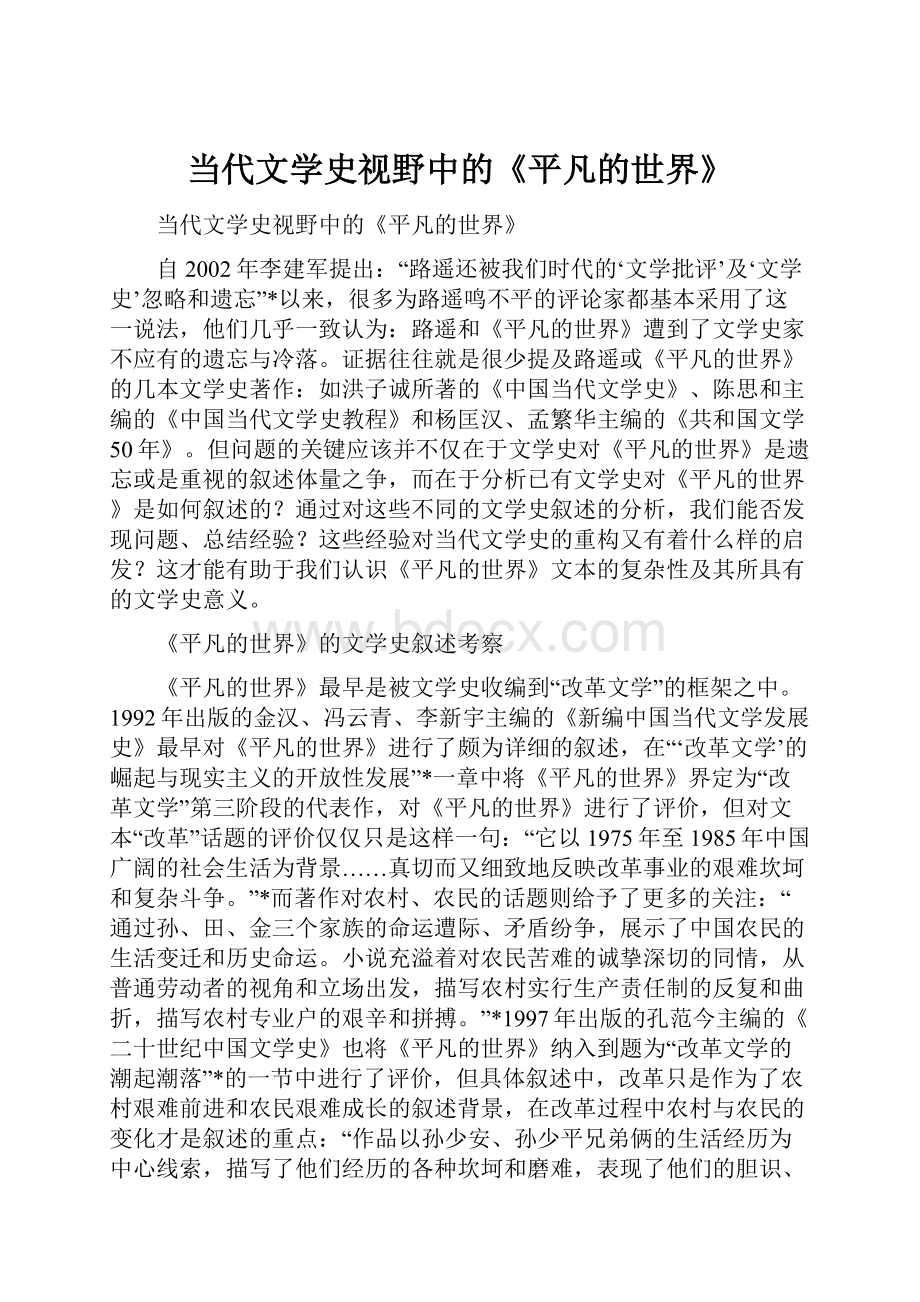
“通过孙、田、金三个家族的命运遭际、矛盾纷争,展示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变迁和历史命运。
小说充溢着对农民苦难的诚挚深切的同情,从普通劳动者的视角和立场出发,描写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反复和曲折,描写农村专业户的艰辛和拼搏。
”*1997年出版的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将《平凡的世界》纳入到题为“改革文学的潮起潮落”*的一节中进行了评价,但具体叙述中,改革只是作为了农村艰难前进和农民艰难成长的叙述背景,在改革过程中农村与农民的变化才是叙述的重点:
“作品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的生活经历为中心线索,描写了他们经历的各种坎坷和磨难,表现了他们的胆识、魄力、理想和奋斗精神,从而表现了古老黄土地的子孙们在农村改革的新形势下逐渐觉醒和与传统观念决裂的过程,奏出了一曲积极奋进的人生凯歌。
”“小说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组成了一幅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西部农村艰难奋进的生活画图。
”*1998年出版的於可训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将《平凡的世界》定位于“以反映现实变革为艺术取向的长篇代表作”,*并将其置于“改革文学”的谱系之中。
而著作中对《平凡的世界》的评价更多地则是侧重于农村和农民的话题:
“反映了变革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和中国农民命运变化的历史趋势。
”“《平凡的世界》更多地是从积极的建设性的方面去描写在新一代的中国农民身上正在生长着的新的精神品质和传统的美德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创造性转化。
”*2000年出版的郑万鹏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世界文学视野中》也将《平凡的世界》划入到“改革文学”的框架下给予了评价:
“描写了从大队到公社、县、地区、省会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作和政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于‘改革’的态度……讴歌了神州大地上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
”*但显然作者的侧重点并不在“改革”话题上,而是在农村和农民的话题上:
“而路遥所关心的还是农民——平凡的人,平凡的世界。
他的全景法的意义在于表现这场自上而下掀起的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反响、变动。
”更有意思的是,作者此外又将发表于1999年的一篇论文略加修改后用《平凡的世界——中国农民二次翻身的史诗》为题,以整章的篇幅呈现在该著作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小说中农村、农民书写的推崇。
此外,在“改革文学”的框架下叙述《平凡的世界》的文学史著作还有2003年出版的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2004年出版的李赣、熊家良、蒋淑娴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但在具体的叙述中,“改革”字样已经很少出现了。
总体而言,将《平凡的世界》划入“改革文学”的框架中是很多文学史叙述所选择的路径,但根据上述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关于《平凡的世界》的文学史叙述是在“改革文学”的框架下展开,但“改革”话题往往只是作为了叙述的背景,而改革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所产生的影响才是文学史叙述的重点,也被文学史家们认为是文本中最精彩的部分。
从文本而论,《平凡的世界》如作家所说为读者提供了三条人物运动的河流,分别是“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
*以孙少安为中心的主流线主要呈现了社会变革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冲击,属于农村题材的小说;
以孙少平为中心的主流线主要讲述了孙少平追求人的尊严与生活的意义的个人奋斗史,属于个人成长小说;
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主流线主要聚焦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所遭遇的阻力,属于改革题材小说。
*但三个层面的文本归结起来最恰当的表述应该是一个描写改革背景下农村急速变动,农村新人快速成长的农村题材小说。
无论是从文学史家的主观意愿还是文本本身的意蕴来说,将其归入到“农村题材小说”的文学史叙述框架下应该是最为贴切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现象,一方面是文学史家积极认同《平凡的世界》对农村与农民生活的深刻描绘,却努力想要把它纳入到主流文学史概念“改革文学”的叙述框架之下;
另一方面是主流文学史叙述中的“改革文学”这一框架又不能有效阐释《平凡的世界》中农村题材所折射出的丰富意蕴。
既然如此,文学史家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文学史叙述策略呢?
从作为“改革文学”的“有名无实”到“无名”状态
对于文学史研究者来说,“如果想整体性地把握一个作家,仍然需要把他从精神个体重新还原到历史之中,以目录学的眼光,判定他是哪个年代、哪种文学思潮、流派和类型中的作家”,“不这样把作家作品的活动重新历史化,置于目录学的视野中,他的工作就很难称得上是理性的、客观的和超越性的,称得上是一种文学史的研究”。
*
那么,《平凡的世界》能够被冠以何种名目呢?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平凡的世界》冠以“农村题材小说”的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对《平凡的世界》进行这种命名处理的文学史有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但该书并没有对文本展开论述,仅在“农村题材小说”一节中提及书名。
“农村题材小说”作为描述“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文学史概念之一,它的合法性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述中遭遇到了危机,随着纯文学观念的深入人心,它“被贴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标签”,“‘农村题材小说’由一个文学素材的中性词汇演化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充满贬义的文学史概念”。
*在这样的语境下,沿用“农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来界定《平凡的世界》显然不算明智吧。
与此同时,包含了农业改革题材和工业改革题材的“改革文学”成为了新时期初期的一种重要文学思潮,“改革文学”这一概念则在新时期的文学语境中表现出积极、奋进的意味,成为一个富有褒义色彩的文学史概念。
文学史家们欣赏《平凡的世界》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和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努力将其纳入到主流文学史的叙述中,但在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又找不到合适的文学史概念对其进行界定,只能以充当其时代背景的“改革题材”作为判断依据,将其划入到“改革文学”的框架下,这样就难免出现了文学史叙述框架与具体叙述内容出现名不副实的尴尬状态,《平凡的世界》在这些文学史的叙述中被置于“有名无实”的境地,徒有“改革文学”之名。
而它能空享“改革文学”之名还得益于文学史家们在界定“改革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时,对其进行了拓展与延伸。
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在谈到“改革文学”时写道:
有人称改革文学为“改革者文学”,意在强调塑造改革家、开拓者的人物形象;
有人称改革文学为“改革题材文学”,意在强调反映改革和改革进程中的矛盾斗争。
实际上改革文学的定义还应该再宽泛一些:
凡反映我国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命运的变化的文学作品,都应属改革文学。
此外,该著作还将“改革文学”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979年夏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脱颖而出,“改革文学”开始了它的发轫期;
1981年底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问世,“改革文学”进入了第二阶段;
1985年以后,“改革文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进入到了第三阶段,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被视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作,而对“改革文学”的时间下限没有作明确说明。
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将“改革文学”分为了三个阶段,不过其对每一阶段具体时间界限的划分与《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稍有差异,但同样对“改革文学”的下限没有作明确说明。
於可训在《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中没有从时间的角度对“改革文学”进行划分,而是将“改革小说”的中短篇创作分为“直接反映改革和间接反映改革”两种类型,*而将“改革小说”的长篇创作分为“以思想的新锐著称”“以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精神世界的揭示见长”“以厚重的历史感和深邃的文化意蕴取胜”*三个层面。
总之,在这些文学史中,虽然《平凡的世界》的文本内涵与“改革文学”这一概念框架并不是十分吻合,但尚能纳入到这一叙述框架之中。
但在部分文学史叙述将“改革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缩减化的表述之后,《平凡的世界》在这些文学史中,连“改革文学”的“空名”都被抹掉了,陷入到了尴尬的“无名”状态。
1999年出版的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改革文学”的叙述,仅在“80年代初期的小说”这一章中用了不到300字的篇幅。
他对“改革文学”的描述为:
面对“文革”的“伤痕”和“废墟”,呼唤、表现在城市和乡村的改革。
蒋子龙在这个时期,显然是特别关注这一题材的作家。
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乔厂长上任记》,被看作是开“改革文学”的风气之作。
另外一些被列举为“改革小说”的作品,还有《沉重的翅膀》(张洁)、《龙种》(张贤亮)、《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等。
有的批评家,还把《人生》(路遥)、《鲁班的子孙》(王润滋)、《老人仓》(矫健),以及贾平凹、张炜的一些小说,也归入这一类型。
“改革文学”或“改革题材小说”既切合创作贴紧现实,与社会生活同步的要求,又能平衡对于“伤痕”揭发在创作上的比重,因而受到指导创作部门的重视、提倡。
根据这一表述,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洪子诚所谓的“改革文学”的时间下限为1985年之前,而且“改革文学”的范围被极度压缩了。
1999年出版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称:
到1985年之后,作家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表现一部分人的改革热情或铁腕行动,改革精神也更多地成为普通劳动者的自觉要求,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情态之中,这些作品在题材的开拓上,更趋于生活化和多视角,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写改革与人心世态、风俗习惯的变化,与前两个时期相比,描写改革已经很少那种理想主义色彩,而是交织着多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更加强烈的悲剧性。
其实从文学发展的整体来看,“改革文学”已无法涵盖许多新的现象,或者说,对社会改革的敏感和表现已经融入作家们的一般人生观念和艺术想象之中,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的“改革文学”则已经结束。
2005年出版的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认为“改革文学”潮流“以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开端”,“到80年代初,随着现实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改革题材的作品则大量涌现逐渐形成一个高潮”,“8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反映社会变革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意蕴还是在叙事方式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不能再纳入这一创作潮流的现有框架中”。
后两本文学史著作都对“改革文学”的时间下限进行了明确界定,认为“改革文学”这一潮流在1985年之后已经不复存在。
那么发表、出版于1986年至1989年的《平凡的世界》在这三本文学史的叙述中自然不会被归入到“改革文学”流派之下,要么处于缺席的状态,要么被放到一个无比宽泛的框架下予以叙述。
总之,这两种方式基本上都是对《平凡的世界》的“无名化”处理。
《中国当代文学史》根本没有提及《平凡的世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仅仅在文中提到了《平凡的世界》的书名,《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将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纳入到了“找寻深入写‘人’的新路子”*的框架中予以解读,注意到了小说中的爱情描写的突破性意义,认为“爱情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常常和生存的意志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性的复归”。
*这样的叙述虽然体现出了某种新意,但将其笼统地放到“人”的文学的大框架之下,模糊了小说的独特性。
《平凡的世界》在文学史叙述中从“有名无实”到“无名”的悬置状态,与文学史家的叙述策略有着密切关系,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也不容忽视。
“断裂”的文学史叙述与“交叉地带”的《平凡的世界》
“当代中国文学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大体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社会政治变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50-70年代’和‘新时期’。
”*两个不同时段的文学特征,被很多文学史家用诸如“一体化”/“多元”、“非文学”/“纯文学”等二元对立的关键词进行表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在这种二元对立式的理念预设中被“断裂”了。
“50-70年代文学”惯常使用的文学术语大多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作为需要受到批评与反拨的对象,在“新时期文学”的表述中消失了。
而“50-70年代文学”的某些价值理念和叙事成规远未消散,还残留在很多过来人的脑海中,他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或文学史写作时会潜在地受到影响。
作为一个成长于“50-70年代”的作家,路遥不仅参与到了“50-70年代”的政治、学习、生活与文学创作之中,而且有意识地“将中国建国以来的几乎全部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文革’开始后的终刊号”,“检阅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
*可以说“50-70年代”的生活、学习作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路遥的脑海中,在“新时期”的写作中路遥的写作难免会受到“50-70年代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十七年文学”的影响。
关于他的写作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很早就被论者发掘,而关于他的写作与柳青等人的关系更是被论者津津乐道。
路遥也毫不讳言柳青及其《创业史》对其所产生的影响,自述在创作《平凡的世界》前曾“七次阅读《创业史》”,*“《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我们也确实能够从《平凡的世界》中看到《创业史》的身影,从“农村题材小说”这一层文本来看,无论是对创作手法的选择,还是人物关系与情节的设置,《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都构成了连续对话的关系。
但路遥并未满足于对过去的一味恋战,他也有着汇入80年代主流文学叙事大潮的主观意愿。
“改革”视角的切入使得他的这一主观意愿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但此时的社会改革局势已经失去了“改革文学”初期所描绘的那种激昂奋进的乐观画面,出现了很多不谐和的声音。
作为一个对时事很敏感、对农村和农民很熟悉的作家,路遥不会不知道农村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历史进程中将付出的巨大代价。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表现出的在支持“改革”与质疑“改革”之间的犹豫徘徊,使得作品对于“改革”的叙述,包含了“改革”的别样可能性,暗示着90年代以来“改革”的“走向”,*文本中的“改革”叙述呈现出暧昧的状态。
《平凡的世界》本意是描写1975年初到1985年初,“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巨大历史性变迁”*的“改革”,它既与“十七年文学”遥相呼应,又能够与90年代以来的“改革”文学形成对话,而作为文学史主流叙述的“改革文学”的典型特征却不够明晰。
它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寻找某种“永恒”的努力中,置身于历史的“交叉地带”,由此获得了极具张力的文本效果。
能否将其划入到“改革文学”的框架下进行叙述,《平凡的世界》作为一个叙述对象已经不重要了,文学史家的叙述策略才是关键因素。
1985年被部分文学史家形容为“断裂年”,将1980年代的文学分成为明显不同的两种类型。
对于1985年前后两部分的文学发展状况的表述基本上是:
与主流意识形态联系紧密/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的二元对立模式。
《平凡的世界》既受到了“十七年文学”的影响,又从时事“变革”的角度来构思,按照“断裂”的二分法来看,《平凡的世界》无疑属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作品,而它的写作与出版时间又在1985年之后,这样就形成了错位。
按照时间划分,它不能归属于“改革文学”的范畴,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它又很难归入到1985年之后的任何一个流派之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50-70年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断裂化”叙述,《平凡的世界》作为“农村题材小说”不具备合法性,勉强可将其放入到“改革”特征不是很典型的“改革文学”的框架下,但容易使其陷入“有名无实”的尴尬状态;
而当1985年作为分界线将1980年代的文学进行“断裂化”的叙述后,《平凡的世界》作为“改革小说”也失效了,对其进行命名化的处理更加困难。
对《平凡的世界》进行“有名无实”和“无名化”的处理,虽然都与文学史的“断裂化”叙述有关,但二者背后所呈现的文学史叙述观念还是有所差异的。
将《平凡的世界》纳入到“改革文学”的框架下进行表述,虽然在文学史概念的表述上存在着“断裂”的迹象,但是他们对小说中农村题材叙事的凸显,体现了其对“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之间延续关系的认可;
而他们对“改革文学”时间下限的不明确界定,也是希望保持对1980年代文学的整体性叙述。
从他们的文学史叙述来看,他们有着寻求文学史整体性、连续性表述的努力。
於可训在《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的总论中说:
“80年代,有些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之类的概念和观点,即是注意到了当代文学与现代中国新文学的这种整体的历史联系。
这种整体的中国新文学观不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同时也反映了现代中国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实际”,*“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由一代又一代新文学作家的文学活动构成的一个连续性的文学链条。
这些作家无论属于何种文学派别,持有何种艺术主张,他们之间,不但存在上下传承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其创作成就和艺术经验,也因为这种传承和影响的关系,经纬交织,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文学家族的谱系”。
金汉在绪论中说到“1985年文学新潮所提出和显示的一些新的文学观念和美学理想,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出和尝试过了,而且从史实上说,1985年文学界的这场革新,实际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仍旧留有“断裂化”处理的痕迹。
对《平凡的世界》进行“无名化”的处理则要简单的多,要么直接忽略,要么用一个很大的框架对其进行泛泛而谈。
这样处理的背后有着更彻底的“断裂论”作为支撑。
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专门用《断裂与承续》为题对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和文学中的“断裂”话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
“在这一百多年里头,断裂和变革可以说是历史的中心主题。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历史上,也留下了一串大大小小的断裂现象和时间。
”*“被我们所指认的‘文学断裂’,既是一种存在的现象,同时,指的又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情绪,或者是一种姿态。
在有的时候,‘断裂’与其说呈现在‘文本事实’中,不如说带有更多的文本外姿态成分。
”*而对于1985年“断裂论”做出明确表述的,陈思和应该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他提出:
“‘文革’后的文学史上,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
在此之前,作家们的主要工作集中体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而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却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
”*但很有意思的是,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以一种近乎考古的方式,对当代文学的发生、“一体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对现代文学与“50-70年代的文学”进行了接续;
而陈思和则主张“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主张将当代文学纳入到“20世纪文学”的整体中进行考量,梳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传承脉络。
《平凡的世界》被文学史命名化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努力从“整体性”上把握文学史、突出其“连续性”的文学史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断裂论”的影响,最终没能进行彻底的“连续性”书写;
而服膺于“断裂论”的文学史家,却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探寻其间的传承、演变脉络。
既然“连续性”书写与“断裂化”书写二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相互渗透,那么有没有一种文学史叙述方式能更好地处理“连续”与“断裂”之间的关系,构建一部真正的具有“整体观”的文学史呢?
程光炜认为,学术界通常所说的“整体观”是“一种预设的‘真理性’的东西”,它“采用‘排斥性’的理解问题的方式把历史整体性缩小压瘪,变成历史功利性的东西,这种所谓‘整体性’,实际是一种产生于狭隘历史观的整体性”。
而他所谓的“整体观”,“则是从‘个体观’出发的”,将“被‘新时期叙述’强行拆解、撕裂和断开的若干个‘文学期’”,“通过讨论和辨析的工作重新整合起来,在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关联点上整合起来的”。
*程光炜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找寻关联点的“整体性”研究,也许不失为一种处理文学史“连续”与“断裂”叙述矛盾的好方法。
《平凡的世界》作为一个处于历史“交叉地带”的“过渡性”文本,它既有着“十七年文学”的痕迹,又与其有着明显的差异;
它既向80年代的“改革文学”靠拢,又与其迥异,其意义遥指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思潮中的“改革”文学,甚至接通到了中国当下,触及到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某些病灶。
《平凡的世界》“在‘断裂’与‘延续’之间的犹疑与彷徨,出人意料地成为了沟通两个时期的历史桥梁”。
*如果能将它作为一个“个体”案例推及到更多类似的“个体”,也许能够将被“断裂化”的当代文学史重新整合起来。
如果说上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因为文学史家们执著地从题材的角度出发对《平凡的世界》进行文学史定位所造成的,那么我们换个角度,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界定《平凡的世界》,也许既能让其“实至名归”,又能巧妙地解决文学史“断裂”和“连续”叙述不协调的问题。
对《平凡的世界》用“现实主义”这一术语解读,符合作家本人的创作宗旨,作家在创作自述中谈道:
“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承认,眼下,也许列夫·
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影响要更深一些。
”*“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
”*“我决定要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
”*也符合作品本身的内在意蕴,作品甫一出版,关于其“现实主义”方法与精神的评论文章不绝如缕。
而后也有文学史家将其纳入到“现实主义”的框架下为其定位,2002年出版的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将路遥放入到“执著的现实主义者”*的框架下予以评价,认为“对现实主义的开放性理解和自觉坚持,构成了路遥小说创作的基本美学品格”。
*对《平凡的世界》也着重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其开列的小标题“对现实主义的开放性理解和自觉坚持”可以说是对《平凡的世界》本质特征的把握。
虽然该书只是罗列了不同时期有影响的评论观点和部分摘录,但它们却能够反映文本特征和内涵,也能够取得评论者和读者的认可。
说《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一般不仅是从普通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这一角度来说的。
《平凡的世界》无疑受到了柳青的《创业史》的影响,保留了“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的痕迹;
但同时它在某些方面又超越了《创业史》,汲取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某些因素,使得作品具备了一定的批判力度,汇入到了80年代初期“现实主义的探寻与回归”的潮流之中;
在80年代中后期现代派思潮席卷文坛的语境下,路遥对现代派作品采取并不排斥的态度,而是力图使其笔下的现实主义能获得现代意义的表现,这使得《平凡的世界》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框架而融进了部分现代元素,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
“现实主义”作为《平凡的世界》的本质特征,融会了旧与新、传统与现代诸多元素,旧与新或者传统与现代之间既相互区别呈现“断裂”之势,又在转换之间相互渗透融会为一个整体。
现实主义在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