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的情趣与文人园林文档格式.docx
《禅的情趣与文人园林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禅的情趣与文人园林文档格式.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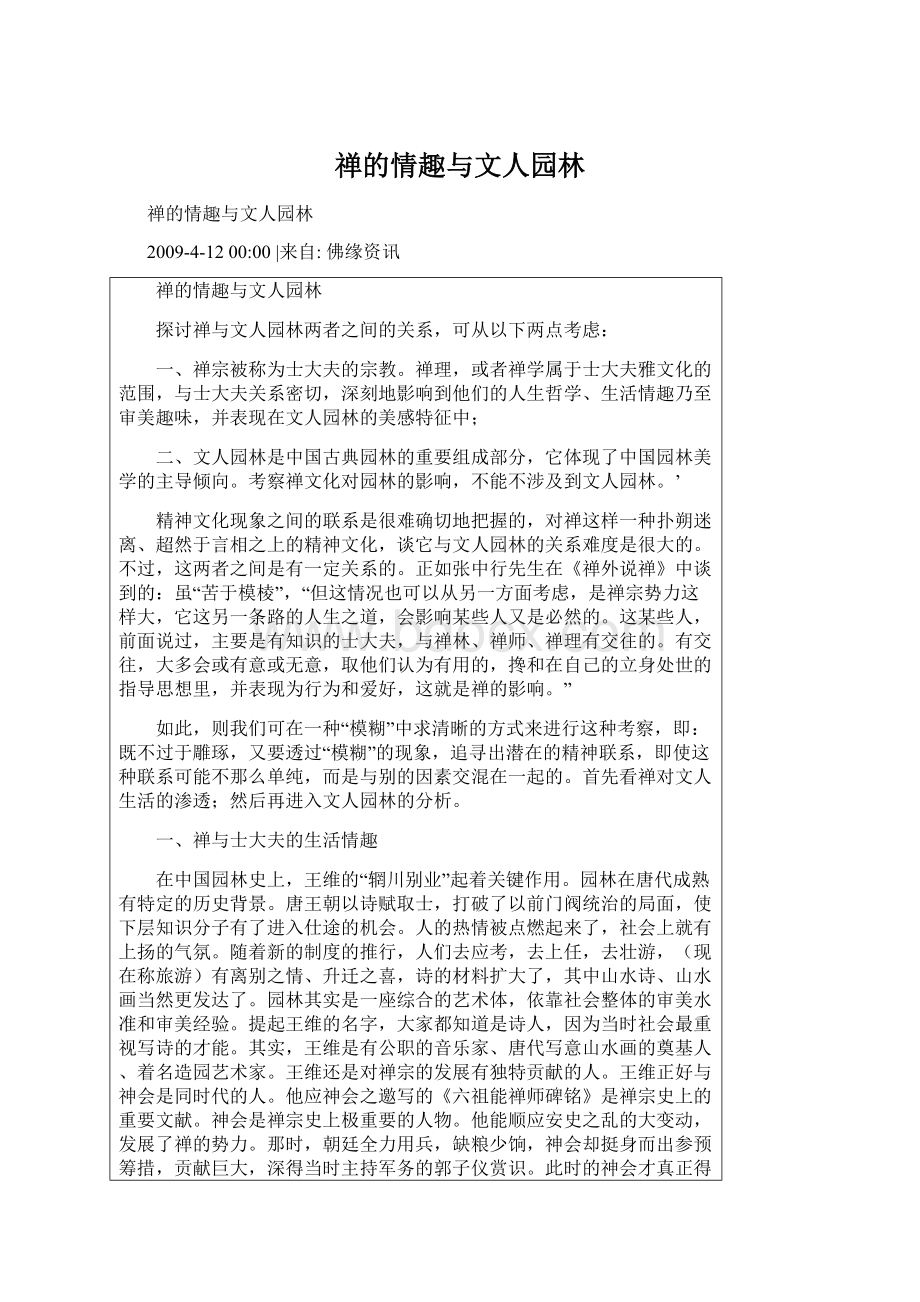
神会提出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那时他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以他在会上说:
“令一切众生,珍惜生命!
”在这场辩论的影响下,王维也倾向于南宗了。
王维在与神会直接交往中领悟了禅的顿悟大义,并写出这篇碑文,碑文称赞慧能学说高妙,而且有益于社会:
“永惟浮图之法,实助皇王之化。
”而且明确提“一花六叶”,一花指禅,六叶指达摩以来的六祖,这就将慧能定为六祖了。
宗门内部之争,由文人出来表态,影响非常大。
“安史之乱”时,北宗和尚因原本在大庙中受供养,敌寇来时就纷纷附逆,只有南宗能自立,在战乱中显得有骨气。
所以,神会的自身表现就更为这场南北之争做了结论。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历史出现了转折。
以前上扬的、理想的气氛破灭了,社会矛盾又尖锐起来。
知识分子中挫折感和绝望情绪盛行。
连王维本人也在安史之乱中受了挫折,虽未获罪,内心矛盾相当激烈。
这时候,社会需要一种心灵上的安慰剂,需要使自己的“自性”,有一个发挥的方向和范围,禅正好符合了这种精神的需要,主要是文人的这方面的需要。
唐宋以来,禅宗普遍渗透到士大夫中间,影响到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新唐书·
五行志》记载:
“天宝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
”王维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
他“笃志奉佛”(《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曾在大荐福寺道光禅师那里,“十年座下,俯从受教”(《王右丞集》卷二十五(道光禅师塔铭》)。
在受慧能的弟子神会所托而作的《能禅师碑并序》中,王维表达了他对慧能禅法的深刻理解,所谓“即凡成圣,举足下足,长在道场”,又所谓“至人达观,与物齐功。
无心舍有,何处依空”(《王右丞集》卷二十五)。
受禅影响,王维形成了一种自在适意的人生哲学。
在《与魏居士书》(《王右丞集》卷十八)中,他把这种人生哲学表露无遗。
他劝魏居士不再固守“山栖谷隐,高居深视”的山中隐士生活,出任适当的朝廷官职:
“……若有称职,上有致君之盛,下有厚俗之化,亦何顾影躅步,行歌采薇?
”他提出这样做的根据是:
“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
”人只要心性根本把握住了,身在山林还是在朝阙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以“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劝导魏居士,正基于禅理。
他还说,人应“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是要人不妄执空、有之别。
因此,他对古往今来的高人隐士们颇有微辞:
“古之高者曰许由,……闻尧让,临水而洗耳。
耳非驻声之地,声无染耳之迹;
恶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
此尚不能至于旷士,岂人道者之门欤?
降及嵇康,亦云顿缨狂顾,逾思长林而忆丰草。
顿缨狂顾,岂与侥受维絷有异乎?
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
异见起而正性隐,色事碍而慧用微,岂等同虚空,无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见独存之旨邪?
……”
出处之情一致,筌蹄之义两忘。
他的生活情趣中也体现了这种人生态度。
他中年以后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自在恬澹,正体现了“长林丰草”与“官署门阑”视为一如的适意明心的人生哲学。
这种生活情趣与他的所谓“好道”(主要是禅佛教)密切相关。
王维所代表的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具有普遍性。
唐宋以来,士大夫普遍取出处之情一致、筌蹄之义两忘的人生哲学和自然清静、澹泊适意的生活态度。
白居易、苏轼等人都是如此。
白居易自元和十年(als年)起,便屡谪外官。
这促使他日渐倾向于禅趣佛理。
他自云:
“余早栖心释梵,浪迹老庄”(《白居易集》卷三十五(病中诗十五首·
序》)。
他在《传法堂碑》文中,记述了他向兴善惟宽禅师问道的过程。
其中就有一问是:
“无修无念,亦何异于凡夫耶?
”禅师回答说:
“凡夫无明,二乘执着;
离此二病,是名真修。
……”(《白居易集》卷四十一)。
他的人生态度中就有离二乘执着、常适常乐的特点,如他所说的“道行无喜退无忧,舒卷如云得自由”。
(《白居易集》卷三十五(和杨尚书(罢相后,夏日游永安水亭,兼招本曹杨侍郎同行》))行退俱适,恬淡自如,所以他能够做一个“人间事了人”,不管人事如何沉浮变迁,都能悠然适意。
他十分明确地把禅家的心性作为立足点:
“若论尘事何由了,但问云心自在无?
进退是非俱是梦,丘中阙下亦何殊?
”(《白居易集》卷三十五《杨六尚书频寄新诗,诗中多有思闲相就之志。
因书鄙意,报而谕之》)。
他也是立足心性自适,得出了和王维一样的齐一仕隐、出处俱可的结论。
以清净淡泊之心性而随缘任运,以心性之常应付世间沧桑万变,这种人生态度在苏轼那里也体现得很突出。
他的一生虽几经波折起伏,却能调整为旷达自如,安之若素。
他曾以“静常”命名其斋,就是深含禅意的。
《静常斋记》中云:
“虚而一,直而正,万物之生芸芸,此独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静。
泛而出,渺而藏,万物之逝滔滔,此独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日常。
无古无今,无生无死,无终无始,无后无先,无我无人,无能无否,无离无着,无证无修。
……既以是为吾号,又以是为吾室,则有名之累,吾何所逃。
然迹趋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苏轼文集》卷十一)。
这里面庄、禅糅合;
“无离无着,无证无修”是典型的禅家宗旨。
事实上,苏轼与禅师来往甚密,经常与禅师们参学或是斗机锋,也有不少诗词酬唱之作。
《五灯会元》卷十七专门列有“内翰苏轼居一节,记他参禅的雅事:
内翰东坡居士苏轼,字子瞻。
因宿东林,与照觉论无情话,有省。
黎明献偈曰: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未几抵荆南,闻玉泉皓禅师机锋不可触,公拟抑之,即微服求见。
泉问:
“尊官高姓?
”公曰:
“姓秤,乃秤天下长老底秤。
”泉喝曰:
“且道这一喝重多少?
”公无对,于是尊礼之。
后过金山,有写公照容者,公戏题曰: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琼州。
类似的机锋应对之事在苏轼还有不少。
融合禅理于庄、玄,所以苏轼的人生态度格外旷达。
这种态度在他的词中处处流露出来。
在寄禅师参寥子的《八声甘州》一首中,就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之语。
抒发在词中的这种态度在他实际生活中也常流露出来。
《避暑录话》卷二记,苏轼在黄州时,曾有一次“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
翼日喧传:
‘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孥舟长啸去矣。
’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
”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由此可见。
它和禅家所谓“于境上心不起”、“于境而不着境”是相通的。
苏轼一生与不少禅师交往,机锋应答之间,受其影响是明显的。
苏轼所代表的这种人生态度,深得禅家三昧。
《五灯会元》卷七记龙潭崇信禅师向天皇道悟禅师问道,天皇道悟云:
“任心逍遥,随缘放旷。
但尽凡心,别无圣解。
”禅师们就常有洒脱不拘、任性自适之举。
药山惟俨禅师“一夜登山径行,忽云开见月,大啸一声,应澧阳东九十里许”(《五灯会元》卷五《药山惟俨禅师》)。
李翱为此赠诗曰:
“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李诗无疑表达了士大夫对禅家意趣的赞赏。
在仕隐间摇晃时,苏轼想到园林的作用: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
……今张君之先君,所以为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
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
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
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苏轼文集》卷十一(灵璧张氏园亭记》)。
我们再来看看宋代士人赵孟坚的生活形象。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说他“襟度潇洒”,并记述了一段雅事:
·
庚申岁……余偕一时好事者邀子固,(即赵孟坚)各携所藏,买舟湖上,相与评赏。
饮酣,子固脱帽,以酒唏发,箕踞歌离骚,旁若无人。
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舣棹茂树间。
指林麓最高处瞪目绝叫曰:
“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笔也。
”邻舟数十,皆惊骇绝叫,以为真谪仙人。
这种洒脱不羁的人生态度在宋以来很普遍。
时风所及,连皇亲贵戚也以此为尚。
《齐东野语》卷十就记有这样一则:
“庄简吴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寿特亲爱之。
……一日,王竹冠练衣,芒鞋筇杖,独携一童。
纵行三竺、灵隐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游人望之,俨如神仙,遂为逻者奏闻。
”皇帝知道了,也十分欣赏他的举止,为他作赞云:
“富贵不骄,戚畹称贤。
扫除膏梁,放旷林泉。
沧浪濯足,风度潇然。
国之元舅,人中神仙。
”虽然这里面也许有皇亲贵戚的矫饰成分,但时风之盛,才会有人去附庸风雅。
沈括在《梦溪自记》中,说他“与之酬酢于心目之所寓者:
琴、棋、禅、墨、丹、茶、吟、谈、酒、谓之‘九客’。
”禅被列为“九客”之一,与诗、书、画、酒等同为士大夫园居生活的主要内容。
由此可见,宋以来参禅悟道不再是僧人的“专业”。
在这样的风尚下,士大夫即使不都像苏轼那样嗜好参禅,也免不了受禅理禅趣的濡染。
他们在向外参与政治、时事的同时,也常常退回到一己心中,以内心的安恬淡泊为乐。
司马光所说的“独乐”,就表现了这种乐趣。
在《独乐园记》中,司马光谈到几种“乐”,一是孟子所说的与众同乐,他称之为王公大人之乐;
而颜回所代表的那种是圣贤君子之乐,就是“一箪食,一瓢饮”,而仍“不改其乐”。
然而司马光并不以这些“乐”为乐,他所追求的乐是这样的:
“若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
”故此以“独乐”名园。
“各尽其分而安之”的“独乐”,也就是追求安恬自足、顺任自己的平常性情,自足自适,这与苏轼等人的适性逍遥、淡泊无求的情趣有内在的一致性。
就唐宋以来士大夫们的山林之趣而论,不能排除其中有禅的成分在,和这之前的隐逸风尚有不完全相同的内涵。
唐宋以来,士大夫普遍追求林泉之乐,这里面有禅的心性观和自然理趣的痕迹在。
像王维: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酬张少府》)他的山林情趣是自觉地联系到禅趣的:
他是出于一种心性追求而近山林的,并非出于仕途失意的无奈被迫退隐其间。
晚唐的司空图,本可以进入仕途,这方面并不失意,他却辞官人隐中条山王官谷。
他的《二十四诗品》中用以形容意境的语句,弃满了山林气和禅意,不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生活情趣的流露。
我们随手拈起其中一则就可以看到这种情趣。
如“冲淡”一条中,有“阅音修篁,美曰载归。
遇之匪深,即之愈稀”之句;
“沉着”中云:
“绿杉野屋,落日气清。
脱风独步,时闻鸟声。
……”;
“典雅”中说到: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
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
眠琴绿荫,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无言的、清淡悠远的境界,体现在天然趣深的山林气氛中,里面飘动着若即若离的禅意。
这样的情趣与文人的心性意识有关,正如“疏野”等条中所点明的:
“惟性所宅,真取不羁。
……筑室松下,脱帽看诗。
但知旦暮,不辨何时。
倘然适意,岂必有为。
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山间林下的悠然情趣,是和“真”、“性”、“适意”联系着的。
“清涧之曲,碧松之阴。
一客荷樵,一客听琴。
情性所至,妙不自寻”(《二十四诗晶·
实境》)。
这是在一种山林气氛中实现的情性自适的境界,有淡远、恬静、幽妙的禅味。
所以,清代张商言对司空图以“以禅论诗”誉之。
有意味的是,宋代理学大师们也一面大讲“天理”,一面悠游于山水林泉之间。
周敦颐任虔州通判,“道出江州,爱庐山之胜,有卜居之志,因筑书堂于其麓。
堂前有溪,发源于莲花峰下,洁清绀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缨而乐之,遂寓名濂溪。
”(《周子全书》卷二(年谱》)周早年读书于鹤林寺中,寓居其间,与鹤林寺寿涯禅师相交甚善,“每师事之,尽得其传焉。
”(<
鹤木寺志》)另一位理学家朱熹也建有“竹林精舍”,并明确表达过对山林放逸的倾心,他的一首词中就有“归把钓鱼钩。
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句。
理学把“天理”纳人人的自觉的心性修养中,说明它本来就与吸收禅的心性说有关;
他们这种林泉之趣也未尝不与理学中的“尽性”说有关。
朱熹对所谓“曾点气象”的推崇,就明显地运用了禅宗思想:
“曾点之学,盖有以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
故起动静之际,从容如此。
”“他看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
”(朱子语类》卷四十、<
四书章句集注·
论语·
选进)在这里,宇宙本体和人的心性自然融贯;
“天理”就在道德修养圆满的自然心性中,而不再是外在强加的约束机制。
由此也可见禅宗思想的渗透力之大。
理学家们不只是从理论上自觉融化禅理,而且是在自己的生活情趣中也吸收了禅趣。
邵雍的一首咏景诗,就很有禅趣,这首题为《清夜吟》的诗云:
“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
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境与心得,理与心会,清空无执,淡寂幽远,是生活情趣,也不妨说是禅趣。
士大夫的山林情趣还有一种极为独特的表现方式,那就是在各种书屋、斋室的名称上大做山水文章。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它更多地体现着禅家“境由心造”的旨趣。
借这种方式实现山林之志更为自由,不必定要仰赖实有的山水环境或其他园林因素;
只借一个山林气的名称就可以在居室主人的心中引发那种野逸之趣,从而使这场所变成了主人精神上的林泉之境。
这类书斋之名很多,如“怀麓堂”、(李东阳)“文木山房”(吴敬梓)“雪涛阁”(袁中郎)“岁寒堂”、(张戒)“稼轩”(辛弃疾)等等,不一而足。
其情趣淡泊、幽远。
明代中叶以后,有一段时期禅悦之风又风靡于士人生活中。
李贽、袁宏道、袁中道、董其昌等,与名禅师紫柏、憨山等相交甚密。
沈德符《敝帚轩剩语》卷上云:
“紫柏名振东南,缙绅趋之若鹜。
”这股禅悦之风在士大夫生活情趣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袁氏兄弟就很典型。
袁宗道“酷爱白、苏二公”,“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二幅。
倦则手一编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
(《袁宏道集笺校》卷三十五(识伯修遗墨后》)使他倾心的,是白居易、苏轼那种放旷、闲适的生活态度。
这种情趣与自觉的心性意识有关。
“中郎与小修皆知向学,先生(指袁宗道一引者注)语以心性之说,亦各有省,互相商证。
……逾年偶于张子韶与大慧论格物处,有所人,急呼中郎与语。
甫拟开口,中郎即跃然曰:
‘不必言。
’相与大笑而罢。
至是始复读孔孟诸书,乃知至宝原在家内,何必向外寻求。
……”(《公安县志》卷六(袁宗道传》)正是这种落脚于心性的旨趣,才是他们兄弟三人沉溺林泉、推崇白居易和苏轼的根本缘由。
从明末文震亨《长物志》所列举的消闲之物中,我们也能领略到禅与士人生活情趣的关系。
他列举的有:
山斋、佛堂、水石、太湖石、禅衣、香炉,等等。
《长物志》中处处流露着那种淡雅静幽的生活情趣,颇近于禅家。
例如,谈到室庐的台阶设计时说:
“……愈高愈古,须以文石剥成,种绣墩或草花数茎于内,枝叶纷披,映阶傍砌。
……复室须内高于外,取顽石具苔斑者嵌之,方有岩阿之致。
”(《长物志》卷一<
室庐》)又如卷四“禽鱼”一条中说:
“语鸟拂阁以低飞,游鱼排荇而径度,幽人会心,辄令竟日忘倦。
顾声音颜色,饮啄态度,远而巢居穴处,眠沙泳浦,戏广浮深;
近而穿屋贺厦,知岁司晨,啼春噪晚者,品类不可胜纪。
……故必疏其雅洁,可供清玩者数种,令童子爱养饵饲,得其性情,庶几驯鸟雀,狎鱼凫,亦山林经济也。
”他所求的是“会心”忘忧,是“清玩”中的雅趣。
因此,他对那些在宅园中繁杂罗列、竞奇逞富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因为这样做不得“性情”,而推重那种以涵咏情性为旨归的清雅之举。
《长物志》卷二“花木”中云:
“吴中菊盛时,好事家必取数百本,五色相间,高下列次,以供赏玩,此以夸富贵客则可。
若真能赏花者,必觅异种,用古盆盎植一株两株,茎挺而秀,叶密而肥,至花香时,置几榻间,坐卧把玩,乃为得花之性。
这种情趣在清代士人那里也不乏其例。
像李渔、王士稹以及郑燮(板桥)等人的诗文中就流露出这种情趣。
李渔《闲情偶记》中就十分鲜明地体现出适意为上、闲适恬淡的人生情调与趣味。
不论谈居室构造,还是谈山石、花木设置,都贯穿着这种情趣。
卷四“居室部·
山石”一章中,有“零星小石”一节云,“贫士之家,有好石之心而无其力者,不必定作假山。
一卷特立,安置有情,时时坐卧其旁,即可慰泉石膏盲之癖。
”这也是一种自适其性的方式,借此人的精神、心理也就获得了谐调与平衡。
不论贫富、穷通,都可以在恬淡自足的心境中获得安宁。
这种心境,在富贵闲暇时表现为风雅脱俗,在穷困潦倒之际则表现为豁达知足。
正如明代高濂《遵生八笺》卷七中《高子自足论》一篇所说的:
“……有山可樵,有水可渔,便当谓足于庄田;
残卷盈床,图书四壁,便当谓足于珍室;
门无剥喙,心有余闲,便当谓足于荣华;
布衾六尺,高枕三竿,便当谓足于安享;
看花酌酒,对月高歌,便当谓足于欢娱;
……若此数者,随在皆安,无日不足,人我无竞,身世两忘,自有无穷妙处,打破多少尘劳。
这种心造其境、随遇而安的意趣发展到极端时,竟产生了靠纯粹子虚乌有的幻想中的林泉闲境来补偿其精神生活的现象,连最起码的物质实体也不依赖了。
清人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中记:
“吴石林痴好园亭,而家奇贫,未能构筑,因撰《无是园记》,有《桃花源记》、《小园赋》风格。
……余见前人有所谓‘乌有园’、‘心园’、‘意园’者,皆石林之流亚也。
”从中看来,这类“园林”还不少呢。
文士们耽溺于那种闲逸的林泉雅好竟如此之深!
之所以如此,是和士大夫们的精神需要密切相关的。
中国封建社会越发展到后期,士大夫们也就越来越逃遁于内心天地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着禅家立足于心性的观点,在一己心灵中求得精神的平衡、安恬。
林泉放旷,自得其乐,便是精神生活平衡机制的重要形式。
他们的林泉雅好最终落实在一个“心”字上。
正如明代一位理学家所表白的那样:
“月下咏诗,独步绿阴,时依修竹,好风徐来,入境寂然,心甚平淡,无康节所谓‘攻心’之事。
”“中堂读倦,游后园归,丝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风静,天壤之间,不知复有何乐!
”(《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
吴康斋先生语》)——林泉之乐,乐在由此获得的“平淡”、“悠然”的心境。
在对山水竹木的赏爱中,寄托着他们要求相对的精神独立、人格的自我完善和心性的自由自足的深层需要。
这种“平淡”、“悠然”的心境追求和林泉之趣,已深深地积淀于中国士大夫的生活中。
清代郑板桥的生活情趣就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典型。
对他来说,一丛兰草,几竿修竹,或有片块山石,足以成无限清雅之境。
“茅屋一间,天井一方,修竹数竿,小石一块,便尔成局,亦复可以烹茶,可以留客也。
月中有清影,夜中有风声,只要闲心消受耳。
”“一块石,两竿竹,小窗前,清趣足,伴读书,戛寒玉,夜灯红,窗纸绿。
”这里描述的环境极素朴、简净,却足以供“闲心”消受,充满了“清趣”。
它是物境,更是闲心、清趣构建的心境或意境,迥超尘表,清脱洒然。
主人那安恬自足的心灵世界由此可见。
郑板桥受过禅佛教的影响。
从他的诗文书信看,他与禅僧、居士多有来往、应对。
《与勖宗上人书》中他说:
“燮旧在金台,日与上人作西山之游,夜则挑灯煮茗,联吟竹屋,几忘身处尘世,不似人海之中也。
迄今思之,如此佳会,殊不易遘。
兹待秋凉,定拟束北上。
适有客人都之便,先此寄声。
小诗一章,聊以道意:
昔到京师必到山,山之西麓有禅关,为言九月吾来住,检点白云房半间。
””在《僧家》一词中也曾有写禅僧的句子云:
“……非矫,也亲贵胄,也踏红尘,终归霞表。
”这写出了禅家风貌与神韵。
郑板桥在与禅师的交往中,也不免受到影响,流露出洒脱的生活态度和淡雅、清幽的情趣。
像他在《画芝兰棘刺图寄蔡太史》中所说的:
“写得芝兰满幅春,傍添几笔乱荆榛。
世间美恶俱容纳,想见温馨淡远人。
”这里面就有禅理的意味在。
在《寄青崖和尚》中有“透脱儒书千万轴,遂令禅事得真空”之句,赞美青崖和尚。
其实,这两句也不妨看作他自己及那时代许多文士内在情怀和精神结构的写照。
像郑板桥一样,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是一面有儒家的对现实人伦的关怀;
一面又持淡泊自足的超然情怀,内心世界是洒脱清净的。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注意的精神现象之一。
与林泉雅好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晶茗、珍品赏玩等,这些也都是士大夫生活情趣的表现方式或者说具体实践,同样反映了他们的心性意识和精神追求。
并且,晶茗、珍品赏玩等本身也是士大夫园居生活的组成内容,所以和我们的主题关系紧密,须考察一番。
先来看看品茗中的趣味。
宋代张淏《云谷杂记·
补编》卷一有“饮茶盛于唐”一条,称中唐以来“尚茶成风”。
白居易就耽于此道,他的闲适诗中多有描述。
《琴茶》一首中他写道:
“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白居易集》卷二十五)抚琴或品茗,萧散任性。
中唐时还出现了陆羽着的《茶经》。
其后,宋代士大夫更精于此道,玩味得越来越精致和深人了。
他们更明确地把品茗和士大夫们的人生态度和精神趣味联系在一起。
北宋黄儒(道辅)说得透辟:
“自国初以来,士大夫沐浴膏泽,咏歌升平之日久矣,体势洒落,神观冲淡,惟兹茗饮为可喜,相与摘英夸异,制卷鬻新而趋时之好。
故殊绝之品始得出于榛莽之间,而其名遂冠天下。
……”(《品茶要论·
总论》)洒落、冲淡的外在风貌下体现的是内心的情趣与精神追求。
苏轼曾点破个中三昧。
在《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中,他说黄道辅“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
作《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
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此详哉?
……今道辅无所发其辩,而寓之于茶,为世外淡?
白之好,此以高韵辅精理者。
”(《苏轼文集》卷六十六)这就明确道出了士大夫淡泊无求、恬静无碍的情怀与嗜好品茗之间的关系。
品茗日渐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常课,与.诗词、书画、棋、酒等一起,为他们构造起一个自在悠然的心性天地。
宋末张炎说:
“润色《茶经》,评量山水,如此闲方好。
”([清]厉鹗撰(增修云林寺志》卷六)
文士们与禅师一起品茗消闲、怡情安性的情况,也是常有的。
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文中都有记述。
清代云林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