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思想中的儒佛道三家思想的体现Word文件下载.docx
《苏轼思想中的儒佛道三家思想的体现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苏轼思想中的儒佛道三家思想的体现Word文件下载.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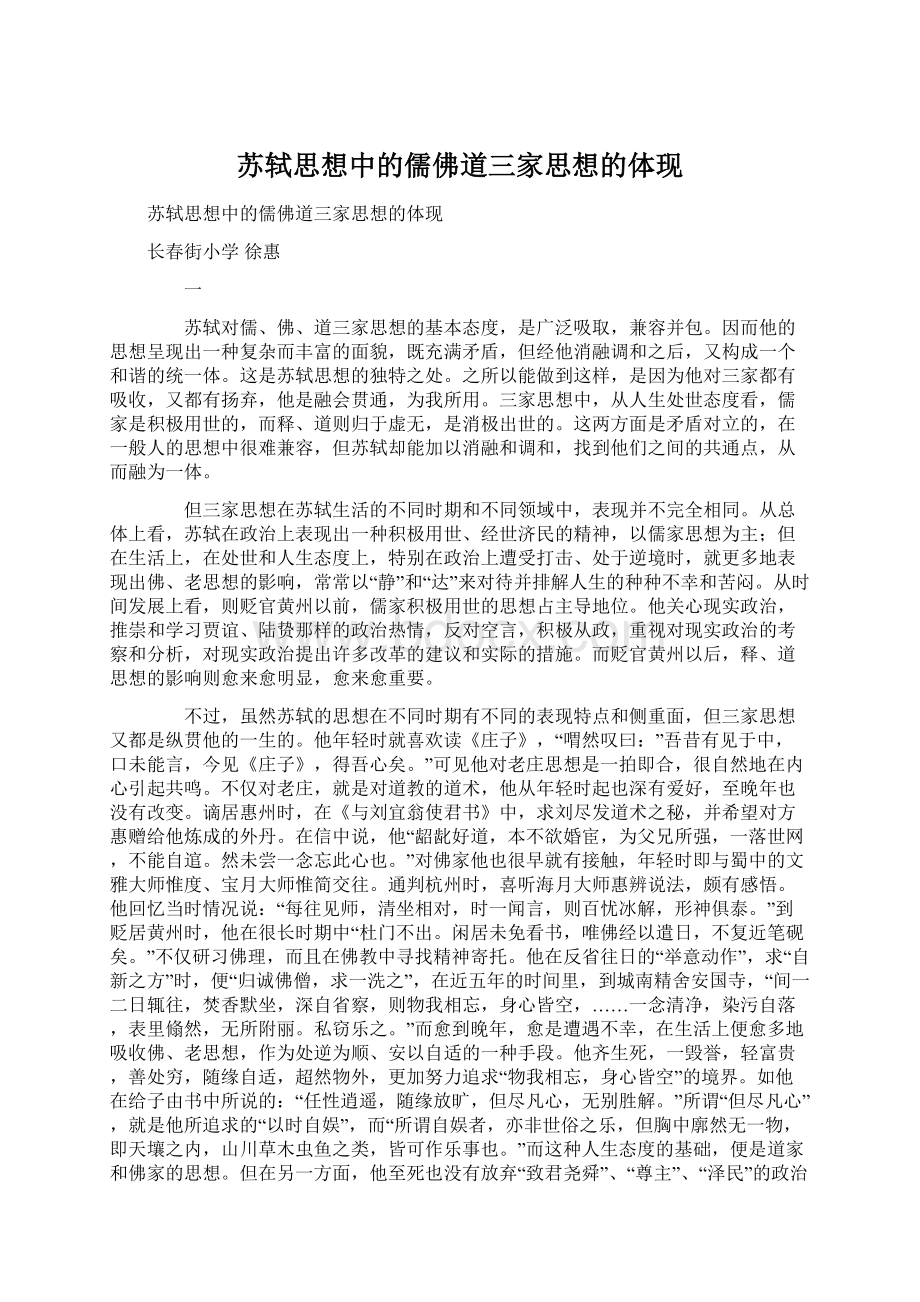
”而愈到晚年,愈是遭遇不幸,在生活上便愈多地吸收佛、老思想,作为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手段。
他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善处穷,随缘自适,超然物外,更加努力追求“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
如他在给子由书中所说的: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
”所谓“但尽凡心”,就是他所追求的“以时自娱”,而“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可作乐事也。
”而这种人生态度的基础,便是道家和佛家的思想。
但在另一方面,他至死也没有放弃“致君尧舜”、“尊主”、“泽民”的政治理想。
因此,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在苏轼一生的不同时期,尽管有主次的不同,有消长的变化,却是始终并存的。
二
苏轼的儒家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忠君、报国、利民的从政原则;
第二是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
第三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
这三方面是互为联系,不能分割的。
下面着重谈谈第二个方面。
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在苏轼考试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就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
文中热烈赞颂儒家一贯标榜并引以为典范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之际”,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的仁政德治的样板,其特点是“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进而说明统治者赏善罚恶是为了勉励和惩戒,故“赏”能使人“乐其始而勉其终”,而“罚”则能使人“弃其旧而开其新”。
然后提出“广恩”、“谨刑”的原则。
他引《传》(《尚书》孔安国传)云:
“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
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
”又引《书》(《尚书·
大禹谟》)曰: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指违背常规)。
”在此基础上又加以发挥,提出坚持实行仁政的基本原则: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
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
过乎义,则流入于忍人。
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最后概括出“天下归仁”的理想(在他看来也是一种规律):
“以君子长者之道得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
忠厚之至也!
”这虽然是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但确实反映了苏轼的政治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成了他后来一生从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贯彻始终的。
《思想论》也是表现他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章。
此文作于嘉祐八年(1063),在从政不久的凤翔任上。
这篇文章表现了苏轼在政治上的务实精神。
文中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要有坚定明确的目标,同时经过实际的考察,提出周详而又可行的计划,然后按照计划坚持下去。
这篇文章本身就体现了他提出的这一原则和精神。
文章中的论点,就是他对当时宋王朝的政治经济情况进行了实际深入的考察以后提出的。
文章一开始就指出:
“方今天下何病哉?
其始不立(“立”指施政以前提出的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切实可行的计划);
其卒不成(指结果不能获得成功);
唯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
……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
苟立而成矣。
”然后明确地提出当今之世的“三患”:
“常患无财”、“常患无兵”、“常患无吏”,进而提出“丰财”、“强兵”、“择吏”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指出这是宋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
“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
”他又提出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原则:
一是:
“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也就是要事先定好计划,不可盲目行动,这是“贵于立”的首要问题。
二是:
反对“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
对政策、用人等用舍、兴废,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确定,也不能以口头上赞同者的多寡来确定,而是要以绝大多数人(指老百姓)内心是否拥护来决定。
他指出:
“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
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意思是说,那些直接传到自己耳中的意见都是不敢指责非难我的看法的)。
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
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
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同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
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
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
”在苏轼看来,政策一定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才能取得成功,但这个多数,不是指对自己说好话的人有多少,而是指天下实际拥护的人有多少。
苏轼的这一见解是很深刻的,是他德治仁政思想和重民思想的集中表现。
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苏轼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即使到了晚年远贬岭海时期,那时他已是罪废之人,不在其位也不谋其政了,但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中,却仍然坚持这些理想,仍然努力加以阐发、提倡。
这集中地表现在他在海南所写的收在《志林》中的十三篇史论(又名《海外论》)中。
在《武王非圣人》一文中,他极力反对武王伐纣,提出“天下归仁”的原则:
“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
不至,不取也。
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
”也就是说,即使纣暴虐无道,亦不能诉诸兵。
“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以不得辞也。
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
”因此他认为,神器随仁义自来,不可强取,也不得推辞。
以“天下归仁”的思想看,武王伐纣为强取,所以他认为“武王非圣人”。
在《赵高李斯》一文中所表现的政治思想,同他早年的改革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一是重视任人,二是反对严刑峻法。
他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历史经验,其一就是始皇用人不当:
“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
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
”其二就是秦法过严,结果是“以法毒天下”。
因此,他引用周公的话说:
“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又引用孔子的话说: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其‘恕’矣乎!
”主张“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
”
在统治方法上,他崇尚礼治而反对法治;
在法与人的关系上,他认为人比法更重要,反对“任法而不任人”,反对重法而轻人。
这些思想都是在他早期的政治思想中明确提出的,而到晚年仍没有改变,可见他是一贯坚持的。
由此看来,儒家思想在他的晚年不仅没有放弃,而且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并没有完全被佛、老思想所取代。
三
苏轼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在仁宗、神宗、哲宗三朝表现是不一样的。
仁宗朝,嘉祐六年(1061),他向皇帝献《进策》和《进论》各二十五篇,系统地提出自己的革新主张;
八年(1063)又作《思治论》,进一步阐发自己的改革主张。
神宗朝,熙宁二年、三年,王安石变法时期,他却上《议学校贡举状》,又两上神宗皇帝书,全面反对新法。
而到哲宗朝,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废除新法时,他又反对尽废新法,尤其是反对废除免役法。
对于苏轼在这三个时期的不同表现,学术界曾有不同的看法。
分歧主要在两点上:
其一是,苏轼在政治上到底是属于革新派还是保守派?
抑或是属于游移于革新和保守派之间的中间派?
其二是,三个时期的不同表现,是反映了苏轼政治思想的重大转变呢,还是在本质上是体现了他政治思想的一贯性,只不过具体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特点不完全相同罢了?
我们认为,从总体看来,苏轼在政治上基本上是一个革新派,既不是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利益的保守派,也不是动摇于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中间派。
当然应该承认,苏轼的政治思想是存在着矛盾的。
三个时期的不同表现、不同主张,是他思想中固有的矛盾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
但不是动摇,更不是随风转舵。
在不同的政治条件下,思想肯定会有变化,但不仅不是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在变化中仍表现出其前后的一贯性、一致性。
这一贯性和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哲学上动与静的矛盾的自然观,形成了他政治上既积极主张革新,又要求以静待变的稳健改革的思想。
在《御试制科举》中,他表述了万物皆生于动的进步的自然观:
“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
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
”在《策略一》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仲尼赞《易》,称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由此观之,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也。
唯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
”又在《苏氏易传》卷一中说:
“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
以不息故健也。
流水不腐,用器不蛊。
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
”这就是苏轼主张政治革新的思想基础。
这无疑是进步的、积极的。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在二十五篇《进策》的《策略一》中就鲜明地表达了他积极革新的锐气:
“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
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
”意思十分明白,就是说如果不改革,将是十分危险的。
但另一方面,苏轼又主张微变、渐变和以静待变,而反对过激、过猛、过速的变革。
《宋史》本传在谈到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时,就指出他主张“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他赞扬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思想。
盖公为秦末汉初人,提倡黄老之术,主张以清静无为的思想治理国家,得到苏轼的赞扬,他“师其言,想见其为人。
”在他后来写的《问养生》一文中,将这种渐变的思想阐述得更加清楚:
“寒暑之极,至于折胶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
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
使此二极者,相寻而狎至,则人之死久矣。
”因此他主张“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这一点,应该说同主张激进改革的王安石很不一样的。
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主张以“征诛”为变法开路。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苏轼确实有他偏于保守的一面。
这是他既主张革新而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在对政治形势的认识上,同王安石并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
天下有治平之名,无治平之实;
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
此其有未测者也。
”并指出当时的“三患”在“无财”、“无兵”、“无吏”。
而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也在于富国、强兵。
但苏轼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任才,而不在变法。
早在仁宗朝他就指出:
“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
”苏轼强调吏治的重要有他合理的一面,同时指出王安石实行新法中由于任人不当(“新进勇锐之人”),给新法带来不少弊病,也是正确的。
但将变法和任人对立起来,完全否定变法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也有其片面性和保守的一面。
第三,苏轼从政的原则是忠君、报国、利民,所以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又不是全部地绝对地否定新法,他也肯定某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改革,这同他关心民生疾苦,以是否便民、利民为出发点分不开。
所以他在通判杭州时,就“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而后来他在检讨自己反对新法是“辄守偏见”时,也申言自己是“此心耿耿,归于忧国。
”旧党当政时,他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尤其反对废除免役法,也是从对人民有利无利这一点出发的。
他论析“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而主张去其弊而不变其法。
总观王安石和苏轼的改革主张,并加以对比,可以这样说:
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以法家思想为基础,特点是激进和峻刻;
而苏轼的改革思想则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又杂以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特点是渐进和宽简。
或者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苏轼的改革主张是儒家的宽简之政与道的不为而为思想的混合物。
两家的改革主张,可以说是各有短长、利弊。
苏轼虽然缺乏王安石变法的激进性,但他稳健渐进的思想,又可以避免激进派操之过急以至苛峻扰民的缺点。
由以上三方面来看,苏轼的政治思想中既有进步和革新的一面,也有片面和偏于保守的一面,但从主导和本质方面看,他是主张革新的,是爱国爱民的,或者可以说他是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稳健的革新家。
他在仁宗、神宗、哲宗三朝政治上的表现,不是动摇,更不是随风转舵,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是在不同政治条件下,一贯固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的不同表现,同时也是他思想中固有矛盾的反映而已。
四
如前文所指出的,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态度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他对儒家有吸收,也有批判;
对释、道二家,也是有吸收,有批判。
但在积极从政和遭贬失意的不同时期,因处于顺境和逆境的不同,又有不完全相同的表现;
同时,他对三家又有意地加以调和。
从对社会人生的基本态度看,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是积极入世的,而释、道思想的主要倾向则是消极出世的,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
苏轼看到这种矛盾,在他政治上奋发有为、想望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他曾经批判过释、道思想。
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他说:
“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
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
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其真能然哉!
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
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
”指出佛老思想之虚空不着边际,很难实行,真的实行了,对“人主之名器爵禄”也是有极大危害的。
但在他处于逆境时,即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于实现而个人又遭受到排斥打击时,则又更多地接受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释、道思想中找到精神的寄托。
与上引的一段文字相反,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
“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
”这完全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
《庄子·
齐物论》主张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齐寿夭,认为“道未始有封”,即认为道是没有界限差别的,认为任何事物的差别和人们认识的是非,都是相对的。
苏轼所表现的,实际上就是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
而在《超然台记》一文中,他更阐发和推崇那种超然物外的思想,他说:
“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
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是谓求祸而辞福。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
”他认为美恶齐一,因而无所谓“去取之择”,这样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
而他之能“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可见他的乐天派的性格和生活态度,确实跟庄子齐生死、齐得丧、等富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但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上,而且主要在身处逆境需要排解内心苦恼的时候;
而在牵涉到政治,牵涉到国家的治乱兴亡时,他又是排斥和批判佛、老的。
如在《六一居士集叙》中,他说: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
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没有人能加以矫正)。
”因而大力推崇韩愈和欧阳修,认为以韩愈配孟子是相宜的,认为欧阳修“其学推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
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之。
他对儒学也是有所批判的,有所强调的。
他批判儒者强调性而忽视情。
在《韩愈论》中他说:
“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
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
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
老子曰:
‘能婴儿乎?
’喜怒哀乐,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
”但他反对空谈性,反对把情和性对立起来,“离性以为情”。
他认为儒学是近于人情的。
在《中庸论》中他说:
“夫六经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
”又在《诗论》中说:
“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
他还调和儒学和佛、老思想之间的差别和矛盾。
他认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有其相通之处。
在《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他说:
“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
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
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
”他批评《史记》中所说庄子诋訾孔子之徒是并不真正了解庄子,实际上“庄子盖助孔子者”。
“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意即实际上赞同而文辞上不赞同),阳挤而阴助之。
”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中,他甚至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并且肯定南华长老认为佛家虽是出世的,但与入世的儒家实际相通不悖的思想:
“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他却极力调和,可见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是要努力使儒、释、道三家熔于一炉。
对韩愈他是十分尊崇的,却批评他固守孔孟而不能吸收杨、墨、佛、老之学。
他说:
“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
何者?
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
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
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苏轼学习佛、老思想,虽然是想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境地,而实际上却是达不到的。
对于一般学佛、学道者的玄虚莫测,他是扬弃的;
他所重视和吸取的,是比较切近人生的实用的一面。
所以他说: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
”在本为玄虚缥缈的佛老思想中去追求一种简易、粗浅、实用,这是苏轼学佛学老的独特态度,也是他能将三家思想融通的又一方面。
他同陈述古谈禅理,曾有极风趣的“龙肉”和“猪肉”之比,是很说明问题的。
陈批评他所理解的禅理过于粗浅,而禅理照陈看来是比较玄妙精深的;
苏轼就将粗浅的比作“猪肉”,将精妙的比作“龙肉”,说:
“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
”当然,苏轼并不是一点没有受到佛家和道家的虚空、命定论等思想和人生观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也是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
如下面这样的诗句在他的诗集中就为数并不算很少:
“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
那于信仰间,用此委曲情。
”(《次丹元姚先生韵》)“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
”(《浰阳早发》)“宠辱能几何,悲欢浩无垠。
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
”(《用前韵再和孙志举》)等等。
由此可见,他对佛老思想和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基本上一样的,即为我所用,从自我需要出发,加以利用和改造。
五
从总的倾向和基本精神看,苏轼学习和吸收佛老思想,并不是为了避世,更不是出于一种人生幻灭,而是体现为一种人生追求。
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是超世俗、超功利的。
如果不是从表面上看,那就不难发现,他是吸收佛老思想中他认为有用的部分,并加以改造利用,以构建他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
这种境界是超脱的,因而也是自由的;
它的积极的意义在于,体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的升华。
他在《答毕仲举》中曾说:
“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
静似懒,达似放。
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
”这里讲的“静”和“达”,就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生境界。
这种境界,第一个层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世俗人生的超脱。
名利、穷达、荣辱、贵贱、得失、忧喜、苦乐等等,都是人生现实欲念所生出的一种羁绊和枷锁,到了“静”和“达”的境界,就从这种羁绊和枷锁中解脱出来了。
第二个层面,可以理解为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而变得无比的开阔和广大,可以不受尘世的污染,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包括极痛、极苦、极悲的境况之中)都能处之泰然,甚至得到一种愉悦和欢乐,得到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
但这种境界,在实际上充满倾轧、争斗、残害、悲苦、烦恼等等的尘世中,是很难找到,也是很难实现的。
因此,这种人生追求,常常只能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或理想,或者说只是一种想象,而作为一个诗人,这种追求和想象熔铸在他创作中,就变为一种艺术创造。
例如《前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超然台记》等等作品中所创造的,就是这种不受外物羁绊的、超旷的、自由人生的境界。
这是一种人生追求的艺术化,他所创造的,既是艺术境界,也是精神境界。
不过,从表面的超脱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隐含其中的人生的忧苦。
在“静”与“达”中,身处现实世界中的诗人,也不免时时露出挣扎的痕迹。
他所追求和构想的这种人生境界,除了熔铸为艺术境界,表现于许多杰出的作品之中以外,在诗文中还有不少对他自身内心体验的直接表述。
如说:
“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
”(《与孙志康》)“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
”(《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又在前引给子由书中说:
“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
此外万端皆不足介怀。
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
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吾作乐事也。
”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所说的,那种“私窃乐之”的“一念清净,染污自落。
表里翛然,无所附丽。
”的境界,不就是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获得了极大自由的人生境界吗?
正由于他对佛、老思想持这种态度,因此他能入亦能出。
许多人引用他的《和陶神释》诗:
“莫从老群言,亦莫用佛语。
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
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
”认为是他对佛、老思想的否定,或者说是由于在佛、老思想中得不到寄托排解而产生的一种信仰的幻灭。
其实纵观苏轼整个一生的人生态度,我们不妨说,他从早年到晚年,学佛学道,实在并未真正相信过佛、道所宣扬的那种虚无缥缈的仙山与天国,这些诗句只不过是表明,他对于佛、道思想同样不受其束缚羁绊,能入也能出而已。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认识到,佛老思想对苏轼文艺创作的影响,主导方面还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关于这一点,他在《送参寥师》一诗中有过非常鲜明的表述: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参寥是一位诗僧,他的思想已达于“空且静”的境界,但并非寂灭虚空,而是洞达群动的“静”,是包容了万境的“空”。
“卧云岭”的静观自身,同“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