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高考经典记叙文范文精选word文档良心出品文档格式.docx
《历年高考经典记叙文范文精选word文档良心出品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历年高考经典记叙文范文精选word文档良心出品文档格式.docx(3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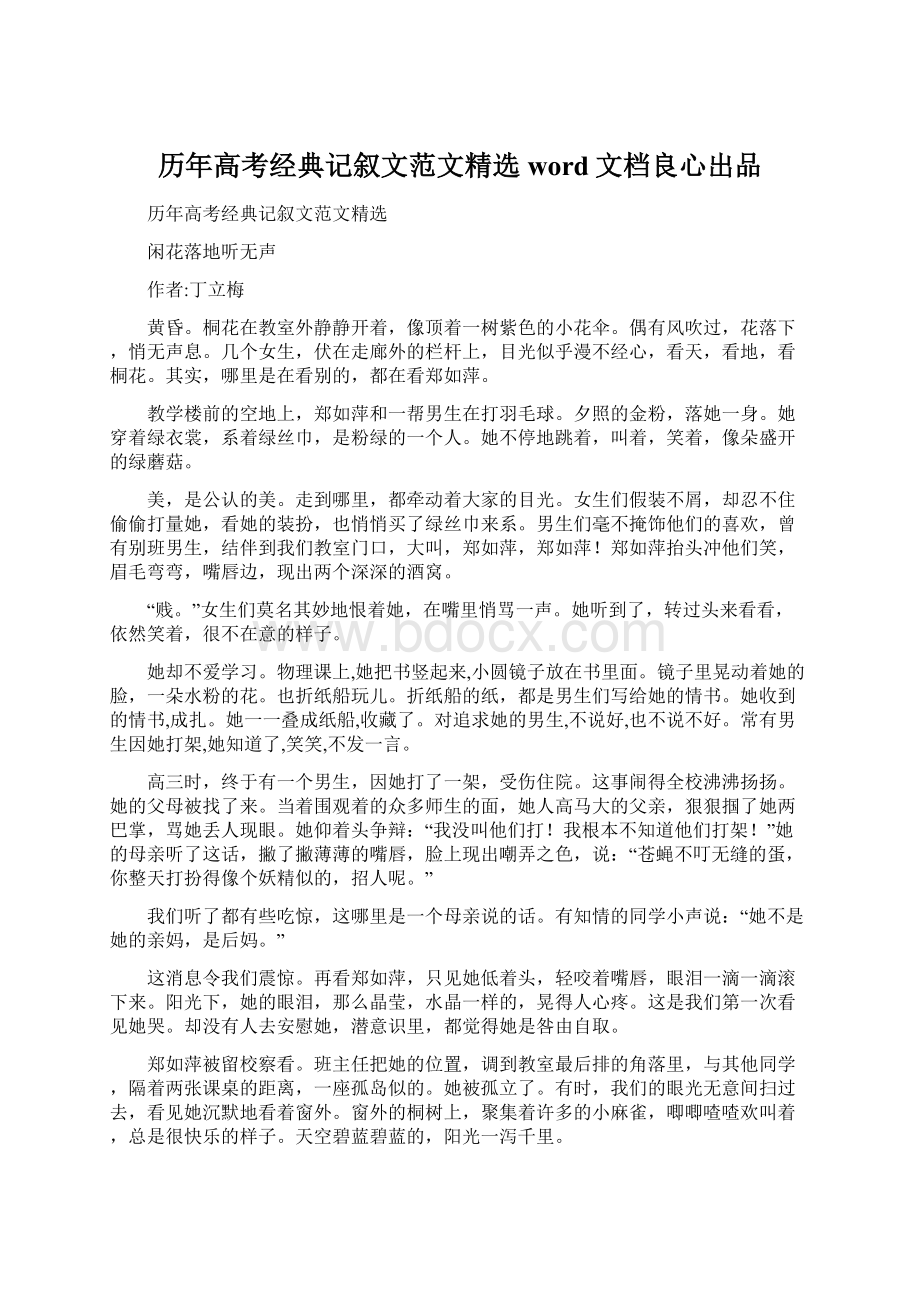
”
我们听了都有些吃惊,这哪里是一个母亲说的话。
有知情的同学小声说:
“她不是她的亲妈,是后妈。
这消息令我们震惊。
再看郑如萍,只见她低着头,轻咬着嘴唇,眼泪一滴一滴滚下来。
阳光下,她的眼泪,那么晶莹,水晶一样的,晃得人心疼。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她哭。
却没有人去安慰她,潜意识里,都觉得她是咎由自取。
郑如萍被留校察看。
班主任把她的位置,调到教室最后排的角落里,与其他同学,隔着两张课桌的距离,一座孤岛似的。
她被孤立了。
有时,我们的眼光无意间扫过去,看见她沉默地看着窗外。
窗外的桐树上,聚集着许多的小麻雀,唧唧喳喳欢叫着,总是很快乐的样子。
天空碧蓝碧蓝的,阳光一泻千里。
季节转过一个秋,转过一个冬,春天来了,满世界的花红柳绿,我们却无暇顾及。
高考进入倒计时,我们的头,整天埋在一堆练习题里,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堆里。
郑如萍有时来上课,有时不来,大家都不在意。
某一天,突然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郑如萍跟一个流浪歌手私奔了。
班主任撤掉了郑如萍的课桌,这个消息,得到证实。
我们这才惊觉,真的好长时间没有看到郑如萍了。
再抬头,教室外的桐花,不知什么时候开过,又落了,满树撑着手掌大的绿叶子,蓬蓬勃勃。
教学楼前的空地上,再没有了绿蘑菇似的郑如萍,没有了她飞扬的笑。
我们的心,莫名地有些失落。
空气很沉闷,在沉闷中,我们迎来了高考。
十来年后,我们这一届天各一方的高中同学,回母校聚会。
我们在校园里四处走,寻找当年的足迹。
有老同学在操场边的一棵法国梧桐树上,找到他当年刻上去的字,刻着的竟是:
郑如萍,我喜欢你。
我们一齐哄笑了:
“呀,没想到,当年那么老实的你,也爱过郑如萍呀。
”笑过后,我们长久地沉默下来。
“其实,当年我们都不懂郑如萍,她的青春,很寂寞。
”一个同学突然说。
我们抬头看天,天空仿佛还是当年的样子,碧蓝碧蓝的,阳光一泻千里。
但到底不同了,我们的眉梢间,已爬上岁月的皱纹。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有多少的青春,就这样,悄悄过去了。
我喊爸的那个人,不在了
碣石山
那个深秋,爸不断地咳嗽,全家人都以为是感冒,谁也没有在意。
况且大哥家正在盖新房,忙得两眼发黑。
隔了几天,爸的痰中带了血丝,找村里的医生来打针。
几天之后,还是发烧,咳嗽也没好。
医生说,去城里看看吧。
一天下班回家,才知道哥和姐夫带着爸去了天津肿瘤医院。
姐告诉我,爸得了肺癌。
记得当时我不敢哭,只是呆呆地立着,恐惧排山倒海一样压迫下来,压迫着心脏,钝钝地疼。
我看着姐,她早已满脸都是泪水。
我在爸做手术的前一天赶到天津。
爸手术后被推到监护室。
他瘦了许多,脸上的皮肤蜡黄,身体上插了很多的管子。
看着爸虚弱地躺在白色的床单里,像个无辜而无助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医生进来,让护士把爸翻到另一边,看他的伤口。
这时,我才看到,刀口从右前胸一直划到后背。
我忍不住泪水,替爸喊疼。
可怜的爸,看着他在疼痛的海洋中挣扎,像个溺水的人,我却无能为力。
我不懂厄运因何降临我家,恶魔偏偏选中爸。
他智慧而健康,在村里享有很好的名声。
早年做生产队长,承包到户之后,率先在村里造了一艘不大的船打鱼。
靠着他的聪明,我们家很快就富了起来。
爸总在每年快过春节时,提了酒和肉去给大队部看院子的孤寡老头送钱。
爸60岁的时候,买了一辆一万多块钱的摩托车,骑着它去港口收海货。
村里村外,甚至城里做生意的年轻人都知道爸,乐于和他合做生意。
爸从来不藏着掖着自己的本事,带着他们建立海产品批发基地。
我们都不相信,这样的爸会被病魔击倒。
早晨,我推着爸站在病房的窗前,看天津灰蒙蒙的太阳。
爸很安静,眼睛注视着朝阳,许久许久都不收回视线。
他忧郁得像个诗人,伤感充溢在他残破的胸腔内。
我握着他的手说,过段时间,咱们就能回家了,咱家的太阳比这里的清亮。
爸说,不知道还能看多少次日出,掰着手指头能数过来了。
听完爸的话,心里泛酸,泪水就收不住往外冲。
那天正好是十五,夜里月亮又圆又大,我站在医院的大院里,双手合十,抬头看着月亮,我对月亮说:
天上的神灵,我愿意减去5年的寿命给爸,求你让他多留在这个尘世一段时间陪伴我们。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春暖花开了,小院中白的梨花、粉的桃花争先恐后地绽放,爸却没有心情去看一眼。
因为疼痛在折磨着他。
右胸的癌细胞扩散成一个鼓包,突出出来了。
这一切似乎就注定了,上帝一定要收回父亲的生命,不可忤逆与违背。
如果不能帮他延长生命,不能代替他的疼痛,能够做到的,也只有让他舒服一些。
一直不相信有鬼神存在,爸病了之后,我宁愿自己相信。
尊敬所有的人,谦卑而恭敬,希望通过敬人得到恕己,痴想能感动神灵。
每次去医院买药,都要绕道行驶,去南城外果酒厂附近的一个小教堂。
看着高高竖起的十字架,祈祷爸的病能出现奇迹。
爸的身旁放着妈的老式手表。
疼痛来临,他咬着嘴唇,眉峰蹙起,右手捂着肺部的位置,一会儿侧躺,再翻过来。
不到一分钟,坐起来,把双腿盘在下面,前倾,膝盖支撑起整个上半身,左右摇晃。
我感觉到他几乎是屏住了呼吸,然后长长地吸一口气,伴随着瓮声的呻吟。
即便如此疼痛不堪,他也不曾忘记去看一下时间。
尽管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每一分每一秒地消失,对于他来说都是如此地昂贵与奢侈。
爸难得有个不疼痛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对于他和我们来说,简直如同过节。
这是全家最快活的时候。
牵着他的手去外面晒暖。
我和爸特别喜欢中午。
太阳一副吃饱喝足的状态,毫不吝啬地把阳光释放出来,暖意融融而不暴躁。
在充足的阳光下,这是个尘埃遍布的世界。
万物都在以自己的状态生存。
爸用一句文学语言,说出他的感受。
然后眯着眼睛坐在墙根,不再说话。
我注视着爸奇怪的表情,觉得他很孤单,慌忙给他按摩、揉腿,想打破这句话凝固的空气。
爸对我说:
“别忙了,歇会儿吧!
依着我还有个头儿。
”心头的刺,猛地跳出来,一下下地扎。
我知道为爸做这些小事是有尽头儿的,不知道哪一天,为他做些什么的权利也不再属于我。
而那一天真的来了。
那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节日的余温还在,孩子、老人、男人、女人、恋爱的情侣在阳光里欢笑、歌唱、说着缠绵的情话。
院子里嫩绿的黄瓜顶着小黄花往上生长;
还有开白花的瓠子纯情而优雅;
看起来甜蜜幸福的西红柿;
疯狂的蔷薇爬满了墙,一朵花对着另一朵花讲它的梦想……这是一个有颜色、温度、光亮、声音、气息的世界。
而我的父亲离开了—他为什么要离开呢?
我的眼睛看不到他的去路,我以怎样的方式和怎样的温暖,他才不会在黑暗中感到孤单与寒冷?
在他生病的日子,我甚至没有勇气和他坦诚地交谈,问问他是否害怕死亡。
无法想象他一个人,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那些日子里,如何抗拒恐惧,遏制那种即将消失在这个世界的想象。
我后来想,如果引导他说出来,和他一起坦然面对,比绝口不提一个“死”字,要好。
一天前,虽然爸不能说话,但他活着,我高兴。
仅仅一个瞬间,他温热的身体就没有了温度,我还能摸摸他的脸,也能得到些许的满足。
今夜之后呢?
这个真实存在过的躯体就不在了?
疼痛又一次袭击了我,我无法让自己安静地跪在爸的灵前。
想跑出去,跑到很远的一个地方,一个人,放声大哭,哭它个天旋地转,昏天黑地。
哀乐响起,殡仪馆的车来了。
车开动,房屋树木后退,缓缓驶出村庄。
公路两边是翠绿的庄稼。
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闪过,爸路过无数次,但今天是最后一次了。
村庄啊,请你记住,有一个人来过,他又走了。
我请求司机把车开慢点儿。
他们把爸抬下来,去那个大厅。
又一把锋利的短刀狠狠地捅了我一下。
我惶恐,心焦。
这一次,爸进去后就不会出来了。
这个在世上行走了65年的人就彻底不在了。
我使劲喊:
把我爸留下,不要啊。
可怜可怜我吧。
我不想没有爸,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可是没有人听我的哭喊,他们丝毫没有迟疑。
有人拼命地抱住我,紧紧抱着,我无法呼吸,疼痛窒息着我。
大脑一片空白,眼前是黑色的,那些人的叫喊在耳边消淡下去。
一会儿,大哥抱了爸的骨灰出来。
下车之后,我接过来抱着,骨灰还在烫热。
我把爸贴在心口,和他说话:
我们回家了,爸。
再走一次尘世的路。
这一次,我抱你。
妈妈的时间表
优 游
“生了孩子后,感觉很美吧?
”老有人这样问她,一开始,她也抬头挺胸:
嗯,好玩儿极了!
可日子长了,她笑不起来了,谁说当妈妈是最幸福的啊?
她开始怀念一年多前的时光。
那时,她是个了无牵挂的都市女白领,夫妻俩都在外企工作,家庭月收入一万多元。
日子过得充裕,每月能净攒8000元。
尝试过买最好牌子的化妆品和包包;
尝试过出国旅游;
还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番……折腾完了体验过了,空虚的感觉还在,她就跟老公说:
“得,养孩子吧。
“那你得掂量清楚了,至少得花50万元。
幼儿园赞助费,中小学择校费,出国留学……”老公掰着指头一一数来。
“行了行了。
咱俩都年轻,工资只会往上走,一年攒8万元问题不大,50万元,几年就搞定。
比咱穷的人都有家有口的,咱俩还养不活一个娃?
”她的妈妈也自告奋勇,要来北京带外孙。
刚出产假,她就忙着打电话联系客户,竞争这么激烈,客户跑掉了怎么办?
可不知怎的,效率竟比以前低了许多,好像什么事都没干,就到深夜了。
怎么回事?
一天,无意中拿起月子中的记录本,她大吃一惊:
1∶00~5∶00哄宝宝睡觉;
5∶00母乳;
9∶00~12∶00出去晒太阳;
17∶00宝宝喝粥;
20∶30给宝宝洗澡;
21∶00配方奶。
天啊!
原来时间都分配在这些婆婆妈妈、屎屎尿尿上面,真不值得!
可当她把想法一说,以前千依百顺的老公,竟激动地嚷嚷起来:
“你这亲妈,连后妈都不如!
一句话,把她的眼泪勾了出来!
后妈会为孩子疼得死去活来吗?
会为他的未来拼命工作吗?
错在哪儿了?
她想不明白。
一天,看见她在电脑前发呆,妈妈走了过来:
“忙啥呢?
“在定时间表,太紧张了。
”说到这儿,她忽然心念一动,问妈妈:
“从小到大,我看您都不慌不忙的样子,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有啥子可忙的哟?
”妈妈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在她的一再要求下,老人用围裙擦擦沾着水珠的手,接过笔歪歪扭扭地写下一份古老的时间表:
23岁7月,生下囡囡。
8月,背着囡囡下地,田里忙;
24~27岁,把囡囡放田埂上。
一边插秧忙,一边唱山里的歌;
27~37岁,给囡囡洗衣服、做饭、扎小辫;
37~50岁,给囡囡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
55岁到现在,给囡囡带小囡囡……
看到这里,她的眼睛湿润了。
以前,她以为,做一个母亲,赚钱供宝宝花销就够了,所以,她满不在乎地拼命工作,很心安。
可妈妈的时间表,让她懂得了:
所谓母爱,就是照顾、陪伴、关爱孩子。
一味着眼于未来给他更好的成长条件,拼命挣钱却错过孩子成长的关键期,是多么不合时宜。
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最好的礼物,就是妈妈的陪伴。
(黄如玉摘自《婚姻与家庭》2008年2月下半月刊)
一路逃不掉你
安 宁
那时他与母亲,尽管并不相爱,但在平淡琐碎的生活里,还是有些许的明亮。
这样的光亮,犹如阳台上许久没有打理的一盆花,在晦暗里,悄无声息地开着小朵小朵纯白的花儿,你于忙碌之中,不经意间扫上一眼,会觉得心内欢喜。
我记得冬日里我步行回家,每每快到家时,最期盼的,便是看到他站在当街的路口,等我飞奔过去。
同行的孩子们嘻嘻哈哈地散去,我则哭哭啼啼地将手交给他,任由他用力地握着,牵回家去。
这样冬日的一抹橘黄色的温情,被我记忆的长镜头探伸过去,定格在岁月颗粒质感的胶片上。
之后他与母亲争吵不断,在离婚的路上,不再能顾及我的冷暖。
而我,也在他日渐与我疏离的微凉中,生出恨意,甚至,刻意地将他忘记。
那一年他买了摩托,打算周末的时候,去我读书的县城拉散客赚钱。
彼时我住校,恰好车站就在学校旁边,所以每到下课,我隔墙听见马路上穿梭而过的摩托,常常就出神。
他极少在我与母亲面前,提起在县城所受的种种委屈。
母亲与他一样脾气暴躁,并不怎么关心他在外奔波的辛苦,只一味抱怨他挣钱太少,连买一件漂亮衣裙的钱都没有。
他每次听到,都要愤怒地摔东西发泄,甚至连我,都不再避讳。
有一次,他正与母亲争吵,我周末放学回家,一推门,一个杯子擦着我的额头,在身后的门上碎裂开来。
我与他,彼此注视着,足足有5分钟,没有一句话。
他双唇微微地动着,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我却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便抖一抖落在脖颈中的玻璃碎片,径直走入自己的房间。
那个春天的午后,我在抽屉中,无意中翻看到了那张无情的纸。
他在上面写着,等到一年后我考入大学,他们将协议离婚,我将跟随着母亲生活,他除了供我读大学的费用,还会给我和母亲每月的生活费,直到我大学毕业后可以挣钱养活母亲。
我当着他的面,将那张纸,撕得粉碎,而后我冷冷地告诉他,我不用他养活。
他第一次过来拉住我,说,丫头,别这样……
我不等他说完,便将那双有些陌生的粗糙的大手,重重地甩开去,头也不回地,拎起书包,大踏步地走出了家门。
我在学校里,住到弹尽粮绝的时候,去找母亲讨钱。
母亲劈头撂下一句:
“找那个要甩掉我们独自过的男人要去!
”我一扭头,说,用不着你们任何人!
我很快地找一个小混混,借了一笔钱,而后打算远远地离开这个小城。
我不知道火车能够载我去哪个城市,但我却清楚,火车驶得越长,我与他之间的距离也越远,远到我可以将他给予我的一切,都忘记。
我一个人背着书包,在邻城下了火车。
陌生的环境,与离家的欢欣,让我有短暂的新鲜,但随即而来的,便是被人盯视的恐慌与不安。
我随便租了一个地下的旅馆,买了一大堆零食,而后缩在隔音效果很差的房子里,漫无目的地翻一本书。
我捧着书,很快地在冷硬的床上睡过去了。
再醒过来,已经是天亮,翻一下身,觉得昏沉沉的,摸一下头,很烫,这才知道是感冒了。
挣扎着起身去前台要一杯热水,服务员给我倒上,又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问我,你是邻城高中里过来的学生吧?
我毫无防备地点一下头,她若有所思地看我片刻,便又低头,去忙别的。
半个小时后,有人敲门,打开来,他便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想要逃开,却被他一把抱住。
我踢他捶他,甚至想要像一只小狗一样地咬他,可他却像儿时在风雪中等我扑过来那样,丝毫不动地挡住了我的去路。
一路上,他始终没有提起他如何骑着摩托,顺着火车的方向,追赶着我,又如何找遍了邻城的每一个旅馆。
我一直记得那一年的春天,桃花开得格外地热烈,路边的木槿与连翘,也孜孜不倦地盛放着。
我在他刻意营造的幸福中,有些恍惚,似乎,我真的可以凭借这一次的出走,赢取我想要的未来。
可是我却忘记了,春天会很快地过去,那些怒放的花朵,也总有一天,会逆着春天的方向,枯萎凋零。
我在他许诺的美好未来里,安静地读书。
他在那一年中,像所有尽职尽责的父亲一样,在周末骑着摩托,载我回家改善生活。
摩托开过的声音,在我听来,不再那样地刺耳,而是慢慢如一首曲子,我隔着校园高高的墙,听见了,觉得有一股暖流,漫溢过我的心田。
一年之后,我拿到了省城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同时得到了他们离婚的消息。
我依然记得他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扭身过去,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终于没有能够阻挡住他要离去的脚步。
而他,也没有能够阻挡住我拒绝再与他见面的执拗。
那一个暑假,他在县城租了房子,拼命地打工赚钱,为我挣开学的学费。
我依然记得那个初秋的午后,我即将踏上去省城的火车,提了大大的行李包,在候车室里坐着,他突然就朝我走了过来,而后将一沓钱塞进我的书包。
我等他开口,他却慌张地转身便要离开。
然后便有一群人,气势汹汹地赶过来,一边高喊着:
别让他跑掉!
一边朝他围拢过来。
那些人,使劲地踢他,骂他,说他这一个月,一次次厚着脸皮,违反行规,抢别人的活干。
而他,则无声无息地抱着头,任由他们打骂,一直到警察赶过来,将那些人带走。
我在人群的注视之下,径直地朝他走过去,而后,在他还没有开口之前,将他紧紧地抱住。
他手足无措地轻拍着我的后背,说,丫头,爸没事,爸只是想多挣钱供你读书,爸……
我听他语无伦次地絮叨,像母亲嘴里抱怨的世上最无用的那个男人,又像许多年前的冬天,我们依偎在一起说,我要让你,做我一辈子最温暖的手套。
母亲和那口老掉的井
谢 云
入夏后,一个多月时间,持续艳阳,持续高温,滴雨未落。
母亲从老家来信,说“天干得很”,包谷蔫了,树叶萎了,村前那条河,断流了,连屋后那口井,也快没水了。
那井,就在我家屋后,这些年来,一直被我深情眷念着,清澈、甘洌、幽深,仿佛将永远长流。
我渐渐觉察,自己的许多作为,似乎都与那井有关。
而现在,它居然就这样老了。
那一天,接到母亲来信的那一天,得知那口井老了的那一天,它的形容、情调、场景,竟又一次在记忆里清晰。
那清冽的水,素色的青石板,紧挨着的穷人的家,屋顶上袅袅升起的一柱柱炊烟……我跟着那气息走了回去。
在薄暮中,在柴烟弥漫的一天结束时。
井水没了,那口老井,或许真是老了。
就像一丝涓细的泉流被堵塞,被淤埋,我忽然想不起下面该有什么内容。
我只是莫名地想到母亲,在乡下奔波操劳的母亲。
然而,父亲上次来我这里时说过:
“你母亲这两年,又老了一大截,头发也白了许多。
记忆中,母亲是有过一头茂盛的长发的。
乌黑,柔软,油亮,光洁。
那是她的骄傲,是她在乡村里的旗帜。
母亲喜欢它们,疼惜它们。
即使最困难的年头,她也把它们梳洗得一丝不苟,呵护得无微不至。
我一直记得,小时候,再忙的时节,从田地里,或山坡上归来,洗脸或洗手后,母亲总要抚点水在头上,然后认真梳理,到一丝不乱了,再将它们精心编成两条粗大的辫子。
劳作或奔走,它们就在母亲肩上,在田边或地埂,在蜿蜒的村道上,一晃一晃地荡着秋千,像极了母亲当年的身影:
活泼,轻盈,欢跳。
后来,父亲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你母亲每次洗头,都是蹲在井边,用一大盆水,将头发漂着,用皂角荚浸润。
这让我总禁不住想象,在那些岁月里,这该是怎样一种风景:
黑发披垂下来,该是多么闪亮的瀑布,而当它们飘扬,也该是微风柔柔拂过湖面的感觉吧。
苦难的岁月,艰辛的生活,把母亲磨砺得那么粗糙,泼辣,强悍,唯有那一头黑黑的秀发,似乎远离了生活的困厄和挫顿,一如既往地,在乡村里柔顺着、飘拂着。
然而,自几个妹妹依次出世后,母亲就不再蓄发了。
她剪了便于梳洗的短发。
早晨起来,只需用手蘸水,略微抿抿,再蓬松零乱,也变得顺溜了。
贫困,劳累,鸡鸭猪狗的忙乱,养儿育女的烦杂,使她早早告别了年轻和爱美的心境。
像她的头发一样,母亲提前进入了枯涩的中年—而那时,母亲还不到30岁。
现在想来,母亲那时实在太操劳了。
从我知事起,家里家外,大烦小事,都得靠她奔波,操持。
父亲一直体弱多病,几乎是母亲一个人,撑持着我们的家,撑持着那方遮风避雨的天空。
她的一生,始终在为我们操劳、操心。
起早贪黑,含辛茹苦。
她像母鸡一样,护卫着她的鸡崽。
孩子长大后,却鸟儿一样飞走了,只有节假日才能回家看看。
而母亲,仍像一只窝旁守候的老鸟。
她牵挂的心,始终那样悬着,被我们牵扯着,放不下来。
儿子出世后,我常常在想,母亲究竟是什么?
想不出明确的答案。
我只知道,那个在下雨的黄昏,在路的尽头,满眼焦灼,静等迟归孩子的人,是母亲;
那个把叮咛缝进鞋垫,把牵挂装进行囊,把所有慈爱写在心底的人,是母亲;
那个在孩子面前不流泪,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为孩子辛苦奔忙,毫无怨言的人,就是母亲—我只知道,这世上有一个最伟大而最平凡的女人,那就是母亲。
而在我懂得爱人的时候,我最爱的人,便是母亲。
在我仅有的文字里,写得最多,最富感情的,也便是母亲。
我在远离她的地方,通过文字诉说,感叹,但母亲只是默默奔忙,像深井一样沉默。
自读大学后,我在家里待的时间,就一年比一年少,离家时,走得也一年比一年仓促。
偶尔回家,母亲总是格外高兴,不知疲倦地在菜园、井边和灶台上忙活,为我们做饭,给我们炒菜。
在母亲,或许这就是最快乐、幸福的事。
记得前年春节,早早写信回家,告诉了母亲行期,却没料到,接连不断线的事情跟在脚边,弄得我一时半时动不了身。
待好不容易做完事,回到家中,差不多已是预约时间一周以后。
刚进村口,就有乡邻告诉我,你妈天天到街上等你们,把垭口都望矮了。
未能如期而归,母亲该是如何着急,这我能够想象。
但当我带着风尘和一脸歉意,出现在母亲面前,她却只说了一句:
“回来了就好。
”我所有的歉意,凝为泪滴落下来。
也就是那时,猛然看见母亲头发中间,凛然生出一撮撮白发,像春天黛青的远山阴影里的一抹抹残雪。
这不经意的发现,在我心里,不啻一次剧烈的山崩或海啸。
近年来,母亲常说,她眼涩了,手钝了,缝东西时,穿针都很困难了。
而我记得,母亲的手脚,曾是全村里最快的,母亲的针线活,是全村最出色的。
无论她缝制的衣服,还是衣服上打的补丁,都会惹得别人夸赞。
小时候,每年春节前,母亲都要给我们几姊妹做鞋。
那时,她的眼睛明亮如镜,她纳的鞋底,针脚又细又密,鞋帮和鞋底,都有好看的花纹。
可是现在,她却连穿针引线,都感到困难了。
“本来想给孙娃做两双鞋的,眼睛看不清了。
”母亲声音里,有些无奈和惶。
我听了,鼻子酸酸的,眼睛涩涩的,直想哭。
为母亲的苍老,也为自己的粗心。
虽然我早知道,南来北往人自老,白发取代青丝,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
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忽略了母亲的变化。
每次想到她,浮现眼前的,总是年少时看到她的样子:
精神,精明,能干。
数十年如一日,母亲一直辛苦奔波,承忍,一直为我们提供着温暖和关爱。
那样的自然而然,让我们以为,她会一直如此。
让我们一点儿也没觉察到,她会一年比一年老;
她的皱纹,会一年比一年密;
她的头发,会一年比一年白。
也许,我是真的太大意了。
连七岁的儿子都知道,世界上一去不复返的东西是时间,我怎么就没在意呢?
就像那口沉默在屋后的井。
那井水,一直那么清澈,纯净,一直那么源源不断,让我们从没想到,它也会有枯衰的一天,也会有再不能让我们汲饮的一天。
记得,读过台湾诗人琼虹的一首诗,叫《妈妈》:
“当我认识你,我十岁/你三十五。
你是团团脸的妈妈/你的爱是满满的一盆洗澡水/暖暖的,几乎把我漂起来……等我把病治好/我三十五/你刚好六十/又看到你,团团脸的妈妈/好像一世,只是两照面/你在一端给/我在一端取/这回你是泉流,我是池塘/你是落泪的泉流/我是幽静的池塘。
或者,对我们而言,母亲就是那不停地供我们汲饮、滋润着我们心田的一眼井。
(许晓红摘自《四川文学》2008年第10期)
你是我们的孩子
叶 子
我从襁褓中的婴孩蜕变成一朵美丽的花,而数年如一日娇惯我、疼惜我的外公,却经不住岁月的蹉跎,渐渐失去力量,丢失记忆,成为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孩子。
1
外婆去世后,外公病了。
他的精神时好时坏,总黏住妈妈一个人。
快放暑假时,妈妈很焦虑。
公司安排她去北京学习,她丢不下外公。
我早就对她有意见,觉得是她惯坏了外公。
爸爸常年出差,妈妈独自包揽外公的大小事务。
一年时间,我就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