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事作者于德北Word文档格式.docx
《城事作者于德北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城事作者于德北Word文档格式.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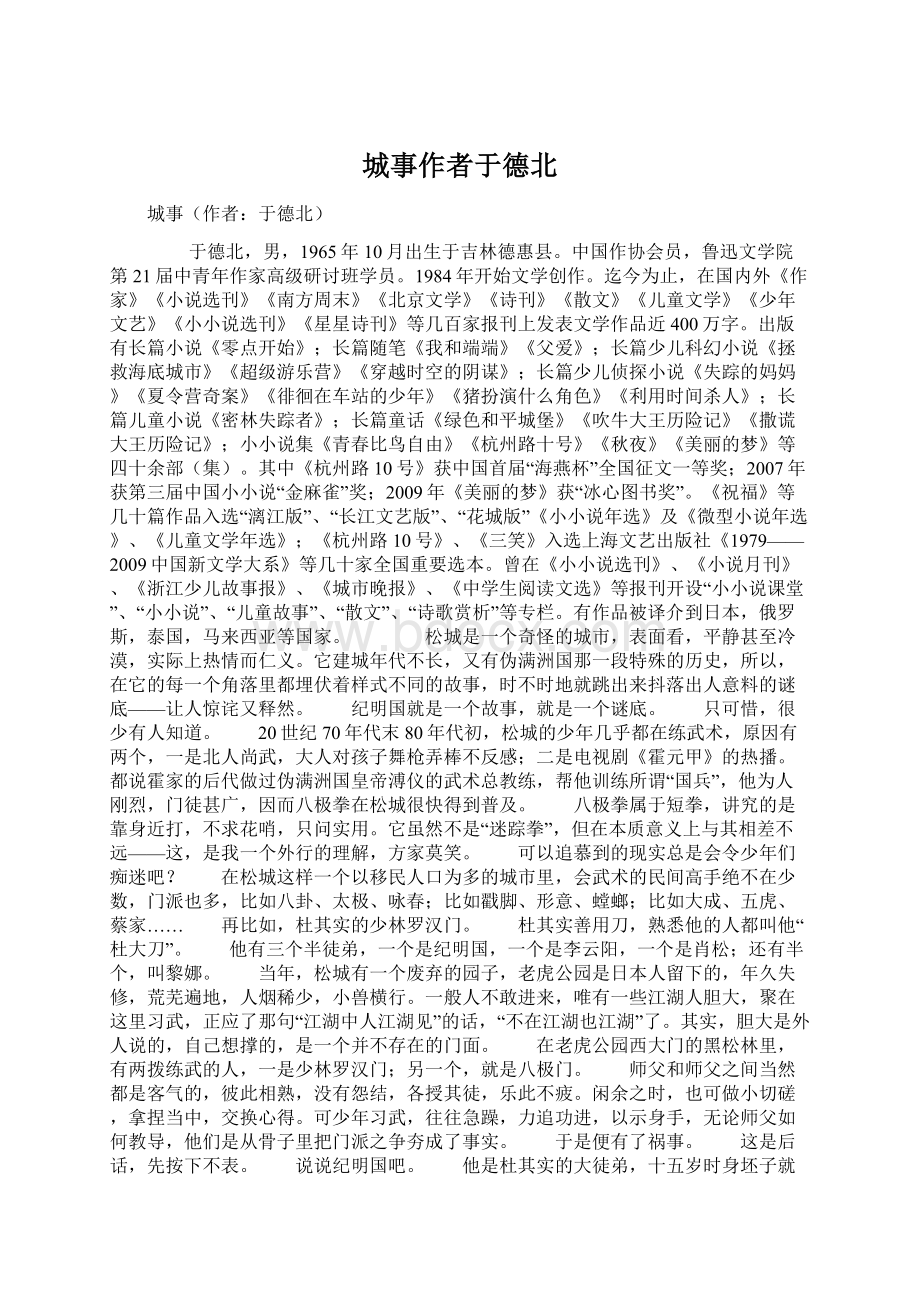
他有三个半徒弟,一个是纪明国,一个是李云阳,一个是肖松;
还有半个,叫黎娜。
当年,松城有一个废弃的园子,老虎公园是日本人留下的,年久失修,荒芜遍地,人烟稀少,小兽横行。
一般人不敢进来,唯有一些江湖人胆大,聚在这里习武,正应了那句“江湖中人江湖见”的话,“不在江湖也江湖”了。
其实,胆大是外人说的,自己想撑的,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门面。
在老虎公园西大门的黑松林里,有两拨练武的人,一是少林罗汉门;
另一个,就是八极门。
师父和师父之间当然都是客气的,彼此相熟,没有怨结,各授其徒,乐此不疲。
闲余之时,也可做小切磋,拿捏当中,交换心得。
可少年习武,往往急躁,力追功进,以示身手,无论师父如何教导,他们是从骨子里把门派之争夯成了事实。
于是便有了祸事。
这是后话,先按下不表。
说说纪明国吧。
他是杜其实的大徒弟,十五岁时身坯子就定了型,车轴汉子,横竖上下一边高,所有的人都把他当成一个木箱子。
他祖籍河南,幼年随父母移民松城,定居在黄瓜沟的南分水线上,住的是半阴半阳的地窨子。
他的父亲在市政工程处工作。
纪明国毕业后在运输队干临时工。
干的是杂活。
李云阳、肖松、黎娜的情况与纪明国相差无多。
他们是小学同学、邻居,李云阳和纪明国上了同一所初中,而肖松和黎娜在另外一所初中学习。
初中毕业后,李云阳去了稍远的一所中学读书,肖松、黎娜就读于离家较近的一所高中,同班同座,于是,顺理成章地成就了早恋。
肖松和黎娜早恋了。
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后来他们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孩子。
这和纪明国有什么关系吗?
当时还不知道。
运输队在老虎公园的西北角,占据了很大一块地方,它的门是斜开的,正冲着西北方。
运输队的车出来,要么向西行,上斯大林街,寻找它必去的方向;
要么上衡阳街,奔自由路,当然也可以去解放路,或者沿着阳泉路东行,经过臭气熏天的印染厂,转入某条小街,在颠簸的路面“多快好省,大干快上”。
20世纪80年代的松城,苍白得很。
就是在这看似苍白而空旷的维度里,纪明国遇到了杜其实。
纪明国的家和运输队只有一条衡阳街相隔,但他从工作之初在队里住宿之后就再未回家住过。
家里太拥挤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地窨子里,住着姐姐、弟弟、妹妹、父母,简直透不过气来。
十五岁离家,他感觉自己像陀螺一样解脱,终于可以按主观承诺一切,并获得自由自在的呼吸。
杜其实是队里的锅炉工,在那个年代,锅炉工无论如何优秀,如何尽职尽责,夏天都是要回家的。
但杜其实不必。
他有一套猎猫的功夫,这在队里备受推崇。
用细铁丝做套,放在地沟里,佐以饵料,总有收获。
这种收获是全队的喜悦,在那个少肉的年代,吃肉是人的本能追求。
因为这个技能,杜其实一年四季都住在队里。
纪明国年纪小,没有人愿意和他住在一个宿舍里,即便床铺空着,那些师傅们也会不耐烦地催他回家,因为他家近,队里没有给他安排固定的房间。
他可以睡任何空床,所以,实际上他的住宿问题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流浪状态。
直到有一天,杜其实喊他,他才真正有了安身之所。
杜其实在自己的锅炉房给他打了一个地铺——木板隔地,上边是草垫子,再上边是门帘子,加一条旧床单。
杜其实说:
“回家取自己的被吧,还有枕头。
” 就这样,他们有了开始。
就这样,在朦胧中,纪明国知道杜其实是一个武术家。
那天夜里,纪明国被尿憋醒了,他从地铺上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走,一脚绊在大块煤上,险些跌了一个跟头。
这一跌,彻底清醒过来,他听见锅炉里的煤在嗞嗞地暖响,细分辨,除了煤的响,还有一种声音,既来自锅炉房内,又来自锅炉房外,不压抑但沉闷,不开放但热烈,像煤块,更似煤核,一下一下地吸纳着冷气,又绝对不容置疑地保持着自己的热度。
纪明国的尿一下子没了。
是十月,外边大霜降。
纪明国回头看一眼杜其实的床铺,一堆被子蜷在枕头边;
他又看了看煤堆,铁锨坚硬地插在那里,这是杜其实填火的姿势,填一次四锨,然后铁锨停在下一次行走的开端。
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冲动,想独自面对一些问题,这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自始至终都无从明了。
他轻轻地掀开门帘,将半个脑袋探了出去。
这时,他看到的场景完全是他意想不到的了。
外边一片银白。
月亮是白的,大地是白的,树木是白的,汽车是白的,地上的一根细小的草棍是白的,就连老虎公园的墙头也是白的。
但是,有一个影子是绿的,他手中的刀也是绿的。
其实应该是黄的、蓝的,但是,因为周边的一切都是白的,所以,他们或者它们的本质都被染绿了。
这无妨,黄的绿,绿的蓝。
融合成一道细窄的链子,砍,挑,劈,刺,挂,撩,扫,压,崩,缠头裹脑地把所有的固定的物体都震乱了。
包括纪明国的心。
纪明国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叫了一声:
“师父,我想和你学武艺。
” 杜其实收了刀,大气不喘地应了一句:
“起来。
填煤去。
” 纪明国的尿一下子就出来了。
那以后,纪明国就成了杜其实的大徒弟。
杜其实一生不婚,原因只有一个,养不起。
他只养父母,用自己做临时工的工资。
他的父亲爱吃肉,但他从不猎猫给父亲吃。
每月开工资,他便去红房副食店买一小条五花肉,在运输队给父亲炖好,然后借一辆自行车,飞快地送回家去。
纪明国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在队里炖。
他的回答很简单,省火。
纪明国想了想,笑了。
从那时起,他每天早晚随杜其实练功。
扎马,压腿,踢腿,下腰,旋风脚,旋子,双飞燕,小架,趟子,一样样的都有,就是没有他最想学的套路和刀法。
他不急。
他为什么不着急呢?
好像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一切都急不得。
后来,李云阳加入进来,再后来肖松加入进来。
肖松一进来,自然不能落下黎娜,所以,黎娜也进来了。
但是杜其实不收黎娜为徒,他说女孩打不了罗汉拳。
他的说法对与不对且不讲,黎娜可以和大家一起练功,却在杜其实这里注定拿不到武术真传。
除了纪明国,李云阳、肖松和黎娜只能每天晚上来练功。
平时他们课多,在高考的独木桥上,无论真假,每一个学生都不能也不敢松懈自己的心劲儿,不管未来的结果如何,他们都得要求自己哪怕是下意识地付出努力。
可是因为爱好、友情、梦想与憧憬,他们又恋恋不舍地在鲤鱼打挺和空翻中获得身心的沉醉、自豪与轻松。
真是这样的。
下面,再说一说黑松林吧。
运输队在黄瓜沟的北岸,而黑松林在其南岸,是老虎公园存留下来的最大的一片松林。
黑松是松树中一个比较独特的品种,因植株高大、挺拔、粗壮而著称。
前面说过,当年的老虎公园是废园,一般人是很少涉足其中的,杂树丛生,荒草高密,即或艳日高照,也时有耸闻发生,所以,在晚间进入园子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习武之人。
杜其实的场子在黑松林的中部,八极拳的场子在黑松林的东部。
实际上他们交会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因为八极拳天未黑便收功,而杜其实几乎是天黑了才入西门。
原因很简单,要下班,要吃饭,要写作业,待一切完成,基本就八点了。
扎马,下腰,压腿,踢腿…… 经年不变。
有的时候,杜其实会走一趟刀,那么,黑松林一定就变白了。
杜其实是不允许他的徒弟吃猫肉的,尽管传闻中猫肉如何细腻、鲜美,尽管李云阳和肖松也有所冲动,但是,杜其实的一句话便给他们上了紧箍咒。
那句话是:
“你们谁敢再动猫的主意,就趁早给我回家里去。
” 那是一个星期天,学校里没有功课,李云阳和肖松坐在老虎公园的大墙上,畅想着未来的生活。
李云阳是要上大学的,他父亲来松城不久就因工伤去世了,他和母亲一直享受着市政工程处的解困金,他的理想充实又简单,考大学,分配工作,然后带着母亲和自己一起生活。
肖松要悲哀一点,他和黎娜的学习成绩均一般,很难通过预考,不能通过预考,那么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提前离开校园,把身份改换成待业青年,好的话考工,不好的话接班,再不好的话就当个体户,开个小馆子,自食其力,养活自己。
因为有了这样明晰的概念,肖松反而有了另外一种更为有力的轻松,他要和黎娜成为两口子,一辈子生活在一起。
可是,悲剧的效果总是令设置悲剧的人自觉可笑。
肖松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纪明国是如何爱黎娜。
包括黎娜自己。
记忆中黎娜是1979年6月15日那天在学校的操场上跌倒了,她跳皮筋“老高”一级的时候奔跑不当,即将侧翻的时候将脚踝扭伤了。
她的脚向内转动了至少二十五度,脚面几分钟之内就肿胀成了红萝卜。
所有的同学都束手无策,而所有的老师都回家吃饭去了。
李云阳问肖松,怎么办呀?
所有的女生都在哭,她们觉得自己就是皮筋,正因为她们的存在,才使黎娜受到了游戏的伤害。
就在这时,纪明国冲了过来,他二话没说,背起黎娜就跑,先是往家跑,跑了一半,又折转身往回跑,跑向自由路,跑向师大医院,最后把黎娜放到了外科病室的诊床上。
在他的身后,是一百个小学生组成的长长的队伍。
1979年6月15日。
谁能记得这个日子?
谁又能知道这一天发生了什么?
迄今为止,恐怕只有并不存在的纪明国自己清清楚楚地记得。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接着来讲这个毫不脱俗的故事。
李云阳和肖松坐在老虎公园的大墙上。
李云阳问肖松;
“你家几天没吃肉了?
” 肖松说:
“不知道。
”停了一下,反问:
“你家呢?
” 李云阳说:
“除了过年,我家不吃肉。
” 肖松半晌没说话,他抬头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地,突然说:
“你去喊黎娜,告诉她,晚上我让师父给咱们炖肉吃。
” “真的?
”李云阳睁大了眼睛。
“真的,快去吧。
”说完,肖松一挺身就跳进了公园里。
仅仅二十分钟后,当李云阳和黎娜神秘兮兮地站在纪明国的面前欲言又止故弄玄虚的时候,肖松回来了。
他的手里拎着两只肥大的野猫,一前一后地丢在了李云阳的脚下。
“师父呢?
”他问。
“回家去了。
”纪明国回答。
“啥时候回来?
” “还得一会儿吧。
” 肖松不再说话,拎着猫来到院外,往木柱的铁钩子上一挂,开膛,剥皮,水洗,改块,一丁一丁地丢进师父炖猫的小铝盆里。
葱花,姜,花椒,大料,酱油,盐,一样不少。
他麻利地把两只猫给炖了。
香味很快就飘了出来。
猫肉的香味一飘出来,运输队的师傅们便得了信号一般,纷纷从自己的房间跑出来,他们拿着酒,端着碗,把刚刚买来的豆腐、鱼干、罐头、咸菜统统拿出来,一股脑地丢在乌黑乌黑的货板上。
今天是开支的日子,他们原本就闷着劲儿准备大喝一通呢。
纪明国也开支了,不少,四十七块三毛六。
在几个师兄弟当中,他是令人垂涎的富翁。
猫肉快熟的时候,杜其实回来了,他一进院子,就呆立在那里,待见到三个半徒弟和铝盆的热气时,他突然把自行车往墙边一推,一个箭步就跳了过来。
“谁?
”他喝问。
“我。
”肖松说。
他猛地举起手,又猛地放下,他猛地转过身,又猛地扭过脸,两条横眉直立,一张阔嘴紧绷,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走!
” 他在前边走,三个半徒弟在后边跟,这个奇怪的阵势并未引起师傅们的重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用筷子试了一下猫肉,然后夹了一块“稀稀溜溜”地丢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
“熟了,熟了。
” 众人哈哈大笑,十几双筷子一同向口水的集合处探去。
肖松的手艺从此广为流传。
他无意中成了一位炖肉的大师傅。
杜其实带着徒弟们走出运输队,站在老虎公园的大墙边,他沉默良久,终于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吗?
纪明国、李云阳、肖松和黎娜分明听到了他腹腔里发出的丹田之声——你们谁再打猫的主意,就给我滚回家里去。
今天晚上不练功了。
杜其实回去了,几个徒弟不知所措,茫然相望半晌,决定各回各家。
可是,各回各家干什么呢?
孤独地坐着吗?
还是忧伤这个不知所措的结局?
这时,纪明国的母亲突然出现在马路对面,她高声地问纪明国:
“你开支了吗?
” 纪明国点点头,说:
“开了。
” 他快速地走过马路去,把手心里汗湿的钱亮在母亲的眼睛里。
母亲笑了,伸手去拿,纪明国突然又收了回来,他从中揭开一张,放进口袋里,然后把余下的钱重又往母亲的手里一塞。
“纪明国,你疯了吗?
”母亲大叫。
纪明国说:
“妈,这个月我不回家吃饭。
”说完,他像师父刚才一个箭步跳到盆边一样,跳过马路,跳到李云阳、肖松和黎娜的面前。
“妈我没疯,我要请他们吃饭。
” 于是,他们去了饭店。
前边说的祸事发生了。
那天,他们去了自由路和斯大林街交汇的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盘肉末豆腐,一盘姜丝肉,一盘肉炒尖椒,一盘锅包肉,一瓶白酒,一瓶“小如意”,痛痛快快地吃喝了一顿。
那是他们第一次在一起喝酒,也是最后一次在一起喝酒。
吃饭之前,他们就向老板借了一个饭碗,把每一样菜都拨出一点留给杜其实,他们心里明白,师父是爱他们的,所以,他们也爱师父。
吃饭间,李云阳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并哭着说:
“肖松其实完全是为了我。
” 平时就话少的纪明国推了他一下,说:
“那你还哭啥呀,快去,把这碗菜给妈先送去,快!
” 李云阳犹豫了一下,依旧哭着端起饭碗跑了。
看着他的背影,肖松和黎娜都含着眼泪笑了。
接下来,纪明国讲了一个关于杜其实的故事。
他说:
“你们知道吗?
师父每次炖的并不是猫肉,而是兔猫。
” 兔猫就是野兔。
那天夜里,纪明国又被尿憋醒了,他习惯性地翻身起来,头也不回地往锅炉房门口去。
这是春末夏初,空气里荡溢着植物的芳香。
植物的芳香是有潮湿气的,所以,黄瓜沟南汊的堤坝成了他最喜欢排泄的地方。
地环儿、红蓼、接骨草、打碗花勾连成片,又各自分割领域,它们同生同死,季季不曾分离。
月亮是红的。
聚精会神地俯瞰众生。
风吹来,纪明国的身上凝成了大大小小的露珠。
他又一次听到了异常的声音,似人非人,似兽非兽,人兽交混,又泾渭分明。
他循声望去,尿意又一次意外消失。
在红月亮的照耀下,他看见杜其实和一只巨大的山猫并排坐在一起,山猫妩媚满脸,杜其实畅意双眸,他们在湿润的土地上交谈着,耳边尽是黄瓜沟涓涓的细流之声。
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是两只死去的兔猫。
突然,山猫一跃而起,跳到兔猫的旁边,一口咬掉它们的脖颈、四爪、尾巴,杂花一般越过黄瓜沟,闪电似的穿过黑松林,流水一样潜入密实的灌木丛中。
紧接着,大力碎裂头骨的声音破空而来。
纪明国“哗”地一下尿了。
尿水先冲入裤衩的裆部,然后滑向腿根,又热辣辣地贴着大腿的内侧直下裤管,连带着那些不知所措的鸡皮疙瘩没头没脑地汇入黄瓜沟南汊的暗流里。
“下来吧。
”杜其实叫他。
他虚飘飘地就下去了,轻轻地坐在杜其实的身边。
“冷吗?
”杜其实问他。
他双手抱肩,点了点头。
杜其实苦笑了一下,把衣服脱下来,凭空一抖,便披在了他的身上。
不知为什么,就在衣服潮湿地包裹着他的那一刻,他忍不住哭了。
杜其实张开手臂,环抱着他,任凭他的泪水打湿自己的臂膀和胸膛。
“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杀过猫,”杜其实说,“这些兔猫都是它送给我的,它每次都是这样,只带走兔头、兔爪和兔尾。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
“这样一来,兔猫就变成了猫。
” “那,”纪明国问,“它,是,是师娘吗?
” 一颗灯泡一样的眼泪砸在纪明国的肩上,迫使他的锁骨快速收紧。
“不是。
” 纪明国绝望地哼了一声。
纪明国讲完杜其实的故事,大家都沉默了,半晌,肖松说:
“我也说一说我的事吧。
我那天为什么能空手带回去两只猫?
”他扭头看了一下窗外,“操!
从小就这样,只要没有外人在身边,那些猫就会悄没声息地聚到我的身边,不吵不闹,只用哀伤的眼神儿看着我。
“那一天,我跳进老虎公园大墙里的时候,那两只猫就死死地趴在了我的脚下,它们来得那么突然,那么迅捷,如同离膛的炮弹,准确落地,拒绝爆炸。
我未假思索,拎起它们便走,这才引起了师父令人难以想象的震怒。
” 真正的震怒都是没有语言的吧?
黎娜看着肖松,无助地摇了摇头。
纪明国沉默了半天,突然举起酒杯,郑重其事地说:
“我是大师兄,你们的事我担着。
” 这是一句斩钉截铁的承诺。
纪明国端着酒杯,回想杜其实行刀走拳的每一个时刻——行云流水,明月清风,平稳、大气,偶鸣金鼓,开合自如。
尤其是杜其实走刀的时候,黑松林啊,或仰或伏,全在杜其实的意念行走,毫无条件,不由分说,缜密细致,没有破绽,恰似刀阵应敌,杀气四腾。
这就是杜其实——像一股强大的暗流。
黎娜恍惚着问:
“我有什么秘密吗?
” 三只手同时伸向了她的头顶,随之传来同一个声音:
“小丫头片子,你有什么秘密?
” 这三只手,一只是纪明国的,厚重而真诚;
一只是肖松的,真诚而爱意;
另一只是和他们在黑松林一起练功的八极拳的大师兄的,爱意迎着醉意摇摆不停。
三只手几乎同时交会在黎娜齐耳的短发上空。
最下边的是纪明国,接下来是八极拳大师兄,再接下来是肖松。
在此之前,八极拳的大师兄曾截过黎娜。
在此之前,他也曾向纪明国挑过战。
今天的见面不知是天意还是偶然?
六目相对,际会风云。
“不服啊,那就过两手。
”八极拳大师兄竖了竖眉。
力从脚下升起,攀腰拔臂,转肘缠腕。
纪明国和肖松不约而同地一较劲儿,八极拳大师兄便陀螺一般旋转着身体跌倒在地上。
紧接着,是纪明国。
他飞身跨过去,对着八极拳大师兄的眉心就是一拳。
这一拳就是祸事,对方为此在床上一躺就是十三年。
而这十三年,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不知道,杜其实不知道,纪明国好像也无法知道。
如同1979年6月15日那一天一样,纪明国背起八极拳大师兄直奔师大医院,他把他放在外科诊室的诊床上,然后转身离去,从此过上了销声匿迹的日子。
为此付出代价的人还有——杜其实作为教唆犯获刑二十年;
肖松和黎娜双双进了工读学校。
李云阳属于表现较好的改邪归正的少年典型受到表彰,得以正式高考,并以高分考入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建筑系,学有所成,最终定居浙江省杭州市。
多年后,他把母亲带离了黄瓜沟南汊的旧家。
肖松和黎娜从工读学校出来后,开了一家小小的饭店,以卖烧烤起家,不几年,便拓展成一家中型酒楼,又后来,他们看准先机,经营了全市第一家素食馆子,身份几经更迭,原始积累却很快完成了。
卖烧烤的时候,人们便盛传他们卖的是猫肉,并联想旧事,称肖松是“猫王”。
肖松和黎娜对此未置可否,一旦有人问及,皆一笑了之。
其实,从他们开店之始,一切原材料均以豆腐和面粉为主,至于佐料,除了他们两口子,恐怕无人知晓。
肖松和黎娜吃起了“十日斋”——每月逢农历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月末三天,双双吃斋念佛,禁肉禁酒。
另外,每月初一,或肖松或黎娜一定会前往监狱探望杜其实,奉上吃用,从未间断。
护国般若寺的钟声响了。
大地一片安平。
松城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城市,表面看,平静甚至冷漠,实际上热情而仁义。
现在,有许多人在研究松城人性格的历史成因,只是尚无明晰的有价值有建树性的学术成果。
但是,松城人的温润、奔放,严谨、任意,随性、刻板,悠游、专注,越来越为天下所知,并广受彰扬,已成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你随意踢开一砖一瓦,都会有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人物跳出来,谦恭而放肆地对你说:
“你好。
” 没有遮拦。
亦没有心机。
纪明国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后来,人们都怀疑,纪明国去了哪里?
其实,他一直生活在松城这个城市里,并常在月满之夜在衡阳街往复穿行,忽而家门口,忽而工读学校的窗台,忽而李云阳母亲的病榻前,忽而监狱的高墙内外,他行如疾风,静若浅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着简单而又繁复的人生。
那一年,他负罪潜逃之后,直接进入老虎公园的西大门,一头栽入黄瓜沟南坡的地环儿丛里,在花香与污臭之间放声痛哭。
月亮出来了,嫣红而圆润。
山猫来了,轻轻地卧在他的身边,没有呼唤他,也没有抚慰他。
但是,在山猫的身后,是成百上千的流浪猫,它们用绿色的灯光温暖他,用长长的绒毛覆盖他,那一夜,他安睡了,天亮之后,他变成了它们之中的一员。
杜其实被带走了,他蹲在锅炉房的门框上目送着他,他现在已经不会说话,但是他的泪水告诉他,他要为杜其实坚守一件事。
他去副食店取肉,然后回到运输队的院子里,劈柴、生火,填汤、煮肉,放入葱花、姜片、花椒、大料、酱油、盐,对了,现在有味素了,一定要加入少许提鲜,让老爷子的胃口好起来。
他把饭盒放入某一辆自行车的前筐里,然后趁着天光未亮之前赶往杜其实的父亲家,把炖肉放在他的门口——轻轻挠门,悄然后退,在楼梯的转角处看着老爷子幸福而疑惑地把饭盒端进屋里。
他知道,老人吃完了,会自己把饭盒洗干净,到那时,它便会在老人打瞌睡的时候悄然取走它,这已经是一个游戏,彼此之间乐而不疲。
饭盒取回来了,他会做第二件事,去副食店取肉,然后回到运输队的院子里,劈柴、生火,添汤、煮肉;
放入葱花、姜片、花椒、大料、酱油、碘盐;
对了现在已经有十三香了,一定要加入少许提鲜,让师父的胃口好起来。
他把饭盒放入某一辆摩托车的后备箱里,然后趁着天光未亮之前赶往监狱,把炖肉放在杜其实牢间的窗台上,然后轻声“喵”叫,悄然后退,只把一只爪子搭在窗台的一角,窃听着师父把饭盒里的炖肉吃光。
吃光了,复又放在窗台上,任由他把它带回原来的地方。
带回原来的地方,便做第三件事。
去副食店取肉,然后回到运输队的院子里,劈柴、生火,添汤、煮肉;
对了,现在已经有炖肉香了,一定要加入一袋,让娘的胃好起来。
他把饭盒一分两半,先衔着一半来到自家门口,然后,再衔着另一半送到李云阳家的门口;
然后,轻轻掩门,悄然后退,在老虎公园的大墙上蹲坐,看着两个老娘幸福而疑惑地把半个饭盒端进屋里。
他知道,娘吃完了,会自己把半个饭盒洗干净,到那时,他便会在两个老人相携散步的时候取走它。
这已经是一个游戏,彼此之间乐而不疲。
直到师父的父亲去世。
直到自己的母亲归西。
直到李云阳把母亲接往杭州。
直到杜其实出狱。
杜其实一出狱,便被肖松和黎娜接到了素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