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管理经济学2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MBA管理经济学2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MBA管理经济学2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9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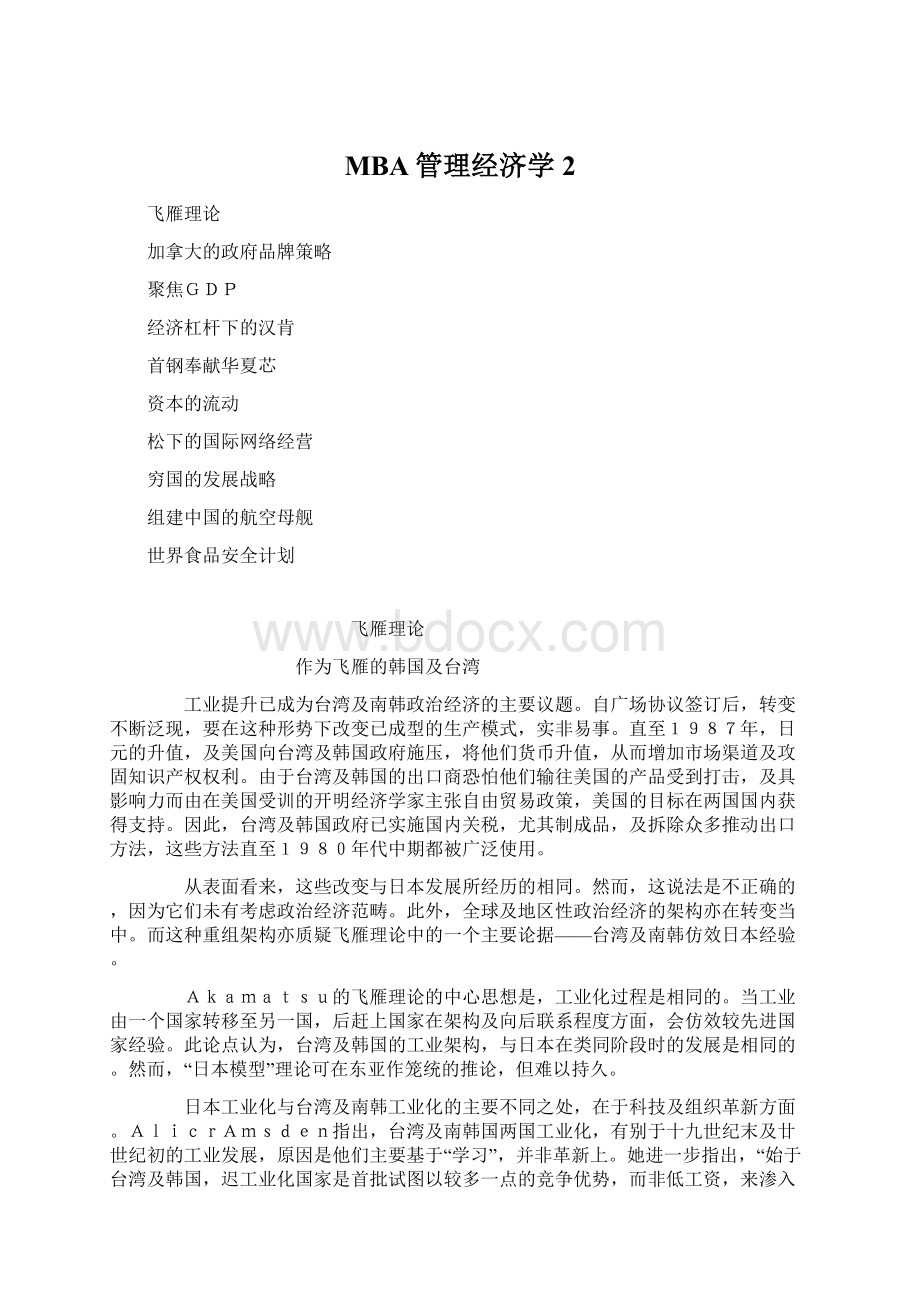
当工业由一个国家转移至另一国,后赶上国家在架构及向后联系程度方面,会仿效较先进国家经验。
此论点认为,台湾及韩国的工业架构,与日本在类同阶段时的发展是相同的。
然而,“日本模型”理论可在东亚作笼统的推论,但难以持久。
日本工业化与台湾及南韩工业化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科技及组织革新方面。
AlicrAmsden指出,台湾及南韩国两国工业化,有别于十九世纪末及廿世纪初的工业发展,原因是他们主要基于“学习”,并非革新上。
她进一步指出,“始于台湾及韩国,迟工业化国家是首批试图以较多一点的竞争优势,而非低工资,来渗入全球输出口的市场。
”相反,日本工业在日本于50年代大大提高其全球经济地位前,有强大的本地革新基地。
棉布纺织业,Akamatsu的飞雁理论亦以此为根据,是一个好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处于全球纺织机械企业领导地位的PlattBrothers,经常派遣其技术员往日本,教导日本客户如何使用其机械。
来自各国公司的技术交流,因欧洲的战事而要停止。
但当战事结束后,PlattBrothers技术员发现他们之前的日本客户已采用日本制造的机械,例如Toyoda的电动织布机,这比英国生产的机械更为先进。
此外,战前的日本企业集团,已创立拥有全球供应品及资讯汇集能力的革新一般贸易公司。
日本在这方面的起步,再加上工资较低,令日本生产商在众多海外市场,取代兰卡斯开生产商地位。
电子工业的情况亦同出一辙。
日本革新始于1920及30年代,比Sony收购晶体管还要早几十年。
当时,重要的突破还有电视讯号的接收、天线科技,以及物体,如铁酸盐的开发。
此外,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日立及东芝等公司进行的武器研究,创制出团体架构及认知,对将战后的外国科技本土化极为重要。
韩国及台湾工业化最大特性,是他们对输入科技的较大规模及长时间的依赖。
起初,他们依赖日本输入科技,后来则是美国,虽然依赖程度较对日本的轻微。
那些成功制造由生产至中间货品的向后联系的工业,如纺织机械工业,透过倒序工程、知识授权许可及学习,从其他地方吸取制造标准产品的技能。
由于科技急剧转变,产品在微型电子时代又趋向复杂化,因此产品不会太易受到倒序工程影响。
因此,韩国及台湾的大多数制造都是依靠主要零件及机械的不断输入。
韩国电子工业最近的一个研究,提供了一个例子。
研究发现工业在1987年有36%的零件
是来自日本。
此数字或许大大削弱了工业对输入口的依赖性。
韩国银行1993年的研究,发现只有38%的半导电体价值是在本地加上。
相反,日本公司不但有能力透过本地的研究及开发和革新零件制造商,来吸取甚至改进外国科技,他亦善于建立强健的市场网络,促进品牌在全球的认知。
输出工业与日本类同的韩国及台湾公司,则欠缺创新能力,而且过分依赖OEM制造。
以电子、成衣及钢为例,韩国贸易联会报告指出,OEM输出占总输出量的比例超过八成。
当制造以OEM为本,生产商难免要依赖产品市场推广网络。
此外,OEM合同限制以制造商品牌为名产品的输出销售,亦局限了市场推广及销售后服务能力的发展。
这情况显示了历史时间、工业化模式、及与全球生产网络联系的特
定策略,如何制造韩国及台湾工业架构及有别于日本的个别生产单位。
有理论认为,近期台湾及韩国增加海外生产的情况,正等同日本公司在1970年代初期进行直接外国投资情况。
这种理论又是错误的。
台、韩两国投资公司所处的实际环境情况不但有别于日本,甚至在地区或全球生产网络中所占位置亦相异。
生产网络提供灵活性之余,亦同时以等级制安排。
等级内的位置与不同企业的生产方针及供应有关,并可影响海外投资的性质。
直接海外投资的内容不可单凭交易数量和涉及资金流动而断定,必须是经过审慎的考虑。
例如,珍宝投资泰国,能促进科技转移或加强泰国工人的技术水平与否,仅是未知之数。
然而,从地区政治经济角度来看,珍宝所处的生产地区架构,是有别于日本大生产商,如声宝(即使两者生产的产品相同)。
声宝已支配全球主要科技,如液晶体显示器,并在区内建设相连的研究及开发中心,及经常为与其产品竞争的规模较小公司提供主要原料。
韩国大型电子制造商,虽然在基本层面上与台湾公司相异,但两国公司在地区网络的工业模式上,仍有不少相同之处。
Bloom指出,韩国内在力量,如紧连日本的生产、早期对OEM的侧重、过份依赖对美国的输出口、廉价劳工等,现在仍可见于迈向国际化的韩国财阀集团大企业。
韩国公司所面对的情况与珍宝投资泰国时相同,两者都是欠缺设计或市场推广能力、困于负责供应主要零件及其他原料的生产等级架构当中,并要依赖低成本生产来维持输出口的竞争力。
因此,韩国公司会采用有别于其他工业的手法,令公司跨国化。
自广场协议签订后,韩国及台湾研究及开发(R&D)的开支有显著的上升。
韩国R&D开支如1986年有170万美元,到1990年已增至450万美元。
然而,我们不可单就数字上的增长,而认定第二层雁已步入下一个发展阶段,上述的广阔架构转变仍须被考虑的。
其实,R&D升幅的主因是科技转变而成,正如我们曾讨论,成熟阶段中的工业不应被视为停滞不前的。
甚至那些在台湾及韩国较悠久的工业,经新科技注入后,都成为颇精通科技的生产商。
因此,新科技不但可将企业推前至更先进位置,亦可维护企业在主要工业所建立的地位。
此外,庞大的R&D经费是必须的,以确保生产单位拥有所需技术,来配合科技急剧转变。
讽刺的是,R&D的开支增长及生产能力的提升,亦促使企业更依赖零件及资本货物的供应。
换言之,R&D开支增长并没有制造更多独立的“国家”工业。
不断依赖人口科技的情况,可见于以出口为主的工业,如电脑业。
由于竞争不断上升,市场对低科技产品的需求下跌,这些以出口为主的制造商便需要改进其出口产品及提高科技。
以前依靠出口黑白电视及彩色电视显示器的小型台湾工厂,现已成为生产黑白电脑和彩色显示器的主要生产商。
1991年,台湾占全球电脑显示器总生产的39%。
然而,正如大部分企业面对的情况,显示器的主要零件,阴极射线管,是由日本输入的。
而此零件已占了制造显示器的30%至35%的成本。
这例子进一步强调,累积的生产技术及知识,促使台湾生产商进军更先进工业的同时,亦没有减少他们对日本科技在架构上的依赖。
最后,产品周期理论指出,由保护主义,尤其美国,能有系统地掩盖日本输出品的浪潮,从而吸引韩国或台湾生产商进军这些工业。
此举表明看来是促进日本发展模式重演于其他国家中,然而所提出的论据过分依赖经济活动的不变概念。
汽车业正好说明,当生产由一个国家转移另一国家,是会出现变化的。
英国政府在1982年,对日本汽车出口,实施自愿出口限制。
在VER实施期间,日本汽车业在生产架构上有重大突破。
日本汽车生产商因此能以低于韩国生产价,制造小型汽车。
韩国的汽车制造商一直都是利用廉价劳工,依赖零件的输入及装配。
韩国商业局估计,虽然韩国工资成本只有日本的1/7,但于韩国制造的HyundaiPoony的生产成本是$3,972美元,而日本制造的ToyotaCorolla只是$2,300美元。
由于VER只是数字上的配额,日本制造商为求更多利润,把廉价汽车市场不纳入汽车输出口当中。
有见及此,韩国首间汽车制造商,Hyundai便乘机进入美国市场。
但日本公司并未因此放弃低价市场,反而更积极在美国及加拿大进行投资。
面对日本的强势竞争,韩国汽车往美国的输出口,由1988年高峰期起,便开始急剧下跌。
韩国汽车输出美国,只享受了一刹那的成功滋味,个中原因正点出飞雁理论所提倡的科技发掘轨道相同的观点是欠全面的。
因此,日本公司并没有放弃小型汽车市场;
相反,他们直接投资北美洲,从而再次收复在80年代因为VERs而失去的市场。
此外,生产技术的转变,有助日本汽车制造商与韩国竞争,纵使日本的工人成本较高。
另外,由于困扰韩国汽车工业的劳方局面不稳定,导致连续六年的工资增长,亦促使韩国失去主要的竞争力。
最后,业内急剧的技术转变,例如引擎控制器电脑化和新材料的应用,意味着韩国人,不像廿年前日本人般幸运,他们所追求的目标还不断远离他们。
这情况亦促使材料及零件的输入,占韩国制造汽车成本的1/4。
台湾及韩国的工业改革,以独特的科技及生产架构模式出现,与日本工业化早期的情况截然不同。
同样,台湾及韩国的重组特色——科技持续及急剧的转变,相信与微型电子革命及冷战后期地理分布改变有关。
此外,机构架构相异、地理分割的遗产、本地市场规模细亦显示了1990年代的韩国及台湾,和70年代日本在架构转变上的相同之处甚少。
事实上,韩国及台湾工业化的特质,以及在全球转变中进行改组的过程,亦引发一连串发生在大部分东南亚地区的问题。
从中或会察觉新雁地位的提升。
东南亚:
最后赶上的雁
1980年代下半期,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所享受的经济增长,可媲美1970和8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
马来西亚等国出口扩张,虽然起初属细规模,但增长的速度实令人惊叹。
由于这三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卓越,故享有“新新兴工业国”及“下一代新兴工业国”美名。
部分研究家认为东盟制造出口的增长,肯定了飞雁理论的观点:
马来西亚及泰国,甚至印尼和菲律宾,均属经济起飞中最迟起步的飞雁。
东南亚经济经验一直与产品周期理论所推测的有出入。
东南亚制造出口的近况,不是依靠输入代替工业化的成功经验,是有别于上述的推测及韩国和台湾的经验。
相反,新出口工业国已加进经济,而当时的小型制造业以低效率和寻找租金见称。
韩国及台湾高科技生产的特点是依赖科技,在东南亚的情况更甚。
Yoshihara评论,东南亚所经历“欠科技”工业化,亦见于大部分工业。
相反,东北亚则非常依赖跨国企业附属公司作制造出口,例如1980年代底的马来西亚,外国操控公司负责99%的电子出口,90%以上的机械及电子用品出口,50%以上的塑胶产品出口及75%的纺织及成衣出口。
东南亚以出口为主制造当中的大部分早期外国直接投资,是在出口过程区(EPZs)进行。
当地区政策准许企业在EPZ外建立通往免税进口的渠道(但这些进口货必需作制造输出品之用),EPZs已变得不太流行。
然而,EPZs的特点仍见于东南亚大部分的外国附属公司:
与本地经济欠缺向后联系。
在1980年代中期,在东南亚进行的多个EPZs研究指出,区内企业与本地经济
的联系不大。
企业侧重与区内或其他自由贸易区内运作的其他公司建立联系,而未有与本地经济没有向后联系。
例如,Lim&Fong研究指出,马来西亚EPZs海外附属公司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工业的联系,较与本地工业的多。
究竟投资东南亚以出口为主制造业的新浪潮,有多大程度上是与较早模式相若?
虽然,只根据近期新投资事项而作出结论,未免言之过早,但马来西亚运作的日本附属公司调查获得的初步证据显示,虽然本地取得的零件价值在1980年代有显著的上升,但这些附属公司总出口占本地收销的比例只有轻微上升,以电子业为例,上升幅度仅由1987年的29.8%升至89年的32.5%。
值得注意的是,少于0.5%电子业的本地所得是来自马来西亚公司,有24%是取自在马来西亚运作的日本附属公司,另外的22%则来自驻马来西亚的欧洲及美国公司附属公司。
虽然,马来西亚公司所供应价值在1987-89年有两倍的增幅,但他们在“本地”所得的比例仍维持不变。
这些数据显示,“本地”内容数字在地区制造网络时代,可以甚具误导性的。
东南亚本地公司在这些网络的参与,远远不及韩国或台湾广泛,从而引发起国家拥有是否对网络地区经济重要的问题,对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的东南亚来说,国家拥有是重要的,因为本地公司的积极参与,有助促进科技转移到本地经济。
Leslie在其马来西亚制造公司的详尽研究总结说,与外国公司比较,本地拥有或控制公司更会与国家经济联系,及改进或制造他们生产设备,来配合本地情况。
然而,由于日本附属公司支配东南亚生产网络,至少在短期内,能为东盟国家提供好处,超越韩国及台湾。
1980年代底,韩国及台湾减少电子产品往日本市场的输入,原因是部分输入货由东南亚的日本附属公司输入。
例如,台湾及韩国彩色电视机的输入,在1989-91年间,由160万部跌至130万部,而同期,马来西亚的输入,则由2,000部,升至38万5千部。
后来,马来西亚取替台湾及韩国的地位,成为输入彩电到日本的第二大重要来源国,以及输往日本市场的收、录音机单一最大供应商。
由于日本公司操控他们驻东南亚附属公司的科技应用,这些生产网络的公司因而较台湾及韩国的本地公司,更易吸取最新的生产科技。
调查指出,日本公司希望增加他们的国内购买,不论是来自其他日本附属公司,还是国内企业。
随着日元的上升,这种倾向更为显著,而生产技术的采用,如Just-in-time亦鼓励此做法。
Just-in-time制造有利邻近供应商品要防止国内企业增加输入的主要屏障,是本地公司未能生产产品,达至日本的品质及可
靠性要求。
这再一次提出,处于严厉工程标准的本地公司,要在微型电子年代进驻生产网络所面对的困难,工人教育水平低和花在R&D的GDP比例少,是国内公司不利条件。
现时,只有少数的跨国附属公司全为国内公司提供科技或管理援助,以协助改进品质控制。
外国公司在东南亚众多生产的支配,和这些公司不断依赖外国公司的科技和零件输入,令人质疑飞雁理论有关东南亚的准确性。
即使不考虑工业化是在不同地区,全球及科技环境进行的因素,这些国家的生产发展模式——过份依赖外国企业,以出口为主的制造并非建基于输入代替,及与本地零件供应商缺乏联系,与日本或台湾和韩国所经历的截然不同。
当然,工业化新浪潮在不同地区,全球及技术环境进行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不同东南亚国家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但较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疏离,而且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泰国的相比,有很大的差异。
当经济开放思维变得霸权,东南亚以出口为主的工业化动向,刚好与东北亚经验相反,减低了国家对本地经济干预。
与台湾及韩国在60年代所面对的全球经济相比,“迟迟”发展国家所面对的就截然不同了。
冷战后的美国已不愿继续容忍周边贸易的不平衡状况。
全球经济环境的转变,是产
品理论最后阶段失败的一个原因。
最后阶段提倡的是,产品会“倒序出口”,即是产品最终会输入产品原创国家。
“倒序出口”未能实现,已引发了政治争论。
产品周期及贸易三角
当产品原创国家停止生产目前的标准产品,而国内市场的需求是由国外生产商的输入满足,这便是产品周期的最后阶段。
这情况从未在东亚出现。
日本生产商不愿放弃产品,或向日本大规模输入外国生产,会令贸易三角成为支配模式。
贸易三角是指,在日本购买原料(渐渐由台湾及韩国供应),然后在新兴工业国,多数是东盟及中国,进行制造,最后输出第三国家市场,而并非日本。
要是整个产品周期出现的话,随着东亚其他国家将完成制成品输入日本,一个自给自足的日本团体便会形成。
正如Frankel及Petri指出,即使东亚跨区贸易在80年代下半期上升(以总贸易%计),但与过往期间比较则有下跌,而且更大大低过欧盟。
产品周期未能走完一整圈,正好说明为何日元团体到目前还未出现。
经济理论没有提供一个原因,说明为何周边贸易必须维持平衡。
不同国家有不同因素。
贸易不平衡可由资金流动抵销。
但这正是健全经济不一定制造健全政治的一个好例子。
周边贸易不平衡,尤其制成品,若然具巨大政治重要性(尤其当全球经济增长低微,令国内经济调整政治难以进行)。
东亚的生产地区化为贸易模式带来两个重要结果。
首先,地区内的所有国家(中国除外,因输入受到国家严重操控)与日本的贸易赤字不断上升,原因是他们的输入不单是日本消费品,亦是国内制造所需的资本货品和零件,国内制造业在80年代下半期有上升。
日本公司海外附属公司的研究指出,他们较其他地方的INC分行,较倾向输入大量来自日本的原料。
驻亚洲所有制造业的日本附属公司,依赖日本的输入平均超过四成。
而驻亚洲新兴工业国和东盟的日本机械制造业附属公司,有接近一半的来源输入是来自日本。
资本设备更依赖日本的输人,驻东盟的日本附属公司在80年代底,有75%的输入是来自日本。
80年代下半期制造品对日本输出量的增加,未有减少资本及中间货品的输入增长。
输出量虽然增加了,但与来自日本的输入相比,仍有一大段距离。
随之而生的贸易不平衡加深了日本和韩国、台湾及东盟国的紧张局势。
韩国和台湾增加在东南亚的投资,导致贸易不平衡不断增长。
世界银行调查所搜集的数据指出,亚洲的驻NIC公司的附属公司主要依靠资本设备和零件的输入、研究发现,受访的90%NIC附属公司,输入超过五成的原料;
37%公司输入所有的原材料、零件和资本货品。
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及韩国和台湾之间的制造赤字的急剧增长,大部分原因与这些公司的本地附属公司输入材料增长有关。
此外,东盟国内NIC公司的大部分附属公司亦从日本输入科技和零件。
东亚生产地区化对贸易模式造成的第二大影响,可见于地区与美国,以及欧盟制造贸易额的急剧改变。
虽然马来西亚和泰国在1985年与美国在制造货品出现贸易赤字,但到90年代早期,两国所赚的盈余每年超过20亿元。
同时,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及新加坡与欧盟的制造贸易亦转亏为盈。
韩国及台湾亦同样地增加与欧盟制造业贸易盈余。
然而,由于里根和布什政府不断施压,限制台湾及韩国入口及进驻美国市场的开放,因此自广场协议签订后,台韩两国与美国的制造贸易盈余增长放缓。
直至1990年,由韩国和台湾输入美国的制造出口总值,已由1987年至88年的高峰期向下滑落。
再加上台湾及韩国货币升值。
1980年代底的出口面值下跌可算最为惊人。
由于韩国没有其他市场来抵销与日本不断上升的贸易赤字,因此美国贸易盈余下降,对韩国的影响最为深远。
相反,台湾也不见得能与美国维持贸易盈余,但她从刚萌芽的中国工业输入当中取得可观收入。
这些合计数据显示1980年代下半期地区政治经济的两方面情况。
首先,美国向东北亚各国施压,削减贸易盈余,对地区贸易模式做成直接影响,这尤其鼓励生产转移至东南亚及中国。
第二,数据显示,由于产品周期未有完成一整圈过程,制成品输入日本市场的数量亦因而没有大升幅,从而促使贸易三角成为地区贸易的主导模式。
所谓贸易三角就是指,从日本及东北亚NICs输入零件及资本产品,以后将制成品输往美国及欧盟。
对日本贸易模式的猛烈评击仍持续不断。
不同的经济模型会引伸至不同的结论,例如以日本的资源架构及地理位置,日本对工业国的输入量,是否不寻常。
事实上,驻NICs,尤其东盟国的日本附属公司的生产,只有少量是再输入日本的。
例如,1989年,驻东盟的日本附属公司销售中,只有10.4%是输往日本市场,相反,输往其他市场的销售超过25%。
而且,超过一半的销售是在“本地”市场进行,其中大部分产品需要在地区生产网络中再作加工,然后才可输出。
所得的结果是,美国须负担部分因东亚工业化调整所致的损失。
自1985年,随着美元对日元下跌,美国在大部分东亚国家的制造出口的占有率都下降。
但美国的制造出口比例比日本还要高。
这不一定与两国的经济有关(日本在1989年的GDP估计是美国的55%)只有在南韩及泰国,日本所占的出口水平是美国的一半,在大部分国家而言,日本与美国的出口比率接近25%。
1992年,日本市场占中国、韩国及新加坡的制造出口的比率,实质上低于1980年的比率。
广场协议后,在东北亚出现的一股外国投资浪潮,其主要目的是设法规避贸易屏障及舒缓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东道国面对的危险是,一旦他们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因素,便会被卷入相同的紧张局势当中,中国亦曾身受其害。
日本在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制造输出比例,亦在广场协议后增长,但增长速度并未足以满足美国或东亚国家政府,当然亦未能抵销日本的资本货品及零件的销售。
纵使货币在广场协议签订后作出重新调查、日本与NICs的跨工业贸易增加、其他东亚国家能成功地增加日本市场的制成品出口,但由于产品周期未能达致最后阶段,迫使
美国继续肩负东亚工业化调整所带来的负担,难免会导致贸易局势紧张。
结论
东亚政治经济的出现必须从三个转变之间的关系探讨:
全球政治经济的改变、个别国家政治经济的改变,以及生产组织的改变。
愈来愈多的文献著重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新兴工业国之间的变化可以很大。
纵管愈来愈多文献说明东亚各国之间经验存有很大差异,但飞雁理论亦被广泛使用。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为何飞雁理论以及其他认为各国工业化步伐统一的理论,现在是安息的时候了。
韩国及台湾的工业模式不单与日本——第一代飞雁的模式有天渊之别,甚至与目前东南亚制造出口的迅速增长,都有显著的不同。
飞雁理论的败笔之处在于未有注意,转变中的全球政治经济及科技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会妨碍工业架构的一致化。
虽然韩国及台湾,以及近期的马来西亚和泰国,或许在日本数年前取得成功的工业输出产品,但从工业组织和地理政治方面看来,他们之间的处理手法有显著的不同。
然而这些国家工业出口仍然非常依赖日本资本货品及科技进口,与飞雁理论所估引的刚好相反。
在韩国及台湾,OEM仍支配高科技工业。
另外,东南亚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大都由跨国公司的附属公司负责。
对日本科技的依赖,再加上地区内日本公司依靠廉价劳工作装配运作,促使地区劳工分配的形成,是建立基于生产地区化网络,而并非国家经济。
地区生产网络的出现,为政治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
各国彼此间的生产架构联系与国家政治有着相互影响。
正如本文提出,集中生产网络,有助察觉现有数据,如贸易、投资及本地内容数据的不足之外。
制造计算机的台湾公司珍宝,是说明地区化生产网络如何将贸易和直接海外投资的数据复杂化的一个典型例子。
同样有关马来西亚的讨论亦指出,地区生产风格如何为诚信不高的“本地”内容提供数据。
要明白东亚地区的生产组织,就必须理解影响网络的国家数据背后意义。
各独特部门应被视为工业活动“综合”的一部分,而并非如产品周期理论,只集中某个产品的流动而忽略所有其他产品。
例如,日本电子生产商在东亚成立的生产网络,正显示个别产品扩散的模式并不等如其生产方式,产品的生产模式,是联系多个国家,涉及多组公司的。
其中大部分设有长期附属公司,生产大批量的相互关联产品。
产品相互联系,是由于日本公司一直不愿放弃那些似乎达到成熟阶段的产品,而这正与产品周期理论所预期的情况背道而驰。
生产技术转变、产品差异化的增加或全新科技的出现,亦会对某些产品的“反成熟”造成影响。
因此,当
R&D变得日益非曲线化,放弃某些成熟产品的生产会带来风险,所涉及风险包括,失去制造科技的认识或零件制造,而这些零件或许对看似不相关的日后生产有巨大影响。
飞雁理论是否过早被否定?
当东亚国家科技能力步入成熟期,他们最终或许是仿效日本的做法?
相信情况不会如此。
要是肯定飞雁理论,就是忽视了近廿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及生产技术的转变。
目前经济正寻求,减少对科技的依赖,而较斜学习线、R&D开支增加,以及配销网络地点,皆恶化了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