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诱惑剖析中国法律职业群体中的关系网Word下载.docx
《致命的诱惑剖析中国法律职业群体中的关系网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致命的诱惑剖析中国法律职业群体中的关系网Word下载.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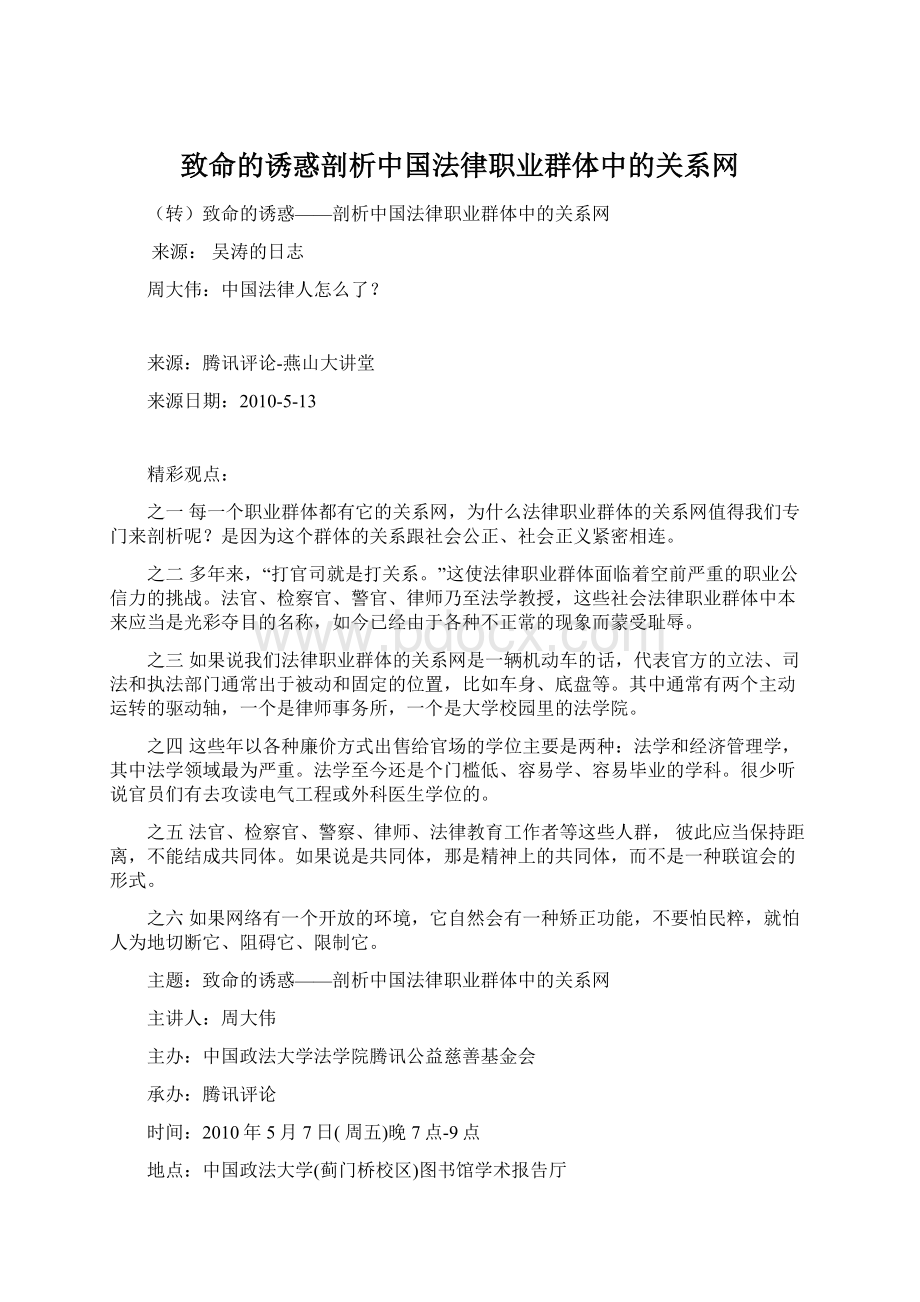
主办: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承办:
腾讯评论
时间:
2010年5月7日(周五)晚7点-9点
地点:
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
杨子云
非常高兴在经过五一短短的假期之后,我们继续相聚燕山大讲堂。
今天是讲堂第68期,主题是中国法律职业群体关系网的剖析。
每一个职业群体都有它的关系网,为什么法律职业群体的关系网值得我们这样来剖析呢?
我个人考虑,是因为这个群体跟社会公正、社会正义紧密相连。
对于法律职业群体关系网的剖析,慕容雪村有本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
去年6月13号,慕容雪村曾来到我们的讲堂做过一次交流和讲座。
今天请来的周大伟先生,他本身是一个法律学者,又从事一些实务工作,同时旅美多年,能够跳到圈外看这个法律群体关系网,能从更加实证的角度,从既是圈内人又是圈外人的角度来剖析法律职业群体的关系网。
关于周老师,他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硕士,又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伯克大学留学和做研究访问。
2007年4月我第一次见周老师,是在政法大学讨论重庆钉子户事件。
随后我经常在《法学家茶座》上看到周老师的一些法学随笔,他经常会把一些比较容易忽视和不太容易懂的法律问题,写得非常清楚。
掌声欢迎周老师!
开场白:
中国语境中的“关系”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感谢主持人的盛情邀请和开场介绍,感谢大家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来光临讲堂。
第一次来到燕山大讲堂,深感荣幸。
记得2007年我曾应邀来到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参加过一次学术研讨会,当时我们在关注和讨论重庆钉子户的事件。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致命的诱惑:
解剖中国法律职业群体中的关系网。
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题目,为了讲述这个题目,我需要把自己平时经历和阅历中的思考碎片整理组织起来。
这显然是对自己思考力的一次锻炼。
所以,在演讲前,我特意做了些功课和准备。
最开始,我在演讲题目中使用的并不是“法律职业群体”,而是“中国法律人的共同体”。
几天以后,我思考中发现“中国法律人的共同体”这个词可能会产生重大误解,所以就改用“法律职业群体”。
具体原因,我在演讲中会做出解释。
演讲的内容首先涉及的一个我们中国文化社会的关键词语:
关系。
这个题目看上去有点儿诱人和生猛,有点儿来势汹汹(笑声)。
直到今天中午,还有朋友打电话提醒我,这是个得罪人的话题,还是不要轻易捅破这个马蜂窝为好。
说话可要小心点儿。
我说谢谢,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先讲一段小小的开场白。
我上个月在美国加州的时候,遇到一个早年和我做邻居的美国朋友,他30多岁,人挺单纯。
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他最近去一个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听试听了几次课程。
我好奇地问他,你在课堂上有什么收获吗?
他告诉我,几堂课下来,他学会了一个新的中国单词:
“关系”。
我和这个美国朋友认识多年,也许部分原因是因为曾经和我做邻居,他对中国文化颇有兴趣,也多次发誓要学说中国话。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他的中国话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和不少老外一样,说来说去,也还是只会说“你好、我喜欢吃中国饭、谢谢、再见这几个简单的中国词语,而且发音很生硬。
不过,这一回,使我惊讶的是,他的”关系“这两个字却发音格外清晰。
他告诉我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子学院的老师反复在课堂上讲这两个字,以至于他印象太深刻了。
我发现,他除了记住了这个词的发音外,至于“关系”这个词语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到底和美国人理解的“关系----RelationorRelationship”一词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他还是蒙在鼓里。
我开始隐隐约约有些担心,我们中国政府在海外投资的孔子学院的课堂里,到底在给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朋友们讲了些什么?
说不定那些政府主管部门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楚。
其实,“关系”或者“关系网”,都是中性的词,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今天在场可能有一些外国朋友,可能还有美国人在场。
说老实话,美国人其实也是讲关系的。
商人们在高尔夫球场、政客们在议会的走廊里、社会名流们在豪华私密的俱乐部里、学者们在各种沙龙里、普通人在各类酒吧和派对的聚会中,以致在教堂和网络中,人们也在相识、相知、沟通、合作。
大千世界、人来人往,只要是人类社会,这一切都是每日每时发生的正常现象。
但是我始终感到,我们的海外孔子学院里向这些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讲述的所谓“关系“,显然并不是这些普通的社交关系,其中似乎隐含着更深更隐秘的含义,比如那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传密码的东西,比如那些可能包含着很多超越正常逻辑、超越道德和法律界限的、具有某种难以捉摸的神秘东方哲学色彩的东西。
言归正传,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法治不太健全。
多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
普通民众当中一直有一种说法,说“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这广泛流传的说法使我们法律职业群体今天就面临着空前的、最严重的职业公信力的挑战。
如果让我们来剖析这些发生的原因,首先就不可回避地触及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神秘而敏感的、可能具有中国特色文化遗传密码的关键词语:
“关系”或者叫“关系网”。
我认为,这个关系网今天正在每时每刻地触及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最敏感的神经。
这个关系网不解决、不理顺,不把它引向健康的轨道,我们中国民众的神经就不得安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就不可持续。
下面就这把问题展开谈一下。
1,经过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法律职业群体?
中国法律职业群体的基本构成。
这个群体太大,有必要给它做一个适当界定。
一般来讲,从古到今,读书人的前途大致分成三条路:
做官、做学问、做生意。
但在古代中国,甚至在改革开发以前的中国,读书人能选择的道路中其实并没有经商做生意这条路。
在读书人面前,除了做官和做学问这两条路,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如同足球比赛场里一个被罚了点球的守门员,当球飞来的一瞬间,或者向左或者向右扑救,简单而明了。
在法律职业群体中,具有智力服务性质的经商之路,比如象律师这样的职业,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生存和发展的时间并不太长。
不过,无论是做官、做学问还是做生意,三者倒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都要往大里做”(听众笑)。
为了使我们讨论的问题简单化,我还是在这里试图将这个法律职业群体规定在狭义的范围内。
比如,我主张首先包括下列几类人员:
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还有法学教育工作者。
当然,如果从广义上说,法律职业群体中还可以包括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人员、各级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公务员、工商、税务、海关、城管、公证、新闻出版、审计、监察等部门的人员,企业专职法律顾问人员,当然,还可以包括拥有“双规”权力的各级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人员(听众笑)。
2,中国法律职业群体成长历史的简略回顾:
严格意义上说,在一百年前,我们中国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律职业群体。
回顾一下这个特殊群体在这一百年里经历的曲折、坎坷,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法律职业群体曾经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尴尬的一个群体。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有很多学者并不愿意正视、也不愿意叙述甚至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我们中国今天正在使用的一整套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职业群体的分类,几乎全部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借鉴和移植过来的。
所以,它们基本上不属于我们所谓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
所谓传统,是本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到现在仍然还在承继和习用的东西。
但是,近现代法律制度、法律职业群体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5000多年的文化里并不存在。
有意思的倒是,这些西方的舶来品进入中国之前是干干净净、道貌岸然的,但来到中国的土壤之中后,则很快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沾染上顽强的本土情结。
简单回顾一下,1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
当我们开始把鞋分成左右脚的时候,将公路分成左右侧的时候,把学校分成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把医院分成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时候,中国人也同时把法律从业人分成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法律教授这些专门的职业类型。
中国的法律职业群体其实是个舶来品。
法律职业群体形成的三个阶段
中国的法律职业群体在清末民初曾经初露端倪。
清末新政中的修法运动,导致大量西方近代法律学说和法典被介绍和移植。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此举突然断绝了天下无数读书人通过考取状元和秀才进入社会上层的唯一路径。
因为过去考秀才、状元的路被封闭了,这一大群人顿时觉得惊慌失措、无路可走。
柳暗花明之间,刻苦读法律,来日去当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的出路,成为很多读书人最新、最时髦的选择。
法学教育从无到有,风靡一时。
在上个世纪初的1907-1919年前后,全国法政专科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生达到数万名之多。
国内专门研究民国法律史的俞江教授曾告诉我,他从研究资料中发现,当年仅在江苏武进(今属于常州)一地,法政学校就有不下三十所之多。
我们今天知道的著名的东吴大学、朝阳大学(1913年创办)都是当时诞生的著名法科学府。
现在的兰州大学的前身,就是一所法政学堂。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曾对美国记者斯诺提及,自己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也曾经在湖南长沙试图报考“法政学堂”。
他交了一块大洋的报名费,但最终他还是去读了湖南长沙第一师范。
然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后,社会变革开始走入激进的道路。
在后来发生的一连串北伐战争、军阀混战、国共分裂并武装对峙中,法律职业群体整体陷入尴尬和失业状态。
大量“法政学校”随即关门和倒闭。
在各派势力混战的年代,当年法政学校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弃笔从戎,成为军人。
从军者,除了一部分人为了信仰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就业。
在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大量农民破产、知识分子失业,当兵有军饷、有饭吃,当兵成为一种就业方式。
我们知道,当时很多贫苦人参加红军,最开始很难断定他们真的搞得懂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
我看到一个老红军的回忆录,他说自己15岁参加红军。
红军师长问他,你为什么参加红军?
他说当红军升官最快,从小跟我一块放牛的人,比我当红军早三个月,现在已经当班长了。
当然这些人当了红军以后,在革命的队伍里接受锻炼和教育,最后追求一种理想,这都是后话了。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贫困百姓参军确实是与就业有关。
从1927年-1937年之间,法律职业群体的发育获得了第二次机会。
此时国民政府基本上统一中国,控制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
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在城市里转入地下,或在农村则活跃在极欠发达的崇山峻岭中,或者行进在万里长征的艰难路途中。
此时,尽管当时也是“万恶的旧社会”,但整个国家,特别是城市生活基本出于相对稳定发展之中。
期间,大批在海外学习法律的人才纷纷回国效力,比如吴经熊、杨兆年、史良章士钊这些人法律人士发挥了很多作用。
国民政府在这个期间制定了著名的“六法全书’,设立了比较齐全的司法审判机构。
不过,这些从西方照抄照搬过来的法律舶来品,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形同“船虽大但池水浅”,这些东西无疑处于搁浅状态。
政法大学一个很优秀的青年教师叫陈夏红,写了一本研究那段时间的历史人物的书。
大家有兴趣可以阅读研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地区为主的外国租界内,却意外涌现和成长出一批本土法律职业人才。
在华洋混杂的租界内,活跃着一批以法律为职业的群体。
租界内的治外法权,显然是清末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后丧权辱国的产物,对此,中国人将没齿难忘。
然而,由于租界法庭直接引入近现代欧美国家比较先进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应用,使一批本土人士积累了知识和经验,并对其后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租界里的法律事件和人物,今后势必成为中国法律史学界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生动有趣但又苦涩尴尬的研究课题。
1937年,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呼声。
法律职业群体面对战火烽烟再次无可奈何。
尽管我们还可以从陪都重庆或上海租界里找到若干法律职业人士的背影,但这个阶段的法律群体显然很难进入人们的视线中。
二次大战结束后,法律职业曾获得短暂的光环。
特别是“东京大审判”中梅汝璈、倪征墺这些法律专业人士的多目光环,再次唤起很多青年人对法律职业的向往。
那个时候,北方的朝阳大学,南方的东吴大学这两所法科大学重新受宠。
法律职业人才又开始活跃起来。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
很快,国共之间和谈破裂,内战爆发。
在中共完成建国大业的时刻,原有的法律职业人一部分人留在大陆观望,还有一部分随国民党逃逸到台湾孤岛。
留在大陆的法律职业人在经历了镇压反革命、反右、文革等数次运动后,相当一部分人被改行,也有不少人遭到不公正的待遇。
在国内有限的几所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里,教师们小心翼翼地模仿苏联法律教科书编写出简陋的教材,勉强讲授一些残缺不全的法律知识。
文化大革命中,大学停办。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红卫兵领袖的谈话中,毫不掩饰地对法律教育表示出怀疑和轻蔑的态度。
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
在强调文科需要改革的同时,毛泽东特别说到:
“法律还是不学为好。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不久,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相继被撤销,出现了长达8年之久的法学教育中断。
在当时国内公检法均被砸烂的情况下,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的命运可想而知。
话说逃到台湾的那批法律人,开始也度日如年,惨淡经营。
但还可以残喘为生。
我2008年去台湾访问时,在台北的龙山寺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本法律旧课本,是1954年出版的《民法原理》。
由于印刷和装帧简陋粗糙,我已经不忍轻易打开翻看,因为每翻一页,均可能严重破损。
当年台湾法律人的艰辛岁月,可见一斑。
有趣的是,在蒋家父子几十年的军管统治下,1927-1937间建立的民国法统基本保留下来了,并成为台湾在全球化潮流中经贸快速发展的重要砥柱。
台湾法律界有人开玩笑说,台湾后来经济起飞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得益于老蒋带到台湾岛上三件宝贝:
一支军队、一船黄金和一本六法全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
27天后,以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秘密逮捕。
由此,中国历史出现重要拐点。
1978年,中国启动了艰难曲折同时也是辉煌宏大的改革开放。
此时的中国,如同“大病初愈”,百废待兴。
“四人帮”后来被押上临时组建的特别法庭上接受审判。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中国律师此刻再次登台亮相。
此后,政府开始全面启动国家的法制建设,中国的国家在立法、司法、法学教育出现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法律职业群体由此获得重生和蓬勃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3、中国法律职业群体在规模和数量上已然形成
说到“群体”,当然就不是一个两个人,一定是有数量有规模的。
我简单地在网上做了一个研究,如果把中国法律职业群体狭义地限定在五种人,中国法律职业群体的人数到底有多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法制化的进程,法律工作者的数量和文化素质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
法官数量。
中国法官的数量已经从1981年的6万人,发展到2009年的189532人。
怎么数字还有零头?
很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从很多渠道找到的统计数字,都是很笼统的。
但是意外发现,2009年中国女法官协会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法院系统有女法官44502人,占法官总数的23.48%(听众笑),结果,我们可以利用并不复杂的数学方程式,计算出全国法院法官的总数。
统计数字说,在法院系统就业的人数,全国有30余万人。
检察官数量。
全国的检察官1986年有9.7万人,2004年的报告是12万人。
估计现在的数量与人民法院的数字差不多;
律师的数量。
律师的数量从1981年的8571人,发展到现在有16.6万人,全行业从业人员22万多人。
这里还有一些数字:
全国的律师事务所现在有1.5万多家,全国律师担任各类诉讼和代理是1967784件,2008年律师业务费达到309亿元,上交税收40多亿。
到现在为止,全国共有3976名律师担任全国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其中16名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2名律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法学教育。
法学教育发展得非常快。
我是1979年入大学读法律本科的,那时全国政法院校不到10所。
2009年,全国法律院校将近700所,每年大专以上法律专业毕业生从改革开放不足1000人,发展到现在每年超过十几万人,法学院也几乎每年都在增加。
公安干警人数。
警察构成非常复杂,腾讯网上有个数据,全国公安警察将近160万。
我没有看到过国家公安部公布的官方数字。
警察又分公安、森林、铁路等很多种类。
所有这些数字加起来,中国法律群体大约300万人左右,占全国人口2—3‰。
从数字和规模看,中国这三十年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庞大的法律职业群体,这一点不应该有所怀疑。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三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法治是有明显进步的。
我们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到中国法治进步的脚印,比如从某一年开始,野蛮的民间私刑被禁止;
从某一年开始,律师可以参加公开的法庭审判;
从某一年开始,某一个不合理的政府条例被废止……。
我们看到,每一个庭审、法案、辩论,很多法律人都非常艰辛地默默地推动着我们国家的进步。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和这类进步有关的,也许不一定是一次又一次的血与火的革命和战争,也许不一定是某个领导一个接一个的理论口号,也许不一定是一轮又一轮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
很多证据证明,法律专业已经从过去的绝学变成名副其实的显学。
这三十年里,很多个案证明,在中国很多领域,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们,已经可以比较自信地为自己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
比如说很多读法律的当了政府官员、法学教授、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企业家、商业顾问、编辑和记者等等。
中国法律人刚刚翻开的,可能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中最充满生机的一页。
近年来,大学扩招,法律专业学生出现暂时过剩,这个问题显然超出了我们今天讨论问题的范围。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国大历史”的结尾部分颇为乐观地写道:
“中国缺乏西方式法治,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
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
因为它的缘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外蒙受重大牺牲。
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为它流泪。
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治生涯人士的黄金时代。
”
听说江泽民先生任总书记在任内时曾参加过一次中国法学会的大会,他在会议上脱稿发言说,他在国外访问时发现,国外政要们大多是律师和法官出身,看来我们今后的领导层也要加强这方面专业背景的人才。
若干年前,我们大陆的领导人,在记者面前站成一排,几乎全是工程师出身。
(众人笑)不过,不知道大家最近是否注意到,最近这一轮的大陆的领导人,在记者面前站成一排,其中已经有几个法学博士了。
黄仁宇的书是在几十年前写的。
他的预言似乎开始显现。
但是,我们还是要执着地追问:
中国法律人士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吗?
下面,我们谈第二个问题。
这个关系网是不是已经蜕变成法律职业群体蒙羞的“江湖”?
第二个问题,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的群体,这个群体是不是存在着一个关系网?
这个关系网是不是出了问题?
是不是已经蜕变成法律职业群体蒙羞的一个“江湖”?
我属于改革开放以后头几批进入法学院读法律的大学生。
现在的80后、90后的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代人很幼稚,带有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重庆读书的时候,在电影院看一个墨西哥电影《冷酷的心》,这个电影结尾有一个法庭辩论的高潮戏,男主人公、被告“魔鬼胡安”当庭痛斥以权谋私的检察官,台词非常精彩,上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的配音也很动人。
当时我记得,同学们看到这个场景时,电影院里掌声雷动。
大家非常激动,觉得将来我们毕业以后,也能为冤屈的人伸张正义,为社会公平实实在在地做一点事情。
我们原来很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一年又一年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法律人才,制定一个又一个法律法规,设立一个接一个司法机构,不管将来有没有一个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我们就可以昂首阔步走进一个光辉灿烂的法治新时代了(听众笑)。
今天看来,我们的这种想法太幼稚了。
其实,我们严重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律制度归根结底还是要由人,由每一个有七情六欲的自然人来执行的,这些人是由普通的俗人组成的,这些人不是天生就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些人是可能结成一个营造腐败的关系网的。
我可能是一个想象力不够丰富的人,我的很多知识和对事物的认识都来自我的亲身经历和阅历。
我写的很多随笔,也大多是我对亲身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情的叙述。
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讲几个我亲身经历的法律案件实例。
第一件事发生在1998年。
我当时在美国为一个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富豪做投资法律顾问。
这个富豪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发达起来的“乱世英雄”,在中国沿海城市做房地产很成功。
后来带着巨款到美国投资并定居。
这个人个性豪爽、行事张扬,特别喜欢结交大量演艺界的明星。
他在中国一个省会城市和一个女演员发生了不动产纠纷,希望我到当地去帮他处理。
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我到达这个省会城市以后,找了一个当地律师跟我配合,这个是聪明能干的年轻女律师。
明天上午要开庭了,今天晚上那个女律师打电话给我说:
“周先生,情况不妙,我已经查明,明天开庭时对方请的律师是这个法院院长的妹妹。
”我一听这个事情,也感到事情可能很复杂。
没有办法,只能开庭后到法庭上见分晓了。
开庭以后,果然看见那个身份特殊的“妹妹”就坐在我对面。
大家知道,法院有一个申请回避程序。
下边的事就很有戏剧性了。
我举手请求发言:
“审判长,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律师,据我们了解,是贵法院院长的近亲属。
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她在本案出任代理人是违反规定的。
她坐着这里,会给庭审人员带来无形的压力,势必会严重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并使案件审理发生不公正的。
所以我申请这位女律师回避。
请问在座的律师,我这样讲对吗?
(有听众答复:
不对。
)
是的,很多人知道,我的这种说法是明显违背法律常识的。
我也知道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但我之所以要将错就错,目的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件事直接说出来。
正常情况,我应当申请所有的法庭庭审人员(包括书记员)回避,这样就搅局了。
所以我只好将错就错把这个事呼喊出来,而且要书记员记录在案。
这时候,法官只好宣布休庭,进入合议庭合议程序。
合议结束后,审判长宣布说,刚才原告代理人提出的回避要求是不符合规定的,因为对方的律师不是庭审人员也不是书记员,不在回避的人员名单上,现在当庭驳回此请求,法庭继续开庭。
我当场回答说,我接受法庭的合议结论,但请求书记员记录在案。
但书记员并不愿意记录这一段内容。
我当庭表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