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马克思幸福观对非共在性思维的超越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独家马克思幸福观对非共在性思维的超越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独家马克思幸福观对非共在性思维的超越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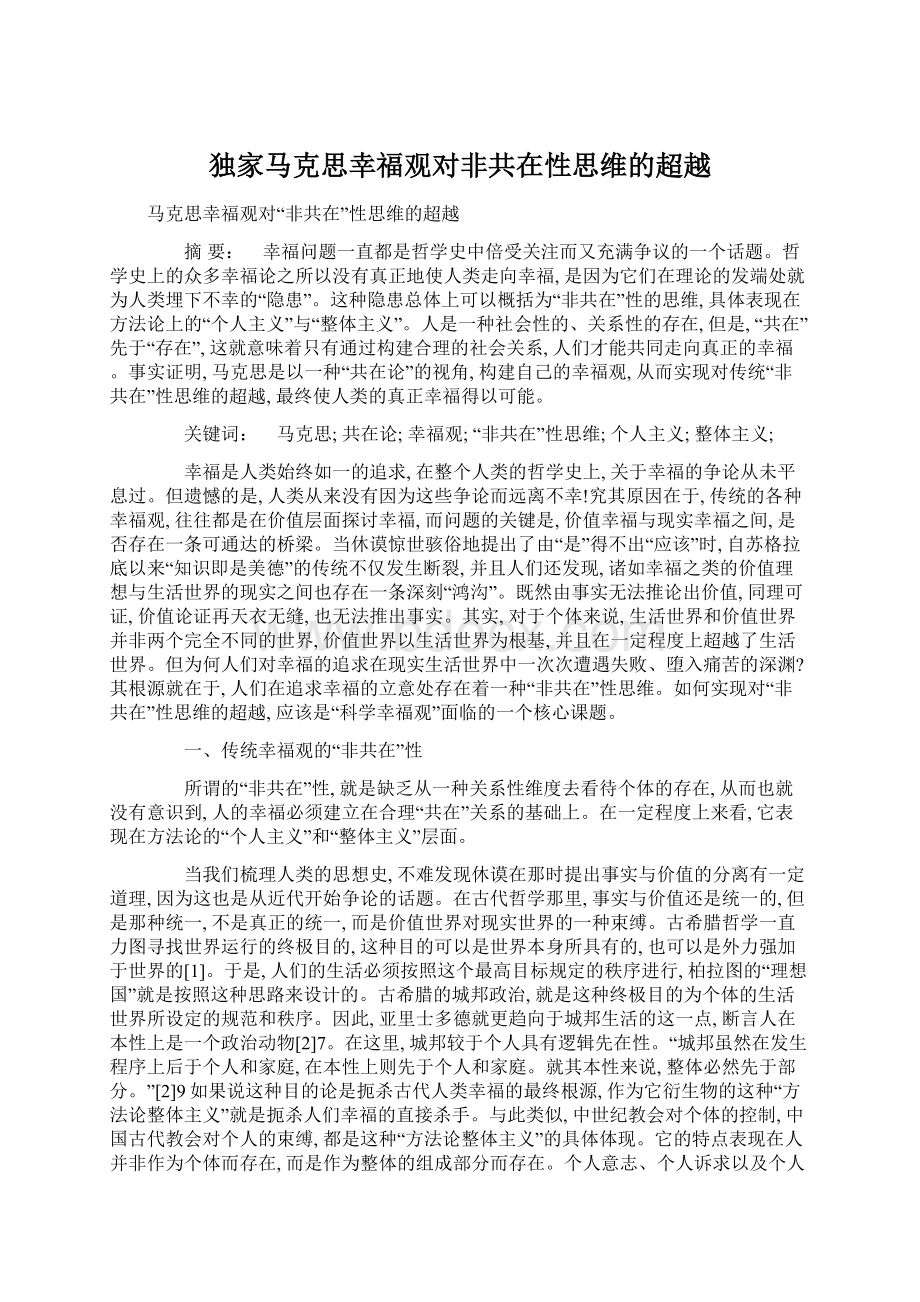
其根源就在于,人们在追求幸福的立意处存在着一种“非共在”性思维。
如何实现对“非共在”性思维的超越,应该是“科学幸福观”面临的一个核心课题。
一、传统幸福观的“非共在”性
所谓的“非共在”性,就是缺乏从一种关系性维度去看待个体的存在,从而也就没有意识到,人的幸福必须建立在合理“共在”关系的基础上。
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它表现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层面。
当我们梳理人类的思想史,不难发现休谟在那时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有一定道理,因为这也是从近代开始争论的话题。
在古代哲学那里,事实与价值还是统一的,但是那种统一,不是真正的统一,而是价值世界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束缚。
古希腊哲学一直力图寻找世界运行的终极目的,这种目的可以是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也可以是外力强加于世界的[1]。
于是,人们的生活必须按照这个最高目标规定的秩序进行,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按照这种思路来设计的。
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就是这种终极目的为个体的生活世界所设定的规范和秩序。
因此,亚里士多德就更趋向于城邦生活的这一点,断言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2]7。
在这里,城邦较于个人具有逻辑先在性。
“城邦虽然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
就其本性来说,整体必然先于部分。
”[2]9如果说这种目的论是扼杀古代人类幸福的最终根源,作为它衍生物的这种“方法论整体主义”就是扼杀人们幸福的直接杀手。
与此类似,中世纪教会对个体的控制,中国古代教会对个人的束缚,都是这种“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具体体现。
它的特点表现在人并非作为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
个人意志、个人诉求以及个人行为隐没在城邦、教会或者是宗族的意志之下,个人没有任何自由可言,自然而然幸福也就无从谈起。
自近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的目的论已经被机械的因果论所取代。
人们对整个世界乃至人类自身的理解都惯用于一种机械式的拆分眼光。
人的生存世界自此被拆分为“广延”与“思维”、“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的双重世界。
由此,人们开始在双重世界中偏激地各执一端,要么走向彻底的唯意志论,要么走向彻底的决定论。
无论选择哪条道路的人们,都认为自己这条道路是通向幸福的大门,实际上,他们又难于到达幸福的此岸。
在价值排序上,如果说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强调的是“整体先于部分”,那么到了近代,“天赋人权”的理念则把价值目标指向抽象的个体,指向个体的自由和幸福。
相应地,古代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也就转向了近代单子式的“个人主义”。
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基于一种个体的理性而存在,追求排他性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它常常陷入一种敌对思维。
例如,作为近代契约论逻辑前提的“自然状态”,在霍布斯的解释中,就是一种“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既孤独又残忍,“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达另一个目标的不断发展”[3]。
从其本质而言,幸福的条件就是保证人们追求欲望的道路畅通无阻。
显然,这种互相敌对的状态又成了通达幸福的一种阻碍。
归根结底,方法论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方法看待个体的存在与价值的排序问题。
而它们最终的根源在于,存在论上对个体的存在做了单一性的、抽象性的理解。
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再次使人们的价值目标和现实生活之间出现一道屏障,就像卢梭所说的“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处处身戴枷锁”[4]。
事实上,启蒙运动在价值层面推行的“天赋人权”,只不过是让人们近于望梅止渴享有的自由和幸福,却从未真正卸掉身上的“枷锁”。
因此,这一点遭到了黑格尔的强烈批判。
黑格尔认为,自由的出发点不是单个的、孤立的“自我意识”,正是相互差异而又统一的自我意识整体才构成了绝对精神,“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5]。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道德”和“伦理”关系的论述,对于家庭、市民社会以及国家关系的阐述,可以说已经有意将对人们幸福的研究由一种个人性视角转向一种“共在论”的维度。
他认为个体获得自己的权利,是建立在他成为良好国家公民的基础上[6]。
个人的幸福也必须置于一个公共性的视角下给予考虑,同众人的福利交织在一起,才是最可靠的,并且某种程度上还能够实现。
由此而来的遗憾是,黑格尔对幸福问题的论证又回到了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是因为它过于强调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优先性。
但是,这种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较古朴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来说是一种质变,它的普遍性是建立在对特殊性承认的基础上。
就这样,幸福的道路在“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徘徊。
重返马克思的出发点,从最初的方法论出发追求幸福,便成了首要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认为马克思的幸福观是建立在一种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基础上,它强调集体权威的至上性,强调集体对个人地位的优先性以及个人幸福在集体利益面前的从属性。
这种认知结果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错误判断。
马克思对幸福的追求正是为了超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以此建立一种从“共在论”的视角出发,探讨现实的、有路可寻的幸福观。
二、马克思幸福观对“非共在”性思维的超越
众所周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实践”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都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
通常意义上,我们理解的这次清算,都只看到了字面意义,即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批判了唯心主义过分强调了人的能动性方面而走向神秘主义。
不可否认,我们忽略了马克思这次清算的深层意蕴,即“实践”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以及它与“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间的关联性,并由此道出了“现实的人”的本质。
如前所述,在黑格尔的整体主义哲学中,国家高于市民社会,人是“大写的人”,也即大写的国家。
因此,马克思对“现实的人”本质的界定,是由于其强调了社会性和关系性,而对黑格尔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超越。
但是,在此之前,马克思曾经还一度痴迷于费尔巴哈的人类学。
费尔巴哈自称他的人类学为“新哲学”,因为自己超越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的视角,从一种感性的、生理的角度来理解人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更倾向于这种“新哲学”,因而他把劳动作为人类的一种本质活动,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本质”的界定。
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里,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类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一样,都是从“整体主义”的视角来把握人,它们强调的都是“大写的人”,只是前者从感性的角度出发,后者从理性的角度出发。
因此,马克思用“社会”范畴批判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建立在人们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地上的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又是什么呢?
[7]”“社会”范畴不仅能够凸显人的整体性和共同性,而且能够体现个体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性和交互性,可以说它体现了一种明晰的“共在论”维度。
马克思对人的现实本质界定,在超越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同时,也堪比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当然,在马克思之前,施蒂纳早已将靶子瞄准了费尔巴哈及其“新哲学”,他指出费尔巴哈并没有突破黑格尔的普遍主义,因此还是旧哲学。
然而,施蒂纳力图建立一种真正的“个人”哲学,也称“唯一者”哲学或者“自我哲学”。
但他这种做法在批判费尔巴哈“类”实体化的同时,又把“自我”给予实体化,他批判了“大写的人”,却又走向“小写的人”,最后走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大加批判。
同样,他们从“社会”的概念出发来批判“唯一者”,施蒂纳的观点与近代自由主义相似,他认为“唯一者”的独立性和至上性是基于他对私有财产拥有排他性的所有权,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尖锐地指出,私有财产恰恰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不是施蒂纳所理解的固有静态物,而是在人的交往中动态地产生。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的主体不是抽象、孤立、离群索居的“唯一者”,而是“现实的个体”,也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体,更是“共在性”中的个体。
据此,基本可以明确马克思把“实践”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联系在一起的初衷。
“感性的人的活动”体现在,实践是一种现实性的力量,它包含能动的主体性,却不是任何一种神秘的实体性力量,它的主体性让人并非单纯地依附于团体或“类”的生理性、情感性存在,而是在积极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与他人产生交往和合作、缔结社会关系的“共在性”存在。
马克思从这种“共在性”的视角出发,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的幸福必然通过改造世界的活动,促成人类社会历经否定之否定的跃迁才能最终实现。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和“自由个性”阶段进行了描述。
相应地,这些阶段对应着“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8]15。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是以共同体的形式而存在,人的存在产生于共同体,或者说为了共同体而生产,虽说共同体对个人来说无异于一种权力的宰制,但个人恰恰只有臣服并依附于这种赤裸裸的宰制,才能找到存在的依托,人与人的关系也只有在共同体的标签下才能找到连接纽带,成为内在于共同体的关系。
由于尚无对个人自由和幸福的诉求,这种共同体的充其量只能自然而然地结成“自然形成的共同体”。
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人的自主性萌生与在此推动下社会制度的陡然转型,催生出人身依附关系的断裂以及原有共同体权威的土崩瓦解。
同时,基于新型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的生产关系,“自然形成共同体”阶段那种赤裸裸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在后续的发展中建立在等价的原则上,这种原则是一种看似平等的交换关系。
由于交换是建立在交易双方具有独立人格和自主权力的前提下,所以它实际上是由前一阶段依附于共同体的内在关系转变为另一种外在关系。
然而,此时人的独立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因为人虽然脱离了他的依赖性,却又陷入了一种“物的依赖性”,即对商品、货币、资本以及对机器的依赖性。
但“物的关系”背后依然是“人的关系”,它体现出了人的那种“异化”,既包括人对于自身本质的异化,又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那么,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挣脱“异化”的局面,既摆脱“人的依赖性”,又摆脱“物的依赖性”,褪去自由的幻象,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并建立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
到那时,建立在“共在论”基础上的人的现实幸福才能够真正实现,这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的存在以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考量正是从一种关系性视角出发。
或者说,在马克思看来,人就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社会的发展阶段也是社会关系的多次飞跃,抑或是“在前资本主义共同体中具体的特殊的内在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的普遍的外在关系;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具体的普遍的内在关系”[8]16。
需要强调的是,通过揭示人的发展本质,可以更好地论证这种辩证否定关系的内在逻辑性。
马克思指出了人的存在离不开关系性,但马克思并没有把个人当做完全的关系附属物,而是把独立现实的自由个体看作是他们进入社会关系的一个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的社会关系完善的过程,也正是人的幸福得以实现和确证的过程。
关系性与个人性使对方具有现实性,马克思正是通过这种“社会性的个人”或“关系性的个人”来界定人的“共在性”存在方式,从而驳斥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也批判了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以此来奠定马克思幸福论的坚实根基。
三、马克思“共在论”幸福观如何实现
对人的关系性存在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前提,马克思认识到了“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
人就是全体的世界,就是国家和社会”[9]。
因此,追求人的幸福,就必须从对人的世界、国家以及社会的批判性重构入手。
“废除作为人民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
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种需要幻觉的处境。
”一个“人民的现实幸福”,实际上摆明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鲜明立场。
马克思并未用过多笔墨论述幸福问题,更没有像传统的幸福论那样在个体的完善与快乐间兜圈子。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一生的所有努力都致力于要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
其实,马克思的幸福观发生了一个重心转移,即从抽象地探讨幸福是什么,即“何谓幸福”的问题转向了“幸福何以可能”或“何以幸福”的问题。
既然,马克思主义没有单独论述他的幸福观,我们就要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重构它的幸福观。
结合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断定,在马克思那里,幸福应该包含以下两个层次的含义:
其一,指向人作为能动的主体,通过自主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来确证和彰显自己创造性本质的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灵魂层面的愉悦体验,就这个层面来看,幸福直接指向马克思的终极价值目标,那就是自由;
这个层次并未彰显人的关系性本质,所以幸福还应该包含另外一个层面的含义,那就是基于人的“共在先于存在”这个前提通过人与人在实践中的合作、交往、互助而实现“共福”,这里的幸福指向“真实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
如果说第一个层次指出了马克思幸福观的基本要义,回答了“何谓幸福”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层次就构成了马克思幸福观的现实基础和实现路径,回答了“何以幸福”的问题。
同时,在上述论证过程中,实际上也勾勒出幸福的主体,那就是“谁的幸福”。
据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幸福观不仅是基于一种人本主义的关怀,而且又关乎一种“共在论”的视角。
当然,我们对马克思幸福观的解读不仅是为了寻找逻辑上的清晰性。
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两者是统一的,毋宁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恰恰就是一种“共在论”视角下的人本主义。
幸福的第一个层次而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马克思还有着费尔巴哈“类哲学”的倾向时,就已经明确地把劳动作为人类的本质。
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劳动本应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是人的幸福源泉,然而事实却是“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10]52。
这种劳动异化实际上是人的异化,它本应是幸福的源泉,却转而成了不幸的根源。
而这种异化又是什么造成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加清晰地揭示了这种异化的根源,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就是建立在劳动力成为商品这种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上。
工人的劳动已经不是彰显自身幸福本质的目的,而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11]。
然而,工人阶级的不幸,却成了资本家“幸福”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他们可以借助对工人的榨取不劳而获,享受安逸,以及享有通过财富带来的社会地位和优越感。
对此,马克思援引孟德维尔的话说:
“要使社会幸福,使人民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让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
”[12]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结果,即以一个阶级的不幸换取了另一个阶级的幸福。
如果我们认真思考,就会发现这里似乎还存在一个亟待追问的问题,资产者或者说是食利者的“幸福”就是真正的幸福吗?
对此,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
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曾经借卡莱尔之笔一语中的:
“从业的先生没有更幸福,寄生先生的土地占有者也没有更幸福。
”[13]632事实上,如果遵循马克思对幸福的理解看过去,作为食利者的资产阶级也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不劳而获、贪图享乐充其量只能获得一种消极的自由,并不是幸福所追求的目标。
当然,以安逸为幸福的观点并非无源可溯,在哲学的思维范式中,“必须汗流满面地劳动”是上帝对亚当的诅咒。
因此以亚当·
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安逸作为一种“适当的状态”,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对象。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低级的“幸福”完全体现不出人的尊严,因为“它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13]636。
也就是说,以安逸为幸福无法彰显人的创造性本质,而以吃喝享乐为幸福则是对人尊严的贬损。
继而,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出发,深入剖析了这种消极幸福观的根源,即“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件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的”[14]。
也就是说,奴隶劳动、徭役劳动以及雇佣劳动并不合理、“非共在”性的生产关系,成为最令人厌倦的事情,不劳而获却成了幸福的范畴。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所有不平等、不合理、“非共在”性的生产关系中,无人幸福。
要获取“人民的现实幸福”,必须建立一种迥别与以往的、新型的、“共在性”的生产关系。
那么,这种“共在性”的社会生产关系又是什么样?
即是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那种外在交换关系的新型的、合理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一种内在的、直接的关系,“共同生产作为生产基础的共同性前提。
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15]21。
在这样的关系中,个体无须为了与他人的交换进行生产,更无须为了生存不等价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的生产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
同样,不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他所享用的劳动产品也是有他自身参与其中的共同劳动。
生产资料属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共同生产的相互依赖关系。
当然,这种依赖关系不同于人类社会初期的依赖关系,最初的“人的依赖性”关系中,共同体凌驾于个体之上,使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成为无稽之谈,而共同体就是这些相互依赖的个体本身,人们的共同生产实践既保证了共同体的凝聚力,同时也能满足每个成员的需要。
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人们不再惧怕、不再逃避劳动,“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会成为个体的自我实现”[15]122。
当然,人们也能从这种自我实现中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在这种生产关系中,没有谁的劳动是他人获取幸福的手段,每个人都力图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和互助结成一种“真正的共同体”,以期追求一种共同的幸福。
并且,这种共同的幸福不以牺牲任何个体的幸福为代价,相反,它以个体的幸福为前提。
通过重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幸福观,我们再次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阐述的统一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证明了自己是类存在物。
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性类生活。
”[10]53-54在这里,马克思概括了人的类本质,即“生产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提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
综合这两个论述,把“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真正本质,也就形成了追求“人民现实幸福”的合理路径。
这也是我们重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一个主要方向。
四、结语
幸福不是一个僵化的目标,幸福问题实际上内在地包含着“谁的幸福”“何谓幸福”“何以幸福”三个问题,只有对这三个问题合理而恰当地回答,才是具有现实性的幸福观。
马克思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其切入点,从“共在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只有破除宰制人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实践中构建以“现实个体”为前提的“自由人联合体”,人的合理“共在性”关系才有可能得以实现,“现实的幸福”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
该思路完整而合理地把上述三个问题逐一给予解答,使马克思的幸福观具有客观现实性。
参考文献:
[1]王南湜.决定论、自由与规范——价值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J].哲学研究,2013(4):
3-12.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3]托马斯·
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
72.
[4]卢梭.社会契约论[M].李平沤,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4.
[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
122.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1:
172.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7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450.
[8]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
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M].王虎学,译.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3.
[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11]马克思.资本论:
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582.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M].北京:
675.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0:
38.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