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上英语翻译Word下载.docx
《大一上英语翻译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大一上英语翻译Word下载.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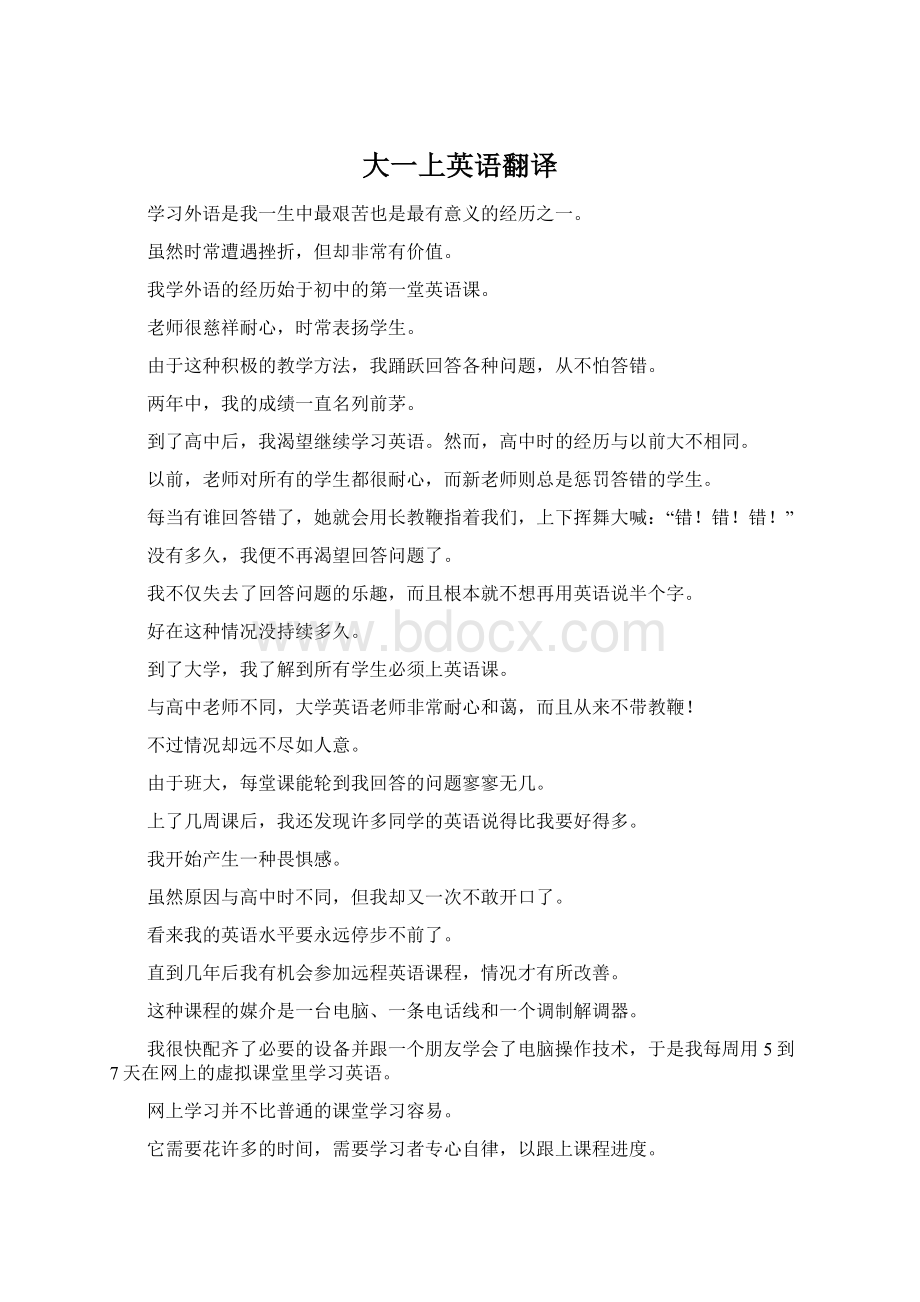
学习一门外语最令人兴奋的收获是我能与更多的人交流。
与人交谈是我最喜欢的一项活动,新的语言使我能与陌生人交往,参与他们的谈话,并建立新的难以忘怀的友谊。
由于我已能说英语,别人讲英语时我不再茫然不解了。
我能够参与其中,并结交朋友。
我能与人交流,并能够弥合我所说的语言和所处的文化与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之间的鸿沟。
收音机“咔嗒”一声,摇滚乐就大声地响开了。
音乐像枪声似的将桑迪吵醒。
她看了一下钟,早上6点一刻。
她躺在床上,听着她喜欢的电台广播,嘴里哼着歌词。
“桑迪,”她父亲喊道,“桑迪,把音乐关了!
史蒂夫·
芬奇冲进她的卧室。
“你为什么一定要听这么糟糕的音乐?
还听了一遍又一遍。
虽然有节奏,可恐怕不是真正的音乐。
“我喜欢这种音乐,爸爸。
这是我最喜欢的。
您听一下吧,您肯定会喜欢的。
”
桑迪伸手把音乐开得更响。
“别,别开那么响,我受不了。
把收音机音量调低点,这样我和你妈妈就听不到了。
我敢肯定,那音乐既伤你的耳朵,又伤你的大脑。
桑迪走进浴室,打开淋浴喷头。
然后她抓起香皂,浑身上下洗个遍,连头发也洗了。
淋浴后,桑迪梳了梳头发,穿上一件旧的绿色圆领衫和一条牛仔裤。
接着她化好妆,走进了厨房。
和往常一样,她不知道早餐该吃什么,便抓了杯牛奶,站在洗涤槽旁吃烤面包。
就在此时,她妈妈简走进了厨房。
“桑迪,你怎么不坐下吃饭?
站着吃饭对身体不好。
“我知道,妈妈,可我没时间坐着吃。
“昨天做作业了吧,宝贝?
“做了。
“刷过牙了?
“妈妈,我还没吃完饭呢。
吃完了再刷。
“桑迪,你怎么穿那件旧圆领衫呢?
难看死了。
“妈妈,请别这样。
“别怎么样?
“别这样烦我。
“桑迪,你怎么描起眼线来了?
“我是描了,妈妈。
我都描了几个月了。
难道不漂亮?
“桑迪·
芬奇,你还小,不能化这么浓的妆。
“妈妈,我都15岁了,到了可以化妆的年龄了。
给您说实话吧,学校的女孩子都化妆,有些还文身,有的还戴耳环、鼻环、舌环呢。
妈妈,我现在没时间给您说,我快迟到了,得走了。
再见。
桑迪匆匆吻了一下妈妈的脸颊,拿起书冲出了屋子。
桑迪离家上学后,简·
芬奇平静地坐下来喝咖啡。
没过一会儿,她丈夫走了进来。
“史蒂夫,喝点咖啡吧?
”简问道。
“不,谢谢,亲爱的。
我胃不舒服,心乱如麻。
可能是因为那讨厌的音乐每天早上把我吵醒。
我想我还不至于老得落伍吧,可没完没了地听那毫无韵律、令人讨厌的歌曲实在让我生气。
“你知道,亲爱的,不同年龄的人喜欢不同的音乐,”简劝说道。
“还记得我们听过的一些音乐吗?
史蒂夫笑了,“你说得有道理。
也许吃点早饭能让我感觉好一点。
“你注意到了吗,今天早晨我们15岁的女儿都化了什么样的妆?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以前没有注意到。
我想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我们女儿的最大问题还只是化妆。
我看到其他年轻人在镇上游手好闲,还文身,浑身穿了许多洞。
“令我担心的是,”史蒂夫说,“那种音乐对桑迪可能有负面的影响。
我不知道我们的女儿到底怎么回事。
她在变,我很担心她。
化妆品,糟糕的音乐,谁知道以后还会有什么花样?
我们得和她谈谈。
新闻里报道的尽是惹上麻烦的青少年,可他们的父母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问题。
“哦,我倒不认为她的音乐如此糟糕。
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说得对,我们需要和桑迪谈谈,”简说道。
去上班的路上,简·
芬奇一面开着车,一面想着她的桑迪。
她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得对桑迪说什么。
她和桑迪之间还可以进行交流,这令她很高兴。
她知道自己得有耐心,得保持自己和桑迪之间沟通的渠道畅通。
她想在桑迪的身边,做她的保护人,同时又给她寻找自我的自由。
在我还未成年时,如果有人看到我和父亲在一块儿,我就会觉得难堪。
他腿瘸得很厉害,个子又矮。
我们一起走路时,他的手搭在我臂上以保持平衡,人们就会盯着看。
对于这种讨厌的注视,我打心眼里感到别扭。
即使父亲注意到这些或感到不安,他也从不表露出来。
我们的步伐难以协调一致——他常常停下脚步,而我的步子却显得不耐烦。
正因为如此,我们一路很少说话。
但每次出门时,他总说:
“你按你的步速走,我跟着你。
我们通常就在地铁口和家门口之间来回,那是他上班的路线。
他生病或天气恶劣时也坚持上班,几乎从不缺勤。
他总是准点到办公室,即使别人做不到。
这是件可以引以为荣的事。
当路上覆盖冰雪时,即使有人搀扶,他也难以行走。
这种时候,我或者我的姐妹们就用一辆带有钢轮的儿童推车拉着他穿过纽约布鲁克林的街道到地铁站口。
一到那儿,他就紧抓着地铁口的扶手一直往下走,因为地铁内比较暖和,下面几级台阶没有冰雪。
曼哈顿的地铁站直通他们办公楼的地下室,他不用出站(就可到办公室)。
下班回家时,我们会去布鲁克林的地铁站口接他。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惊叹:
像他那样一个成年人,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能承受这样的屈辱和压力,而当时他却显得毫无痛苦,也没怨言。
他从不说自己可怜,也从不表现出对那些比他幸运或健康的人的羡慕。
他从别人那儿寻找的是一颗“好心”。
一旦找到了,那人在他心目中就是个大好人。
现在我长大了,我相信这是判断一个人的标准。
虽然我还没有确切理解什么是“好心”,
但我知道自己有时候并没有这么一颗“好心”。
虽说很多活动父亲都不能参加,但他还是试着以某种方式来参与。
当地一个棒球队缺少一个经理时,是他使球队正常运转。
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棒球迷,常常带我到埃贝茨球场,观看布鲁克林道奇队的比赛。
他喜欢参加各种舞会和聚会,虽然在那儿他只能坐着观看,却也能享受一番乐趣。
记得在一次沙滩聚会上,进行了一场殴斗,人人挥拳上阵,相互推撞。
他不满足只是坐着观看,然而在松软的沙地上如果没人帮助,他又站不起来。
于是在极度无助的情况下,他高声喊道:
“谁坐下来和我对打!
谁愿意坐下来和我对打!
”
没有人坐下来和他对打。
第二天,人们和他开玩笑,说是第一次听到拳击手在开打之前,就有人要求他倒地服输。
如今我知道他是通过我,他唯一的儿子,间接地参与了一些事情。
我打球时(球技很糟),他也“打”;
后来我加入海军,他也“加入”了。
我休假回家时,他一定要让我去参观他的办公室。
在介绍我时,虽然没有说出口,但他实际上在说:
“这是我儿子,但也是我。
如果我没瘸,我也会和他一样。
如今父亲已去世多年,但我时常想起他。
不知他当时是否留意在我们同行时,我不愿意被人看到。
若他确实注意到了,那我真惭愧当时没能对他说我是多么对不起他,我是多么不孝,我有多么后悔。
现在,每当我因一些琐事而怨天尤人的时候,每当我嫉妒别人运气比我好的时候,每当我没有一颗“好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
每逢此时,我就设想自己将手搭在他的臂上,重新找回自己的平衡,我会说:
研究显示,我们对他人的判断是根据我们最初遇到他们的七秒钟里所进行的无声交流形成的。
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们都会用我们的眼神、面部表情、形体动作和态度来表现我们的真实情感,从而使他人产生从舒适到害怕等一连串反应。
想想那些让你最为难忘的会面:
被介绍给你未来的妻子或丈夫、一次求职面试、与陌生人的一次邂逅。
将注意力集中在最初的七秒钟,你当时有何感想?
你是如何“解读”他人的?
你认为他又是如何解读你的?
你本人就是信息。
25年来,我在工作中和数千个想要成功的人打过交道。
我帮助他们,使他们所作的演讲有说服力,教他们如何回答不友好的提问,以及如何与人更有效地沟通。
而所有这一切的秘诀都在于要懂得你本人就是信息。
如果你能利用你的优点,别人就会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愿意帮助你。
这些优点包括:
外表、活力、语速、语音语调、手势、眼神,以及使他人对你保持兴趣的能力。
别人对你的印象就是根据这些因素形成的。
想想有哪几次你确切知道你给人留下了好印象。
你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
那是因为你对你所谈论的事情非常投入,你当时完全沉浸其中,以至于完全没有了羞涩的感觉。
保持自我。
许多指导性的书籍会建议你大步走进一个房间,用你的优点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会教你以“有力的握手”问候他人,并且告诉你要用双眼注视对方。
可你如果遵循了所有这些建议,你会让所有的人都受不了——包括你自己。
诀窍在于要始终如一地保持自我,保持最佳状态的自我。
给人印象最深的那些人从不随着情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
无论是在与人交谈时,在园艺俱乐部上发表演说时,还是在求职面试中,他们的表现都是一样的。
他们全身心地与人交流;
他们的音调和手势与他们说的话保持着一致。
然而,演说家常常会传递一些混合不清的信息。
我最喜欢用来作例子的一类演说家是那些边看自己的鞋子边说“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来到这里”的人。
他们看上去并不高兴。
他们看上去气愤、恐惧或沮丧。
听众总是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胜过耳闻。
他们会想,“他告诉我他很高兴,可他并不是这样。
他并没有说实话。
用你的眼睛。
不管你是和一个人交谈,还是对一百个人发表讲话,始终记住你要看着他们。
有些人在开始说话时会直视你,但一句话刚说了几个字,他就会中断与你目光的接触,把目光移向窗外。
当你走进房间时,目光从容地扫视;
然后直视房间里的人,并对他们微笑。
微笑是很重要的,它表明你很放松。
有人认为走进一个有很多人的房间就像走进一个狮子笼。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就算我同意,我也肯定不会看着自己的脚或是天花板。
我会注视那头狮子。
别太当真。
一次在员工会议上,一位娱乐业最有影响的董事长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大发雷霆,责备每一位员工,为能使员工害怕自己而感到满足。
当他走向我,对我喊道,“还有你,艾尔斯,你在忙些什么?
我说:
“你是说现在?
今晚?
还是在我的余生中?
”之后有片刻的沉默。
接着董事长仰头放声大笑。
其他人也跟着笑起来。
幽默可以打破尴尬场合中的紧张气氛。
如果一定要我用几个字说出我的建议的话,那就是“别太当真”!
你总会发现有一些人对待自己太过认真。
他们通常不是在沉思,就是在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
仔细地观察一下你自己,你说“我”的次数是否过多?
你通常是否将注意力集中在你个人的问题上?
你是否经常抱怨?
对于上述问题,哪怕只有其中一个你给出的是肯定的回答,那么你就需要“别太当真”了。
为了让别人感到自在,你自己先要表现得轻松。
不必作出大的改变,只需要保持自我。
你本身已具备了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的能力,因为要保持你的自我,只有你自己才能做得好,谁也代替不了你。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发现的。
自那时以来,艾滋病已夺走了20.4万多美国人的生命——其中有一半是在过去几年中丧生的。
此外,在100万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当中有18.5万人也将在一年内死亡。
被诊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当中有一半是黑人和来自拉丁美洲的美国人。
南部农村社区的妇女和青年是数量增长最快的艾滋病患者群体。
尽管数量大得惊人,但联邦和各州政府在实施防止艾滋病蔓延的计划方面行动迟缓。
鉴于政府行动不力,许多地方性组织便应运而生了。
南卡罗来纳艾滋病教育网络机构成立于1985年,目的在于防止艾滋病病例数量的增加。
和许多地方性组织一样,该组织缺乏资金,这迫使它创造性地使用其资源。
为接触更多的社区居民,有些艾滋病教育计划在美发店实施。
美发店老板在顾客进来时向他们散发艾滋病资料,在他们等着头发晾干时,向他们放映有关预防艾滋病的录像片。
她还在店里放一些书籍和其他出版物,供顾客等候时阅读。
她在工作的同时使许许多多人受到了教育,这一点着实让人赞叹。
最近,这一教育网络机构已开始帮助整个美国东南部的发型设计师们在他们的美发店里实施类似计划。
他们也是向学校、社区组织和教堂传播信息的有价值的资源。
这一组织还总结出了一些对其他从事同样工作的团体颇有裨益的方法。
尽管还没有一种能战胜艾滋病的方法,但这一网络机构在与艾滋病斗争中获得了以下经验:
<
B>
以社区居民能接受的方式与他们交谈<
/B>
。
许多社区的居民受教育比例低,这使得向他们散发艾滋病资料、希望他们自己阅读这一做法不切实际。
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请一些善于绘画的人来编写适合于教育程度低的居民阅读的艾滋病教育图书。
这些书采用简单的、手工绘制的“忧伤的脸”和“幸福的脸”等图画,说明防止感染艾滋病的方法。
这些书也展示一些看上去同那些需要接受教育的人很相似的图片。
当居民们看到熟悉的面孔和能够理解的语言时,就会发表更多的议论和看法。
这样一来,这些书在使用它们的社区里所产生的影响要比政府出版的书产生的影响大,而政府出版的书籍成本要高出数千美元。
培训青少年去教育自己的同龄人<
由于艾滋病在南部农村地区的青少年当中传播速度最快,发型设计师们设立了一个称为“艾滋病克星”的项目,培训8到26岁的青少年,让他们到社区给同龄人上“艾滋病101”课程。
这些青少年使这门课程变得简单易学,在向他们的同龄朋友解释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时,他们干得比成年人出色得多。
他们在帮助父母理解孩子所经受的各种来自于同龄人的压力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对“存在危险”这一概念重新界定,从而把不同背景、不同婚姻状况的妇女都包括进去<
一位妇女的医生对她说她不存在染上艾滋病的危险,因为她已经结婚,而且不吸毒。
这类错误观念困扰着医疗机构。
根据疾病控制中心的预测,女性将占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的80%。
发型设计师们也强调每个人都存在着危险,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权保护自己——无论结婚与否。
这些经验不是解决艾滋病危机的唯一方法,但在找到治疗艾滋病的方法之前,教育不失为预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唯一安全措施。
和以前其他传染病不同,艾滋病这一传染性疾病有可能夺去一代人的生命,从而使另一代人失去双亲。
因而我们决不能让文化、种族和社会的障碍阻止我们专心从事我们必须做的工作。
我们也不能因为政府工作效率低而放弃我们的工作。
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谈论艾滋病会使我们感到难受,而听任人们继续被艾滋病夺去生命。
每个人都必须成为教育者,必须学会生存。
4月7日,星期六
我和史蒂夫已拖运垃圾整整四个小时了,中间只停下来说了约五分钟的话。
每次我将满满的一桶垃圾扛上肩,肩膀就痛得厉害,有时候扛着垃圾朝街上走,腿都打颤,可我心里却对自己说:
“挺住,垃圾工,要挺住。
我原本就没有想过这工作会有什么快乐可言。
倒、扛、走、扛、走。
时间过得飞快。
星期六意味着一路上大多数成年人会呆在家里。
上学的孩子也一样。
我心里琢磨,这可能意味着我挨家挨户收垃圾时可以和人们多搭上几句话了。
很多人在花园里或花房里干活儿。
多数人看上去是可以说说话的。
虽没有工夫聊很久,但问候几句以示礼貌还是有时间的。
但我吃惊地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直到我在几家院子里问候了几次以后,才意识到这么做是不常见的。
偶尔,有人也会看着我,微笑一下,对我说一声“你好”,或者“今天天气真好”。
这时,我还是感到有人情味儿。
可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反应要么是不理我,要么是因为我这个垃圾工竟然也和他们说话而惊讶地盯着我看。
一个身着家常便服的妇女见我绕过她家的拐角,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听到我向她打招呼,她就赶紧用衣服把自己严严实实地遮了起来,并匆忙退回屋里。
我还听到咔嗒一声门被锁上了。
另一个妇女,院子里养了一只巨大古怪的动物。
我问她那是什么动物,
她两眼盯着我。
我以为她耳背,所以提高了声音。
她好像给吓着了似的,冷冷地转身走了。
这儿离垃圾场有很长一段路,在驾车去垃圾场的路上,史蒂夫气愤地叙说着这些事情。
“从多数人看你的那种眼光,就知道在他们眼里垃圾工是怪物。
如果你对他们问声好,他们就惊奇地看着你。
他们根本没想到我们也是人。
“有个女人往垃圾箱里倒烟灰。
我说,我们这样没法装运。
她说,‘我倒什么你管得着吗,你算什么东西?
你不过是个垃圾工罢了。
’
我说,‘听着,太太,我的智商是137,高中毕业时是班上的尖子生。
我干这活是为了挣钱,不是因为我只能干这个。
’”
“我真想对他们说,‘你瞧瞧,我跟你们一样干净。
’可这没用。
我从不对任何人说我是垃圾工。
我说我是卡车司机。
我家里人知道,可我妻子的家人不知道。
如果有人正好碰到,问‘你是给垃圾公司开车吗?
’我就说是。
我相信我们做的事是人们所需要的,就像当警察或者消防队员一样。
我并不为此而感到见不得人,可我也不会到处去吹嘘自己的工作。
“有一天,我妻子的一个朋友见到她孩子从家里跑出来看垃圾车,她就大声叫嚷起来,‘离那些垃圾工远点,他们身上脏’。
我很生她的气。
我说,‘那些垃圾工和我们一样干净。
‘你好像很同情他们似的,’她说。
‘是的,我是很同情他们。
可我从没有告诉她这是为什么。
这活儿我原先只打算干两天,可现在我要干下去。
这可锻炼人呢,虽然肩部肌肉酸痛,可我扛垃圾桶越扛越得心应手了。
我越干越快,越干越利索。
在室外干活还可以呼吸新鲜空气,
而且完全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我干的活儿其实很干净。
我还决定继续在人家的院子里向人们说“你好”。
这不会有什么坏处,而且感觉依旧不错。
说实话,我感到骄傲,我在做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每晚工作结束时,我发现这个国家比早上更干净了。
并不是许多人每晚都能这样说的。
约翰·
加德纳曾写道,一个只赞扬哲学家而蔑视管道工的社会必定会出现麻烦。
他警告说:
“这个社会的管道和理论都会出问题。
他也许应该进一步要求人们既尊重经济学家又尊重垃圾工;
不然的话,他们都会在身后留下垃圾。
大多数城里人一样,我非常小心谨慎。
在把车开进车库前,我会扫视街道和周围的小路,看看有没有异常的人或物。
那天晚上也不例外。
可是当我手里拿着肯德基炸鸡走出车库时,一个身材圆胖、留着短髭、头戴绒线帽、身穿深色尼龙夹克的年轻人从停车处旁的灌木丛中钻出来,把手枪顶在我的双眼之间。
“交出来,他妈的──,”他威胁道,“交出来。
“嗨,”我说,“拿去吧。
我一边说,一边把肯德基快餐盒放在小路旁边的花盆上,同时设法把我房子的钥匙扔进灌木丛中。
“你的钱在哪儿?
你的钱在哪儿?
”他吼道。
在我们遭遇的全过程中,他会重复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出于本能,我也同样重复着自己的话。
“在我钱包里,在我钱包里。
”我说。
他走到我的背后,把枪顶在我的脖子上,开始搜我的裤子口袋。
“钱包在哪儿?
”他问。
“在后面的口袋里。
“还有呢?
“我就这么多钱了。
“手表在哪儿?
“在这儿,”我边回答边把左臂伸出去。
就在这时,他的同伙出现了。
他很瘦小,手持一支加大的蓝色钢制手枪。
他深色的眼睛里闪着光,好似擦亮了的玻璃;
他手臂和双腿毫无预示地移动着,就好像是连着看不见的电线似的。
他厉声说道,“不许看我们,不许看我们。
他并不蠢。
我看过许多刑事审判,因而知道在那些武装袭击的受害者中,很少有人能够辨认出袭击他们的人,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枪上,而没有注意持枪人。
我有意识地留意了一下他们的面部细节。
“我没有看你们。
”当那个大个子劫匪把手表从我的手腕上扯下来时,我撒了个谎。
“趴下,趴下,”那小个子命令我,
并一把摘下了我的眼镜,把它扔到草坪上。
这时,我已面朝下趴在了地上,前额紧贴着地面的泥土。
那个大个子劫匪用枪顶着我的后脑勺,小个子用手枪紧紧顶着我左边的太阳穴。
我当时想,“这下完了。
莱斯利会受不了的。
主啊,可怜可怜我这个有罪的人吧。
“这是什么?
”大个子问道。
我把头转向右边。
“是肯德基炸鸡,”我说。
“我们要带走,”大个子厉声说道。
于是,突然间,劫匪们手里拿着钱包、手表和炸鸡,脚步声在黑暗的街道上越来越远。
我转过身,看见他们的影子钻进了一辆汽车,急速地开走了。
他们没有杀我,但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是仁慈?
是因为时间太紧而顾不上?
还是因为饥饿?
“多奇怪啊,”我心中暗想,“竟然是炸鸡救了我的命。
我看到的是死亡,而他们看到的是食物。
我站起身来,找到了钥匙,进了屋,然后拨通了911。
接线员记下了我对劫匪的描述,然后派了辆警车来。
我为自己倒了一杯烈性酒,不一会儿,两个穿制服的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就到了。
他们对此事作了笔录,说“幸好”没有受伤。
“但是,”临走时一个警察对我说,“他们拿走了你的炸鸡,这实在太不像话了。
后来,一个警察打电话来询问其他细节。
他说这两个劫匪的作案手法表明他们可能就是过去几个月里这一地区多起抢劫案的实施者。
他让我到警察局去看一下疑犯的照片。
于是,上周一我翻看了相簿大小的几本照片,多数是年轻人的──令人惊讶的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还是孩子。
一张张翻看并研读这些照片,仿佛漂流在一条让人伤心的河流上,就像身处英国诗人布莱克笔下的泰晤士河,似乎“看见每一个过往行人都是满脸饥色,一副苦相”。
这些年轻人聚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条河流──一条已失去控制的河流,这条河流正吞噬着我们所珍视的东西的基础:
我们的行动自由,我们的劳动果实,我们的生命,以及那些我们所珍视的人的生命。
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条河流,并探索其对现实不满的深层原因。
而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看看罪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