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徒经历四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我的学徒经历四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的学徒经历四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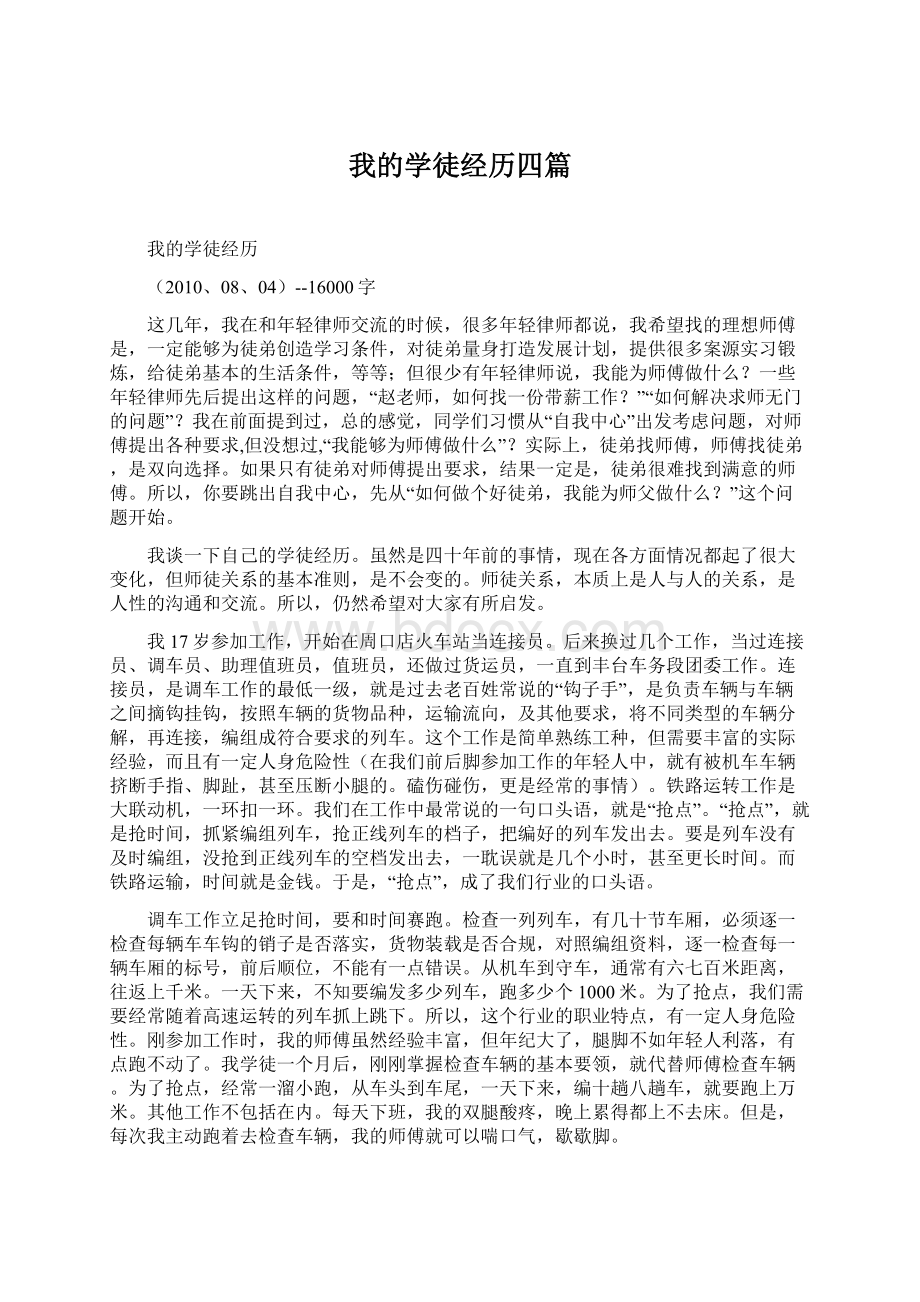
刚参加工作时,我的师傅虽然经验丰富,但年纪大了,腿脚不如年轻人利落,有点跑不动了。
我学徒一个月后,刚刚掌握检查车辆的基本要领,就代替师傅检查车辆。
为了抢点,经常一溜小跑,从车头到车尾,一天下来,编十趟八趟车,就要跑上万米。
其他工作不包括在内。
每天下班,我的双腿酸疼,晚上累得都上不去床。
但是,每次我主动跑着去检查车辆,我的师傅就可以喘口气,歇歇脚。
调车工作,无冬立夏,都在露天作业,也很辛苦。
例如,每次机车到长沟峪煤矿专用线送车皮,我都主动爬上第一节车皮担任瞭望。
冬天,山里的风特别猛烈,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生疼。
有时把脸都吹麻了。
我穿着厚厚的棉工作服,还套着我的老奶奶给我做的一件兔皮坎肩,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被山风一吹,身上的棉衣就像穿着一层纸,浑身透凉。
但我在学徒期间,始终抢着爬上第一节车皮担任瞭望,让我师傅在后面的车厢里躲躲风。
时间长了,听到一些议论,说我的师傅滑头,找了个憨厚的徒弟,苦活累活都让徒弟干了。
我有时听在耳朵里,也不搭腔,笑笑而已。
我觉得师傅带一个徒弟,付出心血很大,徒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为师父分担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后来有一次,师傅利用机车“停轮”的时间问我,“小鲁,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有什么想法吗?
”我说,“挺好的,师傅对我很关心,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师傅说,“有人说,我把苦活累活都让你干了。
这话儿你听说过吗?
”我说,“听过一耳朵,师傅,不用往心里去。
我们年轻,多跑跑是应该的,师傅年纪大了,让师傅歇歇腿,是做徒弟应该做的”。
师傅听了,宽慰一笑,说,“你这样想,就好”。
其实,我早注意到,有时我在几百米外单独作业,但到关键业务环节,师傅都会给我打手势,让我注意关键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
我察觉到,尽管师傅没有和我一起跑,但我的一举一动,师傅都密切注视,一时一刻没有放松。
打那儿以后,我们的师徒关系更近了。
师傅业余时间,经常手把手教我在各种情况下要注意的问题,和应对措施,所有这些,都是实际经验,没有一个字能够在书本中找到。
我在师傅身上,不仅学到技术,也学到了掌握技术的方法。
结果,我是在我们那一批学徒中,第一个“放单飞”的。
以后,我又提升为调车员、助理值班员、值班员。
在我担任连接员和调车员的几年中,浑身上下,没有磕碰到一点,“全须全尾”。
我的父母和全家,都很感谢我师父。
每次我回家休息,父亲都说,“别忘了给你师傅问好”。
并一再嘱咐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师傅”。
后来,我到机关团委工作,又后来,考上大学,离开铁路,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师傅。
我从17岁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从第一个师傅身上,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
可以说,我的师傅真正把心掏给了我,把经验传授给我,使我终生受益。
如果我在当时偷懒耍滑,干活斤斤计较,甚至和师傅攀比,师傅能对我倾囊相授吗?
那是不可能的。
做徒弟,就要首先为师父分担些工作,把心思放在学本领上,千万不要斤斤计较。
这是对徒弟的最基本要求。
所以,徒弟和师傅,是双向选择。
我们要选好师傅不容易,师傅要选好徒弟同样不容易。
师傅如果一旦对徒弟认可,就会倾注心血,倾囊相授。
我在2001年从英国留学回来,有一段时间囊中羞涩。
当时我带的两个徒弟,素质都不错,在相当一段时间,我一直从单位借钱给他们发工资。
所以,当我们问,“如何找一份带薪工作”时,前提首先是,如何得到师傅认可。
顺便说一下,现在一些同学埋怨干活多,师傅给钱少。
我记得我讲过,劳动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工作有可替代和不可替代之分,师傅和徒弟的工作不能类比。
在这里,我要说,我那会儿,一心只想学业务,从没有想过钱多钱少的问题。
我们学徒期间,一个月只有16块大毛,每天都是以粗粮为主,早晚都是窝头和棒子面粥,只有中午才能吃一顿白面。
现在看,条件确实艰苦。
可我们从来没有把心思放在干多少活,拿多少钱上。
我知道,学会挣钱的本领,才是无价之宝。
附录一:
我的师傅梁玉升
(2010、08、12)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师傅,也是唯一的师傅,是梁玉升师傅。
1969年3月17日,我和从城里一起分配来的年轻学生,一批六人,被分配到丰台车务段周口店火车站工作。
从此,我进入了社会。
周口店车站虽然是一个三等站,但铁路线路都是随山势修建,很分散,车站中心只有三条线路,其他的专用线,都延伸到大山深处,所以看上去,显得并不大。
我到周口店时,正好是车站运输最繁忙红火的那一段儿。
当时车站的主要业务,是为正在修建的东方红炼油厂运送设备,还有从长沟峪煤矿拉煤,再就是运输附近山里出产的石灰,矸土等矿产品。
每逢山里起风,石灰、矸土,煤灰就漫天飞舞,刮得人灰头土脸。
我记得有几次大风,居然把夜里值班的师傅刮的东倒西歪,根本站不住脚。
一次夜班,我亲眼看见一阵大风,把半夜查岗的车站党支部书记赵玉龙师傅刮的踉踉跄跄,终于失去平衡,摔了一个跟头,赵师傅用手紧紧抓住了一个道岔手柄,才稳住身形。
我们就常年在这种天气环境下工作。
尽管条件差,但周口店却因闻名世界的周口店“中国猿人”发源地而名闻遐迩。
每逢周末,就会有很多游客到周口店参观游览龙骨山猿人洞。
于是,平日略显寂寞的车站,就透着热闹非常。
每逢这时,年轻师傅都争着在机车前边,手拿信号旗“领车”,并经常选候车旅客多的地方,在机车高速行驶中,像燕子一样飘然而下,在身边呼啸而过的机车衬托下,一脸漫不经心的昂然四顾,惹得站台上的数百名游客一片惊叹之声。
我刚到车站时,看到这一幕,也是惊得目瞪口呆,心中羡慕不已。
想着有一天,也能像师傅们那样在飞奔的列车上飞上飘下,享受一下“露脸”的感觉。
梁玉升师傅的名字,恰恰和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名字近音。
不过,当时在大陆,没有人知道梁羽生的大名。
特别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车站。
所以,从没有人提起过梁师傅和大作家名字相近这档子事儿。
我上班的第一天,正好是夜班,大家都在忙着交接班。
第一天上班,值班站长臧师傅把我介绍给梁师傅时,他正在低头仔细擦一盏信号灯,就是《红灯记》中李玉和拿的那种信号灯。
当时交接班室人来人往,大家都在忙着交接班,对照一个很大的车站线路图,逐一交接车辆分布情况,装卸情况,装卸站台货物分布情况,上个班的安全情况,是否发生了“事故苗子”,以及各种需要交接的注意事项,气氛严肃,几乎和电影上的作战室一样。
大家全神贯注交接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几个从城里来的年轻学生。
梁师傅听了臧师傅的介绍,抬起头,微笑着冲我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又低头擦灯。
一直到把灯擦得锃光瓦亮,又端起那盏信号灯,左右远近端详一番,才满意的轻轻放在一边,开始和我说话。
那一刻,我觉得梁师父岁数很大,好像一个小老头儿。
第一天夜班,我很好奇,到处东张西望。
为了安全起见,师傅不让我跟车,不到半夜,就让我回去睡觉了。
所以,已经忘记当时梁师傅和我说了什么。
但梁师傅对自己那盏信号灯的偏爱,给我留下深刻印像。
以至现在还记忆犹新。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我们调车工人上夜班,全靠一盏信号灯。
信号灯是我们的照明工具,是我们的联络工具,也是我们的伙伴。
晚上,车站货场,会被无数照明灯照的如同白昼,但在专用线,就是漆黑一片,全靠手中的信号灯照明联络。
在照明不足的地方,有时你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那里,等着机车掉头,一时只有天上的星星做伴,会感到很孤单。
这时,远远看到一盏信号灯一闪一闪的,就知道那里是自己的同伴,心里顿时踏实许多。
信号灯对于我们这些调车工人,就像武士的剑,战士的枪,作家的笔一样重要。
徒弟随师父,我也养成了酷爱信号灯的习惯。
我在生产第一线七年,信号灯始终擦得一尘不染。
……写到这里,我才突然发现,对于我进入社会的第一位师傅,也是我唯一的一位师傅,我多年心存敬重的恩师,熟悉的不能再熟悉,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但是又好像并不了解。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认真琢磨过自己的师傅。
年轻时,心中只有尊敬,无从琢磨;
后来,离开师傅,又忙忙碌碌,无暇琢磨。
一晃几十年。
此次要和年轻律师谈谈自己对“师徒关系”的认识,引出“我的学徒经历”一段文字,2000多字,一气呵成,本已搁笔。
昨晚突然连带想起,多年对自己的恩师从无一字着墨,未免大有不敬。
于是诚惶诚恐,一夜不眠。
天没放亮,就翻身下床,起笔“我的师傅梁玉升”。
回忆马上把我带到四十年前的周口店,带到第一次见到梁师傅的那个夜班。
十几岁在周口店度过的三年岁月,马上一幕幕鲜灵活现的浮现眼前。
一时笔下毫无滞涩。
但写到此处,才发现,需要对自己的师傅做些了解和解剖。
说的不对之处,还望梁师傅宽谅。
梁师傅当时好像不到四十岁,个子矮胖敦实,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像个不倒翁。
说话声音很大,一口公鸭嗓子,老远就能听到梁师傅的大嗓门。
梁师傅其貌不扬,眼睛不大,经常眯缝着,但说起正经事,两眼就炯炯发光,十分有神。
梁师傅受过中学教育,也许只是初中,但写得一手好字,好读书,知识面也广。
这在基本上是大老粗的铁路运转车间,已经是凤毛麟角(我们很多师傅,都是装卸工转行,有的连自己的姓名也写不全呢)。
也许是因此,其他师父对梁师傅都有一份尊重。
梁师傅业务十分纯熟,车站运转车间的师傅,几乎个个都是业务尖子,但提起梁师傅,都挑大拇指。
梁师父对工作极其负责。
每次上班,接车前,都拿着业务单子,在线路图前默默地站上一会儿,一直到心中对每一“钩”活都了然于胸,才去和大家逗逗贫嘴,插科打诨。
梁师傅对工作的琢磨,几乎细致到了分丝析缕的程度。
包括待分解列车的车型;
现车的停放位置;
待装车的情况;
站台货物的上货情况;
编组机车的司机是谁,扳道员是谁,货运员是谁,装卸班长是谁,干活是否麻利,都一一考虑周详。
机车尚未动轮,全部作业过程,已经胸有成竹。
最令人称奇的,是两三个小时的分解编组作业,几十“钩”活儿,每次实际所用的时间,竟然和梁师傅的提前预测上下差不了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
我每次编组完了,机车停轮,都看看时间,心中暗暗称奇。
所以,梁师傅当班,值班员也很尊重梁师傅的意见。
梁师傅阅历丰富,内心精明,头脑敏捷,嘴皮子也厉害。
师傅们经常在机车停轮休息时,相互插科打诨,耍嘴皮子逗贫,梁师傅从没有落过下风。
每逢这时,我在旁边看热闹,虽然两不相帮,但看到师傅占了上风,心里也暗暗高兴。
梁师傅似乎十分淡于名利,从不出头争这争那,为人十分随和。
我和梁师傅在一起整整三年,朝夕相处,从没见其他师父和梁师傅红过一次脸,说过一句重话。
我跟这样一位师傅学习,自然很自豪。
当然,梁师傅最得意的,也是教出了我这么个徒弟。
不过这是后话。
开始,我觉得梁师傅很严肃,话不多,除了工作上必须交代的,经常一个人抽闷烟。
后来,接触长了,才知道梁师傅也有很活泼的时候,和大家谈笑风生。
有时机车在大灰厂停轮待装,大家在一间简陋的休息室玩“连儿”(用象棋“五连子”)的时候,梁师傅赢了,会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可是,接触时间更长,又感觉梁师傅好像不太合群,内心深处,似乎和其他师父并无更深的交流愿望。
这种感觉一直使我很奇怪。
因为,梁师傅表面很随和,而内心深处又好像很孤独。
这是为什么呢?
我一直纳闷无解。
在周口店三年,我和梁师傅一直同住一间单身宿舍。
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我们一共分到周口店六个城里的学生。
车站单身宿舍不够住。
这下子难坏了站长和书记。
正巧,靠近交接班室,有一间小仓库,原来是堆放各种杂物的,站长就让腾出来做单身宿舍。
那间小仓库,完全用山上的大石块儿垒成,墙壁很厚,窗户很小,屋里不透风,有些阴潮,不太适合居住。
我因为每天晚上都要读书到深夜,正好喜静,于是就自报奋勇,住了进去。
开始两天,屋子里有很多小虫子,咬得我浑身是包,还有小蜈蚣,小蚰蜒什么的,挺吓人。
后来,梁师傅和其他师父帮助我彻底打扫了一下,又重重的洒上“敌敌畏”,门窗紧闭的闷了两天,估计虫子都死了,我才又住进去。
我用两条横凳子,加上一块床板,铺上一床草垫子,就是“床”了。
为了防范虫子咬,我在草垫子上洒了厚厚一层666粉(味道十分呛人),上面铺了块塑料布,再铺床单,褥子,层层设防,终于彻底和小虫子绝缘。
我于是高枕无忧。
屋里有一张书桌,一盏灯,正好是一个绝佳的学习环境。
不过,还是没有人愿意搬过来,和我同住这间仓库改成的宿舍。
后来,梁师傅搬了进来。
梁师傅家在琉璃河,平时不住宿舍,只有每三天轮值夜班时,上午车站组织学习,中午梁师傅就住在宿舍休息。
晚上直接上夜班,倒也方便。
这样,我们师徒二人在一起,一住就是三年。
和师傅在一起住,聊天的机会就多了,渐渐无话不说。
我开始感觉到,梁师傅的内心深处,有一股傲气,也许是因为识文断字,有些文化使然,也许是和其他人见识不同,其实梁师父十分自负。
作为徒弟,我也只能写到这个程度。
我在周口店工作三年,担任连结员,调车员;
后来调到豆店车站,担任助理值班员、值班员;
然后又调到丰台车务段团委,直至1979年考上大学,离开铁路。
在周口店三年,有的师傅对我天天读书到深夜,颇不以为然,觉得我不太安心本职工作,尽管我工作十分努力,几乎到了吐血的份儿上。
但是我的师傅,自始至终支持我。
说,“小鲁,多读点书吧。
读书好啊。
别管别人说什么。
”“读书为什么好”?
梁师傅没有说过。
但梁师傅对知识的肯定,使我更增加了对他的一份敬重。
梁师傅爱喝酒,喝酒上瘾,上大瘾。
常年每天中午晚上两顿酒,每次三两,一两不少,一次不拉,以至脸膛黑里发紫,据说是长期喝酒对肝脏影响所致。
那时企业工人的收入都不高。
铁路历来有铁饭碗之称,铁路工人收入高一点,也有限。
但梁师傅结婚多年,膝下无子(只领养了一个女孩儿,好象叫“燕子”),家庭花销不大,经济就显得宽裕很多。
梁师傅每天都能喝二锅头,这在师傅中间,已经很奢侈。
铁路运转车间的工人师傅,因为常年上大夜班(一班十二个小时,算上交接班时间,一个大夜班,总要十四五个小时),几乎都有三大嗜好:
抽烟喝酒酽茶(浓茶)。
梁师傅一直喝好酒,二锅头,不是像绝大多数师傅,只能喝散装劣质白酒;
抽好烟,纸烟,不是像绝大多数师傅,抽不起纸烟,只能“卷大炮”;
喝好茶,一直喝茶叶,不是像绝大多数师傅,只能喝茶叶末,号称“高末”。
很多师傅经常半调侃半嫉妒的说:
“小梁子,二锅头茶叶外加纸烟,好生活啊”。
每逢这时,梁师傅不管对方是否调侃,都流露出得意的微笑,故作大方的拿出纸烟,随手扔给大家两三支。
有的师傅一时舍不得抽,就拿过来夹在耳朵后边。
我和梁师傅一起生活工作了三年,梁师傅生活上最满足的,就是这么一点事儿。
我父亲知道梁师傅爱喝酒,逢年过节,就把别人送给自己舍不得喝的好酒,拿出来托我代给梁师傅。
每次梁师傅都很感动,嘱我向老爷子谢了又谢。
那时候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真诚。
1979年,我考上大学以后,离开了铁路。
父亲多次说,“小鲁,千万别忘了梁师傅”,并叮嘱我有时间常去看看师傅,一定要带瓶好酒。
我诺诺连声。
我和梁师傅一直都有联系。
直到1998年我去香港工作,联系不便,逐渐断了音讯。
近几年,我和几个当年一起在周口店工作的伙伴,多次想到周口店车站看看梁师傅和那些老师傅,却又始终没有成行。
再后来,几次给周口店车站打电话,才知道我们那时候的老师傅,像身轻如燕的“车上飞”崔启云师傅,早已退休多年;
而声如洪钟的“大将”王震师傅、车站篮球队主力队员,“神投手”王连路师傅,都已经去世;
还有我十分亲近和敬爱的李文会师傅,也已去世多年。
打听梁玉升师傅,竟然“没有人听说过”。
一时惊愕而沉重。
想起我和梁师傅在一起的三年,梁师傅是如此出色,心中不无感叹。
正是,“人生壮年,也曾浓烈如酒;
渺如烟云,而今来去无痕”。
每每思之,心中不胜欷觑。
但是在我心中,虽历数十载,不曾一日忘却我的梁玉升师傅。
谨以此文,权作纪念。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晨
附录二:
做人要能够吃亏
---浅谈“智商与情商”
在最近几次给年轻律师讲课和沟通交流过程中,很多同学都谈到,自己干活多,师傅给钱少,心里不平衡;
或者认为,自己苦读8年,拿到了律师执照,应尽快办案挣钱。
但和老律师合作,经常是老律师拿钱多,自己拿钱少,心里不平衡。
这些问题提得多了,我就有一个感觉。
我们这一代年轻律师有突出优点,例如,接受信息量大,眼界宽阔,建功立业的心情比较急迫,思路活跃新颖,等等。
但也有明显不足,就是考虑问题,好像“以自我为中心”多了一些。
这个感觉不一定对,同学们可以不接受,算是我的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以我个人成长的经历看,年轻人在成长中,都会遇到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智商高,情商低”。
必然要有一个“开始智商高,情商低,需要努力提高情商,逐渐达到情商与智商的平衡,最终实现情商高于智商的过程”。
我的理解,简言之,智商,叫做聪明;
情商,叫做智慧。
智商,和个人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和受教育程度有关系,和个人的书本知识有关系。
情商,则和社会环境、人情历练、实践经验有关系。
或者说,“读有字之书,培养智商;
读无字之书,培养情商”。
我认为,人是社会动物,必须在特定的社会生态系统中生存发展。
因此,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就(不是自然科学和实验室中的成就),最终是由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如何处理这些社会关系所决定。
因此我说,从社会学角度看,大家要想建功立业,“七分靠情商,三分靠智商”。
“情商”,说白了,就是“待人接物”的学问。
“待人”,是修养自己,对待别人,包括处理和别人关系的学问;
“接物”,是指如何处理事情的经验和技巧,也包括处理和别人关系的学问。
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以我半生感悟,情商的核心,是品德修养,而不是待人接物的技巧。
品德是“道”,技巧是“术”。
“术为道用”,“道以御术”,“术中有道”。
所以,孔子为《易经》做卦辞,说,“厚德载物”,真是人生大智慧。
年轻律师要想做事,特别要注意培养情商。
培养情商,首先要学做人。
我的半生体会是,“做人要能够吃亏”。
凡是待人接物能吃亏的人,吃得起亏的人,就能比较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看问题容易从大处着眼,不计小利,最终能够做成一些事情。
同时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可以跳出个人的小圈子,开阔心胸和眼界,减少化解很多不必要的烦恼,把时间精力用于自己更需要的地方。
过去讲课,很多同学都说,“赵老师,请您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吧”。
但我总是回避这一话题。
因为个人的人生经验总是具有局限性。
但现在我抓住了一个主题:
“做人要能够吃亏”。
从这个角度,讲几件自己人生的小故事,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启发。
一、养猪五年,每年最后一个分猪肉。
我在窦店火车站工作五年。
窦店站有二百多员工,是京广线上的一个三等站。
当时那个年代,物质十分匮乏,车站只能自力更生,想方设法搞副业,改善职工生活。
我自告奋勇,利用业余时间,和一个叫赵全的师傅,一起给车站养猪。
这一养,就是五年。
赵全师傅当时五十来岁,身高一米八几,为人宽厚随和,做事不慌不忙,经常笑咪咪的,好像从没见他犯过愁。
赵全师傅年轻时当装卸工,过度劳累,落下一身病。
所以车站照顾他,不让他在生产第一线盯“大班”。
但他特别热心帮助别人,常年在单位做后勤工作,整天东摸摸西看看,一点也闲不住。
我的一点养猪和种地的知识,都是跟他学的。
养猪,先从自己垒猪圈开始,然后到农贸市场买猪秧子。
我们两个人,每年养三头猪。
赵全师傅家在农村,养猪很有经验,就手把手耐心教我怎样挑选小猪仔。
选猪仔一定要挑活蹦乱跳,吃食狼吞虎咽的。
那年头,什么都奇缺,我们为了解决猪饲料问题,着实犯过愁。
连赵全师傅也没了主意。
后来,我猛地冒出一个点子:
和附近部队建立联系,他们的食堂肯定有泔水。
结果和附近部队一联系,人家还真热情。
于是,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车站附近的部队,用平板车拉泔水。
第一次蹬平板车,怎么也掌握不住车的重心,平板车扭来扭去,有一次转弯快了点,平板车还翻了。
不过努力练习几次,也就逐渐掌握了要领,最后蹬起平板车来得心应手,来去如风,和“板儿爷”的专业水平毫不逊色。
平板车上放一个硕大的汽油桶,每次到部队拉泔水,战士都把食堂积攒的泔水拿出来倒到汽油桶中,几个部队一转悠,一大桶泔水就拉回来了。
小猪越来越能吃,我每一两天,就要拉一大桶泔水。
看着猪仔吃得兴高采烈的,我也很高兴。
养猪,还要经常起圈,把猪粪起出来,担到车站的自留地中,给红薯玉米施肥,然后再垫上新土。
新土都得自己一挑一挑从附近的地里担回来,开始,肩膀都压得生疼红肿,后来,渐渐也习惯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小猪仔变成了大肥猪,养到200多斤,就赶上过年了。
春节前,由当过屠夫的师傅指导杀猪。
我看到自己养的小猪被宰杀,虽然早知猪的命运就是如此,但心中总是不忍,从不参加杀猪的活儿。
师傅们把猪杀好褪毛,再按照200多人的人数,每人分一份儿,用报纸包的严严实实,一包包码放在会议室的兵乓球台上。
下班的师傅,每人拿走一份儿。
师傅们在过节前拿着猪肉回家,脸上笑容满面。
我和赵全师傅看到自己养的肥猪,给车站每位师傅改善了生活,心里美滋滋的。
照现在年轻人的说法,“很有成就感”。
一直等所有人都把猪肉领走了,我和赵全师傅,才走进会议室,拿最后两块猪肉。
我把猪肉拿回家,奶奶一看,有点遗憾的说,你这块是猪囊膪(猪肚子肉)。
下回再分肉,要是肥肉多点,就可以炼点油了。
我和赵全师傅养了五年猪,每回都是最后一个进会议室拿猪肉。
我每次拿的都是猪肚子肉,渐渐心里不平衡。
觉得也应该给家里拿一块好一点的猪肉,让老奶奶高兴。
但父亲却对我说,“做人要能够吃亏。
工人师傅生活都不富裕,你不吃亏谁吃亏?
”
“做人要能够吃亏”,这句活,我牢记至今。
二、业余时间管工资,月月自掏腰包贴补。
车站管财务的师傅退休了,没人愿意接财务。
站长让我业余时间兼管财务。
车站财务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每月制定工资表,月末发放工资。
我接过来才发现,这个活儿吃力不讨好。
我每月要一一核对200多人的出勤表,病假事假和加班,错记一天也不行。
然后算出每个人每月的工资总数,一毛一分,都不能错。
到月底发工资最紧张。
工人等着拿工资回家买粮食吃饭,等米下锅。
发工资那天,是全站最大的大事。
早上,我要起个大早,和车站的两个师傅,坐通勤车到车务段财务室,拿个专用的小麻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