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解纷机制衔接问题探要余文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多元解纷机制衔接问题探要余文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多元解纷机制衔接问题探要余文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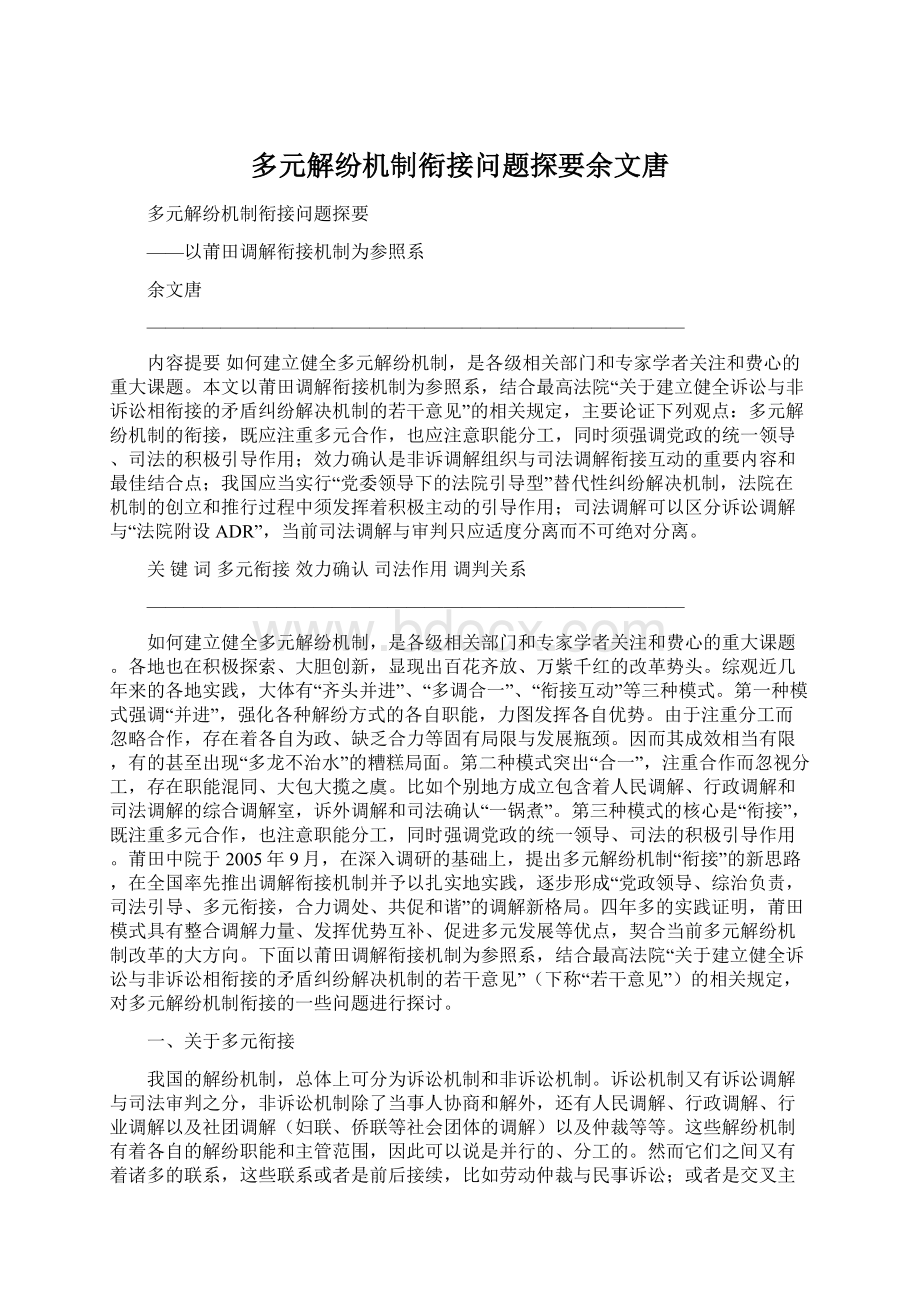
莆田中院于2005年9月,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多元解纷机制“衔接”的新思路,在全国率先推出调解衔接机制并予以扎实地实践,逐步形成“党政领导、综治负责,司法引导、多元衔接,合力调处、共促和谐”的调解新格局。
四年多的实践证明,莆田模式具有整合调解力量、发挥优势互补、促进多元发展等优点,契合当前多元解纷机制改革的大方向。
下面以莆田调解衔接机制为参照系,结合最高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对多元解纷机制衔接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多元衔接
我国的解纷机制,总体上可分为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
诉讼机制又有诉讼调解与司法审判之分,非诉讼机制除了当事人协商和解外,还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以及社团调解(妇联、侨联等社会团体的调解)以及仲裁等等。
这些解纷机制有着各自的解纷职能和主管范围,因此可以说是并行的、分工的。
然而它们之间又有着诸多的联系,这些联系或者是前后接续,比如劳动仲裁与民事诉讼;
或者是交叉主管,比如人民调解、行业调解与民事诉讼在案件主管上很多是重叠的。
各种解纷机制的联系,就为它们之间的衔接提供了基础;
而其区别则要求衔接有度、不可混同合一,不能大包大揽。
我们认为,多元解纷机制之间相互衔接的目的应当包括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于整合解纷力量、形成解纷合力,协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另一方面则在于分流繁简案件、落实司法为民、减缓司法压力,以及提升非诉调解权威、强化调解协议效力等。
莆田调解衔接机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创立的。
莆田调解衔接机制实行的是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以及社团调解等非诉调解与司法调解之间的衔接,衔接的内容主要包括“四维衔接”。
一是组织网络衔接。
其主要体现为:
在市、区(县、管委会)两级成立由党委、政府统领的调解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统一协调辖区内调解衔接工作;
在村居社区、乡镇街道、机关团体等设立调解衔接工作站、调解衔接示范点和调解衔接巡回点,各站点均配备挂钩法官;
在基层法院立案庭附设调解速裁室,中院设立调解衔接工作办公室,并设立温馨调解室。
二是工作制度衔接。
主要是建立在调解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统一协调下,各调解衔接工作成员单位之间的联席会议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复杂疑难纠纷问题联调制度和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制度。
三是调解活动衔接。
其方式可以概括为:
“三调解、一确认、一指导”,即诉前调解、委托调解、邀请(协助)调解、效力确认、调解指导。
其中,三种调解属于程序上的衔接,效力确认属于实体上的衔接,调解指导属于工作上的衔接。
四是调解队伍衔接。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由法院在人民调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中选聘特邀调解员,作为委托调解、邀请(协助)调解等的调解力量来源;
二是法院从退休的法官、司法调解员、人民陪审员等中选聘聘任调解员,常驻法院调解速裁室、人民法庭办理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等相关事宜。
同时设置触摸屏,介绍特邀调解员和聘任调解员的相关情况,供当事人选择调解员。
莆田模式在侧重于诉讼调解(司法调解)与非诉调解之间相互衔接的同时,还在法院内部实行全员、全程、全方位调解的“三全调解”。
全员调解:
即参加案件审理的所有法官都开展调解工作,疑难复杂案件的调解还可能进行主审人、庭长、院长的“三级联调”;
上级法院对上诉案件进行调解时,应了解下级法院对该案的调解情况,必要时邀请下级法院参与调解,形成“上下互动”。
全程调解:
即从案件起诉到法院至矛盾纠纷化解之前都要注重做好调解工作,包括诉前调解、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庭后调解以及复查调解、再审调解等,力争以调解撤诉的方式结案,实现“案结事了”。
全方位调解:
强调除了法律规定不得调解或案件性质决定不能调解的案件外,其他各类案件都要坚持调解优先,把调解作为法院结案的首选方式,提高调解、和解和协调的比率;
行政诉讼案件、刑事公诉转自诉案件、轻微刑事公诉案件以及执行案件也要参照民事调解的原则和程序,做好协调、和解工作。
应该说,莆田模式在各类调解之间的衔接方面,其机制框架是比较全面、规范的。
它既包括诉讼调解与非诉调解之间的“四维衔接”,还包括法院内部的“三全调解”;
既有宏观上的组织网络、调解队伍和工作制度上的衔接,也有微观上的调解活动衔接,其中又具体包括程序上的衔接(三调解)、实体上的衔接(一确认)和工作上的衔接(一指导);
既侧重于调解力量的合理整合、调解合力的有效运用,也注意到各种调解组织的职能分工和优势发挥。
四年多来的实践表明,莆田模式能够较好地实现“两个尽量多”的基本理念:
即尽量多的纠纷消灭在萌芽、消化在基层、化解在诉前,尽量多的诉讼案件通过调解结案,实现案结事了,且在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该模式已被中央列为全国维稳先进经验之一,并由中宣部统一安排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在内的中央各大媒体于今年8月上旬予以集中宣传报道,其做法的大部分也已得到《若干意见》的肯定和吸纳。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衔接互动模式已经成为当前多元解纷机制改革的主潮流。
二、关于效力确认
效力确认是莆田调解衔接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非诉调解组织与司法调解衔接互动的最佳结合点。
效力确认自2005年9月在莆田推行以来,效果相当显著。
因为它具有简捷高效、便民利民等优点,极受专家学者的关注和人民群众的欢迎。
最高法院法研所2007年6月初在莆田召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座谈会”时,中国人民大学范愉教授指出多元衔接与效力确认是莆田模式的两大亮点。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若干意见》已对效力确认(司法确认)作了重点规定,予以权威的认可。
所谓效力确认,在莆田模式中就是对经过非诉调解组织调解包括法院诉前调解达成的民事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并经法院审查合法有效,以民事调解书的形式确认调解协议并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
其要点包括:
1、是对经过非诉讼调解达成的民事调解协议的确认。
未经调解组织调解的和解协议,法院难以审查纠纷是否真实存在,原初的实践发现容易产生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问题;
从职能上说,对和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也有混淆司法与公证之虞。
立案后(诉讼期间)的委托调解、诉外和解达成的协议,则适用最高院“法释[2004]12号规定”第3条第2款和第4条规定予以司法确认。
2、必须是双方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共同申请。
双方分别但同时申请,或者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另一方表示同意的,视为共同提出申请。
3、必须经法院审查合法有效。
审查方式是询问双方当事人,必要时询问调解人或调取调解案卷审查;
审查内容既有实体审查,即是否存在真实的争议事实、法律适用是否正确、是否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
也有程序审查,即调解主体是否适格、调解程序是否合法、协议是否自愿达成、是否属于法院主管和管辖等。
4、以民事调解书形式予以效力确认。
经审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对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并赋予强制执行力。
此外,还要求调解协议具有确认必要。
对于那些事随案了、没有反悔可能或者不具有定期财产给付内容、内有确认某种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当事人申请效力确认的,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莆田做法与“若干规定”中非诉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总体上相一致,但也有些区别:
一是莆田的调解协议包括法院的诉前调解的调解协议,而“若干规定”对此未予明确。
对此,我们认为应将其归入“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的委派调解即法院委派非诉调处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
因为由法院附设的ADR机构虽属于非诉组织,但其进行诉前调解则属于法院委派。
二是莆田法院通过审查程序予以效力确认,而“若干规定”第23条规定的是“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简易程序的规定。
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双方当事人应当同时到庭”,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开庭审查。
对此,我们认为效力确认并非两造争讼,而是双方共同申请,应属于非讼案件。
因此,应以较为宽缓的审查程序,不必像开庭那么严格、严肃。
这样也比较符合“两便原则”。
三是莆田的确认形式是民事调解书而非决定。
对于效力确认或司法确认的法律文书种类,学者们有调解书、裁定书和决定书三种主张。
“若干规定”第25条规定的是决定,最高法院相关部门起草的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所用的则是民事调解书。
我们的看法是,效力确认首先包含的是实体权利义务的确认,从法律文书的使用范围来说,用民事调解书似乎更为合适。
而且,从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执行根据的规定来看,决定的执行通常是诸如民事制裁决定、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支付令之类,调解协议效力确认以决定的形式赋予强制执行力是否符合执行依据的要求尚须进一步斟酌。
四是调解证明与承诺书。
莆田模式要求申请效力确认需提供相关非诉调处组织的调解证明,而“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须提交双方当事人签署的承诺书。
前者重在为调解真实性审查增加保障,后者通过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承诺而增强申请的慎重感。
对此,我们认为两者都很有必要,应予兼收并蓄。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
委托调解所达成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究竟要不要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
对此,最高法院前后规定不一致:
“法释[2004]12号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也即无须申请;
而从2007年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第14条规定来看,似乎要求与诉讼过程中的和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一样须由当事人申请;
今年的“若干意见”第15条第2款则规定“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撤诉、申请司法确认,或者由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后制作调解书。
”这一规定似乎是说作出司法确认决定的须申请,而制作调解书的不需申请。
然而,这样区分有意义吗?
如果按照区分申请司法确认与制作调解书的区分,那么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法院对委托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也要开庭审查,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也不合“两便原则”。
我们认为,委托调解的实质是非诉调处组织代理法院对受托案件进行调解,按照代理理论受托行为的效力应由委托人承受,因此法院对委托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当依法审查确认,并且宜统一以民事调解书的形式予以司法确认。
三、关于司法作用
对于法院在多元解纷机制建立中的作用问题,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学者立场与实务立场。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法院是解纷的最后一道保障,应当恪守司法被动的本性,即所谓“司法之手不可伸得太长”。
相反,司法实务界则一般主张,司法应当适度主动,在多元解纷机制的建立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认为,一方面,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法院工作只有主动融入大局、服务大局,才能有作为才会不被边缘化。
法院在处理社会矛盾过程中应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等、不看、不靠、不推,主动负起法律、政治和社会的职责。
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保障公平和正义的事业、构建社会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另一方面,就我国目前的国情看,法院在多元解纷机制建立中,其权威性、协调力都远远不够。
因此,法院可以运用自身具有的纠纷解决的最终裁决权、强制执行力,以及司法专业化和严格程序化等优势,为多元解纷机制的建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规范化的指导。
但在整个多元解纷机制中不可能是龙头老大,只能是重要的一员;
不可能当指挥员,只能当急先锋。
在国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主要有“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法院主导型”等三种类型,法院主导型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就是所谓的“司法ADR”。
莆田调解衔接机制属于“党委领导下的法院引导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法院在机制的创立和推行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
但这种主动又是适度、有节制的。
在全面而紧密的衔接中,我们注重的是各调解组织之间的力量整合和功能互补,同时特别注意各调解组织的职能界限,不搞职能上的相糅合和工作上的大包揽。
特别需指出的是,引导不等于领导,法院在调解衔接工作中的引导作用是在党委领导下而发挥的。
在调解衔接机制的创立和推进过程中,莆田法院始终坚持依靠党委的领导和支持。
在提出工作设想之初,就及时向莆田市委作了具体汇报,取得市委的理解与支持,并转化为市委的决策部署。
工作中遇到需要市委统筹协调的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建议,由市委出面协调各方共同解决。
正是在莆田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调解衔接工作才能够列入莆田市“十一五规划”及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考评内容,提升为一项全市性重要工作。
莆田还在市、县区两级成立由党委、政府统领的调解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织、协调、指挥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在调解衔接工作上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
这一重要举措,使得党的领导更加具体实在,调解衔接工作的推进更有保障。
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是莆田调解衔接机制获得成功的最为重要的经验和最为宝贵的启示。
莆田法院积极引导调解衔接工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提出建议。
在调解衔接工作推行的各个阶段,莆田中院都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提出建议,为市委、市政府建立、创新和完善调解衔接机制出谋献策,起草相关文件,推动该项工作深化与发展。
二是规范流程。
莆田中院先后制定《关于调解衔接工作程序的暂行规定》、《关于规范调解协议效力确认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十多个规范性文件,对适用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和效力确认等的案件范围、办理程序和期限等作出明确规定,使调解衔接工作要求更加具体、程序更加规范。
三是指导调解。
主要是通过业务培训、庭审旁听、个案指导等方式,帮助调解组织提高调解能力;
通过调解衔接工作站和示范点的建设,帮助调解组织健全组织机构;
通过责任法官包片挂点,指导调解组织完善工作制度;
通过每月一次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例会暨调解衔接工作例会制度,共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对策,指导涉诉信访等重点案件的调解。
四是效力确认。
效力确认是增强司法服务、提高非诉调解组织地位和作用的有益尝试,是莆田调解衔接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如何概括诸如莆田法院在多元解纷机制衔接中的作用和地位上,主要有“主导”、“引导”、“推动”可供斟酌。
学者们通常喜欢用“主导”一词,譬如“法院主导型ADR”。
莆田模式最初也用该词进行定位,那是该模式还在探索初创和深化推进阶段,基本上由法院来运作。
后来机制进入提级强化阶段,成立了由党委、政府统领的调解衔接领导小组,便将“主导”改为“引导”。
从词语涵义来说,“主导”是“主要”与“引导”的结合,“引导”则取“引路”、“导向”之义,两者存在着份量上的差别。
如此理解,莆田模式中的法院地位从“主导”退居“引导”,是符合机制不断推进、法院角色转变的实际的。
当然,正如以上所述,“引导”不等于“领导”,这里存在的不仅是份量的差别,更是角色的质别、地位的悬殊。
最近,最高法院领导和包括《若干意见》在内的一些文件的提法,似乎更经常用的是“推动”一词。
我们感觉该词用在多元解纷工作的开展上是比较恰当的,法院应该推动这项工作。
但在建立健全多元解纷机制方面,似乎有那么点儿“在后推”而缺少“在前引”的微憾。
此外,还有“指导”、“积极参与”。
前者有置身之外之感,比如法院指导人民调解,但不是去做人民调解这项工作;
而“参与”只是参加其中,加上“积极”一词,也还是“以第二或第三方的身份加入、融入某件事之中”。
因此,在上述诸词中,我们选择“引导”一词来概括法院在现今莆田模式中的作用与地位。
四、关于其他问题
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的出台,已为多彩多姿的改革指明了方向、统一了基调。
然而,该意见还只是一种宏观指导性意见,其规定还比较原则,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细化。
下面结合《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就一些尚存疑问的事项进行斟酌:
(一)法院委派、委托仲裁机构调解和仲裁机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
根据《若干意见》第14条和15条的规定,法院可以在起诉后立案前或立案后,委派或委托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协助进行案件调解。
从字面上理解,仲裁机构应该属于这里的“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因而也可以被法院委派或委托对案件进行调解。
问题是,仲裁机构的调解有仲裁程序内的调解与仲裁程序外的调解之别,这就产生委派或委托仲裁机构调解的程序疑问以及依何种程序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的问题。
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仲裁机构被法院委派或委托调解的,只应适用仲裁程序外的调解,而不应适用仲裁程序内的调解;
申请司法确认的仲裁机构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仅限于仲裁程序外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
因为可以委派仲裁机构调解的只能是没有仲裁协议或仲裁协议因不明而无法确定仲裁机构、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依法不能进入仲裁程序;
而委托仲裁机构调解的案件若是已经仲裁程序包括程序内调解的,在仲裁裁决作出并起诉到法院后予以回炉则是不合适的。
这是其一。
其二,委派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申请立案前调解协议的确认,委托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则应予诉讼内调解协议的确认。
而根据《仲裁法》的有关规定,仲裁程序调解协议本身就具有强制执行力。
因而如果委派或委托仲裁机构调解可以适用仲裁程序内的调解,也就不需要进行任何司法确认,这与委派、委托调解制度不相协调。
(二)共同调解、协助调解与联合调解。
《若干规定》第16条规定:
“对于已经立案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邀请符合条件的组织或者人员与审判组织共同进行调解。
”这一规定应该是基于《民事诉讼法》关于协助调解的规定而作出的,但由于用语问题,很容易被理解为是被邀调解人员与审判组织共同进行调解,即有些地方所称的“联合调解”。
我们认为,这里的“共同”,应当按照民诉法的规定理解为“协助”,即在法官主持下,被邀请的调解人员协助法官调解。
而联合调解作为一种探索中的调解方式,只宜在民间性质的非诉调解组织之间试行。
而法院与非诉调解组织、行政调处组织与民间调解组织之间,在纠纷调解上应是主持、牵头与协助、配合关系,不宜为联署式的联合调解,否则法律文书的署名就成问题了。
同级法院、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化解难调难判尤其是涉诉信访案件时所采取的互动式调解,同样有牵头与配合(主次)之分。
(三)司法调解与审判的关系。
一般认为司法调解就是诉讼调解,两者是同一个概念。
就目前的法律框架下,这种认识不无道理。
因为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严格意义而言,仅是区别于判决的一结案方式,尚未从程序上确定其非诉程序地位。
一些专家提出对我国诉讼调解运行中的弊端进行合理改造的理想模式:
“将调解设置为与审判程序并行的非诉程序,将传统调解向司法ADR转型。
调解程序存在于一审程序的准备阶段,纠纷被提交诉讼后,可根据当事人的合意或强制进入调解程序,调解达成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予以确认,调解不成的则进入审判程序”。
从莆田法院的实践来看,司法调解似乎可以区分为两类:
一类是诉讼调解,立案之后的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庭后调解等诉讼内的调解均属于此。
另一类应当能够称为“法院附设ADR”,即以法院为主持机构,或者在法院的指导下,所采取的与诉讼程序不同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
莆田在基层法院立案庭附设调解速裁室,选聘聘任调解员常驻法院从事诉前调解工作,实行效力确认等,便属于此类调解。
这种将司法调解加以分化而向两极发展的做法,似乎很矛盾,但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因为当前正是我国社会急剧转型期,社会矛盾纠纷凸现,为了实现前述的“两个尽量多”,最大限度地实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只能采取调解与审判适度分离而不可绝对分离的做法。
(四)司法确认与案件统计。
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有非诉讼调解协议的确认与诉讼内调解协议的确认两类。
前者是指法院对《若干意见》第20条规定的非诉调解组织调解和第14条规定的法院在接到起诉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委派非诉调处组织调解所达成调解协议的确认;
后者在《若干意见》中是指法院对其第15条规定的法院在立案后委托非诉调解组织调解所达成调解协议的确认。
根据“法释[2004]12号规定”第4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经当事人申请也可以予以司法确认。
基此,我们的意见是:
诉讼内调解、和解协议确认的案件属于诉讼案件,应当列入诉讼调解案件予以统计;
非诉讼调解协议确认的案件虽因属于非诉案件而不宜作为诉讼调解案件统计,但它也是法院的一项工作、一种全新的办案方式,应当单独列项进行统计。
这不仅是对法院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多元解纷机制衔接工作的促进。
[作者单位: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