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野性的呼唤Word下载.docx
《15 野性的呼唤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15 野性的呼唤Word下载.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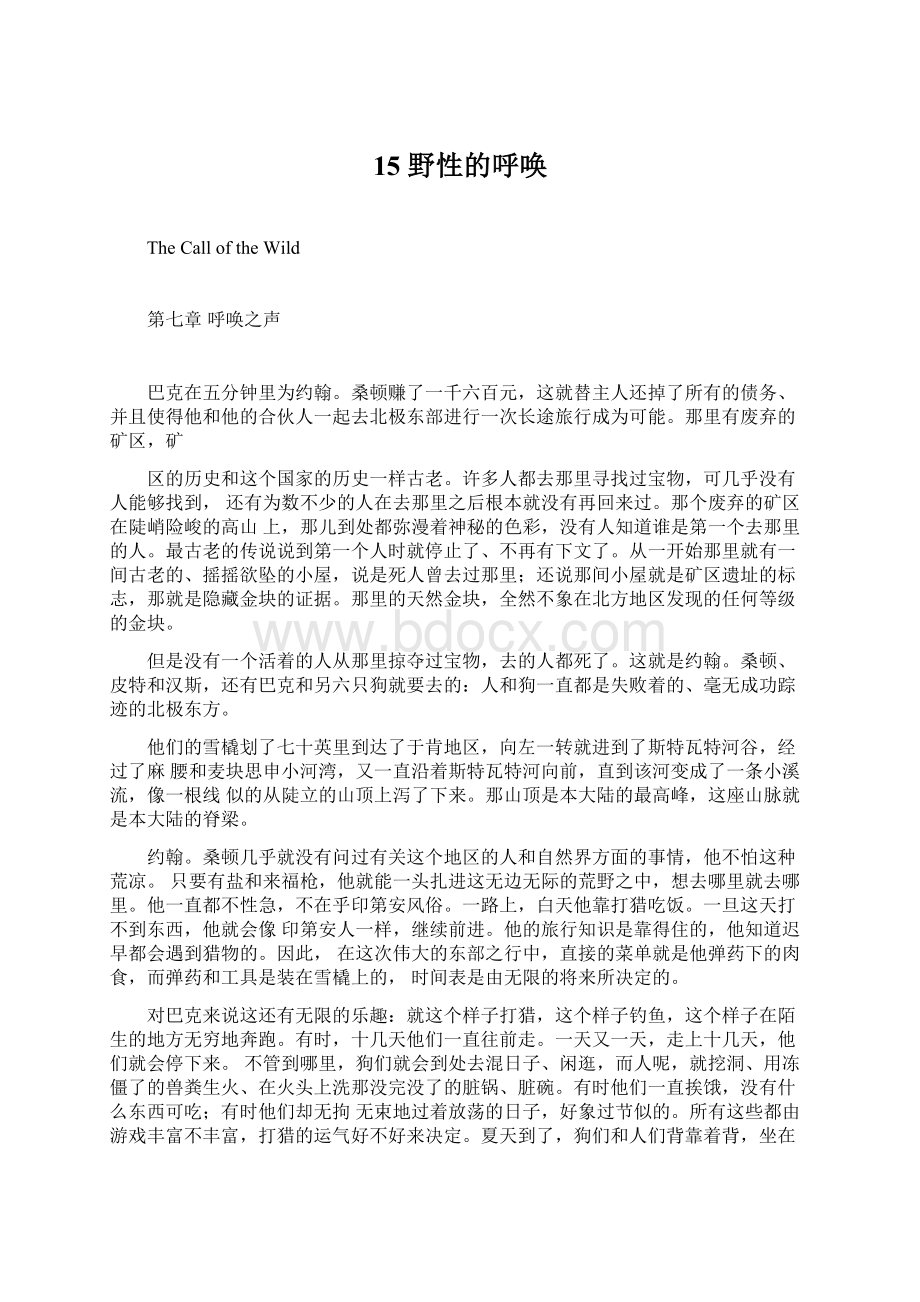
有时他们却无拘无束地过着放荡的日子,好象过节似的。
所有这些都由游戏丰富不丰富,打猎的运气好不好来决定。
夏天到了,狗们和人们背靠着背,坐在筏子上横过高山湖泊;
或者坐在用从岸边挺拔的森林里砍下的巨木做成的细长小船上,在那些不知道名字的河流里上上下下。
一月又一月,时间过来了,又离去了。
他们在这无边无缘、没有被画进地图、没有人来过的、如果真有那间小屋也许就有人来过的地区穿来穿去。
夏天,他们曾被大风大雨吹得四分五散;
冬天,他们曾在林带线和永久雪线之间光秃秃的山顶上,在冷冰冰的午夜日光下冻得瑟瑟发抖;
还曾掉进山谷里,身处在成群的蚊虫和苍蝇中;
而在冰河的阴凉中采集到的草莓和鲜花,和在引以自豪的南方采集到的一样多、一样好。
在这年的秋天,他们陷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多湖地区。
这个地区暗淡、荒凉而又寂静。
这里曾经有过各种野禽,但这时却毫无生命,也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只有阵阵冷风吹过,随处可见冰雪的痕迹,潺潺流水孤独而忧郁地泛着阵阵浪花。
又一个冬天,他们漫游在一个曾有人到过可踪迹却已湮没了的地区。
一次,他们来到一条通往森林的小路,这是一条古代的小路,好象是离那间传说中的小屋很近了。
可是这条小路不知道起于何地、终于何处,路上到处补满了玄机。
谁开的这条路、以及他为什么要开出这条路都充满着神秘。
又有一次,他们偶然见到一间样子像古墓、早已损坏了的打猎人用的小屋。
在那些腐烂了的毛毯碎片中,约翰。
桑顿发现了一个长桶似的燧石发火装置,他知道这个装置是用在早期西北地区哈德森海湾公司制造的枪上的。
当时这样的一只枪能值包裹住它高度那么厚的所有海狸毛皮的价钱。
除此以外,关于建造了这间小屋、把枪留在毯子里的早年间的这个人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了。
春天又来了。
他们漫游到了一条勉强能称得上是路的尽头。
在那里,他们没有发现那间迷失的小屋,
而是在一个宽阔的山谷里,发现了一个含有金粒矿砂的浅地。
这里,金子像是横过洗衣盆底部的黄油似地闪着光。
他们再也不用往前去寻找更多的了,他们决定就在这里干,哪儿都不去了。
每天他们工作着,赚到几千元洁净的金沙和天然金块。
他们日复一日地干着,金子装进了驼鹿皮做成的袋子里,五十磅装一袋,堆起来有那么多,如同云杉树枝搭成的小屋外面的柴火堆一样高。
他们就像力大无比的巨人一样苦干着,日子也像做梦一样一天天地过去。
他们的财富堆积得越来越高。
狗们没什么事,只是时不时地拖一网桑顿猎到的肉过来吃。
巴克长时间地在火边冥思苦想着,那个短腿长发人的幻影经常被它想起。
此刻没有多少事可做。
那个人的影子就经常在火边眨眼,巴克和这个人在它能忆起的另一个世界里到处漫游着。
这另一个世界里最突出的东西就是恐怖。
那位长发人睡在火边时,巴克观查着:
他的头放在膝盖之间,两手互相紧握着。
巴克看见他睡得很不安稳,有许多动作,表明他始终醒着;
不时地,这个人会在黑暗中恐怖地、朦朦胧胧地出现,把更多的木头扔进火里。
巴克能感到它和这个人沿着海边在走,长发人拣着贝壳,边拣边吃;
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提防着随处隐藏着的危险,双腿则随时准备好,只要危险一出现就要像风一样去奔跑;
巴克又和他无声地爬着穿过森林,巴克跟在长发人的后面,他们各自分开、互相警戒着。
他们两个耳朵扯动着、鼻孔哆嗦着。
因为这个人和巴克一样,都敏捷地听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
长发人能荡到树丛中,能在树梢上行走,速度快得和在地上行走一样。
他用手抓住树枝荡来荡去,有时能一下子荡过去十几英尺,又一把抓住树枝,从不失败,从不掉在地上。
实际上,他呆在树上的家里就和呆在地上的家里一样。
巴克想起来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它在树下守夜时,这个长发人都是双手紧紧地抓住树枝,睡在它头顶上的树上的。
和这个长发人的影子同样虚幻的是,在森林深处有一种声音在呼唤。
这种声音使巴克的心中充满了不安,充满了陌生的欲望,这使它感到非常模糊。
为此它经常发呆,并有一种甜蜜的愉快感。
因为终究不知道这声音到底是什么,因而它就判断:
这是一种野性的怀念,野性的躁动。
有时它追赶这种声音直到森林深处。
它到处寻找,仿佛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
它轻声地叫着,但是很明显,它的声音小、胆却很大,有一种反抗的意思。
它的这种心情是可以控制的。
它会把它的鼻子伸到冷冷的木头上、伸到那些苔藓里;
或者伸进黑色的土壤里,那里生长着茁壮的绿草。
每当闻到这肥沃土地上的气息,它的心中就充满了愉快;
或者它会好几个小时地蹲在那里,仿佛在执行着埋伏的任务。
它的身后是霉菌复盖着的、倒下去的大树干。
它大睁着双眼、支起双耳,机敏地捕捉着它能听到、看到的一切。
这极可能是——就算是在自我欺骗吧,它对这种它所不能理解的呼唤感到很是吃惊。
它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关心这些:
乱七八糟的这一切东西,它是被推着这样去关心的。
对此它没有任何理由。
不可抵抗的冲动掌握了它。
它会躺在营地上,懒懒地在日头下打瞌睡。
但是它的头会突然抬起、耳朵突然翘起,专心地去听;
它会猛地跳起、冲过去,冲啊、跑啊,这样子地奔跑几个小时。
它会跑过森林里的小道,穿过那些长满了一束束叫不上名字、北极地区特有的黑色植被的开阔地带;
它爱跑到下面干枯的河道里;
它爱偷偷地爬到树丛中窥探小鸟们的生活。
白天的某个时候,它会躺在树丛的下面,观看鹧鸪鸟咕咕地鸣叫;
另一些时候,它则在树林中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
它尤其喜欢在夏天的子夜里跑进朦胧的月光下,倾听大森林睡眠中柔和的喃喃声。
像人类阅读书籍一样,它也要试图去弄懂那些符号、听懂那些声音,追寻那种神秘:
那种呼唤、那种醒着时候的、或是睡着时候的呼唤,那种自始至终都在让它去关心的东西。
一天晚上,它从睡梦中惊醒、睁开了热切的双眼、颤抖的鼻孔灵敏地嗅着、全身毛发竖起、形成了一个个波浪。
从森林深处又传来了那种呼唤。
(或是那种呼唤的一个音调。
这种呼唤一直都被巴克记录着,有多种音调)这次呼唤:
音色分明,音调准确,过去从没有过—
—这是一种拖得很长的嗥叫。
巴克知道这种嗥叫:
这是一种古老的、从远古时代一直传到如
今的嗥叫,连嗥叫的方式都是一摸一样的。
就像以前听到这种嗥叫一样,巴克穿过了沉睡的草地,快速而平静地猛冲过树丛。
它接近了这种嗥叫声,越是接近,它就走得越慢。
它小心地迈着每一步,终于走到林中的一个开阔地。
它挺起腰来,抬头向前看去,原来那是一只像木头似的、斜立着长长的细身材、鼻孔正冲天而叫的狼。
巴克没有弄出任何声音。
那只狼停止了嗥叫,感到了它的存在。
巴克大大方方地摆了个姿势,半蹲半坐着、身体简洁地收拢在一起、尾巴又直又硬、四肢不屈服地踏在地上。
巴克的每一个动作都混合着恐吓、还暗示着一种友好,这是一种使野兽和被掠夺者之间的会面濒于休战的表示。
但是这只狼还是逃离了它的视线。
巴克带着野性的跳跃跟随着,狂暴地扑了过去。
巴克跟随着那只狼进到了一条黑黑的通道,在小河的河床上,有一大堆木头挡住了去路。
那只狼旋转了起来,以它的后腿为轴心、用巴克以前的队友乔的时髦动作、以及所有那些被逼到困镜中的、声音嘶哑了的狗们的疯狂咆哮着,毛发高高地竖起、龇着牙咧着嘴、连续、快速、成功地猛扑、猛咬着。
巴克没有进攻,而是用一种友好的态度,围着它转着圈。
这只狼有点迟疑,有点害怕,因为巴克的身体有它三倍大,而它的脑袋只及巴克的肩膀那么高。
看见巴克过来了,它猛地又跑开了。
追击又重新开始了。
过了一会儿,那狼又被俘获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又重新做了一遍。
显然这狼的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不如巴克。
但巴克却也很难抓住它。
一等巴克的头到了它的侧面,它就会跑,就会旋转着穷叫大喊,一有机会就会跑开。
但到最后巴克的顽强终于被这只狼所接纳。
因为它靠鼻子去闻,终于发现:
巴克根本就不想伤害它。
于是它们就变得友好了,开始半害羞地、有点过敏地、违背了它们那种野兽的凶狠劲而玩到一起了。
这样地过了一会儿,这只狼用一种大步子来表示它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它很明白地向巴克表示它还要过来。
于是它们就肩并肩地穿过了阴沉沉的朦胧,直向着小河湾的河床上跑去,跑进了小河流出的峡口,跨过了一个荒凉的分水岭。
那里是小河的发源地。
沿着小河的那一面斜坡,它们下到了一个较低的地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向外延伸的森林。
森林里有许多河流。
它们平静地跑过了这个巨大的森林,跑了一小时又一小时。
太阳越升越高了,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巴克大喜过望,它知道它正在对那种“呼唤”做出最后的回答。
它并肩和它的像木头似的狼兄弟朝着那个地方跑去。
旧时的记忆很快向它袭来,它被惹起了性子、跑起了兴趣,它渴望地要想见一见这种“呼唤”的影子,那怕是鬼的影子也好。
它以前已经做过这种事情了:
那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在一个它能模模糊糊记忆起来的世界。
现在它又要原样地把这事再做一遍了。
此刻,它是那样地自由自在,在空旷开阔的土地上奔跑。
大地就在脚下,蓝天就在头上。
它们跑到一条溪流边停了下来,喝起了水。
巴克想起了约翰。
桑顿,于是它就坐了下来。
那只像木头似的狼向着那个确实传来“呼唤”的地方跑了去,然后又反身向巴克跑来,用鼻子闻闻它,做出种种动作,仿佛是在鼓励它跑过去。
但巴克却慢慢地站起身,转回了头,向着来得路上走去。
它的野兄弟走到它的跟前,陪着它走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在这一段美好的时光里,对它反悔的举动轻轻地、软软地悲鸣着。
巴克又坐了下来,鼻子向天空伸去,大声地嗥叫了起来。
这是一阵悲伤的嗥叫……巴克坚定地走在了回家的路上。
它听着它的野兄弟们的悲鸣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飘渺,一直消失在遥远的大森林里。
桑顿吃晚饭时巴克冲回了营地,它向主人表达了狂暴的欢喜,把他推翻,爬在他的身上,舔着他的脸,咬着他的手——像个大傻瓜似的玩着。
桑顿对这种玩法给出了一种特殊的回报:
他抱着巴克前仰后合、笑着、乐着、深情地骂着。
两天两夜,巴克没有离开营地,从没有离开过主人的视线。
它跟着他、看着他工作、看着他吃饭、晚上看着他钻进毛毯里、早上看着他走出帐篷来。
可是两天之后,那种“呼唤”
从森林里又传了过来,比过去的声音更大、更急、更响。
巴克又不安宁了,它又被它的野兄弟的影子缠住了。
它又想起了分水岭的那片微笑的土地,又想起了和它并肩跨过那片大森林的木头兄弟。
它又一次在树林中徘徊,但是却见不到它的野兄弟。
虽然它整夜整夜地守侯在那里,可那种悲伤的嗥叫却再也没有传过来。
它开始晚上在外面睡觉。
有一度曾有好几个白天离开了营地、呆在了外面。
有一次它跑到了小溪尽头的分水岭,下到了溪流间堆放木材的那快低地。
在那里它漫游了整整一个星期,徒劳地寻找着它那位野兄弟的新踪迹。
在这期间它咬死了一些小动物,用来充饥;
它迈着轻松的大步,到处走着,好象从不疲倦;
在那条不知在哪里就流进大海的宽阔大河里,它抓起了很多大麻哈鱼,而在抓鱼时也被遮天盖日的蚊虫咬了个够戗;
随后它又在这段河边杀死了一头大黑熊。
它无助而可怕地在森林中咆哮着。
就是这样地,它就好象是经过了一场艰苦的战斗,这场战斗唤醒了潜藏在它身上最后的剩下来的残忍。
两天之后,它又返回到它杀死那头大黑熊的地方,发现有十几只狼獾正围着那头死熊争吵。
它像愚弄小玩意儿似的把它们驱散开,只剩下了两个,使它们不再吵了。
巴克对血的渴望变得比以前更加强烈了。
它是一个杀手,专门去捕食,就靠干这种事来谋生,孤单而独立。
它觉得,只有靠自己勇猛力气的美德,才能得意扬扬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只有强者才能活下去。
因为所有的这一切,它变得非常骄傲,这种骄傲传遍了它的全身。
这种骄傲,在它的所有行动中都显现了出来,很鲜明地在它的每一块肌肉上起着作用,用简单明了的话来说:
恰恰就是这种骄傲在驱使着巴克行动。
这使得它光荣的皮毛比任何其它东西都更光荣,它的肌肉上、眼眉上飘逸着美丽的棕色色彩,胸脯正下方白色的毛发上散射着一种光亮。
它很容易被错认为是一只巨大的狼,但它比它远古血统里最大的狼还要大。
它从它的圣。
伯纳犬的父辈那里继承了高大的身材和沉重的躯体;
又从它的牧羊犬母亲那里,将它这种巨大的身材和沉重的躯体发展到了极点。
它的肌肉是结结实实的狼的肌肉,可比任何狼的肌肉还要多、还要长;
它的头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更宽、更阔,比所有巨大笨重的狼头都要大许多。
它的狡猾是狼的狡猾,是那种野性的狡猾。
它的智慧:
那种综合了牧羊犬和圣。
伯纳犬的智慧;
加上现在这所有的一切:
在这野蛮凶残的生存学校里它所经历的一切,以及从中获得的各种经验,知识。
这一切,造就了它,使它成为一个可怕的生物。
作为一个直接靠吃肉来生存的动物,它浑身上下充满了力气。
况且它现在正处于生命的高潮期,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生命的能量随处可见。
当桑顿慈爱的大手抚摩它背的时候,能感到随处爆发的活力在皮毛下啪啪做响,能觉出每根毛发都在迸发出被囚禁在体内一触即发的力量。
巴克的全身,从大脑到身体,生机勃勃,肌肉里的每根纤维都焕发着生气,都被激活到了剧烈的顶点。
全身上下各个部位都配合得那么协调、那么平衡、那么丝丝入扣,那么饱满、那么不能再多一分、那么不能再少一厘,那样地恰到好处。
但凡目力所见、听力所及,需要行动时,它都能像闪电那样予以快速地反应。
凡是一只声嘶力竭、拼死拼命的狗在跳起来保卫自己,或进攻对手时所能采取的一切,巴克都能以两倍的速度和能力做到。
它观查着每一个动作,倾听着每一个声音,用最少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而这一点,在别的狗,则仅能做到只是听一听、看一看而已。
巴克能在同一个时间里做到:
发觉、判断、行动,三位一体。
面对一件事,别的狗是先发觉、再判断、后行动。
而在它,这三个动作,既是原因、又是结果。
它这种对相关动作不需间隔时间的能力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根本就分不清,它的哪个动作在先、哪个动作在后,这三个动作它是同时做出的。
它的肌肉是那样地充满硬度,外面来的牙咬起来,就像咬上了钢铁做成的弹簧。
生命的溪流流过了巴克的身体,恰似灿烂的潮水,那么狂烈、那么欢快。
看来这股潮水,一旦变得消魂忘形,就会从它巴克的体内爆裂开来,迸发成涓涓细流,变化为无数个碎片,慷慨地冲向前去,冲向全世界。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一条狗!
”一天约翰。
桑顿说。
当时他的伙伴们正看着巴克冲出营
地。
“上帝就是照着它的摸子把它造出来的。
”皮特说。
“太棒了!
我想我再也找不出什么话来形容它了。
”汉斯断言。
他们看着它冲出了营地,但他们没有看见,它在冲进森林的秘密地方之后的那种可怕的变化。
巴克不再往前冲了,它马上变成了一个野蛮的东西。
什么柔软的动作、像猫似的行走都丢掉了。
快速奔跑的影子,在更加疯狂的影子中出现了、消失了、又出现了、又消失了。
它知道如何去获得每一个借口能带来的利益;
它把肚子贴在地面像蛇一样地爬行,并像蛇一样地跳跃和进攻;
它能不被发现地从窝里弄到一只松鸡;
能无声无息地杀死一只睡着了的兔子;
它能咬死一只飞过半空的花栗鼠,并且把时间算得恰倒好处,若再稍迟一点,那花栗鼠就飞进树丛中去了;
在开阔的水池子里,鱼的动作对它来说就太慢了,海狸也没有它快。
它把它们抓住吃了,还能小心翼翼地修复好被弄坏了的堤坝。
它杀死它们,是为了吃掉它们,是为了填饱肚子;
不是为了嬉笑打闹。
但它宁愿去吃它亲自杀死的,而不愿去吃那些已经死了的东西。
因此,一种潜在的滑稽就贯穿在它的行动中:
它喜欢偷偷地接近松鼠。
而一旦它抓住了这只松鼠,它又会把它放开,在树尖上用一种使松鼠们感到有种致命恐怖地和它们瞎聊,闲扯。
随着秋天的到来,驼鹿(产于北美的一种大鹿——译者。
)大量地出现了。
它们轻轻地移动着脚步,在低凹、严酷的峡谷里迎接着即将到来的冬天。
巴克已经拖倒了一头迷路的、就要长大的小驼鹿,但它强烈地希望能得到一个更大一些、更凶一些、更可怕一些的猎物。
一天,它来到了分水岭,走到了小河的尽头,就遇见了这样的一头。
一队有大约二十头的驼鹿已经走过了溪流和木材区,为首的是一头巨大的公驼鹿。
这头公驼鹿性情狂野,站在地上有六英尺高,是一个甚至连巴克都希望的那种凶恶可怕的敌手。
巴克走了上去,这头公驼鹿突然抬起了它那巨大的手掌状的鹿角。
这鹿角分开有十四个点、漫开有七英尺宽。
公驼鹿的小眼睛里燃烧着刻毒的火焰,露出恐怖的凶光。
它吼叫着凶狠地看着巴克。
公驼鹿的上半身有一处露出了一只羽毛弓箭的末端,这更加衬托了它的凶野。
受一种蛮荒世界的、古老狩猎时代的本能驱使,巴克把这头公驼鹿从鹿群中分了出来。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它在公驼鹿前大声地吼叫、放肆地跳跃。
站在那巨大的公驼鹿以及可怕的鹿蹄子前,若稍有不慎,公驼鹿只需轻轻一击,巴克就会命丧黄泉。
公驼鹿无法转身,面对巴克獠牙的危险和咄咄逼人的劲头,它变得狂怒了,于是鹿劲大发,它向巴克进攻了。
巴克狡猾地躲开了,用一种无能力跑开的假象引诱着公驼鹿。
巴克用这种方法,把公驼鹿从鹿群中分离开来。
这时有两三头小驼鹿从后面冲了上来,试图将受伤的公驼鹿救回去,好让它再回到鹿群中间。
有一种野狗般的、不知疲倦的、像生命本身一样坚韧不拔的耐心。
这种耐心可以保持一个动作,在没完没了的几个小时里一动不动。
蜘蛛网里的蜘蛛;
盘成圈的蛇;
草丛中守侯着的豹,它们都具备这种耐心。
这种耐心尤其属于有生命的东西,尤其属于当这种生命在猎取它赖以生存的食物的时候。
这种耐心巴克也有。
它缠在驼鹿群的周围,减慢着进攻的速度,以便激怒那些小驼鹿,骚扰那些小驼鹿来使大驼鹿们担心,挑起它们无助的愤怒而使受伤的公驼鹿更加疯狂。
这种状况持续了半天之久。
巴克的勇气不断地增加着,从各个方位发起进攻。
旋风般的威胁包围着这只驼鹿群,分散了的驼鹿一被巴克咬倒,其余的就又聚集在一起。
但是这些驼鹿们的耐心越来越少,动作越来越急噪,失误越来越多。
一天的时间用完了,太阳落在了西北方的河床下。
(黑暗返回了,秋天的夜晚只有六个小时)年轻的驼鹿们折回了它们的脚步,越来越勉强地围住了它们的领袖。
日益临近的冬天正蹂躏着这些处在低纬度的驼鹿们,看来它们将永远不能摆脱掉这个不知疲倦的家伙了。
这家伙一次次地把它们拦住,它唯一要得到的东西就是它们的命,它对命这种东西的兴趣要比
其它任何东西大得多。
到了战斗的终点,它们只能付出越来越多的死伤数字。
随着夜幕的降临,老公驼鹿站在那里,头更低了。
它悲切地看着它的伙伴们——它所了解的这些母驼鹿们、它父亲般地统帅着的这些小驼鹿们、以及它所掌握着的所有这些驼鹿们
——它们踉踉跄跄地走在正快速衰弱了的光线里,脚步乏力而急迫。
老公驼鹿是不能再跟着它们走下去了。
老公驼鹿把鼻子猛地冲向巴克那残忍的獠牙、那不让它走开的恐怖前……。
三百磅呀,比巴克的体重还多一倍呐!
它,这头公驼鹿,曾经活得那么长、曾有那么强的生命力、在它的生命中曾经充满了那么多的战斗和奋争,它都挺过来了。
但是此刻,在这最后的关头,在这样的一个动物的牙齿前、这动物的头还没有达到过它那有着巨大关节的膝盖呢,它却面对着死亡!
从那一刻起,不管是天黑还是天亮,巴克就再也不放过它的这个猎物,再也不给它的这个牺牲者以片刻的休息了。
它不容许其余的那些驼鹿们去吃嫩条、嫩叶或是什么桦树、柳树的枝枝芽芽;
而当这头受伤的老公驼鹿在跨过那些狭长细小的溪流、意欲消除掉它那燃烧着的干渴、要去喝水时,巴克是怎么都不会给它这种机会的。
很经常地,那些驼鹿们拼死地跑上了一条长长的逃跑之路,在这种时候巴克不是试图去拦住它们,而是大步地慢跑、轻松地跟在它们的后面,以满意的心情看着这种游戏进行下去。
而当驼鹿们停在那里,它还干脆就躺在那里;
可一旦它们要力争去吃、去喝时,它就猛烈地向它们进攻。
老公驼鹿那巨大的头在鹿角的下面垂得越来越低了,步履蹒跚的步子迈得越来越虚弱了。
它终于只能仅仅是沉溺于长时间地站立在那里,鼻子贴在地面上,沮丧的耳朵耷拉了下来。
巴克也终于找到更多的时间为自己了,它有更多的时间去饮水、去休息了。
在这种时候,它红色的、懒洋洋的舌头垂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那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大公驼。
巴克看来终于要下手了,它能感到大地在颤动。
当这些驼鹿们跑进这块土地时,其它种类的生物也在跑进来。
森林、溪流和空气看上去早就为各种类别生物的存在而颤动了。
这种颤动的信息一直使巴克忍住,它不靠视力、不靠听力,也不靠嗅觉,只靠一些别的难以琢磨的什么感官,就能确确实实地感觉到这种颤动。
它听不见什么特别的、也看不见什么异样的,可它能知道,这块土地是有点儿不同东西的。
这种不同的、奇怪的东西通过这块土地,已经在进行中、蔓延中,巴克决心在它完成了眼前这件事情后,就着手去好好地调查一翻、研究一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在第四天结束的时候,巴克终于最后咬倒了这头巨大的公驼鹿。
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它把它杀死了,吃了它的肉,它睡了下来,转过头来四下里张望着。
休息了一会儿后,它的力气又重新恢复了过来,它觉得比以前更强壮了。
它把脸转向了营地、转向了约翰。
桑顿。
它突然开始大步地慢跑了起来,它跑呀、跑呀,跑过了一小时又一小时。
在杂乱无章的路上它知道该往哪里去,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它要穿过这陌生的土地,它要跑到那个人的跟前。
这方向,那人,都仿佛是一根有很强吸引力的针,刺得它羞愧。
它往前跑着,越来越感到大地有一种新的涌动,在这块森林里分明还有一种更宽广的生命,这种生命不同于巴克在整个夏天能感觉到的所有的生命。
这已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了。
这个事实已经用某种微妙的秘密方式被它感觉到了,不再折磨它了。
鸟们在谈论着这个事实,松鼠们在闲聊着这个事实,微风也在耳语着这个事实。
有好几次它停了下来,深深地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思考着这个事实,思考着这个使它更快速地跳跃、更快速地向前奔跑的事实。
巴克被一种要发生灾难的感觉压迫着,如果这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不是灾难的话,但是它却还是觉得有一种压迫感。
当它跨过了最后的溪流,跑在通向营地的山谷之中,它向前奔跑着,那种警惕的感觉更大了。
离营地还有三英里,巴克看到了一种新鲜的踪迹。
这种新鲜的踪迹使它脖子上的毛发起了波浪,竖了起来。
它沿着这踪迹径直跑向营地,向着约翰。
桑顿跑去。
巴克急急忙忙地跑着、飞速地、秘密地、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拉直了。
它机敏地注意到了还有更多踪迹的细
节。
这里每一个细节都在讲述着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