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论《瓦尔登湖》中的矛盾生态哲学.docx
《读书心得论《瓦尔登湖》中的矛盾生态哲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读书心得论《瓦尔登湖》中的矛盾生态哲学.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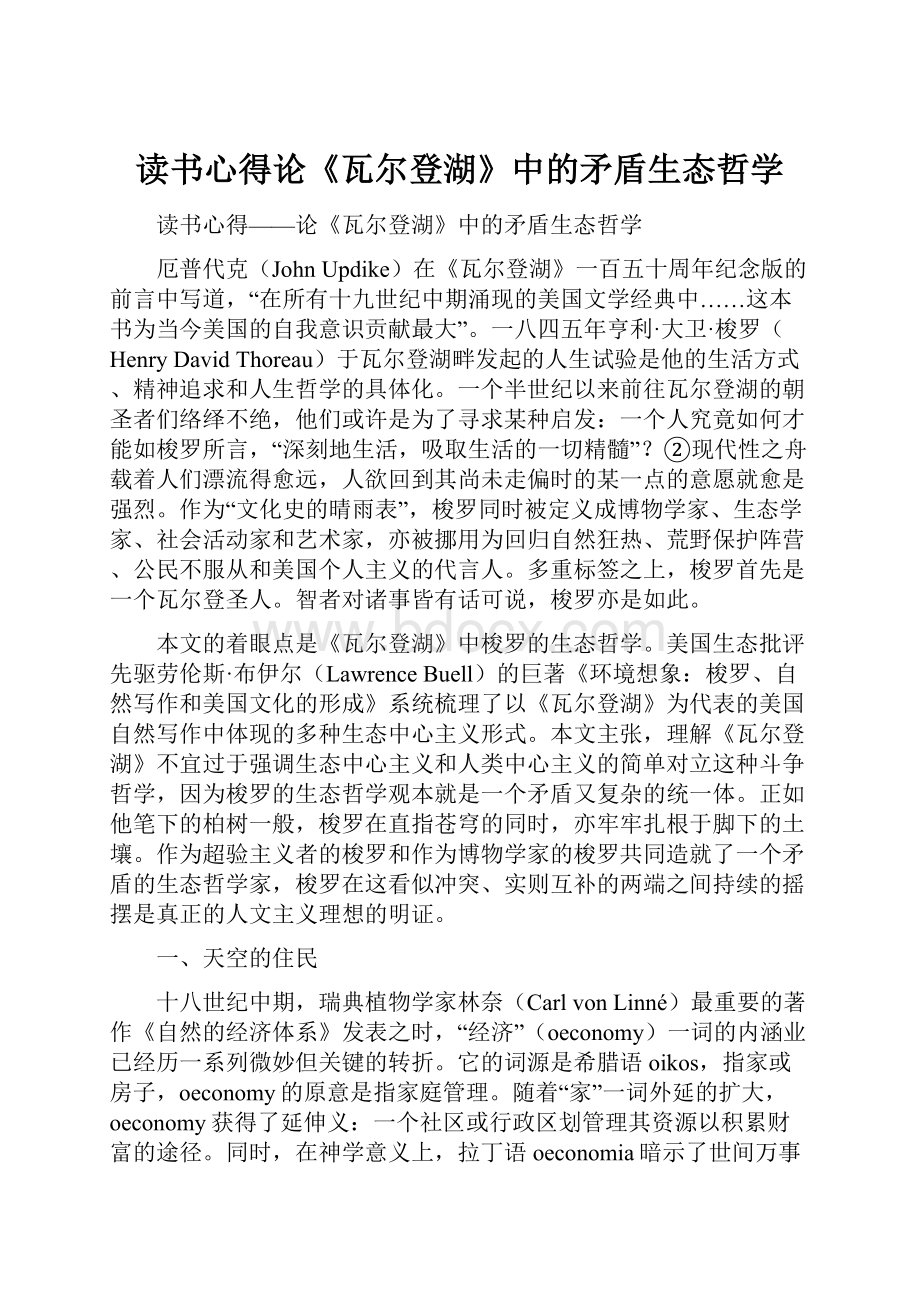
读书心得论《瓦尔登湖》中的矛盾生态哲学
读书心得——论《瓦尔登湖》中的矛盾生态哲学
厄普代克(JohnUpdike)在《瓦尔登湖》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版的前言中写道,“在所有十九世纪中期涌现的美国文学经典中……这本书为当今美国的自我意识贡献最大”。
一八四五年亨利·大卫·梭罗(HenryDavidThoreau)于瓦尔登湖畔发起的人生试验是他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和人生哲学的具体化。
一个半世纪以来前往瓦尔登湖的朝圣者们络绎不绝,他们或许是为了寻求某种启发:
一个人究竟如何才能如梭罗所言,“深刻地生活,吸取生活的一切精髓”?
②现代性之舟载着人们漂流得愈远,人欲回到其尚未走偏时的某一点的意愿就愈是强烈。
作为“文化史的晴雨表”,梭罗同时被定义成博物学家、生态学家、社会活动家和艺术家,亦被挪用为回归自然狂热、荒野保护阵营、公民不服从和美国个人主义的代言人。
多重标签之上,梭罗首先是一个瓦尔登圣人。
智者对诸事皆有话可说,梭罗亦是如此。
本文的着眼点是《瓦尔登湖》中梭罗的生态哲学。
美国生态批评先驱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巨著《环境想象:
梭罗、自然写作和美国文化的形成》系统梳理了以《瓦尔登湖》为代表的美国自然写作中体现的多种生态中心主义形式。
本文主张,理解《瓦尔登湖》不宜过于强调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简单对立这种斗争哲学,因为梭罗的生态哲学观本就是一个矛盾又复杂的统一体。
正如他笔下的柏树一般,梭罗在直指苍穹的同时,亦牢牢扎根于脚下的土壤。
作为超验主义者的梭罗和作为博物学家的梭罗共同造就了一个矛盾的生态哲学家,梭罗在这看似冲突、实则互补的两端之间持续的摇摆是真正的人文主义理想的明证。
一、天空的住民
十八世纪中期,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vonLinné)最重要的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发表之时,“经济”(oeconomy)一词的内涵业已经历一系列微妙但关键的转折。
它的词源是希腊语oikos,指家或房子,oeconomy的原意是指家庭管理。
随着“家”一词外延的扩大,oeconomy获得了延伸义:
一个社区或行政区划管理其资源以积累财富的途径。
同时,在神学意义上,拉丁语oeconomia暗示了世间万事中上帝之手的作用,到了十七世纪,oeconomy也带有了上帝对宇宙的神圣管辖的意义。
上帝负责保障宇宙的一切组成部分均在其掌管、控制和计算之下精准有效率地运作。
oeconomy一词循着这两条线索形成的最终含义,是对所有物质资源或者说地球生命的掌管和组织。
十八世纪时上帝同时扮演“造设地球家庭的最高家政师”和“确保其有效运转的管家”的角色。
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梭罗有意反转了他所处时代对“经济”一词的一般理解。
《瓦尔登湖》首章的标题在现代读者看来或许稍显古怪:
在现代世界,追求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的利益和效率最大化的“经济主义”思考和行动方式已然成为“公共政策和政治争论中经济思想里最有力、最广泛的主导形式”。
②十九世纪早期,通过有效管理来创造财富、提高生产力的迫切要求在大英帝国已得到十足的展现;这阵资本主义之风迅疾漂洋过海刮到了美国独立革命的摇篮——新英格兰小镇康科德。
当这个蒸蒸日上的小社区在充斥年轻美国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下行使“经济”手段时,梭罗却在实践他自己的“经济”。
他的“美丽的家政”和“美丽的生活”是“在室外培养出来的,外面既没有房子也没有房主”。
梭罗言及“经济”时,实际是回到了古希腊语词oikonomia,即人生的哲学。
他埋怨当时教给学生的不过是“政治经济学”,而“那与哲学同义的人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梭罗在作为权宜之计的生活和作为哲学的人生之间作了区分。
他把自己的林中人生试验描述成“事业”(原文为“business”),在瓦尔登的居留占据了他当时全部的精力,去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
梭罗提醒当时人们的重要一点,是“人需要的不是他能够用来从事某项事业的手段,而是他能够从事的事业本身,或者他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指出了本末倒置的谬误:
重要的不是手段(人用以积累越来越多富余物品的工具,致使人活在一种舒适的麻醉状态之中,奴役了自己),而是目的(人选择的人生道路),以及人最终能够成为什么。
梭罗去往林中,是要找出人生的意义所在,以及人如何才能最好地度过一生。
不难看出,梭罗的思想能够被置于古希腊人文主义传统之中:
他追求真理、真实和自由,他的双手伸向超越现世自然规则和社会事务的理想(也是理念)领域。
在这位哲学家的眼里,为“谋生”(makealiving)而辛苦劳作的康科德镇民不过是“土地的奴隶”,屈服于物质增殖使他们同真理间隔了两层,导致了他们同自己和同圣灵之间的双重异化。
梭罗主要是
EcologicalIdeas,NewYork:
Cambridge,1994,p.37.
②JulieNewman,ed. GreenEthicsandPhilosophy :
An
A-to-ZGuide,ThousandOaks,CA:
Sage,2011,p.154.从导师爱默生那里继承了柏拉图式理念论。
早在一八三六年,青年梭罗就和当时许多新英格兰年轻人一样,拜读了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匿名出版的《自然》一书,自此爱默生对梭罗的影响可说是终生的。
和爱默生一样,梭罗感到自己从俗世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精神需求似乎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除非他能超越“这黏糊糊的野兽般的生活”并到达更高等的理性(Reason)的完美乌托邦。
虽然爱默生和很多浪漫主义者一样在自然中发现了一种广博的统一性,他却把拥有更高智能的人的头脑——人脑能进行直觉性的认知、洞悉和想象——抬高到了自然规则的中心位置。
正如他在《自然》中所言,“世界之所以缺乏统一性,断裂成堆,是因为人和他自己就不统一”。
爱默生敏锐地察觉到理性(Reason)和理解(understanding)间的差别:
为了恢复灵魂与自然和神圣存在的内在一体性,人必须运用更高层次的理性以区分理念、真实和通过经验主义的分析和比较得出的低层次事实。
唯有将全部的自然(爱默生所说的自然,是指去除人类理性后宇宙的一切剩余部分)理解成一系列深刻的隐喻,人才能达成精神发展,并重获被自我的碎裂打破的连续统一性。
用梭罗的话说,他的同胞们生活在堕落且绝望的境况中,因为他们“只认事实,只关注实情”。
碎裂的问题同“理解”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由牛顿和伽利略领衔的现代实证科学的崛起以肃清古希腊传统中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性为代价。
随着冰冷、超然的数学及物理科学方法企图构筑不同的模型以精准、机械地阐释自然,专业化、劳动分工、组织机构的建立和个人身份的固化紧随其后,完整的人碎裂了,他短浅的目光紧盯着物质进步。
科学的本质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和人自身的过程中得到的知识,近代科学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功不可没,然而科学知识过度的实证性偏向也带来了严重问题。
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化批评家芒福(LewisMumford)写道,伽利略“真正的罪行”在于他“把原本完整的人类经验……换成了其中一个微小的部分,这部分经验只是有限的时间跨度内的观察,以及从质量和运动角度进行的阐释。
与此同时,他贬低了人类经验中未经调解的真实,使其不再重要”。
学生不再学习“人生的艺术”,他们学的只是碎裂的知识分支,这在梭罗看来很难说是进步。
梭罗正是针对此种简化主义范式,提出了自己对文明的见解。
一个真正的文明人应当努力通过更有价值的方式达成更有价值的目的,他若是失败了,那么他不比野蛮人强多少:
“这个国家尚未适应人性文化,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灵性面包切得比先辈们的小麦面包还要薄”。
人自身的异化导致了尊严和完整性的消弭,令他同超验理想越来越远。
“我们的人生惊人地富有道德性。
美德与邪恶无时无刻不在交战”。
与康德(ImmanuelKant)类似,爱默生和梭罗亦视道德的首要焦点为个体的道德或精神成长。
在超验意义上,超越自然正是助人抓往理想的高尚道德之境中的真实的必要条件。
梭罗在“更高的法则”一章中将他对道德纯粹性的强调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讨论素食的同时,梭罗深化了他早先提到的简朴哲学。
对哲学家来讲,简朴意味着同时压制人的食肉本性和发扬人的智能(Intellect)和天才(Genius)以培养“更高的天性”,从而“将形式上最粗鄙的肉欲净化成纯洁和奉献”;梭罗毫不避讳地把人的动物本能描述成“低劣野蛮的兽性”,认为一个感到身上的动物性正逐日被高尚的道德精神所代替的人,是有福之人。
的确,超验理想对人的高等理性的信仰同试图超越物质世界、触及真实的理想形式的人文主义道德传统有着内在一致性。
这能够解释梭罗为何宣称“天性很难克服,但必须被克服”。
在“豆圃”一章,梭罗进行了种豆的试验。
不难看出他实际是在实践其超验哲学。
梭罗在豆圃耕种、锄地、收获,并不和村人一样是为了获取粮食或金钱,而是“为了比喻和表达,为了有朝一日一个寓言家可以引用”。
难道梭罗本人不就是一位寓言家吗?
比起豆子,他更乐意收获人类超验的果实——“真诚、真实、简朴、信念、清白,以及类似的品质”。
当时的新英格兰流行一句谚语:
“他不懂(不会数)豆子”(“Hedoesn’tknowbeans”),以嘲讽无知者,而梭罗故意挪用了这句话,称自己种豆是为了懂豆。
若是以当时的“经济标准”来评判的话,梭罗的种豆试验明显是失败了。
然而,听凭路人如何评头论足,梭罗一心要挖掘出种豆的本质意义。
粗鄙农人对种豆的理解变得无关紧要,梭罗头脑里的双眼望向上苍,他锄的豆子也成了理念的豆子。
由此看来,梭罗似乎很像他自己在瓦尔登湖的一个春日看到的鹰。
鹰的飞翔十分高尚,梭罗甚至觉得它从未落脚土地。
鹰独自飞翔,又有晨光和大气作伴:
它是真正的“天空住民”。
但在“简朴生活”和“豆圃”两章里,梭罗也揭示了他的理念主义追求的另一面。
数张记录其生活试验收支的图表只是他脚踏实地的务实性最显著的表现;他的的确确在活生生的自然中生活。
他不仅以诸多细节提供了实际的生活指导,而且特别描写了他和自然世界的亲近关系。
梭罗称自己砍下的松树非敌是友,说自己和豆子建立了“长期的熟识关系”,这并非完全是隐喻或者精神层面上的。
天空的住民或许的确筑巢于高耸的云端,但这并不是说他从不脚踏实地。
二、康科德的潘神
人脑赋予自然连贯性,从而恢复它与圣灵的统一——这一超验思想似乎是反博物学的,因为这样一来物质环境或者说非人自然不过是用以发掘人同真理的原初关系的舞台而已。
自然世界本身不是目的,人的动物性必须让位于知悉真实的超然追求。
爱默生写道:
“我们要做人,不做土拨鼠。
我们安坐在象牙椅和丝绸地毯上,橡树和榆树会乐于为我们服务”。
①这其中有培根(FrancisBacon)式意识形态的味道:
科学的权力和进步为现代实证科学的繁荣奠基。
但梭罗不会同意这一点:
“我待在户外,是为了我身体里矿物的、植物的、动物的部分”。
②梭罗与活生生的自然的共感指向了他的另一面:
一位朴实的博物学家。
和其他超验主义者不同,梭罗是真正植根泥土的实干家,他能融入到自然世界里去。
梭罗童年与自然生命的亲近一直延续到了成年,对自然的存在,他总是怀着清醒的直觉、动态的本能和深切的依恋和自然互动。
他对土地的归属感发自内心,对野性自然的热爱充满激情:
“我们需要旷野的滋补”。
梭罗高度评价猎人和渔人,因为比起他,这些人更能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梭罗只能抱着哲学家的期待接近自然,因此失去了一部分原有的野性、自然的动物性。
他同自然的感官上的直接接触使他生发出对“原始和野蛮”生活的本能向往。
当他有冲动拥抱野性时,他甚至会产生生吞土拨鼠的想法,希望借此与野物融为一体。
要探究梭罗的博物学倾向,还必须将他置于更大的语境中考量。
生态批评家布朗奇通过追溯十九世纪初建立起来的美国自然散文文类对《瓦尔登湖》及此后的自然写作的影响,得出了相当有理的结论:
巴特拉姆(WilliamBartram)、威尔逊(AlexanderWilson)等人的浪漫主义自然写作中“博物学和文学的艺术性混合”③帮助形成了美国博物写作传统。
自然的博物学研究方法始于英国怀特(GilbertWhite)一七八九年出版的《塞尔伯恩博物志》,这同西方文化中浪漫主义的崛起并存。
将《瓦尔登湖》放在生态思想史的浪漫主义发展线索中考察,能够更好地理解梭罗作为博物学家是如何扎根土壤的。
超验主义对实证科学引发人性异化的批评是基于古希腊理念论传统,而浪漫主义则是以博物学为武器,攻击了实证科学导致人类执
①RalphWaldoEmerson,RalphWaldoEmerson:
Essays,Beijing:
CentralCompilation&TranslationPress,2010,p.394.
②HenryDavidThoreau,Journal,vol.VIIIin TheWorksofHenryThoreau,Boston,1906,p.44.
③MichaelBranch,“IndexingAmericanPossibilities:
TheNaturalHistoryWritingofBartram,Wilson,andAudubon,”pp.282-302inCheryllGlotfeltyandHaroldFromm,eds.,TheEcocriticismReader:
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Georgia:
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297.迷于超越物质世界的倾向,博物学能够为冷然的科学客观性重新注入一点热度。
浪漫主义者们发现人和非人间存在本质上的有机联系,把自然视为动态的整体,它是活生生的,充满无限、错综复杂的关系。
现代数学分析有打破该整体,把机械般的部分分开研究的倾向,这就构筑了一个可预测又可控制的安全世界,尽管这其实只是假象。
浪漫主义者反对这种做法,否定机械类比,着重强调人类和土地间身体和情感上的亲近关系。
古老的博物学传统可回溯到原始人为了生存而代代相传的丰富的自然知识,这一传统在欧美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浪漫主义者对非人自然表现出的虔诚实际是古代异教万物有灵世界观再起的表现,万物有灵论歌颂一切生命中流淌的活的灵魂。
基督教对自然的教条式冷漠体现在保卫羊群不受自然界敌意侵害的“好牧羊人”(GoodShepherd)意象中,浪漫主义者们针对这一点的反叛显然是泛神论的。
梭罗言及上帝时往往模棱两可,野果和晨风是他的精神滋补品,比起耶稣和耶和华,梭罗偏爱晨曦女神欧若拉、潘神和凯尔特祭司德鲁伊。
在浪漫主义的头脑中,人和非人存在之间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共感。
与梭罗同时代的美国地理学家和外交家马什在《人与自然》中写道:
“当我们往有机生命的海洋中扔下一枚极小的卵石,也可能会对自然的和谐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波及无数生命”。
浪漫主义者们质疑“简化式科学不敬的窥探和解释”,对博物学广博、描述性的科学知识更有好感。
《瓦尔登湖》中细致的自然观察隐含着对生命深深的热爱和敬意,梭罗像圣弗朗西斯(St.FrancisofAssisi)一样,与老鼠、松鸡和松树为友,赞颂诸湖,感谢助他重获内心安宁的微雨;他为明媚春光而欣喜,很高兴看到搬到户外的家具融入到野生自然中;他最大限度地把自己融入到作为整体的自然的生命力中,这股生命力是“我们生命恒久的源泉”,是“最接近万物”的“最广大的法则”。
拉斯金(JohnRuskin)所言的情感谬误并不适用于梭罗,他会在冬夜欢迎潘神和自然母亲与他促膝而谈。
梭罗发现人类和自然互通感情,“我怎么能不和大地心心相印呢?
我自己不就是树叶和蔬菜的一部分吗”?
“诗人说人该研究的是人。
我说,忘了这一切;用更广大的眼光看宇宙。
人类太自我了”。
梭罗对远大于人类存在的自然的把握是整体性的。
实证科学的进步创造了人战胜自然的假象,人立于宇宙中心,万物似尽在掌握之中,为他服务。
梭罗却警示道,人一定不能太自负,没必要“胡思乱想人类最终会如何毁灭。
只要北方吹来的强风稍稍再强一点,人类的生命线就断了”。
人类造出的铁马不转弯,像负责切断生命线的命运女神阿特洛波斯一样;但真正的阿特洛波斯正是自然本身的化身。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科学对人在实践中或本能地学到的东西进行的报道,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人类知识,或者说人类经验的记录”。
博物学传统中人类谦卑的地位使人承认,在比他广大得多的宇宙中自己是何等无力。
《瓦尔登湖》全书中,梭罗最激烈的批评口吻出现在“湖泊”一章中谈及弗林特湖命名的部分。
梭罗刚结束他对湖底细沙中生长的海藻的描写,就突然开始了猛烈的批判:
弗林特这个名字源于该湖的前主人,梭罗嘲讽这个“肮脏愚蠢的农夫”无权为它命名,用湖周边居住的野生居民的名字恰当得多,因为它们才是土地共同体的成员,互相依赖,息息相关。
在他的眼里,满脑子都是机器的农夫只想着如何赚钱,他既贫穷,又堕落。
这同梭罗自己对“经济”的理解(美丽高尚的生活)一致,但此处强调的是人对自己在自然中位置的无知。
简单来讲,此处梭罗的看法与其说是超验的、哲学的,不如说是生态的、博物学的。
“奢谈什么天堂!
你们把大地都玷污了”。
人文主义傲慢和狭隘的一面不仅极大地威胁了自然,人类命运也处在危险之中。
人的狭隘视野令世界看起来越来越小,于是他心安理得地盲信自己是大地之主。
对梭罗来说,仅仅是夜行一次,看似安定的熟悉感和可预测性马上会被困惑所取代:
“只有当我们完全迷路,或是转了向后”——当我们再次被置于自然的更大存在中时——“我们才能领略到地球的广阔和神奇……才能开始找到自我,认识到自己的位置以及我们和世界之间的无限关系”。
梭罗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的神秘和自主性。
科学家厄伦菲尔德(DavidEhrenfeld)在其名作《人文主义的傲慢》中指出,人只有“在完全被规制的、可预测的、实验室般的环境中”①才可能完全确认他完美地控制了世界。
但这是不可能的。
梭罗的人文主义很清醒:
测完瓦尔登湖的深度并绘图说明他的科学操作后,他话锋一转,指出人类只了解极少的自然规律,分析测量的结果之所以会出错,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任何混乱和不规律的地方”,而是因为“我们在计算中忽视了很多本质元素”。
偏狭的傲慢态度导致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们所理解的自然的稳定和平衡只在孤立的情形下成立,如果人不能认识自然的整体性,就很容易掉入短视的陷阱。
爱默生说:
“社会从不进步。
它在这一面得到的越多,在另一面就退化得越快”。
现代科学的阴暗面在于它削弱了人对自然的虔诚。
博物学家梭罗提醒人们,人完全仰仗自然而生,必须对未知事物保持惊奇感,而不是试图同化它们。
“唯有在野生状态中,世界才能得到保护”。
梭罗人格的另一面是一位朴实的博物学家。
《瓦尔登湖》对自然界丰富多彩的描述在书出版时就激起了评论界的积极反应,一位英国评论家说,“博物学著作中最优秀最流行的作品中也找不到如此有魅力的描写”。
然而此时读者不禁会产生疑问,尽管作者的超验主义和浪漫主义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攻击了现代实证科学的阴暗面,但这两个方面难道不是一开始就水火不容吗?
超验主义无疑有忽略自然的真实脉动、坚持高尚的沉思式哲学生活的倾向,而浪漫主义特别强调人无法否认的生理和心理根基,以及人和世界的感官和本能交流。
梭罗如何能将这二者融为一体?
这位瓦尔登圣人的自我难道不是分裂的吗?
三、在空中垂钓
爱默生于一八三七年发表的演讲《美国学者》中有这么一句话:
“于是,‘认识你自己’这句远古神谕和‘研究自然’这句现代箴言,终于很好地融汇成了同一句格言”。
数年后,梭罗在夜半时分垂钓,发现自己被一种奇特的感觉笼罩了:
他正在天国的草地上放牧思想之羊,可突然感到“这微弱的抽动”打扰了他的梦,把他“和大自然重新联系起来”;他“同时把渔线甩上天空、垂入这未必更稠密的元素之中”,于是“一箭双雕,用一只鱼钩钓到了两条鱼”。
从这种连续性可以看出,梭罗的“大自然”也是可触摸的、有型的、物质的。
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特别提及瑞典哲学家斯维登伯格(EmanuelSwedenborg)。
他相信人脑和自然间的交流,在外部物质世界和内部精神世界间发现了联系,认为这是真实互相照应的两个方面。
爱默生的超验哲学正是受了这一点的启发,他认为统一性原则就是“每时
每刻都存在于头脑……和外部自然的无限形
式间的一种包罗万象的关系”。
这和浪漫主义对有机整体的理解类似:
人的意识和自然世界间不存在激烈的二元对立。
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谢林(FederickSchelling)就认为自然是外化的头脑,头脑是内化的自然。
物质世界中流动的能量和人体动脉中流动的血液有内在一致性。
在《自然》中爱默生统合了naturanaturata(物质自然的具体形式)和naturanaturans(不可见的自然内部规律),认为前者引导了人脑对后者的探究。
爱默生超验论中的浪漫主义源流也是不容忽视的。
超验主义研究学者麦克格里格在探究梭罗对自然的研究时,主张梭罗试图摆脱爱默生理念论的努力使其思想更具原创性。
他认为爱默生的理念论中,物质世界完全屈服于人的智力,自然“的存在几乎为零”,爱默生否认博物学的重要性,但梭罗有真实的博物学知识。
事实上爱默生热爱自然,对自然知识怀有浓厚兴趣。
他对自然的观察也很细致,对地质学、化学、植物学等科学知识都有了解,认为科学就是对自然的研究。
从现代视角来看,爱默生难逃人类中心主义者的标签,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他看问题的方式。
在他眼中,人与自然互动的终极目标,是要超越感官和道德缺陷,想象出一个理念的完美精神世界。
因此,活的自然并不在这种乌托邦想象之中。
爱默生研究自然是为了超越自然,他聚焦于超验的道德理想。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区别和这种思考并不相关。
爱默生所说的人对自然的支配暗示的是人道德性的提高,并非人对自然的随意占有。
人若是践踏自然,同时也是在亵渎圣灵和他自己的本性。
梭罗进一步思考了超验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他的想象更为均衡。
梭罗专家罗宾逊指出,梭罗读《自然》时,已经很好地把握了柏拉图传统、十八世纪理念论和“试图综合理念论和经验论的新兴哲学”。
②哲学应当融合观察(对应经验事实)和猜想(对应理念沉思)。
“如果我尚未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就开始造一道拱门,我不会得到任何满足”。
《简朴生活》中梭罗举出了人生存的必要条件——“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这些是人无法否认的生物之根。
梭罗的伐木人朋友赛里恩代表了人的动物性,尽管梭罗从未成功培养他的哲学眼光,他依然欣赏赛里恩的质朴、谦卑和天然。
当人性开花结果前,人必须扎根泥土,活在当下。
“如果树丛被砍倒了,你怎么能期望听到鸟儿歌唱呢”?
梭罗的超验论以他的博物学为基础,二者是一个整体,不宜割裂。
所以梭罗写道:
“我们不是完全和自然交织在一起”。
梭罗尝试过动物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又不是为动物性主宰的。
哲学家梭罗不能忍受没有野性自然的生活,博物学家梭罗又不由自主地把视线转向自己的内心。
幼鸟眼中的宁静和天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潜鸟的狂笑让他认输,蚂蚁军团的大战又令他叹为观止。
另一方面,他又感觉自己的思想似乎能脱离自身存在,思想拥有自己的意识,冷静地旁观他的所作所为。
即使在梭罗最像一个博物学家的时候,他的内核仍是超验的。
超验论和博物学的交织以“声籁”一章中有关铁马的片段最为典型。
起初梭罗说费奇伯格铁路是连接他和康科德村的纽带,走在轨道边的梭罗站在旷野和文明的中间点上。
但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暧昧,一方面他开始用“刺穿”“尖叫”和“轰鸣”描写火车的运动,甚至用了邪恶的火龙这一传统意象。
另一方面,他又突然改变贬低的语气,称他“带着和观赏日出一样的心情,观赏着清晨的火车隆隆驶过”。
他把火车驾驶员比作喂养铁马的厩主,说他们有英勇和勤勉的高贵品质;这样一来,梭罗有意把火车自然化了。
接着他开始赞扬商业,称其自信、安宁、进取又勇敢,它的“方法十分自然”,“当火车叮叮咣咣地从我身边驶过时,我觉得耳目一新,身心舒展”。
虽然梭罗也流露出对商人们粗鄙追求的批评,他的批评对象不是商业本身。
火车纯洁又英勇的品质和人应当追求的精神成长的高贵目标一致。
高潮临近,梭罗又话锋一转:
听到铁马载着禽畜呼啸而过,他评论道:
“你的田园生活也就这样疾驰而去……我必须离开轨道,让列车驶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