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风吹花幽鸟鸣春文档格式.docx
《晚风吹花幽鸟鸣春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晚风吹花幽鸟鸣春文档格式.docx(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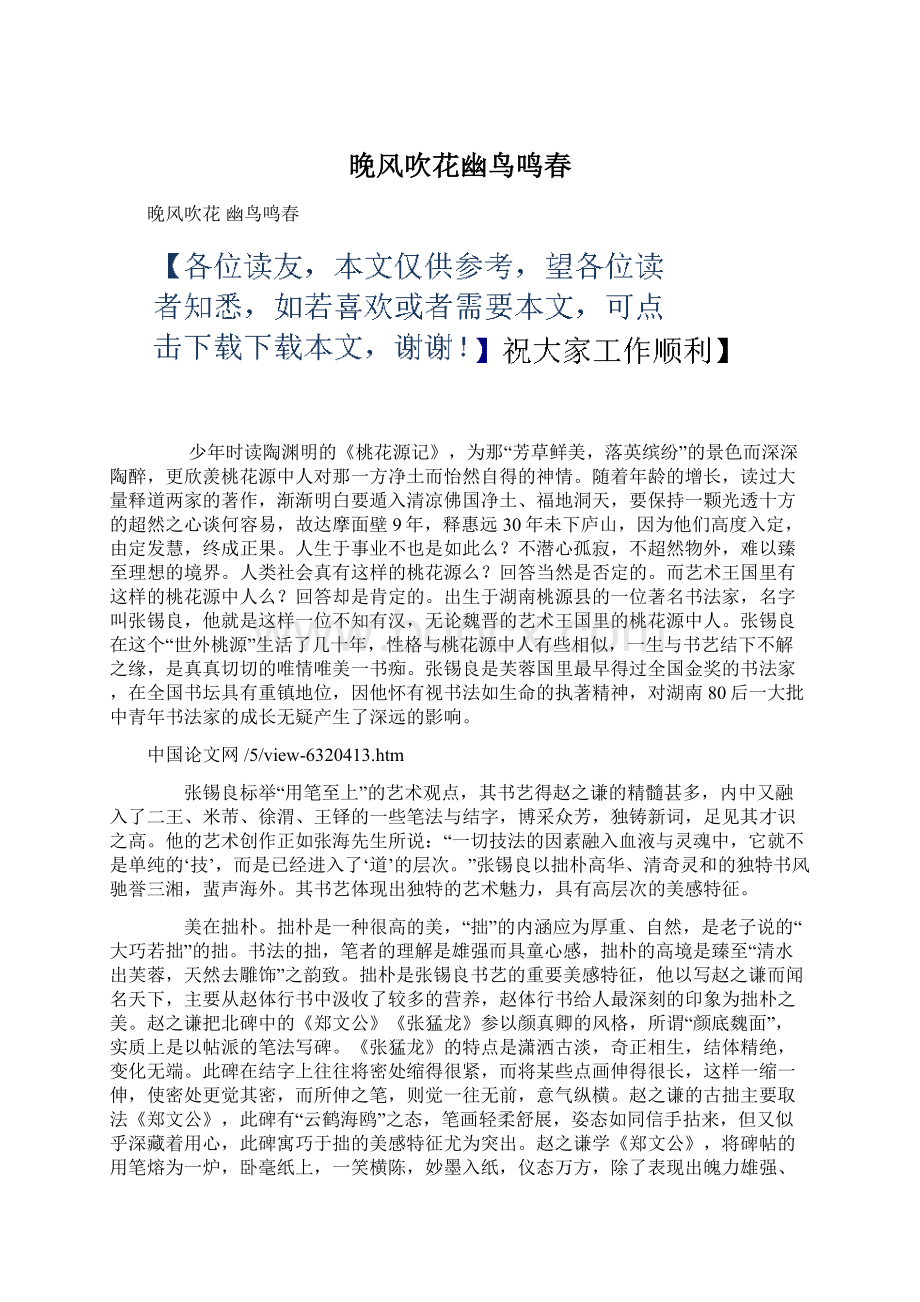
张锡良是芙蓉国里最早得过全国金奖的书法家,在全国书坛具有重镇地位,因他怀有视书法如生命的执著精神,对湖南80后一大批中青年书法家的成长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论文网/5/view-6320413.htm
张锡良标举“用笔至上”的艺术观点,其书艺得赵之谦的精髓甚多,内中又融入了二王、米芾、徐渭、王铎的一些笔法与结字,博采众芳,独铸新词,足见其才识之高。
他的艺术创作正如张海先生所说:
“一切技法的因素融入血液与灵魂中,它就不是单纯的‘技’,而是已经进入了‘道’的层次。
”张锡良以拙朴高华、清奇灵和的独特书风驰誉三湘,蜚声海外。
其书艺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具有高层次的美感特征。
美在拙朴。
拙朴是一种很高的美,“拙”的内涵应为厚重、自然,是老子说的“大巧若拙”的拙。
书法的拙,笔者的理解是雄强而具童心感,拙朴的高境是臻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韵致。
拙朴是张锡良书艺的重要美感特征,他以写赵之谦而闻名天下,主要从赵体行书中汲收了较多的营养,赵体行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为拙朴之美。
赵之谦把北碑中的《郑文公》《张猛龙》参以颜真卿的风格,所谓“颜底魏面”,实质上是以帖派的笔法写碑。
《张猛龙》的特点是潇洒古淡,奇正相生,结体精绝,变化无端。
此碑在结字上往往将密处缩得很紧,而将某些点画伸得很长,这样一缩一伸,使密处更觉其密,而所伸之笔,则觉一往无前,意气纵横。
赵之谦的古拙主要取法《郑文公》,此碑有“云鹤海鸥”之态,笔画轻柔舒展,姿态如同信手拈来,但又似乎深藏着用心,此碑寓巧于拙的美感特征尤为突出。
赵之谦学《郑文公》,将碑帖的用笔熔为一炉,卧毫纸上,一笑横陈,妙墨入纸,仪态万方,除了表现出魄力雄强、点画峻厚的整体气势美之外,而且还寓圆于方、寓柔于刚,表现出婉转清秀、神采飞动的端庄之美。
书法以线立骨,以线传情,简单的线条可以表达无穷的美感。
其实西方艺术也非常重视线条的美感表达,布莱克说:
“艺术和生命的基本法则是,弹性的线条愈是独特鲜明、坚韧,艺术作品就愈是完美。
”张锡良的艺术语言丰富而老到,他于碑版用功甚深,《石门》之雄厚奔放,高古苍茫;
《乙瑛》之骨肉匀适,情文流畅;
《礼器》之瘦劲如铁,清圆超妙,一一精嚼细咽,消化吸收。
他钟情颜鲁公的行书《祭侄稿》的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
正因为对碑板、对颜体的造诣极深,这为他写赵之谦打下坚实基础。
张锡良执着于传统,但师古不泥古。
当代书坛取法赵之谦的书家少之又少,大致为赵体的强烈风格范式和由碑帖兼融所臻至的笔法高度令人望而止步的缘故,而张锡良敢于问鼎赵之谦,因深厚的功力给予了他自信的力量。
读其《摘录滕王阁序》《秋瑾诗・梧叶》等书品,其点线形态及笔墨关系的处理,或润含春雨,然肥而不涨;
或干裂秋风,然干而不枯;
或点画披离,似断非断;
或紧劲连绵,左右逢源,无不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
书家能摄取赵体拙朴之精魂而以自然出之,用笔的“圆”与“虚”臻至和谐统一之境界。
这里的“圆”是指起收笔以圆势和用笔的肥厚体现出颜书的特征;
“虚”主要是竖、撇、捺等出锋线条的未端墨色的枯渴。
虽然是用偏锋,却内力强劲,气满势厚,有立体感,通篇气势统一,变化有致,读来使人感觉胸无滞碍,不禁拍手称快。
美在高华。
张锡良的用笔之精湛能以神遇而不以目即,将赵体行书笔意融入创造性的一片天机之中,书境高度的诗化,境界澄澈高华。
艺术出现高华境界甚为艰难,必须脱尽尘滓,独存孤迥,那是学养、才情、技法、灵感的综合表达。
艺术多有相通之处,司空图品诗: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
饮之太和,独鹤与飞。
”这是对高华之境的形象描绘。
书法的高华之境有较多的唯美色彩,有人认为二王行书的一个特点就是风姿艳溢,气格高华,故以“清风出袖,明月入怀”而状之。
艺术不可为伪,高华之境的产生来自人格的高洁,高品位的艺术创作自然是人格之光的映照。
康有为诗云:
“山谷行书与篆通,兰亭神理荡飞红。
层台缓步��远,高谢风尘属此翁。
”羲之、山谷的书品无疑是其高洁人格的映照。
从艺技而言,没有把握玄解之宰而窥意象运斤的功夫,那么操翰殊多俗笔。
日本佛学大师铃木大拙有一首诗:
“天然存娇姿,肌肤洁如玉。
铅丹无所施,奇哉一素女。
”艺术语言达到铅华落尽见真纯的功力方有高华之美可言。
诗境与书境可以相通,张锡良人格高洁,技法精湛,才气横溢,胸次超旷,故部分佳作近乎臻至超逸绝尘的高华境界。
细读《萧绎・咏阳云楼檐柳》《辛弃疾・水调歌头・盟鸥》等佳品,格高调古,气息和雅,精纯跳达的线条仿佛是生命本体的自然流露,朗现一种静穆空明之韵致。
中国的书画艺术往往以庄禅为思想内核,境界之高华,往往是艺术家这颗道心、禅心的精光外射。
笔者曾与张锡良品茗而谈,可知书家对禅道之理的领悟是甚为深刻的。
书作《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巨幅条屏,书境如天翠浮空,明霞秀野。
此诗有孤篇压全唐之称,被闻一多誉为诗中之诗,顶峰中的顶峰。
书写这首诗的人甚多,很少表达出诗作超逸空明之意境,而张锡良的此篇书作,从用笔而言,时而斩钉截铁,时而婉转流媚;
时而疾涩互现,时而刚柔兼济,能置密匀于疏放之间,寓劲挺于流动之中。
从意境而言,由书法意象幻化出来的艺术境界,极静极幽,仿佛使人感受到时而月色如霜,空蒙皎洁;
时而江流浩渺,怅然神伤;
时而南浦横舟,高楼吟笛;
时而思妇怀人,愁情难遣,书境与诗境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美在清奇。
好奇心是人类最普遍的心理特征,出奇制胜往往是艺术家寻求突破的法宝。
司空图《诗品・清奇》:
“神出古异,澹不可收。
”王羲之论书好以兵法设喻,其实兵家重在出奇制胜: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孙子兵法・势篇》)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而悟笔法,自然是从风云变化的景象中领悟到以奇制胜的道理。
董其昌说:
“书家以险绝为奇,此惟鲁公、杨少师得之。
”奇与新与美有较多的联系,奇中见新,奇中见美,方是艺术的高境。
书法的尚奇是正中见奇,奇中有正。
一幅书品写得规规矩矩,平平正正,偃仰顿挫,联络照应,然而给人的印象是“好生面熟”;
而不那么循规蹈矩,不那么安分守己,参差起伏超越法度,腾凌射空颇为奇险,往往新人耳目,正如苏轼所说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达到“天真烂漫是吾师”的境界方为佳妙。
张锡良是王羲之所说“生而知者发奋,学而悟者忘餐”的艺术家,在世外桃源生活了数十年,妻毫颖而子楮墨,侣二王而友鲁公,传统的功力甚为深厚,兼之悟性超卓,具有了尚奇的学养功力。
他情系赵之谦,也表现出超人的艺术胆识。
其实,赵之谦在清代书坛独步一时,本身就是以奇制胜的艺术典范。
他以诗书画印的全才特点雄踞艺坛,其篆刻专以侧媚取势而出新意;
他以隶书笔法画桂树,笔势奇崛,墨韵酣畅,他把自己流动活泼、巧丽姿媚的各种书法与“使刀如笔、视石若纸”的师刀功力统一起来,顺应清末上海的社会文化特点,由雅返俗,新人耳目。
赵之谦以超人的胆识和足以相副的技巧,从历史的夹缝中拓开一条艺术的坦途。
张锡良取法赵之谦,没有照葫芦画瓢,而是凭借深厚的学养功力对赵体进行了很好的消解,开始以摄取特殊的笔画形态和结字特点为目标,追求形似,之后领悟到了赵氏用笔的内在信息,将赵氏的行书内化为自己的语言,做到提按顿挫得心应手,方圆虚实一任自然,其中自蕴了个性化的因素,如碑的弱化、笔墨的畅达和书写性的强化,充分表明书家创作的自我开拓意识。
读其楷书作品《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统而观之,其点画结构皆静中见动,若飞鸿舞鹤,栖鸟游鱼,安闲自得,舒展洒脱。
徐而察之,起笔多用折锋,逆入平出,笔画遒劲圆浑,刚中有柔,结体茂密,峻拔爽朗,于沉雄中见拙朴,于方劲中见圆通。
细读《向秀・思旧赋》等巨幅书品,平中寓奇,险中涵平,古朴奇巧,纵横自如,气息上雄强飞动,博大精微,而又朗现拙朴自然、烂漫多姿的奇趣之美。
美在灵和。
艺术的高品位应达到一种境界的和谐,中国的哲学历来以中和为最高境界,赫伯特・里德说:
“中国艺术家试图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宇宙的和谐。
”书法作为表现时代精神和生命情调的高雅艺术,就是艺术家用百变不穷的线条、波谲云诡的意象来表达难以言说的美感。
张锡良深得碑板用笔之神髓,又谙熟以二王为正脉的帖系书法之遗意,以才情驱遣造化与传统,故自然湛发一种灵和之美。
所谓“灵”,即灵秀,空灵,也指书境闪耀着一股灵气。
古人说:
“若夫小王风范,骨秀灵运。
”艺术境界只有虚静清空才会灵气畅流。
“和”为中和,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
孙过庭在《书谱》中指出:
“违而不犯,和而不同。
”灵和之美实为中国哲学尚和的美学理想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
明人项穆在《书法雅言》中指出:
“评鉴书迹,要诀何有?
温而历,威而不猛,恭而安,宣尼德性,气质浑然,中和气象也。
”灵和之美为晋韵的重要表现特征。
书法宗晋,这是进入高境的重要标志,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周俊杰对学生和书法爱好者反复强调:
“书不入晋则难成正果。
”书艺要打造时代经典,谨慎创新,以晋韵为宗无疑是正确的。
张锡良数十年来着意追求书艺的灵和之境。
他善于将释道两家的超然哲学运用于人生修炼之中,当周遭的世界被传媒和各种新观念、新思想装点得“花团锦簇”“热闹繁华”时,他还在抱持着“用笔技法对于书法艺术来说,我认为是底线也是高境”;
当有人提出“艺术可以胡搞”,书坛被日本前卫书法、西方的现代艺术弄得晕头转向时,他还津津有味地品读赵之谦的大量尺牍,从中感受到的是一片多姿多彩的烂漫世界;
当人们在不遗余力地炒作,自我吹虚有如大跃进亩产粮食数万斤,一个字值多少多少之时,他还是尽量谢绝参加各种笔会,一门心思考虑如何与赵之谦若即若离,而今又努力写徐渭,写黄宾虹,在艺术境界寻求新的突破。
他一再强调要关注那些艺术的本体因素,而不为非艺术的东西如名利地位等牵萦。
从艺术创作而言,他固守书法延续传承的本质和体现其本质的艺术技巧与时代精神,试图形神兼备地解决传统笔法在当代书法创作中的诸多问题,在强调碑学骨力的同时强调帖学的笔法。
他关注的是帖学化了的赵体本身,肆力张扬赵体高难度的笔法,他书写的大量书品,如《心经》、王维《桃源行》、苏轼《洞仙歌》等都带有清穆之气,把读者带入一种“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超然境界。
他晚近的创作,赵体的基因仍然得到很好地强化,而又充分体现自己的个性特征,读其巨幅书品《朱自清・匆匆》四条屏,俊逸婀娜,天流自流,天骨秀成,风神自在,旷达高古,拙巧互用。
那碑版的雄强,二王的妍逸,鲁公的刚烈,米芾的爽畅已糅合为一。
摧刚为柔的语言,拙朴潇洒的意象,圆融浑成的布局,空灵浑茫的意韵,把读者带入空谷飞泉、幽花自舞的艺术境界之中,将作家超旷、感伤的意绪予以了强化。
其他如《黄宾虹论画语》《古诗・庭中有奇树》等书品,都是写心写情写意写志的艺术力作。
张锡良已过古稀之年,他在艺术王国的世外桃源怡然自得,流连忘返。
艺术创作超于功利而自然硕果丰盈,而书家在鲜花与掌声中依然故我,宠辱不惊。
赵之谦是他永难舍弃的情结,但他能入能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张海先生说过,高出古人一厘米就是创新。
张锡良的书艺新与美达到了和谐统一。
”晚风吹花,幽鸟鸣春”用此八字来概括张锡良书艺的美感特征,我认为是极为恰当的。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