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不起来的女人从萧红小说探究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文档格式.docx
《飞不起来的女人从萧红小说探究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飞不起来的女人从萧红小说探究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文档格式.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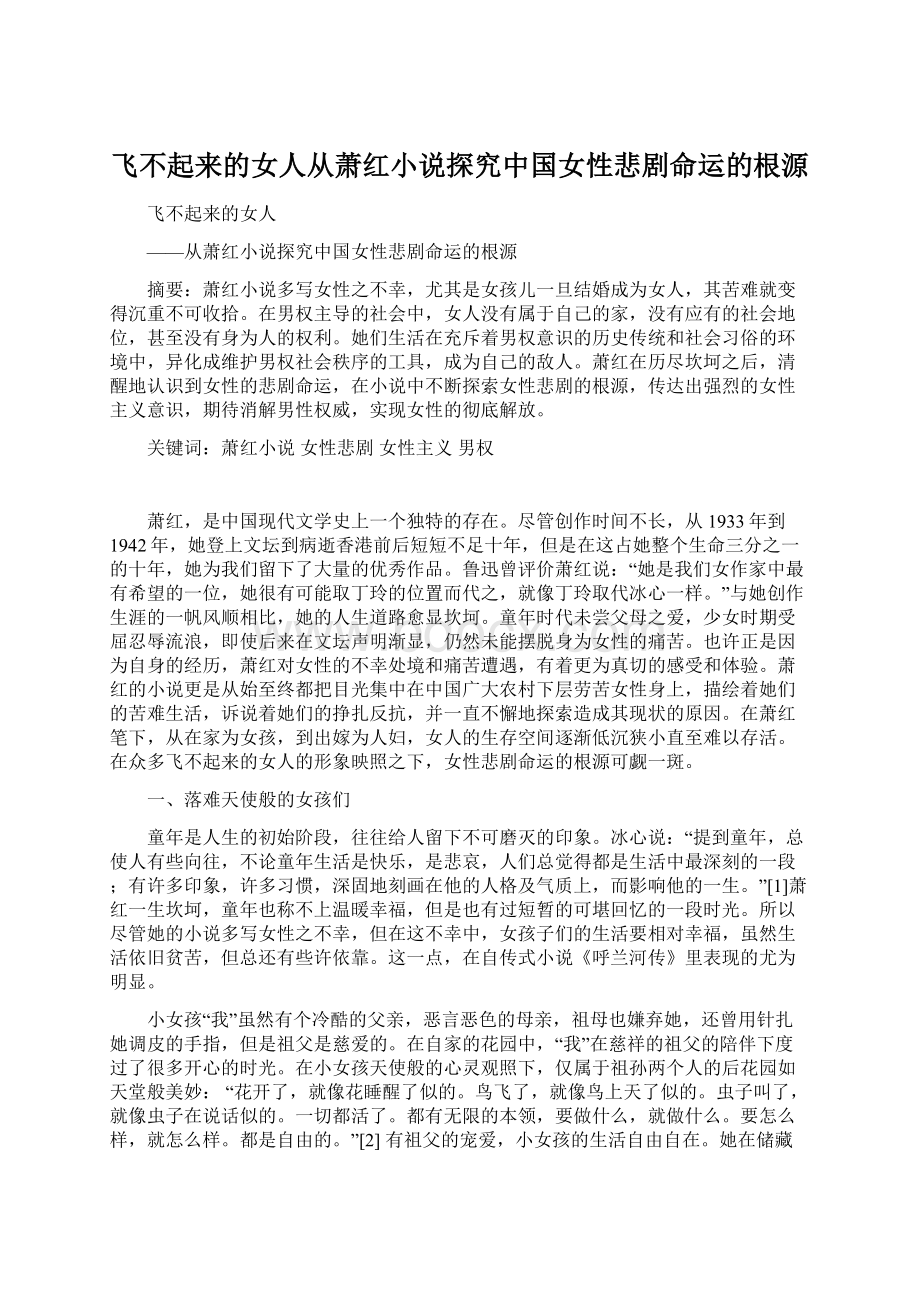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
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一切都活了。
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都是自由的。
”[2]有祖父的宠爱,小女孩的生活自由自在。
她在储藏室探险,翻出各种旧东西,跟祖父学念诗,烤猪烤鸭子。
有时挨祖母骂了,就和祖父一起避到后花园里去。
花园里是“另一个世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
[3]
《小城三月》中也有个“我”,到外祖父家,和翠姨及一众表姐妹们玩儿在一起,逛街买东西,什么流行就追着买什么。
回家后,和堂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因为“咸与维新”,家长都较为开通:
打网球,聊天,玩弄乐器。
在没涉及婚姻之前,女孩们的日子过得很是悠闲快活。
甚至是《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刚刚来到胡家,也还是个小姑娘,头发又黑又长,黑乎乎的脸上挂着笑,可见在家里时过的是不错的,只是后来成了团圆媳妇,才几经折磨,惨淡收场。
不难发现,萧红小说中存在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小女孩的生活往往要比成年结婚的女人好那么一点点。
其差别,一是小女孩有“娘”疼,至少有人来充当母亲的角色:
小女孩“我”有祖父(《呼兰河传》),流浪女小环遇上了好心的王阿嫂(《王阿嫂的死》);
二是小女孩还只处于女儿的位置上,不是妻子,不是儿媳妇,不用戴着社会礼法强加给妻子、媳妇的枷锁,不用受到来自丈夫和婆婆的权威的压制。
小女孩们的生活或贫苦或富足,与大人们无差别,但是她们的人格是自由的。
二、折翼的女人
如果说女孩儿是自由飞翔的天使,那么萧红笔下封建传统规定的婚姻,就是折断天使翅膀的隐形的刀。
女孩儿一旦结婚成为女人,其苦难就变得沉重不可收拾。
(一)女人·
无家
在封建礼制下,从某种角度上讲,女人是没有家的。
列维·
斯特劳斯曾用结构主义思路研究婚姻和亲属系统。
他在《结构人类学》中提出:
“把婚姻规则和亲属系统当成一种语言,当成一种在个人和群体之间建立某种沟通方式的一系列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起到中介作用的是能够在氏族、宗族和家族之间流通的群体内的妇女,她们代替了能够在个人之间流通的群体内的语词,但这种代替根本改变不了以下事实:
这两种情形在现象上有着完全一直的本质。
”[4]斯特劳斯把妇女的流通和词语的流通放在一起思考,一个属于社会婚姻系统,一个属于语言学系统,却有相同之处,这一点极具启发性。
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女人生而承担着流通这样一种责任。
在母亲家的十几年小女儿生活,是为了以后把自己的家庭(家族)与另外的家庭(家族)联系起来做准备,不管她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不管女人是否愿意承担这一切,她们只能在社会婚姻系统规定好的通道中走下去,借助“生命的再生产过程而不是其他符码形式,使自己能够为流通本身所利用(这就是她们的命运之一)”。
[5]
流通是平等的互通有无,各自有得也有失。
在旧中国,娘家得到彩礼,失去女儿;
婆家得到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劳动力,失去一些钱财。
女人在娘家生活十几二十年,注定离开,不得长远。
古有说法:
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
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嫁出去的女儿也不再属于娘家的人,不能再得到父母亲人的庇护。
嫁到婆家后,女人又终究是外来的,婆婆不会把儿媳放在和儿子同等的位置来疼爱。
等到媳妇终于熬成婆,她已经苍苍老矣,对待自己的儿媳同样如对待外人。
这样一来,女人终其一生是没有家的,她只是作为家庭(族)所有的一种物品在不同家庭(族)之间流通。
小团圆媳妇(《呼兰河传》)小小年纪就来到了胡家,扮演着“团圆媳妇”的角色。
长得太大方,性子活泼一点,就遭人非议,婆婆开始打骂她,而且对不驯服的小团圆媳妇越打越厉害,还有人热心献计献策,烙脚心、剪辫子、赶鬼、跳大神、开水洗澡等等轮番上阵。
小团圆媳妇由最初的“头发又黑又长”,“脸长得黑乎乎的,笑呵呵的”,继而有点黄,但是还带着笑,最终“哭也不哭,笑也不笑”全身伤痛悲惨死去。
为什么要打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呢?
婆婆给出了两点理由:
一、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
不打的狠一点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
这是为她着想;
二、“有娘的,她不能够打。
她自己的儿子也舍不得打。
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
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
打猪,怕猪掉了斤两。
打鸡,怕鸡不下蛋。
唯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
”[6]小团圆媳妇挨打了总喊着要“回家”我们现在都可以理解,她说的是回到给她温暖的有娘的家,而婆婆以及众人都以为是去“阴间”。
在她们看来,小团圆媳妇既然已经到了胡家,就生是胡家人,死是胡家鬼。
封建社会,女人出嫁到丈夫(婆婆)家被称为“归”,似乎女人生来即属于夫家。
而婆婆显然并不会把外来的媳妇当成自己家人,所以,无家可归的小团圆媳妇最终只能成为流通的牺牲品。
(二)婚姻·
男权
结婚,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之一。
萧红小说中也多次写到婚姻,但是描写的并不是结婚的美好,婚事的盛大,而是把婚姻写的如坟墓一样,女人踏进婚姻,就失去了女孩儿的幸福,成为男权的附属,为男性所迫害。
《生死场》里面萧红倾注笔墨最多的女性形象是金枝。
天真美丽的少女爱上了强健粗犷的青年,可她只享受了极其短暂的爱情的甜蜜,就落入了男权织就的大网,再也逃不脱。
她从来没有享受过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所应该有的欢乐,而仅仅是男人发泄原始冲动的工具。
萧红是这样描写二人在一起的场景的:
“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
男人着了疯了!
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握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噬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
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尸体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
于是一切音响从这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
”[7]在这些赤裸裸的描写中,两性结合带给女性的幸福感和愉悦感我们根本看不到。
我们能看到的只是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其中充满原始冲动的色彩。
男性彻底无视他们对女性造成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伤害。
后来金枝辛苦怀胎生下女儿,却被丈夫当作累赘,气急之下随手摔死,就像摔坏一个杯子一样随意。
等到金枝做了寡妇,到城里去谋生活,她又受尽男人的种种侮辱。
金枝回村子时,满怀羞愤之情,她想的是:
“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鬼子。
·
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8]只有从女性自身心理出发,探究她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我们才能够理解金枝为什么最恨中国人,而不是残酷侵略的日本人。
因为伤害她最深最直接的,是中国男性。
同金枝一样,男权社会的羁绊,打渔村最美的女人月英也难以逃脱。
曾经她“如此温和,从不听她高声笑过,或是高声吵嚷。
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就好比落到棉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
”[9]这样美好的一个女子,结了婚患了病,不能下地干活后,就遭到丈夫的冷漠摧残。
月英的丈夫撤去她的被子,用砖块围住她,自顾自地吃饭休息,连最起码的水都不给她喝一口。
最终她臀下生蛆,牙齿变绿,原本如花般美丽的的女人悄无声息地死去,生命的尽头除了荒芜的乱坟岗之外,什么都没有。
还有五姑姑的姐姐,当她准备生产,痛苦地扬起灰尘的土炕上爬行时,她的丈夫,那个使她遭受痛苦的男人却走进来咒骂她装死,用烟袋甚至大水盆砸她。
而她“几乎一动也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10]她们是男权下的女人,她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作为人的尊严,而是如奴隶,如工具一般地存在着。
如果说金枝等人是封建男权意识的直接受害者,那么间接受害者就是翠姨(《小城三月》)。
翠姨温婉娴静,聪明多才,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家碧玉”,基本符合传统儒家对“妇德”的要求:
“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
[11]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在烈女不事二夫的封建伦理渗透下,就因为是寡妇的女儿,婚姻不得已成了悲剧。
与翠姨订婚的人在乡下读书,又矮又小,未来婆婆也是个寡妇,似乎只有这样两人才般配。
翠姨接触了时代文明的新鲜气息,渴望读书、想要自由恋爱,后来隐约对读过洋学堂的表哥产生了爱情。
可现实逼迫她走千百年来女性所走的老路,她抑郁、拖延、苦苦挣扎,最终却至死也没有说出心里话。
这不可不说是男权文化教养的一大胜利。
翠姨默默地死去了,她喜欢的那人却完全不知情。
翠姨根本不敢有追求婚姻自由的奢望,只是默然承受男权意识对她的戕害。
在婚姻这座坟墓里,埋葬了女性的青春和梦想,换来男性的超然地位与权力。
相对于小说,萧红的散文更直接鲜明地表达了她的观点。
在她的诸多散文中,多次明确地表达了萧红内心的激愤,对男女地位不平等的现状她深感不满,对女子的命运她很是忧虑。
在《祖父死了的时候》一文中,她指出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婚姻家庭中,女性没有任何地位。
甚至在她自己家中,父亲对待新娶来的继母就如同对待猫狗之类的宠物:
“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的时候便骂她”。
[12]在《女子装饰心理》中,她写道:
“在文明社会,男子处处站在优越地位,社会上的一切法律权利都掌握在男子手中,女子全处于被动地位。
”[13]这些语句都传达出萧红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三)生育·
刑罚
在传统人眼中,生育是女性的天职。
《孟子·
离娄》之中就说:
“于礼有不肖者三事·
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
三者之中,无后为大”,七出之中,也有无后这一条。
结婚之后却没有孩子,是女人的过错,男性可以根据这个理由休妻。
然而却没有人考虑女性生育时所遭受的苦难。
萧红作为女性作家,自己亲身经历过没有爱的生育,也许正是因此,她的小说中女性生育场景描写得惊心动魄,震撼人心。
她把生育定义为对女性的惩罚。
《生死场》中全村都在生产,大狗生下小狗,大猪带着成群小猪乱跑的时候,五姑姑的姐姐也在准备生产。
卷起了席子,露出柴草的土炕上,五姑姑的姐姐在痛苦地爬行。
然而柴草也被婆婆收去了,因为收生婆说:
“压柴,压柴,不能发财”。
女人只能在像一条鱼似的爬在扬起灰尘的土炕上,挣扎着耗尽最后一分力气。
男人对妻子毫不关心,反而很厌恶她生产,依旧使唤、打骂她。
“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
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
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
”[14]也就是萧红,能把生育场景写的这么绘声绘色,这么令人胆战心惊。
繁衍后代本是女性神圣的使命,在这里却几乎等于犯罪。
女人在忍受身体上的痛苦时,还要遭受来自男性的精神虐待乃至暴力行为,这是多么不合理的现象,周围人却熟视无睹,只是把暴怒的丈夫拉开而已。
这场不公,萧红笔下的每个女人都在劫难逃。
金枝(《生死场》)很快也面临着这场刑罚。
曾经喜欢她娶了她的那个男人,婚后也成了“严凉的人类”。
金枝因身子笨重劳作不力而遭受责骂,她的丈夫依旧依着自己的性子,在她身上发挥男人的本能,全然不顾金枝可能为之丧命,最终导致金枝早产。
王阿嫂(《王阿嫂之死》)“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15]最后与早产的孩子一起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李二婶子(《生死场》)在怨恨男人的大哭中小产。
在乡村里,“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
女人处于一种非人的生存状态。
女性生育不再是自然界的伟大创造,而是像动物的生理繁殖一样,泛滥而又盲目,带给人无尽的痛苦。
把生育变成刑罚的罪魁祸首是男人,是男人的自傲、粗暴与性别偏见,把女人变成传宗接代的工具,成为没有自我意识的符号。
生活本身的苦难、剥削阶级的无情、侵略者的残暴固然虐杀了很多女子的生命,但更广大的普通女人们,却是被充斥着男权意识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习俗所扼杀。
三、异化的女性
著名女权主义家西蒙娜·
德·
波伏娃说:
“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
”[16]萧红小说所反映的中国广大劳动女性就是这样的存在。
还是女孩子时,她们处于被养成的阶段,天性还未完全被磨灭,如《呼兰河传》中的小女孩“我”、刚到胡家的小团圆媳妇,《小城三月》中的众表姐妹们等等。
她们快活地探索世界,探索生活,如同坠落凡尘的天使一般,不知烦恼为何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增长,女孩们到了结婚生子的年纪,她们的地位、命运也已基本定型。
小团圆媳妇被各种规矩束缚,天天挨打才正常;
翠姨要嫁给寡妇的矮小的儿子才符合常理,她抑郁而终无人知原因;
金枝、月英们在丈夫的打骂中如花的生命迅速枯萎。
男人打女人是正常的,他们说:
“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
何况你一个长舌妇!
”由此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
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
”[17]
萧红挨过父亲的打,挨过伯父的打,挨过丈夫的打。
所谓“温顺”就是“温柔的顺着”,这一点她深有体会,她更认识到,那是男性中心文化模式对女性的定义,对女性生命权利的剥夺。
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形象是由男人来塑造的,是男人们为了方便自己统治而规定的。
就像波伏娃说的那样:
“制定和编纂法律的人都是男人,他们袒护男人,而法理学家则把这些法律上升为原则。
”[18]也就是说,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男人不仅拥有统治女性的权力,而且有塑造这种统治的根据的权力。
千百年来属于男性的历史掩盖了这一事实,女性只能承受这种结果,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是被统治的。
女性变成欲望的对象,是被奴役的物件,没有自己的意识和思想,成为了一个符号。
萧红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作品中流露出这种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体验。
《小城三月》里“我”和翠姨去亲戚家参加婚礼,看到一群年轻媳妇,穿着打扮行为举止几乎相同,“她们就都是一样的,好像小孩子的时候,所玩的用花纸剪的纸人,这个和那个都是一样,完全没有分别。
都是花锻的袍子,都是白白的脸,都是很红的嘴唇。
”[19]她们就是被塑造的成果,符合社会的审美,代表着男人眼中的标准,却完全没有自我。
比被塑造成一种没有自我的符号更可悲的是,女性在承受一切苦难的同时,不自觉地异化成了自己的敌人,不自觉地充当了男权社会的工具,压迫自己的同性,成为鲁迅的文章《我之节烈观》中所说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就是被这些人杀死的,除了祖父和“我”,她的婆婆,周围出主意的邻居们都或多或少的参与到了对小团圆媳妇的虐杀之中。
也许他们并未怀有歹意,就像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说的那样:
“虽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
”[20]话里话外都是为了小团圆媳妇好,可是正是他们的“好心好意”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同样不幸的还有冯歪嘴子的媳妇王大姐,还是姑娘时,又高又大,人们都夸她是兴家立业的好手,可一旦王大姐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和冯歪嘴子同居,力气大、眼睛亮、辫子长等等都成了过错。
这个冒犯规矩礼法的女性成了众矢之的,与丈夫一家在数九寒天被赶出碾磨房,在众人的冷漠中悲苦地死去。
如果说蓄意杀人是一种犯罪,那么无意识的杀人后而不自知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比有意识的犯罪更可怕的愚昧。
这种愚昧带给人更强烈的心灵上的震撼。
无数个活泼健康的小团圆媳妇、王大姐就是这样被剥夺了生命。
那些不合理的陈规陋俗因为千百年的强制实施,内化成了女性对自己的要求,使女性异化成维护男权社会秩序的工具,成为自己的敌人,这是怎样的悲哀。
四、得不到的解放
萧红在历尽坎坷之后,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悲剧命运。
她在小说中一遍遍地摹写女性的艰难处境,一次次探索造成女性悲剧的根源。
在萧红早期作品如《夜风》、《生死场》中塑造了李婆子、王婆子这样的起来反抗的女性,之后就更多的是不再反抗,而是在穷困愚昧的生活中苦苦煎熬的女性,这似乎是创作上的倒退。
茅盾就曾对《呼兰河传》提出严厉的批评:
“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血腥的侵略。
而这两种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他批评萧红“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狭小的私生活圈子所束缚,和广阔地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
“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
[21]然而实际上这恰恰是萧红成长的一种表现。
表现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女性命运的变革之艰难,这作为萧红的创作主题一直没有改变。
萧红在历尽世事沧桑,尝遍酸甜苦辣的人生滋味之后,对女性的命运有了更为深化的认识,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逐步成熟起来。
她曾对聂绀弩说:
“你知道吗?
我是个女性。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
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我知道,可我还是免不了想:
我算什么呢?
屈辱算什么呢?
灾难算什么呢?
甚至死算什么呢?
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
是这样想的是我呢?
还是那样想的是。
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
我会掉下来。
”[22]这段话隐约透露出一丝萧红对女性命运的绝望,这是她无数次探索后的结果。
五四之后,人们的女性意识有所觉醒,但是女性的命运,事实上并未有根本的改变。
鲁迅先生曾提出“娜拉出走之后该怎么办”的命题,引发无数人探讨,在萧红看来,娜拉出走,其实无路可走。
金枝想出家当尼姑,可尼姑庵不复存在;
翠姨无声反抗命运,可也是至死无人理解。
女性的解放离与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绝不是阶级、民族解放之后,女性就会自然而然的随之得到解放。
束缚中国广大女性的,远不只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还有种种传统道德、封建习俗。
她们一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她们被压制并且自我压抑、相互压抑。
所以直至今天人们仍在讨论妇女解放的问题。
女性的真正解放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许多层面,彻底实现解放仍长路漫漫。
萧红漂泊一生,追寻一生,一次次抗争又一次次失望。
她临终时曾说: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23]她把灵魂寄托给小说,对那些在男权重压下不自觉地挣扎的女性奉献出了她全部的怜悯、关注与同情。
她塑造了一个个女性形象,期待着唤醒人们对女性的悲剧命运的认识,消解男权在社会中的权威,给女人们留出一片广阔的天空,展翅飞翔。
注释:
[1]《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42页
[2]、[3]、[6]、[7]、[8]、[9]、[10]、[14]、[15]、[17]、[19]、[20]均出自萧红《萧红经典》,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326页,329页,384页,27页,91页,42页,55页,55页,8页,321页,267页,373页
[4]列维·
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转引自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约翰·
斯特罗克编《结构主义以来》,渠东、李康、李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7页
[11]班昭《女戒》,转引自杜芳琴《女性观念演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13]萧红《女子装饰心理》《祖父死了的时候》,均转引自张玉秀《萧红小说的女性主义色彩》,《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3月
[16]、[18]均出自西蒙娜·
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版
[21]茅盾《茅盾选集·
五》,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2]王观泉《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版
[23]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版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经典》,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
[2]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
[3]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施军《叙事的诗意——中国现代小说与象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8]赵园《论小说十家》,生活·
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9]艾晓明《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0]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记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2]皇莆晓津《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3]王桂青《书写在“女性身体”上的民族主义——论<
生死场>
兼与刘禾、摩罗商榷》,《小说纵横》,2012年9月
[14]张国飞《“沉默”的“羔羊”——再读萧红<
中的女性命运》,《安徽文学》,2008年第12期
[15]李晓华《乡土话语的女性言说——论萧红与迟子建的地缘小说》,《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
[16]李福熙《论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3月
[17]黄晓娟《萧红的生命意识与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9月
[18]王维燕《妇女解放的两难——<
中女性反抗意识解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12月
[19]姜红《萧萧落红觅归处——论萧红小说中的色彩意蕴》,《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0]秦林芳《童年视角与<
呼兰河传>
的文体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9期
WomeninBondage
——AccordingtoXiaoHong'
sNovelstoExploretheRootCausesofChineseFemaleTragicFate
Abstract: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