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侠客诗风 林宗正在复旦大学的讲演DocumentWord格式.docx
《唐朝侠客诗风 林宗正在复旦大学的讲演Document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唐朝侠客诗风 林宗正在复旦大学的讲演DocumentWord格式.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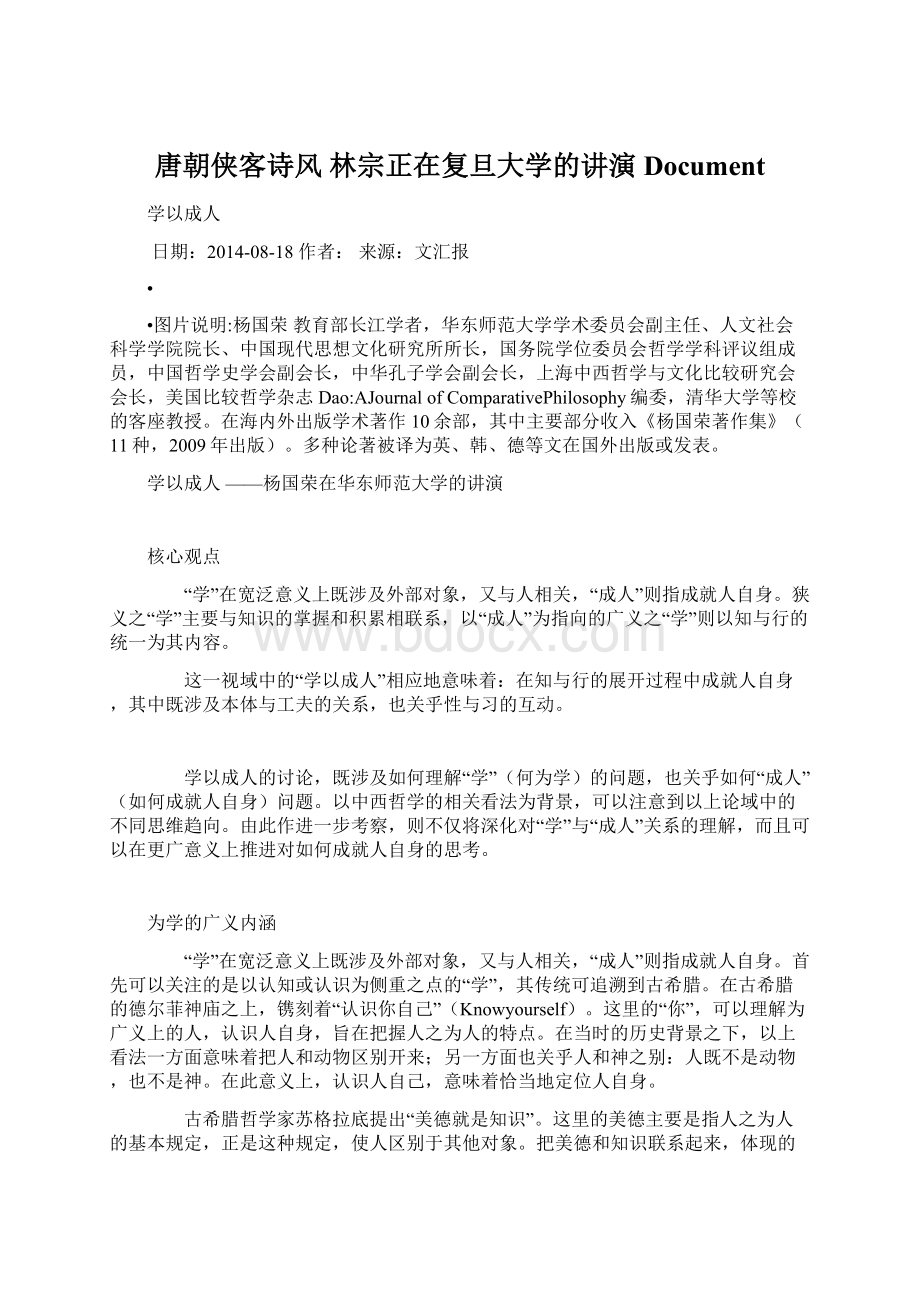
在此意义上,认识人自己,意味着恰当地定位人自身。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就是知识”。
这里的美德主要是指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正是这种规定,使人区别于其他对象。
把美德和知识联系起来,体现的是认识论的视域。
作为与知识相关的存在,人主要被理解为认识的对象。
以“美德即知识”为视域,与人相关的“学”,也主要展现了狭义的认识论传统和进路。
在近代,对“学”的以上看法,依然得到了某种延续。
康德在哲学上曾提出了四个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能够期望什么?
人是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具有综合性,涉及对人的总体理解和把握。
康德对“人”的理解涵盖多重方面,包括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人的规定,以及从价值论的层面把握人的价值内涵。
从实质的层面看,何为人这种提问的方式,仍然主要以认识人为指向。
就此而言,康德对人的理解基本上承继了古希腊以来“认识你自己”、“美德即知识”的传统。
除以上传统外,对与人相关之“学”的理解,还存在另一进路,后者具体体现于中国的儒学。
先秦儒家奠基人孔子的经典《论语》,第一篇是《学而》,其中所讨论的,首先便是“学”。
先秦时代儒家最后一位总结性的人物是荀子,《荀子》第一篇即为《劝学》。
在儒家论域中,“学”既涉及“知人”,也关乎“成人”,从而表现为知人和成人的统一。
这种理解,也体现了中国哲学关于“学”的主流看法。
理解人的以上视域,在中国哲学中首先与人禽之辨相联系。
“人禽之辨”发端于先秦,其内在旨趣在于把握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人禽之辨”同时表现为“人禽之别”。
就其以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为关切之点而言,“人禽之辨”所要解决的,也就是“人是什么”的问题。
对人的以上把握,在中国哲学中往往更概要地被理解为“知人”。
这里的“知人”既涉及人禽之辨,又在引申的意义上关乎人伦关系的把握。
作为人禽之辨引申的“知人”,在中国哲学中常常与“为己之学”联系在一起。
此所谓“为己”,并不是在利益关系上追逐私利,而是以人格上的自我完成、自我充实、自我提升为指向。
这一意义上的“学”,旨在提升自我、完成自我,可以视为成就人自身之学。
与此相对的“为人”,则是为获得他人的赞誉而“学”,其言与行都形之于外,主要做给别人看。
在区分“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的背后,是对成就人自身的关注。
以“为己”、“成己”为目标的“学”,在中国哲学中同时被赋予过程的性质。
在《劝学》中,荀子开宗明义指出:
“学不可以已”,这一看法意味着“学”是不断延续、没有止境的过程。
作为过程,“学”又展开为不同阶段,与之相应的是人成就自身的不同目标。
荀子曾自设问答:
“学恶乎始?
恶乎终?
……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这里,荀子区分了学以成人的两种形态,其一是“士”,其二为“圣人”,学的过程则具体表现为从成就“士”出发,走向成就“圣人”。
作为“学”之初始目标的“士”,是具有相当文化修养和知识积累的社会阶层。
从人的发展看,具有知识积累、文化修养,意味着已经超越了蒙昧或自然的状态,达到了自觉或文明化的存在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谓“文野之别”。
这里的“野”即前文明的状态,“文”则指文明化的形态。
荀子所谓“始乎为士”中的“士”,首先便可以理解为由“野”而“文”的存在形态。
与“始乎为士”相联系的是“终乎为圣”,后者构成了学以成人更根本的目标。
相对于“士”,“圣”的特点在于不仅仅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知识结构,而且已达到道德上的完美性。
正是道德上的完美性,使“圣人”成为“学”最后所指向的目标。
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由“野”而“文”、超越自然状态的成人的过程,离不开“礼”的制约。
自殷周开始,中国文化便非常注重礼。
“礼”涉及多重维度,从基本的方面看,它主要表现为一套文明的规范系统,其作用体现于实质和形式两个层面。
在实质的层面,“礼”的作用体现于对应该做什么与应该如何做的规定。
在形式的层面,礼的作用之一在于对行为的文饰,即所谓“为之节文”,这里的“文”便是形式层面的文饰。
通过依礼而行,人的言行举止、交往的方式便逐渐地取得文明化的形态。
与礼相联系的“学”,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又与“做”、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礼”的引导之下展开的成人过程,同时按照礼的要求去践行。
《论语》开宗明义便指出: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里,“学”和“习”即联系在一起,“习”的涵义之一是习行,即人的践履。
从“习行”的角度看,所谓“学而时习之”,也就是在通过“学”而掌握了一定的道理、知识后,进一步付诸实行,使之在行动中得到确认和深化,由此提升“学”的境界。
“学”的以上含义,在中国哲学中一再得到肯定。
孔子曾指出: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在这里,“好学”首先体现于日用常行、勤于做事的过程。
荀子对“学”的以上意义作了更简要的概述。
在《劝学》中,荀子指出:
“为之,人也;
舍之,禽兽也。
”“为之”,即实际的践行,“舍之”,则是放弃践行。
这里的“为”,也就是以“终乎为圣人”为指向、以礼为引导的践行。
在荀子看来,如果依礼而行(“为之”),便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反之,不按照礼的要求去做(“舍之”),那就落入禽兽之域、走向人的反面。
这里再一次提到了人禽之辨,其涵义则已不仅仅限于从观念的形态去区分人不同于禽兽的特征,而是以是否依礼而行为判断的准则:
唯有切实地按照礼的要求去做,才可视为真正的人。
实际的践行(“为之”)构成了区分人与禽兽的重要之点。
广而言之,在中国文化中,为学和为人、做人和做事往往难以相分。
为学一方面以成人为指向,另一方面又具体地体现于为人过程。
前面提到的道德实践、政治实践、社会交往,都同时表现为具体的为人过程,人的文明修养,也总是体现于为人处事的多样活动。
同样,做人也非仅仅停留于观念、言说的层面,而是与实际地做事联系在一起。
在以上方面,“学”与“做”都无法分离。
“学”既涉及本体,又和工夫相联系
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中,对“学”的理解首先与人禽之辨联系在一起。
从狭义上说,“人禽之辨”主要涉及人与动物之别,在引申的意义上,“人禽之辨”同时关乎对人自身的理解,后者区分本然意义上的人和真正意义上的人。
本然意义上的人,也就是人刚刚来到这一世界时的存在形态,他更多地呈现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对象,还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这里可以看到两重意义的区分:
其一,人与动物之别,亦即狭义上的人禽之辨;
其二,人自身的分别,即本然形态的人与真正意义上的人之分。
从历史上看,中国哲学上不同的人物、学派不仅关注人禽之别,而且对后一意义的区分也有比较自觉的意识。
以先秦而言,孟子提出性善说,后者肯定人一开始即具有善端,这种“善端”为人成就圣人提供了前提或可能。
但同时,孟子又提出“扩而充之”之说,认为“善端”作为萌芽,不同于已经完成了的形态,只有经过扩而充之的过程,人才能够真正成为他所理解的完美存在。
所谓“扩而充之”,也就是扩展、充实,它具体展开为一个人自身努力的过程。
从逻辑上看,这里包含对人自身存在形态的区分:
扩而充之以前的存在形态与扩而充之以后的存在形态。
扩而充之以前的人,还只是本然意义上的人,只有经过扩而充之的过程,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本然意义上的人一方面尚不能归入真正意义上的人,但另一方面又包含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可能。
儒家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便是指每一个人都具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隐含在人的本然形态中,构成了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内在的根据。
后者既区别于现实的形态,也使后天的作用成为必要:
唯有通过这种后天作用,本然所蕴含的可能才会向现实转化。
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成人的以上的过程,又与本体与工夫的互动联系在一起。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工夫”和“本体”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
“本体”的直接涵义即本然之体(originalsubstance),也就是内在于本然之中的最初可能。
对中国哲学而言,正是这种可能,为人的进一步成长提供了内在的根据。
以本体为根据,意味着成就人过程既不表现为外在强加,也非依赖于外在灌输,而是基于个体自身可能而展开的过程。
在中国哲学中,“本体”同时被用以指称人的内在的精神结构、观念世界或意识系统。
人的知、行活动的展开过程,往往与人的内在精神结构以及意识、观念系统相联系。
这种精神结构大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价值层面的观念取向及认知意义上的知识系统。
成人的过程既关乎“成就什么”,也涉及“如何成就”,前者与发展方向、目标选择相联系,后者则关乎达到目标的方式、目标。
精神世界中的价值之维,更多地从发展方向、目标选择(成就什么)等方面制约着成人的过程;
精神世界中的认知之维,则主要从方式、目标(如何成就)等方面,为成人过程提供了内在的引导。
以知识、德性等观念系统为具体内容,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地生成、发展和丰富。
关于这一点,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黄宗羲曾作了言简意赅地概述:
“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
”精神形态意义上的本体并非人心固有,而是形成于知、行工夫的展开过程。
在知行工夫的展开过程中所形成、发展和丰富的本体,反过来又影响、制约着知行活动的进一步展开。
在这一意义上,精神本体具有动态的性质。
与本体相联系的是工夫。
从学以成人的视域看,工夫展开于人从可能走向现实、化当然(理想)为实然(实际的存在形态)的过程之中。
上述视域中的工夫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为观念形态的工夫,即中国哲学所理解的广义之“知”,其二为实践形态的工夫,即中国哲学所理解的“行”,“知”和“行”构成了工夫的两个相关方面。
广义之“学”不仅体现于“知”,也包含“行”(“做”),对于后一意义上的工夫(“行”),中国传统哲学同样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在社会领域中,“是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与“做什么”(从事何种实践活动),往往无法相分。
具体而言,人正是在参与政治实践的具体过程中,逐渐地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的动物”(政治领域中的主体);
在从事法律的实践活动中,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主体(包括成为守法的公民);
在伦理、道德的实践(包括儒学所说的“事亲”、“敬长”等等)过程中,成为伦理领域中的道德主体。
广而言之,正是在社会领域展开的多样践行工夫中,人逐渐成为多样化的社会存在。
“学”既涉及本体,又和工夫相联系。
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学”应有所“本”,这里的“本”既指本然存在中所蕴含的成人可能,也指内在的精神世界、观念系统。
“学”有所“本”则相应地既意味着以人具有的内在可能为学以成人根据,也指“本于”内在的精神世界展开“为学”过程。
在学以成人的过程中,一方面,“学”有所“本”,人的自我成就离不开内在的根据和背景,另一方面,“本”又不断在工夫展开过程中,得到丰富,并且以新的形态进一步引导工夫的展开。
德行和能力制约着人的自我成就
作为本体和工夫的统一,“学”所要成就的,是什么样的人?
从现实的方面看,人当然具有多样的形态、不同的个性。
然而,在多样的存在形态中,又有人之为人的共通方面,其一是德性,其二为能力。
中国古代哲学曾一再提到贤能,所谓“选贤与能”,便将贤和能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里的“贤”主要与德性相联系,“能”则和能力相关。
从学以成人的角度看,德性和能力更多地从目标上,制约着人的自我成就。
上述意义上的德性,首先表现为人在价值取向层面上所具有的内在品格,它关乎成人过程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目标,并从总的价值方向上,展现了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
与德性相关的能力,则主要是表现为人在价值创造意义上的内在的力量。
人不同于动物的重要之点,在于能够改变世界、改变人自身,后者同时表现为价值创造的过程,作为人的内在规定之能力,也就是人在价值创造层面所具有的现实力量。
德性与能力的相互关联所指向的,是健全的人格。
人的能力如果离开了内在的德性,便往往缺乏价值层面的引导,从而容易趋向于工具化与手段化,与之相关的人格,则将由此失去价值方向。
另一方面,人的德性一旦离开了人的能力及其实际的作用过程,则导向抽象化与玄虚化,由此形成的人格,也将缺乏现实的创造力量。
唯有达到德性与能力的统一,“学”所成之人,才能避免片面化。
从学以成人的角度看,这里同时涉及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
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已经开始自觉地关注并讨论这一问题。
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和《美诺》篇中,德性是否可教便已成为一个论题。
在这方面,柏拉图的观点似乎存在某种不一致。
一方面,他不赞同当时智者的看法(认为德性是可教的),并借苏格拉底之口对此提出质疑:
“我不相信美德可以教。
”另一方面,按照“美德即知识”这一观点,则美德又是可教的,柏拉图也认为“如果美德不可教,那就太奇怪了”。
从总的趋向看,柏拉图主要试图由此引出德性的神授说:
美德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靠教育获得,只能通过神的恩赐而来。
较之柏拉图,中国哲学对上述问题具有不同看法。
按中国哲学的理解,不管德性,抑或能力,都既存在不可教或不可学的一面,也具有可教、可学性。
中国哲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以“性”和“习”之说为其前提。
从孔子开始,中国哲学便开始讨论“性”和“习”的关系,孔子对此的基本看法是: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这里所说的“性”,主要是指人的本性以及这种本性所隐含的各种可能。
所谓“性相近”,也就是肯定凡人都具有相近的普遍本性,这种本性同时包含着人成为人的可能性。
作为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形态,“性”是不可教的:
它非形成于“教”或“学”的过程,而是表现为人这种存在所具有的内在规定;
人来到这一世界,就已有这种存在规定。
所谓人禽之辨,从最初的形态看,就在于二者具有相异的存在规定(本然之性)以及与之相应的不同发展可能和根据。
与“性”相对的是“习”,从个体的层面看,“习”的具体内涵在广义上包括知和行,这一意义上的“习”与前面提到的工夫相联系,既可“教”,也可“学”:
无论是“知”,抑或“行”,都具有可以教、可以学的一面。
与德性一样,人的能力既有其形成的内在根据,又离不开后天的工夫过程。
王夫之曾以感知和思维能力的形成为例,对此作了简要的阐述。
在他看来,“目力”(目可视)、“耳力”(耳可听),“心思”(心能思)这一类机能属“天与之”的“性”,它们构成了感知、思维能力形成的根据,作为存在的规定,这种根据不可教、不可学。
“明”(目明)、“聪”(耳聪)、“睿”(智慧)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感知和思维能力,这种能力唯有通过“竭”的努力过程才能形成。
中国哲学对能力形成过程以上理解,同样注意到了内在根据与后天工夫的统一。
以德性和能力的形成为视域,学以成人具体便表现为“性”和“习”的互动,这种互动过程,与前面提到的本体和工夫的互动,具有一致性,二者从不同方面构成了学以成人的相关内容。
当然,如前所述,人的现实形态具有多样性。
然而,从核心的层面看,真实的人格总是包含德性和能力的统一,后者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自由人格的表现形式。
要而言之,一方面,学以成人以德性和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为指向,另一方面,作为德性与能力统一的真实人格又体现于人的多样存在形态之中。
“礼治”的当代意义
2014-09-22作者:
“礼治”的当代意义——姜义华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敬老崇文论坛的讲演
礼治,被混同于旧礼教,在上世纪初倡导新文化而同旧礼教决裂时被一并抛弃,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了。
在谋求建立近代法治国家时,德治、礼治都曾被当成和法治截然不相容的东西,而遭到全盘否定。
其实,这既是对德治与礼治的误解,也是对法治的误解。
要了解礼治的当代意义,必须正确认识礼与礼治的根本性质,礼治与德治、礼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以及礼和礼治在维系当代各伦理性实体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
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礼:
贯串于伦理性实体的制度化责任伦理
西方各国倡导的法治,无论是源于边沁功利主义的英美法系,还是源于《罗马法》的大陆法系,在实践过程中,同强大的宗教力量的现实存在及宗教信仰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入渗透,从来都紧密联系在一起。
尽管英美分析法学派力图分割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但清教徒精神支撑着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与崛起,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为克服这种二元分裂状态,黑格尔在他的名著《法哲学原理》中将理想中的现代国家与现代法治分成形式的法、主观意志的法、实定法三个层面。
形式的法就是指成文法,主观意志的法即道德,实定法能够贯通法律与道德,它指现实的伦理制度,包括婚姻、家庭、市民社会、等级、国家。
在黑格尔那里,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伦理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
黑格尔认为,人们的行为不是在宗教生活中,而是只有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中经受住了考验,才能获得真正的正当性。
黑格尔关于法治内涵的这一理想的三分法,自然是立足于欧洲和德国的社会与历史,但和中国历史上德治、礼治、法治三者必须互相结合确实有某种契合。
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不少法国启蒙思想家曾注意到中国历来融道德、礼仪、法律、风俗习惯于一体的治国特点,注意到中国历来以家庭、社会、国家这三大伦理性实体的伦理制度。
中国很早就已形成家庭、社会自组织、国家三个层次的伦理性实体。
家庭(包括个人的身体和生命在内)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细胞;
广泛存在的社会自组织,包括家族、宗族、亲友、乡里、同窗、同门、同事等,经常互相交错、互相重叠,不仅为家庭的存在提供多方面的保障,而且构成了国家由以成立的基础;
国家以王朝、皇室、宰辅、郡县为代表,它如果不能适应家庭和社会自组织的需求,就会被更迭。
尽管中国传统的伦理实体结构和黑格尔的构想不完全相同,但就每一伦理性实体内部都有其特定的运行规则,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在中国,礼,从根本上说,就是依托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借助于包括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各种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礼仪,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承担起必要的伦理责任,以保障各层面的伦理性实体稳定、有序地运行。
从夏礼、殷礼算起,礼在中国已有四千年历史。
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对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产生深远影响。
其后,礼的形式与内容都代有损益,但本质特征可以说一以贯之。
《荀子·
礼论》说:
“礼起于何也?
曰: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則不能不争;
争則乱,乱則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说的就是礼的缘起。
荀子这里强调的是,礼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人们懂得如何“度量分界”,知道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度。
据此,荀子说:
“礼者,人道之极也。
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
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
”
《礼记·
礼运》从人这一生命体的根本特征论及人们在家庭、社会及国家等伦理性实体中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绝不是随意为之,“必知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礼运》就此具体解释说:
“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何谓人义?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讲信修睦,谓之人利。
争夺相杀,谓之人患。
”礼的作用,就是治人七情,修人十义,成人利,去人患。
《礼运》还指出: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
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
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
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
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凭借礼,深藏于内心之中的美恶方才能够测度,方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加以治理。
于此可知,礼,不仅是国家的自觉行为,更是各种社会自组织的自觉行为,是每个家庭的自觉行为,是伴随着每个人生命成长全过程的自觉行为。
只要国家仍然存在,社会联系、社会自组织仍然存在,家庭仍然存在,人的身体与生命仍然存在,礼就不应缺位。
《礼运》因此告诫说:
“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先去其礼。
”《礼记·
曲礼》中说: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
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这都非耸人听闻之词。
中国传统责任伦理在百年三大挑战的浴火中重生
中国传统礼治、传统责任伦理,近百年来接受了前所未有的三大挑战,在浴火中经受了涅槃与重生。
上个世纪前50年,中国经历中长时间的战争与革命的洗礼;
随后,在1950-1970年代,中国又经历了一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或全方位政治挂帅的日子。
《论语·
为政》中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当然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传统价值、道德、礼仪、信仰及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摧毁了长期有效地维系着这一切的各种传统社会自组织,进行了空前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使政治权力得以首次直入到社会最底层。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实际上是以高度强化与扩大了的社会二元化或裂分化为前提。
道之以政,是以政治信念、政治信仰、政治信任为其凝聚民众、动员民众的主要手段,而其一旦在实践中被证实背离生活实际,就必然会导致严重的信念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从而丧失其凝聚力、动员力。
齐之以刑,依靠的是政治高压、不讲情面的持续斗争和对受压方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这虽能在短时间内奏效,但必然会导致“民免而无耻”,便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反而会一再激化。
伴随近代工业化、市场化经济的勃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国家转向集中全力发展经济,一段时间实际工作中由GDP挂帅,形成了“道之以利,齐之以律,民多欲而上下交征”的新局面,不免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理想、道德、信仰、礼仪、责任、高尚的情操,在这一过程中被许多人抛到一边。
物质欲望被激发、被释放、被纵容,而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结果,自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泛滥起来,并将越来越多的人席卷进去。
众多得利者仍经常愤愤不平,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