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罪与入罪宽严相济视阈下罪刑圈的标准设定的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出罪与入罪宽严相济视阈下罪刑圈的标准设定的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出罪与入罪宽严相济视阈下罪刑圈的标准设定的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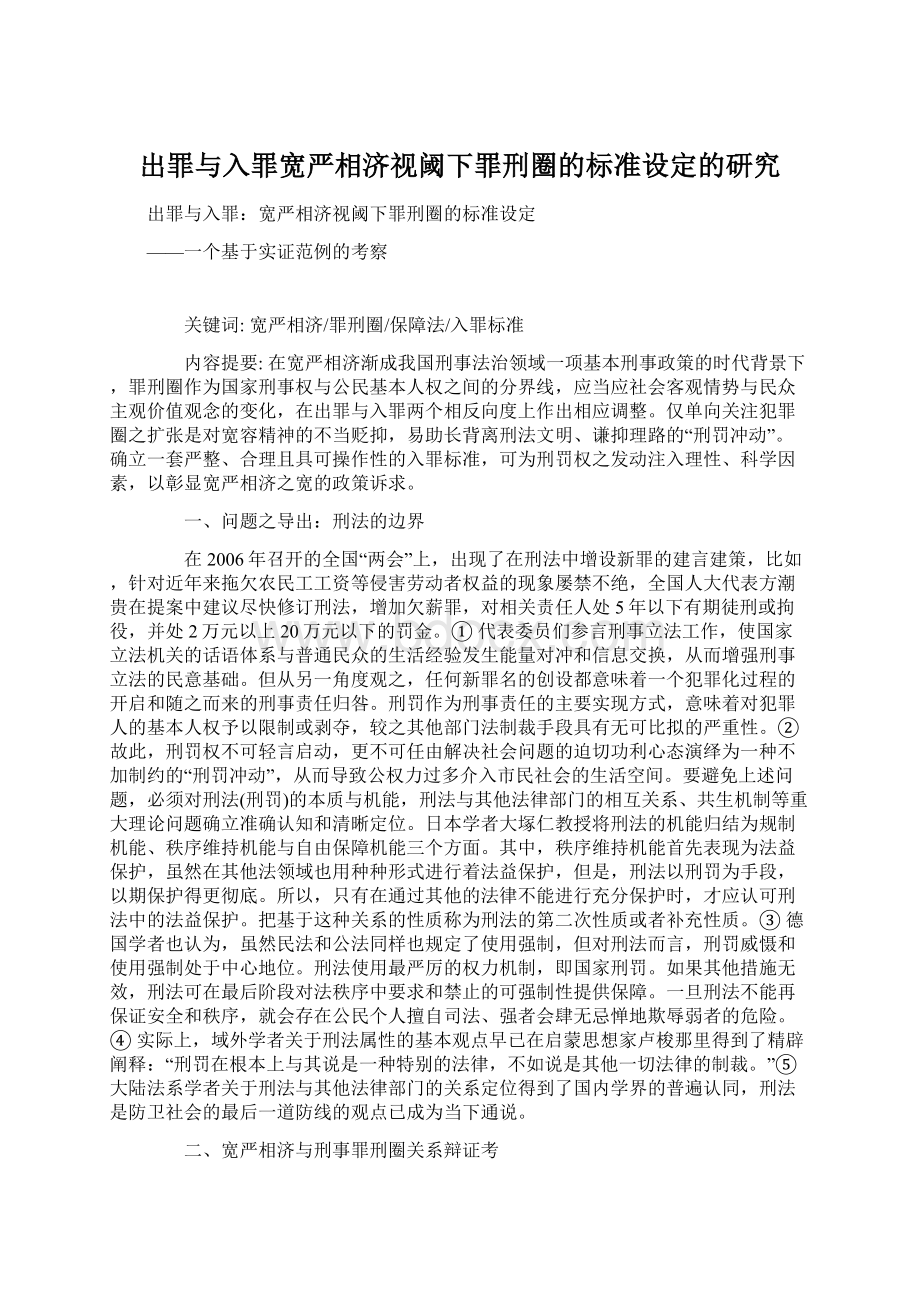
确立一套严整、合理且具可操作性的入罪标准,可为刑罚权之发动注入理性、科学因素,以彰显宽严相济之宽的政策诉求。
一、问题之导出:
刑法的边界
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出现了在刑法中增设新罪的建言建策,比如,针对近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屡禁不绝,全国人大代表方潮贵在提案中建议尽快修订刑法,增加欠薪罪,对相关责任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金。
①代表委员们参言刑事立法工作,使国家立法机关的话语体系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发生能量对冲和信息交换,从而增强刑事立法的民意基础。
但从另一角度观之,任何新罪名的创设都意味着一个犯罪化过程的开启和随之而来的刑事责任归咎。
刑罚作为刑事责任的主要实现方式,意味着对犯罪人的基本人权予以限制或剥夺,较之其他部门法制裁手段具有无可比拟的严重性。
②故此,刑罚权不可轻言启动,更不可任由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功利心态演绎为一种不加制约的“刑罚冲动”,从而导致公权力过多介入市民社会的生活空间。
要避免上述问题,必须对刑法(刑罚)的本质与机能,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相互关系、共生机制等重大理论问题确立准确认知和清晰定位。
日本学者大塚仁教授将刑法的机能归结为规制机能、秩序维持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三个方面。
其中,秩序维持机能首先表现为法益保护,虽然在其他法领域也用种种形式进行着法益保护,但是,刑法以刑罚为手段,以期保护得更彻底。
所以,只有在通过其他的法律不能进行充分保护时,才应认可刑法中的法益保护。
把基于这种关系的性质称为刑法的第二次性质或者补充性质。
③德国学者也认为,虽然民法和公法同样也规定了使用强制,但对刑法而言,刑罚威慑和使用强制处于中心地位。
刑法使用最严厉的权力机制,即国家刑罚。
如果其他措施无效,刑法可在最后阶段对法秩序中要求和禁止的可强制性提供保障。
一旦刑法不能再保证安全和秩序,就会存在公民个人擅自司法、强者会肆无忌惮地欺辱弱者的危险。
④实际上,域外学者关于刑法属性的基本观点早已在启蒙思想家卢梭那里得到了精辟阐释:
“刑罚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的法律,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
”⑤大陆法系学者关于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定位得到了国内学界的普遍认同,刑法是防卫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观点已成为当下通说。
二、宽严相济与刑事罪刑圈关系辩证考
(一)和谐社会语境中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和谐并非自然达成之状态,矛盾的解决需要一系列理性的制度、规则所形成的解决纠纷机制,对利益群体的行为进行规范,为利益主体的诉求提供表达渠道,并对业已出现的利益冲突进行疏导。
显然,和谐社会所依赖的制度设计乃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诸多界面,那么,如何从众多的制度资源中选择并构筑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制度架构呢?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回溯世界法治源流,自人类跨入阶级社会以来,法律就始终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法治状况的程度也直接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好坏。
和谐社会作为经由理性制度调控的理想社会形态,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石之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已内化于和谐社会的本体属性之中。
以部门法为视角,法治由宪政、刑事法治、行政法治、民事法治等多维界面构成,各部门法规范均以相应的违法行为为专属统辖对象,规制对象的交合、重叠属例外情形。
在不同性态的违法行为群落中,犯罪乃藐视社会秩序、与国民基本人权相对立之最极端失范行为。
近代社会学、犯罪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犯罪是社会有机体的必然伴生现象,只要被控制在合理限度之内,就不会妨碍社会的正常发展。
⑥在部门法的视阈下,刑事法治的规制对象直接指向以社会整体为侵害对象的犯罪,并具有制裁对象的最广泛性和惩治措施的最严厉性两大基本特征,因而与社会秩序之维系关涉重大,被喻为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闸门。
刑事法治具有多种模式,选择不同的刑事法治,意味着刑事资源和刑事元素的组合形态均有疏别,进而影响刑事法治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效能发挥程度。
由于刑事政策是刑事法治的灵魂与导向,决定着刑事法治内部诸要素的结构和功能,所以刑事法治模式的选择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问题。
因此,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关联密切。
那么,在和谐社会的时代语境中,究竟需要何种具体的刑事政策形态呢?
作为对这一重大命题的回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运而生。
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何谓宽严相济?
国内学者的阐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笔者在合理借鉴的基础上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界定为:
国家基于特定刑事安全形势的要求,以符合法治要求的方式,从宽与严两个向度上合理运用刑事权,通过实体刑法与程序刑法(包括行刑法)的制定、修改、实施,以应对复杂的犯罪态势和犯罪人类型,从而达到防卫社会、保障人权、增进社会和谐的刑事策略系统。
这一界定以刑事一体化为方法论基础,关注从宽严相济与刑事法相关联的视角揭示其内涵。
众所周知,基本型与具体型作为刑事政策的一种分类,其基准在于刑事政策关涉刑事法治活动环节之多寡,政策功能全面与否,以及政策目标宽泛与否。
基本刑事政策居于较高位阶,贯穿刑事法治各个环节,即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行刑等。
同时,政策目标往往兼及犯罪防控、秩序维持、人权保障等,并具有复合的政策功能。
在当下理论界,关于宽严相济的政策定位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多数学者仍然恪守在刑事司法政策的向度内研究宽严相济;
另一些学者虽然在学术姿态上没有突破前述立场,但实际研究的域度已然突破司法环节,延伸至刑事立法层面;
还有一些学者旗帜鲜明的提出将宽严相济定位于基本刑事政策加以研究。
⑦笔者赞同第三种学术立场,因为,我们对任何新事物的认知都是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对宽严相济的政策定位也必然符合这一规律,不能因为决策层关于宽严相济的政策定位就故步自封,停止在应然层面对相关理论问题的进一步追问。
将宽严相济定位于基本刑事政策更趋合理:
首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事实上已被扬弃,严打政策在倡扬人权保障的和谐社会语境中亦日渐式微,宽严相济作为对前者的理性反思和承继超越,如果自囿于司法政策的“一亩三分地”,将导致在刑事司法之外的刑事立法、刑事执行等重要法治界域出现刑事政策缺位的尴尬现象,这种局面无疑会折损刑事法治的建设成效,因而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刑事司法与刑事立法相比,更显“柔性”色彩。
作为将刑事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个案的刑事活动,刑事司法环节存在着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以供司法人员便宜行使,故宽与严均有发挥之空间。
但是,刑事立法作为刑事司法生成规范依据的环节,并非没有宽与严的用武之地,比如,哪些刑事犯罪宜根据客观情势非罪化、非刑化,哪些非罪行为又应当完成入罪化、刑事化,同样彰显着宽抑或严的政策态度。
由此,在刑事立法、刑事执行等环节同样需要刑事政策之辐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语义上的周延性折射出其内在价值域度的完整性,完全可以胜任对刑事法治诸环节、诸流程的政策导向与价值指引使命。
(二)宽严相济视阈下罪刑圈运动之合理样态
在宽严相济政策视阈下,立法者运用刑事立法权确定罪刑圈的活动应当是双向的,既包括正向的入罪(向外扩张),即犯罪化、刑罚化,亦涵盖反向的出罪(向内紧缩),即非罪化、非刑化。
所谓扩张,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1)将确实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的新型危害行为纳入犯罪圈,并设置与其匹配的法定刑;
(2)当一般危害行为因主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具备了应受刑罚处罚性时,将其纳入犯罪圈,并设置与其匹配的法定刑;
(3)当已然之罪的社会危害性显著增长且已不能通过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断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时,通过修法改变其法定刑,具体包括提高原有法定刑幅度的下限、上限或者同时提高上下限。
至于罪刑圈向外扩张的立法技术,则分为直接设立新的罪名或将现有罪名的构成要件予以扩张两种方式,前者如《刑法修正案(三)》设立的资助恐怖活动罪,后者如《刑法修正案(六)》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由原来的四种扩及七种,但仍维持洗钱罪罪名不变。
而所谓紧缩,主要涵盖两种情形:
(1)对社会危害性已经发生质变,减低到应受刑罚处罚性之下的已然之罪,立法机关应及时进行除罪化处理;
(2)对于社会危害性显著降低但尚具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已然犯罪,可通过修法以降低其法定刑下限、上限或同时降低上、下限。
罪刑圈的适时扩张与紧缩,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环节的渗透,其中,扩张体现了严的选择,紧缩彰显宽的趋向。
新刑法颁行以来,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八个特别刑法,所涉及的犯罪圈变动均属于正向扩张。
近年来罪刑圈的变动仅反映出宽严相济政策之严的纬度,政策之宽表现阙如,而包括各级人大、委员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建言建策也无一例外是关于刑事入罪的。
笔者认为,罪刑圈因应社会情势作适宜调整,是确保刑事立法时代品格的必然选择,但这一变动宜呈现扩张与紧缩并立的双向性,方能反映社会生活的全貌,也有利于全面释放宽严相济的政策能量。
在犯罪圈的扩张问题上,应避免不理性的“刑罚冲动”,谨守刑法是社会防卫的底限这一基本原则精神。
三、刑事入罪具体标准之确立
显然,刑法作为社会防卫的底限这一基本原则精神过于笼统抽象,对于解决具体层面的问题助益甚微。
笔者尝试提出四项环环相扣、逐层递进的具体标准,任一危害行为只有同时经过这四项标准的评判,方可证成入罪之正当性,即:
(1)该危害行为是否经由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部门调整。
就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而言,只有在某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不能为其他部门法律所有效规制,并且如果不用刑法调整,其他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法律制度就可能崩溃的情况下,国家才具备发动刑罚权的正当性;
(2)其他法律部门调整该危害行为的方法是否确当;
(3)在社会政策方面是否存在治理该行为的替代性选择;
(4)该危害行为入罪的现实可操作性。
下文中,笔者拟以当前各界热议的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为切入点,对上述具体标准进行全面深入的解析,以示范其逻辑关系和运用规则。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我国新生儿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6.9比100,远高于国际认同的最高警戒线——107比100,而实际上我国局部地区的性别比甚至接近150比100,这已使我国成为全球人口性别比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
”⑧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若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将造成婚姻挤压,卖淫嫖娼及性犯罪增多,同性恋及性传播疾病泛滥,女性生命健康权益严重受损等严重后果,长此以往,势必危及人类种群平衡与社会和谐发展。
鉴于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与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是导致新生儿性别比失调的主要人为原因,包括刑法学家、计划生育专家在内的社会各界均有人士主张将上述行为犯罪化,借助刑罚的最高威慑性遏制人口性别结构日趋失衡的态势。
至于刑事化的具体方案则略有疏别:
有的主张设立新罪,如非法堕胎罪;
有的建议对现有罪名(如非法行医罪)的构成要件予以扩充,以统摄上述行为。
⑨民间舆情在决策层获得了一定的回应,2005年上半年,针对近年来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的问题,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说,要通过修改刑法来遏制人为因素造成的新生儿出生比例持续失衡,即通过刑法打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
⑩对此,笔者拟运用前文提出的评判入罪的具体标准对相关建言的合理性、科学性进行全面论证:
(一)标准一:
是否经由其他法律部门调整
就现代法律体系而言,刑法属于对人的行为进行第二次调整的法律,(11)就法律制裁措施的严厉性程度而言,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