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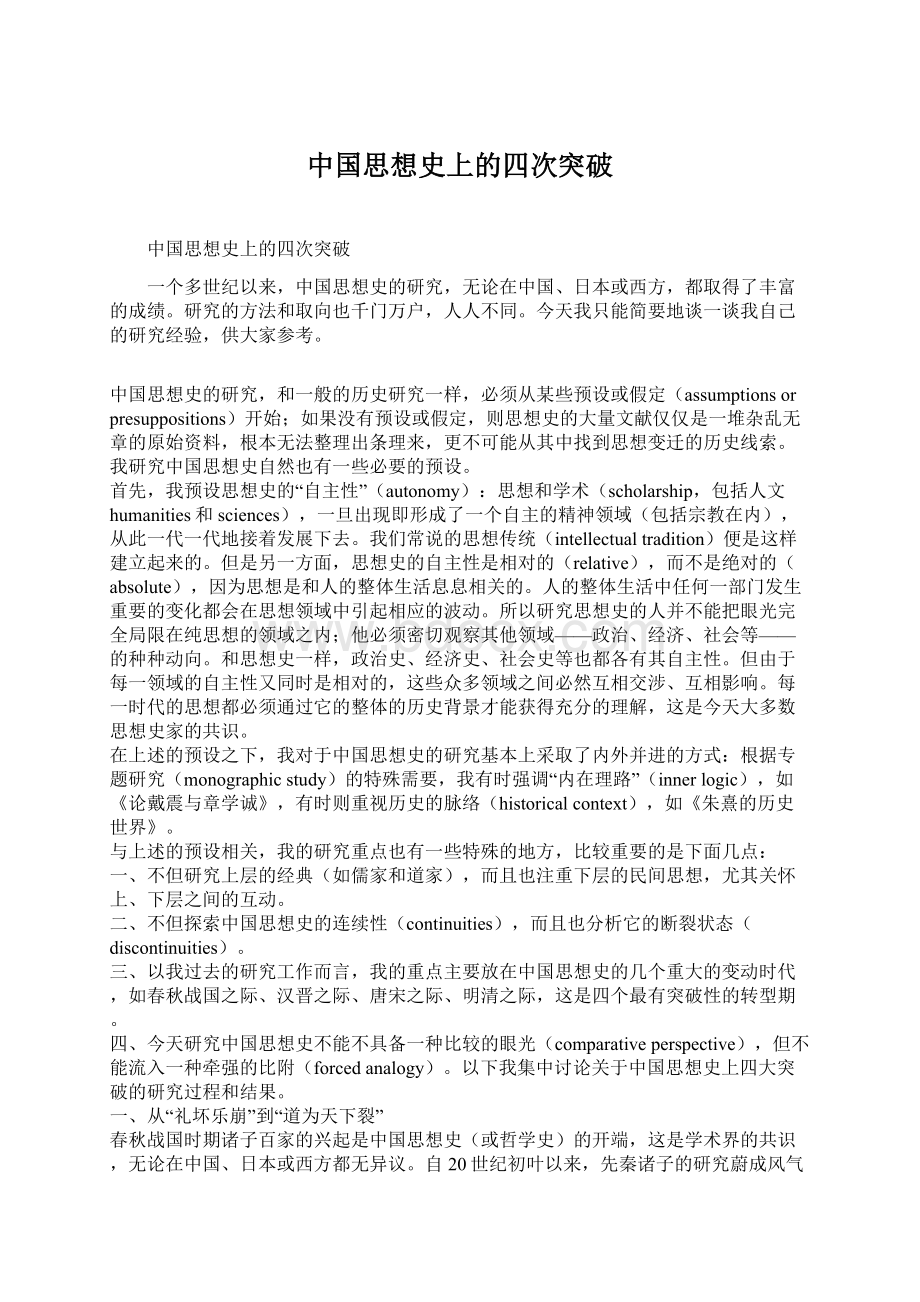
所以研究思想史的人并不能把眼光完全局限在纯思想的领域之内;
他必须密切观察其他领域——政治、经济、社会等——的种种动向。
和思想史一样,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也都各有其自主性。
但由于每一领域的自主性又同时是相对的,这些众多领域之间必然互相交涉、互相影响。
每一时代的思想都必须通过它的整体的历史背景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这是今天大多数思想史家的共识。
在上述的预设之下,我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基本上采取了内外并进的方式:
根据专题研究(monographicstudy)的特殊需要,我有时强调“内在理路”(innerlogic),如《论戴震与章学诚》,有时则重视历史的脉络(historicalcontext),如《朱熹的历史世界》。
与上述的预设相关,我的研究重点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较重要的是下面几点:
一、不但研究上层的经典(如儒家和道家),而且也注重下层的民间思想,尤其关怀上、下层之间的互动。
二、不但探索中国思想史的连续性(continuities),而且也分析它的断裂状态(discontinuities)。
三、以我过去的研究工作而言,我的重点主要放在中国思想史的几个重大的变动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这是四个最有突破性的转型期。
四、今天研究中国思想史不能不具备一种比较的眼光(comparativeperspective),但不能流入一种牵强的比附(forcedanalogy)。
以下我集中讨论关于中国思想史上四大突破的研究过程和结果。
一、从“礼坏乐崩”到“道为天下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是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开端,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无论在中国、日本或西方都无异议。
自20世纪初叶以来,先秦诸子的研究蔚成风气,取得了丰富的成绩。
1970年代至今,由于地下简帛的大批出现,如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之类,这一领域更是活跃异常。
这一领域虽然日新月异,论文与专书层出不穷,但从文化史的整体(holistic)观点说,其中还有开拓的余地。
这是因为大多数专家将注意力集中在比较具体的问题方面,如个别学说的整理、文献的考证与断代,以及新发现的文本的诠释之类。
至于诸子百家的兴起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现象究竟应该怎样理解?
它和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变动又是怎样联成一体的?
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重大问题还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
我研究这一段思想史主要是希望对这些大问题试作探求。
站在史学的立场上,我自然不能凭空立说,而必须以坚实的证据为基础。
因此除了传世已久的古文献之外,我也尽量参考新发现的简帛和现代专家的重要论著。
但在掌握了中国基本资料的条件下,我更进一步把中国思想史的起源和其他几个同时代的古文明作一简略的比较,因为同一历史现象恰好也发生在它们的转变过程之中。
通过这一比较,中国文化的特色便更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我早年(1947-1949)读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的著作,对先秦诸子发生很大的兴趣,1950年后从钱穆先生问学,在他指导下读诸子的书,才渐渐入门。
钱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是一部现代经典,对我的启发尤其深远。
所以1954年曾写过一篇长文《〈先秦诸子系年〉与〈十批判书〉互校记》,是关于校勘和考证的作品。
1955年到美国以后我的研究领域转到汉代,便没有再继续下去。
1977年我接受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上古史》计划的邀约,写《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章,于是重新开始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与社会的大变动。
由于题目的范围很广阔,我必须从整体的观点,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
我的主题是“士”的起源及其在春秋、战国几百年间的流变,但顺理成章地延伸到思想的领域。
为什么说是“顺理成章”呢?
在清理了“士”在春秋与战国之际的新发展和他们的文化渊源之后,诸子百家的历史背景已朗然在目:
他们是“士”阶层中的“创造少数”(creativeminority),所以才能应运而起,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
我在这篇专论中特别设立“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breakthrough)一节,初步讨论了诸子百家出现的问题。
“哲学的突破”的概念是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Parsons)提出的,他根据韦伯(MaxWeber)对于古代四大文明——希腊、希伯菜、印度和中国——的比较研究,指出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这四大文明恰好都经历了一场精神觉醒的运动,思想家(或哲学家)开始以个人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
“哲学的突破”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情形,所以我借用了它。
更重要的是,它也很准确地点出了诸子百家兴起的性质和历史意义。
但是必须说明:
我之所以接受“突破”的说法同时也是因为当时中国思想家中已出现了相似的意识。
《庄子·
天下》篇是公认的关于综论诸子兴起的一篇文献,其中有一段说:
天下大乱,圣资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后世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这是描述古代统一的“道术”整体因“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而分裂成“百家”。
这个深刻的观察是从庄子本人的一则寓言中得到灵感的。
《应帝王》说到“浑沌”凿“七窍”,结果是“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七窍”便是《天下》篇的“耳目鼻口”,“道术裂”和“浑沌死”之间的关系显然可见。
“道术为天下裂”的论断在汉代已被普遍接受。
《淮南子·
俶真训》说: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
”这里的“列道”即是“裂道”;
而“儒、墨”则是泛指诸子百家,因儒、墨两家最早出现,所以用为代表,《盐铁论》中“儒墨”一词也是同一用法。
另一更重要的例证是刘向《七略》(收入《汉书·
艺文志》)。
《七略》以《六艺略》为首,继之以《诸子略》。
前者是“道术”未裂以前的局面,“政”与“教”是合二为一的,所以也称为“王官之学”,后者则是天下大乱之后,政府已守不住六经之“教”,道术散入“士”阶层之手,因而有诸子之学的出现。
所以他有“诸子出于王官”的论断,又明说:
“王道既微……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这和《天下》篇所谓“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说法是一致的。
清代章学诚熟读《天下》篇和《七略》,他研究“六经”如何演变成“诸子”,更进一步指出:
“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
”(《文史通义·
史释》)所谓“官师治教分”是说东周以下,王官不再能垄断学术,“以吏为师”的老传统已断裂了。
从此学术思想便落在“私门”之手,因而出现了“私门之著述”。
诸子时代便是这样开始的。
章学诚的论述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域中发生了重大影响,许多思想史家或哲学史家都以它为起点。
总之,无论从比较文明史的角度或中国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上作观察,“突破”都最能刻画出诸子兴起的基本性质,并揭示出其历史意义。
但“哲学的突破”在中国而言又有它的文化特色,和希腊、希伯莱、印度大不相同。
西方学者比较四大文明的“突破”,有人说中国“最不激烈”(leastradical),也有人说“最为保守”(mostconservative)。
这些“旁观者清”的观察很有道理,但必须对“突破”的历史过程和实际内涵进行深入的考察,才能理解其何以如此。
我在上述论文《哲学的突破》一节中,由于篇幅的限制,仅仅提到“突破”的背景是三代的礼乐传统,无法详论。
春秋、战国之际是所谓“礼坏乐崩”的时代,两周的礼乐秩序进入逐步解体的阶段。
维系着这一秩序的精神资源则来自诗、书、礼、乐,即后来所说的“王官之学”。
“突破”后的思想家不但各自“裂道而议”,凿开“王官之学”的“浑沌”,而且对礼乐秩序本身也进行深层的反思,如孔子以“仁”来重新界定“礼”的意义,便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论语·
八佾》:
“人而不仁,如礼何?
”)
1990年代晚期,我又更全面地研究了“突破”的历史,用英文写成一篇长文,题目是《天人之际——试论中国思想的起源》。
正文虽早已写成,但注释部分因阻于朱熹的研究而未及整理。
我后来只发表了一篇概要,即“BetweentheHeavenlyandtheHuman”,经过这第二次的深入探索,我才感觉真正把“突破”和礼乐秩序之间的关联弄清楚了。
同时我也更确定地理解到中国思想的基础是在“突破”时期奠定的。
这篇《天人之际》中牵涉到许多复杂的问题,这里不能深谈。
让我简单说一个中心论点。
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不少合理的成分,经过“突破”的洗礼之后仍然显出其经久的价值。
但其中又包含了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却成为“突破”的关键。
我指的是“巫”的传统。
古代王权的统治常藉助于“天”的力量,所以流行“天道”、“天命”等观念。
谁才知道“天道”、“天命”呢?
自然是那些能在天与人之间作沟通的专家,古书上有“史”、“卜”、“祝”、“瞽”等等称号,都是天、人或神、人之间的媒介。
如果仔细分析,他们的功能也许各有不同,但为了方便起见,我一概称之为“巫。
我们稍稍研究一下古代的“礼”(包括“乐”在内),便可发现“巫”在其中扮演着中心的角色;
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与天上的神交通,甚至可以使神“降”在他们的身上。
《左传》上常见“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之类的话。
这些说法都是在“巫”的精神传统下逐渐发展出来的,研究萨满教的专家(如MirceaEliade)便称之为“礼的神圣范式”(divinemodelsofrituals)。
可见在三代礼乐秩序中,巫的影响之大,因为他们是“天道”的垄断者,也只有他们才能知道“天”的意思。
现代发现的大批商、周卜辞便是最确凿的证据。
但巫在中国的起源极早,远在三代之前。
考古学上的良渚文化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相当于传说中五帝时代的中期。
良渚文化发现带有墓葬的祭坛,和以玉琮为中心的礼器。
玉琮是专为祭天用的,设计的样子是天人交流,都是在祭坛左右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
这些墓与一般的集体墓葬隔开,表示墓主具有特殊的身份。
考古学家断定墓主是“巫师”,拥有神权,甚至军权(因为除“琮”以外,墓中还有“钺”)。
这样看来,三代的礼乐秩序可能即源于五帝时代,巫则是中心人物。
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便是针对着这一源远流长的精神传统展开他们的“哲学突破”的。
诸子不论属于哪一派,都不承认“巫”有独霸天人交流或神人交流的权威。
在《庄子·
应帝王》中,有一则寓言,描写道家大师壶子和神巫季咸之间的斗法,结果前者胜而后者败。
这可以看作当时诸子和巫在思想上作斗争的暗示。
大体上说,他们有两个共同点:
第一是将“道”——一种精神实体——代替了巫所信奉的“神”;
第二是用“心”的神明变化代替了“巫”沟通天人或神人的神秘功能。
巫为了迎“神”,必须先将自己的身体洗得十分干净,以便“神”在巫的身体上暂住(如《楚辞·
云中君》所描写)。
现在诸子则说人必须把“心”洗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