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渊源及演变文档格式.doc
《略论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渊源及演变文档格式.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略论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渊源及演变文档格式.doc(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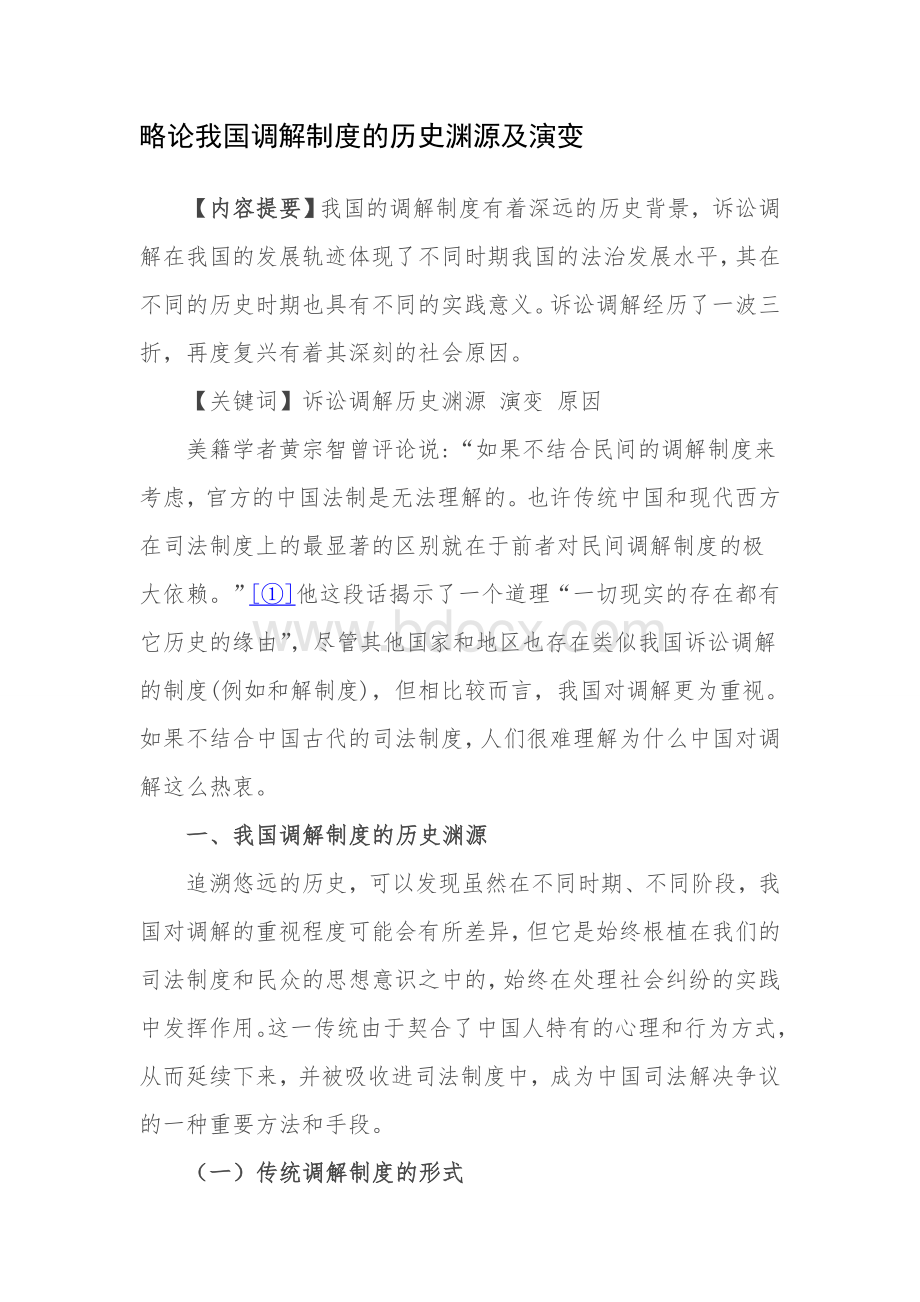
这一传统由于契合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从而延续下来,并被吸收进司法制度中,成为中国司法解决争议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
(一)传统调解制度的形式
在古代统治者看来,如果不能使老百姓不打官司,不如劝他们平息诉讼,想办法进行调解。
所以,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官府,调解息讼均被视为基本原则,并形成了一套相辅相成的调解机制。
依调解主持者的身份区别,可把我国的传统调解分为民间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和州县官府调解四种形式。
民间自行调解是指纠纷双方当事人各自邀请乡邻、亲友、长辈或在当地民众中有威望者出面说和、劝导、调停,从而消除纷争的活动。
民事纠纷因多发生在邻里亲友之间,所以由民间有威望的人或亲友中公道正直之人出面调解,具有很好的社会效果。
它既没有固定的程序,也没有差役的勒索,方法简单灵活,因而在民间很受欢迎。
宗族调解是指宗族成员间发生纠纷时,族长依照家法族规进行的调解。
我国古代多数同姓族人聚族而居在同一村落里。
这种聚居的宗族推举辈长年高且有威望者作为族长,并制定或约定俗成一些规范作为族人的行为准则。
宗族族长一方面负有统辖管理宗族之权,另一方面对国家承担维持族内秩序的义务。
早在周代,钟鼎铭文中就有“宗子”调解纠纷的案例记载。
清朝《大清律例》规定,轻微罪犯、妇女罪犯可以送交宗族,责成宗族管束训诫,至于民事纠纷,特别是婚姻、继承争端也大多批转宗族处理,由全族进行公议,大力倡导封建宗族及乡绅的“自治”权。
与民间自行调解、宗族调解存在的同时,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乡治调解,它是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调解。
春秋战国之际,设有专门调解复仇案件的官员,称为“调人”,调人专司“谐合”而不管审判。
唐朝乡里的诉讼,要先由里正、村正来进行调解。
明朝的乡治调解更具特色,明初在各乡设有“申明亭”,由本乡推举公直老人三五名,报官备案。
本乡有纠纷小事,由老人主持,在申明亭调解。
清朝的保甲组织同样负有调解纠纷的职责。
在清代档案中记载道光年间,宝坻县村民季庄、季云山因土地买卖告状,官府批乡保查明究竟,乡保马得山事后禀复:
经官府批准查明纠纷原因,因为两人同属一族,特把两方邀集一处,最终促使双方调解解决。
州县官府调解又称司法调解或诉讼内调解。
我国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二为一,大量民事案件集中于州县衙门。
他们以诉讼案件的多少作为评定官员政绩好坏的标准之一,这就驱使州县官吏对民事纠纷甚至一些刑事案件,运用多种方法予以调解息讼,想尽一切办法达到无讼的状态。
如西汉人韩延寿任某地太守时,“有兄弟因田争讼”,他倍感是自己“不能宣明教化”,于是称病不办公,闭门思过,致使当事人大为感动,互相让出土地,至死不争。
[②]
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源远流长,久盛不衰,为什么调解制度会在我国古代长期存在,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足以说明它的存在适应了特定的需要,有着深层次的的历史原因和厚重的社会基础。
(二)传统调解制度的存在根源
1、“无讼”论是调解制度的思想基础
孔子在作鲁国司寇的时候,有父子俩诉讼,孔子拘留了他们,三个月不予审理,父亲请求撤销诉讼,孔子就把他们释放了。
据说,孔子将这对父子放出后,父子二人抱在一起哭,并发誓“终身不讼”。
这个让现代的法律人听起来似乎“哭笑不得”的故事却真实的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和合思想”和“无讼”的法律文化。
秩序和谐是古代中国所有的统治者都极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无讼”的追求就是对秩序的追求,这是“天人合一”的和合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孔子将诉讼的父子拘留三个月不审理案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2、宗族宗法的存在是调解制度的社会基础
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族内组织,传统的宗法伦理观念则是维系宗族的精神力量。
秦朝吸收了法家的思想,用强制手段把人们束缚在狭小的土地上,实行“邻里连坐”,如果邻里之间互相都有血缘关系,从内部管理上讲,便于及早发现问题预防犯罪,这从客观上加强了宗族的凝聚力。
到了汉朝,分封很多刘姓后代为诸侯王,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宗族网络,以宗法关系为主干,由一个个宗族构成社会网络,宗族族长往往兼具国家大小不等的官职,从而很自然地就把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与自身所拥有的伦理权力结合起来。
按照封建大家族的观念,一族之内“和为贵”,一个个家族都和睦了,那么整个社会也就安定了,所以说在血族亲情的掩盖下,以和谐为目的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自然受到欢迎。
可以说,古代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是传统中国的自然农业经济与宗族结构以及现实政治的需求相契合的结果。
3、当事人诉权的限制是调解息争的制度条件
从秦朝到明清,我国历朝都有对当事人诉权条件的法律限制。
首先诉讼主体上有限制,汉代首定“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唐朝规定,除了法定的几种重罪外,告祖父母、父母者,处以绞刑。
古代法律对卑幼诉权的限制,使得小辈一旦与长者产生摩擦或纠纷,只能寻求族长或亲友的调解进行救济。
另外,我国古代还有民事案件受理时间的限制,官府只在指定的日、月受理案件,农忙季节不受理民事案件,即便在允许起诉的月份内,民众也不是每天都可起诉,有定期的“放告日”允许告状。
封建官府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诉讼的进行必影响农业生产,讼累的延续,还有可能造成家破人亡,这不仅关系到国家赋税的收入,而且还可能会增加流民大军。
这些不安定因素极易破坏其统治秩序,所以就长达几个月时间不受理民事纠纷,但对发生了纠纷的当事人来说,要想尽快从纠纷中解脱出来,也只能借助于调解来实现,从制度上促使当事人尽快和解。
4、当事人逃避讼累是调解制度得以发展的直接根源
古代官府对有讼诉到公堂的人,第一反应便是把涉讼各方统统羁押待质。
在审讯之时,不论原告、被告、证人都要跪听发落,稍有言辞不慎,便会招致一顿棍棒之灾。
除刑讯之累外,诉讼费用的负担也是人们选择调解息讼的直接而又现实的原因。
所谓“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反映了人们为讼费所累不得已放弃诉权的无奈。
清代诉讼,打官司有挂号费、递状子有传呈费、领传票有出票费、想排期开庭有开堂费、开庭时交坐堂费、结案时有衙门费,名目繁多的收费使当事人官司终结之日,也是家资耗尽之时,所以多选择调解息诉。
[③]
二、诉讼调解的U型演变及现实价值分析
诉讼调解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一定层面上体现了我国法治发展的轨迹,新中国成立后,诉讼调解制度经历了从着重调解到重判轻调,现在又发展为着重调解,由兴到衰,由衰到复兴,呈现的是“U”型演变过程。
(一)诉讼调解制度的演变
诉讼调解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确立。
这一方式最主要的特点是解决纠纷的裁判者直接深入到纷争现场,了解纠纷形成的过程,调查收集有关纠纷的证据,并在此过程中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说服教育,最终化解纠纷(审判与调解相结合)。
其中“着重调解”被视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最基本特点之一,也是这种审判方式的主要标志。
这种审判方式由于和当时的社会情境、政治要求相适应,因此成为一种模范的司法行为模式。
这种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进一步延续下来,并在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中得到体现。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6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
调解无效的,应当及时判决。
”该条规定的“应当着重调解”就集中反映了《民事诉讼法(试行)》对传统审判方式的继承。
在以后实施的几年中,诉讼调解依然被作为解决民事争议的重要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社会改革的扩展和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作为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国推广开来。
同时改革开放后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导致民事案件大量增加,法院面临很大审判压力,依照原有的着重调解的审判方式审理案件,无法及时解决积案问题。
此外,受外国民事审判制度和严格执法要求的影响,人们在意识上比较强调民事判决的作用,诉讼调解的运用逐渐被弱化。
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举证责任制度的推行又为弱化诉讼调解、强化裁判提供了制度支持。
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过去重视诉讼调解的审判方式被视为传统审判方式的一个特点,因此,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要改革传统的审判方式,也就自然会淡化诉讼调解。
1988年召开的全国第14次审判工作会议正式启动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行驶的“列车”。
在这次会议上,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中心工作”,主要包括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调整调解与判决的相互关系等等事项。
[④]所谓“调整诉讼调解与判决的相互关系”,其实质就是弱化诉讼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强调的是“该调则调,当判则判”。
这在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在法条表述上不再使用“着重”二字,我们认为是改为“调判并重”,而在实践中,由于对法治的恣意追求,人们开始对法院在法治社会中所担负的职责进行反思,把关注的焦点聚集于程序公正,调解以其反程序性而受到人们的冷落,曾一度形成了“重判轻调”的局面。
尤其是随着法官整体素质、法律技能的提高,以及人们对诉讼效率和公正的恣意追求,调解被看作是“和稀泥”,法官一改过去热衷调解为不屑于调解,法院的案件调解率也急转直下。
就全国来看,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从1989年的76。
7%下降到2001年的30。
78%。
[⑤]诉讼调解呈逐年萎缩的发展态势。
进入21世纪后,调解又被赋予新的使命,再一次彰显了在诉讼中的位置,诉讼调解渐渐热起来,形成了明显的回归态势。
这是因为在经过了对理想法治狂热的追求以后,人们开始对这种追求进行冷静地思考,尤其是各种非法治因素对法院工作的困扰,如上访问题、执行难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审判资源“不足”问题等,法院承载了太多的社会职能和期望,使人们不得不再一次重新考虑诉讼调解—---这一种传统的解决纠纷的瑰宝。
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重新提出了“着重调解”的原则。
[⑥]200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将婚姻家庭、相邻关系等6类民事案件确定为调解前置案件,[⑦]许多地方法院专门针对诉讼调解进行了调研论证并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实施办法,诉讼调解再次被重视起来。
(二)诉讼调解复兴的原因
诉讼调解为什么会呈现“U”型回归态势?
分析诉讼调解复兴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受国外纠纷解决方式变化的影响。
实际上在上世纪80、90年代,国外已经开始关注纠纷解决的ADR(AlternativeDisputerResolution),ADR这个术语泛指一切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
国外已经开始强调解决纠纷的弹性化和多样化,想办法建立多元化的调解机制,解决社会矛盾。
他们的这种发展趋势在21世纪初期被作为一种“西方意识”影响到我国,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如前所述,在我国历史上,“息讼”的官方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间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用,民间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等等的实行,也是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说我国具有ADR的传统并不为过。
新中国成立后,1991年民事诉讼法受我国传统调解制度的影响,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