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Word下载.docx
《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Word下载.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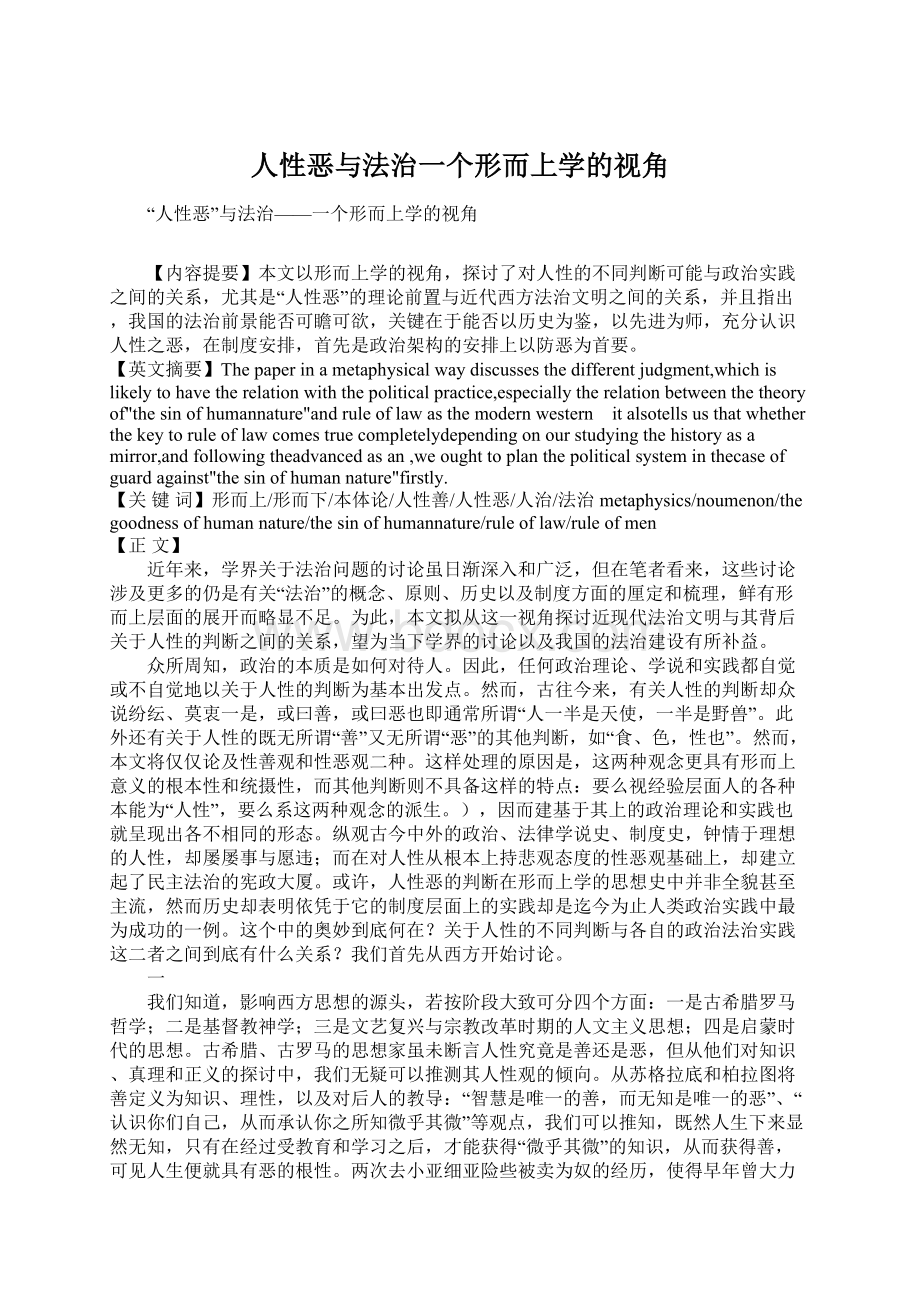
近年来,学界关于法治问题的讨论虽日渐深入和广泛,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讨论涉及更多的仍是有关“法治”的概念、原则、历史以及制度方面的厘定和梳理,鲜有形而上层面的展开而略显不足。
为此,本文拟从这一视角探讨近现代法治文明与其背后关于人性的判断之间的关系,望为当下学界的讨论以及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补益。
众所周知,政治的本质是如何对待人。
因此,任何政治理论、学说和实践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关于人性的判断为基本出发点。
然而,古往今来,有关人性的判断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曰善,或曰恶也即通常所谓“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此外还有关于人性的既无所谓“善”又无所谓“恶”的其他判断,如“食、色,性也”。
然而,本文将仅仅论及性善观和性恶观二种。
这样处理的原因是,这两种观念更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根本性和统摄性,而其他判断则不具备这样的特点:
要么视经验层面人的各种本能为“人性”,要么系这两种观念的派生。
),因而建基于其上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也就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形态。
纵观古今中外的政治、法律学说史、制度史,钟情于理想的人性,却屡屡事与愿违;
而在对人性从根本上持悲观态度的性恶观基础上,却建立起了民主法治的宪政大厦。
或许,人性恶的判断在形而上学的思想史中并非全貌甚至主流,然而历史却表明依凭于它的制度层面上的实践却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实践中最为成功的一例。
这个中的奥妙到底何在?
关于人性的不同判断与各自的政治法治实践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首先从西方开始讨论。
一
我们知道,影响西方思想的源头,若按阶段大致可分四个方面:
一是古希腊罗马哲学;
二是基督教神学;
三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四是启蒙时代的思想。
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虽未断言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但从他们对知识、真理和正义的探讨中,我们无疑可以推测其人性观的倾向。
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将善定义为知识、理性,以及对后人的教导:
“智慧是唯一的善,而无知是唯一的恶”、“认识你们自己,从而承认你之所知微乎其微”等观点,我们可以推知,既然人生下来显然无知,只有在经过受教育和学习之后,才能获得“微乎其微”的知识,从而获得善,可见人生便就具有恶的根性。
两次去小亚细亚险些被卖为奴的经历,使得早年曾大力推崇“哲学王”的柏拉图从现实生活中发现,人性是靠不住的,即使是集智慧与德行于一身的哲学王的统治也难免演化为独裁的丑剧,从而极大地动摇了他对人性的信心。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古希腊先哲的思想深处对“人性之恶”已有相当的警觉。
身为其弟子的亚里士多德进而声称“不敢对人类的本性提出过奢的要求”[1],则更是深刻地意识到人之为恶的能力,并指出:
“正如当人完成为人的时候,人才是最好的动物一样,当脱离法律和裁决的时候,人就是最坏的动物。
”他还认为:
“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据此提出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着名论断。
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止是他对“一人之治”的否定,而是对“人性”的根本否定。
这为非人格的法律提升到“统治者”的地位确立了理论的逻辑前提,也开创了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思维模式。
古希腊先哲对人性的这种警惕,也渗透到了古罗马的政治哲学与实践中。
它通过西塞罗“人服从自然理性”的逻辑梳理,法律在理论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形象渐渐明朗。
然而,我们仍然发现古希腊罗马的先哲们对人性的批判远未至达根本意义的形而上层面,尚带有较多的经验事实成份。
很显然,这种对人性的不彻底批判并不能必然地逻辑出“法律至上”的结论。
只要对人性的判断还更多地停留在事实层面而未上升到形而上的价值高度,对人性的否定就不可能是根本的,法律也就实现不了对人的超越。
同样构成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的古希伯莱文明及其后来的基督教文明却因对人性的彻底批判,从而对法律地位的提升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夸张地说,没有古希伯莱文明及其后来的基督教文明,就没有今天西方的宪政与法治。
由于西方自古以来就具有世俗与宗教、人与神的二元对立的源远流长的宗教思想,故而对古典的性恶论获得本体论的提升影响至深。
以希腊神话表达出来的宗教观念,若以世俗的眼光执拗地破解其义,可能是荒诞的,但若觉悟其象征意义,就会领略个中精巧的智慧。
这种思想的中心意思大概就是:
神以其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基本的一点“灵明”,但这“灵明”却因人对神的叛离而沉落,由此黑暗势力在人世间伸展,造成人性与人世的堕落。
这种对人性的双面认识,一方面,因人为神造而肯定其固有的尊严;
而另一方面,则认为人人都具有与始具来的堕落趋势和罪恶的潜能。
这意味着,人虽可以得救,却永远不能变得象神那般完善。
也就是说,在至高无上且完美无缺的神的面前,人的提升是有限的,而其堕落却是无限的。
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人制定的法律必须让位于神法的主张,正是这种宗教观念的生动表达。
这种对神的信仰被后来影响西方文化更为深远的基督教文明所承袭。
性恶论透过“原罪”说以及欧洲中世纪宗教文化的渗染成为了不争之说。
按照基督教的“原罪”说,人人都生而有罪。
为了获得自身灵魂的拯救,人必须向神忏悔,遵守神的戒律。
如果说神的莅临本身就是对人、人性的绝对否弃,那么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就是甄别人类行为正义与否的最高尺度。
因此,圣·
奥古斯丁坚信,“世俗的政治秩序不可能是真正正义的秩序”。
他对人性的悲观在其所描述的“地上之城”里有充分展现:
“自私统治着这个国度,各种自私自利的目的相互冲突,使它终将沦为罪恶的渊薮。
”十三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
阿奎那在其四种法的分类理论中进一步佐证了前三种“自在之法”高于人法的理由,并强调指出,在有关灵魂的拯救方面“人们应该服从宗教权力,然后再服从世俗权力”,因为世
俗的政策法令“只能对外在行动作出判断”;
而“只有作为神法制订者的上帝才能判断意志的内在活动”。
无疑,作为一个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此论的前提仍是基于人性恶的假定。
近代的西方世界,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复归,人的自我意识和自信得到一定的恢复。
但是,正如宗教改革并未改掉人们对上帝的信仰,而作为宗教理念不可或缺的性恶观在宗教改革以后的西方文化中依然被承袭下来,并深刻影响着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与实践。
将西方法哲学从中世纪神学和教会的直接影响下解放出来的路德和加尔文,也都“信奉人的完全堕落”,并且认为,堕落的人“倘若不被管束,那么在凶暴残忍方面,他就会远胜过所有凶禽猛兽”。
十六世纪的另一个神学家胡克尔也认为:
“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并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以防范人们的外部行动,使他们不致妨碍所要组成社会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这种地步,它们便不是完善的。
”胡克尔的理论深深地影响了洛克,他在其《政府论》一书中写到:
“谁认为绝对的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
”而另一位为近代分权论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孟德斯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10]尽管这些现实主义的思想家,未必言称上帝,甚至得出的结论也多为经验观察的结果,但是“他们所由出发的立场,乃至他们寻求解决的方法所依循的途径,都明显带有基督教文明的印痕”[11]。
基督教文明留给后世西方文化的遗产是多方面的,但人性恶的思想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政治哲学,无论是基于典型的宗教形而上学或是基于经验主义的实证观察,在支持民主与法治的理论上,都遗传了基督教文明的基因,对人性的缺陷怀有深刻的警惕。
在《美国百科全书》对“民主”的词条解释中就有这样的评论:
“对于民主的信心根本不以人性的善良为依据,……民主确实也作过不少愚蠢的决定。
但是,如果这类错误不被较为健全、较为见多识广的民主行动所纠正,而求助于独裁者或超凡的领袖时,往往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12]。
性恶论与法治的关系以及对法治的意义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性恶论作为一种对人性的终极判断,断然否定了“完人”临世的可能性,这既拆除了指望“圣贤”或“哲学王”等好人救世的价值基础,并且为“法律的统治”确立了理论的逻辑前提。
主张人治的哲学在解决政治权力的归属上往往都归结于拥有完善人格的统治者,这在古今中外不乏其例。
从柏拉图的理想政治“哲学王的国家”,到孔子的“圣王”政治,都同出一辙,骨子里透出的还是对人性的自信。
这种理论上的一厢情愿和实践上的行不通,不仅被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而且也被后世的历史所证明。
贤明的君主总是可遇不可求,或许恩泽一时,但其英明只能是结果的公正,没有任何道义或程序的必然。
更何况“皇恩浩荡”毕竟是一件稀罕的礼物,至于寥若晨星的“清官”,更无法刷新整个政治的颜色,他们总是被诗意的美化,仅成为一种期望的象征。
当然,性恶论对人治的釜底抽薪,还不仅是政治经验的。
至少,西方的性恶论,是通过宗教的神与人的绝对分立展开的。
基督教不相信人在世间有体现至善的可能,因为,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堕落性,虽靠着自己的努力和神的恩宠,人可以得救,但却永远无法变得完美无缺。
这份完美、至善,只有神才拥有,而人神之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人无完人。
可见,在形而上意义的“性恶论”基础上,人治无由生长。
其次,性恶论对人性的根本否定,与形而上学的“法”的提升,不仅拥有共同的哲学理念,而且二者在理论上的相互关照,为法治提供了必要的价值基础。
仅有对人性的否弃,而没有对法律的提升,或许可以否定人治,却并不能当然地推导出法治;
否则就不能解释,同样基于性恶论,何以在西方发展出了“法治”,而在中国却强化了“人治”。
这要归因于贯之西方文化始终的“自然法”理念。
即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对自然法的坚信,尤其是主张自然法作为不证自明的法与人定法的对应,以及对人定法的绝对的超越。
在西方法律文化中,不同时期人们对自然法有不同的解说,或称为“正当理性”或“神的意志”,甚至有人对其存在的方式及意义抱有怀疑,然而一个可与上帝比肩、超越了人、负载正义且永恒存在的法的理念却始终伴随着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