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缺陷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缺陷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缺陷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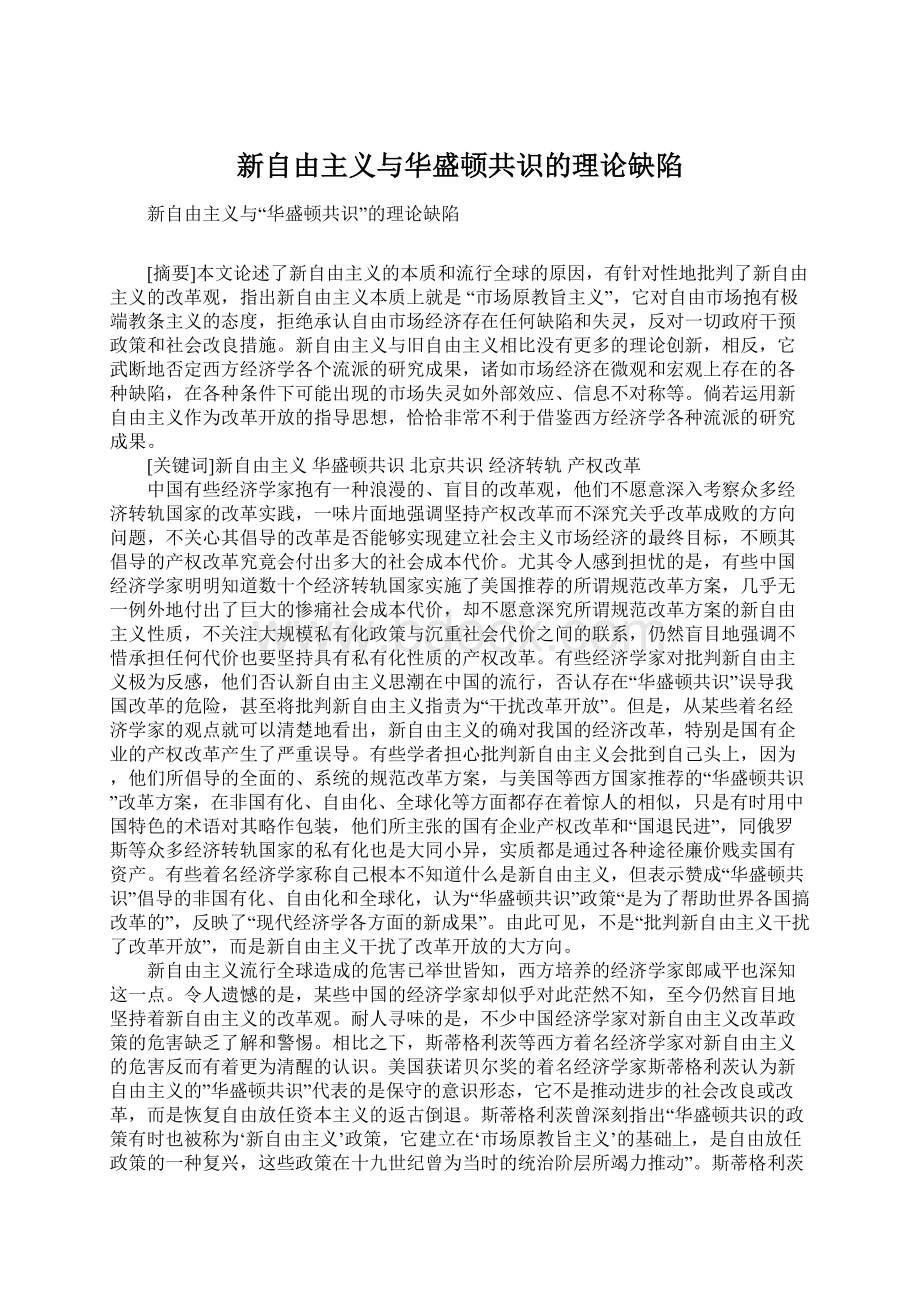
中国有些经济学家抱有一种浪漫的、盲目的改革观,他们不愿意深入考察众多经济转轨国家的改革实践,一味片面地强调坚持产权改革而不深究关乎改革成败的方向问题,不关心其倡导的改革是否能够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标,不顾其倡导的产权改革究竟会付出多大的社会成本代价。
尤其令人感到担忧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明明知道数十个经济转轨国家实施了美国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几乎无一例外地付出了巨大的惨痛社会成本代价,却不愿意深究所谓规范改革方案的新自由主义性质,不关注大规模私有化政策与沉重社会代价之间的联系,仍然盲目地强调不惜承担任何代价也要坚持具有私有化性质的产权改革。
有些经济学家对批判新自由主义极为反感,他们否认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流行,否认存在“华盛顿共识”误导我国改革的危险,甚至将批判新自由主义指责为“干扰改革开放”。
但是,从某些着名经济学家的观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新自由主义的确对我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产生了严重误导。
有些学者担心批判新自由主义会批到自己头上,因为,他们所倡导的全面的、系统的规范改革方案,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荐的“华盛顿共识”改革方案,在非国有化、自由化、全球化等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只是有时用中国特色的术语对其略作包装,他们所主张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国退民进”,同俄罗斯等众多经济转轨国家的私有化也是大同小异,实质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廉价贱卖国有资产。
有些着名经济学家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但表示赞成“华盛顿共识”倡导的非国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认为“华盛顿共识”政策“是为了帮助世界各国搞改革的”,反映了“现代经济学各方面的新成果”。
由此可见,不是“批判新自由主义干扰了改革开放”,而是新自由主义干扰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新自由主义流行全球造成的危害已举世皆知,西方培养的经济学家郎咸平也深知这一点。
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却似乎对此茫然不知,至今仍然盲目地坚持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观。
耐人寻味的是,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危害缺乏了解和警惕。
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西方着名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反而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
美国获诺贝尔奖的着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代表的是保守的意识形态,它不是推动进步的社会改良或改革,而是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返古倒退。
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它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复兴,这些政策在十九世纪曾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竭力推动”。
斯蒂格利茨强烈地批评了“华盛顿共识”,称其“往坏里说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时代,还说“无论新的共识是什么,都不能基于华盛顿”,直接点出了从华盛顿的立场出发,不可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西方的社会党国际也深感“正面临着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威胁”,“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要求反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道路”。
倘若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反而对新自由主义的威胁毫不知晓,对其危害采取一种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态度,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就可能像俄罗斯一样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
从这种意义上说,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恰恰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维护受到举世赞扬的“北京共识”的成功改革道路,扞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受新自由主义侵蚀、威胁,防止中国重蹈俄罗斯等经济转轨国家的灾难覆辙。
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旧自由主义倡导的极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历史,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改良的基础上,对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除弊兴利”,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温和中间改良道路,依照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改革才能建立现代的规范市场经济,不然国际权威组织为何积极向转轨国家推荐新自由主义理论呢?
其实,这是一种对新自由主义本质的肤浅理解,新自由主义不是“与时俱进”的温和社会改良,而是重新恢复极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返古复辟”。
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渊源可追溯到旧自由主义,它在学术理论上并没有更多的创新,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旧自由主义因大萧条早已声名狼藉,遭到西方社会改良思潮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则以种种理论返古复辟,重新否定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同时也更彻底否定社会主义革命。
我国留学西方长期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前辈如陈岱荪、胡代光教授,在论述新自由主义的特征时就特别强调它的“浓厚的复古色彩”,将它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更为极端的翻版”。
由于新自由主义顽固坚持“绝对个人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改良,抨击政府调节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甚至反对政府禁止贩卖毒品,在西方学术界也曾普遍被视为一种“极端学说”。
我国着名经济学前辈陈岱荪曾撰文深刻指出,“近年来在国内滋长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深究起来,实质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这一古旧学派的崇拜,而人们之所以以腐朽为神奇,盲目崇拜这一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的学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主流派经济学;
二是为其光怪陆离的理论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它与从亚当·
斯密到马歇尔的旧经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关系;
三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
西方媒体普遍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流行,归功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等右翼保守派执政后,推动的反对二战后社会改良的“世界保守革命”,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后曾明确无误地宣称,其奉行的政策目的是要重新回到“亚当·
斯密时代”,充分暴露了她领导的“世界保守革命”的本质,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复辟极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早已存在,但是,自从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以来它在西方国家仅仅是一种边缘学派,从未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
新自由主义骤然时来运转,摆脱以前边缘地位风靡全球,首先,是因为代表美英垄断财团利益的右翼势力,将其作为谋求全球霸权利益的战略工具,其次,作为打击社会改良思潮的意识形态,再次,才是作为抨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
自由主义是代表19世纪统治阶层利益的经济政策,与之对应的是政治领域的保守主义政策,国际领域中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对亚非拉民族实行的殖民主义政策。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全球范围流行,同样伴随着右翼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潮流崛起,臭名昭着的帝国主义政策死灰复燃,摇身变为英美右翼政客公开鼓噪的“新帝国主义”,以及对亚非拉国家实施的隐蔽新殖民主义。
有些中国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的极右本质茫然不知,误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搞极左回潮”,殊不知新自由主义与旧自由主义同属“极右”,旧自由主义是昔日帝国主义国家推崇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则是今日新帝国主义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而无论新的还是旧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都代表昔日和今天帝国主义经济利益。
倘若我们为了纠正以前“极左”的错误,将新自由主义误当作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其所犯荒谬错误的“极右”程度,就好像为了纠正王明的极左错误,干脆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
正因如此。
陈岱荪等长期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才尖锐地指出:
美国和某些国际组织“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
当年陈岱荪先生提出的深刻见解,今天重读显得格外令人回味。
许多新一代的着名中国经济学家,都误将陈岱荪先生的谆谆告诫当做是思想僵化。
其实,陈岱荪早年留学获得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不留恋美国高等学府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还拒绝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的诱惑,解放后又因提醒人们重视战后西方的社会改良,不赞成盲目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在政治运动中屡次挨整、遭受批判。
他的警世告诫来自一片爱国真情,来自长期严谨治学的真知灼见。
尤其值得敬佩的是,陈岱荪先生富有远见的警世之言,正越来越为世界局势的发展所证实,特别是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还得到了许多西方着名学者的呼应,尽管他们对于国际组织的强烈批评,来得要比陈岱荪先生晚了好多年。
值得指出,陈岱荪、胡代光、陶大镛、高鸿业等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前辈,他们之所以能够深刻地洞察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与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和丰富人生阅历有很大关系。
他们解放前曾留学海外熟知西方和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对旧自由主义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掠夺有深刻体验,对当年华人在西方遭受的歧视、屈辱有切肤之痛。
尽管当年留学西方的前辈经济学家,也曾长期被灌输过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但他们通过旧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负的亲身经历,很容易看破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貌似科学的抽象演绎,不会轻易迷信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效率高的神话。
但是,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被迫放弃了冷战遏制,主动对社会主义中国表现了种种友好亲善行为,邀请了大批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访问,许多没有前辈经济学家阅历的年轻学者和党政干部缺乏免疫力,很容易为西方国家的富裕和财富所倾倒,人们很容易相信美国推荐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是为了帮助经济转轨国家建立规范市场经济并走上富裕之路,即使依照科斯产权定律推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甚至复辟了类似解放前的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风险,美国也会像对待台湾一样帮助中国度过经济转轨的难关。
难能可贵的是,陈岱荪、胡代光、高鸿业等老前辈经济学家,对美国扩大文化交流的友好姿态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像当年提醒人们不要盲目地批判西方经济学一样,告诫人们对美国推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保持警惕,不要走另一个极端再犯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错误。
倘若说当年搞计划经济应该警惕“极左”错误,今天搞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应特别警惕另一个极端,因为,新自由主义与旧自由主义一样具有“极右”本质,同属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背道而驰,为帝国主义经济利益服务且危害巨大的意识形态武器。
值得关注的是,前苏联酝酿改革的早期阶段,人们很羡慕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曾将其视为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后来受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的诱导,为了推行所谓“最彻底的规范改革”,俄罗斯又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方案。
但是,经历了十年改革的曲折历程后,人们纷纷指责激进改革的设计者,表面上是推行“最彻底的规范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搞“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导致了私有化过程中腐败掠夺泛滥,形成了操纵经济的暴富权贵阶层,国民经济下降一半,严重削弱了综合国力,国防力量衰落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利益,巨额掠夺资产通过各种非法途径流亡海外,致使投资远低于折旧和社会设施严重老化,民众生活困苦和社会严重两级分化,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系统陷入瘫痪,恶性传染病死灰复燃而人口出现持续下降。
改革结果与期盼的反差巨大令人惊叹,但即使是从学术理论角度深入反思,这种结局并不意外而且尽在情理之中。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早已公开声称,他们反对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主张恢复亚当·
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
试想依照这样的返古复辟的理论搞改革,自然只能得到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的结果。
中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