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可译性理论反思与个案分析Word格式.docx
《论不可译性理论反思与个案分析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不可译性理论反思与个案分析Word格式.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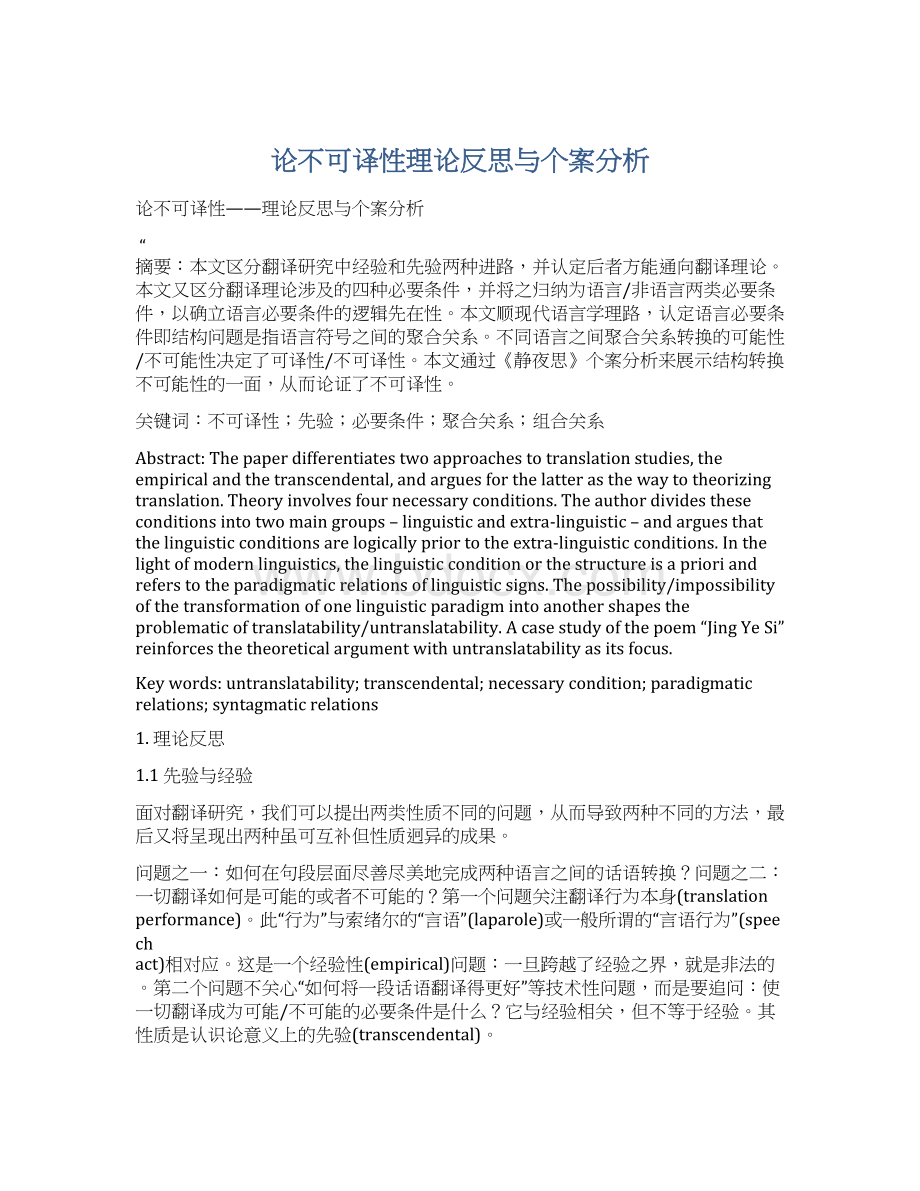
聚合关系;
组合关系
Abstract:
Thepaperdifferentiatestwoapproachestotranslationstudies,theempiricalandthetranscendental,andarguesforthelatterasthewaytotheorizingtranslation.Theoryinvolvesfournecessaryconditions.Theauthordividestheseconditionsintotwomaingroups–linguisticandextra-linguistic–andarguesthatthelinguisticconditionsarelogicallypriortotheextra-linguisticconditions.Inthelightofmodernlinguistics,thelinguisticconditionorthestructureisaprioriandreferstotheparadigmaticrelationsoflinguisticsigns.Thepossibility/impossibilityofthetransformationofonelinguisticparadigmintoanothershapestheproblematicoftranslatability/untranslatability.Acasestudyofthepoem“JingYeSi”reinforcesthetheoreticalargumentwithuntranslatabilityasitsfocus.
Keywords:
untranslatability;
transcendental;
necessarycondition;
paradigmaticrelations;
syntagmaticrelations
1.理论反思
1.1先验与经验
面对翻译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方法,最后又将呈现出两种虽可互补但性质迥异的成果。
问题之一:
如何在句段层面尽善尽美地完成两种语言之间的话语转换?
问题之二:
一切翻译如何是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
第一个问题关注翻译行为本身(translationperformance)。
此“行为”与索绪尔的“言语”(laparole)或一般所谓的“言语行为”(speechact)相对应。
这是一个经验性(empirical)问题:
一旦跨越了经验之界,就是非法的。
第二个问题不关心“如何将一段话语翻译得更好”等技术性问题,而是要追问:
使一切翻译成为可能/不可能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它与经验相关,但不等于经验。
其性质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transcendental)。
第一个问题和涉及的方法,与常识相通,而且实用价值显著。
正因为此,这种淡化了认识论维度的翻译研究,如同缺乏科学性的传统语法一样,仍然充当着课堂教学的主角。
通过翻译的成果,也可以从翻译行为中抽象出几条乃至几十条训律,当做“理论”来讲授。
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它对技能训练的关注。
但是,技能训练与理论思考毕竟是两回事。
一旦混淆,此进路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
此弊端可称之为“从经验到超验的飞跃”:
一方面,每一次翻译行为,都是一次语用事件,既不可重复又不具备普遍有效性;
另一方面,对尽善尽美的追求,又往往驱使经验行为膨胀成对超验的追求(transcendentinquiry)。
熟知的案例是所谓“信达雅”三字经。
这个念了近百年的经,隐含了一个不合法的哲学认识论假定:
我们可以超越自身的经验界线,在语言和语境两个方面同时进入他者的世界。
其政治和伦理学蕴含是将异质归约为同一(reductionoftheOthertotheSame)。
这种“从经验到超验的飞跃”,既是对意识形态嬗变的回应,也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在翻译研究中的折射。
从唐代佛经翻译到如今,一千三百余年了,汉民族的翻译研究一直执着不懈且洋洋得意地在“经验——超验”这个怪圈中徘徊。
①就研究的主体而言,文学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之间几乎没有区别,审美和认知混为一谈。
这种严重匮乏先验意识的智性传统,正是近代科学认识论未能在汉语文化圈中生成的根本原因。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往往用经验来理解先验,然后通过各种渠道直奔超验。
文学/文化批评如此,翻译研究亦然。
经验当然要研究。
但是,无先验则无理论。
第二种性质的问题和理路,要探索那些逻辑地先在于一切翻译行为同时又是任何一种翻译行为都无法摆脱的基本要素。
它感兴趣的是“科学”,不是立竿见影的“技术”。
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最关心的不是如何描述和说明某一个家族的某一种遗传现象,而是要探讨一切遗传现象如何是可能的这个先验问题。
他们为这个逻辑地先在于一切遗传现象的必要条件取了一个名字“基因”,然后再通过可控制的实验去证明它的存在——从先验假设返回经验证明。
同样道理,翻译理论不是教会学生如何去从事具体的翻译活动并获得优质的译文,而是要解释翻译本身如何是可能或不可能的。
在这个先验的问题框架内,不容许出现任何超验的问题,如“上帝存在”、“终及关怀”、“信达雅”等等。
立于认识论和现代语言学基础之上的翻译理论,只涉及“临在性”(immanent)领域。
②它要探讨这些临在性领域,如何影响和决定了翻译的行为。
对其中任何一个临在性领域的全面关注,都可衍生出一套相对独立的翻译理论;
但是,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涵盖其它临在性领域内的所有问题。
这些临在性的、逻辑先在的必要条件,大致区分如下:
A.原文语言(sourcelanguage)和译文语言(targetlanguage)的结构,即:
符号与符号结合并构成系统的特定方式。
B.使原文和译文能被各自社会接受的写作成规和阅读成规。
成规是多价性的;
认知、伦理、审美都包括在内。
C.写作/翻译发生时的社会文化上下文。
它指向特定的意识形态动因。
此动因必然影响创作和作为再创作的翻译行为并在原文/译文中再显。
D.原文产生时那种特殊的个人化的情景,即:
一种绝对不可重复的语用事件,其中包括了创作者个人才智的闪耀和对社会文化上下文的独特回应。
此语用事件,又必须通过译者在另一社会文化上下文中的想象来重构,从而导致了另一个语用事件。
重构的可能性,是建立在头一个语用事件的不可重复/必须重复这个悖论之上的。
显而易见,上述四类必要条件全部都逻辑地先在于一切经验性翻译行为,同时又对后者施加决定性影响。
先验进路,必须分门别类地瞄准上述不同的临在性领域,提出各自的理论框架。
另外,按分析法而不是综合法,③上述四种必要条件的先验程度也不一样。
从第四往第一倒数,逻辑的先在性不断增强,其理论的涵盖面也不断拓宽。
最具先在性的,便是语言的结构问题。
追到底,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将取决于这么一个问题:
在什么意义上,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性转换是可能的?
在什么意义上,则是不可能的?
通过翻译行为而出现的理解/误解之共生现象告诉我们,可能/不可能同时存在。
研究不可译性,出于方法论和主题的需要,当然会悬置可译性,但不等于否定后者。
无论侧重可译性还是不可译性,最基始的翻译理论仍然是研究结构转换问题的理论。
这也是本文反思和个案分析的焦点。
1.2区分两类必要条件
上述第一种必要条件即语言结构,为语言共同体全部成员分享。
作为结构,它是一种抽象的形式,没有具体的内容,却为所有的内容(包括敌对的内容)提供了逻辑先在的运作机制。
此条件,可称为语言的必要条件(linguisticnecessarycondition)。
后三种必要条件涉及具体内容,与特定意识形态发生关系。
它们不是“语言性”的——非语言结构的,却又与语言性纠缠在一起。
三者可并称为非语言的必要条件(extra-linguisticnecessaryc”onditions)。
在研究语言翻译问题时,一定要区分语言的必要条件即语言结构(lalangue)和那种包含形形色色非语言要素同时又“寄生”于语言结构的所谓“语言”(lelangage)。
后者就是常识所指的“语言”,它总是与非语言的必要条件纠缠在一起,使“语言”这个概念处于一种“未经审视”(unexamined)的状态。
符号学的实际创始人叶尔姆斯列夫指出:
一定要先弄清语言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然后再进入涉及哲学、文学、社会、逻辑、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内的各种语言问题(Hjelmslev,1963:
5-8)。
70-80年代的语用学转向,将研究的重心投向各种非语言的必要条件。
但是,不能为了语用而悬搁结构,更不宜抛弃“语言结构”(lalangue)而返回“语言”(lelangage)。
因为这无异于重拾19世纪的语言观。
文化人类学内的结构主义神话批评和后现代的社会语用学就是这样做的。
④顺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开辟的共时语言学理路,我们甚至可以追问:
英美语言哲学所言的“语言”,是指lalangue还是指lelangage?
(英语中无langue和langage之分,只有一个词language。
)我以为是指后者。
那么,这种“集物理、生理、心理、逻辑、社会学等等为一体”的“语言”(Hjelmslev,1963:
5-6),又如何能将意义、指涉、真理等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呢?
同样道理,忽略了语言结构的先在性和结构转换的可能性/不可能性,一切翻译理论都会有违初衷地被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非语言学问题冲淡乃至消解自身的理论目标,从而失去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
当然,语言的必要条件和非语言的必要条件,不能绝对分立。
但是,两者之间的范式性区别和语言的必要条件之先在性必须坚持。
综合了两类必要条件的翻译理论,至今尚未出现。
笔者以为不可能,并视之为诗学乌托邦终极关系之非法套用。
所谓“全面地整体地看问题”,并不等于将问题的全景都能同时纳入视域,而是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持视角的局限性,明白其边界线大致在何处。
各种翻译理论之间的互补,有助于克服单一理论的局限性。
但是,互补不等于否定各种理论之间存在的逻辑先在性强弱之别。
研究语言翻译,首先要研究语言的结构。
语言结构的转换,是一切翻译理论无法回避的基始问题。
1.3警惕翻译理论的误区
翻译理论的另一误区是玩“提喻”(synecdoche)的游戏,即:
以部分代全体。
典型案例是解构主义对翻译“再创造性”的极度张扬。
有论者尊之为一种新的翻译理论(陈德鸿、张南峰,2000)。
解构策略的线索并非“不确定”,而是非常清楚:
在质疑“我注六经”之可能性的同时——即推翻“信”的原则,将“六经注我”的不可避免性推向极端,以“再创造”来消解不可重复/必须重复的悖论。
此悖论,其实是一种“二律背反”(antinomy),因此不可以通过等级二元的重建来消解。
换言之,即便在语用事件之“重构”这个问题框架内,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合法性就已经颇成问题了。
然而,此翻译“理论”并没有到此就收手。
它的最终目标是以“再创造”或“六经注我”为武器,去颠覆先在的语言结构,瓦解先在的写作/阅读成规,批判先在的社会文化上下文。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