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渊源及新浙派的崛起doc.docx
《浙派渊源及新浙派的崛起doc.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浙派渊源及新浙派的崛起doc.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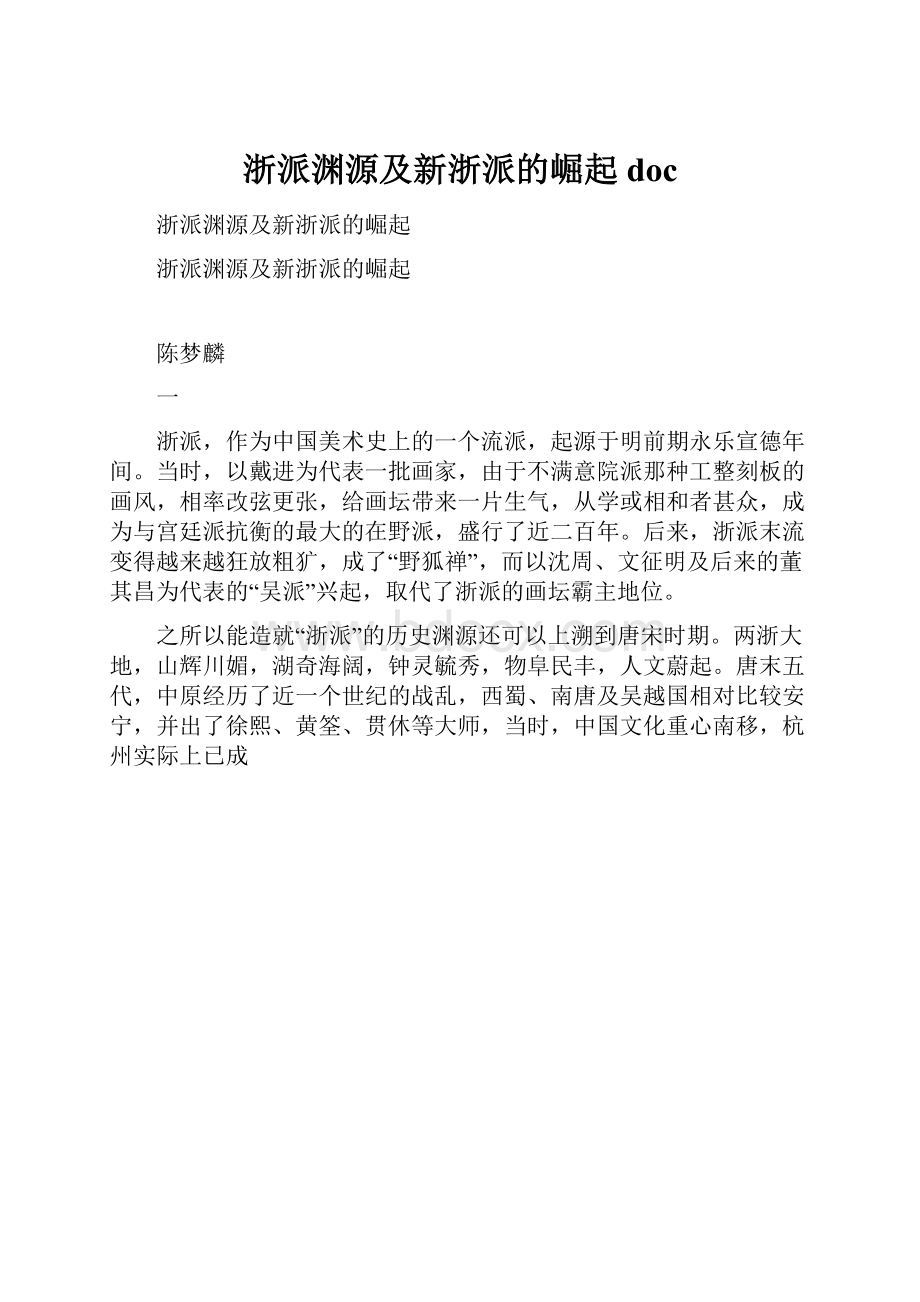
浙派渊源及新浙派的崛起doc
浙派渊源及新浙派的崛起
浙派渊源及新浙派的崛起
陈梦麟
一
浙派,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流派,起源于明前期永乐宣德年间。
当时,以戴进为代表一批画家,由于不满意院派那种工整刻板的画风,相率改弦更张,给画坛带来一片生气,从学或相和者甚众,成为与宫廷派抗衡的最大的在野派,盛行了近二百年。
后来,浙派末流变得越来越狂放粗犷,成了“野狐禅”,而以沈周、文征明及后来的董其昌为代表的“吴派”兴起,取代了浙派的画坛霸主地位。
之所以能造就“浙派”的历史渊源还可以上溯到唐宋时期。
两浙大地,山辉川媚,湖奇海阔,钟灵毓秀,物阜民丰,人文蔚起。
唐末五代,中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战乱,西蜀、南唐及吴越国相对比较安宁,并出了徐熙、黄筌、贯休等大师,当时,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杭州实际上已成
朝第一”,从学者甚多。
山水,当时画院的李在、周清等都是马夏遗规,戴进在马夏的基础上,同时取法郭熙、李唐,变南宋浑厚之趣而成健拔劲锐之风,面目为之一新;人物用蚕头鼠尾描,佛像用铁线描或兰叶描,运笔顿拙有力;走兽、花鸟亦很精致,喜作葡萄。
由于戴进已经从宫廷画院出来了,所以人们就把以戴进为代表的画风,包括与他风格相近的画院待诏李在,他的学生吴伟、陈景初等称为“浙派”。
吴伟,江夏人,当时与沈周、杜堇等齐名,尤为此派健将,传其衣钵者有蒋嵩、宗臣、王仪等,亦能发扬,号“江夏派”,实则浙派之支流。
蒋嵩好用焦墨枯笔,点染粗糙;后郑文林(号颠仙)、张平山、汪肇等专尚粗毫颓放,被后起的“吴派”讥为“魔道狂态”。
其后,兰瑛的画风虽与戴进不同,但通常被称“浙派殿军”。
大致说来,从国初到嘉靖近两百年间,盛行浙、院两派,实质就是朝野两派,嘉靖之后,则吴派独盛。
如果要把院、浙、吴三派画风作一个比较的话,大体说来,浙派雄浑博大,吴派柔淡雅秀,院派似乎介于两者之间,细巧缜密,又不乏坚挺劲拔;浙派阳刚,吴派阴柔,但是浙派容易流于粗顽,吴派容易流于纤弱,因此,两派虽不同时并出,但其后人们之间的口水战打了一百多年。
对此,清代的大师王石谷很感叹:
“呜呼!
画道至今而衰矣。
其衰也自晚近支派之流弊起也。
顾陆张吴,辽哉远矣。
大小李以降,洪谷、右丞,逮于李范董巨、元四大家,皆代有师承,各标高誉。
未闻衍其余绪,沿其波流。
如子久之苍茫,云林之淡寂,仲圭之渊劲,叔明之深秀,虽同趋北苑,而变化悬殊,此所以为百世之宗而无弊也。
洎乎近世,风趋益下,习俗愈卑,而支派之说起。
文进、小仙以来,而浙派不可易矣。
文、沈而后,吴门之派兴焉。
董文敏起一代之衰,抉董巨之精,后学风靡,妄以云间为口实。
瑯琊、太原两先生源本宋、元,媲美前哲,远迩争相仿效而娄东之派又开。
其他旁派绪沫,人自为家者,未易指数。
要之承讹借舛,风流都尽。
翚自韶时搦管,仡仡穷年,为世俗流派拘牵,无由自拔。
太抵右云间者,深诋浙品;祖娄东者,辄诋吴门。
临颖茫然,识微难洞。
已从师得指法,复于东南收藏好事家纵揽右丞、思训、荆董、胜国诸贤上下千余年名迹数十百种,然而知画理之精微,画学之博大如此,而非区区一家一派之所能尽也。
”(《清晖画跋》)
如此深思卓见,确令人感动。
石谷也终于融汇南北,成为一代大家。
现代潘天寿亦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写道:
董华亭倡文人画,主“直指顿悟,一超直入如来地”,其着想自系文人本色。
《画禅室随笔》论文人画云:
“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
”则董氏对“积劫方成菩萨”一点,自觉有所未迨耳。
故其绘画论著中,非但未曾攻击马远、夏圭、赵伯驹、伯彇诸家,并对当时吴派末流,随意谩骂浙派,加以严正之批评。
《画禅室随笔》云: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
王叔明,湖州人;黄子久,衢州人;吴仲圭,钱唐人;惟倪元镇,无锡人耳。
江山灵气,盛衰故有时。
国朝名手,仅戴文进为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不知赵吴兴亦浙人。
若浙派日就澌灭,不当以甜邪俗赖者,尽系之彼中也。
”殊属就学术论学术,不失其公正态度。
董氏书画学之成就,平心而论,不减沈文,其论画见地及鉴赏之眼光亦然。
其对浙派戴文进氏之成就,不但未加轻视或贬抑,且曾予以公正之称扬,其题戴氏《仿燕文贵山水轴》云:
“国朝画史,以戴文进为大家。
此仿燕文贵,淡荡清空,不作平时本色,尤为奇绝。
”董氏绘画原系文人画系统,戴氏则为画院作家,其绘画途程与董氏有所不同。
然董氏之题语,劈头则肯定戴氏为“国朝画史大家”,其结语亦谓“淡荡清空,尤为奇绝”,可知董氏全以戴氏之成就品评戴氏,不涉及门户系统之意识,有别于任意谩骂之吴派末流多矣。
对此,潘天寿感叹:
“习俗纷争吴浙间,相讥纤细与粗顽。
苦瓜佛去画人少,谁写拖泥带水山!
”
二
“清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浙江。
咸同之乱,浙江受祸最烈,文献荡然,后起者转徙流离,奋发事功,更不以学术为主”,鸦片战争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
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恶之情日烈,……于是以其极幼雅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致用’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公然举叛旗矣。
”(梁启超)前面说过,我们是把美术流派作为一个学派来对待的,故其衍变流迁的外因是世界变迁,内因是人心变迁,与学术流派的变化发展有惊人的同步。
有清一代,总的来说是“四王”的一统之下,“四王”本华亭嫡传,吴派余绪。
清学始祖有顾炎武、戴震,画学有陈洪绶、倪元璐等“另类”;“乾嘉学派”兴起,阮元、俞樾等相继主盟学术,有趣的是,这时绘画形式上也出现了博古汉砖;“经世致用”之学起来后,画家也走出明末遗民的“新安派”,向“金陵派”、“扬州派”、“海上派”发展,一步步走向经济实用;西学东渐了,画坛就出现了朗世宁、吴历、曾波臣……到清末,学术界高扬“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艺术界也群雄蜂起,甚至自标“艺术叛徒”也出现了。
这一切都说明,画派的流变,不仅是随着经济重心的变化而变化,更内在的因素是随着学术思想的流变而流变。
浙江老是领天下风气之先。
清代朴学起源于浙江,流向全国,遂成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清一代最重要的学术成果,留下了从顾炎武、朱尊彝、戴震、黄宗羲到阮元、魏源、龚自珍、俞曲园、章太炎,吴昌硕、王国维等一连串闪光的名字。
同样地,浙江的画人也是领天下风气之先,从兰瑛的“武林画派”,陈洪绶、倪元璐、祁豸佳、查伊璜,到康乾时代的“三毛”、“二王”、沈铨、陈书、金农、董邦达、钱箨石、沈宗骞、方兰士、余集、黄易、奚冈、钱杜、顾洛,嘉道时代的“三熊”、戴熙、费丹旭、包栋、咸光时代的赵之谦、钱慧安、“三任”、蒲华及“海上派”……也是一连串闪光的名字,而且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于“正统派”之外别树一帜的、或者风格奇崛宏肆“不合时宜”的,往往是由浙人首倡,如陈老莲、金冬心、赵撝叔,吴缶庐;而近于院体的那类工整严谨的工笔人物,也往往由浙人继承,如余集、费小楼、改七芗、顾西梅,似乎象明代“浙派”那样还遗留有一丝“北宗情结”。
所以整个清代,虽然没有“浙派”之名,却仍有浙派遗风,其原因主要在画人们在战乱后流离四方,以谋生计,清末的“海上派”从它的学术支柱(乾嘉之学)、骨干力量(任伯年、吴昌硕、蒲华等)和作品风格(大写意、强骨线)来看,亦是昔日浙派的一个发展(不过“海派”的源头是多方面的,还有黄山派、扬州派、娄东派、常州派及金石学等)。
“京派”的领袖人物金城和周肇祥也都是浙江人。
三
以胡适之、陈独秀为精神领袖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史的转折点,也是思想史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张扬了清代朴学的革命内核,以白话文、打倒“四王”、科学求证为口号,实质是高扬“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也就是说,以“科学”为旗帜提出“民主”的要求,以图挽救日益衰落的国势。
当时,经济领域有留洋开放,兴办实业;文化领域也西学东渐,百家争鸣;美术领域则有高呼“打倒四王”者,有主张调和中西者,有主张中体西用者,有主张保存国粹者,此时,蔡元培所倡立的国立艺专,再一次使杭州成为中国的美术重镇。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立艺专的历史可以看作中国20世纪上半叶艺术发展的缩影。
它不但最开放,而且也最传统;对于西方艺术思潮的反应,没有哪一所学校象国立艺专这样迅速、敏感,对于传统艺术的固守,也没有任何学派像国立艺专这样的坚定不移,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全面捍卫它。
以林风眠为代表的融合派和潘天寿为代表的传统派,其主张大相径庭,但它们不是互相轻视、互相攻讦,而是互相促进、互相发展。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宽阔的学人胸襟,更是因为他们都具有要让中国画新生中兴的学术信念。
因而他们不仅营造了一种有利于艺术发展的兼容并蓄的学术氛围,卓然不群,而且扬芳飞文,把火种播向全国。
林风眠执掌国立艺专后,便以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为建院方针,提出了“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学术目标,立志要让中国画获得新生。
为革新中国画,他邀请潘天寿任国画科主任教授。
潘天寿亲眼目睹中华帝国的衰落,也亲自体会了传统艺术在西潮侵袭下岌岌可危的命运,作为一个艺术家,如何来振兴和发展这个传大传统,是他在艺术实践和艺术教育中刻骨铭心的问题。
他既清楚地意识到西画的长处,也不否认近代中国在物质文明上的落后,但他却并不因此就接受中国传统艺术已日暮途穷的说法。
他严格地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标准区别开来,拒斥康有为、陈独秀等人提出的用西画来改造中国画的方案,并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画是东方绘画最中心的主流,与西方绘画并峙形成世界的两大艺术高峰;并且身体力行,以他的艺术实践,给中国画带来一种强健乃至霸悍的新风,希望挽回明清以来颓落的情势;同时他对所谓南北宗、吴浙派有极其深沉的见解和苦心,本着深刻的心得,将两者熔诸一炉,实质上是重振了北宗和浙派,也给甜媚园熟的南宗吴派注入了生机。
在林、潘两人同心殊途地立志振兴中国画的时期,一位早有会心的学者耆宿应潘天寿之邀驻杖杭州,这就是黄宾虹。
“力挽万牛要健笔,所以浑厚能华滋,粗而不犷细不纤,优入唐宋元之师。
”黄宾虹实质是乾嘉学派之传人,亦是近代变法的参与者,只因面对国势疮痍,无力补天,故潜心金石,整理国故,见清季画坛虞山、娄东、苏松、姑熟诸派,陈陈相因,甜熟柔靡、空虚薄弱,每况愈下,曾引吭高呼,说“道咸间金石学盛起,为吾国画学之中兴”,希冀能挽回画学衰落之颓势,并集我国绘画笔墨之大成,总结出“五笔七墨”之说,揭示出传统法意之根底,及其精华糟粕之所在,既有吸收,又有批判,既有评隲,又有弘扬,披荆斩棘,导河归海,为后学指针。
1928年国立艺术院创立(后改名国立杭州艺专),林风眠为首任院长,潘天寿国画主任教授。
1929年春,合并中国画、西画两系为绘画系。
1937年日战爆发,国立杭州艺专内迁。
1938年杭州艺专与北京艺专在湖南沅陵合并为国立艺专,林风眠辞职,滕固任院长。
1939年迁至昆明安江村,中西画分科,潘天寿任国画科主任。
1940年滕固病逝,吕凤子、陈之佛先后继任。
1944年潘天寿赴重庆磐溪任国立艺专校长。
1964年国立艺专迁回杭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刘开渠任院长,江丰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再度将中国画科和西画科合并为绘画系。
1950年,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1953年为成立彩墨画科作准备,抽调青年教师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等进修彩墨画。
1954年绘画系在高年级分为彩墨画、油画、版画三科。
1955年撤消绘画系,改三科为三系。
1957年改彩墨画系为中国画系。
1958年,中国美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59年,潘天寿任院长。
国立艺专对中西两大绘画的教育体制经过了30年的分分合合,至此总算尘埃落定,三次分合,使中西绘画理念和技法撞击交融,互借互补,既整理了国故,批判吸收,传承发扬,又借鉴了西画的合理成分,所经历的曲折,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绘画的重新认识,并在教学结构上以体制进行了肯定。
接着,潘天寿、吴茀之等提出中国画系分设人物、花鸟、山水三科的建议,并得到高教部的支持。
当时的学校,云集了黄宾虹、刘开渠、潘天寿、吴茀之、沙孟海、诸乐三、顾坤伯、陆维钊、陆抑非、陆俨少、邓白、莫朴、张漾兮、黎冰鸿、周轻鼎、史岩、金冶、金浪、朱金楼等全国一流的艺术家、教育家及学科带头人,而且个个都具深湛的国学功底,且学贯中西,志在振兴中国美术。
可以说,经过了三十年的痛苦怀孕,学院在学术上、人才上、体制上都积累了雄厚的条件,只待到外界的东风一吹(这个“东风”就是当时政府号召,权力支持),一个中国美术史上的世纪婴儿便呱呱落地了,这就是“新浙派”。
四
“新浙派”开头是以“新浙派人物画”名著全国的。
共和国建立后,对杭州国立艺专实行军管,刘开渠任校长,江丰任副校长兼书记。
面对旧美艺只设山水花鸟专业,而无人物专业的缺陷,学校提出彩墨画系“以人物为主,写生为主,工笔为主”的方针,把教育纳入马列主义轨道,师生参加各项政治动动,批判脱离群众的思想情感和笔墨追求,以革命和现实生活的内容为题材取向,主要描绘工农兵形象,提倡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和领袖像,当然,这是共产党执政后对全国美术院校的统一指令。
然而浙江有它的特殊性,浙江的传统人文积淀深厚,浙江有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执教的杭州艺专。
可以比较一下当时京浙两大流派的同异:
相同的是都要画新时代的工农兵题材,不同的是两派的技法完全不同,北京是徐悲鸿、蒋兆和先生等基本上是用毛笔画西画,而浙江则是从中国传统人物画——从陈洪绶、余集、费丹旭、改琦、任伯年出发,吸收西画的合理成分和中国传统写意花鸟的技法而成的。
1953年学院成立彩墨画研究培训班,为彩墨画从绘画系中独立出来作师资准备,于是从众多有为青年学子中筛选出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等精英,从此,开始了现代人物画的创作实践,(1959年又把顾生岳从素描教研室调到人物画专业)。
这个新组建的艺术群体,在新体制下,受着统一思想观念和审美模式的制约,通过他们个人的才智和努力,使传统艺术在向现代的转换中,赋于传统以现代生命,使艺术成为现实社会的生命载体,在观念、审美、造型和技艺上呈现出一种新的图式,标志着新中国人物画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拓性一步。
尤其是以周昌谷、李震坚、方增先为代表的水墨人物画,影响遍及大江南北,直至今日;以宋忠元、顾生岳为代表的工笔人物也为世瞩目,处国内领先地位。
这个群体被美术界誉为“新浙派人物画”。
他们的开创性的劳动给社会留下了丰厚的有形和无形的资产:
周昌谷在1954年考察敦煌后的艺术实践中,创作了《两只羊羔》,并在1955年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金奖,从此他声震画坛,成为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他天才的艺术悟性使他的笔墨处处透射出清新幽远的文人气息,他自创的用水用彩技法,营造出明丽多姿的理想美,其对传统人物画的创新程度,甚至至今还无人企及。
李震坚擅长写实,用笔凝炼老辣,质朴劲健,丰富沉雄,所创作的《井冈山的斗争》时代气息浓郁,人物特征鲜明,当时很有影响,兼长山水、花鸟、书法,充分体现了开创者们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全面的传统修养,是“浙派人物画”前期的主要掌门人。
方增先从年轻时的成名作《粒粒皆辛苦》到成熟期的《说红书》到“文革”中的《艳阳天》直到新时期的《母亲》,都是各个时期浙派人物画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作品,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美术界,其生动的造型与传统水墨的结合,以及对水墨语言的深化力度,令人痴迷,他著写的《怎样画水墨人物画》,构筑了浙派人物画的基本理论,使他无意之间显示了学术领袖地位,再加上周昌谷、李震坚一系列笔墨技法的经验总结,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周昌谷明丽,李震坚凝重,方增先潇洒,相当于一个是奠基人,一个是掌门人,一个是学术领袖,交汇出“新浙派人物画”的美术流派,贡献着几十年的辉煌。
在开创时期,共同参与缔造“新浙派人物画”的还有:
刘文西、李山、姚有信、王庆明先生。
毕业后刘文西去了陕北,李山进了天山,姚有信去了上海(后两位最后都定居美国),他们都传着浙派之薪火,发展到自成门派了。
王庆明留校任教,得李、周、方三家精要而自成一格,造型生动,形象真实,特性鲜明,笔墨挥洒大胆,一派豪气,她的影响主要在教学,几代人的成长都蕴含着她的艺术生命的延续。
“浙派人物画”经过了50年代的创业,60年代到70年代的完善发展,几乎是成了全国的样板模式,于是自我固守、陈陈相固的危机悄悄来临,北有周思聪、南有杨之光,以及黄胄、程十发等各画派向浙派敲响了警钟。
如何继承前辈的事业,弥补体系的疏漏,继续革新发展,使得学派常新,承前启后的责任落到第二代传人身上。
第二代走在前沿的有:
吴永良、吴山明、冯远、刘国辉、李子侯、黄发榜、程宝泓、吴宪生、吴自强等,而早在1960年就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中央美院的徐启雄也在这个时期调入浙江画院,给浙江的工笔人物添上一道绚丽的色彩。
吴永良在1962年以优秀的处女作白描《鲁迅》毕业于五年制本科,得周昌谷亲授,文革后又考入方增先为导师的研究生班。
他针对意笔人物教学中存在的造型能力与笔墨技法长期脱节的问题,尝试在专业素描与水墨写意之间进行意笔线描的实验,成为一个成功范例,后被列入正式课程。
意笔线描写作为吴永良率先开拓的成果,对浙派人物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以水墨、线条见长,技巧高超,墨戏小品富有特色,且擅长指墨。
吴山明深得方增先法门而有胜蓝之意,中锋行笔,技艺娴熟,流畅苍润,气息清新。
90年代后,他自创了一种艺术样式:
宿墨水渍,以避开甜媚园熟,他似乎有意地在人物画中引入黄宾虹的山水线条,而且通过虚实相生以一炬之光使通体透明,这一个性化的印记从另一个方面充实和发展了浙派人物画。
冯远作为方增先的研究生,对恩师有着透彻的理解和深刻的虔诚,他有着北大荒的经历,忍耐奋发,锲而不舍,故能获得骄人的成绩。
喜作大场面的鸿篇巨制,正好填补了浙派人物画的薄弱环节,且勤于笔耕,为理论界所关注。
刘国辉早在60年代就以连环画名噪全国,文革后作为李震坚的研究生,他很想将传统的浙派模式来一次重新的提练组合,大胆地吸纳中外的文化成果,相信新的一代一定会更具生命力,更符合新时代的审美要求。
他纵向继承,横向借鉴,使写意的水墨技法与深化写实能力有机结合,变传统的意笔长线为线皴同构,既精致生动,又挥写自如。
1992年由他任导师的“中国人物画高级研修班”,向人们展示了水墨人物多种发展的可能,也是浙派人物画在当代深化发展的成果。
程宝泓的军旅生活,拓宽了浙派人物的创作题材,他注重写实和人物性格刻画的深度。
在水墨技法方面,有意追求平,层次简洁和谐,如同版画效果,展示出浙派人物画多方面的可能性。
早几年,当有人就“新浙派”采访方增先先生时,方先生说了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
“按潘老的设想,浙派人物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什么样子,方先生没有说。
对此,我请教了吴山明先生,他说:
“我的理解,按潘老的设想,画得还要平,不要掺进结构肌理这些手法,象潘老经常说的‘脸要洗干净’。
”我认为,包括程宝泓在内的有一群传人,似乎在实验着潘老提出的这一返朴归真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李子侯、黄发榜在工笔人物上各有千秋,前者以江南田园间的桑姑见称于世,后者以跨学科的探索老而弥坚。
当今,活跃在浙江人物画坛前沿的的上是“新浙派”第三代传人了。
年长的一辈如梁平波、励国仪、吴宪生、刘健等似乎是横跨十年“文革”的时间桥梁,传承着薪火,所以走的都是稳健的“新浙派”传统路子。
梁平波、吴宪生都有李震坚流韵,造型生动严谨,笔墨全面娴熟,梁以省委副书记的政事之余还创作了大型的《西藏风情》,为世瞩目;吴则继续着吴永良、吴山明、刘国辉等开创的探索,在素描与水墨的有机转换这一课题上深化研讨;励国仪的神话女性,吴带当风,细腻优美,刘健的汉唐壁画,古拙伟岸,厚重古艳,都令人耳目一新。
文革后出现的精英则有尉晓榕、杜觉民、王赞、胡寿荣、徐默、池沙鸿、张卫民、张谷良、周晋、盛天晔、顾迎庆及女画家钱小纯、张禾、朱春秧等。
其中尉晓榕的文人雅逸,王赞的生气浓郁,杜觉民的重墨沧桑,钱小纯的质朴奇特,都形成自己的个性语言了。
五
在“新浙派人物画”异军突起、蜚声画坛的五十年代,山水和花鸟两科如何发展?
可以说是浙江花鸟、山水的笔墨滋养了人物,造就出人物的一马当先。
那么花鸟和山水两个画科如何继往续绝、传统出新?
为此,在60年,学院在潘天寿家举行了一个简朴而庄重的拜师仪式:
叶尚青、陈贯时拜潘天寿为师,朱颖人拜吴茀之为师,刘江拜诸乐三为师,孔仲起拜顾坤伯为师,分别专攻花鸟、篆刻、山水。
在五十年代,浙江美院的师资力量是花鸟最强,潘天寿、诸乐三、吴茀之“三老”长于写意,邓白先生长于工笔,后又增添了海派名宿陆抑非先生,擅没骨和小写意,陆维钊在古文诗词之余亦擅文人画,可谓人才济济,国手如云。
栽培出诸如叶尚青、陈贯时、朱颖人、卢坤峰、诸涵、刘江、洪世清、张立辰、朱豹卿、单眉月、舒传曦等第二代传人,因为学院是艺术摇篮,他们大都作为工作母机留校任教,但都能以各自的悟性学养而各领风骚。
浙江的花鸟画以其深湛的传统功底、清新的创新能力而名列全国前茅。
能在十年文化浩劫中不被埋没,卢坤峰是比较幸运的一位了。
64年他以优异的毕业创作《双鹤》获潘天寿院长高度评价而留校任教;“文革”中,他与方增先、姚耕云、陆抑非合作的《毛竹丰收》,其题材和形式创新而又保存着优秀的传统,既获得当时把持文化部的“四人帮”的认可,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赏识,成为当时中国新花鸟画的代表,一下子风靡国内外,与五十年代“新浙派人物画”异曲同工。
在同代画人中,卢坤峰最早出画册、最早办画展、最先入选《荣宝斋画谱》,其兰竹翎毛堪称国朝第一;改革开放后,他也是最早开始卖画的,似乎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比他人先知先行一步。
后来当全国的画家统统挡不往诱惑下水卖画甚至不断包装炒作求售的时候,卢坤峰却一头钻进故纸堆,赋诗填词,在书画市场中匿迹了。
——一个画中贤者。
叶尚青、朱颖人、刘江,可能还要加上陈贯时、诸涵,是“三老”的入室弟子,得乃师之真传,可是由于文革十年,有的弃艺从政,有的亦艺亦政,有的受到冲击,犹如抗战时学人说的“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造成了文脉传承的中断。
但在文革结束后,他们都立即兴废续绝,挑起传薪重担,门墙桃李繁茂,时有出蓝之势。
在教学的同时,他们还筹办起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的艺术研究团体,使上辈的道德文章得以阐发和弘扬。
历来院派师弟相授的教学,易流于陈陈相因,技法纯熟而生气全无,故齐白石说“似我者死”,潘天寿说“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者是笨子孙”。
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罢,在第二代传人中,反倒是几位不在国画系工作的画家迸出的别具一格的异彩。
洪世清早年自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分配于筹建版画系工作,曾先后师事刘海粟、齐白石、潘天寿、黄宾虹等大师,且得其衣缽真传,国油版雕乃至篆刻、摄影,无一不能,无一不精,然而其最痴迷最执著的是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传统的崇拜。
其绘画,固守传统出新;其刻石,进而意追秦汉。
在他退离教学岗位的花甲之年,迸发出惊人的毅力,集绘画、雕塑、金石、石窟、环境艺术于一体,创作出一批划时代的海岛岩雕作品,为举世所瞩目。
舒传曦不是杭州艺专毕业的,他从新华艺专毕业后赴德国留学,学成回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执教。
这位留洋回来的才子竟对潘天寿、林风眠、黄宾虹有深刻的与常人不同的理解,他和林风眠一样经历了从西方回到东方、并用东方来阐释西方的道路,但是他选择了与林风眠不同的方式,他首先在潘天寿的钢筋铁骨中找到了东方传统的支点,上溯到八大、青藤、梁楷、范宽,他认为人类艺术发展历程可用“枣仁核”来比喻,核的一边是东方,另一边是西方,它们源于一个起点,亦将汇于一个终点。
因此,在教学理论方面,他针对常人对舶来的“素描”的偏见,把素描区分为研究性素描、表现性素描和速写性素描这三种不同的形式,尤其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绘与画”这一对命题,绘重图绘,画重线描,以中国形式分析视觉艺术,诠释中西艺术殊途同归的基础。
在创作实践方面,他在透过了中国画笔墨关后,进而抓住了“韵”这一内核,实现水墨和色彩兼得,甚至还给书法式的线条留下一地。
如《金丝猴》《猫头鹰》,色彩鲜明,水墨浑厚,线条飞扬,透射出作者在画面后面不同寻常的艺术思考灵光。
朱豹卿、单眉月毕业后离开美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