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法律渊源考一.docx
《清代法律渊源考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清代法律渊源考一.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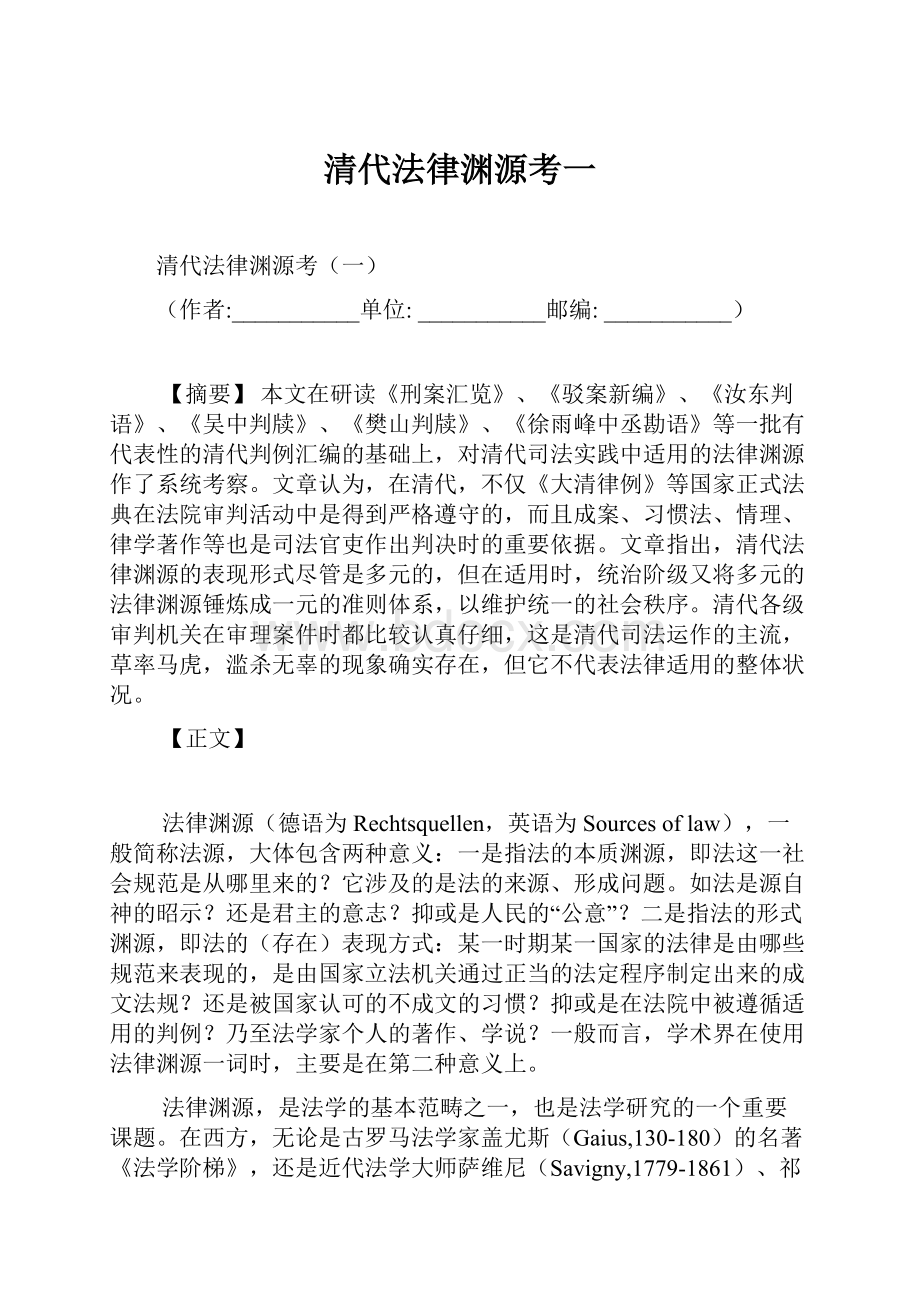
清代法律渊源考一
清代法律渊源考
(一)
(作者:
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摘要】本文在研读《刑案汇览》、《驳案新编》、《汝东判语》、《吴中判牍》、《樊山判牍》、《徐雨峰中丞勘语》等一批有代表性的清代判例汇编的基础上,对清代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法律渊源作了系统考察。
文章认为,在清代,不仅《大清律例》等国家正式法典在法院审判活动中是得到严格遵守的,而且成案、习惯法、情理、律学著作等也是司法官吏作出判决时的重要依据。
文章指出,清代法律渊源的表现形式尽管是多元的,但在适用时,统治阶级又将多元的法律渊源锤炼成一元的准则体系,以维护统一的社会秩序。
清代各级审判机关在审理案件时都比较认真仔细,这是清代司法运作的主流,草率马虎,滥杀无辜的现象确实存在,但它不代表法律适用的整体状况。
【正文】
法律渊源(德语为Rechtsquellen,英语为Sourcesoflaw),一般简称法源,大体包含两种意义:
一是指法的本质渊源,即法这一社会规范是从哪里来的?
它涉及的是法的来源、形成问题。
如法是源自神的昭示?
还是君主的意志?
抑或是人民的“公意”?
二是指法的形式渊源,即法的(存在)表现方式:
某一时期某一国家的法律是由哪些规范来表现的,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正当的法定程序制定出来的成文法规?
还是被国家认可的不成文的习惯?
抑或是在法院中被遵循适用的判例?
乃至法学家个人的著作、学说?
一般而言,学术界在使用法律渊源一词时,主要是在第二种意义上。
法律渊源,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西方,无论是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Gaius,130-180)的名著《法学阶梯》,还是近代法学大师萨维尼(Savigny,1779-1861)、祁克(Gierke,1841-1921)和惹尼(Geny,1861-1956)的作品,首先涉及的课题也是法律渊源。
[1]对一国法律渊源的研究,比对一国法律体系的研究更具有立体感和深度。
因为法律体系比较侧重于法的静态组合;而法律渊源则更侧重于法的动态运作——在一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它依据的是哪些规范?
[2]
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其实力曾达到了中国古代之最,其司法机关适用的法律渊源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丰富的。
对其法律渊源进行专项研究,不仅可以获取中国古代法律适用的典型图像,也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法律渊源在近现代中国的变异和影响,对分析所谓中国法的“本土资源”也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中国古代并无“法律渊源”一词,该词是西方语境中的概念,但由于它对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法律规范具有正确的概括力和抽象表述的能力,也由于本文研究的虽是清代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法律规范,但读者却是受过现代法律训练的专业人员。
故这里还是使用了法律渊源这一基本概念。
就中国法律史和法学史研究的现状而言,对清代法律渊源的研究尚未系统展开,在已发表的零星成果中,学者之间的认识也是不统一的。
并且往往是从法律体系的角度即从成文立法角度阐述此问题。
而笔者认为,弄清某一时期法律渊源的实际状态,必须深入到这些法律渊源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去。
为此,笔者比较认真地阅读了清代一批典型的判例文献,如《刑案汇览》、《刑案汇览续编》、《驳案新编》、《汝东判语》、《樊山判牍》、《徐雨峰中丞勘语》、《吴中判牍》、《鹿洲公案》等,有了一些心得和体会。
下面,试将其归纳总结,并向学界同仁作一汇报,以求正于诸贤。
一
在清代的法律渊源中,最为重要和基本的,当然是律和例了。
在清代,律,就是大清律,例,就是条例。
清王朝建立以后,曾于顺治四年(1647年)、[3]雍正三年(1725年)[4]和乾隆五年(1740年)分别颁布了《大清律集解附例》、《大清律集解》和《大清律例》三部正式的成文法典,最后定本律四百三十六条,附条例一千零四十九条。
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大清律吸收了唐以后各朝大法的精华,是统治阶级成熟的意志的表现,自乾隆五年定本以后,至清王朝解体,不再有增损。
而适应社会发展,不断作出调整并有发展有变化的是例,它不断得到增补,至同治年间已增加到一千八百九十二条。
[5]关于例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皇帝的诏令以及依据臣下所上的奏议等文件而作出的批示(上谕);二是从刑部就具体案件所作出的并经皇帝批准的判决中抽象出来的原则。
关于律和例在清代司法实践中是否得到严格贯彻的问题,学术界的认识并不一致。
大部分学者认为,《大清律例》是得到严格遵守的。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清代,例是得到遵守的,但律的遵守并不严格。
[6]尤其是由于例基本上是皇帝在适用律文之基础上颁发的敕令,且数量众多,因此,它的适用往往冲击了律的执行,出现了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情况。
[7]
那么,实际的情况到底如何?
笔者通过对上述判例文献的研读,分析出律例的适用,在清代共有六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对律文的严格遵守,在刑事案件中,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大清律例》“刑律·断罪引律令”条明确规定:
“凡(官司)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如不具引),笞三十。
”《刑案汇览》卷三十七还记录了皇帝上谕:
官员承问引律不当,将应拟军流以下之人错拟斩绞者,府州县官降三级调用。
[8]
因此,在清代,审案首先必须认真、审慎地引用律文是一条基本原则。
从《刑案汇览》等案例汇编来看,判案不引用律文的极少。
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时首先出现的用语往往是“查律载……”、“依……律,拟……”。
县府衙门及刑部在引用律文审理案件时,不仅反复推敲各案的具体情节,寻找与其最为妥贴(“允协”)的律文,而且在适用律文时,往往会层层分析,反复推敲,以使其最为恰当:
东抚(山东巡抚)咨:
外结徒犯内刘虎臣殴伤无服族婶刘郑氏成废一案。
查刘郑氏系刘虎臣无服族婶。
刘虎臣将其殴伤成废,系卑幼犯尊。
自应照同姓亲属相殴、卑幼犯尊长加一等之律问拟。
该省将刘虎臣依凡殴伤人成废律拟以满徒,系属错误。
应改依折跌人肢体成废满徒律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仍令专咨报部(道光八年说帖)。
[9]
有时,甚至还出现了如下改适用例为适用律的情况:
乾隆四十六年,湖北黄冈县民曾荣怀诬窃拷打徐起才身死。
湖北巡抚比照“诬窃为盗”之例,处斩监候。
刑部认为量刑尚可,但定罪不准,应改依“诬良为窃拷打致死律”处斩监候,秋后处决。
并提出:
“嗣后,遇有诬良为窃拷打致死之案,俱照此引用,不得循旧牵引,致案情不符,并通行一体,遵照办理。
”乾隆皇帝批示:
“依议。
钦此。
”[10]
第二种情况是,当没有律文可引时,审判机关一般以例文为准,“查例载……”、“依例……,拟……”也是各判例法文献中的基本用语。
如嘉庆中叶,内务府包衣旗人海寿,因违反伊父教令被呈送发遣黑龙江当差,在配不服管束,被当地将军解部销除旗档,改发云贵两广与民人一体管束。
适逢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恩诏释回。
该犯仍不悛改,时常醉闹,兹经伊母恳求发遣,内务府遂将其照民人之例发遣新疆为奴。
对该案的处理,大清律上并无专条,上述内务府的判决,完全是遵照了例的规定:
“旗下另户人等因犯逃人匪类及别项罪名发遣黑龙江等处,不行改过复行犯罪,即销除旗档,改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与民人一体管束。
又,触犯父母发遣之犯,遇赦释回后再有触犯,复经父母呈送民人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
[11]
清中叶以后,各级审判机关在处理贩卖鸦片烟、涉外贸易、华洋诉讼等案件时,基本上也都是适用条例的。
从笔者接触的材料来看,在清代的司法实践中,无律文或律文不合适时引用例的约占刑事案件的五分之一左右。
第三种情况,是对律文作扩张解释,扩大律文的适用范围。
如在《驳案新编》卷三“本夫奸所获奸将奸妇杀死奸夫到官不讳·貌应瑞”一案中,貌应瑞之妻张氏与王幅多次通奸,被貌应瑞撞破后受到责打,仍不思悔改。
后王幅买馍送与张氏,在巷道内共坐谈笑,被貌应瑞撞见,张氏被貌应瑞殴死。
初审据杀奸处为非奸所而判奸夫、杀者(本夫)各杖一百,徒三年(依律,如系奸所杀死奸妇,本夫为杖责,奸夫为绞候)。
刑部认为:
“平日未经和奸之人,一男一女面见然一处,亦涉调戏勾引之嫌,况王幅素系该氏奸夫,今复同坐说笑,其为恋奸欲续情事显然。
是同坐既属恋奸,巷道即属奸所。
律载非奸所一条,非谓行奸必有定所,亦不必两人正在行奸之时。
巷道之内,奸夫奸妇同坐一处,不可不谓之奸所。
”故此案中本夫貌应瑞杀死奸妇张氏,应定杖责,而奸夫王幅则定绞监候。
皇帝批准了此判决。
很清楚,此案中,刑部扩张解释了律文中“奸所”的含义,扩大了该条律文适用的范围,从而创立了一项判例法的原则,完成了一项新的立法。
第四种情况是既适用律,又适用例。
《刑案汇览》、《驳案新编》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如《驳案新编》卷十“轮奸·赵二虎”一案,赵二虎见狄元魁出门,其女儿狄有姐孤身在家,遂起意邀周黑虎前去轮奸。
在处理此案时,刑部不仅引用律,也适用例:
“臣部查例载,轮奸之案,审实俱照光棍例分别首从定拟。
又,光棍(例)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绞监候。
又,律载:
强奸者绞监候,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律)注云:
若以强合以和成犹非强也等语,是强奸与轮奸之犯,罪名轻重不同。
”此案中,刑部最后依律及律注将赵二虎核定为轮奸犯,并依例处以斩立决。
有时,在适用律还是例的问题上,各级审判机关会反复推敲,仔细斟酌,以达到罪与刑的最相适应。
如在《刑案汇览》卷三十五“调戏人妻致夫自尽”一案中,天津人刘添贵见李发之妻貌美,多次带人公然前去调戏,使李发气愤之极而自尽。
省巡抚在审理此案时,先是感到”棍徒扰害之例”比较合适,故适用此例将其定罪。
刑部在复审时,又认为“因奸威逼人致死律”更加适合此案,遂下令该省照律重审。
该省重审时,又感到应当适用“调戏致其夫羞忿自尽例”为妥当,故依此例判刘添贵为绞监候。
刑部最后认可了该省的判决。
在《刑案汇览》卷十九“李有亮割人生殖器”等案件中,审判机关也是依据具体的案情而审慎地决定是适用律还是例。
第五种情况,是既无合适的律文,又无相应的条例可以适用时,审判机关一般会寻找最为接近的律例,类推比照适用。
如《大清律例》有孀妇守志因亲属逼嫁自尽而加以旌表的规定,但对有夫之妇未作规定。
在《驳案新编》卷四“逼嫁有夫堂妹自刎·李金钊”一案中,刑部就认为,“查有夫之妇因亲属逼嫁自尽,例无旌表明条,……应比照孀妇守志因亲属逼嫁自尽之例……。
”又如,《驳案新编》卷五“擅用赦字世表字样拟徒·韦玉振”一案记载:
乾隆四十三年,江苏韦玉振于引述家谱内妄用“赦”字、“世表”字样,该省巡抚照违制律处杖一百、衣顶裭革、折责发落。
刑部认为,韦玉振除妄用“赦”字、“世表”之外,虽然无“悖逆之迹,然究属僭疾,非仅违制可比。
但查律例内,并无僭妄治罪专条。
例得比照引用。
查律载:
僭用违禁龙凤纹者,杖一百,徒三年。
”最后,比照此律处韦玉振杖一百,徒三年。
第六种情况是以例改律、以例破律。
由于律文变化很小,有时确实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故通过例来予以补充或修正的情况也是很多的。
这也可以理解为以例改律、以例破律。
在《刑案汇览》卷八“掖刀匪徒奸占良妇情节凶横”一案中,田二和其父田坤、弟田三都是掖刀匪徒,素来横行乡里。
田二先后奸占民妻谢氏、张氏,田三也强行奸占民妻王氏为妾。
山东巡抚和刑部山东司在定案时依据“豪势之人强夺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律”将田二拟绞监候,田坤、田三依棍徒例拟军。
皇帝在复核此案时指出:
田二等作为掖刀匪徒,本来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
现在田二又多次奸占民妻,横行乡里,实属罪恶之极。
照律判处绞监候未免太轻,应加重判以绞立决,并下旨:
嗣后,如有类似案件,均照此案办理。
此案中,原有的律文没有涉及掖刀匪徒这一层次,量刑时不够严厉。
故皇帝以例破律,创制了新的量刑原则。
在大清律中,旗人犯了罪之后,一般在处罚上可以享受比汉人轻的优遇。
但随着满清统治秩序的日益稳定,旗人和汉人的同化,有些方面再给予旗人以特权就没有意义了。
《驳案新编》卷一“庄屯无差使旗人不准折枷·方天秃”一案就反映了这种社会变化。
此案中,天津县旗人方天秃伙同船户盗卖漕米。
按照《大清律例》“名例律·犯罪免发遣”条的规定:
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
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
刑部在复审时认为:
方天秃虽为旗人,可以享受律的优遇,但在此案中情况有例外,因为一方面,方天秃驻扎在京外,与民(汉)人混居日久;另一方面,清王朝统一已久,海内外一统,“中外一家”,“民人与旗人并无歧视”,故对方天秃仍处以实徒五年,不准折枷。
并在此判例上形成一条新例:
嗣后,凡“庄屯旗人及各处庄头并驻防之无差使者,其流徒罪名俱照民人一例发遣。
”
像上述以例改律、以例破律的情况在《刑案汇览》、《驳案新编》中还是比较多的。
但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在清代,律文已经不重要了,或者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例的地位高于律。
而只能说,由于乾隆五年以后,清政府不再对律文进行修改和补充,故它对以后社会的发展变化无法作出适时的调整,加上律文比较原则,数量比较少,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统治阶级不得不用例来适应这些变化,对律文规定的“盲点”进行救济。
清代律少例多,以及律不变例常变,就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
第五种情况,是以新例破旧例。
乾隆五十六年江苏省拿获私盐罪犯谢鸿仪、孙元梅等。
孙元梅是监生,窝藏私盐有四千斤之多。
按旧例“监生犯事,罪应发遣者,例只发往当差”,不必为奴。
刑部认为,孙元梅“恃符庇匪”,不能因他是监生就可以免其为奴,“应将该犯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乾隆认为刑部的意见非常正确。
于是在名例律的“徒流迁徙地方”条后续纂了一条新例:
“进士、举贡、生员、监生犯事,如只系寻常过犯,不致行止败类者,仍照旧例办理外;若系党恶窝匪卑污下贱,罪应发遣黑龙江等处者,俱照平人一例问拟,发遣为奴”。
[12]
这种以新例修改旧例的判例,在《刑案汇览》和《驳案新编》中比比皆是。
它实际上是通过颁布新例开创了一项新的判例法原则。
有时,还会从这种以新例破旧例中诞生一系列新的条例。
比如,在乾隆年间,曾发生了这么一案:
王学孔、敖子明于乾隆三十六年、三十九年间多次盗坟剥取尸体之衣服出卖。
按照律的规定应拟绞监候。
但因为二犯是过了三年后才被抓获的。
遵乾隆三十九年的上谕:
“凡有重罪应入情实罪犯,经二、三年后始行就获到案,其本罪如系应拟斩绞监候者,均著改为立决。
”[13]
据此上谕(新例),刑部将王学孔、敖子明改为绞立决。
案件经三法司核拟于乾隆四十年上报皇帝以后,乾隆进一步批示:
“刨坟绞犯逃后二、三年被获之王学孔、敖子明,仿照上年谕旨拟改立决一本所办未免误会朕意。
前旨所云凡有重罪应入情实人犯,经二、三年后始行就获,应改为立决者,原指谋故杀等犯情罪重大者而言,以其事关人命,应即抵偿。
若复潜窜稽诛,其情尤为可恶,一经弋获,自应决不待时,以戟凶恶而申宪典。
若此等刨坟为首及三次人犯,虽例应拟绞入于情实,然皆贫民无奈为此,有司民之责者当引以为愧,而其犯实无人命之可偿也,即入本年秋审情实足矣。
有何不可待而改为立决乎?
朕办理庶狱,凡权衡轻重,一准情理之平,从不肯稍有过当。
王学孔、敖子明即著照此旨办理。
嗣后问拟斩绞监候之犯,经二、三年后始行就获者,何项应改立决,何项仍应监候,并著刑部悉心核议酌定条例具奏。
余依议,钦此。
”据此批示,刑部整理出有关人命应拟斩候者五十三条、应绞候者六十九条内,如犯罪拒捕杀人等类与谋杀、故杀情罪相等者,共计六十七条,[14]若脱逃至二、三年后始行就获,均应即改立决外,寻常命案如斗杀误杀,本出无心为从加功,首犯业已拟抵,及尊长致死卑幼、长官致死部民并一切被逼受累死由自尽等项,共计五十五条,虽其中间有所犯情节较重秋审时应拟情实之案,但其犯案之时尚非有心藐玩,则脱逃被获稍缓其须臾之死,以待秋决,亦属情法适平,应仍照本律本例拟以监候,秋审时入于情实办理。
[15]
在律例的适用方面,刑部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主要承担者,起着核心的作用。
从大量判例卷宗来看,刑部在复核各地上报的案件时,不仅非常仔细、认真地弄清犯罪事实,寻找最为适合于此案的法律渊源,而且常常以“事关人命,未便率复,应令该抚再行详核……”等为由,驳回让地方重审。
有些属死刑以下的案件,或地方早已审结且已执行的案件,如刑部在审核地方上报的名册中发现有问题,也会毫不犹豫地作出改判的决定。
如道光九年刑部的一项说帖(刑部内部的意见书)记述了如下一案:
苏抚(江苏巡抚)咨:
道光七年冬季分外结徒犯一案。
查:
册内赣榆县民皮常刃伤孟金一案。
查律载:
“过失伤人,准斗伤依律取赎”。
注云:
“或因升高险足有蹉跌累及同伴,或共举重物力不能制损及同举物者。
凡初无害人之意而偶致伤人者,皆准斗伤收赎”等语。
此案皮常与同主雇工孟金素无嫌隙,因一同铡草喂牛,该犯将刀提起,孟金右手伸进刀下取草。
该犯将刀失手落下,以致铡落孟金右手。
情异争斗,伤非意料。
正与过失杀律注所称“初无害人之意,偶致伤人者”情事相同。
自应照过失伤律收赎。
该抚将该犯照刃伤人律拟徒,殊未允协。
惟该犯业已发配杖责,遇赦减释,未便再追赎银,以致重科。
应于稿尾声明更正备案(道光九年说帖)。
[16]
一般情况下,刑部感到总督、巡抚所判不合适,就将其驳回重审。
重审时总督、巡抚一般都照刑部的意见办。
有时上下几次来回,督抚也不能违背刑部的意见。
但有时情况也有例外,据《驳案新编》卷十“谋杀人从而加功减一等·葛高氏”一案记载:
刑部认为将葛高氏拟(充)军殊为允协,驳回让其重审。
而山东巡抚则认为:
葛高氏虽与葛秉学通奸,但后者起意谋杀她丈夫葛秉魁时,葛高氏未与同谋。
葛秉学逼令她帮砍,并声言如不砍,也杀死她。
葛高氏顾及性命,不得不取斧帮砍了两下。
但此时,葛秉学已经砍了二十二刀,即使没有葛高氏的帮助,葛秉魁也必死无疑。
故葛高氏与葛秉学还是应有所区别。
所以,拟“谋杀人从而加功者绞监候”律,因未同谋而量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最后,刑部也同意了巡抚的判决。
有学者认为,在适用律例时,皇帝起着关键作用。
中国的司法实践都是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的。
“居于复审制度顶点的皇帝不仅对需要比附的案件,而且对所有上奏案件的原案,都享有不受现存成文法或自己以前所下判断拘束,自由地作出最终裁决的权力。
……换言之,在这种制度中皇帝发挥着两种不可或缺的特殊功能。
一个功能是居于以成文法为根据而展开的复审制的顶点,通过保证脱法擅断的行为受到惩罚,监督并强制着官吏们严格遵循成文法。
但皇帝的另一个功能却在于自由地改变官吏们严格依照成文法作成的判决原案,以超越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的方法来求得实质的平衡。
”[17]
上述说法与清代司法实践并不完全相符。
虽然,在理论或制度上,皇帝在适用法律时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
但事实上,皇帝在判案时,也不是能随心所欲的,他也要受当时的各种社会关系、统治秩序、政策因素等的制约。
《刑案汇览》中有一个案件,皇帝阅后认为不妥下令臣下重审,但刑部官员却固执地抵制住,最后,皇帝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刑部的意见:
“晋抚(山西巡抚)咨:
孙伦元因窃锯孙守智树枝,被殴后自缢身死一案。
查:
孙守智系孙伦元无服族孙。
因孙伦元窃锯树枝,该犯用枣木铁鎝钩背殴伤孙伦元右,并臁肕偏裹骨折。
嗣孙伦元因行窃被殴,无颜做人,羞愧自缢身死。
职等查孙伦元身死之处,系行窃败露,轻生自尽,与人无尤。
惟孙伦元系孙守智无服族祖,尊卑名分犹存。
该抚将该犯依‘折伤成废满徒’律上加一等,拟杖一百,流二千里,与律相符,应请照复。
奉批:
究因尊长犯窃所致,应令再行查核等因(显然,皇帝认为处刑太重了一点)。
遵查:
亲有养赡之义。
故‘相盗律’内,得以服制递减、免刺;若有杀伤,仍以本律从其重者论。
所以轻窃盗而重杀伤也。
职等检查,并无办过此案成案。
公同酌核,应请仍照前议照复。
奉批:
既无成案,只可照复(嘉庆元年说帖)。
”[18]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皇帝的意志都是得到刑部的重视和执行的,修改原有的律文以及条例,创设新例,主要是皇帝的意志。
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在大部分情况下,皇帝也是严格遵循既定的法律行事的,他还常常提醒各级司法官吏体察其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执法公正的良苦用心。
在《驳案新编》卷三十一“斩候重犯毋庸声叙不足蔽辜改拟立决·窦十”一案中,窦十持刀砍死夏喜,又砍伤夏三、张禄等四人,畏罪逃逸,后被抓获。
巡抚审明定拟,并称该犯情罪可恶,仅按律拟斩监候不足蔽辜,请旨即行正法。
乾隆批示:
“此等淫恶凶犯,情节固为可恶,但按律拟以斩候,于法已无可加。
若因其情罪较重,只须赶入本年秋审情实,不使久系稽诛。
尚非决不待时之犯,乃声叙以为不足蔽辜请即正法,恐无识者转疑为有意从严。
所办未免过当。
朕办理庶狱,惟期公当,不肯稍存畸轻畸重之见。
内外问刑衙门,均当体朕此意。
著传谕各督抚:
嗣后如遇此等案犯,按律定拟后即夹片声明,赶入本年秋审情实,较之寻常案件归入下年秋审者已属从严。
毋庸将不足蔽辜字样声叙。
此案除交刑部存记办理外,并著传谕国泰及各督抚奏事之便谕令知之。
钦此。
”笔者对《驳案新编》的所有案例作了分析统计,在三十二卷所收总共三百十二件命案中,皇帝推翻刑部的判决作出改判的只有二十八件,占全部案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在刑部上报的案卷上,只是批:
“旨……,余依议,钦此。
”“旨,依议,钦此。
”“旨……,依拟应斩(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
”只有极少数案件,皇帝才推翻刑部的意见,作出新的判决。
至于不顾律例,不考虑刑部的意见,不顾具体的案情,随心所欲地乱判的事例,从笔者接触到的案卷来看,还没有过。
[19]
事实上,皇帝改变律、例的适用,一般都是有其相当理由的,下面试举几例:
康熙二十年,理藩院处理一案:
盗马罪犯阿毕大等五人,被依律判处斩立决,家产妻子,则给失马之人为奴。
理藩院上报案情后,康熙指出:
“朕念人命关系重大,每于无可宽贷之中,示以法外得生之路。
《书》所谓罪疑惟轻也。
阿毕大等,家产妻子,既给失马之人,若本犯免死,给与为奴,则失马者,得人役使,于法未为不当。
嗣后著为定例”。
[20]
此案中,皇帝改变法律适用的主要理由,在于减少不必要的杀戮(盗马毕竟不如谋反、谋大逆等罪行对统治阶级有致命的威胁),让罪犯为失马者服役干活,于经济上考虑也是合适的,有利于稳定社会的秩序。
乾隆二十四年,贵州县民吕明善与卢氏通奸,为达到长期霸占卢氏之目的,在一次搬家途中乘卢氏不备,用刀捅死了其丈夫吕明弼,并持刀威吓卢氏一起移尸弃沟。
当时,卢氏虑吕明善凶恶未敢声张,仅将杀人凶刀捡藏。
后遇乡约,卢氏即上前哭诉前情,并交出凶刀。
乡约等立将吕明善抓获送官。
该省巡抚将吕明善依奸夫起意杀死亲夫例拟斩立决,卢氏依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不知情绞监候律拟绞监候。
刑部虽指明了巡抚适用法律上的一些问题,但仍维持了原判。
案子送到皇帝处,乾隆批示:
“旨:
吕明善著即处斩。
卢氏本不知情,见夫被杀,当即哭喊,因迫于凶悍,勉强隐忍,密藏凶刀,一闻乡约访查,即交出凶刀,将吕明善拿获,以雪夫冤,实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
著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
”[21]
这里,乾隆改变了法律的适用,主要是认为此法律太过于僵化,也太过于严酷。
因为卢氏有通奸之过,但无谋杀丈夫之心,处以死刑似太过分。
[22]
嘉庆初年,湖北安襄郧荆道胡齐仑私扣军需二万九千余两,并捏报战果,骗得晋升。
事发后,被依“侵盗仓库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斩监候”之例,判决斩监候。
皇帝批示:
胡齐仑“今业已动刑监禁一年之久,或致病弊,转得幸逃显戮。
然予以斩决,在胡齐仑虽不足惜,而于本律究有所加。
朕详慎庶狱,俱系按例办理,从不肯有意从严。
胡齐仑着即处绞,余依议。
将此通谕中外并领兵大员及现办军需者知之。
钦此”。
[23]
此案中,嘉庆作出改判,表明了皇帝的良苦用心:
既要避免由于长期拘押犯人如病死则会使其逃避法律惩处的遗憾,又不愿随意加重法定的刑罚。
故最后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将斩监候改为绞立决,绞刑比斩刑轻,但立决又比监候重,两相抵销,在观念上取得执法公允的效果:
既不能让当事人逃避法律制裁,又要公正执法,不违背律意。
嘉庆十年六月二十三日,皇帝在阅刑部上报嘉庆九年河南省秋审情实册中赵芳一案时指出:
此案赵芳先与胡约之母赵氏通奸,又因见胡约之妻向氏年轻貌美,起意强奸不从。
该犯因胡约向其借钱,即主使将向氏殴逼。
向氏仍不依允。
该犯辄喝令胡约将向氏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