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李约瑟之谜学术自治与科学革命游五岳.docx
《直面李约瑟之谜学术自治与科学革命游五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直面李约瑟之谜学术自治与科学革命游五岳.docx(3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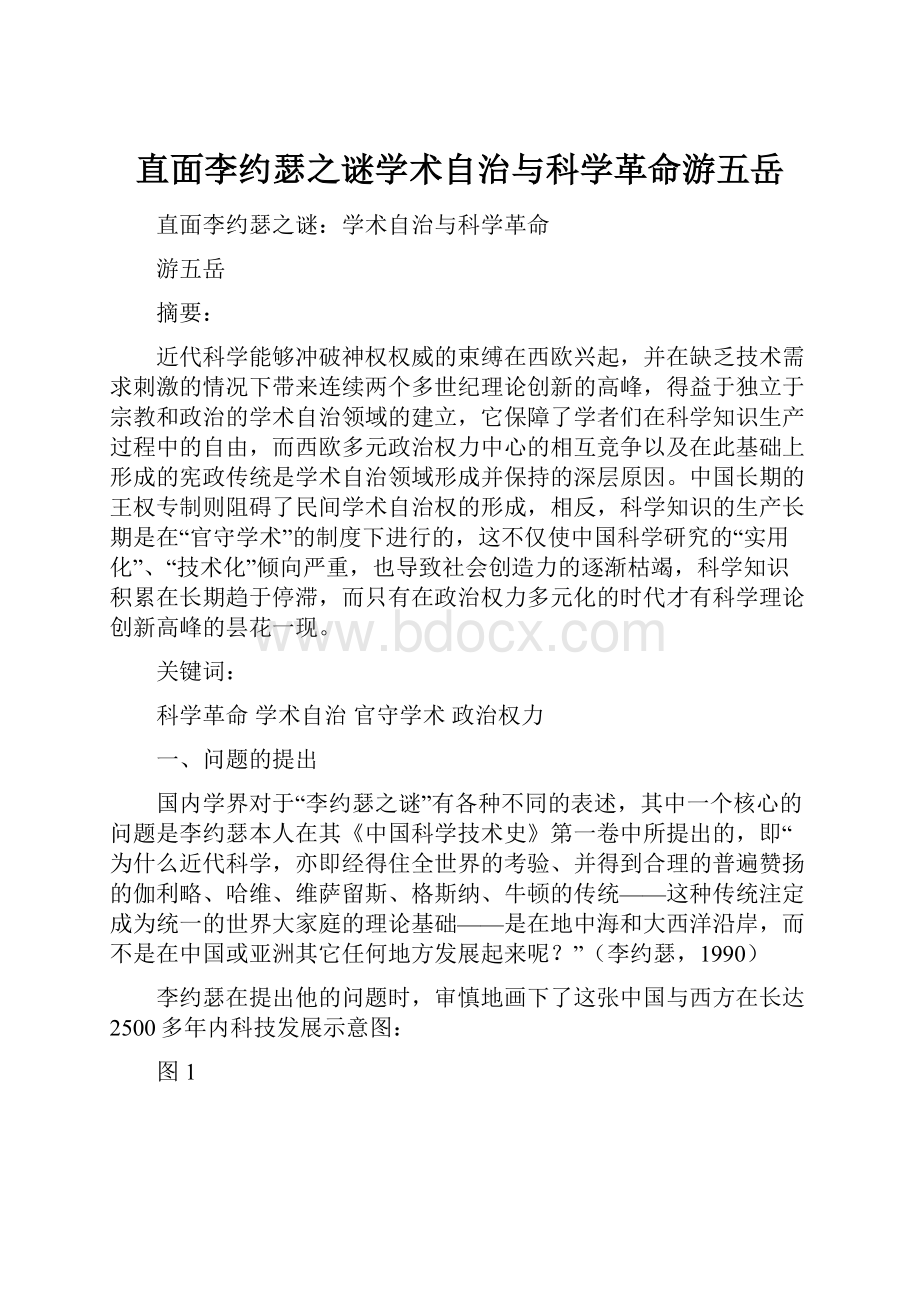
直面李约瑟之谜学术自治与科学革命游五岳
直面李约瑟之谜:
学术自治与科学革命
游五岳
摘要:
近代科学能够冲破神权权威的束缚在西欧兴起,并在缺乏技术需求刺激的情况下带来连续两个多世纪理论创新的高峰,得益于独立于宗教和政治的学术自治领域的建立,它保障了学者们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自由,而西欧多元政治权力中心的相互竞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宪政传统是学术自治领域形成并保持的深层原因。
中国长期的王权专制则阻碍了民间学术自治权的形成,相反,科学知识的生产长期是在“官守学术”的制度下进行的,这不仅使中国科学研究的“实用化”、“技术化”倾向严重,也导致社会创造力的逐渐枯竭,科学知识积累在长期趋于停滞,而只有在政治权力多元化的时代才有科学理论创新高峰的昙花一现。
关键词:
科学革命学术自治官守学术政治权力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学界对于“李约瑟之谜”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李约瑟本人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所提出的,即“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住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它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
”(李约瑟,1990)
李约瑟在提出他的问题时,审慎地画下了这张中国与西方在长达2500多年内科技发展示意图:
图1
资料来源:
胡菊人,1978
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中西方科技发展的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在于,中国维持了连续稳步的缓慢增长过程;而西方则曾经突然跌落并长期停滞在谷底,在1500年以后科技发展突然开始高速增长,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保持了这种迅猛态势。
那么让我们先来看看西方在这几个世纪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金观涛等人(1982)统计了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末这两千五百年内中西方近两千项科学技术成果,并将它们分为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部分,分别对中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里科学技术成果的净增长作出了统计,以下是西方1500年到1900年各类成果的表现:
图2
图3
从以上两幅图可以看出,从16世纪开始一直到18世纪中期,西欧科技发展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由科学理论的大量出现所带动的,同一时期科学实验也呈现增长态势,而18世纪中期开始,技术也开始加速增长,整个19世纪技术、科学理论和实验齐头并进,使西欧科技发展曲线急速攀升。
16世纪开始科学理论和实验的加速与18世纪中期开始的技术起飞显然分别与西欧两场重要的变革有关——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然而技术起飞远在科学理论起飞之后2个多世纪,并且大量研究表明,科学革命并非工业革命的前提,实际上“19世纪前技术很少直接得益于科学,它们的目标与方法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E.E.里奇、C.H.威尔逊等,2003),科学与技术真正结合并形成循环加速机制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North,1981)。
那么问题就在于,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三个多世纪),没有技术需求和利润动机的推动,科学理论成果为何能保持持续高速的增长?
并且,一旦想到这是一场兴起于天主教神学支配下的旧科学范式仍主导着科学领地时代的革命,并因此曾经引发与宗教之间的残酷斗争,近代科学如何“一发而不可收”、取得斗争的胜利,就成为更加有趣的问题。
而反观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从下图金观涛等(1982)作出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来看,中国在漫长的科技发展过程中却从未出现由科学理论主导的科技增长,技术水平一直远远高于科学理论和实验而几乎决定了各个时期科技发展的总水平,并且科学理论成果大约从7世纪一直到17世纪(除了中间在12世纪左右有小幅增长以外)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13世纪左右成为最先被西方赶超的部分,此后技术、实验以及总的科技水平也从大概14世纪开始增长趋平。
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古代这种科技发展的“技术化”倾向以及科学理论的率先停滞呢?
它们与“近代科学未在中国兴起”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
图4
备注:
图中曲线是取对数值绘出的;A、B、C、D分别为西方的理论、实验、技术和总分赶上中国的交叉点。
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单独对各个朝代科学理论成果的净增长做横向比较的话(见下图),还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科学理论的“小高峰”总是对应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权力多元化时期(如战国、东汉魏晋南北朝、两宋),而低谷则对应着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时期(如几乎整个隋唐和明朝)。
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图5
二、文献回顾
对于“近代科学为什么只在西方而不是中国兴起”这个问题,目前为止学界已经有很多种解释,其中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首先是思维方式决定论,唐君毅(1947)提到中国文化缺乏主客之对待意识,缺乏分的意识,因而中国缺乏科学精神,刘志一(1988)也指出东方人注重应用效益,轻视理论思辨;注重经验积累,轻视实验检验。
但是早在战国时期,墨家就已经建立了“一种可以作为实验科学基础的思想体系”和“堪称为科学方法的一套完整理论”,(李约瑟,1975)它与西方近代科学“种子”的古希腊科学不仅极为相似,且处于相当水平(见正文第五部分)。
所以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为什么这样一套科学思想体系没有被后世继承并发扬。
其次是地理环境影响论,有学者指出,欧洲开放式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各种文明的交流,尤其是12、13世纪古希腊文明的回归直接促成了中世纪后新科学的破土而出,而地理环境天然的封闭性基本上隔绝了中华文明与其他异域文明的相互冲击与交互。
但是这类学说却无法解释,当地理环境的束缚被逐渐突破,西方科学知识在明末获得传入我国的机会时,这一“西学东渐”过程在中途却被刻意地打断了,有证据表明,从1723年至鸦片战争,中国几乎没有再引进任何新的西方数学(Engelfriet,1998),显然这需要从中国自身的非地理环境因素寻找原因。
此外,还有制度说。
这其中又包括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体制,以及科举制等解释。
戴尔蒙德是中央集权制这一学说的代表之一(Diamond,1999),但是他并没有分析对近代科学的兴起,中央集权或多元政治权力竞争的具体阻碍或促进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而李约瑟本人则是官僚体制说的代表,他断言官僚政治“绝对阻碍了商人的兴起”(李约瑟,1975),因此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无法结合在一起,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科学革命并不是在技术需求或利润的推动下发生的,尚无直接资料或研究成果表明商人阶级的兴起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
林毅夫(1995)则认为是科举制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研究,但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会有科举制这种对科学知识生产具有负向激励效应的制度?
这背后的原因是否与我国古代科学的发展特征具有更为根本的联系?
另外,科举制本身也曾经起到鼓励人力资本在科学知识上投资的作用,如唐朝时就设有“明算科”和“医举科”来分别来选拔具有较高数学和医学水平的人才,为什么这种科目后来就取消了,而转向越来越单一、僵化的考试形式了呢?
同时,这三种制度学说都没有从正面分析中西方科学研究及教育的制度安排究竟有怎样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显然对于近代科学的兴起与科学革命有更为直接的意义。
本文试图从中西方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具体制度安排出发,分析这种制度性的差异对中西方科学发展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形成这种制度性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在此基础上对前文所提出的关于“李约瑟之谜”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尝试性的解答。
本文以下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以背景介绍引出“制度”解释的角度;第二部分介绍西欧科学革命发生所依赖的科学教育研究领域的制度安排,即学术自治团体的形成;第三部分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教育研究领域的制度安排,指出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中“官守学术”对民间学术自治领域的替代;第四部分是在前文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科学知识“技术化”倾向的制度性解释;第五部分是对西方学术自治领域形成原因的探讨,提出“多元政治权力中心的竞争有利于学术自治领域形成”的假说,并以中国古代科学理论高峰期的史实对此假说进行验证;第六部分讨论中国专制王朝维持“官守学术”的科学生产方式、压制民间学术自治领域生长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王朝后期科学知识生产趋于停滞的原因;最后一部分是结论性评论和进一步研究任务概述。
三、本文的逻辑与历史证据
(一)“野火烧不尽”?
1600年布鲁诺因对“哥白尼学说”的信奉与宣传被执行火刑;1616年教会宣布哥白尼的学说封禁,直到一切和被奉为教条的天文学观点不一致的地方从哥白尼《天球运行论》中被清除为止;1632年教会禁止伽利略《对话》的发行,同年10月,罗马宗教法庭传审伽利略,他虽年事已高且有病在身,又有托斯卡纳大公爵费迪南二世的求情和医生的证明,但教皇却丝毫不肯宽容。
1633年1月20日,伽利略被担架抬着赴罗马受审,经3个月四次的严酷刑讯,于6月22日结案,被判终身监禁。
(鲍·格·库兹涅佐夫,2001)
在同一时代的东方,明朝的统治者们也正颁布着严酷的法令制止天文历法知识在民间的传播:
“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沈德符,1959)。
同时,为防泄密,对于官府的天文机构也加强管制,规定钦天监生员完全实行世袭制,“凡本监人员,洪武六年令,永远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明会典》·卷一百七十六)。
然而在西方,教会神权的强力压制并没有能够阻止这场科学革命的迅速扩散,当哥白尼的学说被封禁时,当伽利略被软禁在阿瑟提的别墅里时,革命却仍在进行。
在大多数大学里有关哥白尼思想的研究、教学和尝试性批判仍在继续,很大程度上并未受到干扰;甚至在伽利略事件的75年前,哥白尼躺在弥留的病床上时,他的《天体运行论》一送到印刷商手里,全欧洲及英国的学者们很快就人手一册了(托比·胡弗,2010);而伽利略那些颇具争议的著作也很快冲破禁令由荷兰出版商出版了。
与之相比,中国明王朝统治者们的禁令却似乎有效得多。
弘治十一年,由于朝廷天文历法人才奇缺,于是颁布诏令“访取世业原籍子孙,并山林隐逸之士,及致仕退闲等项官吏、生儒、军民人等,有能精通天文、历数、阴阳、地理及五星子平、遁甲大定、六壬、龟卜等术者”以征召天下时,民间却“卒无应者”,(《明会要》·卷二百二十三),以至于明代只能一直使用元朝的《授时历》,历法误差越来越大,交食不验成为朝廷头痛的问题,但已无人能改历了。
一个很自然的疑问是,在西方这场持续了差不多3个世纪的科学革命过程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能够在天主教教会无情的打压下保护着这些新科学体系的支持者和继承者们,使他们不断创造着近代科学“高峰”式的增长?
而在中国,同样功能的制度支持是否是缺失的呢?
(二)西欧的学术自治制度
先来看一看在这次科学革命中有所建树的科学家们的活动背景。
据统计,1450年到1650年之间出生的被认为有资格收入到《科学家传记辞典》之中的欧洲科学家,大约87%都接受过大学教育。
更重要的是,这一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仅受过大学教育而且还在大学任过职。
在1450年到1650年期间,这一比例是45%,1450年至1550年是51%。
(Gascoigne,1990)而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开普勒和牛顿这些开创性学说的建立者,无一例外都是那些统一的欧洲经院大学的非凡产物。
而一项针对英国科学家的数据统计表明,17世纪末65名因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而被载入《国家传记辞典》的英国科学家中,75%的人曾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还有5%是其他大学的毕业生。
同样,1663年伦敦皇家协会的115名成员中65名成员在大学学习过。
(M.Hunter,1981)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科学家移向科学思想,同样会发现大学对于科学革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16、17世纪,那些发生了巨大变革的科学领域,那些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的科学领域,恰恰正是大学里最突出的课程。
“我们要把哥白尼到牛顿的科学革命与天文学和宇宙论领域的巨大革新联系起来,与物质理论方面的转变联系起来(从亚里士多德的元素论到微粒、机械哲学的转变),与新的运动理论、机械规律、动力学、惯性和动力思想联系起来,与接收普遍性自然规律支配的无限空间论和同质性宇宙论的胜利联系起来,而且至少要与定量的出现,尤其是在牛顿《数学原理》中达到顶峰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联系起来。
自13世纪以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海桑及其评论家为中心、以传授‘三艺’‘四艺’为基础的大学形成以来,所有这些广泛的科学领域——天文学、物理学、数学,以及更广泛的自然哲学——均深深地植根于大学的土壤中。
”(瓦尔特·吕埃格等,2008b)而一个反面的例证是,这场科学革命对于那些处于大学边缘领域的探索并不太成功,大量的化学实验、海上航行、农业、矿业和其他科学探索活动,都是在大学之外进行的。
而17世纪以来,在欧洲大学之外还出现了科学家们聚集活动的新领域,那就是各种科学学会。
科学学会在整个欧洲的扩展打破了大学作为高级教学和科研场所的垄断地位,有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关于理想科学活动蓝图的规划均不是在大学或学院中完成的,而是在一些专业性更强、设备更齐全、更独立的研究机构或研究社团中完成的”。
(M.Ornstein,1928)17世纪也被称为“第一个俱乐部和学会的时代”(E.E.里奇、C.H.威尔逊等,2003)。
这一时期成立的最著名的学会莫过于一直延续至今并已成为英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伦敦皇家学会,它在使英国成为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科学革命中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胡克,波义耳,牛顿,哈雷等人都是皇家学会最早的一批会员。
那么这一时期欧洲的大学和科学学会作为承载科学学者们学习、教育、研究等活动的主要空间,是否已经能够为他们提供有效地隔离宗教或其它外部世俗权力干涉的保障了呢?
换句话说,它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独立于宗教或政治的自治权呢?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大学和科学学会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它们的社团法人地位以及享有的相关自治特权。
于12、13世纪兴起于欧洲的大学多是由民间教师和学生自发组成形成的,它们的社团法人地位基本上兴起不久就得以确立,自治的特权一些来自最高权威,皇帝(对于波伦亚大学的“居住”宪法)和教皇(对于巴黎大学的1215年的章程,或“科学之母”教皇谕旨),其他一些来自地方政权,在巴黎、牛津或萨拉曼卡是来自国王,在意大利是来自公社。
(雅克·韦尔热,2007)而科学学会则源于欧洲学者和科学爱好者们自发性的讨论聚会,其法人身份多是在17、18世纪通过国王的特许状获得。
如英国皇家学会最早的活动兴起于17世纪40年代伦敦格雷山姆学院定期讨论新哲学和自然科学问题的聚会,它于1660年正式形成为社会团体,并在1662年、1663年、1669年陆续获得了三个来自查理三世的特许状,确认了其法人地位。
通过研究社团法人以及相关自治特权的具体权利特征,我们能够对大学和学会为科学知识生产与传播提供的独立于宗教或政治权力的保护有更清晰的了解。
对于大学和科学社团来说,自治法人的身份首先赋予了它们在进行科学教育或研究的方向和内容上的自主权。
在大学,从12、13世纪起,授课许可证的颁发无须再通过教会或国家,而是由大学内部自行管理;学者们可以不受中央政府和宗教权威的左右设置课程、安排讲座和公开讨论,他们“确定了以基础性科学读物为核心的课程和讲座,其中涵盖了那几个世纪(12、13世纪)开始为人所知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书籍。
所有这些著作共同确立了一个新的自然主义框架。
这种新的智识议程不但属于彻底的自然主义研究,而且还被置于研究过程的核心。
”(瓦尔特·吕埃格等,2008a)从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法国各大学已经普遍开设了有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哲学、伦理,希腊化时期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天文学以及包括阿拉伯的哲学和科学在内的多种课程。
(宋文红,2010)下面这个事例为大学在知识选择上的自主权提供了很好的例证,1215年,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与形而上学著作在巴黎成为禁书,但很快发现禁令无法操作,因为同样书籍在牛津,甚至在图卢兹都被人们阅读着。
因此在约1252-1255年间,禁令被官方解除。
而巴黎大学艺学院的非正式阅读书目显示,在1230-1249年间,在考试课程规定的文献之外,学生们仍可以阅读亚里士多德的禁书。
巴黎大学的全体教员甚至在1255年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了亚里士多德自然著作的阅读以及讲授时间。
(贺国庆等,2009)
这种自主权也使大学在科学革命前夕以及过程中成为对新旧观念进行严肃批判的主要阵地。
保罗诺尔曾这样描述这一时期的大学,“它们是生存状态、论文交汇点,其实体并不依赖于有形地点,而在于特权、辩论和个人。
因此该传统培养出来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及学术辩论造就了天文学革命和权威变革。
”(Knoll,1975)大学里经常有随意性辩论会,学院的全体人员参加,听众可以随机提出问题,其原则使人联想到现代记者会,无论什么主题都可涉及,还有不定期的公开讨论和讲座,出席的人们想出涉及重要逻辑及哲学的问题供人论证,同时提出新的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革命一个很伟大的转变就包括对亚里士多德学派关键理论所进行的一系列反驳,而大学不仅培养了那些既精通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传统理路体系,又非常熟悉其理论体系内部的许多反对意见的学者们,同时更为这种辩驳提供了一个合法性、公开性场所。
伦敦皇家学会组织科学研究活动的方式也体现了极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成员可以自由确定自己的科研方向。
在每周的例会上,会员们可以把自己的新研究或新的实验介绍给其他学者,引起大家的讨论。
学会还会在会议上把具体的研究项目分配给有兴趣的会员个人或小组,并要求他们及时向学会汇报研究成果,学会将全力资助这些项目的研究。
(Thomas.Sprat,1667)
对于科学革命时期的大学和科学学会来说,更重要的是司法特许权以及以法人的名义起诉或被起诉权利的获得。
教皇们为大学建立了一些独特的司法权,负责对大学特许权的所有侵犯进行处置,它们不仅使大学学者避开世俗司法,甚至在某种方面避开地方的教士司法。
(石广盛,2007)而在伦敦皇家学会1662年的特许状中规定“从现在起可以凭借皇家学会的名义永远享有起诉与被起诉,被传讯与应诉,以及辩护的能力,不论在法庭或其他地方,不论所面对的是何种正义、审判或是人物……在所有或任何单一的行为、申辩、起诉、抗议、事件中,无论其属于何种性质、形式,它们作为一个法人组织将会和英格兰王国的臣民、自然人拥有同样的能力。
”(RoyalSociety,1912)这就使得学会中的每个个体成员的利益和权利受到了团体身份的直接保护,避免了与外部强权的直接对抗。
此外皇家学会社团法人也无法被判处任何形式的入狱或肉体的刑罚,更无法被剥夺公民权利。
正因此皇家学会在获得法人资格之后也真正摆脱了宗教的干涉以及宗教法庭的威胁。
此外大学和皇家学会还取得了出版印刷的特权。
在大学周围形成了由大学控制的,图书快速传播并保证文字质量的系统。
若干大学授权的书商如获得一份学院使用的主要文献的样本,经博士委员会审查之后便可流行。
(雅克·韦尔热,2007)这种特权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自由思想不受政治和宗教审查的侵扰,为知识生产活动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同时也是教会禁书令往往难以有效的重要原因。
而在伦敦皇家学会1662年特许状所规定的特权中,首先被提及的就是关于出版印刷的特权。
皇家学会社团法人根据国王的特许“拥有和被授予……全权和权威随时推选,任命,以及指定一个或更多的印刷商和印刷工,雕刻师,并可以通过加盖公章和会长签名的文件授权印刷商、印刷工、雕刻师印刷有关或涉及皇家学会文本,内容和事务”的特权。
(RoyalSociety,1912)1665年3月6日,《皇家学会哲学学报》第一期出版,在杂志的第一页特意标出了“特准出版”的字样。
此后,皇家学会利用出版特权印刷出版了大量的科学和科学史的著作,以及大批的皇家学会档案文献。
借助于这些科学杂志或者学术杂志,学会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其学术成员组成的圈子之外,使大学教授、爱好数学的教师、数学实践及私人贵族科学家能跟上科学或者学术进步的步伐。
(E.E.里奇、C.H.威尔逊等,2003)
可见,在科学革命之前,欧洲于12、13世纪就在制度上建立了受法律和特权保护的学术自治区域,使非教会精英们的研究能够自主地开展,并有权利发布其思想,即使这种活动违背了学术权威或传统,也被认为是合法的。
这种制度在科学革命中得以扩展并完善,它创造的自治空间容许人们讨论新的科学体系的优劣,并确保了新体系支持者的人身安全。
正如本杰明-纳尔逊所说,“哥白尼革命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哥白尼假说是否已被确立的问题,而是非官方授权的事实发言人能否最终就真理及其认证发表主张,是基督教神学之外的任何人能否就世界组成这一问题作出权威表述”。
(Nelson,1981)所以,“近代科学的突破不仅是智识突破,更是制度突破”(托比·胡弗,2010)。
这种“制度突破”所创造的学术自治领域为那些“反权威”、“反传统”的创新思想提供了进入公共话语的机会,使人们能够有争论这些见解优劣的自由空间,并辅助创新者们与“权威的”“传统的”知识体系相抗争,从而推动了近代科学的理论创新突破了神权和政治权力的控制最终成为席卷整个西欧的“科学革命”。
(三)中国的“官守学术”
那么,这种学术自治的团体或空间在中国有没有生长起来呢?
与欧洲中世纪由民间学者自发组织形成的大学相似,中国在唐末五代也出现了一种民间自发的教育机构——书院,并曾在宋代发展成为我国古代的教育和学术中心。
然而这种由私人藏书、读书之所演变而来民间书院很快就开始了“官学化”的进程。
南宋时州县官学教官兼任书院山长的情况就时有所见,景定四年(1263)还有“诸授书院山长者并视州学教授”的诏令发表。
(欧阳守道,1998)这种趋势在元代进一步加强,书院的山长必须经过中央礼部或行省的任命或备案,并由官派的“直学”掌管书院的钱粮收支书目。
明朝初期,朝廷曾两次下令,改天下山长为训导,将书院并入地方官学或者社学。
(李才栋,1993)并且明朝统治者还曾多次以“倡其邪学,广收无赖”、“聚党营私”等名义对民间书院进行毁灭性打击。
(稽璜等,1987)而清朝则命令所有书院皆由封疆大臣控制,并由政府拨给经费,书院彻底官学化,沦为科举的附庸。
可见,虽然最初同是民间自发兴起的教育组织,中国古代的书院却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个被逐渐纳入官方教育体系,在政府的控制下,丧失越来越多的自主权,成为政治的附庸;而一个却逐渐确立了独立于政治与宗教的法律地位,甚至获得了许多拓展其自主空间的特许权。
这仅仅是书院与欧洲大学的对比,如果我们将中国古代学者们所结成的学术团体与欧洲的大批学会作比较,会发现中国古代很多社团组织事实上仍然是官僚政治的延伸与变种,王家范(2001)尖锐地指出,明末那些标榜以文会友的结社,“或明或暗,都与‘科举——官场’的角逐紧相攀援”,社团与社团之间互相攻讦,无所不用其极,“有意无意地起了恶化晚明政局的作用,与后来亡国破家不无关系”。
而即便是纯粹的学术团体(历史上多被称为“学派”),也多属师友私下往来,无论规模还是制度都不具有近代学会组织的公共性,核心人物溃散或去世之后,学派也不久就消失了。
而事实上,那些具有较长远影响的学派往往也不得不借助于统治者的“政治恩泽”,因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学术的独立性。
如清朝康乾年间以梅氏家族为核心所形成的“安徽数学学派”,据记载,康熙帝曾召见梅文鼎于舟次“赐坐奏对,三接皆弥日,御书绩学参微以赐”,又征召梅珏成入内廷蒙养斋任编修,这使梅氏祖孙的影响大大扩展,以至于阮元在《畴人传》“梅文鼎传”的评论中所说:
“自征君以来,通数学者后先辈出,而师师相传,要皆本于梅氏”。
然而梅氏家族的学术思想也不得不打上“正统”的烙印,由于康熙帝本人在对待中算与西算的关系上,有明显的“西算源于中算”的错误观点(《东华录·康熙八十九》),梅文鼎在疏解西算时尽量在中算里寻找相应算法,而梅珏成在所著《赤水遗珍》中,更将康熙帝的错误意见加以发挥,认为西算中的代数学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天元术(钱宝琮,1981)。
既然民间独立的、稳定的学术自治领域在中国难以生长,那么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生产主体是否有别于欧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