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传七.docx
《托尔斯泰传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托尔斯泰传七.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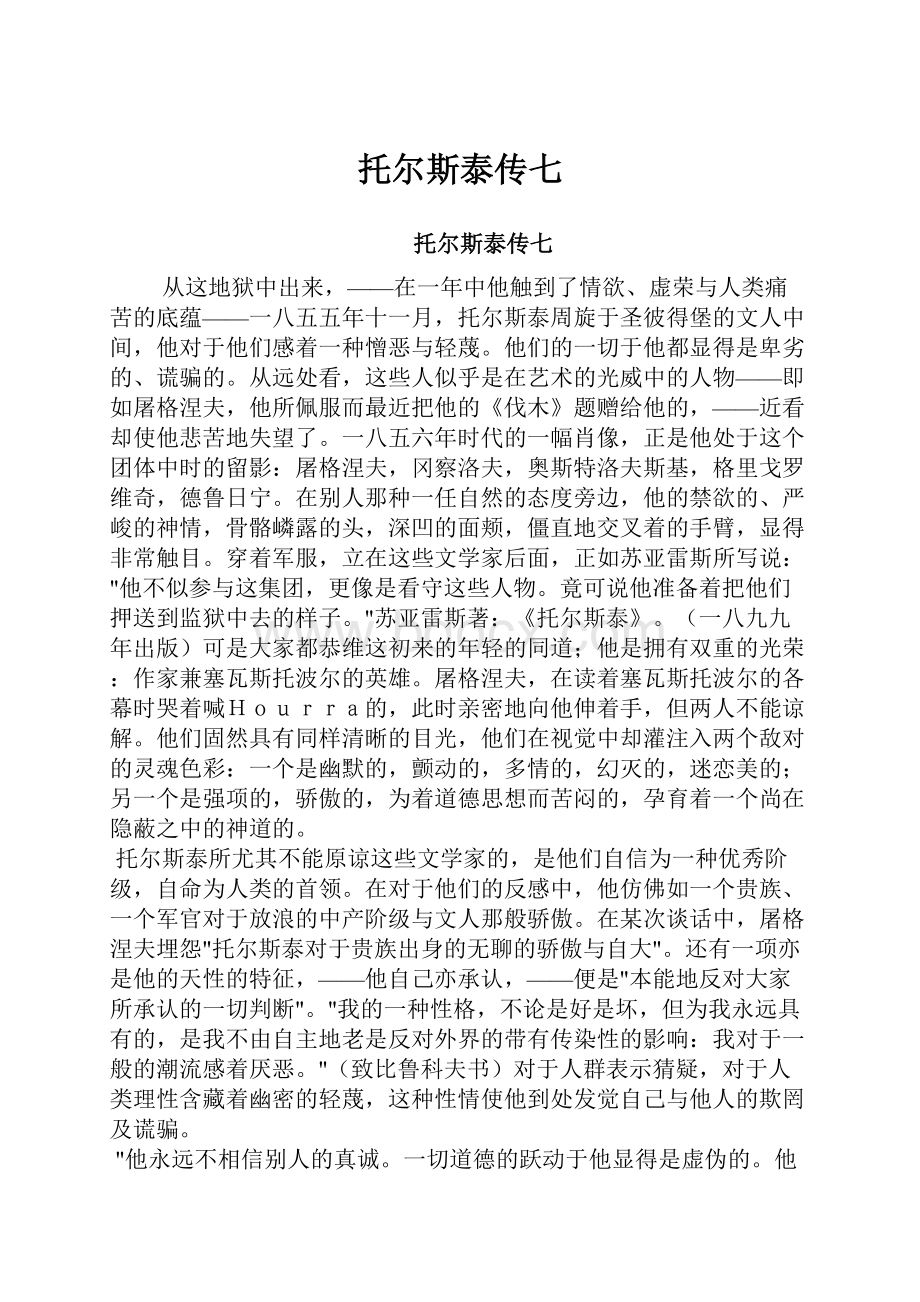
托尔斯泰传七
托尔斯泰传七
从这地狱中出来,——在一年中他触到了情欲、虚荣与人类痛苦的底蕴——一八五五年十一月,托尔斯泰周旋于圣彼得堡的文人中间,他对于他们感着一种憎恶与轻蔑。
他们的一切于他都显得是卑劣的、谎骗的。
从远处看,这些人似乎是在艺术的光威中的人物——即如屠格涅夫,他所佩服而最近把他的《伐木》题赠给他的,——近看却使他悲苦地失望了。
一八五六年时代的一幅肖像,正是他处于这个团体中时的留影:
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
在别人那种一任自然的态度旁边,他的禁欲的、严峻的神情,骨骼嶙露的头,深凹的面颊,僵直地交叉着的手臂,显得非常触目。
穿着军服,立在这些文学家后面,正如苏亚雷斯所写说:
"他不似参与这集团,更像是看守这些人物。
竟可说他准备着把他们押送到监狱中去的样子。
"苏亚雷斯著:
《托尔斯泰》。
(一八九九年出版)可是大家都恭维这初来的年轻的同道;他是拥有双重的光荣:
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
屠格涅夫,在读着塞瓦斯托波尔的各幕时哭着喊Hourra的,此时亲密地向他伸着手,但两人不能谅解。
他们固然具有同样清晰的目光,他们在视觉中却灌注入两个敌对的灵魂色彩:
一个是幽默的,颤动的,多情的,幻灭的,迷恋美的;另一个是强项的,骄傲的,为着道德思想而苦闷的,孕育着一个尚在隐蔽之中的神道的。
托尔斯泰所尤其不能原谅这些文学家的,是他们自信为一种优秀阶级,自命为人类的首领。
在对于他们的反感中,他仿佛如一个贵族、一个军官对于放浪的中产阶级与文人那般骄傲。
在某次谈话中,屠格涅夫埋怨"托尔斯泰对于贵族出身的无聊的骄傲与自大"。
还有一项亦是他的天性的特征,——他自己亦承认,——便是"本能地反对大家所承认的一切判断"。
"我的一种性格,不论是好是坏,但为我永远具有的,是我不由自主地老是反对外界的带有传染性的影响:
我对于一般的潮流感着厌恶。
"(致比鲁科夫书)对于人群表示猜疑,对于人类理性含藏着幽密的轻蔑,这种性情使他到处发觉自己与他人的欺罔及谎骗。
"他永远不相信别人的真诚。
一切道德的跃动于他显得是虚伪的。
他对于一个为他觉得没有说出实话的人,惯用他非常深入的目光逼十视着他……"屠格涅夫语。
"他怎样的听着!
他用深陷在眼眶里的灰色的眼睛怎样的直视着他的对手!
他的口唇抿紧着,用着何等的讥讽的神气!
"格里戈罗维奇语。
屠格涅夫说,他从没有感得比他这副尖锐的目光,加上二三个会令人暴跳起来的恶毒的辞句,更难堪的了。
于也纳·迦尔希纳著:
《关于屠格涅夫的回忆》。
(一八八三年)参看比鲁科夫著:
《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
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第一次会见时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一八六一年,两人发生最剧烈的冲突,以致终身不和。
屠格涅夫表示他的泛爱人间的思想,谈着他的女儿所干的慈善事业。
可是对于托尔斯泰,再没有比世俗的浮华的慈悲使他更愤怒的了:
——"我想,"他说,"一个穿装得很考究的女郎,在膝上拿着些龌龊的破衣服,不啻是扮演缺少真诚性的喜剧。
"争辩于以发生。
屠格涅夫大怒,威吓托尔斯泰要批他的颊。
托尔斯泰勒令当时便用手槍决斗以赔偿名誉。
屠格涅夫就后悔他的卤莽,写信向他道歉。
但托尔斯泰绝不原谅。
却在二十年之后,在一八七八年,还是托尔斯泰忏悔着他过去的一切。
在神前捐弃他的骄傲,请求屠格涅夫宽恕他。
远离之后,他们都镇静下来努力要互相表示公道。
但时间只使托尔斯泰和他的文学团体分隔得更远。
他不能宽恕这些艺术家一方面过着堕落的生活,一方面又宣扬什么道德。
"我相信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恶的,没有品性的,比我在军队流浪生活中所遇到的人要低下得多。
而他们竟对自己很肯定,快活,好似完全健全的人一样。
他们使我憎厌。
"《忏悔录》,全集卷十九。
他和他们分离了。
但他在若干时期内还保存着如他们一样的对于艺术的功利观念。
"在我们和疯人院间,"他说,"绝无分别。
即在那时,我已模糊地猜度过,但和一切疯人一样,我把每个人都认为是疯子,除了我。
"(同前)他的骄傲在其中获得了满足。
这是一种酬报丰富的宗教;它能为你挣得"女人,金钱,荣誉……""我曾是这个宗教中的要人之一。
我享有舒服而极有利益的地位……"为要完全献身给它,他辞去了军队中的职务(一八五六年十一月)。
但像他那种性格的人不能长久闭上眼睛的。
他相信,愿相信进步。
他觉得"这个名辞有些意义"。
到外国旅行了一次——一八五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法国,瑞士,德国——这个信念亦为之动摇了。
参看这时期,他给他年轻的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姑母的信,那么可爱,充满着青年的蓬勃之气。
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在巴黎看到执行死刑的一幕,指示出他"对于进步的迷信亦是空虚的……""当我看到头从人身上分离了滚到篮中去的时候,在我生命的全力上,我懂得现有的维持公共治安的理论,没有一条足以证明这种行为的合理。
如果全世界的人,依据着若干理论,认为这是必需的,我,我总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可以决定善或恶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
"《忏悔录》。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看见寓居施魏策尔霍夫的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者施舍,这幕情景使他在《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写于卢塞恩地方),全集卷五上写出他对于一切自由主义者的幻想,和那些"在善与恶的领域中唱着幻想的高调的人"的轻蔑。
"为他们,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是恶。
这些幻想的认识却毁灭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
而谁将和我确言何谓自由,何谓奴隶,何谓文明,何谓野蛮?
那里善与恶才不互存并立呢?
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普在的神灵。
"
回到俄罗斯,到他的本乡亚斯纳亚,他重新留意农人运动。
从瑞士直接回到俄罗斯时,他发现"在俄国的生活是一桩永久的痛苦!
因此他所要启示的对象并非是群众,而是每人的个人意识,而是民众的每个儿童的意识。
因为这里才是光明之所在。
他创办学校,可不知道教授什么。
为学习起见,自一八六○年七月三日至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旅行欧洲。
这次旅行中他结识了奥尔巴赫(在德国德累斯顿),他是第一个感应他去作民众教育的人;在基辛根结识福禄培尔;在伦敦结识赫尔岑,在比京结识普鲁东,似乎给他许多感应。
他研究各种不同的教育论。
不必说他把这些学说一齐摒斥了。
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使他明白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学校以外完成的——学校于他显得可笑的——如报纸,博物院,图书馆,街道,生活,一切为他称为"无意识的"或"自然的"学校。
强迫的学校是他认为不祥的,愚蠢的;故当他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时,他要创立而试验的即是自然的学校。
尤其在一八六一——六二年间。
自由是他的原则。
他不答应一般特殊阶级,"享有特权的自由社会",把他的学问和错误,强使他所全不了解的民众学习。
他没有这种权利。
这种强迫教育的方法,在大学里,从来不能产生"人类所需要的人,而产生了堕落社会所需要的人:
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还有若干毫无目的地从旧环境中驱逐出来的人——少年时代已经骄傲惯了,此刻在社会上亦找不到他的地位,只能变成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
《教育与修养》。
参看《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卷二。
应当由民众来说出他们的需要!
如果他们不在乎"一般知识分子强令他们学习的读与写的艺术",他们也自有他们的理由:
他有较此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的需要。
试着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满足这些需求!
这是一个革命主义者的保守家的理论,托尔斯泰试着要在亚斯纳亚作一番实验,他在那里不像是他的学生们的老师更似他们的同学。
托尔斯泰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杂志中发表他的理论(一八六二年),全集卷十三。
同时,他努力在农业垦殖中引入更为人间的精神。
一八六一年被任为克拉皮夫纳区域的地方仲裁人,他在田主与zheng府滥施威权之下成为民众保护人。
但不应当相信这社会活动已使他满足而占据了他整个的身心。
他继续受着种种敌对的情欲支配。
虽然他竭力接近民众,他仍爱,永远爱社交,他有这种需求。
有时,享乐的欲望侵扰他;有时,一种好动的性情刺激他。
他不惜冒了生命之险去猎熊。
他以大宗的金钱去赌博。
甚至他会受他瞧不起的圣彼得堡文坛的影响。
从这些歧途中出来,他为了厌恶,陷于精神狂乱。
这时期的作品便不幸地具有艺术上与精神上的犹疑不定的痕迹。
《两个轻骑兵》(一八五六年)全集卷四倾向于典雅、夸大、浮华的表现,在托尔斯泰的全体作品中不相称的。
一八五七年在法国第戎写的《阿尔贝》全集卷五是疲弱的、古怪的,缺少他所惯有的深刻与确切。
《记数人日记》(一八五六年)同前更动人,更早熟,似乎表白托尔斯泰对于自己的憎恶。
他的化身,涅赫留多夫亲王,在一个下流的区处自杀了:
"他有一切:
财富,声望,思想,高超的感应;他没有犯过什么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情:
他毒害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可并非为了什么剧烈的情欲,只是为了缺乏意志。
"
死已临头也不能使他改变:
"同样奇特的矛盾,同样的犹豫,同样的思想上的轻佻……"死……这时代,它开始缠绕着托尔斯泰的心魂。
在《三个死者》(一八五八——五九)中,全集卷六。
已可预见《伊万·伊里奇之死》一书中对于死的陰沉的分析,死者的孤独,对于生人的怨恨,他的绝望的问句:
"为什么?
"《三个死者》——富妇,痨病的老御者,斫断的桦树——确有他们的伟大;肖像刻划得颇为逼十真,形象也相当动人,虽然这作品的结构很松懈,而桦树之死亦缺少加增托尔斯泰写景的美点的确切的诗意。
在大体上,我们不知他究竟是致力于为艺术的艺术抑是具有道德用意的艺术。
托尔斯泰自己亦不知道。
一八五九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文学鉴赏人协会的招待席上,他的演辞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演辞的题目是:
《论文学中艺术成分优于一切暂时的思潮》。
倒是该会会长霍米亚科夫,在向"这个纯艺术的文学的代表"致敬之后,提出社会的与道德的艺术和他抗辩。
他提出托尔斯泰自己的作品《三个死者》作为抗辩的根据。
一年之后,一八六○年九月十九日,他亲爱的哥哥,尼古拉,在耶尔地方患肺病死了,托尔斯泰的另一个兄弟德米特里已于一八五六年患肺病而死了,一八五六、一八六二、一八七一诸年,托尔斯泰自以为亦染着了。
他是,如他于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所写的,"气质强而体质弱"的人,他老是患着牙痛,喉痛,眼痛,骨节痛。
一八五二年在高加索时,他"至少每星期二天必须留在室内"。
一八五四年,疾病使他在从锡利斯特拉到塞瓦斯托波尔的途中耽搁了几次。
一八五六年,他在故乡患肺病甚重。
一八六二年,为了恐怕肺痨之故,他赴萨马拉地方疗养。
自一八七○年后,他几乎每年要去一次。
他和费特的通信中充满了这些关于疾病的事情。
这种健康时时受损的情景,令人懂得他对于死的憧憬。
以后,他讲起他的病,好似他的最好的友人一般:
"当一个人病时,似乎在一个平坦的山坡上往下走,在某处,障着一层极轻微的布幕:
在幕的一面是生,那一面是死。
在精神的价值上,病的状态比健全的状态是优越得多了,不要和我谈起那些没患过病的人们!
他们是可怕的,尤其是女子!
一个身体强壮的女子,这是一头真正犷野的兽类!
"(与布瓦耶的谈话,见一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时报》)这噩耗使托尔斯泰大为震惊,以至"摇动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使他唾弃艺术:
"真理是残酷的……无疑的,只要存在着要知道真理而说出真理的欲愿,人们便努力要知道而说出。
这是我道德概念中所留存的惟一的东西。
这是我将实行的惟一的事物,可不是用你的艺术。
艺术,是谎言,而我不能爱美丽的谎言。
"一八六○年十月十七日致费特书。
然而,不到六个月之后,他在《波利库什卡》一八六一年写于比京布鲁塞尔一书当中重复回到"美丽的谎言",这或竟是,除了他对于金钱和金钱的万恶能力的诅咒外,道德用意最少的作品,纯粹为着艺术而写的作品;且亦是一部杰作,我们所能责备它的,只有它过于富丽的观察,足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太丰盛的材料,和诙谐的开端与太严肃的转纽间的过于强烈、微嫌残酷的对照。
同时代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一篇简单的游记,名字叫做《雪的苦闷》(一八五六年),描写他个人的回忆,具有一种极美的诗的印象,简直是音乐般的。
其中的背景,一部分又为托尔斯泰移用在《主与仆》(一八九五年)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