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慎其独说及其相关问题.docx
《《中庸》慎其独说及其相关问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庸》慎其独说及其相关问题.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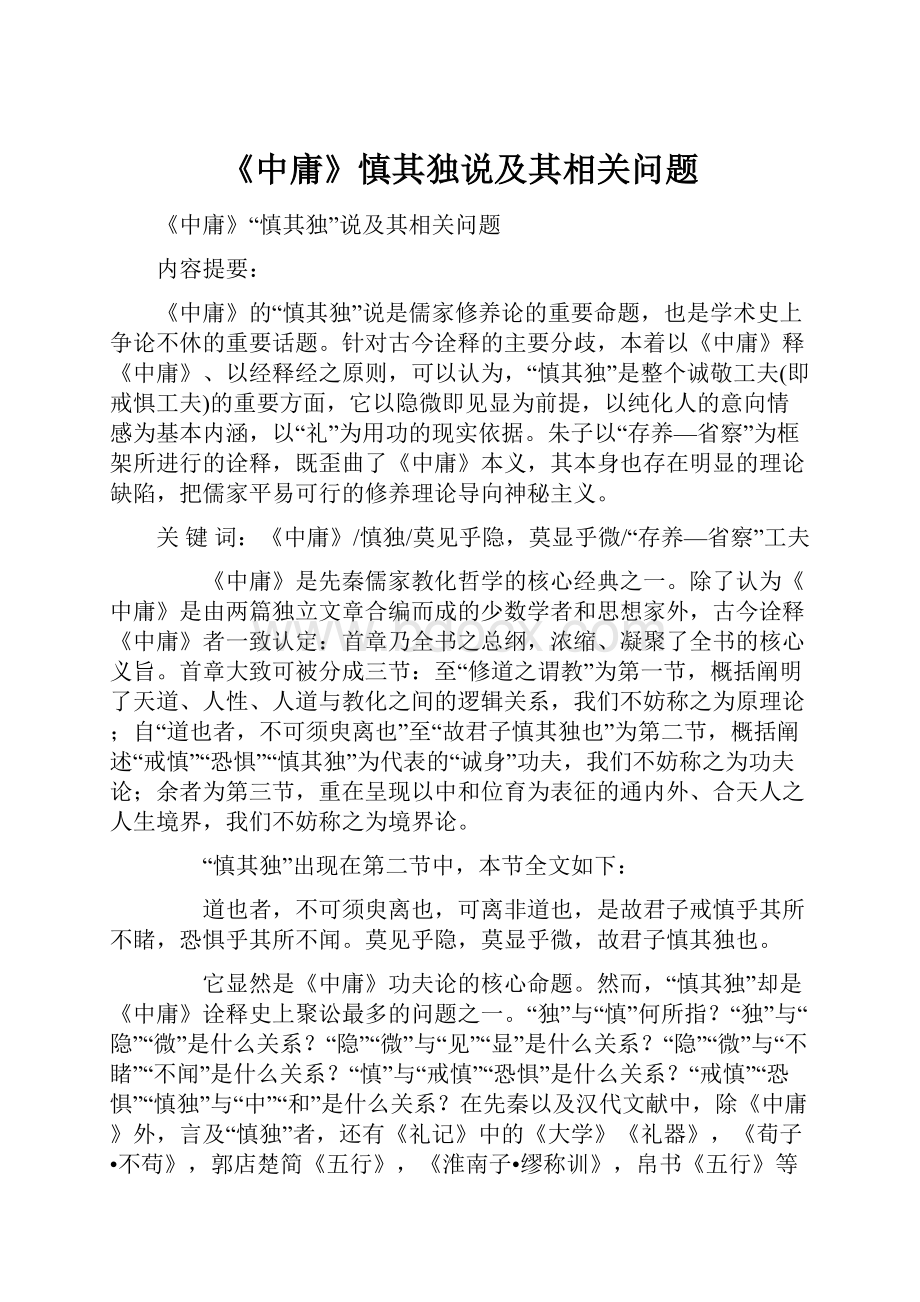
《中庸》慎其独说及其相关问题
《中庸》“慎其独”说及其相关问题
内容提要:
《中庸》的“慎其独”说是儒家修养论的重要命题,也是学术史上争论不休的重要话题。
针对古今诠释的主要分歧,本着以《中庸》释《中庸》、以经释经之原则,可以认为,“慎其独”是整个诚敬工夫(即戒惧工夫)的重要方面,它以隐微即见显为前提,以纯化人的意向情感为基本内涵,以“礼”为用功的现实依据。
朱子以“存养—省察”为框架所进行的诠释,既歪曲了《中庸》本义,其本身也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把儒家平易可行的修养理论导向神秘主义。
关键词:
《中庸》/慎独/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存养—省察”工夫
《中庸》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核心经典之一。
除了认为《中庸》是由两篇独立文章合编而成的少数学者和思想家外,古今诠释《中庸》者一致认定:
首章乃全书之总纲,浓缩、凝聚了全书的核心义旨。
首章大致可被分成三节:
至“修道之谓教”为第一节,概括阐明了天道、人性、人道与教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不妨称之为原理论;自“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至“故君子慎其独也”为第二节,概括阐述“戒慎”“恐惧”“慎其独”为代表的“诚身”功夫,我们不妨称之为功夫论;余者为第三节,重在呈现以中和位育为表征的通内外、合天人之人生境界,我们不妨称之为境界论。
“慎其独”出现在第二节中,本节全文如下: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它显然是《中庸》功夫论的核心命题。
然而,“慎其独”却是《中庸》诠释史上聚讼最多的问题之一。
“独”与“慎”何所指?
“独”与“隐”“微”是什么关系?
“隐”“微”与“见”“显”是什么关系?
“隐”“微”与“不睹”“不闻”是什么关系?
“慎”与“戒慎”“恐惧”是什么关系?
“戒慎”“恐惧”“慎独”与“中”“和”是什么关系?
在先秦以及汉代文献中,除《中庸》外,言及“慎独”者,还有《礼记》中的《大学》《礼器》,《荀子•不苟》,郭店楚简《五行》,《淮南子•缪称训》,帛书《五行》等。
《中庸》的“慎其独”,与相关文献所言者有何异同?
这些问题,自古以来争论不休,迄今未有定论。
欲弥合分歧,除了广泛研读自古以来的《中庸》学文献、充分吸纳前人的考证成果、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比较互证外,更根本的途径,还是对《中庸》文本本身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深入揭示其各部分间的逻辑关系。
离开了对《中庸》本身的逻辑分析,不同文献间的比较互证也很难得出准确结论。
限于篇幅,本文暂不展开讨论《中庸》与其他先秦两汉“慎其独”说之关系。
一、关于“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首章第二节是一个整体,分析讨论不能不从戒惧不睹、恐惧不闻开始。
理解这段话,首先要弄清:
“不睹”“不闻”,是谁不睹不闻?
系指他人不睹不闻,还是君子自己不睹不闻?
郑玄注以“虽视之无人,听之无声,犹戒慎恐惧自修正”[1]1385为解,其主体虽指君子,但表达的显然是没有他人在场、不为他人所睹所闻。
与之相比,孔颖达之疏则在君子自己与他人之间游移不定,一方面说“人虽目不睹之处犹戒慎”,指向他人之不睹;另一方面又说“虽耳所不闻,恒怀恐惧之”,又好像指向了君子自身之不闻。
[1]1387朱子则认为,正因道不可须臾离,“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2]33。
这里的“不见闻”者,则被理解为君子自己。
其实,解决这一分歧并不困难,只要明确“其所不睹”“其所不闻”的“其”字何所指即可。
在首章第二节中,“其”字共出现三次,“其所不睹”“其所不闻”“其独”,它们的主语都是“君子”,“其”字的含义也应该是一致的。
毫无疑问,“慎其独”的“其”,指君子自己,决不会指他人。
由此即可断定,前两个“其”字,也应该指君子自己。
经典为文,往往极其精审。
如果紧相联接的三个“其”字所指不同,在表述上也应该有所差异。
“不睹”“不闻”若指他人,其恰当表述应该是“人所不睹”“人所不闻”。
因此,朱子的理解是准确的:
“‘其所不睹不闻’,‘其’之一字,便见得是说己不睹不闻处,只是诸家看得不仔细耳。
”[3]2030
既然如此,那么君子自己的“不睹”“不闻”又指什么呢?
理解经典之文,有两条相反相成之途径:
其一,是由部分到整体,即由字句之义来合成章节之旨;其二,是由整体到部分,即由章节之旨来确定字句之义。
在前者难以奏效时,我们不妨采取第二条途径。
“是故”二字表明,“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与“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其含义是:
正因为道不可须臾离,故君子时时处处戒慎恐惧以修道——不仅有所睹闻之时与地,即便是所不睹不闻,亦当心存敬畏、修道不懈。
在这里,“不睹”“不闻”与“睹”“闻”构成了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
一方面,是用“不睹”“不闻”来统括“睹”“闻”,因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决不能被理解为只在“不睹”“不闻”上下功夫,而“睹”“闻”之时与地可以放任无忌;另一方面,“不睹”“不闻”又是把“睹”“闻”推向极端的产物,以达成无时无地不戒惧修道之修辞效果。
因此,不能由此就确认生活中真有那么一个闭目塞听、完全与世界断绝往来的修行空间或时段,君子应该在那里尽其戒慎恐惧之功。
更何况,即便是闭目塞听,耳目之睹闻又何曾停止?
只是睹于无形、听乎无声罢了。
由此看来,所谓“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与末章的“不动而敬,不言而信”,用词虽不同,意义却完全一致。
“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字面上是敬、信已确立于动、言之先,实际上表达的则是“敬”“信”已成为君子稳定的人格品质,君子无时无地不敬之信之。
如果拘牵于字面意义,君子在视听言动之外修其敬信,就会堕入佛学末流以心观心之窠臼。
“不睹”“不闻”,即是“不动”“不言”;更准确地说,“不睹”“不闻”可以概指“不视听言动”。
“视听言动”所代表的,正是人与世界相感通的一切活动。
人之一生,即便在安睡之中,也未尝完全断绝与世界之往来交通。
说到底,“不睹”“不闻”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法,以凸显君子修道功夫之遍布周满,无须臾之间断,无毫厘之间隔。
《中庸》何以要以“不睹”“不闻”“无声无臭”为说?
乃因同以有形之物与外界相感应相比,睹、闻、嗅觉分别诉之于光、声、气味等无形之物,其所感所应相当微妙精致,故祭拜神灵常以烛、以乐、以荤腥为之。
而不睹不闻、无声无臭则连光、声、气味等无形之物一并超越之,岂不更加精妙深微?
其中道理,刘咸炘(1896-1932)在《三虚》一文中,已阐发无余。
他说:
凡天地之间万有,可一言以蔽之曰气。
气之所生,或实或虚。
实者五,曰木、火、土、金、水,昔之论者常减之增之而不能也。
虚者四,曰味、光、声、臭,佛家谓之色、声、香、味。
味之用,不若光、声、臭之大。
光、声、臭者,神明之道也,不见其用而用莫大焉,故曰无用之用。
……夫四者之用,光易验而声、臭难验。
人之静也,目闭而耳不闭,故子思推上天之载曰“无声无臭”。
声之感人犹易知,而臭之感人尤难知,故《记》之论臭特详焉。
[4]1015-1019
古今释《中庸》此节,多有索求“不睹”“不闻”、“无声无臭”于窈冥之地、无何有之乡者。
如:
或曰:
“不睹不闻,正是天命本体,原是自无声无臭来的,岂可得而睹闻?
君子于其所不睹者戒慎,谓观道于无形也;于其所不闻者恐惧,谓听道于无声也。
玩两个‘所’字,则不睹不闻自性体言,非自时、境言。
”张侗初曰:
“视听有起灭,天性无起灭,故所不睹是谓见性,所不闻是谓闻性。
”[5]卷二《中庸》
天命本体既然无法睹闻,而论者却把“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解释成“观道于无形”“听道于无声”或“见性”“闻性”,岂非以荒唐无类之言论光明正大之事乎?
如此之类,所在多有。
其说愈多愈妙,其引入误入歧途者愈深。
当然,非要说戒慎恐惧的对象是天命之性,也未尝不可。
《中庸》第二十七章就有“尊德性”之语。
所谓“尊德性”,即是恭敬奉持天命之性。
但要知道,“尊德性”并空无所事地跪拜于“德性”面前,它只能落实在日用常行的修习之中、落实在问学之中,故曰“尊德性而道问学”。
因此,谭玉怀曰:
“不睹不闻,世儒必欲深其旨,以道体无声无臭言。
愚按:
率性修道之说,并篇中论道之旨,子思子明以道之显见处示人,何必谈玄说妙?
”[5]卷二《中庸》笔者亦曾为各种曲说玄谈所惑,在此不得不详辨而繁说焉。
其他种种玄论,恕不一一辨驳。
二、关于“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在“莫见”这段话中,“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与“君子慎其独也”之间,又构成了一对因果关系,即:
正因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所以君子会“慎其独”。
在这里,“独”显然是从属于“隐”“微”一类的事物,或者说,“独”具有“隐”“微”类事物之特征。
因此,“独”与“隐”“微”不是等值的概念。
有人说“隐微即独”,严格说来,是不准确的。
那么,“独”何以具有隐微之特性?
这就必须弄清“独”之大体内涵。
郑玄曰:
“慎其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
”[1]1385孔颖达曰:
“言虽曰独居,能谨慎守道也。
”[1]1387可见,郑、孔都把“独”理解为无他人在场的闲居独处。
其解确有所本。
《中庸》末章云: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问题在于,“人之所不见”,不仅可指有视听言动而他人不在场,也包括他人虽在场却又无法察识的君子之内心活动。
正是有见于此,朱子曰: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
”[2]33在《朱子语类》中,朱子曾针对弟子之问,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思想:
问:
“‘慎独’,莫只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处,也与那暗室不欺时一般否?
”先生是之,又云:
“这‘独’也又不是恁地独时,如与人对坐,自心中发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独处。
”[3]2033
让“独”同时容纳了独居与内心的思想活动两方面,似乎使朱子之解更加严密周全。
其实,慎其独居与慎其内在思想活动并非相互分离的两件事。
这是因为,身、心一体,身为心所支配,一个独居时能管束其身的人,必定拥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心”。
所以,从根本上讲,“独”就是指“心”。
自古以来,解《大学》《中庸》者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大学》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
其实“独”就是《中庸》之“心”的代名词。
帛书《五行》篇曰:
“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
”此即以“心”指“独”的重要旁证。
先秦两汉典籍中言及“慎独”的,除了《大学》《中庸》,还有《礼记•礼器》《荀子•不苟》《淮南子•谬称训》及郭店楚简《五行》等。
众书所说的“独”虽有细微差别,但其最大公约数就是“心”。
为什么要用“独”来指称“心”?
“独”的基本含义是“单”(《诗经•小雅•正月》“哀此惸独”毛传)或“单独”(《广韵•屋部》)、“单一”(《方言》卷十二),而与“众”(即“众人”和“众多”)相对,孤独、独立、独断、独特等含义,都是由“单”派生出来的。
以“独”名“心”,就是要凸显其个体内在性(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隐密空间)、自明性(自察自知)、自主独立性(自为主客)等。
总之,“慎独”之“独”就是心,即每个人隐密而自明、可以自主处置的独立精神空间。
①隐密而不自明,或虽自明却无法自主处置,皆不得名为“独”。
“隐”“微”是用来描述“独”之特性的。
“隐”字的本义是“蔽”(《说文》),可有遮蔽、隐藏、藏匿、潜伏(《中庸》末章引《诗》言“潜虽伏矣”,即用此义)等义。
但同样是“蔽”,对于人之生活来说,又有有意与无意之分。
朱子以“暗处”释之,显然是着眼于无意之“蔽”,即人心本来就是幽蔽的,此人与彼人之内心不能直接相互察知。
“微”字在甲骨文、金文中作“”,“应从攴、长会意。
长为髮字最初文……发既细小矣,攴之则断,而更微也”(高洪缙《散盘集释》)。
“微”本义为细小、细微;可引申出精微、精妙、晦暗、隐匿、潜行等义。
《说文》曰“微,隐行也”,当为其引申义。
朱子以“微,细事也”(《中庸章句》)为释,则是其本义。
总之,以“隐”“微”来描述“独”,正是要凸显人之内心活动的隐蔽性(对他人而言)和细密性(相对于有形之物而言)。
然而,人心之“独”虽隐蔽细密,却又是每个人皆能自察自知的,故朱子以“人所不知而己独知”释“独”,最能得其要领。
那么,“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又是何义?
这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概念表述的形式方面,即隐微与见显间的逻辑关系;二是关于表述的实质方面,即何物莫见显于隐微。
关于其形式方面,古今之说大致有三种:
其一,认为隐微与见显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先隐微而后见显;其二,认为隐微与见显之间具有必然性,即隐必见、微必显,如《大学》的“诚于中,形于外”,以及《中庸》第十六章的“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其三,隐微当下即是见显。
陶起庠曰:
“莫见”是不容藏,“莫显”是不少晦。
须就“隐”“微”当下勘出,非隐而后见,微而后显,姑且有待之谓。
亦非隐则必见,微则必显,宜防其渐之谓。
只隐处便是见,微处便是显,无两境,并无异时。
“隐”“微”即是“独”,“莫见”“莫显”,正见“独”之当“慎”,故与“故”字紧接。
[6]
陶氏显然是反对前两说而力主后说的。
欲定三者之取舍,必须明确何物必见显于隐微,这就涉及其实质方面。
关于其实质方面,朱子的解释是:
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明显而过于此者。
[2]33
朱子的意思是说:
君子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了解,比起对于天下之事的了解来,更加清楚明白。
此解显然是有问题的。
了解自己的内心与了解天下之事(比如,对于日月当空的感知)并不具有可比性,难言谁比谁更清楚。
更重要的是,即便独知最清楚显明,也不意味着一定要“慎其独”:
因为对于自己的内心最了解,所以君子会“慎其独”——这一因果关系根本不成立。
原因在于,了解自心只是为“慎其独”提供了可能性,却没有揭示其必要性、必然性。
其实,“隐”“微”是对于“独”之特性的描述,在此即代表着“独”。
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说人的德性(或曰品德、品行、修养等,皆可)的善恶好坏,最直接地表现在“独”(即内心世界)上,而不是外显的言谈举止上。
正因如此,王夫之才说:
“‘显’‘见’止是是非分明。
”[7]《中庸》此处如有不慎,则亏性丧德、离道而去。
君子不欲亏性丧德,故能“慎其独”。
既然如此,那么,“隐”“微”与“见”“显”之间的逻辑关系,就容易确定了。
陶起庠之说是正确的:
既非先隐微后见显,亦非内在的隐微必见显于外、必为人所知,而是隐微即见显、即是德性高下的直接确证。
陶氏的所谓“无两境,并无异时”意味着:
隐微与见显存在于同一个场域,而非一内一外的两个空间;是共时态的,而非一先一后两个时段。
末章的“潜虽伏矣,亦孔之昭”,也是同一个意思。
正因如此,君子“慎其独”才具有了彻底自主、自律的道德意义,才是真正的学以为己。
末章的“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就是对“慎其独”的具体说明之一:
“内”,即心;“内省”,即是省察、反省自心;“不疚”,即是没有瑕疵或毛病;内省不疚,则自然“无恶于志”,即无愧于天德良知,而与《大学》的“此之谓自谦”直接相通。
正是这一高度自主自律性,使君子超越了常人、与常人区别开来,故末章云: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因为担心显现于外、为人所知而慎之,在道德的自律水平上,已经低了一格,可知其绝非真君子;小人则有更甚者,虽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也猖狂妄为、无所忌惮,此即第二章所谓“小人而无忌惮”也。
而今天的慎其隐微是为了将来的显明,则会把道德上的即微即显、即修即得(一日修之则有道而为人,一日不修则离道而沦为非人),割裂成两个孤立的片断。
这两种说法都是有缺陷的,不合《中庸》本义。
正是在这里,“隐”“微”与上文的“不睹”“不闻”区别开来:
前者是他人不睹、不闻、不知;后者是君子自己所不睹、不闻,却又是自知的。
古今不少学者把两者等同起来,这只能造成思想的混乱和理解的困难。
三、关于“慎其独”之“慎”的具体含义
“慎其独”之“慎”,郑注《中庸》没有单独作解,可能是因为在注《中庸》之前的《礼器》时,已有“致诚悫”的说法,似有以“慎”为“诚”之意。
孔颖达之疏也不单独为释,而以“恒须慎惧如此”说“慎其独”,可知其视“慎”与“戒慎”“恐惧”同义。
朱子处理“慎”的方式,与孔颖达相似,亦以戒慎、恐惧为义。
但在部分清代考据学家看来,训“慎”为“诚”与训为“戒慎”是有区别的。
郝懿行(1757-1825)说:
“‘慎’当训‘诚’。
《释诂》云:
‘慎,诚也。
’非谨慎之谓。
《中庸》‘慎独’与此义别。
……‘慎’字古义训‘诚’,《诗》凡四见,毛、郑俱以《尔雅》为释。
《大学》两言‘慎独’,皆在‘诚意’篇中,其义亦与《诗》同。
惟《中庸》以‘戒慎’‘慎独’为言,此别义,乃今义也。
”[8]卷上郝氏的意见可概括为两个要点:
其一,“诚”与“谨慎”分别为“慎”之古义与今义;其二,先秦典籍言“慎独”多用古义,只有《中庸》例外,用今义。
王念孙(1744-1832)则认为,《中庸》“慎独”也应当训“诚”,训“谨”训“诚”虽取义不同,却无古今之异:
《中庸》之“慎独”,“慎”亦当训为“诚”,非上文“戒慎”之谓。
[自注: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即《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则“慎独”不当有二义。
陈(奂)云:
“《中庸》言‘慎独’,即是‘诚身’。
”]故《礼器》说礼之以少为贵者曰:
“是故君子慎其独也。
”郑注:
“少其牲物,致诚悫。
”是“慎其独”即诚其独也。
慎独之为诚独,郑于《礼器》已释讫,故《中庸》《大学》注皆不复释。
孔冲远未达此旨,故训为谨慎耳。
凡经典中“慎”字,与“谨”同义者多,与“诚”同义者少。
(自注:
“慎”之为“谨”,不烦训释,故传注无文。
非“诚”为古义而“谨”为今义也)唯“慎独”之“慎”,则当训为“诚”。
故曰“君子必慎其独”,又曰“君子必诚其意”。
《礼器》《中庸》《大学》《荀子》之“慎独”,其义一也。
[9]
应该说,在字面上,“谨”与“诚”当然有区别:
“诚”者固然谨慎,而“谨”者未必有“诚”。
不仅如此,“戒慎”与“恐惧”在字面上也大有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然而,《中庸》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显然有互文之意,言戒慎而恐惧在其中,言恐惧而戒慎在其中。
如果孤立地看待、处理这里的“戒慎”与“恐惧”,自然是讲不通的。
合首章第二节与整篇《中庸》而观之,则“戒慎”“恐惧”也好,“慎”也好,以及后文的“拳拳服膺”“尊”“敬”“笃”“笃恭”“纯”“不贰”等,莫不指向《中庸》那一根本范畴“诚”,都是“诚”的不同侧面和具体表现。
因此,如果我们承认首章是《中庸》之总纲,那么,“戒慎”“恐惧”与“慎”,不过是以部分来概指“诚”之总体。
同样,“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以及“慎其独”,也不过是以部分来概指作为总体功夫的“诚身”。
因此,从根本上讲,“慎其独”就是“诚其独”。
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五行》篇出土;90年代,又有郭店楚简《五行》篇出土,其书均有“慎其独”的材料。
依据这些材料,人们开始重新讨论慎独问题。
关于“慎”字,出现了几个比较有新意的说法。
魏启鹏释为“顺”。
[10]11不管此说能否解通简、帛之文,以之解《中庸》显然是不通的。
因为《中庸》之“独”乃善、恶两存之物,若顺从之,必陷于两歧。
廖名春则力排众议,通过曲折论证,力主以“慎”为“真”。
他说:
前贤时人将“慎独”之“慎”或训为“谨”,或训为“诚”,或读为“顺”,皆不足取。
笔者认为,“慎”字之本义应是“心里珍重”。
其字应是形声兼会意,“心”为义符,而“真”既为声符,也为义符。
严格地说,“慎”应是“真”的后起分别字。
[11]50
廖先生认真追溯“慎”字本义,认为其为“真”字的后起分别字,而以“内心珍重”为义,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就概念的内涵而言,“内心珍重”也是“诚”的表现之一,最终还要归结到“诚”上。
它跟“戒慎”“恐惧”“谨慎”皆统于“诚”一样,都是以部分指代全体的表达方式。
如果只抠字眼儿,仅在“珍重内心”上打转儿,怎能体现“慎独”乃《中庸》的根本修养原则,并与“至诚”“诚身”相通呢?
其实,“慎”字之训,还有一种更奇特的说法,它出自清末民初国学大师廖平(1852-1932)之手。
他认为,“慎”当读作“内卦曰贞”之“贞”:
《论语》:
“敏于事而慎于言。
”,“敏”“慎”当作“”“贞”。
内贞外,非“戒慎”之“慎”。
(《廖平全集》第五册《大学中庸演义》)[12]
以“慎”为“贞”,取贞定、贞固其心之义,说亦可通,最终还要通之于“诚”。
总之,“诚”有众多表现形式,因而,“慎”之字义尽可以有多种训释,但总不外于一“诚”、通于一“诚”。
毛奇龄深明其理,曰:
“慎独只是诚,而诚只是明善择善。
”(《中庸说》卷一)[13]
四、关于“慎其独”之“独”的具体内涵
那么,“独”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上节诠解“慎其独”之“独”,还只是立足于“心”(内心世界)这一比较宽泛的意义。
完整说来,“心”包括情感、意志和认知三方面内容。
那么,《中庸》所说的“独”,是涵盖了“心”之全体,还是侧重于“心”的一两个方面呢?
笔者认为,它既涵盖了“心”之所有方面,也有所侧重。
为什么说“独”涵盖了心之所有方面?
第二十章中作为“三达德”的“知”“仁”“勇”,就是分别指向知、情、意的。
尽管其“知”首先指道德智慧,但道德智慧本身就包含着正常的认知、判断与选择能力。
在第三十一章中,《中庸》用“聪明睿知”“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描述至圣之心,就涵盖了心的所有方面。
此外,“明善”“虽愚必明”“自诚明”之“明”,作为“明善”工夫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的学、问、思、辨等,也都充分容纳了认知的内容。
“择善而固执之”之“择”,则融合了认知与意志。
当朱子以“人所不知而己独知”来界定“独”时,其“独”显然包括认知、辨别能力在内。
尽管儒学确认道德善恶、价值判断的根本尺度在于情感和意志,但正常的认知能力始终是道德活动所不可或缺的。
一个人一旦丧失了基本的认知能力,其一切作为已与道德无关,失去了道德价值和意义。
第六章盛赞舜之“大知”,也与此有关。
为什么说“慎独”之“独”于“心”有所侧重?
这有几个明显证据。
首先,历来有不少学者认定,末章的“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就是具体阐述“君子慎其独”之功夫的。
此“志”即指志意、心志、气志或情志,显然属于情感意向范畴。
此“独”近于《礼记•孔子闲居》所谓的“气志”或“志气”:
“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志气塞乎天地”。
其次,《中庸》自第二章起以至于篇尾,前半部分主要论中庸,后半部分主要论诚,“诚者”“诚之者”“自诚明”“自明诚”“至诚”等字眼儿,在其中反复出现。
所谓“诚”,无疑也属于情感与意向范畴。
此外,首章第三节论中和位育,乃基于喜怒哀乐以立论,喜怒哀乐当然是情。
更重要的是,整篇《中庸》处处充斥着意志与情感的字眼儿:
“戒慎”“恐惧”“慎”“无忌惮”“拳拳服膺”“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大孝”“达孝”“忠信”“忠恕”“无忧”“齐明盛服”“敦厚”“肫肫”“笃恭”“不疚”“纯”“不贰”“好学”“知耻”“力行”,等等,何一不关乎情感意向之事?
这充分表明,《中庸》言“独”,是侧重于情感与意志维度的。
此心之“独”本自广大,朱子以“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释“独”,业已得其要义。
然而,在具体阐释“慎其独”之时,朱子却把它锁定在意志活动的萌芽阶段上,所谓“动静之几”。
这不仅大大窄化了“独”与“慎独”之内涵,还给人造成了理论上的错觉:
似乎君子只要闭目塞听、默坐澄心,即可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达道,即可收“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下平”以及参赞化育之奇效。
由于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在诠释原始儒学时,大多数理学家都存在这一理论偏差。
针对宋、明理学释经之偏颇,以礼学名世的清代大儒凌廷堪(1757-1809)指出:
《礼器》曰:
“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
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足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
是故君子慎其独也。
”此即《学》《庸》之正义也。
慎独指礼而言,“礼之以少为贵”,《记》有明文言之。
然则《学》《庸》之慎独,皆礼之内心精微可知也。
后儒置《礼器》不观,高言慎独,与禅家之独坐观空何异?
由此观之,不惟明儒之提倡慎独为认贼作子,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