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烟蔓寻何处寻吴佩孚遗址.docx
《茫茫烟蔓寻何处寻吴佩孚遗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茫茫烟蔓寻何处寻吴佩孚遗址.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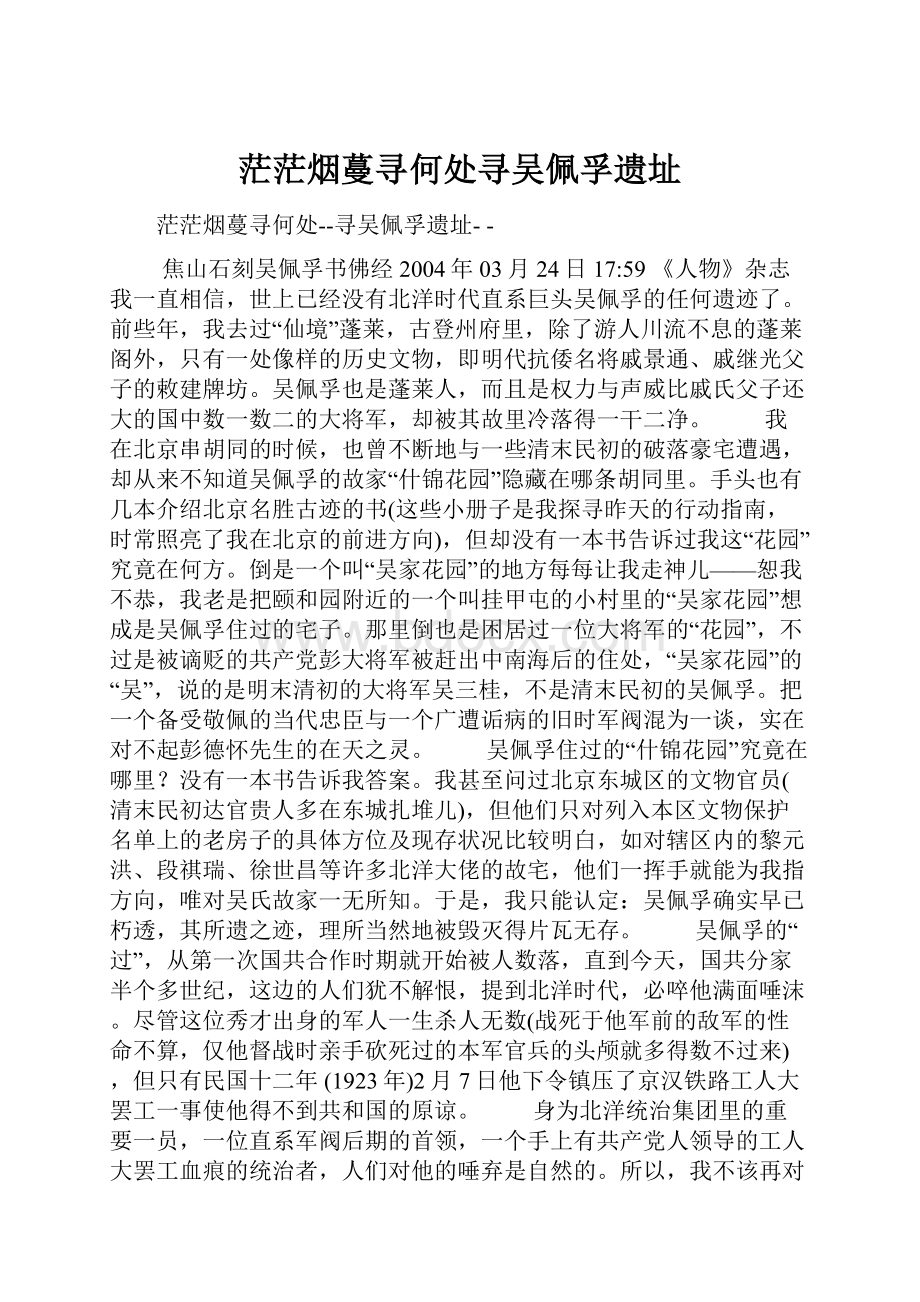
茫茫烟蔓寻何处寻吴佩孚遗址
茫茫烟蔓寻何处--寻吴佩孚遗址--
焦山石刻吴佩孚书佛经2004年03月24日17:
59《人物》杂志 我一直相信,世上已经没有北洋时代直系巨头吴佩孚的任何遗迹了。
前些年,我去过“仙境”蓬莱,古登州府里,除了游人川流不息的蓬莱阁外,只有一处像样的历史文物,即明代抗倭名将戚景通、戚继光父子的敕建牌坊。
吴佩孚也是蓬莱人,而且是权力与声威比戚氏父子还大的国中数一数二的大将军,却被其故里冷落得一干二净。
我在北京串胡同的时候,也曾不断地与一些清末民初的破落豪宅遭遇,却从来不知道吴佩孚的故家“什锦花园”隐藏在哪条胡同里。
手头也有几本介绍北京名胜古迹的书(这些小册子是我探寻昨天的行动指南,时常照亮了我在北京的前进方向),但却没有一本书告诉过我这“花园”究竟在何方。
倒是一个叫“吴家花园”的地方每每让我走神儿——恕我不恭,我老是把颐和园附近的一个叫挂甲屯的小村里的“吴家花园”想成是吴佩孚住过的宅子。
那里倒也是困居过一位大将军的“花园”,不过是被谪贬的共产党彭大将军被赶出中南海后的住处,“吴家花园”的“吴”,说的是明末清初的大将军吴三桂,不是清末民初的吴佩孚。
把一个备受敬佩的当代忠臣与一个广遭诟病的旧时军阀混为一谈,实在对不起彭德怀先生的在天之灵。
吴佩孚住过的“什锦花园”究竟在哪里?
没有一本书告诉我答案。
我甚至问过北京东城区的文物官员(清末民初达官贵人多在东城扎堆儿),但他们只对列入本区文物保护名单上的老房子的具体方位及现存状况比较明白,如对辖区内的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许多北洋大佬的故宅,他们一挥手就能为我指方向,唯对吴氏故家一无所知。
于是,我只能认定:
吴佩孚确实早已朽透,其所遗之迹,理所当然地被毁灭得片瓦无存。
吴佩孚的“过”,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开始被人数落,直到今天,国共分家半个多世纪,这边的人们犹不解恨,提到北洋时代,必啐他满面唾沫。
尽管这位秀才出身的军人一生杀人无数(战死于他军前的敌军的性命不算,仅他督战时亲手砍死过的本军官兵的头颅就多得数不过来),但只有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7日他下令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事使他得不到共和国的原谅。
身为北洋统治集团里的重要一员,一位直系军阀后期的首领,一个手上有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大罢工血痕的统治者,人们对他的唾弃是自然的。
所以,我不该再对“什锦花园”心存侥幸。
只是难免替这位“大帅”鸣不平:
同样是“反动派”,皇帝老儿的家(紫禁城、中南海、北海、景山、颐和园)被保存得好好的,北洋政府的其他巨头的故宅总能被用文物保护的石牌标示出来(或被要人或单位占用,或沦为百姓杂院),唯性情最倔的吴氏的故址永远消失了,这总有失“费厄泼赖”(fairplay)吧!
然而,在二十世纪快要过到尽头的一个异常晴朗的日子,我在北京美术馆后街旁的一个胡同口怔住了——头顶上方的墙角上,一块金属牌明明白白告诉了我这是什么地方:
什锦花园胡同 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大佛寺东街,全长607米,宽7米。
明属仁寿坊,西段称红庙街,东段为适景园。
清乾隆时称石景花园,宣统时称什锦花园,民国后沿称。
1965年改称什锦花园胡同。
民国时北洋军阀吴佩孚曾住过适景园旧址。
胡同内19号四合院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办公室 一九九三年 广州侨光制药厂赞助 我无法不念叨“踏破铁鞋”的那句成语,禁不住咧嘴朝随行的小彤释然而笑。
“蓬莱腿子,黄县嘴子,掖县鬼子。
”这是清末民初在山东半岛流传甚广的一句有点带骂人意味的民谣。
其实这三县的人本没招谁惹谁,只因彼时走南闯北做买卖的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具有超前的商品经济意识”,像无所不在的温州人似的,所以,邻县的那些只知道“拉锄钩子”(种地)的人就醋溜溜地编造了这句民谣,以发泄吃不着葡萄的酸劲儿。
但同为四处做买卖,蓬、黄、掖又各有特点:
“腿子”是指能跑,形容全国乃至海外都能看到蓬莱籍的买卖人在奔波;“嘴子”是指会说,演小品的那个大个子魏积安一口一个“伙计”,就是地道的“黄县模式”,谈生意时没准能把对方说晕了;“鬼子”是指精于计算,掖县人的算盘拨拉得噼哩叭啦响,有些鬼点子,与吴佩孚同时代的军阀张宗昌即是掖县人,他粗犷的外表一直迷惑了好多人呐。
不过,“腿子”也罢,“嘴子”也罢,“鬼子”也罢,蓬、黄、掖乃至胶东半岛甚至加上整个山东,哪个“腿子”能比得了吴佩孚走得远、走得高、走得山摇地动?
哪张“嘴子”能比吴佩孚说话管用竟致一言九鼎?
哪个“鬼子”能像吴佩孚那样精于运筹帷幄且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吴佩孚是民国初年胶东人的骄傲。
1874年春,登州府蓬莱城县学后街开杂货铺的吴家有了第二个儿子。
由于头一个儿子不幸夭折,所以这一个小子的啼哭声就格外令吴家夫妇欣慰。
传统的说法是,儿子出生时,其父恰好梦见本县前朝英豪戚继光!
戚继光,字佩玉,所以,粗通文墨的老吴头就为“孚”字辈的儿子取名“佩孚”,字“子玉”,他把戚大人的名与字都嵌进了儿子的名字中,指望儿子长大后能像戚继光那样为国雪耻并光耀祖宗。
我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中国历史上这种攀缘大人物的“梦”也忒多了点,往往都是追慕者为尊者所造的谣。
但吴佩孚之名与戚继光有关却是事实。
吴家老二初长成,父亲却过世,少年失怙的他只能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为解家贫,十三岁那年吴佩孚便投军登州水师当学兵,为的是每月二两多的银子补贴家用。
这一点,他和日后的军校老师段祺瑞差不多,都是少年丧父后投军自救的。
但与段不同的是,吴佩孚从戎后却并没放弃读书,而是拜了一位登州府的宿儒执经问义,且一学就是数年。
当兵之后仍能做学问,自是件很苦的事。
若不是骨子里有一股奋发向上、立志出人头地的韧劲,吴佩孚断断乎成不了北洋军阀里学历最高的人——聪慧的天资加勤奋的学习,使这个二十二岁的瘦高的青年一举考取本县秀才。
不过,该秀才没等参加下一轮高考就被革了功名,因为他竟然领头砸了一台男女同台的戏场子!
坚信“男女受授不亲”的吴佩孚看不惯本县的头一台“男女混杂”演出,所以,“替天行道”,成了闹事的主角。
为躲避县衙的追捕,不得已他背井离乡去了京城。
吴佩孚一辈子把“戒淫”当成大事来做,他早在年轻时就写过:
“率性而节欲,可庶几于圣贤;纵欲而灭性,则近于禽兽。
”这道理说得多简明而形象?
你想当圣贤,就要节制性欲,否则,就是禽兽!
他比别人更想做个道德完善的真君子,所以,就恪守传统,就谢绝纵欲。
一个人年轻时“戒淫”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戒淫”而不纵情。
老吴算是难能可贵的一位。
他迟至三十开外才娶了结发妻子李氏,后在母亲的坚持下纳妾张佩兰,但对两位夫人的位置排得很正。
李氏病故后,他曾对日本好友说过:
将来武力统一中国以后,欲往峨嵋山皈依佛门,为战死的众多将士和李氏的亡灵超度。
日人问:
张氏如何处置?
吴不以为然道:
张乃第二夫人,不值一提。
后张氏依然未能有孕,便在吴五十多岁以后主动献上自己的婢女,然该小女子仍未为吴氏留下子嗣,可见,问题出在老吴自身。
婚后不孕乃人生之大疾,自古以来就被认定是女子的责任,直到二十世纪末人们才知道,其实男人的原因甚于对方。
可惜吴佩孚生不逢时活得太早,若是挺到现在,不管驻军哪个城乡,派人随便到街头找根电线杆看看,都会发现“专治不孕不育”的膏药广告。
得,又扯远了。
吴佩孚是有魅力的男子。
某次,一位前去洛阳帅府采访他的外国女记者竟会一见钟情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但这个正人君子却一抹脸,把金发碧眼的洋小姐泼他一头的热辣辣的秋波拂个一干二净,然后,把人家打发走。
在那个年代,以他的身份,妻妾成群已属正常,嫖宿召妓也不为过,像他的顶头上司曹锟、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都是美女、帅男兼爱的纵欲主义干将。
比之领导们,同僚们,部下们,吴玉帅算是清教徒矣。
北洋军人多不读书,所以,吴的秀才出身就成了很让哥们儿羡慕的光辉履历。
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里,秀才只不过是头一磴台阶,实在没什么可吹的。
可在一群半文盲里,秀才成了金光闪闪的最高学历,所以,即使吴佩孚当了威风八面的“孚威上将军”后,军政界当面以“玉帅”、“吴二哥”恭维之,背后却全起哄叫他“吴秀才”;而他也欣然默认了。
后世的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显然也看重这个北洋军人的文化背景,在他的那套《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干脆叫吴为“学者军阀”。
从秀才到大帅,吴佩孚靠的是少时清贫的砥砺与传统文化的铺垫——只不过,后者把他夯得太实了。
在北洋巨头中,吴的起步不算早,辈份更不算高——当段祺瑞成为中华民国首任陆军总长时,当张作霖贵为奉天督军兼省长时,当冯国璋以江苏都督职实领直系诸军时,他吴佩孚不过是中华民国陆军第三师的副官长、炮兵三团团长,曹锟师长手下的一员干将而已。
数年过去后,当比他还小一岁的张作霖成为奉军“老帅”时,他虽已成为曹锟大帅的智囊,但职务却只是第三师的师长。
对了,这里有个故事:
某次,吴佩孚随曹锟去天津与张作霖会晤,他因屡屡插言而被张作霖好一顿挖苦:
“我同三哥有要事相商,一个师长跟着搀和什么?
要是师长能参加的话,俺奉军有好几个师长哩!
”三哥即曹锟,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那时军阀们素以兄弟相昵称。
颇有自尊的吴佩孚羞恼离去,上车前恨恨地说:
“早晚要让你张胡子认识认识俺这个师长的厉害!
”胡子不是指张作霖的外表,恰恰相反,张作霖还不是满脸胡须,“胡子”是对土匪的另一种叫法,吴佩孚是骂张作霖早年当过土匪。
没过几年,张胡子果然领教了吴佩孚的厉害——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张作霖虽入主了中南海,却不得不邀直奉战争中的死对头、现在的伙伴吴佩孚来京会商国是。
吴大帅抵达时,张在门前谦恭地迎候并亲昵地称其为“大哥”,待吴入室坐定后,开口即说:
“过去一切错误,承兄海涵原谅……” 你看,这个吴秀才是够厉害的吧?
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领军大获成功的例子,前清的曾国藩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无疑,民国初年的吴佩孚也算其一。
吴佩孚因文人领军而成为近代名副其实的儒将。
现在的人动辄就爱把能诌几句打油诗能捏毛笔的官员称为“儒将”,这实在是无知之笔或过誉之辞,读读吴氏的那首《满江红?
登蓬莱阁歌》,就知道何谓“儒将”也:
北望满洲, 渤海中风浪大作。
想当年, 吉江辽沈, 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藩篱, 黑龙江畔列城郭, 到而今倭寇任纵横, 风云恶!
甲午役, 土地削; 甲辰役, 主权堕。
江山如故, 夷族错落。
何日奉命提锐旅, 一战恢复旧山河, 却归来永作蓬山游, 念弥陀。
这词的韵节与行间透出的那股子正气,显然来自岳飞那儿。
傲骨岸然的吴佩孚一生只佩服两个人,一个当然是他的明代乡贤戚继光,爹娘已经将戚大将军的英名嵌在了他身上;而另一个,就是南宋的岳武穆。
有意思的是,岳飞是因坚持抗击外族入侵而被昏庸的朝廷杀害的,那首“怒发冲冠……”的《满江红》也因其忠烈而传诵千秋;同为国之大将军的吴子玉也被怀疑为异族入侵者杀害的,但他的同样也是“仰天长啸”的《满江红》却早被人们遗忘了。
其实,在“五?
四”运动期间,吴将军的这首《满江红》和他的那些反对政府对日本妥协的通电一样就广受赞誉并被传诵一时。
如果——我常爱替古人作这类无谓的假设——吴佩孚不是窝窝囊囊地死在沦陷区的宅第中,而是阵亡在与倭寇决战的国土上,那他的这首词《满江红》难保不会像岳飞的那首千古绝唱一样地刊印于中国人的课本上,让每个受过起码教育的人都知道民国时代有个民族英雄叫吴佩孚,且每读到他的这首诗后一样会“壮怀激烈”;而他身后的“什锦花园胡同”也极可能被改称“佩孚花园胡同”或“子玉胡同”——京城里的那条现在已经十分宽敞通达的“张自忠路”不就是一例?
只是,多情应笑我,历史从不肯“如果”。
我因历史事件而对当事人有兴趣,又因人而对其故居有兴趣。
故居往往是残存某些真相碎屑的旧日磁场。
“什锦花园”正是这样一个诱我前往扫寻点什么的磁场。
意外走到了什锦花园胡同,却不敢肯定会真的走进昔日的“花园”,因为历史的变迁让京城乃至整个中国留下了太多的名不副实的地名。
只是,根据路口那块金属牌的指示,我对本胡同19号心存侥幸:
或许,那儿就是吴的故宅?
于是,我们自西而东,去找19号。
两边是矮而破的街门,一望便知是平民百姓杂处的大院;再往前,两侧有了楼房,是很典型也很难看的那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办公楼。
我的心,渐凉下来。
不觉走到一个并不起眼的大院门口,看墙上的门牌号,是什锦花园胡同23号。
铁栏门大开,传达室墙上,挂有这样一块牌子:
国家经计委运输研究所 不知哪根筋让我一激灵,我突发奇想:
当年的什锦花园也许就藏在这大院里边?
敲窗。
里边看门人出来,不出意料地发问:
找谁?
人面比天气还冷。
我一手举相机一手举一本北京文物书籍,问此地是否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故宅?
人家答非所问:
这里是机关,不许进入。
我正失望,传达室后的一排平房中,挑帘走出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子:
干嘛呢?
记者?
找吴佩孚的家?
对喽,正是这儿。
进来看看吧。
我就管这事呢!
我激动得鼻腔都发酸了(不像是冻的)!
在多年的异乡寻访记忆中,没有哪次能像今天这样巧合与顺畅!
该管事姓刘,叫刘建国,是这家单位管行政后勤的人。
也许难得有人来参观他经手维修过的“花园”,所以,他很热情地领我们从一座高大的白楼前经过,在一座灰砖墙小院门前停步,推开两扇小红门,过了一条窄得只容一人出进的小过道,说声到了,我们就置身于一座修葺一新的典型的北方小四合院中了。
这是我们单位内保留的最后一套完整的老房子了。
原先,大院里有八座这样的小院,一个套一个,个个有长廊相通但又个个不同,非常漂亮!
现在嘛,就这一个了,是去年我张罗着修缮的——刘先生不无惋惜地介绍道。
说实话,一陷入这座小院中,我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造反有理”的“红小将”们居然也有打盹的时候!
大军阀吴佩孚的故宅竟然在国家机关的楼群之中被深藏了一角,尽管已经是十分狭隘的一角!
小院极美,我第一眼看去就有点懵,为这仅存的吴的家园的幽静与优雅而懵得一时无语!
西厢屋有位长者出来探问:
找谁?
刘建国随口打了个招呼,那长者便退回屋里。
看看厢屋门上的牌子,知是该单位的资料室。
小院复归静谧,静谧得如一方琥珀。
我定定地站着,想不起看过的哪座旧日豪宅能留下如此恬然而完美的一角。
完完全全的一座京城四合院,红门红窗红廊柱,灰砖灰瓦灰墙面,北面的正房、东西厢房和南房,都十全十美地呆在正晌的阳光里,东西厢房的四个墙头上,还分别砖刻着松、梅、竹、兰的图案,每一幅都古朴而深邃。
院当中,是一株巨大的古树,虬龙一样弯向天空。
因是寒冬,整树失绿,但漫天挣扎向上的枝杈犹体现了倔强的生命力。
树下,有一对很旧的汉白玉的雕花金鱼缸,缸体上缕空的雕花极是瑰丽。
另一边,一方石桌,细辨桌侧四周,竟是十二生肖的浮雕!
我失声叹曰:
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石鱼缸与石桌!
这三样东西是老房子的原物,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刘建国说着。
你们来晚了,早来一个多月,这棵老树还是绿的呢,满满的叶子遮了大半个院子,人在树下很凉快。
六十年前,那位寓居此地的中国老军人一定常在这树下徘徊,并百无聊赖地伏身金鱼缸前发怔——有回忆文章说,吴佩孚每每愿在鱼缸前与来客洽谈。
他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回到北京的——噢,那时,北京因已不再是国之首都而被国民政府改叫了“北平”。
驻守北平的是他的北洋故友和夙敌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
张学良因上一年稀里糊涂地丢失了东三省而受到世人谴责,他不得不辞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要职,专任北平靖绥公署主任。
北洋时的少帅给了父辈的“玉帅”好大的面子,亲率北平的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
从前门火车站到东四附近的什锦花园,上百辆小汽车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可谓极一时之盛。
张学良为他安排的居所是前京兆尹(北洋时期北京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薛之珩的公馆,亦即什锦花园。
张学良为他提供的生活费也相当可观——每月高达四千银元。
然而,好一个旧朝败将吴子玉,居然当众冷落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甚至连起码的礼节都懒得回,就在他的庞大卫队的簇拥下登车而去。
当晚,他回访张学良时,刚一坐定,就发火了:
“沈阳事件,你为什么不抵抗?
”原来,吴当众冷淡张学良,是痛恨他去年“九?
一八”时的糟糕表现!
回到故都的吴子玉虽还不到六十岁,但已没了壮年时的豪气。
第一次直奉大战前,在与张学良父亲的几十万大军交火时,这位直军总司令的“战前动员”曾是何等的惊天动地:
此次系共和与帝制之最后战争,胜则我将解甲归田,裁兵恤民;败则我惟一死,以谢天下!
我妻已死,我子豚犬,杀之可也。
真是咬钢嚼铁!
如果战败,我就自杀,反正发妻(李氏)已逝,继子(他没有亲生儿子)就当猪狗一样杀了也无所谓——有这样视死如归的指挥者,哪个将士不用命?
于是,就有了直军的一次次大捷,有了吴氏傲视九州的威风。
民国九年至十二年,直拗的直军首领吴佩孚不可一世呐!
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晚年定居北平的吴大帅,只有捋着花白的胡须长叹的份儿了。
困居这所院子里的前蓬莱秀才,已不再是北洋集团里率先挥师南征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更不再是“五?
四”时期万众景仰的“爱国将领”,他麾下的五六十万大军(号称百万)早已被本军叛将冯玉祥拆散并被国民党北伐军收买或击溃。
四面楚歌之际,他被仰慕他的四川军阀杨森迎迓进川,一住就是五年。
他失败了,却不肯向胜利者献媚。
他的部下,多数去了南京接受新朝的委任状了,他明白,那只不过是扔掉鸡毛帚高筒军帽换一顶前仰后伏的大檐帽而已;而他的那些北洋政界同僚、军中袍泽们,多去天津的洋人租界里当了富甲一方的寓公兼实业家。
只有他耿耿如初,两袖清风,一怀未酬之志,在远离南京的瞿塘峡口白帝城中,靠不断吟咏杜工部写于斯的悲秋韵句抚慰自己,靠研读《周易》夜观天象饮酒赋诗打发日子。
我曾三上白帝城。
长江三峡最诱人的历史遗物是悬棺,而白帝城可算是万里长江上的最大一块悬棺——多少历史朽骨和秘笈被永远封存于这座小小的江山之巅了。
刘备托孤诸葛亮后,在此一命呜呼,恢复刘汉王朝的宏愿自兹飘落江底;后来,落魄的杜甫气喘吁吁地爬了上来,望着一江浊浪和无边落木,肝肠寸断地吟下了一堆千古绝唱,一代诗圣用诗句宣告了他对世间的绝望;而近代建于白帝庙西侧的那栋小小的西洋楼,又像活棺材一样闷住了吴子玉这位失意大将军的冲天豪气,使他反反复复闻到了刘备、孔明、杜甫这些落魄国士的阴魂的幽泣。
小小的白帝城之巅,有座三层西洋小楼,这原是一位川籍小军阀建的,其风格与朱壁飞檐的白帝庙极不协调,吴佩孚入川后,即被杨森安排在此居住。
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人家也怕他进了成都或重庆后影响了自家的统治,所以,把他像白帝庙堂里的众多三国偶像一样地供养起来了。
老吴不是阿斗,明白自己的处境,便天天听滔滔江水低哭,看森森夔门禁闭。
这位风骨嶙峋的丈夫,对成为王败为寇的道理理解得透着呢!
于是,他一次次用诗来检讨起自己,意气颇低沉。
且读以下三首:
我昔屠刀未放下, 气吞七雄小五霸。
宁知世事不可为, 刚愎自用遭人骂。
往事不堪重提起, 魂魄收入诗囊里。
世外有世天外天, 从前种种昨日死。
曾统貔貅百万兵, 时衰蜀道苦长征。
疏狂竟误英雄业, 患难偏增伉俪情。
楚帐悲歌骓不逝, 巫山凄咽雁孤鸣。
匈奴未灭家何在?
望断秋风白帝城。
他终于承认自己失败了,因为“刚愎自用”,因为“疏狂”。
他想起英雄末路的项羽,感叹自己未能与敌寇搏杀的遗憾,最后,是一声长叹:
从前的一切,都已经死了!
单从“言志”来讲,他比别的下野军阀强,他能把心里的苦闷言出来。
只是,现今已成孤岛的白帝城里,了无吴氏遗迹。
庙里有三国时期蜀国的王相将们的塑像,庙外有罕见的周恩来题写的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全诗,亭柱上镌有杜工部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联句,唯在此居住时间最长且有过峻拒倭寇拉拢壮举的历史名人吴子玉在此销声匿迹,尽管他在此书写过大批的诗文。
现在的西洋楼,门外挂着“奉节县白帝城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木牌。
一楼是卖白帝城古碑拓片和当地书法家作品的门市。
我没兴趣。
想登二楼一览,总以为吴氏会把英雄末路的心态镌刻在哪层楼的哪根柱子上。
有人在窄而陡的木楼梯口拦住我,说:
要看哪一国(个)的字嘛,要买就在一楼买好喽。
在白帝城,我没找到一页与吴佩孚有关的纸——无论是遗碑拓片还是文字介绍。
人们用政治的橡皮把他的遗痕擦得干干净净。
上世纪的民国初期,“吴佩孚”这三个字是无法擦掉的,报章上隔三叉五地就会出现这个名字。
这是个让很多人看了高兴又有很多人看了不舒服的名字。
想当年,吴佩孚是何等威风!
他率部南征,出直隶而河南而湖北而湖南,势如破竹,一气逼近广东。
本来,袁世凯已经凭武力统一了中国,但老袁的“帝制自为”又惹恼天下领兵人,西南遂竞起割据政权。
老袁死后,段祺瑞领衔内阁,便迭令各省取消独立膺服中央,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湖南书生毛润芝后来说得真好!
),段总理便下令大军南征。
北军南下,气壮山河,而其中最锐者,即吴佩孚的陆军第三师。
谁都明白,只要这位中将师长一声令下,他的军纪严明、军威凛然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而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捷报频传之际,吴佩孚却突然按兵不动了,他开始匪夷所思地与占领区的军政首领与士绅终日饮酒赋诗,不再言战!
军民融洽如一人,试看老段能奈何?
对了,吴的那首不同凡响的《满江红》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写的,他甚至请人谱上了曲,成为本军的军歌,每逢出征或年节日或自己的生日,便让部将们唱上一遍,好不悠哉!
老段急得亲往前线劳军,并破格授予保定速成学堂的测量科学生出身的吴佩孚以“孚威将军”的殊荣和勋位,以励其一鼓作气扫平两广进而统一中华。
可是,吴佩孚愣是不买账!
过了段时间,竟开始擅自撤军,把北洋军打下的大片江山拱手送还南方!
说实话,没有吴佩孚的罢兵,就没有日后孙中山和他的党徒们在苏联人的倾力扶助下统一粤省的可能,也就更没有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倾巢出兵浴血“北伐”一统九州的成功。
哎!
一部民国史到底怎么落笔,还真的挺难说哩!
吴佩孚息兵衡阳的日子里,博得了极好的声誉,因为他罢兵的理由是呼吁和平,所谓“罢兵主和”是也。
为什么这样做呢?
“阋墙煮豆,何敢言功?
”“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
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吴佩孚通电语),所以,俺不干了!
老段气得直蹦:
“秀才造反啦!
” 其实朝野都明白,战功赫赫的吴秀才理应被任命为湖南省督军或省长。
老段没把吴佩孚放在眼里,安排了别人,这才惹得秀才造了反。
你说,手握重兵者带兵打仗不就是为捞这位子坐嘛!
段总理不论功行赏,也许是怕性情刚毅的吴佩孚坐大不能羁縻吧?
正在北京政府为吴的罢兵猜测不已之际,湖南那边又传来吴氏的“四不主义”:
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
果然,他吴子玉一生没破此“四戒”。
在那个纷纷借重洋人的时代,敢公然向国人做出这样承诺者,绝无仅有。
就在吴佩孚与政府大打通电战时,民国八年(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强烈要求政府拒签出让我家乡青岛的《巴黎和约》,游行途中示威者捣毁并焚烧了被舆论认定是卖国官员的私宅。
政府认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了,于是,军警们便逮捕了三十来个“暴徒”。
不曾想,却于次日激起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
然而,呼吁拒签的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而统治集团内部怕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忍辱接受这一条约。
关键之时,远在南岳衡山之下的吴佩孚发言了,这个“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区区师长,在湖南驻地公开越过好多级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一纸电文搅扰了中国政坛上的死水:
5月9日孚威将军的通电曰:
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
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数日后,他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政府签约,此即轰动一时的“删电”(“删”为15日的代称):
顷接京电,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
……某(吴及签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