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教案3.docx
《秦汉文学教案3.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秦汉文学教案3.docx(8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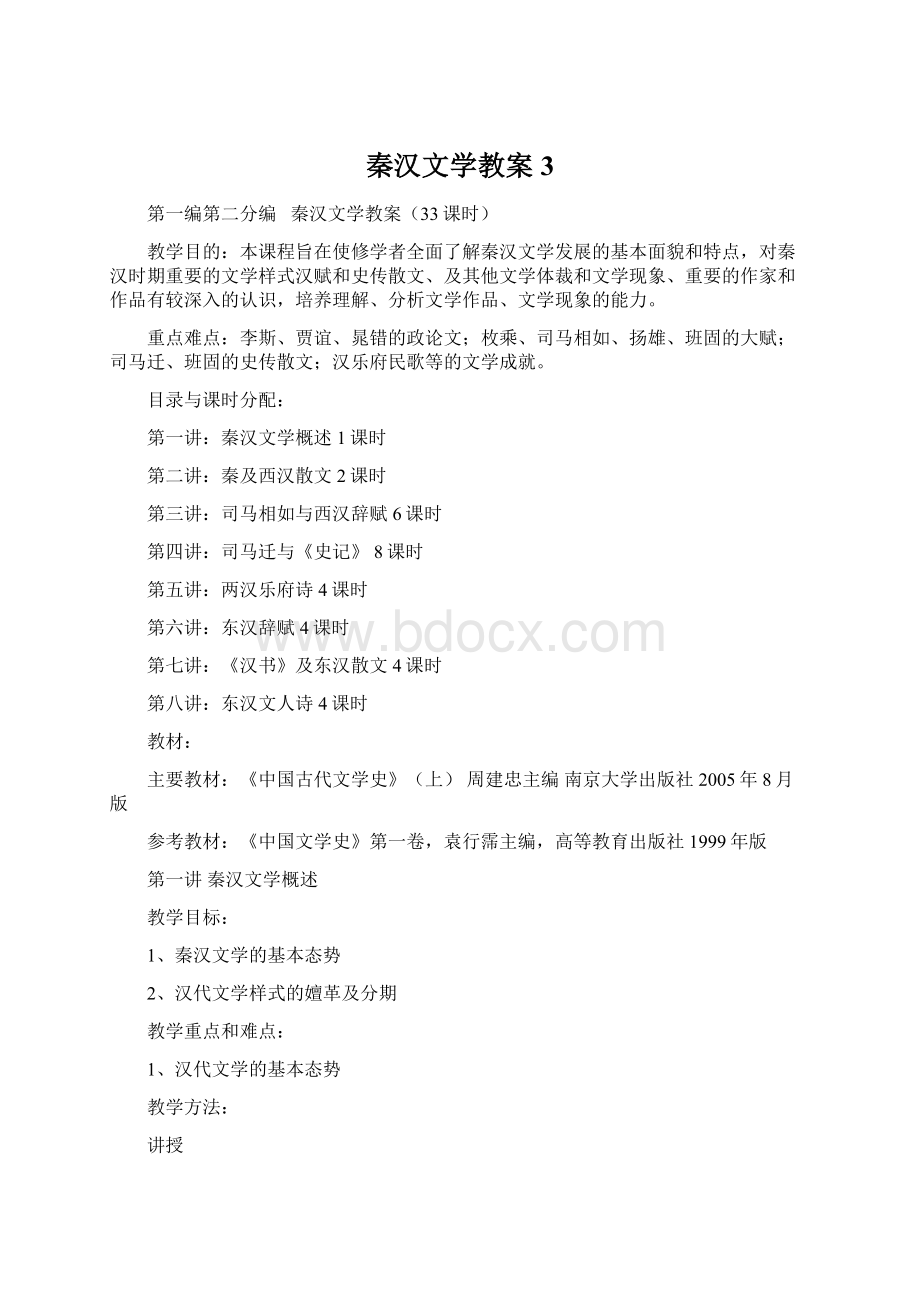
秦汉文学教案3
第一编第二分编 秦汉文学教案(33课时)
教学目的:
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秦汉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对秦汉时期重要的文学样式汉赋和史传散文、及其他文学体裁和文学现象、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较深入的认识,培养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
重点难点:
李斯、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的大赋;司马迁、班固的史传散文;汉乐府民歌等的文学成就。
目录与课时分配:
第一讲:
秦汉文学概述1课时
第二讲:
秦及西汉散文2课时
第三讲:
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6课时
第四讲:
司马迁与《史记》8课时
第五讲:
两汉乐府诗4课时
第六讲:
东汉辞赋4课时
第七讲:
《汉书》及东汉散文4课时
第八讲:
东汉文人诗4课时
教材:
主要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周建忠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参考教材: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一讲秦汉文学概述
教学目标:
1、秦汉文学的基本态势
2、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汉代作家群体的形成、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汉代文学的嬗变与分期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朝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系列改革以适应统一的需要。
秦朝文化上统一文字给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暴政统治,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强盛的大汉王朝,汉初采取了一些与民生息的政策,如制定律令、减轻田赋、宽政省刑等,使国力日益强盛。
文化思想上除秦挟书律和訞言诽谤之罪,尊黄老无为之说,对各家学说也采取了宽容并蓄的政策,思想文化比较活跃自由。
汉初为了娱乐和制礼作乐的需要,沿承秦制设置了乐府机构。
一些楚歌广为传唱。
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实行统一货币、均输平准、官营盐铁等经济措施,确保国力富足;北击匈奴、打通西域,扩大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帝国进入了空前强盛的时期。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各类矛盾日益激烈,王莽篡权改制,更加激化了矛盾,导致绿林、赤眉的起义,西汉王朝随之覆灭。
汉光武帝刘秀依靠豪强势力夺取政权,于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王朝。
东汉土地财富集中问题仍没解决。
统治集团外戚、宦官长期争斗、吏治黑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在黄巾起义和各路豪强割据势力的打击下,终于被魏取而代之。
秦汉文学就是从秦始皇统一到三国时期魏代汉,这一时期的文学。
一、汉代作家群体的形成
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第一,汉代形成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
因此,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
事实上,汉代士人的阅读范围并不限于五经,而是广泛得多,尤其是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
西汉时期,解读楚辞是一种专门学问。
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硃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同时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因此得到提拔。
武帝还令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作注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
”(《汉书·淮南王传》)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汉赋和楚辞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种新文体确立之后,也和楚辞一样成为士人贵族的诵读物,汉宣帝时还有过这样的事情:
王褒等人用诵读奇文及自己作品的方法为宣帝的太子、亦即后来的元帝治病解闷,其中的奇文当有楚辞类作品。
这种精神疗法效果明显,不但太子得以康复,而且经他倡导在后宫形成了诵读王褒赋的风气。
(事见《汉书·王褒传》)
到了东汉时期,人们诵读辞赋的兴趣依然很浓,就连贵族妇女也主动参与,出现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的专门著作。
诵读辞赋在汉代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是士人文化素养的标志。
虽然诵读辞赋者并未都成为辞赋作家,但汉代许多人确实是从诵读辞赋开始而顺理成章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扬雄少而好学,“顾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他诵读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赋,并且加以摹拟,他本人也成了汉代重要的作家。
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他还创作诗赋等作品多篇。
汉代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汉代的文人也以辞赋家居多。
第二,以文才取士的用人制度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
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
两汉选拔人才注重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并不是他们经通行修,而是在于他们的文才。
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制度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却起到了推动作用。
汉代不仅中央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
第三、诸侯王养士的风气
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
“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如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
”(《汉书·地理志》)投奔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枚乘、邹阳、严忌,他们都擅长辞赋。
后来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见刘濞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就离开吴地而投奔梁孝王。
梁孝王待他们为上宾,司马相如也弃官前往梁国,宾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
参加梁园唱和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韩安国等。
“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
”(《汉书·地理志》)流传下来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刘安的宾客之手。
《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82篇,淮南王群臣赋44篇。
显然,淮南王群臣不但著书立说,而且还是一个从事辞赋创作的群体。
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
第四,帝王的爱好与提倡
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职。
因擅长文章辞赋而被录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扬雄等。
有些人虽然不是靠文学创作才能而进入仕途,但是,他们成为朝廷命官之后,在天子的倡导下也加入了辞赋创作的行列。
自武帝起,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
东汉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辞赋,但是,兴起于西汉的进献辞赋之风依然在东汉延续,基本上保持了它的连贯性,许多文人就是因文才出众而倍受青睐。
东汉政权长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东汉许多著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
杜笃曾任车骑将军马防的从事中郎,战殁于射姑山;傅毅任军司马,马防以师友之礼待之。
(《后汉书·文苑列传》)马融先后依附大将军邓骘、梁冀。
(《后汉书·马融列传》)在那些显赫的外戚中,窦宪网罗的文人最多,“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
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
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
”(《后汉书·文苑列传》)当时几位著名作家都在窦宪府供职,成为历史上一件盛事。
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
汉代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第五,乐府、东观等设立
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
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
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荟萃之处,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
东观是文人向往的地方,“是时学者称东观以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
”(《后汉书·窦融列传》)东观任职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不过,既然众多作家汇集在一起,当然少不了诗文唱和之类的活动。
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
学生由州郡选送,一度多达千人。
灵帝下诏,为在鸿都门就学的乐松、江览等32人图像立赞,用以激励学者。
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历史上是首创,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
第六,游宦风气
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
西汉早期,文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
武帝朝至东汉初期,游宦之风稍衰。
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
“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
”(《后汉书·王符列传》)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成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
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
二、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第一,以巨丽为美的审美风尚。
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
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
司马相如说过:
“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
”(《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
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
在史传文学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经济文化等面面俱到,远至黄帝,近至当世,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类人物纷至沓来。
就是篇幅有限的郊祀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
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第二,文人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
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
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
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
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
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
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谨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是主要潮流。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
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后汉书·党锢列传》)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精神,好高尚义、轻死重气的品格,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并产生了许多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作品。
第三,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汉代文学在表现士人的进取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士人的命运还和所处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
对于古代士人来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魄的感慨。
在抒发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时,汉代文学也显示出历史上升期的特点。
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幽怨和不满,但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文人所感慨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西汉昌盛时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
而从西汉后期开始,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命运方面,正如扬雄所说“遇不遇命也”(《汉书·扬雄传》),由西汉昌盛期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
到了东汉的衰落期,文人们则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
第四,从批判到歌颂再到批判的创作态度。
西汉朝廷是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短暂的楚汉相争而建立起来的。
批判秦朝的暴政,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汉初文学的重要内容。
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到司马迁的《史记》,都贯穿着对历史的批判精神。
从武帝开始,思想界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系的构筑,与此相应,文学也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
从东汉开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
从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到郦炎、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精神日益强烈。
批判的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
汉代文学以历史的批判发轫,经由昌盛期的歌功颂德,最后又以现实的批判而告终,完成了一次循环。
不过,和前期的历史批判相比,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
和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
汉初的枚乘、庄忌、邹阳等人游食诸侯间,为大国上宾,他们来去自由,具有独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纵横家的品性。
从武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迎合天子的口味而创作。
东汉时期被外戚招纳的幕僚文人,有时也要牺牲自己的人格为主人唱赞歌,他们和宫廷侍从文人一样,都是不自由的。
这些依附于天子、外戚的作家,多数是文人兼学者的类型,王褒、扬雄、刘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此。
从西汉末年起,向慕人格独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队伍中萌生,扬雄、班固、张衡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摆脱侍从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从事创作。
东汉后期的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从他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人的影子。
从汉初出处从容、高视阔步于诸侯王之间的枚乘、邹阳等人,到汉末赵壹、祢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汉代文人在经历了一段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且达到更高的层次。
第五,由浪漫走向现实。
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人神同游、人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
进入东汉以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
把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和班固、张衡的同类作品相比,把《史记》和《汉书》相比,都可以看到浪漫和现实的差异。
当然,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
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并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
文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
至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政论,在东汉也问世了。
第六,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共同繁荣。
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两汉时期存在采诗制度,通过采集民间歌谣用以充实乐府的乐章,有时也用来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风民俗。
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
这种新的诗歌样式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的加以模仿,于是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乐府诗中也有文人的作品。
民间五言诗在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又日益走向成熟。
除诗歌外,汉代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史记》、《吴越春秋》都把许多民间传说写入书中,增加了这两部作品的传奇色彩。
三、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相继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
汉代文学和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交流是相互的,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
西汉时期,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学,郡国置五经率史。
汉代经学教育为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并不期待就学人员成为作家,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却具备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
自公孙弘倡导经学教育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
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主要是通过他们得以实现的。
第一,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
无论是辞赋、诗歌还是散文,也不管是出自文人之手还是乐府民歌,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从而形成汉代文学的唯美之潮。
汉代文学对现实的一切都怀着极大兴趣去描绘、去表现,而且漫无节制地铺陈扩展。
进行罗列时不忌堆砌,不避重复,描写叙述过程中靡丽夸饰、多闳衍之辞,许多作品因此显得笨拙、呆板。
和汉代文学铺张扬厉风气相映成趣的是汉代经学的繁琐解读习尚,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二三万字。
更有甚者,秦近君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之义,竟至十万言。
汉代文学和经学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都是不厌其繁,多多益善,铺天盖地而来。
这使得某些文学作品篇幅过长,如同辞典字书,令人不能卒读;经学也因其过于细碎繁琐、牵强附会而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第二,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
汉代文学作品经常出现神仙世界的画面,人和神灵可以自由往来,许多作品都流露出长生不死的幻想。
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
汉代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后来又一度兴起谶纬之学,“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
”五经之义皆以谶决,用图谶来附会人事。
汉代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神化,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虚妄之学。
汉代经学和经学思维机制有相通之处,都以想象沟通天和人,架起现实生活和彼岸神灵世界的桥梁。
刘勰称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文心雕龙·正纬》),这话有一定道理。
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
第三,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
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许多文人不但摹拟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时代的文人也相互模仿。
这种摹拟有题材方面的,也有文体方面的,甚至具体的谋篇布局也多有雷同之处。
流行于汉代的大赋、骚体赋、七体、九体、设辞等,都留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
汉代文人在摹拟他人作品过程中也有创新,但在整体格局上的因循守旧是显而易见的。
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强调传授先师之言。
不依先师之言而断以己意,就会被视为轻侮道术,受到学界的谴责。
汉代经学的传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惰性,使人受到很大束缚。
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本质是相同的。
只有那些在经学上不守章句、不拘师法家法的博通之士,在文学创作上才真正有所建树;汉代有创造力的文人,确实也都突破了经学传授上陈陈相因的传统。
从总体上看,汉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
作为大汉天声的辞赋,从东汉中期起,大赋呈现衰微趋势,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
正统的史传文学作品也出现由繁到简的趋势。
把《汉书》和《史记》相比,班固删去了司马迁许多精彩细致的叙述和描写,篇幅大为减少。
从文学样式上看,短小精练的五言诗从附庸变为大国,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霸主地位。
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似,从东汉初期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为的是便于传授。
有的是一删再删,解经文字大幅度精减,是对以往烦琐之风的有力矫正。
第四,汉代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思潮也有很深的影响,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的籓篱,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许多作家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重身份。
《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
《毛诗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
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色彩。
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
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对汉赋的评价,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各家的褒贬毁誉不同,但都是从经学的基点上立论,以经论屈骚,以经论汉赋,在这点上并无根本的差异。
即使像王充那样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评论各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也经常以儒家经典为依据。
汉代文学思潮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这就是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提出的“发愤著书”说,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压抑以后的情怀爆发。
但是,在经学风气弥漫的汉代,司马迁的这种文学理论难以得到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击。
四、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一)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
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
第一,赋体的兴盛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
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
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
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
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
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
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拟屈原的《离骚》、《九章》,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
西汉刘向曾编集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人摹拟之作,署名《楚辞》。
其中被收录作品的汉代作家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
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又附加了自己的《九思》。
除此之外,扬雄、冯衍、蔡邕、赵壹等人也有楚辞体作品传世。
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许多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因此,许多楚辞类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
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
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