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论.docx
《唐诗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唐诗论.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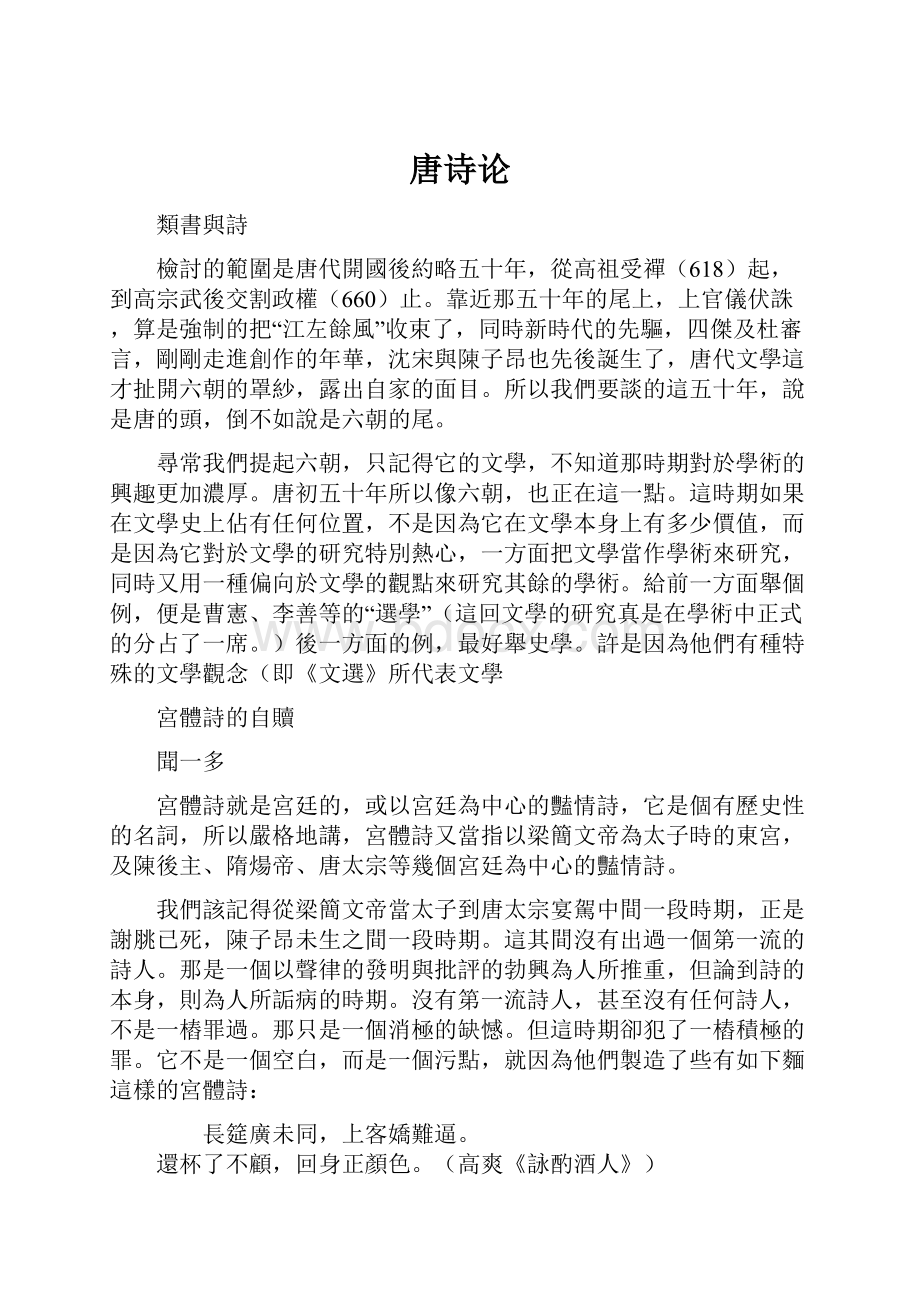
唐诗论
類書與詩
檢討的範圍是唐代開國後約略五十年,從高祖受禪(618)起,到高宗武後交割政權(660)止。
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制的把“江左餘風”收束了,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傑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後誕生了,唐代文學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露出自家的面目。
所以我們要談的這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
尋常我們提起六朝,只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於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
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
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上佔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於文學的研究特別熱心,一方面把文學當作學術來研究,同時又用一種偏向於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其餘的學術。
給前一方面舉個例,便是曹憲、李善等的“選學”(這回文學的研究真是在學術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
)後一方面的例,最好舉史學。
許是因為他們有種特殊的文學觀念(即《文選》所代表文學
宮體詩的自贖
聞一多
宮體詩就是宮廷的,或以宮廷為中心的豔情詩,它是個有歷史性的名詞,所以嚴格地講,宮體詩又當指以梁簡文帝為太子時的東宮,及陳後主、隋煬帝、唐太宗等幾個宮廷為中心的豔情詩。
我們該記得從梁簡文帝當太子到唐太宗宴駕中間一段時期,正是謝脁已死,陳子昂未生之間一段時期。
這其間沒有出過一個第一流的詩人。
那是一個以聲律的發明與批評的勃興為人所推重,但論到詩的本身,則為人所詬病的時期。
沒有第一流詩人,甚至沒有任何詩人,不是一樁罪過。
那只是一個消極的缺憾。
但這時期卻犯了一樁積極的罪。
它不是一個空白,而是一個污點,就因為他們製造了些有如下麵這樣的宮體詩:
長筵廣未同,上客嬌難逼。
還杯了不顧,回身正顏色。
(高爽《詠酌酒人》)
眾中俱不笑,座上莫相撩。
(鄧鑒《奉和夜聽妓聲》)。
這裏所反映的上客們的態度,便代表他們那整個宮廷內外的氣氛。
人人眼角裏是淫蕩:
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橫陳。
(鮑泉《敬酬劉長史詠名士悅傾城》)
人人心中懷著鬼胎:
春風別有意,密處也尋香。
(李義府《堂詞》)
對姬妾娼妓如此,對自己的結髮妻亦然(劉孝威《郡縣寓見人織率爾贈婦》便是一例)。
於是髮妻也就成了倡家。
徐悱寫得出《對房前桃樹詠佳期贈內》那樣一首詩,他的夫人劉令嫻為什麼不可以寫一首《光宅寺》來賽過他?
索性大家都揭開了:
知君亦蕩子,賤妾自倡家。
(吳均《鼓瑟曲有所思》)
因為也許她明白她自己的秘訣是什麼。
自知心所愛,出入仕秦宮。
誰言連屈尹,更是莫遨通?
(簡文帝《豔歌篇》十八韻)
簡文帝對此並不詫異,說不定這對他,正是件稱心的消息。
墮落是沒有止境的。
從一種變態到另一種變態往往是個極短的距離,所以現在像簡文帝《孌童》,吳均《詠少年》,劉孝綽《詠小兒采蓮》,劉遵《繁華應令》,以及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類作品,也不足令人驚奇了。
變態的又一型類是以物代人為求滿足的對象。
於是繡領,袹腹,履,枕,席,臥具……全有了生命,而成為被玷污者。
推而廣之,以至燈燭,玉階,梁塵,也莫不踴躍地助他們集中意念到那個荒唐的焦點,不用說,有機生物如花草鶯蝶等更都是可人的同情者。
羅薦已擘鴛鴦被,綺衣複有葡萄帶。
殘紅豔粉映簾中,戲蝶流鶯聚窗外。
(上官儀《八詠應制》)
看看以上的情形,我們真要疑心,那是作詩,還是在一種偽裝下的無恥中求滿足。
在那種情形之下,你怎能希望有好詩!
所以常常是那套褪色的陳詞濫調,詩的本身並不能比題目給人以更深的印象。
實在有時他們真不像是在作詩,而只是制題。
這都是慘澹經營的結果:
《詠人聘妾仍逐琴心》(伏知道),《為寒床婦贈夫》(王胄),特別是後一例,盡有“閨情”,“秋思”,“寄遠”一類的題面可用,然而作者偏要標出這樣五個字來,不知是何居心。
如果初期作者常用的“古意”、“擬古”一類曖昧的題面,是——種遮羞的手法,那麼現在這些人是根本沒有羞恥了!
這由意識到文詞,由文詞到標題,逐步的鮮明化,是否可算作一種文字的裎裸狂,我不知道。
反正讚歎事實的“詩”變成了標明事類的“題”之附庸,這趨勢去《遊仙窟》一流作品,以記事文為主,以詩副之的形式,已很近了。
形式很近,內容又何嘗遠?
《遊仙窟》正是宮體詩必然的下場。
我還得補充一下宮體詩在它那中途丟掉的一個自新的機會。
這專以在昏淫的沉迷中作踐文字為務的宮體詩,本是衰老的,貧血的南朝宮廷生活的產物,只有北方那些新興民族的熱與力才能拯救它。
因此我們不能不慶倖庾信等之入周與被留,因為只有這樣,宮體詩才能更穩固地移植在北方,而得到它所需要的營養。
果然被留後的庾信的《烏夜啼》,《春別詩》等篇,比從前在老家作的同類作品,氣色強多了。
移植後的第二三代本應不成問題。
誰知那些北人骨子裏和南人一樣,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麗的毒素的引誘,他們馬上又屈服了。
除薛道衡《昔昔鹽》,《人日思歸》,隋煬帝《春江花月夜》三兩首詩外,他們沒有表現過一點抵抗力。
煬帝晚年可算熱忱的效忠於南方文化了,文藝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煬帝還要熱忱。
於是庾信的北渡完全白費了。
宮體詩在唐初,依然是簡文帝時那沒筋骨、沒心肝的宮體詩。
不同的只是現在詞藻來得更細緻,聲調更流利,整個的外表顯得更乖巧,更酥軟罷了。
說唐初宮體詩的內容和簡文帝時完全一樣,也不對。
因為除了搬出那僵屍“橫陳”二字外,他們在詩裏也並沒有講出什麼。
這又教人疑心這輩子人已失去了積極犯罪的心情。
恐怕只是詞藻和聲調的試驗給他們羈系著一點作這種詩的興趣(詞藻聲調與宮體有著先天與歷史的聯繫)。
宮體詩在當時可說是一種不自主的、虛偽的存在。
原來從虞世南到上官儀是連墮落的誠意都沒有了。
此真所謂“萎靡不振”!
但是墮落畢竟到了盡頭,轉機也來了。
在窒息的陰霾中,四面是細弱的蟲吟,虛空而疲倦,忽然一聲霹靂,接著的是狂風暴雨!
蟲吟聽不見了,這樣便是盧照鄰《長安古意》的出現。
這首詩在當時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放開了粗豪而圓潤的嗓子,他這樣開始: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
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
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
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
……
這生龍活虎般騰踔的節奏,首先已夠教人們如大夢初醒而心花怒放了。
然後如雲的車騎,載著長安中各色人物panorama式的一幕幕出現,通過“五劇三條”的“弱柳青槐”來“共宿娼家桃李蹊”。
誠然這不是一場美麗的熱鬧。
但這顛狂中有戰慄,墮落中有靈性:
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
比起以前那光是病態的無恥:
相看氣息望君憐,誰能含羞不肯前!
(簡文帝《烏樓曲》)
如今這是什麼氣魄!
對於時人那虛弱的感情,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
最後:
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
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
似有“勸百諷一”之嫌。
對了,諷刺,宮體詩中講諷刺,多麼生疏的一個消息!
我幾乎要問《長安古意》究竟能否算宮體詩?
從前我們所知道的宮體詩,自蕭氏君臣以下都是作者自身下流意識的口供,那些作者只在詩裏,這回盧照鄰卻是在詩裏,又在詩外,因此他能讓人人以一個清醒的旁觀的自我,來給另一自我一聲警告。
這兩種態度相差多遠!
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
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這篇末四句有點突兀,在詩的結構上既嫌蛇足,而且這樣說話,也不免暴露了自己態度的褊狹,因而在本篇裏似乎有些反作用之嫌。
可是對於人性的清醒方面,這四句究不失為一個保障與安慰。
一點點藝術的失敗,並不妨礙《長安古意》在思想上的成功。
他是宮體詩中一個破天荒的大轉變。
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頹廢,教給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給他欲望的幻滅。
這詩中善與惡都是積極的,所以二者似相反而相成。
我敢說《長安古意》的惡的方面比善的方面還有用。
不要問盧照鄰如何成功,只看庾信是如何失敗的。
欲望本身不是什麼壞東西。
如果它走人了歧途,只有疏導一法可以挽救,壅塞是無效的。
庾信對於宮體詩的態度,是一味地矯正,他仿佛是要以非宮體代宮體。
反之,盧照鄰只要以更有力的宮體詩救宮體詩,他所爭的是有力沒有力,不是宮體不宮體。
甚至你說他的方法是以毒攻毒也行,反正他是勝利了。
有效的方法不就是對的方法嗎?
矛盾就是人性,詩人作詩本不必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原來《長安古意》的“年年歲歲一床書”,只是一句詩而已,即令作詩時事實如此,大概不久以後,情形就完全變了,駱賓王的《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便是鐵證。
故事是這樣的:
照鄰在蜀中有一個情婦郭氏,正當她有孕時,照鄰因事要回洛陽去,臨行相約不久回來正式成婚。
誰知他一去兩年不返,而且在三川有了新人。
這時她望他的音信既望不到,孩子也丟了。
“悲鳴五裏無人間,腸斷三聲誰為續”!
除了駱賓王給寄首詩去替她申一回冤,這悲劇又能有什麼更適合的收場呢?
一個生成哀豔的傳奇故事,可惜駱賓王沒趕上蔣防、李公佐的時代。
我的意思是:
故事最適宜於小說,而作者手頭卻只有一個詩的形式可供採用。
這試驗也未嘗不可作,然而他偏偏又忘記了《孔雀東南飛》的典型。
憑一枝作判詞的筆鋒(這是他的當行),他只草就了一封韻語的書劄而已。
然而是試驗,就值得欽佩。
駱賓王的失敗,不比李百藥的成功有價值嗎?
他至少也替《秦婦吟》墊過路。
這以“一抔之土未幹,六尺之孤何托”,教歷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膽的文士,天生一副俠骨,專喜歡管閒事,打抱不平,殺人報仇,革命,幫癡心女子打負心漢,都是他於的。
《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裏沒講出具體的故事來,但我們猜得到一半,還不是盧、郭公案那一類的糾葛?
李榮是個有才名道士。
(見《舊唐書·儒學羅道琮傳》,盧照鄰也有過詩給他。
)故事還是發生在蜀中,李榮往長安去了,也是許久不回來,王靈妃急了,又該駱賓王給去信促駕了。
不過這回的信卻寫得比較像首詩。
其所以然,倒不在——
梅花如雪柳如絲,年去年來不自持。
初言別在寒偏在,何悟春來春更思。
一類響亮句子,而是那一氣到底而又纏綿往復的旋律之中,有著欣欣向榮的情緒。
《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的成功,僅次於《長安古意》。
和盧照鄰一樣,駱賓王的成功,有不少成分是仗著他那篇幅的。
上文所舉過的二人的作品,都是官體詩中的雲岡造像,而賓王尤其好大成癖(這可以他那以賦為詩的《帝京篇》、《疇昔篇》為證)。
從五言四句的《自君之出矣》,擴充到盧、駱二人洋洋灑灑的巨篇,這也是宮體詩的一個劇變。
僅僅篇幅大,沒有什麼。
要緊的是背面有厚積的力量撐持著。
這力量,前人謂之“氣勢”,其實就是感情。
有真實感情,所以盧、駱的來到,能使人們麻痹了百餘年的心靈復活。
有感情,所以盧、駱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預言的,“不廢江河萬古流”。
從來沒有暴風雨能夠持久的。
果然持久了,我們也吃不消,所以我們要它適可而止。
因為,它究竟只是一個手段,打破鬱悶煩躁的手段;也只是一個過程,達到雨過天晴的過程。
手段的作用是有時效的,過程的時間也不宜太長,所以在宮體詩的園地上,我們很僥倖地碰見了盧、駱,可也很願意能早點離開他們,——為的是好和劉希夷會面。
古來容光人所羨,況複今日遙相見?
願作輕羅著細腰,願為明鏡分嬌面。
(《公子行》)
這不是什麼十分華貴的修辭,在劉希夷也不算最高的造詣;但在宮體詩裏,我們還沒聽見過這類的癡情話。
我們也知道他的來源是《同聲詩》和《閑情賦》。
但我們要記得,這類越過齊梁,直向漢晉人借貸靈感,在將近百年以來的宮體詩裏也很少人幹過呢!
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棲共一身。
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
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
(《公子行》)
這連同它的前身——楊方《合歡詩》,也不過是常態的,健康的愛情中,極平凡、極自然的思念,誰知道在宮體詩中也成為了不得的稀世的珍寶。
回返常態確乎是劉希夷的一個主要特質,孫翌編《正聲集》時把劉希夷列在卷首,便已看出這一點來了。
看他即便哀豔到如:
自憐妖豔姿,妝成獨見時。
愁心伴楊柳,春盡亂如絲。
(《春女行》)
攜籠長歎息,逶迤戀春色。
看花若有情,倚樹疑無力。
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頭。
相逢不相識,歸去夢青樓。
(《采桑夕)
也從沒有不歸於正的時候。
感情返到正常狀態是宮體詩的又一重大階段。
惟其如此,所以煩躁與緊張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晶瑩的寧靜。
就在此刻,戀人才變成詩人,憬悟到萬象的和諧,與那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的神秘的不可抵抗的美,而不禁受創似地哀叫出來:
可憐楊柳傷心樹!
可憐桃李斷腸花!
(《公子行》)
但正當他們叫著“傷心樹”、“斷腸花”時,他已從美的暫促性中認識了那玄學家所謂的“永恆”——一個最縹緲,又最實在;令人驚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
在它面前一切都變渺小了,一切都沒有了。
自然認識了那無上的智慧,就在那徹悟的一刹那間,戀人也就變成哲人了: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
洛陽女兒好顏色,坐見落花長歎息:
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複誰在!
……古人無複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代白頭翁》)
相傳劉希夷吟到“今年花落……”二句時,吃一驚,吟到“年年歲歲……”二句,又吃一驚。
後來詩被宋之問看到,硬要讓給他,詩人不肯,就生生地被宋之問給用土囊壓死了。
於是詩讖就算驗了。
編故事的人的意思,自然是說,劉希夷洩露了天機,論理該遭天譴。
這是中國式的文藝批評,雋永而正確,我們在千載之下,不能,也不必改動它半點。
不過我們可以用現代語替它詮釋一遍,所謂洩露天機者,便是悟到宇宙意識之謂。
從蜣螂轉丸式的宮體詩一躍而到莊嚴的宇宙意識,這可太遠了,太驚人了!
這時的劉希夷實已跨近了張若虛半步,而離絕頂不遠了。
如果劉希夷是盧、駱的狂風暴雨後寧靜爽朗的黃昏,張若虛便是風雨後更寧靜更爽朗的月夜。
《春江花月夜》本用不著介紹,但我們還是忍不住要談談。
就宮體詩發展的觀點看,這首詩尤有大談的必要。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瀲灩隨波千萬裏,何處春江無月明!
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
在這種詩面前,一切的讚歎是饒舌,幾乎是褻瀆。
它超過了一切的宮體詩有多少路程的距離,讀者們自己也知道。
我認為用得著一點詮明的倒是下麵這幾句:
……江畔何人初見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更敻絕的宇宙意識!
一個更深沉,更寥廓更寧靜的境界!
在神奇的永恆前面,作者只有錯愕,沒有憧憬,沒有悲傷。
從前盧照鄰指點出“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時,或另一個初唐詩人——寒山子更尖酸地吟著“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時,那都是站在本體旁邊淩視現實。
那態度我以為太冷酷,太傲慢,或者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帶點狐假虎威的神氣。
在相反的方向,劉希夷又一味凝視著“以有涯隨無涯”的徒勞,而徒勞地為它哀毀著,那又未免太萎靡,太怯懦了。
只張若虛這態度不亢不卑,沖融和易才是最純正的,“有限”與“無限”,“有情”與“無情”——詩人與“永恆”猝然相遇,一見如故,於是談開了——“江畔何人初見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
”對每一問題,他得到的仿佛是一個更神秘的更淵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滿足了。
於是他又把自己的秘密傾吐給那緘默的對方:
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
因為他想到她了,那“妝鏡臺”邊的“離人”。
他分明聽見她的歎喟:
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
他說自己很懊悔,這飄蕩的生涯究竟到幾時為止!
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
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複西斜!
他在悵惘中,忽然記起飄蕩的許不只他一人,對此清景,大概旁人,也只得徒喚奈何罷?
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
不知乘月凡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這裏一番神秘而又親切的,如夢境的晤談,有的是強烈的宇宙意識,被宇宙意識昇華過的純潔的愛情,又由愛情輻射出來的同情心,這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
從這邊回頭一望,連劉希夷都是過程了,不用說盧照鄰和他的配角駱賓王,更是過程的過程。
至於那一百年間梁、陳、隋、唐四代宮廷所遺下了那分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這樣一首宮體詩,不也就洗淨了嗎?
向前替宮體詩贖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後也就和另一個頂峰陳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張若虛的功績是無從估計的。
四傑
聞一多
繼承北朝系統而立國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個尚質的時期,王楊盧駱都是文章家,“四傑”這徽號,如果不是專為評文而設的,至少它的主要意義是指他們的賦和四六文。
談詩而稱四傑,雖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
是借用,就難免有“削足適履”和“挂一漏萬”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瞭解,詩中的四傑是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人死於非命)——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罵,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
依這樣一個概括、簡明,也就是膚廓的瞭解,“四傑”這徽號是滿可以適用的,但這也就是它的適用性的最大限度。
超過了這限度,假如我們還問到:
這四人集團中每個單元的個別情形,和相互關係,尤其他們在唐詩發展的路線網裏,究竟代表著那一條,或數條線,和這線在網的整個體系中所擔負的任務——假如問到這些方面,“四傑”這徽號的功用與適合性,馬上就成問題了。
因為詩中的四傑,並非一個單純的、統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中包孕著兩個小宗,而兩小宗之間,同點恐怕還不如異點多,因之,在討論問題時,“四傑”這名詞所能給我們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糾葛多。
數字是個很方便的東西,也是個很麻煩的東西。
既在某一觀點下湊成了一個數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觀點下隨便拆開它。
不能拆開,又不能廢棄它,所以就麻煩了。
“四傑”這徽號,我們不能,也不想廢棄,可是我承認我是抱著“息事寧人”的苦衷來接受它的。
四傑無論在人的方面,或詩的方面,都天然形成兩組或兩派。
先從人的方面講起。
將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楊盧駱”這特定的順序,據說寓有品第文章的意義,這是我們熟知的事實。
但除這人為的順序外,好像還有一個自然的順序,也常被人採用——那便是序齒的順序。
我們疑心張說〈裴公神道碑〉“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和郗雲卿〈駱丞集序〉“與盧照鄰、王勃、楊炯文詞齊名”,乃至杜詩“縱使盧王操翰墨”等語中的順序,都屬於這一類。
嚴格的序齒應該是盧駱王楊,其間盧駱一組,王楊一組,前者比後者平均大了十歲的光景。
然則盧駱的順序,在上揭張郗二文裏為什麼都顛倒了呢?
郗序是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講。
張碑,我想是為了心理的緣故,因為駱與裴(行儉)交情特別深,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駱來。
也許駱赴選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見到他。
果然如此,則先駱後盧,是採用了另一事實作標準。
但無論依哪個標準說,要緊的還是在張郗兩文裏,前二人(駱盧)與後二人(王楊)之間的一道鴻溝(即平均十歲左右的差別)依然存在。
所以即使張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實——赴選的先後作為標準,我們依然可以說,王楊赴選在盧駱之後,也正說明了他們年齡小了許多。
實在,盧駱與王楊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
據《唐會要》卷八二,“顯慶二年,詔徵太白山人孫思邀人京,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贄之禮。
”令文是宋之問的父親,而之問是楊炯同寮的好友。
盧與之問的父親同輩,而楊與之問本人同輩,那麼盧與楊豈不是不能同輩了嗎?
明白了這一層,楊炯所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后”,便有了確解。
楊年紀比盧小得多,名字反在盧前,有愧不敢當之感,所以說“愧在盧前”,反之,他與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說“恥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齡的距離更重要的一點,便是性格的差異。
在性格上四傑也天然形成兩種類型,盧駱一類,王楊一類。
誠然,四人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浮躁淺露”不能“致遠”的殷鑒,每人“醜行”的事例,都被謹慎的保存在史乘裏了,這裏也毋庸贊述。
但所謂“浮躁淺露”者,也有程度深淺的不同。
楊炯,相傳據裴行儉說,比較“沉靜”。
其實王勃,除擅殺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殺奴在當時社會上並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過分的“浮躁”。
一個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裏,已經完成了這樣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大唐千歲曆》若干卷,《黃帝八十一難經注》若干卷,《合論》十卷,《續文中子書序詩序》若干篇,《玄經傳》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能夠浮躁到哪里去呢?
同王勃一樣,楊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學者傾向的,這滿可以從他的〈天文大象賦〉和〈駁孫茂道蘇知幾冕服議〉中看出。
由此看來,王楊的性格確乎相近。
相應的,盧駱也同屬於另一類型,一種在某項觀點下真可目為“浮躁”的類型。
久曆邊塞而屢次下獄的博徒革命家駱賓王不用講了,看〈窮魚賦〉和〈獄中學騷體〉,盧照鄰也不像是一個安分的分子。
駱賓王在〈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裏,便控告過他的薄幸。
然而按駱賓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龍頟貴,詎隨中婦鳳樓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氣概的煙幕下實行薄幸而已。
看〈憶蜀地佳人〉一類詩,他並沒有少給自己製造薄幸的機會。
在這類事上,盧駱恐怕還是一丘之貉。
最後,盧照鄰那悲劇型的自殺,和駱賓王的慷慨就義,不也還是一樣?
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動的結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徘側,一悲壯,各有各的姿態罷了。
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發展;由年齡的兩輩,和性格的兩類型,到友誼的兩個集團。
果然,盧駱二人交情,可憑駱的〈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來坐實,而王楊的契合,則有王的〈秋日餞別序〉和楊的〈王勃集序〉可證。
反之,盧或駱與王或楊之間,就看不出這樣緊湊的關係來。
就現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見的說,盧王有兩首同題分韻的詩,盧楊有一首同題同韻的詩,可見他們兩輩人確乎在文酒之會中常常見面。
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談不到。
他們絕少在作品裏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楊在〈王勃集序〉中說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這反足以證明盧駱與王楊屬於兩個壁壘,雖則是兩個對立而仍不失為友軍的壁壘。
於是,我們便可談到他們——盧駱與王楊——另一方面的不同了。
年齡的不同輩,性格的不同類型,友誼的不同集團,和作風的不同派,這些不也正是一貫的現象嗎?
其實,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們早就應該發覺“詩”方面的不同了。
假如不受傳統名詞的蒙蔽,我們早就該驚訝,為什麼還非維持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後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傑”,王楊為“後二傑”?
難道那許多跡象,還不足以證明他們兩派的不同嗎?
首先,盧駱擅長七言歌行,王楊專工五律,這是兩派選擇形式的不同。
當然盧駱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還是五律,而王楊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傳下來,但他們的長處決不在這些方面。
像盧集中的
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贈李榮道士〉)
川光搖水箭,山氣上雲梯(〈山莊休沐〉),
和駱集中這樣的發端:
故人無與晤,安步涉山椒……(〈冬日野望〉),
在那貧乏的時代,何嘗不是些奪目的珍寶?
無奈這些有句無章的篇什,除聲調的成功外,還是沒有超過齊梁的水準。
駱比較有些“完璧”,如〈在獄詠蟬〉之類,可是又略無警策。
同樣,王的歌行,除〈滕王閣歌〉外,也毫不足觀。
便說〈滕王閣歌〉,和他那典麗凝重,與淒情流動的五律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呢!
杜甫〈戲為六絕句〉第三首說“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
”這裏是以盧代表盧駱,王代表王楊,大概不成問題。
至於“劣於漢魏近《風》《騷》”,假如可以解作王楊“劣於漢魏”,盧駱“近《風》《騷》”,倒也有它的妙處,因為盧駱那用賦的手法寫成的粗線條的宮體詩,確乎是《風》《騷》的餘響,而王楊的五言,雖不及漢魏,卻越過齊梁,直接上晉宋了。
這未必是杜詩的原意,但我們不妨借它的啟示來闡明一個真理。
盧、駱與王、楊選擇形式不同,是由於他們兩派的使命不同。
盧駱的歌行,是用鋪張揚厲的賦法膨脹過了的樂府新曲,而樂府新曲又是宮體詩的一種新發展,所以盧駱實際上是宮體詩的改造者。
他們都曾經是兩京和成都市中的輕薄子,他們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庭的墮落,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所以他們的歌聲需要大開大闔的節奏,他們必需以賦為詩。
正如宮體詩在盧駱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