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史记》太史公自序兼谈司马迁及其史记.docx
《第十一讲 《史记》太史公自序兼谈司马迁及其史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十一讲 《史记》太史公自序兼谈司马迁及其史记.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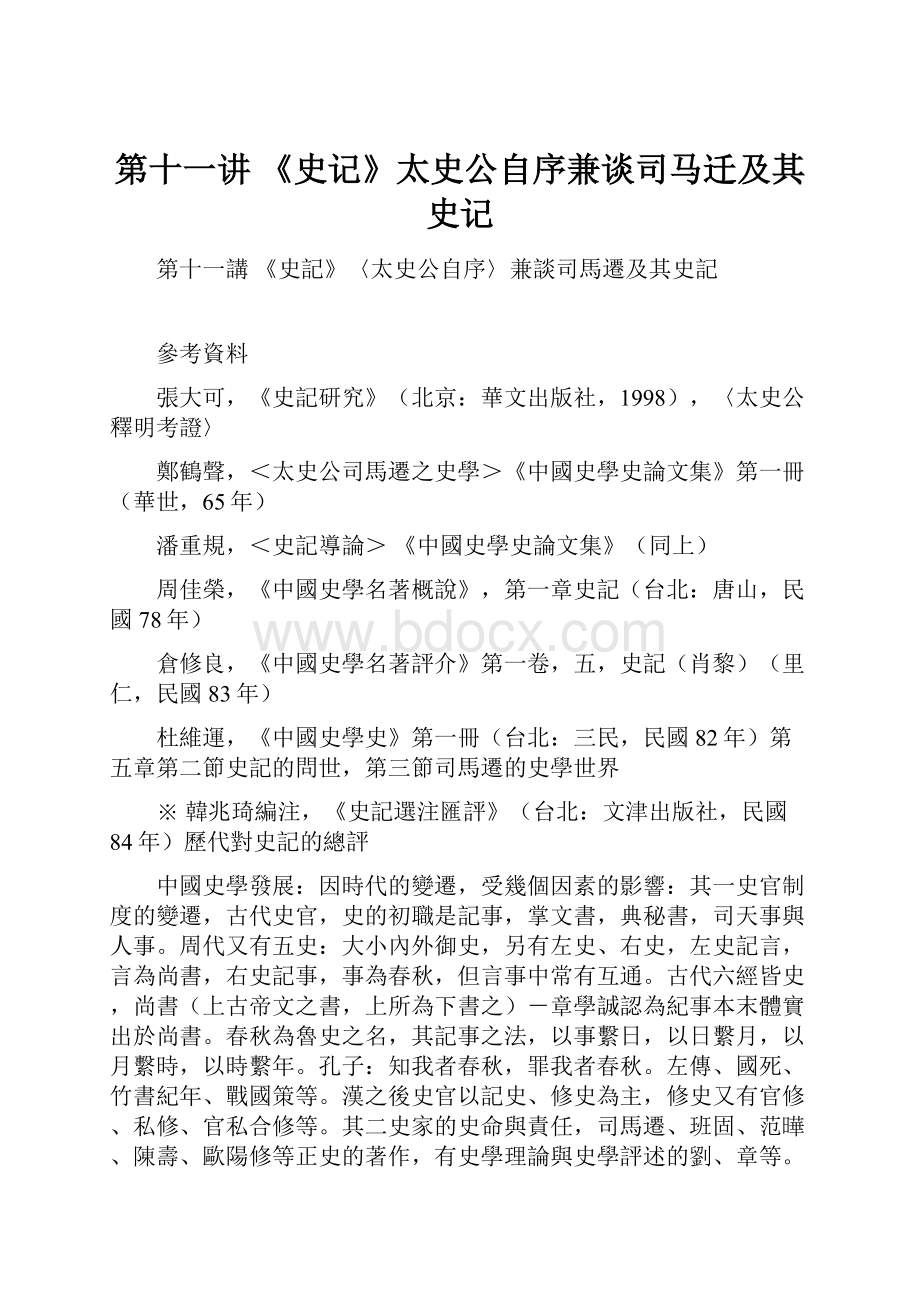
第十一讲《史记》太史公自序兼谈司马迁及其史记
第十一講《史記》〈太史公自序〉兼談司馬遷及其史記
參考資料
張大可,《史記研究》(北京:
華文出版社,1998),〈太史公釋明考證〉
鄭鶴聲,<太史公司馬遷之史學>《中國史學史論文集》第一冊(華世,65年)
潘重規,<史記導論>《中國史學史論文集》(同上)
周佳榮,《中國史學名著概說》,第一章史記(台北:
唐山,民國78年)
倉修良,《中國史學名著評介》第一卷,五,史記(肖黎)(里仁,民國83年)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一冊(台北:
三民,民國82年)第五章第二節史記的問世,第三節司馬遷的史學世界
※韓兆琦編注,《史記選注匯評》(台北:
文津出版社,民國84年)歷代對史記的總評
中國史學發展:
因時代的變遷,受幾個因素的影響:
其一史官制度的變遷,古代史官,史的初職是記事,掌文書,典秘書,司天事與人事。
周代又有五史:
大小內外御史,另有左史、右史,左史記言,言為尚書,右史記事,事為春秋,但言事中常有互通。
古代六經皆史,尚書(上古帝文之書,上所為下書之)-章學誠認為紀事本末體實出於尚書。
春秋為魯史之名,其記事之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孔子:
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
左傳、國死、竹書紀年、戰國策等。
漢之後史官以記史、修史為主,修史又有官修、私修、官私合修等。
其二史家的史命與責任,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歐陽修等正史的著作,有史學理論與史學評述的劉、章等。
史學發展談最多是劉知幾與章學誠,劉氏的史通外篇中史官建置、歷代正史兩篇,論史學的源流
太史公
一,太史公為史記的書名:
漢書、後漢書持此說,二,太史公為其外孫楊惲所加:
王國維持此意見。
三,太史公為官名。
四,太史公為司馬遷尊稱其父。
五,太史公為太史令的尊稱。
六,太史公為尊稱也是遷自題。
太史公曰的內容(周虎林:
司馬遷及其史學):
記敘經歷、嚴定褒貶、補苴遺闕、寄託感慨、闡明緣起、論略篇義。
太史為官名,公為尊稱,司馬遷稱其父,亦自題。
史記
史記與太史公書皆為該書之名稱:
屢見史記本書,悉指舊史而言
史記:
三國魏志王肅傳,明帝稱遷著史記;荀悅漢紀:
「司馬子長遭李陵之禍,發憤而作史記」晉人司馬彪續漢書持此說,隋志據以著錄,史記遂為太史公記的簡稱,錢大昕認為史記之稱是出於魏晉之後。
書名的演變:
「史記」原是史書的泛稱。
《史記‧太史公自序》: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東漢已有《史記》之稱,隋唐以後漸成專名,隋書‧經籍志》:
《史記》130卷。
楊明照《太史公書稱史記考》(《燕京學報》第26卷),指出《史記》名稱,開始於東漢靈獻之世。
司馬遷
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太史公自序中談到遷生龍門(今陜西韓城)據王國維考證,生於漢景帝中元5年(145BC),卒於昭帝始元元年(86BC)一說卒於漢武帝後元元年(87BC),年60歲,大部份活在漢武帝時期。
出身史官世家,父司馬談,曾任太史令(通稱太史公,掌圖書與天文曆算),從小遊歷許多地區,走遍東南及中原地區,學習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隨父到京師長安後,他又學習了古文(如籀文),向當時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向古文大家孔安國學習《尚書》。
20歲前便能誦讀古史書,如:
《左傳》、《國語》《尚書》等。
大約20-36歲間遊各地,《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的: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
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乙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所經路線是:
長安→江陵→汩羅江西省→長沙(憑弔賈誼)→九嶷山(舜葬之地)→沅江→長江→廬山(禹疏九江)→登會稽山(勾踐臥嘗膽事→江蘇淮陰(韓信「胯下之辱」處→泗水→→曲阜(孔子)→山東薛縣(孟嘗君封地)→彭城(楚漢相爭處)→梁地→楚地→回長安。
司馬談死後繼任為太史令(元封3年,108BC),約38歲,讀檔案史料,經過了四、五年,太初元年(BC104),以太史令身分主持改秦漢以來的顓頊曆為夏曆的工作和中大夫孫卿、壺遂及曆官鄧平、天文學家唐都等二十餘人,改革曆法。
經這批專家通力合作,反覆計算、選擇,終於在這年五月造成新曆,這就是著名的《太初曆》。
此外他秉父遺志著手準備編寫《太史公記》(《史記》)這年42歲。
天漢2年(99BC)李陵征匈奴,因寡不敵眾,加上後無援兵,戰敗被俘而投降。
朝廷震驚,武帝本希望李陵兵敗時戰死或自殺,給朝廷爭回一些面子,但卻投降,武帝大怒,下令把李陵家人全部扣押起來。
只有司馬遷,認為李陵勇敢孝義,加罪於他實在冤枉,於是為李陵抱不平,受腐刑(宮刑),三年後獲赦出獄,任中書令(57歲),繼續編寫史記,征和2年(91BC)大致完成。
後由其外孫楊惲傳佈出來。
《史記》前後著作的時間長達十八年,加上日後的改訂刪削,以及司馬遷從前遊歷各地、搜羅史料的前置作業,歷時近二十年。
全書一百三十篇,分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五類,其材料來源,其一是書籍和前代文獻,如春秋、禹本紀、尚書等,其二為檔案,其三為親身遊歷和見聞。
史記撰述動機及背景
一,秉承父志之遺言,而作史記,其父因不能參加泰山的封禪大典,引為憾事,死前要司馬遷繼其志,司馬遷遂以封禪書列為八書之首
二,因保李陵不降敵,受腐刑,本為奇恥大辱,因著書未就,故受刑而不悔,引古人發憤以自況。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
三,司馬遷足跡遍及山西、江浙、山東、湖南等地,因此得以完成此書。
司馬遷曾談到:
「於嘗西至空桐,北過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
四,受古書的影響如《周易》特別是《易傳》、《尚書》、三禮等,具有史家的責任感,遷作史記自比孔子作春秋。
清代史家錢大昕指出史記之微旨:
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
史記的得失
失
後漢書班彪傳中談到史記的缺點是:
「至於採經樜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以多閱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
」
漢書揚雄傳:
「太史公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
優點
(一)文質相稱:
後漢書班彪傳中談到史記:
「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
」
(二)不虛美、不隱惡: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
「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
(三)材料豐富:
引用大量的文獻及檔案,具科學性:
敘史事採「詳近略遠」「疏密相間」的原則,不糾纏於荒遠無稽之談。
所述之事必盡量加以考證,有疑者則闕之,極富科學精神。
(四)內容廣泛:
從歷代大事及重要人物到下層群眾生活,有本紀、世家到游俠、貨殖。
(五)體例獨特:
開創紀傳體的寫史方法。
(六)文筆生動、有卓越眼光,寫作方法,以項羽本紀為例:
1.對比法:
劉邦比項羽大25歲,項羽自刎時31歲,,劉邦已56歲,一個是「年少氣盛」要鬥力,一個是「世故老人」只想鬥智;另一方面拿范增和項羽對比(范增大項羽40多歲),項羽的人物形象便被烘托出來了。
2.直描法:
文中生動逼真地描寫出項羽、劉邦、范增、張良及樊噲等人的個性,如果說「鉅鹿之戰」、「垓下之圍」如一幅幅氣勢磅礡的巨大油畫,「鴻門之宴」便如工筆畫,成功塑造人物創造一個生命,使一個個的歷史人物又活生生的復活在歷史舞台上。
(七)對人物的評述有獨特的意見,如項羽、呂雉兩人又皆非天子列本紀,孔子非侯列世家,對下層民眾及經濟的重視,如遊俠列傳、貨殖列傳,《平準書》記漢代賦稅及經濟情況等。
將天文、曆法、水利、經濟、文化、社會、禮樂、藝術等列專史
史記在史學的地位
其一,開創重要的史書體裁,以紀傳體寫史書,成為後世正史的沿襲。
其二,史記的五體(本紀、世家、列傳、表、書)結構是一個完整的體係,有助於擴大歷史研究的領域,本紀是全書的提綱,以王朝的更替為體系,用編年的形式排比;世家是記載諸侯和特殊有貢獻的人物;列傳是各種人物的傳記,有專傳、合傳和類傳;表是用譜牒的形式,蓋括錯綜複雜的史事。
其三,內容豐富,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時間從黃帝到漢武帝;空間敘國內及鄰國的歷史;敘述人物,從帝王將相到遊俠貨殖;所書內容,從物產到風土民情。
其四,保存古代一些重要歷史文獻,李斯傳中錄入秦統一前李斯幾次上書的原文。
其五,記載少數民族的歷史,如東越、西南夷、匈奴、朝鮮。
其六,特殊的意見,將孔子列為世家,將項羽列為本紀,並著重古今之變,強調人的作用,為各種人立傳,也注意到時勢對人的影響。
其七,創立太史公曰的史評形式,太史公曰的內容不僅是史評,也有補充
其八,寫史態度謹慎,網羅天下亡失的舊聞及文獻,又具有懷疑的態度及闕疑的精神,且多方考據。
秉筆直書是其另一特點。
其九,對文學的影響,文章風格樸實有力、平易簡潔,是兩漢以後散文的典範,對於明清以來的通俗小說中有關人物傳記的描繪具啟迪作用。
史記中許多動人的故事,為戲曲和雜刻創作提供材料,如「趙氏孤兒」、「霸王別姬」。
其十,《史記》的「通史」體裁亦為後人所模效。
杜維運稱司馬遷的史學具真實的世界、遼闊的世界、美善的世界、奧深的世界。
歷代評價:
1.韓愈以「雄深雅健」形容史公文章風格
2.柳宗元著其「潔」
3.蘇轍指出《史記》的特色,是「其文疏蕩,頗有奇氣」
4.曾國藩說:
「自漢以來,為文者莫善於司馬遷。
遷之文,其積句也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
」
5.鄭樵:
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度,故能上稽仲尼之意……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
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
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茲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
6.班固:
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8.杜維運:
甲骨文中,皆可得其名,與《史記》<殷本紀>所載大致無異。
可知《史記》所記商代歷史的可信程度。
也可知《史記》的真實,能經得起地下資料的考驗。
史記問世兩千餘年,到目前為止,沒有另外一部書可以代替它在上古史的地位。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當周
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司馬氏世典周史。
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
其在衛者,相中山。
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
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
而少梁更名曰夏陽。
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
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
當始皇之時。
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
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
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
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巿長。
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
太史公仕於
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傳》: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
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
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
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儒者則不然。
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
如此則主勞而臣逸。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
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
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
則亡,未必然也,故曰:
「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
《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
「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
椽不刮。
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霍之羹。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
尊卑無別也。
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
要曰彊本節用,則
人給家足之道也。
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
可以行一時
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
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
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
失真」。
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
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
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
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
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
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
光耀天下,復反無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
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
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
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有子曰遷。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
年十歲則誦古文。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
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
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
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
後世中衰,絕於予乎?
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
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
哉!
」遷俯首流涕曰: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
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
「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讓焉。
」
上大夫壺遂曰:
「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
「余聞董生曰: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
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
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
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
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
壺遂曰:
「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
太史公曰:
「唯唯,否否,不然。
余聞之先人曰: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
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且士賢能而不用,
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迥也。
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
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謂述故事,
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
於是論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
乃喟然而歎曰:
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毀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
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
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
自曹參薦
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
曰:
「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
至於余乎,欽念哉!
欽念哉!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
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
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
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第七十。
太史公曰:
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太史公自序:
瞭解其背景,著書的動機及原因,並瞭解當時的學術概況。
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囊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僕雖罷駑,亦嘗側問長者之遺風矣。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語。
諺曰:
「誰為為之!
孰令聽之!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何則?
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請略陳固陋。
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
僕聞之:
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
故禍莫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
夫中才之人,是有關於宦竪,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
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
所以自惟:
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
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
向者,僕常厠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闡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
嗟乎!
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載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
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
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
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僕誠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半當。
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
轉鬥千哩,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向爭死敵者。
陵未没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接奉觴上壽。
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
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誰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辭。
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
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家貧,或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
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
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
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關笑。
悲夫!
悲夫!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