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花又开放.docx
《梨花又开放.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梨花又开放.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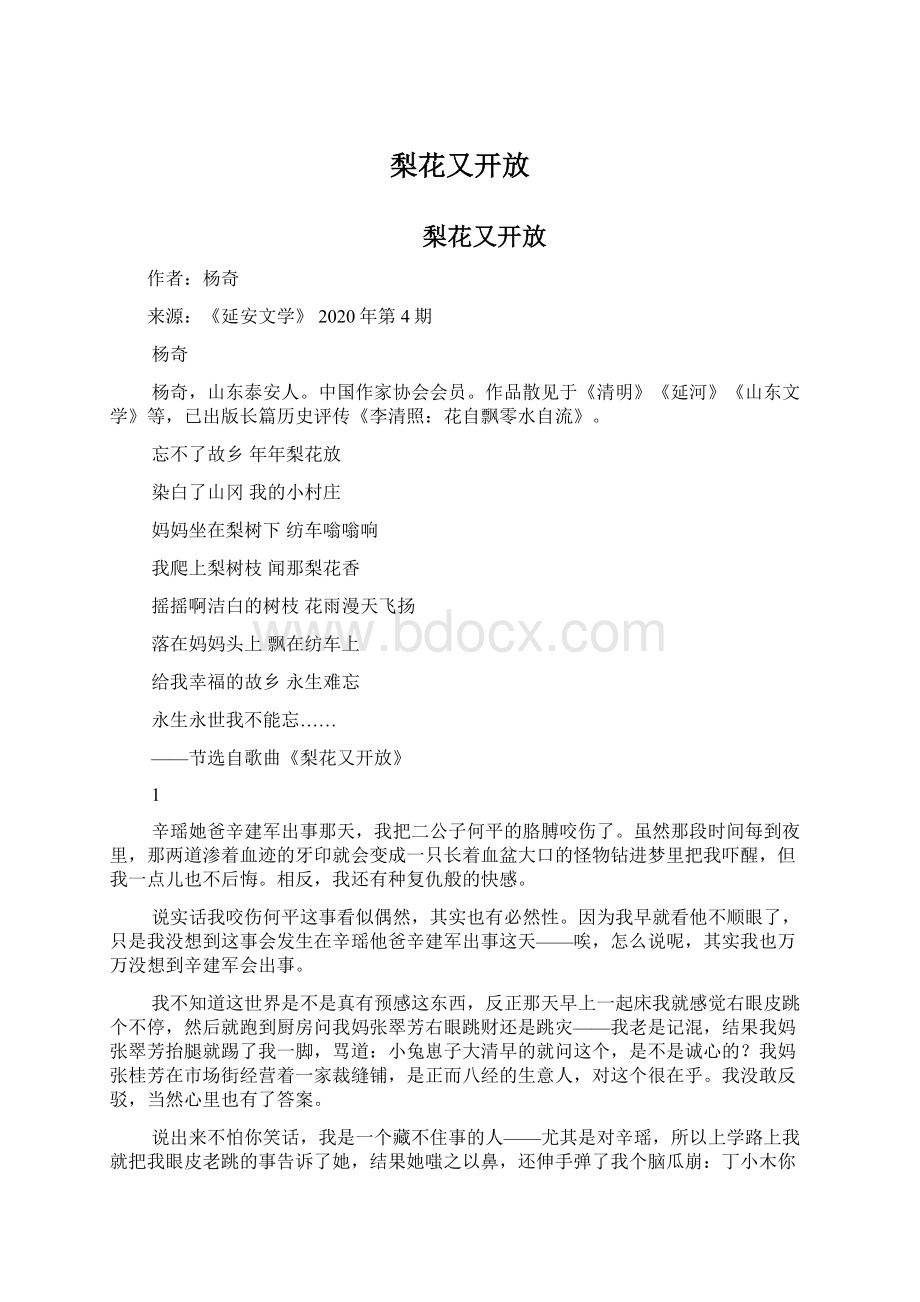
梨花又开放
梨花又开放
作者:
杨奇
来源:
《延安文学》2020年第4期
杨奇
杨奇,山东泰安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散见于《清明》《延河》《山东文学》等,已出版长篇历史评传《李清照:
花自飘零水自流》。
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
染白了山冈我的小村庄
妈妈坐在梨树下纺车嗡嗡响
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
摇摇啊洁白的树枝花雨漫天飞扬
落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
给我幸福的故乡永生难忘
永生永世我不能忘……
——节选自歌曲《梨花又开放》
1
辛瑶她爸辛建军出事那天,我把二公子何平的胳膊咬伤了。
虽然那段时间每到夜里,那两道渗着血迹的牙印就会变成一只长着血盆大口的怪物钻进梦里把我吓醒,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
相反,我还有种复仇般的快感。
说实话我咬伤何平这事看似偶然,其实也有必然性。
因为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只是我没想到这事会发生在辛瑶他爸辛建军出事这天——唉,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万万没想到辛建军会出事。
我不知道这世界是不是真有预感这东西,反正那天早上一起床我就感觉右眼皮跳个不停,然后就跑到厨房问我妈张翠芳右眼跳财还是跳灾——我老是记混,结果我妈张翠芳抬腿就踢了我一脚,骂道:
小兔崽子大清早的就问这个,是不是诚心的?
我妈张桂芳在市场街经营着一家裁缝铺,是正而八经的生意人,对这个很在乎。
我没敢反驳,当然心里也有了答案。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是一个藏不住事的人——尤其是对辛瑶,所以上学路上我就把我眼皮老跳的事告诉了她,结果她嗤之以鼻,还伸手弹了我个脑瓜崩:
丁小木你还学习委员呢,迷信疙瘩一个。
没错,我学习是挺好的,成绩一直稳定在我们朝阳煤矿子弟学校五年级一班的前三甲。
这时候我的死党木瓜(本名吴一鸣,因为头长得像市场街上待售的木瓜而得名)急忙把他的木瓜头伸到辛瑶跟前说:
辛瑶我是迷信疙瘩,你也弹我一下吧?
我气急败坏地一把把他推开,吼道:
吴一鸣我都说过多少次了,辛瑶只能弹我的脑瓜崩,别人谁的都不能弹,你再这样我不跟你做兄弟了!
木瓜急忙缩着他的木瓜头躲一边儿去了。
下午最后一节课上到一半的时候班主任于翠华把辛瑶叫走了,一直没回来。
看着辛瑶空荡荡的座位,我是如坐针毡,一下课就飞跑到于老师的办公室,结果辛瑶并不在。
于翠华老师则趴在办公桌上,脸色很难看,像是害了肚子疼。
我感觉很不妙,也顾不上关心于老师是不是真肚子疼了,直接问她辛瑶去哪里了,于老师有气无力地摆着手说:
她爸出事了……
一听这话我急忙转身朝教室飞奔,等跑进教室的时候,辛瑶他爸辛建军被砸死在矿井底下的消息已经满天飞了。
木瓜像欢迎凯旋的将士一样一把握住他我手,啧啧赞道:
木哥你的预言太准了……我一把甩开他,抓起书夺门而出。
辛瑶家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混乱场面,相反还有些安静甚至井然有序。
院子里,从凤凰村请来的负责红白喜事的许二爷正指挥一干人搭设灵堂,参与的人严格按照分工默默地忙活着。
许二爷也是手势多于言语,只是在猛吸一口旱烟之后会发出一长串的不规则的咳嗽声。
屋里也静悄悄的,只能依稀听到一些压低了嗓门的细碎的说话声。
我先上前给许二爷鞠了个躬——这是朝阳矿区人业已形成的规矩,然后直接奔了屋里。
屋里的大炕上,几个矿区女人把辛瑶和她妈童淑娴围在中间,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辛瑶跟童淑娴抱在一起,眼神一起朝着地上,脸上挂着泪痕,显然是刚哭过。
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像被刀子剜了一下,急忙走上前去对辛瑶说:
辛瑶你别怕,有我呢。
这时候木瓜火急火燎地冲进来,结巴着说:
还有我还有我……
其中一个女人忍不住“噗嗤”一笑说:
就你两小不点儿,能干啥?
一听这话我来气了,但也不好反驳,就说:
你还笑,要是你爸死了你也笑吗?
那女人立刻变了脸,朝我举着巴掌。
童淑娴一把按住了,对我说:
小木,你的好意我们领了,天不早了,你快回家吧。
我扬了扬脖子说:
不,童阿姨,我不走,我还要留下保护你们呢。
那女人又“咯咯”一笑说:
你这张小嘴,一点也不帮你爸丁大路……
我当然不帮他。
我立刻打断她的话。
那你帮谁?
女人追上一句。
我帮……,我咬住嘴唇想了想,然后朝童淑娴做了个鬼脸说:
我帮童阿姨……
这小子嘴可真甜!
一个人喊了一声走进门来。
我打了个冷战,同时看到辛瑶的脸上掠过一阵惊慌。
我知道她也听出了声音的主人是谁,急忙举起一只手朝她摆了摆,另一只拍在了胸脯上说:
辛瑶别怕……
我话还没说完,一只大手就扣在了我头顶上。
我本能地使出浑身力气挣脱掉那只手,然后跳到一边,指着来人大声说:
何平你来捣什么乱?
来者的确是“二公子”何平,他身后跟着两个小弟——都是跟他一样整天游手好闲的小年轻儿。
何平显然没料到我会是这种腔调,先是愣了一下,旋即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摆摆手说:
滚一边儿去。
然后换成一幅讨好的表情冲童淑娴说:
嫂子你看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有兄弟们在,一定会让建军哥走得体体面面的。
童淑娴则摇摇头说:
何平兄弟的好意我领了,有许二爷在,没啥可帮的,您请回吧。
一旁的女人似乎没听到童淑娴的话,脸带娇羞地说:
二公子可以在葬礼上吹口琴嘛,这建军哥一死,整个矿区可就您会吹口琴了。
一听这话我可来气了,指着女人喊道:
你真是老糊涂了?
葬礼上有吹口琴的吗?
被我这一喊,那女人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忙缩起脖子不说话了。
何平却拍了一掌说:
这主意不错嘛。
建军哥活着的时候喜欢吹口琴,他这死了一定也想听吧,要不嫂子……
你也老糊涂了吗?
我再次喊断何平的话:
建军叔死了你还要吹口琴,你是巴不得他死吧?
你小子!
何平脸上的肉瞬间扭曲了,他再次朝我举起了胳膊,我没有丝毫胆怵,反而感觉身体里突然生出一股力量,在它的驱使下,我噌地跳起来,张开大嘴朝何平的胳膊咬了上去……
2
对于我咬伤何平这事,我爸丁大路和我妈张翠芳却表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在我爸丁大路看来,我这一口简直是英雄之举,咬得太解恨了,“不仅严重挫伤了何平的傲气,还大大振奋了矿区男人的信心”——我爸丁大路在矿办宣传科工作,有名的“一支笔”,说出话来总是一套一套的。
而在我妈张翠芳眼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她看来我这一口“简直是要挨天刀的”——她说这话的时候大概激动到忘了我是她亲生儿子了吧?
其实我爸丁大路和我妈张翠芳的观点正好就分别代表了朝阳矿区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观点。
在女人们眼里,何平是老矿长何继业的幺儿子新矿长何宏的亲弟弟,要家世有家世要模样有模样,简直比《上海滩》里的许文强还有吸引力,做梦都想嫁给他,所以我咬何平就跟咬她们自己差不多。
而女人们长久以来对何平的热捧——甚至说是喜爱——又催发了男人们的“酸葡萄心理”,所以他们一直对何平采取极为排斥的态度——当然如果往深层次追究的话,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与童淑娴的关系。
何平与童淑娴是啥关系呢?
还真有点儿说不清楚!
关于他两个人的关系有很多传言,而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了,传言也一直是传言而已。
比如童淑娴是何平高考那年嫁进矿区的,何平本来成绩不错,考上大学是没问题的,结果他却在高考前卷着铺盖回来当起了矿工。
传言说是因为他对童淑娴一见钟情不想离开。
再比如童淑娴结婚之后不久,就像绝大多数矿工家属一样,进入充电室工作,就是为矿工下井时候佩戴的探照灯充电。
其中一个叫刘铁柱的矿工老是借取矿灯或者送矿灯的时候骚扰童淑娴。
这个刘铁柱人如其名,长得虎背熊腰,是个没人敢惹的主儿,辛建军也奈何不了他。
且说有一天这个刘铁柱下夜班的路上却被人抡了闷棍,差点命都没了。
传言说这个使闷棍的人就是何平,只是谁都没亲眼见过,不过这个刘铁柱伤好之后却像变了个人,不再骚扰童淑娴,对人也客客气气的,尤其是对何平,点头哈腰地简直有些奴相。
当然还有许多多如牛毛的传言,比如说为了童淑娴,何平曾不止一次地跟辛建军大打出手,两人甚至还约到凤凰岭上决斗。
何平经常趁辛建军上夜班的时候翻墙去他家里跟童淑娴幽会等等,但说者也就说说罢了,谁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
何平跟童淑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无疑又加深了矿区男人们对他的排斥程度。
童淑娴可是所有矿区男人们的梦中情人,凭什么被他何平一个人占了先?
而男人们的这一想法又激发了女人们的“酸葡萄心理”,而更加玄妙的是,因为有同样的“酸葡萄心理”,原本水火不容的男人和女人却又有了某种默契,那就是绝不容许让何平和童淑娴走到一起。
所以一直以来,只要有关于两人的流言蜚语冒出来,男人女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一起予以否认,就好像自己才是流言蜚语中的真正男女主角一样。
当然在这种事上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辛建军,在矿区男女的心目中,他就像一堵墙——他沉默寡言的个性也的确符合人们关于墙的要求——横亘在何平跟童淑娴之间。
而现在这堵墙却突然坍塌了,消失了,何平和童淑娴之间没有任何阻挡,他们可以直面对方了。
这可是谁都要不愿意看到的啊,于是人们一下乱了阵脚。
这时候就有头脑稍微清楚的人提出来,何平跟童淑娴的关系到底走向何方关键在于童淑娴的态度。
于是人们急忙问怎么知道童淑娴的态度,那人的脑子似乎更加清楚了,他不慌不忙地说,就看她是不是允许何平在辛建军葬礼上吹口琴了。
于是几乎就在一瞬间,人们的关注点从我咬伤何平这件事一下转移到了何平是否会在辛建军的葬礼上吹口琴上了。
朝阳矿区的公墓在朝阳煤矿北面的凤凰山上。
凤凰山上长满了梨树,它们属于山下的凤凰村,在困难时期都是村民们的命根子。
所以当年老矿长想要买下向阳的一面当做朝阳煤矿的公墓时,遭到了凤凰村民的强烈反对。
后来是时任村支书的许二爷出面调停,并拿自己的一片梨树林置换之后,事情才得以解决。
不过就在准备砍梨树修公墓的时候,老矿长又改变了主意,他说在矿区这些年,已经对这些老树有了感情,于是便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对梨树林进行了选择性砍伐,最终保留下了三分之一。
梨树稀疏了,中间的空地用来修造坟墓。
这样一来,这片林地虽然做了坟地,但有这些梨树在,倒使之显得不那么凄凉了。
公墓建成后没几年老矿长就去世了,他的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他葬在了墓地里。
为此他的故友、懂风水的许二爷特地为他选了块宝地,位于整座公墓的正中间位置,说他在这里可以俯瞰朝阳矿区,保佑矿区人平安。
只是许二爷的话并没有灵验,在那个生产条件、安全技术落后的年代,煤矿事故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梨树林里的坟墓无规律地增加着。
新矿长也就是老矿长的大儿子何宏上任后,投入大量资金更新生产设备,同时加强工人安全技术培训,总之为保障工人生产安全花费了大量气力,安全事故呈现出了直线下降的趋势。
现在每年的事故量都是保持在个位数,而出人命的事故更是少之又少了,所以说这次辛建军出事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
在大家眼里,辛建军处事谨慎,工作经验丰富,他还曾因为提前预知危险而避免过事故发生呢。
据目睹事故发生的矿工说,那块巨大的碳石滚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迅速地避开了,只有辛建军仿佛懵住了一般躲都没躲一下就被砸在了下面,他这一反应实在太反常了。
甚至还有人指出更加反常的一点,那就是落石的位置,基本是在辛建军的正上方,就好像那块石头就是奔着他来的。
尽管这人说得很含蓄,但渐渐地还是有一些流言像那矿井里的煤灰一样逐渐升腾了起来,说辛建军的死跟何平有关,是他指使人害死的(何平在矿办工作,不下井)。
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说何平跟辛建军的关系虽然不怎么样,但也到不了非要谋害对方性命的地步,而且从技术层面来分析,在密闭的矿井里想要制造一起谋杀案件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会引起整个矿井坍塌,后果不堪设想。
双方的观点似乎都有道理,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就像那再轻浮的煤灰总有落下的时候一样,流言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辛建军葬礼这天,整个朝阳矿区可以说是倾巢出动——除了下井的,甚至还惊动了山那面的凤凰村。
送葬的人群从凤凰山脚下一直延伸到山上的公墓,场面十分壮观,有人说这规模都赶上当年老矿长的葬礼了。
大概是因为人们除了为辛建军送行,还想亲眼看看童淑娴,以及解开何平是否会为辛建军吹口琴这一悬念吧。
凤凰岭一带的葬礼讲究隆重,越隆重越能让逝者走得踏实。
辛建军的老家和童淑娴娘家来了些亲人,但声势太弱,许二爷便又安排了几位陪哭的女人和我们一群孩子。
我们一大群人走在队伍前面,有哭的有闹的,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