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从1980到36年国企改革路线图.docx
《梳理从1980到36年国企改革路线图.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梳理从1980到36年国企改革路线图.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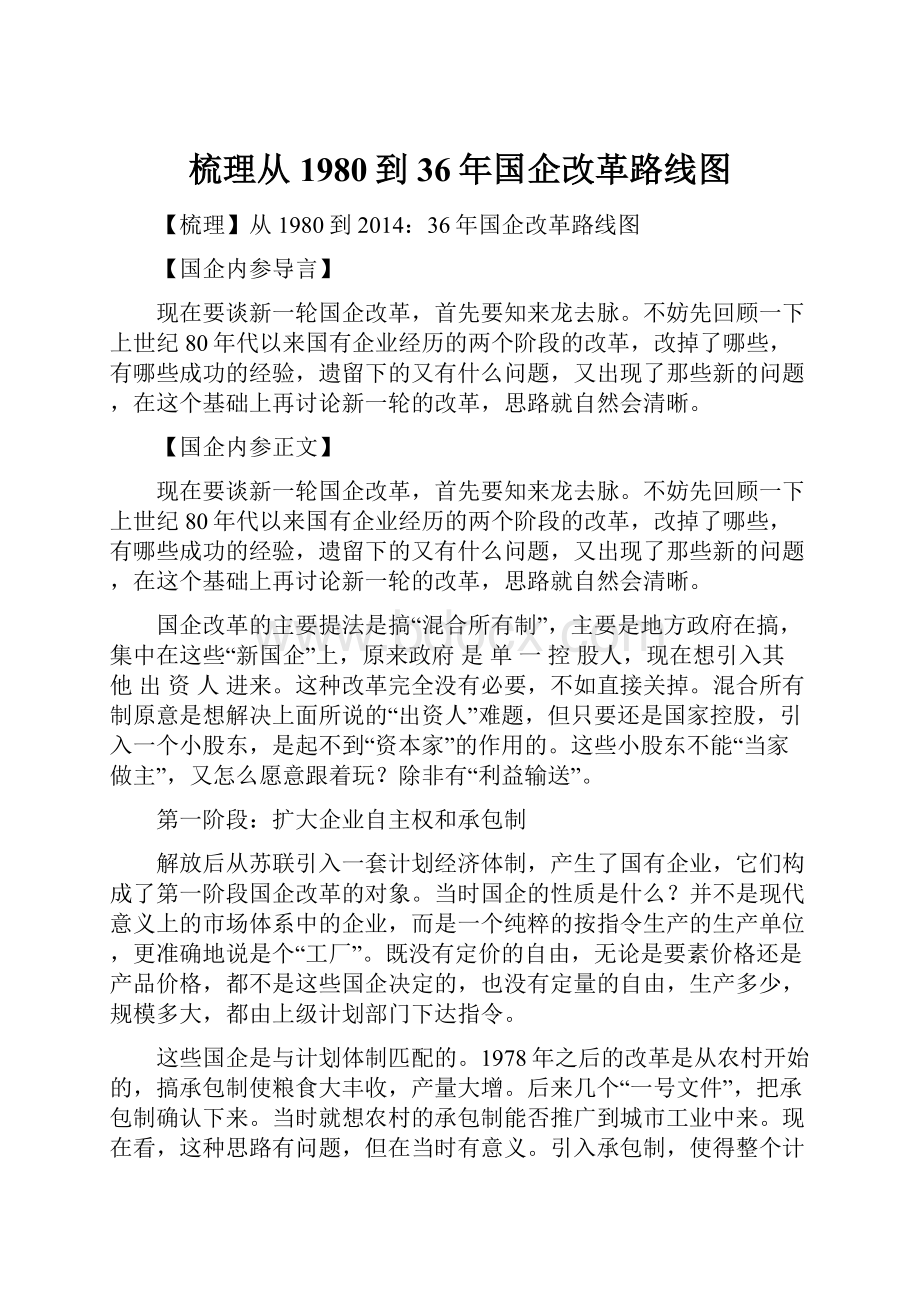
梳理从1980到36年国企改革路线图
【梳理】从1980到2014:
36年国企改革路线图
【国企内参导言】
现在要谈新一轮国企改革,首先要知来龙去脉。
不妨先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经历的两个阶段的改革,改掉了哪些,有哪些成功的经验,遗留下的又有什么问题,又出现了那些新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讨论新一轮的改革,思路就自然会清晰。
【国企内参正文】
现在要谈新一轮国企改革,首先要知来龙去脉。
不妨先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经历的两个阶段的改革,改掉了哪些,有哪些成功的经验,遗留下的又有什么问题,又出现了那些新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讨论新一轮的改革,思路就自然会清晰。
国企改革的主要提法是搞“混合所有制”,主要是地方政府在搞,集中在这些“新国企”上,原来政府是单一控股人,现在想引入其他出资人进来。
这种改革完全没有必要,不如直接关掉。
混合所有制原意是想解决上面所说的“出资人”难题,但只要还是国家控股,引入一个小股东,是起不到“资本家”的作用的。
这些小股东不能“当家做主”,又怎么愿意跟着玩?
除非有“利益输送”。
第一阶段:
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承包制
解放后从苏联引入一套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国有企业,它们构成了第一阶段国企改革的对象。
当时国企的性质是什么?
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场体系中的企业,而是一个纯粹的按指令生产的生产单位,更准确地说是个“工厂”。
既没有定价的自由,无论是要素价格还是产品价格,都不是这些国企决定的,也没有定量的自由,生产多少,规模多大,都由上级计划部门下达指令。
这些国企是与计划体制匹配的。
1978年之后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搞承包制使粮食大丰收,产量大增。
后来几个“一号文件”,把承包制确认下来。
当时就想农村的承包制能否推广到城市工业中来。
现在看,这种思路有问题,但在当时有意义。
引入承包制,使得整个计划体制被打开了大缺口,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回头看苏联,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而是一夜之间把旧体系给废掉,想瞬间建立一套新体系,但新体系怎么玩,不清楚。
中国是旧体系到新体系有一个过程,实际上是民众知识慢慢累积的过程。
当时还不敢提“市场经济”,而是表述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不伦不类。
但改革一旦启动,就发现城市中的这种“工厂”已经与新的体系,与市场经济不匹配了。
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只是从现象出发,认为国企存在问题,比如“偷懒”,没有积极性,缺乏自主权等。
企业本质上是一连串的要素合约。
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比原来的“国有工厂”至少多了两个任务。
一是要定价,二是要定量。
这就是决策权的问题。
所以,当年国企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把原来集中于顶层的权项下放给企业。
权力下放,国有工厂有了定价定量的权力,但权力也必须有一个内在约束。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都要有一个“出资人”,这个出资人的“出资”实际上就是对企业行使权力的一种约束,使其不至于滥用。
当年的国有工厂虽名为“国有”,但却没有具体的“出资人”,行权人不受赌注的约束,权力一旦下放就必然出现权力的滥用,表现出来的就是经营层在买卖时“吃回扣”,当时国企厂长们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新上“生产线”。
这里头个人好处多多,但很多国企就此报废。
权力下放后,为了解决经营层激励和约束问题,引入承包制。
当时经营者虽然有了部分决策权,但上级主管部门,主要是各级经贸委,还是下指令,主要是产值和利润指标。
承包制就是根据这些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奖罚。
承包制当时的确有一定效果,这些指标任务经层层分解后,激励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但两个问题接着就来了。
一个国有工厂今年完成了200万元的利润指标,明年的利润指标该怎么定?
加一点吧,要完成300万元。
若今年没有完成200万元的指标,就减一点吧,150万元。
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
鞭打快牛。
这说明政府主管部门下达产值和利润指标的荒诞,它找不到依据。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与企业经营层签订的这个承包“合约”,履约的费用很高。
厂长们若完成了产值和利润指标,合约就可以履行。
若亏损要惩罚,怎么履约?
厂长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这个合约的奖惩是不对称的。
当时政府是不想放弃公有制,认为搞承包就可以了,说法是搞“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但实践发现,“承包制”不能“履约”。
此外,这些厂长们对市场这套新体系的玩法是很无知的,他们拥有的“决策权”与“知识”是不匹配的。
具体出资人兴办的企业,若经营者“无知”,市场就会以破产的方式淘汰,最终能赚钱的“企业家”在竞争中胜出。
但当时厂长们还是行政部门任命,行政部门也是无知的,不能辨别他们有无经营的“知识”。
因为厂长们的“无知”,致使当时大多数国企是亏损的。
也就是说,当时找不到一条“决策权”与“知识”相匹配的途径(现在的国企仍旧存在这个问题)。
通常情况下,企业“亏损”是有界限的,资不抵债就要破产。
但当时的“国企”没有这个约束,没法“破产”。
亏损常年累积下来,大部分国企已资不抵债了,继续玩,继续亏,但工人工资必须要发。
承包制搞了几年以后发现,政府财政背了个很大的包袱。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很多地方政府每年要把三分之一以上的财政收入拿出来,补国企亏损的窟窿。
采用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强迫银行贷款给这些国企,也不做风险评估,目的是先撑下去。
这些贷款是“肉包子打狗”,最后把银行也拖得要破产了。
开始国企还能还银行一点利息,都后来利息也还不了。
当时一些地方上演了荒诞的一幕:
把银行债转为企业股,强迫银行作为国企出资人。
这时还出现了“三角债”问题,因为国企都没有钱了,原材料和产品就互相“赊借”,互打“白条”。
这就是第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从80年代初开始,历时十多年。
但毕竟开启了改革进程。
经过改革,国企有了一点企业的“要素”了,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不破产,资不抵债还要继续玩。
财政、银行被拖垮后,游戏玩不下去了。
当时的国企就进入到大面积的“停产”阶段,不搞生产经营了,因为继续经营只会亏得更多。
但工人工资总还是要发,要靠财政补。
全国的国企就是这种状况。
也就是说,当时使用的两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不成功的实验。
第二阶段:
“抓大放小”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阶段的国企改革还有点主动性,那么90年代第二个阶段国企改革则是被逼无奈。
国务院当时提出的方案就是“抓大放小”。
“抓大”是对一批国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
“放小”,是部分卖掉或关掉。
当时定下了这个方案,但各地具体怎么处理,要各地去“试”。
先谈“放小”。
当时官方用词叫“关停并转”。
无论关掉或卖掉,职工怎么安置?
当时的国企,政府和职工有一个“隐性合约”:
终身雇佣。
关掉的话,政府要筹一笔钱,对职工进行补偿。
快退休的职工容易补偿一些,那些年轻的职工怎么办?
卖掉也有一个问题:
卖给谁?
当时不是一家两家要卖,是一大批国企。
像长沙仅工业口就有几百家企业。
原国企的管理层有钱也不敢拿来买,否则会被追问钱来自何处。
当时也有一些个体赚了一点钱,但一个城市要找一群有钱人来买,很难的。
关或卖,都碰到一个“钱”的问题。
当时我在长沙市做顾问,协助分管市长做国企改革的方案。
分管市长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
算一下政府当时可以筹到多少钱,用多少钱可以把职工安置好。
财政是没有钱的,要自己想办法。
当时国企是个“有毒资产”,筹不到钱安置不好职工,是处理不掉的。
一些企业廉价卖甚至免费送都没人要,仅职工安置一项,买者就解决不了。
个体买了这些企业,是继续雇佣还是解聘,当时工人要“当家做主”,这些人把厂买去但管不住工人。
所以国企职工这个“终身雇佣”合约,若不由政府出面处理掉,是没人敢买的。
对于这些资不抵债的国企,当时很多地方政府是采取“拖”来摆脱的。
职工靠政府财政发的那一点很少的基本工资,实在活不下了,就外出打工去了。
好就好在当时沿海外资涌入,急需劳工。
长沙的改制没有等,大概用了五年的时间就处理好了。
要解决“放小”,第一个问题是“筹资”。
当时改制的国企,位置较好,90%都在城市二环内,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大。
恰好当时也推出了“商品房”制度,土地开始值钱了。
若改变土地用途,把这些工厂移到外边,甚至直接关掉并把土地卖掉,是可以筹到一笔钱的。
当时算了一下,卖地的钱可以覆盖这些国企的债务和职工安置的费用,政府跟着就出台了配套的政策来卖地。
但有些国企经过年复一年的亏损,已经把资产亏光了,剩下的那些厂房土地也抵押出去了,怎么办?
所以当时不能以单个企业做改制的方案,而是要把长沙所有的企业统起来,一起改。
具体的企业改制是一个个来,但整个费用统筹,否则收支不能平衡。
如何安置职工呢?
一是按工龄买断,就此解除了终身雇佣合约。
年轻职工愿意,因为他们看到了“机会成本”。
解除合约后,他们外出打工能挣到更多的钱,且买断还能拿到一部分钱。
但对一些四五十岁的职工怎么办?
他们外出打工不大可能。
当时要做一次性买断,价格谈不拢,且他们也漫天要价。
面对这种情况,长沙是靠“协议保障”的办法解决的。
要保障这些年纪大的职工此后基本的生活,当时是靠卖地的收入,一次性缴纳这些人到60岁退休之前的社保,届时他们就有退休金可领了。
但到退休之前还有十几年怎么办?
当时从这些卖地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基金,按照约定,发不高的基本工资,但逐年加一点。
长沙用这种“协议保障”的合约创新,解决了“四零五零”人员的安置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债务。
这些国企多年累积的债务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大部分连银行利息都支付不起。
若仅仅安置好职工就关掉,银行是不同意的。
若赖账银行就会破产。
当时长沙是采用“债务包”的方式来处理的。
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央也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长沙就把数个企业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个的“债务包”,打折卖给这些资产公司。
职工安置了,债务处理了,关掉或卖掉就有可能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
当年的国企,实际上是个等级制度,干部除了工资外,还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隐性福利,比如休假、用车、看文件等。
若以工龄买断的方式,这些人是不干的。
对这些干部要做一点另外的补偿,否则他们会在背后捣乱,让你连职代会都开不成。
若明补,职工也一定会不满意,也要闹事,怎么办?
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从卖地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改革奖励”,这些干部若使本厂的改革顺利推进,就按贡献发一笔奖金,“师出有名”,这样就名正言顺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有一些国企产品还不错,还是有销路的,这种企业要卖掉。
在这个过程中,不是简单拍卖一下就卖掉的,原来的经营班子会设置阻力。
这些经营层会认为企业现在还能活,他们是有巨大贡献的。
现在外面来一个老板买了,他们或被解聘或成打工仔,有巨大的心理落差。
设置阻力其实是引起注意,希望政府出面同买者谈他们的待遇问题,因为他们不能自己出面谈。
后来长沙在拍卖时,要求购买者不仅出钱,还要出一个对原经营班子的处置方案,声明政府要做整体比较。
这些经营者对市场有一定了解,或掌握一定的技术,购买者在企业的过渡阶段,对这些人也是能用尽量用。
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长沙的国企改制虽然有一些波折,但总体是很顺利的,没发生恶性事件。
顺利的原因就是在处理债务和职工及经营班子的安置上,有一系列的合约创新,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
后来国资委把长沙的经验做了推广,各地国企的改革或多或少受了一点影响。
但“协议保障”的合约创新,全国做类似处理的很少。
顺便说一句,当时全国各地普遍采用“买断工龄”的办法。
“买断工龄”的说法不准确,其实是要终止原来的“终身雇佣”合约而采用的一种补偿方式。
职工安置时沿海地区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的用工量已经很大了,这些国企的职工恰好是熟练工,否则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现在这个隐性的“终身雇佣”合约终止后,就释放了一大批的熟练劳工,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进入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
二是债务问题处理后,无论是关掉还是卖掉,原来处于闲置状态的国企资源,包括土地、机器设备等,现在也重新被利用起来。
国企改革“放小”之后,经济比之前发展更快,明显加速,是与这些资源的释放,被重新利用相关的。
像长沙的工业产值,改革后增加了十几倍。
“放小”这部分改革,非常成功。
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一下,当时卖掉时,有没有“贱卖”,不好判断,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规范的定价市场作参照。
毕竟国企的卖掉不是常规发生的,也不是拍卖行能拍卖掉的。
当时也有一部分声音,就是像“分田到户”一样,要把国企分掉。
现在再回头看,幸亏没有分掉,否则将是灾难。
问题在“怎么分”?
田地分给个人,不影响产出。
但工厂的机器或生产线分给个人,立马就报废了。
分股权不影响产出,但若是“分股”,谁来“分股”?
当时都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国企的职工来分,还是全国人民来分?
参与分配的界限在何处?
是把当时所有的国企都分掉,每一个企业股的股价是不同的,怎么定价?
怎么加总?
而从企业治理来看,股权太分散,决策是很低效的,不能人人都持股的。
事后也可以看出,当时改为职工人人都持股的国企,改革后多数都死掉了。
可以卖掉,可以关掉,但绝对不能分掉。
这是中国第二阶段国企改革留下的宝贵经验。
现在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又有人在提议“分掉”,是馊主意。
问题在于找不到把国企“分掉”的操作方案,粗略讲可以,但实际没法“分”,强硬地“分”。
会产生巨额的交易费用。
俄罗斯当时采用了世行的建议,那是乱“分”,结果是变成了“寡头经济”,整个国家失序,经济一落千丈。
现在普京打击寡头,又只能以“偷逃税”为由把他们抓起来,财产充公。
实际上是对原来“分掉”那套国企改革方案的否定。
但又不好明说,总不能扇自己嘴巴。
再看“抓大”这块。
中央政府所属的央企怎么处理?
当时对其中100多家央企的想法是不想卖掉,也不想关掉,而是要“盘活”。
不能用承包制了,但怎么“盘活”?
主要是两招,一是做了很多“合并”,后来央企在很短的时间内规模扩大数倍,很多进入世界五百强,成为巨无霸,与这个动作有关。
二是模仿西方的股份公司,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替代了当时的承包制。
架构上看,就是设置了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等机构。
雇佣合约也发生了变化,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新人不再是终身雇佣合约。
当时也成立了国资委,专门管这些大型央企。
很怪异的是,又加入了中组部,来考核任命这些央企的管理层。
与原来不同的是,新的委派任命合约化了,明确了价格和任期。
然后又通过资本市场,这100多家央企绝大多数都上市了。
但这种“移植”是不完全的,由于条件局限,也不可能完全移植西方的股份公司制度。
比如说这种股份公司的出资人是私人,董事会由出资人构成。
但现在央企的董事会成员是“代理人”,而不是“出资人”。
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
其次,股份公司的“总经理”是在企业内部由董事会产生的,而现在央企的经理班子虽然名义上也经过了董事会同意,但实际上是组织部指派的。
如何评价“抓大”?
客观地说,不是完全失败。
但相比于“放小”对中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是明显不如。
所取得的一个显著效果,就是扭转了当时央企在承包制下年复一年一亏再亏的恶性局面。
二是央企内部的管理水平提高了,无论是雇佣合约,还是债权、股权合约,都规范了。
成本控制不像原来处于失控的状态,经营的秩序建立起来了。
现在很多竞争性行业的央企,还能赚一些利润,尽管不多。
也带来了几个问题。
“抓大”后形成的这些巨无霸央企,对当时迅猛发展的民营经济构成了某种抑制。
比如出现融资困难时,民营经济是没有办法与这些央企竞争的。
在一些阶段,的确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
二是这100多家央企尽管有一小部分在竞争性行业,但大部分处在垄断行业。
一些央企利润很高,但高额的利润主要是行政垄断造成的。
这些行政垄断本就存在,问题是“抓大”合并后,客观上强化了原有的行政垄断。
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一些很致命的行业,多少都存在这类垄断,说是鼓励民营进入,但没有办法进入。
金融、电力、民航、能源、铁路、教育、医疗、媒体等领域,都有这类问题。
而这些领域和行业,恰恰对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极其重要。
这些问题很明显,媒体上也多次讨论过。
但有一个重要问题却被忽视了。
央企局部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后,仍然存在一个“出资人”功能缺失的问题。
名义上的出资人是“国家”,但“国家”是个集体,不是具体的人,实际上不能行使“资本家”的功能。
“资本家”有两个功能,一是选人,二是定价。
“出资人”的缺失带来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对企业员工,对人力资本的“定价”是始终不到位或扭曲的。
现在央企的员工收入是高还是低,恐怕很难说。
可能很多人的价格被定高了,一些人又被定低了。
大型央企的总经理,年薪拿一千万元,算不算多?
定价的标准是什么?
这本来是应由资本家来确定的,但现在是缺失的。
现在统一规定大型央企的董事长、总经理年薪多少,合理吗?
要根据才能和贡献大小来定价。
现在是不分青红皂白,统一一个价。
最近又提出要削减这些人的年薪,是因为这个问题又在隐隐发作了。
“资本家”缺位所引起的对人力资本定价的扭曲会带来什么恶果?
如果央企从事的业务活动是常规的,一年一年重复,定价错误顶多是影响一点员工积极性,结果就是成本高一点,利润少一点,影响不大。
但另一个更大的,更隐性的恶果是企业创新的活动不能开展。
因为创新的活动,无论是制度还是技术创新,一定是没有先例的,必须要有很好的激励。
而对人力资本定价扭曲,创新活动一定是被抑制的。
所以大型央企不可能有什么创新。
而这些央企又控制了中国一些很关键的领域和行业,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后继发展危害巨大。
国企的“资本家”缺位造成的问题,在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后果。
但在当前这个阶段,对创新的抑制是致命的。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策略
第二阶段“抓大放小”后,不想又生出了一批“新国企”,这个现象现在还没有引起重视。
“放小”卖掉或关掉很多老国企,但各级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又办起了很多新的国企,现在所谓“地方债”的问题,都与这些“新国企”有关。
原来卖掉或关掉的老国企集中在工业领域,现在这些“新国企”大多数是投资类公司,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不允许地方政府向银行融资,这些投资公司是政府融资平台的替代,还是有其他原因,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这些“新国企”不伦不类,问题比老国企更多。
它们不像改制后的央企,毕竟还是引入了一套治理结构,有流程,有规章制度。
这些“新国企”连这些东西也没有。
与“老国企”不同,也不搞承包制,它们的使命是什么?
也不清楚。
如果说仅仅作为地方政府各级部门融资平台的替代,主要功能是融资,那它们现在又同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亏损了怎么办?
怎么规范这些经营者的行为?
现在很多“地方债”的问题是隐藏在“新国企”的内部。
“地方债”要客观看待。
原来地方政府的城市开发模式没有问题,但不允许政府融资后,只能成立一个投资公司,替代政府去融资,是迂回前进。
但政府融资只需要一个公司就可以了。
现在为什么出现这么多?
基本上各个部门都有,是做什么的?
其中会不会有很多资不抵债的“壳公司”?
总之,这些“新国企”融资操作是摆迷魂阵,会是以后的大麻烦。
现在又重提国企改革,即意味着改革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改革有两个问题,一是这100多家大型垄断央企怎么改?
二是如何处置这些“新国企”。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的看法很简单,就是统统关掉。
这些企业是卖不掉的,它们多是“毒公司”,债务合约无法了结。
哪些部门组建的,就应该由这些部门快速解决掉。
这些“新国企”对一个部门或地方政府是有用的,但从整个社会视角看,是没有理由存在的。
现在中央要摸查清楚这类“新国企”的数量、债务和业务内容,限期关掉,否则会构成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毒瘤。
现在国企改革的主要提法是搞“混合所有制”,主要是地方政府在搞,集中在这些“新国企”上,原来政府是单一控股人,现在想引入其他出资人进来。
这种改革完全没有必要,不如直接关掉。
混合所有制原意是想解决上面所说的“出资人”难题,但只要还是国家控股,引入一个小股东,是起不到“资本家”的作用的。
这些小股东不能“当家做主”,又怎么愿意跟着玩?
除非有“利益输送”。
对大型央企垄断带来的问题,社会是达成共识的。
但现在所采用的办法是“分拆”。
这个办法是不对的。
像国家电网采用“横切”、“纵切”的办法,发电与电网分开,经营线路的公司与配电的公司分拆等。
但拆来拆去,只是规模小一点,这些公司的业务还是互补的,仍旧构不成竞争关系。
只要这些行业和领域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行政垄断的局面仍旧存在,国企天生的致命缺陷:
“资本家”功能丧失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对这些大型央企的改革,“拆”不是重点,要领是要把行政垄断统统打破,让民营资本自由进入。
如果在这种局面下央企还能生存下来,说明央企的这套制度安排是可以的,根本不需要担心。
若在竞争中死掉,说明它们是有先天缺陷的。
竞争中若死掉,采用原来的办法,关掉就是了。
除此之外,找不到别的方案对这类巨无霸央企进行改制。
卖掉,资产规模这么大,卖给谁?
通过证券市场卖掉,股份分散是不行的。
这些巨无霸有很多市场交易的障碍,不是那么好卖的。
新阶段对大型央企的改革,不是直接动刀子改,而是引入竞争者,打破行政垄断,对民营资本全方位开放,新生成一批企业,市场激发的活力会打破当前的这个困局。
【国企内参简评】
国企改革三十年的总体路线其实是抓住命脉,尊重规律。
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开始,对于那些可以放开的企业,就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让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经受考验炼成彩虹;对于涉及命脉的国企,则要紧紧抓在手中,这是原则性问题。
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应该也是按照这条思路去走,但世易时移,国企改革如今面临的客观条件不同于之前两次,这次改革的方式、途径与效果自然也会不同。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国企内参”第五期的文章《【高论】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梯若尔对中国国企改革的独到见解!
》。
国企内参:
微信公众号IDguoqineican
国企监管者、管理者及合作伙伴都在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