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代文学作品发展.docx
《浅析当代文学作品发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浅析当代文学作品发展.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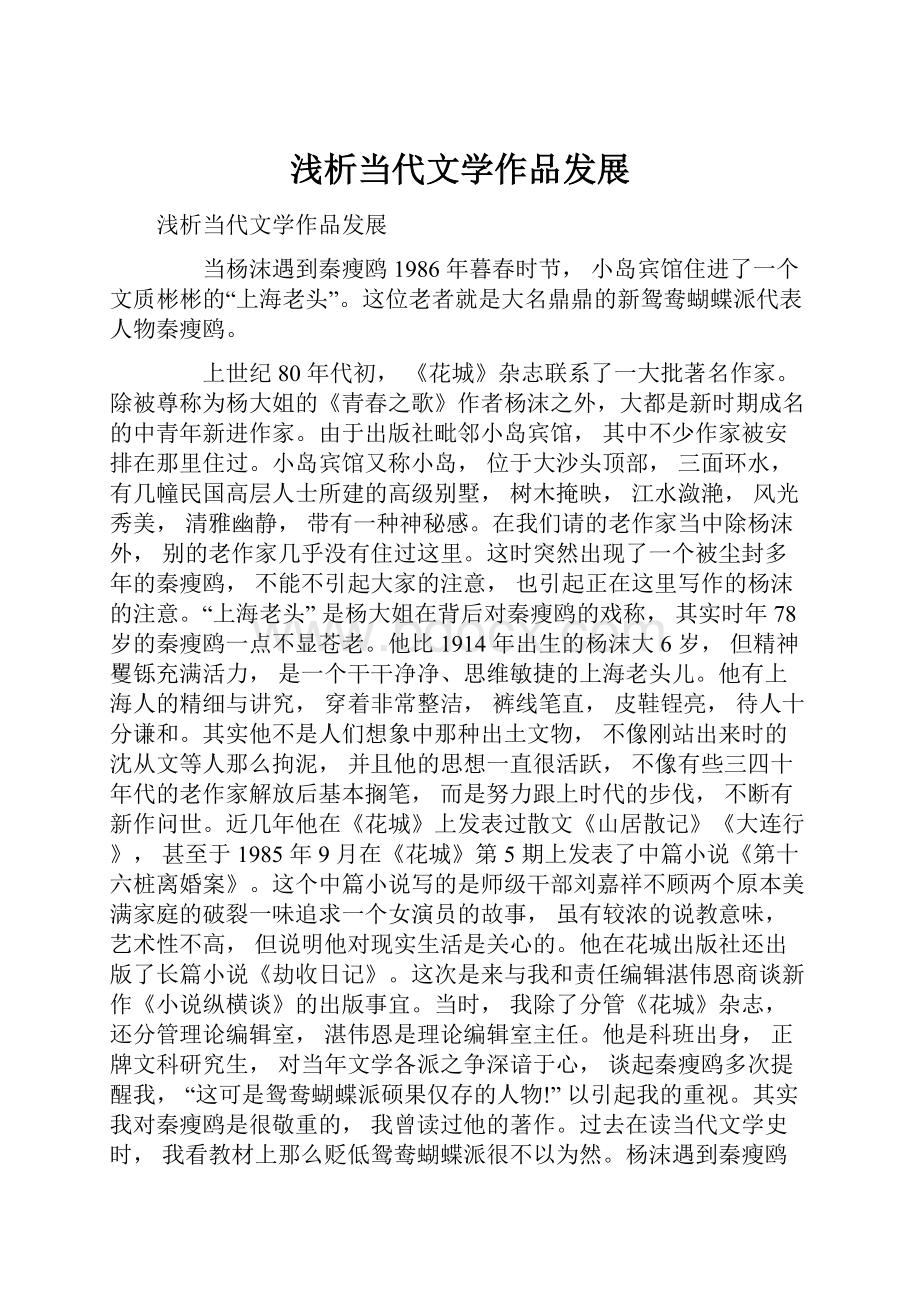
浅析当代文学作品发展
浅析当代文学作品发展
当杨沫遇到秦瘦鸥1986年暮春时节,小岛宾馆住进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上海老头”。
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新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秦瘦鸥。
上世纪80年代初,《花城》杂志联系了一大批著名作家。
除被尊称为杨大姐的《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外,大都是新时期成名的中青年新进作家。
由于出版社毗邻小岛宾馆,其中不少作家被安排在那里住过。
小岛宾馆又称小岛,位于大沙头顶部,三面环水,有几幢民国高层人士所建的高级别墅,树木掩映,江水潋滟,风光秀美,清雅幽静,带有一种神秘感。
在我们请的老作家当中除杨沫外,别的老作家几乎没有住过这里。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被尘封多年的秦瘦鸥,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引起正在这里写作的杨沫的注意。
“上海老头”是杨大姐在背后对秦瘦鸥的戏称,其实时年78岁的秦瘦鸥一点不显苍老。
他比1914年出生的杨沫大6岁,但精神矍铄充满活力,是一个干干净净、思维敏捷的上海老头儿。
他有上海人的精细与讲究,穿着非常整洁,裤线笔直,皮鞋锃亮,待人十分谦和。
其实他不是人们想象中那种出土文物,不像刚站出来时的沈从文等人那么拘泥,并且他的思想一直很活跃,不像有些三四十年代的老作家解放后基本搁笔,而是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有新作问世。
近几年他在《花城》上发表过散文《山居散记》《大连行》,甚至于1985年9月在《花城》第5期上发表了中篇小说《第十六桩离婚案》。
这个中篇小说写的是师级干部刘嘉祥不顾两个原本美满家庭的破裂一味追求一个女演员的故事,虽有较浓的说教意味,艺术性不高,但说明他对现实生活是关心的。
他在花城出版社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劫收日记》。
这次是来与我和责任编辑湛伟恩商谈新作《小说纵横谈》的出版事宜。
当时,我除了分管《花城》杂志,还分管理论编辑室,湛伟恩是理论编辑室主任。
他是科班出身,正牌文科研究生,对当年文学各派之争深谙于心,谈起秦瘦鸥多次提醒我,“这可是鸳鸯蝴蝶派硕果仅存的人物!
”以引起我的重视。
其实我对秦瘦鸥是很敬重的,我曾读过他的著作。
过去在读当代文学史时,我看教材上那么贬低鸳鸯蝴蝶派很不以为然。
杨沫遇到秦瘦鸥是一种机缘。
革命作家杨沫遇到被满身涂上颜色的秦瘦鸥,是谁也想不到的,别人想不到,他俩也想不到。
广东是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地方,作为改革开放的热情支持者,杨沫很喜欢这个地方。
自1982年,她多次来广东访问及写作,与花城出版社关系密切,我多次接待过她。
她平易近人,写作十分勤奋。
作为教育了一代人的《青春之歌》的作者和全国人大常委,她也受到省委和各级领导的尊重,广东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条件。
有时她住珠海,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借给她一套房子;她来广州,省委及有关方面安排她不是住迎宾馆就是住小岛。
她对我不止一次地开玩笑说:
“广东是我半个家。
”由于广东给予了她种种方便,几年来她创作甚丰。
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在《花城》发表之后,虽然有许多不同看法,包括来自上面的看法,但她有种倔劲,有种咬死理的精神,又为《花城》写了续篇《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
接着她整理了几十年的日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几十万字的《自白——我的日记》。
最令她挂心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也在这时反复修改。
这部长篇写于“文革”期间,难免受到当时所谓“三突出”“高大全”之类的文艺思潮影响。
粉碎“四人帮”之后受到批评,她自己更有切肤之痛,一心想将其改好。
但大改一部作品也许比新写一部作品更不容易,她几番修改仍不如意。
一次我陪她和她的助手蒋维嘉往珠海,在车上又谈起《东方欲晓》的修改,我向她进言放下《东方欲晓》,按照《青春之歌》的路子构思“三歌”,将她的生活积累和真实的情感融入新的作品,首先写好《青春之歌》后的“二歌”。
也许她早已有这个想法,即刻表示接受我的意见。
蒋维嘉也赞成这个意见。
我说,“这不能说是我的意见,其实你们二位也都有这个想法。
”正可谓三人不谋而合,车内充满笑声。
1986年暮春,杨沫正埋头写《芬菲之歌》。
可惜《芬菲之歌》没有真正摆脱《东方欲晓》的羁绊,仍是以《东方欲晓》为基础,未能摆脱原作的影响,在思想上艺术上均达不到《青春之歌》的高度,非成功之作。
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往往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有种偏爱,失之明察,杨沫也不例外,难免留下遗憾。
这时杨沫住小岛2号楼,秦瘦鸥住4号楼,都是花城出版社请的客人,吃饭在同一个食堂,有时还同一张饭桌。
秦瘦鸥是个谦和的人,待人亲切,礼貌周到,细微处对杨沫多有照顾。
风度与风韵均佳的杨沫落落大方,也能以礼相待。
两位出身不同、经历不同,甚至于创作流派不同,虽很少谈及写作经验,但也相谈融洽。
几天后,杨沫却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老范,你给那个上海老头说一下,让他不要老来我这里。
这样会影响我写作的。
”我初不解其意,说:
“你们交流一下创作经验不是也很好吗?
”杨沫笑了,“那个老头对我好像有点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追我哦?
”我也同杨沫开玩笑,“这也没什么嘛,好事嘛。
”杨沫笑着推我一下,“你怎么也学坏了。
”两人都笑起来。
我把杨大姐的话说给湛伟恩听,因为秦瘦鸥是他负责接待的,想让他委婉地给秦瘦鸥打个招呼,不要多去2号楼,以免影响杨沫。
不料一向古板的老湛却兴奋起来,说:
“打什么招呼,两人都是单身,你要促成此等好事啊!
”我说两人气质不同,不可能走在一起的。
老湛意犹未尽,说怎么就不可能呢,如果两个人真的走在一起,那可就真的实现两结合了。
我问是什么两结合?
是毛主席说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吗?
湛伟恩想了想说这样说不准确,可以说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鸳鸯浪漫主义相结合吧?
我说他这个文艺理论家说的也不准确,其实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大部分应列入现实主义,并非是浪漫主义的。
两个人谈笑过后,还是尊重杨大姐的意见,将两人就餐的时间适当拉开,这样两人就接触少了,秦瘦鸥好像感到了什么,也不再去2号楼了。
秦瘦鸥也许对杨沫真有点意思。
杨沫是一位著名的革命作家,秦瘦鸥也未必没有读过《青春之歌》和看过改编的电影。
这位旧时代的文人在受革命教育数十年之后,对杨沫未必没有仰慕之情。
他大不了杨沫几岁,杨沫的年岁虽然已过七十,但风韵犹存,性格开朗,为人和善,受到同辈的爱慕,不足为奇。
但杨沫对过去不是一条阵线的秦瘦鸥却隔膜甚深,甚或还有不少误解。
我相信杨大姐对鸳鸯蝴蝶派和其代表人物之一的秦瘦鸥了解并不多。
根据秦瘦鸥的创作成就,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会有一席之地的。
秦瘦鸥,原名秦浩,上海嘉定人。
他青年时期就读于几所商业学院,毕业后曾在工矿、铁路及报社当职员,并兼任大学讲师,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
1934年,他的译作《御香缥缈录》问世,名声鹊起。
《御香缥缈录》的作者德龄郡主是慈禧御前八位女官中最得宠的一位,与妹妹容龄郡主同为慈禧近身侍官,受过西方教育,能说英语、法语及日语,深得慈禧赏识。
《御香缥缈录》是用英文写的,记述了作者在慈禧身边的所见所闻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宫廷政治生活内幕。
该书最先由纽约陶德曼公司于1933年出版,1934年申报馆出版的中译本经由秦瘦鸥译出,即与国内广大读者见面。
秦瘦鸥文笔优美,语言功底深厚,他的译本不仅正确传达出了原作原意,而且将德龄所处环境的气氛与细微的心理感受烘托出来。
以后的译本无有能出其右者。
1941年身处孤岛上海的秦瘦鸥的长篇小说《秋海棠》在《申报》副刊上连载,引起轰动。
小说以主人公京剧青衣吴玉琴与官僚袁宝藩的姨太太罗湘绮的曲折而离奇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平与不公,再现了权贵们横行无忌、欺男霸女的丑恶行径和伶人们的屈辱与愤争。
看起来这又是一个戏子与姨太太的恋情故事,其实不然,因为它具有比较深刻的社会批判内容。
这部书成了秦瘦鸥的代表作,也成了所谓的新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
也有人将《秋海棠》称为言情小说,但言情小说就要归派吗?
如今不是也有很多作者在写些城里城外的男欢女爱的小说吗?
可能在某些细节上写得只有更甚而无有不及!
我没有考证过鸳鸯蝴蝶派的历史,他们开过什么大会?
发表过什么宣言?
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感觉一到新社会,这个“鸳鸯蝴蝶派”怎么就成了恶谥似的标签了呢?
新中国成立后,秦瘦鸥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随着鸳鸯蝴蝶派的消失而消失了。
他曾任香港《文汇报》副刊组组长。
上世纪50年代末回到上海,先后出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
与此同时,他创作了以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刘瞎子开眼》、电影剧本《患难夫妻》《婚姻大事》等。
他性格开朗乐观,经得住生活的磨炼,有一股韧劲。
他的《劫收日记》是在五七干校写的,没有纸就写在纸烟盒里;“文革”中他被拉到街道反复批斗,受尽凌辱,曾有自杀的念头,多亏一个老者走到他身旁对他耳语几句,要他将世事看开,使他受到鼓舞,终于坚持活下来并继续他的文学事业,年过古稀仍不断有新作问世。
我在与杨沫、秦瘦鸥接触当中,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关心人。
杨沫有大姐风,作为女性她对别人的关心多在生活上,而秦瘦鸥的关心则有其浓厚的文人气。
他有一种上海滩文人的禀性,博学多才,兴趣广泛而好玩,对书法、篆刻、绘画、古玩无所不通,同许多名家有来往。
他两次来,每次都带些小玩意给我和老湛。
有一次他笑着塞给我一枚图章,是钱君匋刻的。
钱君匋可是大家,书法、篆刻俱达高峰,早期曾跟随鲁迅为其作品做过装帧设计。
秦瘦鸥在小岛宾馆遇到正在写三部曲的杨沫时,他的《梨园三部曲》也在构思与写作中。
1982年之后,他以《秋海棠》中已经出现的吴玉琴和罗湘绮的女儿梅宝为主人公,续写了三部曲的第二部《梅宝》。
秦瘦鸥幼时受祖父的影响,酷爱昆曲、京剧等戏剧艺术,而且亦熟悉京剧界人士的生活,在写出《秋海棠》和《梅宝》之后,写出第三部已是早晚之事,但可惜天不假年,不幸于1993年病逝,未能完成夙愿。
杨沫最终完成了她的三部曲,于1995年逝世于北京。
两位老作家自小岛宾馆分开之后,再无联系。
杨张情感公案
情感的事很难说,谁都说不清楚。
自已说不清楚,别人更说不清楚。
杨沫与她的第一个爱人张中行的情感纠葛自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之后就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说了几十年,说到今天说清楚了吗?
众口成讼,成了一桩公案。
读者喜欢将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入座,因爱憎而褒贬,不觉就会将小说人物和生活中的人硬扯在一起。
都知道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作家创造的小说人物又往往有原型,难免勾起一些读者如红学家中“索隐派”老先生们那种对“索隐”的兴趣。
杨沫的《春春之歌》甫一出版,就在全国引起轰动,特别在青年读者中间。
小说生动鲜明地刻画了林道静等一系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教育了几代人,成为共和国的经典文学作品。
作家们往往喜欢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入作品,《青春之歌》的作者也不例外。
无疑,主人公林道静身上有杨沫的影子,那么卢嘉川是谁?
江华是谁?
余永泽又是谁呢?
而且读者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这个与林道静有爱情纠葛的余永泽。
余永泽不同于卢嘉川、江华,他不是林道静的同志,但却曾是读者热爱的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的爱人。
余永泽是书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他是作为林道静的对立面出现的。
林道静追求进步、追求理想、追求革命,积极参与火热的斗争;而余永泽却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思想倾向,也不是反面人物。
在现实生活中,杨沫的第一个爱人张中行似乎就是余永泽。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杨沫是《花城》杂志的重要作者,作为编辑的我同她接触较多,并萌生过写杨沫评传的想法。
杨沫很支持我写她的评传,同我多次谈过她的生活经历与创作,并提供了不少资料和旧时的照片。
后来我深感自己学养不够,掌握资料不足而又无暇采访,加之编辑事务繁多,难以脱身,此事只好作罢,然而却因此加深了对杨沫生平的了解。
有一次谈到《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我像一个好奇的普通读者问她,余永泽是不是张中行。
她笑笑说:
“也是也不是,你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明白,余永泽这个形象可以说从张中行身上摘取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同林道静共同生活那一段,但也有不少虚构。
”1914年,杨沫生于北京。
她的父亲以湖南举子身份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创办了第一所中国的私立大学。
杨沫告诉我这所大学的校名是中国女子大学(现在一些资料说是新华大学),并以办校之名趁清王朝崩溃之机,在热河与东北收购了大量王公贵戚们贱卖的土地。
杨沫生活的环境本在富贵人家,但由于父亲讨姨太太,父母感情长期不和,她很少受到父母关爱。
杨沫说,她想不起父母的笑脸,她记不起父母抱过她,父母不关心她兄妹的生活。
北京严寒的冬天,她经常穿一双破烂的棉鞋,露在外面的脚跟冻裂几个大口子,沉醉在大烟里的母亲从不过问。
她的遭遇我深有体会,富家有苦孩,我与她有同感。
我也出身于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但我同她一样,记不起父母温暖的怀抱,也几乎没有见过祖母的慈祥笑容,所以谈起来与杨沫有共同语言。
生长在这种家庭的孩子,也许会直接感受到世事的不平,更早地生成叛逆性格,少女杨沫就是一个很叛逆的女孩子。
杨沫能同北大学生张中行走在一起,同她的家庭环境、她的叛逆性格、她对新思想的追求是分不开的。
母亲强迫只有16岁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她嫁给一个军官,她反抗,跑到西山温泉中学住校。
母亲威胁她,不给饭费学费,杨沫只好想法子自谋生活。
为找工作,一个同学的亲戚知道张中行的长兄在香河县立小学任校长,就带杨沫去见张中行。
一见之下,张中行对杨沫印象很好。
后来在他所著《流年碎影》中是这样说的:
“其时我正幻想维新,对于年轻的女性,而且胆敢抗婚的,当然很感兴趣。
”“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朗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
”张中行将杨沫推荐给长兄,几次见面,两人产生感情。
两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到1932年春天,当杨沫母亲病重,杨沫从香河小学回来探视时,已住到张中行在沙滩一带租的房子。
张中行在家乡已有妻室儿女,当时杨沫受新思潮的影响,对婚姻问题持开放态度。
两人公开同居后,靠家里给张中行的一点生活费过活,日子自然清苦。
初期他们还是幸福的。
虽然物质生活匮乏,但北大学生张中行写诗给杨沫娓娓表达他对爱妻的眷恋,让童年很少得到人间温暖的北大旁听生、热爱文学的杨沫,于精神上得到莫大慰藉。
张中行北大毕业以后到了天津,受聘在南开中学当教员,薪水较高,两个人的小日子有了好转,应该说杨沫此时是满意的。
但久而久之,杨沫不想总是围着锅台转,不想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她这个一直要求进步的年轻人想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
虽然她那时找不到共产党。
在她接触到的人里边,一旦看到了让她敬佩的共产党人,她就更不想去过那种冗长的平庸的家庭生活了。
于是,到1936年她与张中行分开了。
两人分开的原因,老鬼在所著《母亲杨沫》中说,“是母亲抛弃了张中行”,其实原因很复杂,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的。
杨沫是个渴求动荡、不甘平庸、追赶时代前进步伐的青年。
张中行则是一个胡适的崇拜者。
用当时杨沫的四妹白杨的话来说,“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
”“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个书虫,要我早就跟他分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思想上的分歧、行动上的分歧以至于感情的分歧已不可挽回。
杨沫追求的是共产党,热情似火的杨沫找不到共产党居然到监狱里去找。
我记得这样一件事:
1982年杨沫初到广州,百事缠身的省委书记任仲夷曾两次到迎宾馆探望她,而且每次都谈一个下午。
我问她任书记同她谈些什么,她说除了谈目前特区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还谈些以往的私事。
我问她同任书记过去一块工作过吗?
她说没有,不过她过去认识的一个人同他共过事。
任书记告诉她,他在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时,书记处中一位姓郑的书记常谈起她。
说到这里杨沫笑了,当年她找共产党,曾异想天开地到监狱去找。
她去监狱探视她曾见过的一个共产党员,她那时很穷,每次只能蒸点馒头带去,因而认识了与那人同监房的郑同志。
老郑出狱后曾约她在北海公园见面,并表示爱慕之意,想追求她,她未答应。
可想当年杨沫是一个多么富有革命激情的人啊,这与钻在故纸篓里淘学问的张中行必然是渐行渐远的了。
除了思想上的分歧,两人在生活中的冲突与摩擦也是分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杨沫与张中行同居不久怀孕了。
张中行担心将来负担加重,心情愁闷,态度冷淡,两人感情上有了隔膜,常是相对无言。
杨沫不好意思在家生小孩,决定到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小孩生下。
临走时,张也没说送她一程。
杨沫后来在文章中写道:
“眼看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就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
”小孩因照顾不好,早夭了。
后来张中行虽然对杨沫改变态度,并用他写的诗词取得了杨沫的原谅,但这件事无疑在杨沫心头留下了印痕。
1936年3月,杨沫在香河小学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马建民。
马是共产党员,深得杨沫好感,认识后两人感情发展很快。
在天津教书的张中行听到这个消息很紧张,辞去南开中学教职回到北京,力图挽回同杨沫的关系。
杨沫离意已决,张中行很沮丧,在北大新四斋借了个床位,潜心学佛。
其实杨沫这时对张中行还是有留恋的。
谈到她与张中行的分手,杨沫对我是这样说的:
“我听说他单独住在北大学生宿舍,一天去看他,见空落落的房内只有他一个人坐在床上。
天气炎热,一进门就看到他赤裸着瘦骨嶙峋的背脊,面壁对着墙上一张释迦画像,喃喃自语。
他听到脚步声,扭头看到我就泪流满面,劝我回去。
我来的本意是想给他作些解释和劝慰,他不听,一直在说:
‘回来吧!
回来吧!
’我怕感情受不了,赶快转身往外走,疾步穿越前面广场时,还听到‘回来吧,你回来吧’的低声呼唤。
声音很悲伤,这声音好像追赶着我,我越走越快,肩上的纱巾何时丢到地上也不知道。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杨沫回忆她与张中行分手的情景时,依然带着一丝难以消散的温情。
《青春之歌》的写作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回忆、酝酿、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不可能一气呵成。
作家最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会常常在他们的记忆中跳跃、闪动、发光和燃烧,反反复复而后形成文字。
《青春之歌》在写作过程中曾用名《烧不尽的野火》,这团野火长久地在热情奔放的杨沫心头燃烧。
1937年她发表的短篇小说《怒涛》中的女主人公美真是一个热情、真挚、单纯的女大学生。
入大学那年,她与青年昭相爱同居。
但对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充盈她的心灵。
她想着饥寒交迫的大众,不愿再过平庸安逸的生活。
丈夫与她的想法刚好相反,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家出走,去为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已的幸福。
这几乎就是当年杨沫和张中行共同生活的写照,可以说,美真就是林道静的雏型。
不难看出这篇小说也就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到后来,这段刻骨铭心的生活经验自然就转移到《青春之歌》上来了。
我认为,《青春之歌》中余永泽这一形象的塑造并无丑化和污蔑之意,至于人们怎么去议论和猜测,那是别人的事。
《青春之歌》出版以后大红大紫,张中行被人们认为是余永泽,但他对此没有表示过什么不满和怨言,用他的话来说,他“没有发过声”,他始终保持沉默。
我想这一方面是形势使然,另一方面也说明张中行这位老知识分子的涵养与品格。
杨沫对我讲到张中行,从来是敬重的。
张中行在“文革”中的表现令她感动。
她告诉我,“文革”中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审的张中行也成为了批斗对象。
当造反派逼迫他揭发她的时候,他始终没有讲过她任何坏话。
他总是说:
“那时候,杨沫是革命的,我是不革命的。
”说来说去就这两句话。
后来看到他写给北京文联外调人员的揭发材料,写的是“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
杨沫很感动,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那种处境下能坚持独立的人格很是了不起。
相反,杨沫反倒对她的丈夫马建民产生了很深的意见。
杨沫当年遇到英俊的马建民,不仅爱上他,而且频繁向马提出入党要求。
马当时是安国县几个地下党员推举出的县委书记,在杨沫多次催促下,马建民要杨沫写个材料和简历报上去。
当时组织极不健全,马未将材料报上去,就通知杨沫入党了。
“文革”中他在威逼之下将这件只有他知道的事交代出来,杨沫一时成了假党员,受到审查和批判,对马建民暗暗生恨,夫妻关系长期不好。
他们在柳荫街19号住的时候,我去过几次。
杨沫和马建民是三间屋子两头住,中间是会客室,但他们从不在会客室会客,各人的客人在各人的住室接待。
但马建民对我很客气,遇见我就请我到他住室去坐。
好像当时他是在历史研究所工作,潜心研究农民运动。
有一天谈到太平天国,我对太平天国提了几个与正统观点相左的问题,不想他竟能与我交谈下去,态度诚恳,说明他不是一个思想封闭的人。
一次杨沫同我开玩笑说:
“老范呀,凡是我的客人,老马一概不理,你可是个例外呀!
”其实老马是个好人好领导好党员。
他对家人虽然比较冷淡,但对同志却有一副热心肠。
他在北师大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时,帮助过很多人,包括坚决起用被划为右派的老师讲课,做了不少好事。
因而1985年他病逝时,北师大才会有那么多人来同他告别。
杨沫和马建民的感情被“文革”彻底撕裂了,杨沫和张中行的感情会不会在“文革”后弥合了些呢?
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
可能是两位老者在晚年对个人的名声过于重视和敏感,旧的误会和积怨消除了,又产生了新的误会和积怨。
杨沫到晚年似乎愈加珍惜自己的名声。
她曾因别人写文章提到她的感情生活而两次提出抗议和打官司。
《小说林》擅自刊发了《杨沫的初恋》一文,她向有关方面提出抗议,《小说林》召开记者招待会作检查,并公开见报。
1991年她为《梅开二度访杨沫》一文将作者告到法院。
作者汪兆骞是我的朋友,时任《当代》编辑部主任,素知我与杨大姐关系善,托我说情,愿向她当面赔礼道歉,希望不要闹上法院。
《当代》主编朱盛昌也这样托付过我。
我想,杨大姐与中科院一位研究高分子的研究员结婚之事亦非秘密,并无什么隐私可言,即使文中有些词句欠妥,都是熟人,也不必为此大动干戈。
虽然我也不赞赏作为一个严肃文学期刊的编辑部主任去写这类小报文章,但毕竟作者的态度是友善的,再婚亦是事实,我从中调解一下,一向宽厚待人的杨大姐不会再去计较,更何况自己是个公众人物,难免被人注意甚或物议呢。
我很自信,认为向她转达一下老汪的真诚歉意她就会释然,没想到官司还是打了下去。
不知是她要打还是她周围的人要打,我只好怅然地看着这个官司的结局。
暮年的张中行似乎对名声问题亦重视起来,不再像过去那样淡然了。
后来不幸又有人著文谈杨沫和张中行当年的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借以提高自己的名声,张中行则认为杨沫这__种想象是对自己的侮辱,关系再度恶化。
张中行这位老知识分子一身清高,当然不会做那种借别人抬高自己的卑劣事,但这一次似乎他也太当真了。
张中行一生低调澹泊、无欲无求,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
先生一生清贫,86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
几十年默默无闻,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读书》杂志连续发表其散文作品,接着相继出版《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等著作,名声鹊起,读者始认识这位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字、熟悉西方哲学的学者。
时过境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自此可能对往昔的一些看法也有变。
谈及《青春之歌》,难免流露出怨意。
他在《沙滩的住》中写他走过当年与杨沫住过的大丰公寓时说:
“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暗通《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这是可怀念的人,虽然今雨不来,旧雨是曾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