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玉山讲义》.docx
《朱熹《玉山讲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朱熹《玉山讲义》.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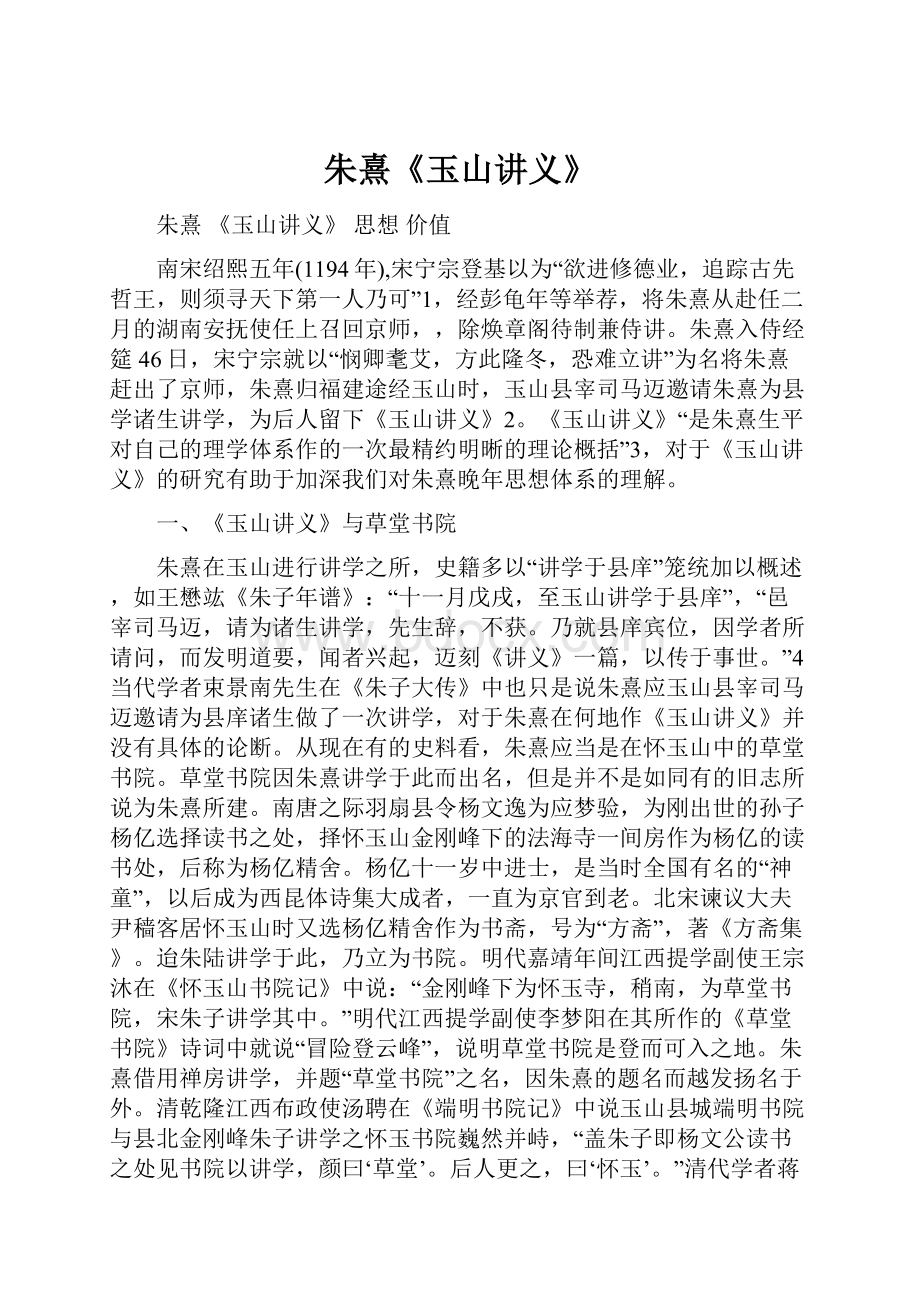
朱熹《玉山讲义》
朱熹《玉山讲义》思想价值
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宋宁宗登基以为“欲进修德业,追踪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人乃可”1,经彭龟年等举荐,将朱熹从赴任二月的湖南安抚使任上召回京师,,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朱熹入侍经筵46日,宋宁宗就以“悯卿耄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为名将朱熹赶出了京师,朱熹归福建途经玉山时,玉山县宰司马迈邀请朱熹为县学诸生讲学,为后人留下《玉山讲义》2。
《玉山讲义》“是朱熹生平对自己的理学体系作的一次最精约明晰的理论概括”3,对于《玉山讲义》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朱熹晚年思想体系的理解。
一、《玉山讲义》与草堂书院
朱熹在玉山进行讲学之所,史籍多以“讲学于县庠”笼统加以概述,如王懋竑《朱子年谱》:
“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讲学于县庠”,“邑宰司马迈,请为诸生讲学,先生辞,不获。
乃就县庠宾位,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迈刻《讲义》一篇,以传于事世。
”4当代学者束景南先生在《朱子大传》中也只是说朱熹应玉山县宰司马迈邀请为县庠诸生做了一次讲学,对于朱熹在何地作《玉山讲义》并没有具体的论断。
从现在有的史料看,朱熹应当是在怀玉山中的草堂书院。
草堂书院因朱熹讲学于此而出名,但是并不是如同有的旧志所说为朱熹所建。
南唐之际羽扇县令杨文逸为应梦验,为刚出世的孙子杨亿选择读书之处,择怀玉山金刚峰下的法海寺一间房作为杨亿的读书处,后称为杨亿精舍。
杨亿十一岁中进士,是当时全国有名的“神童”,以后成为西昆体诗集大成者,一直为京官到老。
北宋谏议大夫尹穑客居怀玉山时又选杨亿精舍作为书斋,号为“方斋”,著《方斋集》。
迨朱陆讲学于此,乃立为书院。
明代嘉靖年间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沐在《怀玉山书院记》中说:
“金刚峰下为怀玉寺,稍南,为草堂书院,宋朱子讲学其中。
”明代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在其所作的《草堂书院》诗词中就说“冒险登云峰”,说明草堂书院是登而可入之地。
朱熹借用禅房讲学,并题“草堂书院”之名,因朱熹的题名而越发扬名于外。
清乾隆江西布政使汤聘在《端明书院记》中说玉山县城端明书院与县北金刚峰朱子讲学之怀玉书院巍然并峙,“盖朱子即杨文公读书之处见书院以讲学,颜曰‘草堂’。
后人更之,曰‘怀玉’。
”清代学者蒋士铨在《怀玉山志》序中说:
“书院本唐法海寺基,迨朱陆讲学于此,乃立为书院。
”清赵佑《献堂集.复建怀玉书院记》也说:
“怀玉诸书院旧点,自紫阳朱子与陆文安、吕文成、汪文定诸公讲道其中。
”明代嘉靖年间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沐到县学视察时将当时已经被和尚占据作为寺庙的该处重新恢复为书院,改题“怀玉”。
明清时的怀玉书院,实际上就是宋时的草堂书院。
对于《玉山讲义》作于何处,朱熹没有明说,而于此前多次讲学之所,朱熹是有所指的。
例如他在给吕祖谦的信中就曾说,鹅湖之会以后,“吾痛不得自鹅湖,遂入怀玉,深山静坐数月”5卷54。
朱熹虽然未明说,但是我们从其在这次讲学后所写的《伏读美轩诗卷谨赋一篇寄呈伯时季路二兄》中,描述了他在游览怀玉山后的感叹之情,也说明他在这次讲学也是上了山的。
同治《玉山县志》卷6也说司马迈令玉山时“尝礼聘朱子讲学于怀玉山”。
而查所有史籍没有记载朱熹在其他地方有过讲学。
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与洪嘉植的《朱子年谱》都笼统说:
“迈刻《讲义》一篇,以传于事世。
”从这些史籍的记载,让人以为《玉山讲义》是玉山邑宰司马迈叫人记录《讲义》一篇而传于事世的。
事实上《玉山讲义》是朱熹在玉山草堂书院讲学后又经过朱熹在武夷山重新思考、再次说讲,将二次讲学后归纳成为一篇而形成的。
朱熹在玉山讲学后,不断思索,对玉山所讲之义并不满意,大有言犹未尽之感。
他在给林德久信中就说道:
“昨在玉山学中,与诸生说话,司马宰令人录来。
当时无人剧论,说得不痛快,归来偶与一朋友说,却说得详尽,因并两次所言,录以报之。
”5卷61因此《玉山讲义》就不是朱熹在玉山讲学的全部记录,而是将记录稿融合了朱熹以后所言经过修改后,阐发形成的,是朱熹深思熟虑的结晶。
二、《玉山讲义》的思想价值
对于《玉山讲义》,学人有不同的评价。
李绂在《朱子晚年全论》中则认为《玉山讲义》“辞繁不杀,不及《鹿洞讲义》之简明亲切耳”6。
朱熹自己认为其论述“之言虽甚简约,然其反复曲折,开晓学者最为深切。
”笔者认为《玉山讲义》是朱熹的晚年全论,是朱熹的晚年定论,也是朱熹晚年亲切之训。
第一,《玉山讲义》是朱熹的晚年全论
从《玉山讲义》看朱子理学哲学思想,内容主要涵括:
性善、四端、气禀、天理人欲、尊德性道问学等,朱子《玉山讲义》一文之内容可以作为朱子晚年思想之全论。
束景南先生将朱熹的《玉山讲义》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归结为六个方面,笔者认为是恰当的,也是全面的:
(1)性即理。
“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
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7所谓“性”,是人从天处所受之理,就此而言,可谓“性即理也”。
朱子“性即理”,实是承自程颐。
他对小程夫子“性即理”一句评价甚高。
二程讲“性即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
”8“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
”
(2)仁包四性。
性是人与物生成的源泉与规律,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与社会的资始。
朱熹的“性”已经区分为人性与物性,使之赋予社会存在现实意义。
朱熹认为性的内涵最主要的仁、义、礼、智四德,“性是理之总名。
仁、义、礼、智皆性中一理之名。
”9卷5性之体无外乎就是仁、义、礼、智四德而已。
正因为如此,朱熹才会说“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以仁义礼智之性矣”,把论“性”放在了首位。
性分仁义礼智信,但仁可包其他四性,仁义礼智可归结为仁义二性,而仁义又可归结为一仁,因此性即仁。
(3)仁义相为体用:
“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
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
”
(4)性一气殊。
在《玉山讲义》中朱熹以事譬性气,以“朝廷之命此官”譬以“天之生此人”;以“官之有此职”比于“人之有此性”,认为“朝廷所命之职,无非使之行法治已”。
朱子持气禀之说:
“性离气禀不得,有气禀,性方存在里面;无气禀,性便无所寄搭了。
”9卷94)人性是共同的,但作为每个个人所具有的人性,却是有差别的,这差别的根源,则在于气禀之不同。
人性皆善,何以人有善有恶?
“人性虽同,而气禀或异。
目其性而言之,则人自孩提,圣人之质悉已完具。
……善端所发,随其所禀之厚薄,或仁或义或孝或悌,而不能同矣。
"10朱子用气禀来说明个人善恶之差异。
性无不善,但气禀有异,所以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差别。
”在《玉山讲义》中他明确地指出:
“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质。
而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或作“清明昏浊”)之不同。
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
禀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
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是皆气禀物欲之所为,而性之善未尝不同也”。
并把人分为“圣”、“贤”、“不肖”三等:
“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
”
(5)存理灭欲。
朱熹以人的品质为核心,他认为恶源在于“人欲”。
他指出:
“人欲正天理之反耳”,“天理中本无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逆生出人欲来”5卷40。
朱熹的“人欲”就是“心之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5卷13;就是“物欲昏蔽”9卷71,“嗜欲所迷,利害所逐” 9卷8;就是“反了恻隐之心”,“如放火杀人,可谓至恶” 9卷97;就是“非”,“非底乃人欲之私”。
9卷13朱熹认为“人欲横流”,使得社会日益纷扰,他提出了人欲是恶的根源观点:
“人欲未尽,是以除恶常不能去其根”5卷14,“只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为恶” 9卷97,“只为私欲蔽疢惑而失其理”9卷46。
由此,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并以此作为思想的指导原则。
淳熙元年以后朱熹开始重定《大学》、《中庸》,对道统之学大纲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四书的思想归宗,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他认为“孔子之所以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
‘人心谓危,道心谓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9卷12所以朱熹又说:
“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存天理灭人欲”正是朱熹理欲之辨的核心,并把这样的思想看作《大学》中所说的“明明德”的主要内容。
故而在《玉山讲义》中以为:
“凡吾日用之间所以去人欲复天理者,皆吾分内当然之事,其势至顺而无难。
”古今圣愚皆同一性,但善性会被物欲所蔽,必须存天理,灭人欲,才能复性初,“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后可以复于其初。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二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存新时之天理,要以新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去节制人们,尤其是贵族豪强的非分贪婪之欲,使个人或某集团的私欲受到一定的约制,实现社会道德规范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指导,以此作为调节社会平衡,约束过度的剥削与压制,抑制劳力者的不满与反抗,最终实现社会统治次序的稳定。
(6)尊德性,道问学。
朱熹提出:
“宜熟读深思,反复玩味,就日用间便着实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谓尊德性者,正谓此也。
”尊德性与道问学虽然是各自加功,但却不是“判然两事”,二者是“交相滋益,互相发明。
”
这六个方面,构成了朱熹的道德人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六个环节,概括了他的朱学的理学文化的“精髓”,即便是在《四书集注》中,也没有能把他的思想表述总结得如此简洁明白。
第二、《玉山讲义》是朱熹的晚年定论
朱熹思想的属性历来就是通过与陆九渊思想的辨证中,加以显现出来的。
无论是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或是陈建的《学通辨》,还是李绂的《朱子晚年全论》,均是通过对朱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辨,确认朱熹的晚年思想之定论。
而事实上朱熹早已经在《玉山讲义》中阐发了他的晚年思想之定论。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初夏.陆九渊及其五兄陆九龄应吕祖谦之约.会朱熹于信州铅山鹅湖寺,就本体认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朱陆之争集中对《中庸》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中“尊德性”与“道问学”哪一个更重要、更优先的问题,也就是读书治学、教书育人在内的方法论之争。
到底应在格物穷理、读书学习上多下功夫还是应在发明本心、省察内心上多下功夫的问题。
随陆九渊参加了这次约会的朱亨道记述道: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
”11从哲学本体论而言,朱陆二人之争是“性即理”与“心即理”之争的外现。
朱熹则认为心与理为二,理是本体;心是认知的主体,理生万物,心具众理而应万物认为理寓万物之中,要穷理致知就必须格物即事,从认识客观事物入手,由感性认识而后上升到理性知识。
“泛规博览而后归之约”,朱熹不否认外部事物的存在,认为明心致善不能脱离外物。
陆丸渊认为理在吾心,吾心即理,吾心便是宇宙,良知良心心人所共有,所以他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认为先验的道德理性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物而就存在于人心之中。
“道问学”与“尊德性”问题上,朱熹则以为“尊德性,所以存心:
而极乎道体之大也:
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趟之大端也。
”朱熹以“道问学”为宗,主张即物穷理、格物致知、读书明理,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内心潜在的良知,朱熹把“道问学”当成了更好地“尊德性”的手段,把“尊德性”作为目的,而把“道问学”作为实施方法;陆九渊以为“既不知尊德,焉有所谓道问学”,以“尊德性”为宗,认为读书不是成圣贤的必要条件主张发明本心、切己自反、立心做人.省免“向外用功”的功夫,不主张多做读书穷理的工夫,抛弃了任何中介手段。
陆九渊把“尊德性”作为根本的实施方法和目的。
事实上陆九渊、朱熹确实以“尊德性”、“道问学”形成了两者在实施方法上的分别.尽管实施方法不同,但总的目标是一致的。
这就是说.“尊德性”和“道问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造就合乎封建圣贤目标的合格人才。
黄宗羲对于朱熹的“尊德性”和“道问学”关系问题上有过认识,认为朱熹以道问学为主.黄宗羲说:
“先生(陆九渊)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人者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
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
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
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
”12实际上鹅湖之会并不是朱熹思想的定论。
从鹅湖之争到玉山讲学,将近二十年过去,朱熹对“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上有了些改变,在《玉山讲义》中指出:
“圣贤教人,始终本来,循循有序,精组原细,无有或遗。
故才尊德性,便有个道向学一段事。
虽当各自加工,然亦不是判然两事也。
”“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
……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以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
要当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贝阙处矣。
”在朱熹看来“尊德性以便其大",“道闸学以尽其小”,“使之交相滋益,互相发明”,“亦不是判然两事”。
提倡尊德性和道问学的统一,致广大和尽精微的统一,极高明与道中庸、的统一,温故与知新的统一,敦厚与崇礼的统一。
可以说《玉山讲义》正是朱熹的晚年定论。
第三、《玉山讲义》是朱熹晚年亲切之训
朱熹在《玉山讲义》中对晚辈的教诲言于表上。
《玉山讲义》完全把抽象的理气性命的玄理探讨变成了一个“勇猛着力”的实行实做的迫切现实问题,正反映了他晚年的一种由博返约、由知到行的思想动态。
他认为: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
”在对待因为“气禀昏愚而物欲深固”,朱子更是洞察清晰,加入指出“其势虽顺且易,亦须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后可以复其初。
”朱熹针对当时科举制度“追求利禄”的功利主义,专以“文词”取士的考试方法,“缀辑言语,造作文词”文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
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
他认为“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缉缀言语,造作文词,但为科名爵禄计”,他还具体指出改革评价内容的主张,即“罢诗赋”。
“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
”
同时朱熹指出:
“今时学者,心量窄狭不耐持久,故其为学略有些少影响见闻,便自主张,以为至是,不能遍观博考,反复参验,其务为简约者,既荡而为异学之空虚,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为流俗之卑近,此为今日之大弊,学者尤不可以不戒。
”朱熹又以玉山籍汪应辰及知县司马君迈先人为例,以为汪应辰“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显而未尝少有自满之色,日以师友前辈多识前言往行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司马光“以盛德大业为百世师”,要求诸生学习,弟子们都把这篇讲义奉为“晚年亲切之训”了。
朱熹是将“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评论的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作为学者治学为政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