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特殊性.docx
《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特殊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特殊性.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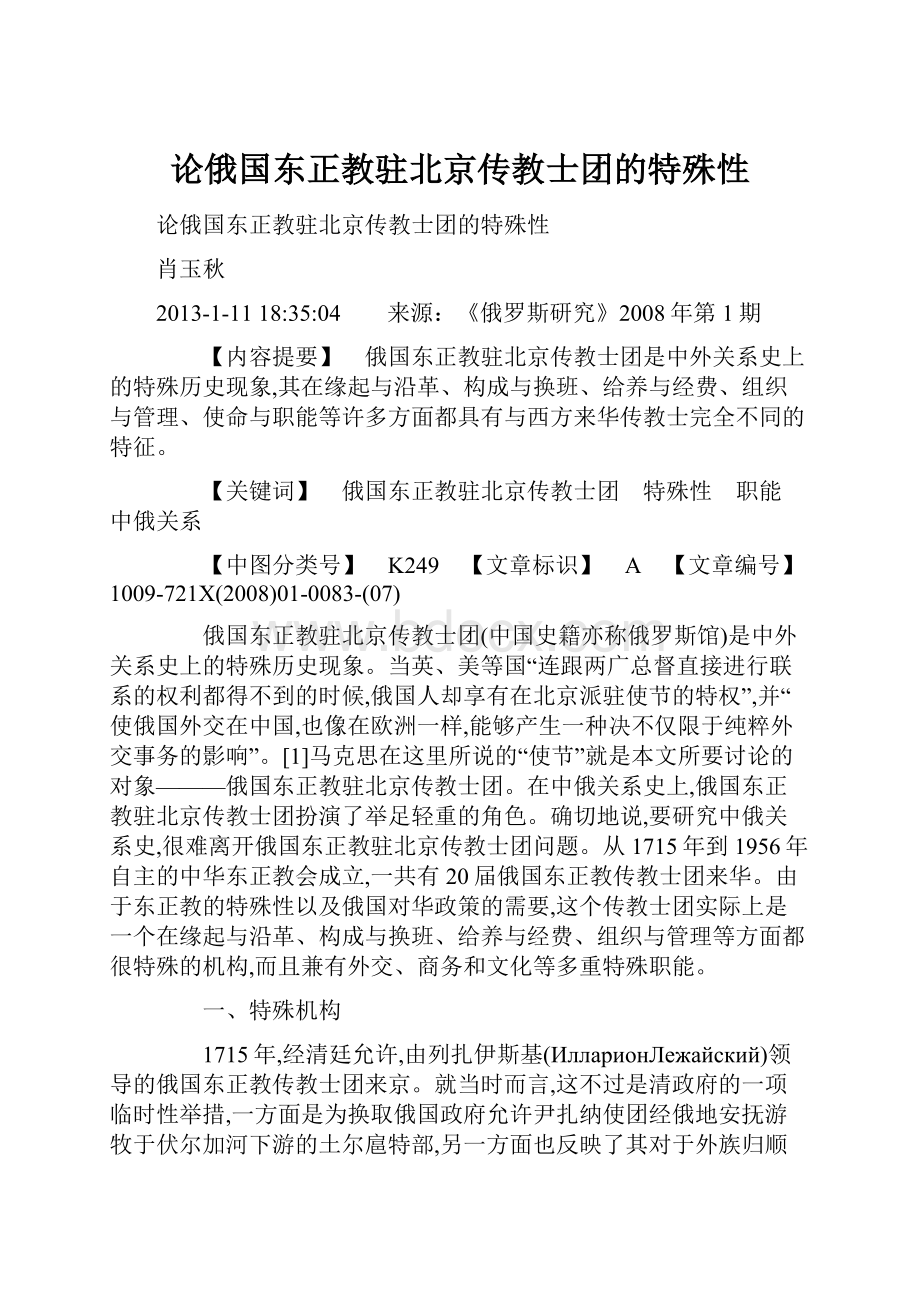
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特殊性
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特殊性
肖玉秋
2013-1-1118:
35:
04 来源:
《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1期
【内容提要】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其在缘起与沿革、构成与换班、给养与经费、组织与管理、使命与职能等许多方面都具有与西方来华传教士完全不同的特征。
【关键词】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 特殊性 职能 中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8)01-0083-(07)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中国史籍亦称俄罗斯馆)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
当英、美等国“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权利都得不到的时候,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特权”,并“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能够产生一种决不仅限于纯粹外交事务的影响”。
[1]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使节”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
在中俄关系史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确切地说,要研究中俄关系史,很难离开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问题。
从1715年到1956年自主的中华东正教会成立,一共有20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华。
由于东正教的特殊性以及俄国对华政策的需要,这个传教士团实际上是一个在缘起与沿革、构成与换班、给养与经费、组织与管理等方面都很特殊的机构,而且兼有外交、商务和文化等多重特殊职能。
一、特殊机构
1715年,经清廷允许,由列扎伊斯基(ИлларионЛежайский)领导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来京。
就当时而言,这不过是清政府的一项临时性举措,一方面是为换取俄国政府允许尹扎纳使团经俄地安抚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对于外族归顺所采取的“怀柔远人”、“因其教,不易其俗”的一贯做法,让俄国神父为主要由雅克萨战俘组建的镶黄旗俄罗斯佐领提供宗教服务。
然而,中国方面的宽容态度为俄国实现其在中国建立一稳定据点的想法提供了机遇。
1727年,俄国政府坚持将在北京建立教堂并派驻传教士和学生的内容写入主要用来解决中俄贸易和划界问题的《恰克图条约》。
这个条约的第5款规定:
“京城之俄罗斯馆,嗣后惟俄罗斯人居住。
其使臣萨瓦所欲建造之庙宇,令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在俄罗斯馆建造。
现在京居住喇嘛一人,其又请增遣喇嘛三人之处,著照所请。
俟遣来喇嘛三人到时,亦照前来喇嘛之例,给予盘费,令住此庙内。
至俄罗斯等依本国风俗拜佛念经之处,毋庸禁止。
再萨瓦所留在京学艺之学生四名,通晓俄罗斯、拉替奴字话之二人,令在此处居住,给予盘费养赡。
”[2]该条约的重要意义在于正式确立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法律地位,同时对其在北京的驻地、人员构成和给养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该条约成为以后130年间俄国政府派遣传教士团来华、清朝政府处理俄国传教士团问题的主要依据。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与天主教耶稣会士的这种根本差别,构成了其得以在中国的禁教政策下长期存在的基础。
1858年的《中俄天津条约》是又一个对传教士团发生重要影响的双边条约。
该条约第8条规定:
“天主教原为行善,嗣后中国于安分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亦不可于安分之人禁其传习。
若俄国人有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者,领事官与内地沿边地方官按照定额,查验执照,果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以便稽查。
”[3]《中俄天津条约》肯定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俄国人前往北京以外地区传教。
据此,俄国传教士团摆脱了《恰克图条约》相关条款的束缚,从以雅克萨战俘后裔为主要服务对象转变为在中国国民中传播东正教,活动范围也从北京扩大到其他省份。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彻底烧毁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驻地———北馆,并杀死中国籍东正教徒222人。
俄国圣务院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К.П.Победоносцев)一度计划关闭驻京传教士团或将其转移到西伯利亚或旅顺口。
然而,俄国政府最终还是没有放弃其经营多年的老巢,不但决定继续保留传教士团,甚至在中国建立了主教区,以方便中国教徒的神职晋升,继续扩大在华宗教影响。
1902年6月10日,俄国政府决定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领班将由主教神阶担任,并由其同时负责俄国在满洲地区的教务,兼管中东铁路沿线的大小教堂。
第18届传教士团领班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ИннокентийФигуровский)成为俄国在中国派驻的第一任主教。
他利用庚子赔款在天津、上海及武汉等地建立教堂,开办学校,发展教徒,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播达到了高潮。
由此看来,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作为一个宗教组织,长期受到中俄双边条约的保护,先在北京立足,进而向全国扩张,这在中外关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从1922年起宣布效忠于流亡的塞尔维亚教廷,直到1945年最后一任主教维克多(ВикторСвятин)才恢复了与莫斯科牧首公署的联系。
1924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更名为中国东正教会,在北京设立总会,下辖北京、上海、哈尔滨、新疆和天津等教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东正教走向衰落。
1955年,莫斯科牧首公署下令关闭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并将其所有财产移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
经莫斯科牧首公署允许,1956年自主的“中华东正教会”成立,中国东正教徒进入自主管理中国教务的新时期。
这样,从1715年到1956年自主的中华东正教会成立,241年间共有20届东正教传教士团被派驻北京,前后跨越了三个世纪。
在这数百年期间,中俄两国都经历了沧桑巨变、政权更迭,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却始终维持了自身的存在。
传教士团虽名为宗教使团,但前14届由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两部分组成。
《恰克图条约》规定,传教士团除4名“喇嘛”外,还包括4名“在京学艺之学生”和“通晓俄罗斯、拉替奴字话之二人”。
而事实上每一届传教士团的人数不等,一般多则十几人,少则不足十人。
神职人员包括修士大司祭(Архимандрит)、修士司祭(Иеромонах)、修士辅祭(Иеродиакон)和教堂差役(Причетник)。
传教士团领班由修士大司祭充任。
世俗人员中起初只有学生(Ученик或Студент)(第1届至第4届、第6届至第14届)一种,后来逐渐增加了监护官(Пристав)(第8届至第14届)、医生(第10届至第14届)、画家(第11届至第14届)以及临时差遣人员(Прикомандированный)(第11届和第12届)。
学生始终是世俗人员的主体。
监护官是俄国政府的特派官员,由文官或武官担任,居留北京半年至一年,主要任务是护送新一届传教士团抵京及上一届返俄,同时搜集中国情报,就中俄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与清政府进行谈判。
第11届监护官拉德仁斯基(М.В.Ладыженский)原是俄国总参谋部上校,第12届监护官柳比莫夫(Н.И.Любимов)和第13届监护官科瓦列夫斯基(Е.П.Ковалевский)后升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监护官职位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与前7届相比,后7届传教士团人员的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神职人员减少,世俗人员增加。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第14届传教士团中的医生和3名学生被转入俄国驻华外交使团,而画家和1名学生的位置被取消。
从第15届传教士团起,世俗人员一律停派,传教士团完全由神职人员组成,规模被确定为6人,即领班1人,修士司祭3人,神父和诵经士各1人,其中神父和诵经士允许录用中国人担任。
1875年根据俄国驻华公使的建议,传教士团的编制扩大到9人。
据笔者统计,从第1届到1902年中国主教区(第18届任内)成立以前,俄国一共派遣传教士团成员178人次,其中神职人员111人次,世俗人员67人次。
世俗人员包括47名学生、5名医生、4名画家、4名临时差遣人员和7名监护官。
前7届神职人员51人次,世俗人员20人,后7届神职人员34人次,世俗人员47人。
《恰克图条约》没有提及传教团的换班问题。
后来每届传教团来京,均需预先获得清政府的批准,由此渐渐形成定例。
从第4届开始,俄国将传教士团在华的居留时间确定为7年,其中不包括往返北京路途用时。
[4]外务院随即于1755年又就传教士团中学生的学习期限做出专门指示:
“对派赴北京学习语文的学生,自他们到达北京之日算起,学习期限为十二年,期满后即行返回俄国。
”[5]1845年第12届领班佟正笏(П.А.Тугаринов)曾就缩短班期问题向理藩院提出过请求:
“俄罗斯国拣选喇嘛学生来至中国学习清文,换班年分不同,或逾十年更换,或不及十年更换,合计程途往返,总须十二年后方能归国。
该喇嘛学生等俱有父母在家,思念情切,恳请定为五年换班。
”[6]从第13届开始,俄国政府将传教士团的在华任期改为6年,但也没有严格执行。
《中俄天津条约》第10条规定:
“俄国人习学中国汉、满文义居住京城者,酌改先时定限,不拘年分”。
[7]实际上在1861年俄国驻华公使馆建立以前,传教士团居京时间长短不一,最短的是第2届为6年,最长的是第5届,长达17年。
从传教士团成员个人角度考察,大多数成员任职一届,但也有人任职两届,如卡缅斯基(П.И.Каменский)(第8届和第10届)、魏若明(ВениаминМорачевич)(第10届和第11届)、佟正笏(第11届和第12届)、固礼(ГурийКарпов)(第12届和第14届)等,而巴拉第(П.И.Кафаров)前后任职3届(第12届、第13届和第15届),居京时间长达30多年。
俄国传教士团在京的日常生活供给从一开始就由清政府提供。
这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形成鲜明对照。
清政府给传教士团所有神职人员授予品级不同的官职,并每月向所有成员发放俸禄。
修士大司祭被赐五品官,修士司祭与修士辅祭被赐七品官,学生享受披甲待遇。
所有传教团成员都在圣尼古拉教堂附近得到了官家住房和土地,另有临时补助:
修士大司祭得银800两(1500卢布),另获赐600两(约1100卢布)用以雇佣仆从;修士司祭与修士辅祭每人获银600两,另有400两用以雇佣仆从;教堂差役每人领到300两,另外每人还有200两用来雇佣仆从。
此外,理藩院每月还给他们发俸银,神职人员每人4两半(武职俸额),教堂差役每人1两半,另从官家粮仓中发给每人禄米3斛。
3年后还向他们发放置衣费,修士大司祭40两(70卢布),修士司祭和修士辅祭每人30两,教堂差役每人20两。
按照当时俄罗斯国喇嘛学生案,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军机处档,《史料旬刊》第二辑,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辑,1930年。
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Z],北京:
三联书店,1982年,第88页。
的汇率,中国政府向俄国传教团发银总计428卢布70戈比。
皇帝对他们恩遇有加,还赐给部分教堂差役妻室。
[8]一直到中俄签订《天津条约》,中国才停止向俄国传教士团提供给养。
《中俄天津条约》第10条就传教士团在华日常开支做了新的规定,即“所有驻京俄国之人一切费用,统由俄国付给,中国毋庸出此项费用”。
[9]至于传教士团在京所需经费,则由俄国方面提供,通常从西伯利亚收入中支出,以现银或为毛皮形式由商队或信使在北京转交。
比如,从1754年到1758年,从商队公款中向传教团发放了7490卢布87戈比的给养。
从1758年到1762年向传教团提供了价值6800卢布的毛皮作为薪俸。
1762年克罗波托夫(И.И.Кропотов)信使另向尤马托夫(АмвросийЮматов)修士大司祭发放了1763年全年和1764年半年的经费共计11050卢布。
[10]
传教士团接受俄国外交部门和圣务院领导,其在华活动由外交部门和圣务院的相关指令规定,其中最早的当数1734年12月31日俄国圣务院发布的名为《修士大司祭及其属下职责和行为管理条例》的第1983号指令。
全文包括11款,规定了传教士团领班在中国任职期间应遵循的行为规则,内容主要涉及宗教层面。
以后各届传教士团的宗教活动或照此指令行事,或在此指令基础上重新制定,如1780年圣务院给第7届领班希什科夫斯基(ИоакимШишковский)的指令就与1734年指令在内容上大同小异。
这一年希什科夫斯基还领受了外务院签发的7条特别训示,其中对给养使用、换班交接以及与清政府交涉等事宜做了严格规定。
无论是圣务院,还是外务院,都指示修士大司祭要把当地情况写成材料上报回国。
19世纪初期俄国与中国的陆路贸易受到西方国家在中国沿海地区贸易的极大威胁,俄国政府开始更加认真地经营这个令欧洲国家羡慕的在华常驻机构。
1818年俄国外交部为第10届传教士团制定了新的指令。
首先,新指令大大增加传教士团的活动经费,由原来的6500卢布升至16250卢布。
其次,在学业上有所成就的传教士团成员回国后不仅可以得到数量可观的奖金,而且还将被加官晋爵。
[11]第三,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世俗人员,新指令为每个人规定了在北京期间的任务。
另外,所有成员必须学习当地语言,神职人员须学习汉语,学生们还须学习满语和蒙古语。
第四,在传教士团中成立以修士大司祭为首的三人管理委员会,处理传教士团的内外事务,以避免领班擅权专断。
新指令特别强调今后传教士团在中国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教而是研究中国国情,为俄国政府搜集情报。
新指令对传教士团的组织、任务和管理重新进行了定位,使其在运作过程中更加积极和高效。
从第10届到第14届,俄国驻京传教士团即是依照1818年指令派出并运作的。
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的当年,俄国圣务院根据条约中有关允许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条款,对1734年指令进行了修订和补充,规定驻北京的传教士们可以在中国人中间传教,但一定要小心谨慎,不事声张,使用温和的办法。
[12]1861年俄国政府依照《中俄北京条约》在北京设立公使馆。
1863年俄国外交部亚洲司经过与圣务院协商,制定了《关于改组驻北京传教士团以及将一名医生和三名学生划归外交使团管理的决定》,对俄国在北京的宗教使团和外交使团两个机构的地位、职能、构成以及给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区分。
1864年9月,俄国圣务院根据《中俄北京条约》有关规定和沙皇谕旨颁布了20230号新指令。
新修订的指令共包括45项内容,规定北京传教士团完全由圣务院领导,同时为改组后的传教士团确定了三大任务:
“第一,在北京的东正教堂中组织礼拜和主持圣礼。
第二,确立并维持由阿尔巴津人、俄罗斯逃人后代以及接受东正教的中国人构成的东正教群体的正教信仰。
第三,根据需要在异教徒中传播正教。
”指令还要求传教士团成员学习汉语,但目的已不是为了搜集中国情报,而是为了翻译东正教经书,并对以往传教士团成员的作品进行补充和完善。
指令允许传教士团领班在中国建立祈祷所,必要时也可以建立教堂,传教士团活动范围可以扩大到北京以外地区这样,俄国传教士团脱离了外交部的管理,直接对圣务院负责。
但是,当传教士团遇到涉及中俄关系和关系俄国利益的问题时,仍须听命于俄国驻京公使。
19世纪90年代,当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准备对传教士团工作进行改革并大力推进在华传教事业时,“俄罗斯外交部以及俄罗斯驻北京的使节将这视为是对俄中正常关系的威胁”,一直到十月革命以前,东正教教权依附于政权的原则没有始终发生改变。
有学者认为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政府的关系是“相依而行,携手共进”。
而东正教之于俄国政府,却是一种奴才和主子的关系。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更多的是代表了俄国政府的利益,而非俄国教会的意志。
二、特殊职能
正如蔡鸿生先生所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中俄关系,无论商务、外交还是文化,几乎事事通过俄罗斯馆,构成一种蜘蛛网式的关联。
”即使在1861年俄国驻京公使馆设立以后,中俄间的外交和文化关系与传教士团之间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名义上的宗教机构在中俄关系史上扮演了极其复杂而重要的角色。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除了宗教职能外,还具有外交、商务和文化等多重功能,这是其最显著的特点。
俄国东正教随俄国雅克萨战俘和越境逃亡者来京,似乎并非俄人有意为之,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
而俄国政府派遣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乍看上去仅仅是为了给俄罗斯佐领主持圣事而已。
但是,无论是沙皇,还是圣务院,都对那已经是大清子民的不足百名雅克萨战俘给予了异常的关注,并硬是将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的条款写入了《恰克图条约》,使驻北京传教士团从第2届开始具有了常设机构的性质。
显然,这其中包含着俄国政府更为深刻而长远的考虑。
俄国政府希望借助传教士团保持与中国的经常性联系,保障在中国的贸易利益,并且希望通过传教士团达到诸如刺探中国情报、培养翻译人才、与西方天主教士竞争等目的。
法国加斯东·加恩就曾说:
“俄国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增加了它与中国的接触,这主要是需要取得经济上的谅解……。
在俄国的远东计划上,它始终把商业利益放在重要地位。
”“俄国利用宗教来达到外交上的目的,这即是说,最后为了达到通商的目的。
”对于俄国政府而言,政治利益和贸易利益始终是其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考虑因素,而在华发展宗教势力只是实现其主导利益的手段;一旦俄国在华宗教活动有可能影响到两国的政治和贸易关系时,俄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宗教利益。
基于这些情况,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势必要同时扮演多种历史角色,其活动“不仅仅限于宗教领域本身,而且还扩展到了政治、经贸、科学和文化领域。
”与此同时,这些角色又因中俄关系的发展、俄国远东政策调整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不断经历着微妙的变化。
在政治方面,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承担着一个外交使馆所应该承载的所有功能。
传教士团建立之后,直至俄国驻华公使馆成立以前,中俄两国间的公文传递,谈判交涉,离不了传教士团的参与。
第2届学生罗索欣(И.К.Россохин)、第3届学生列昂季耶夫(А.Л.Леонтьев)等多人都曾被理藩院借用负责翻译两国间往来的公函,第4届学生萨赫诺夫斯基(ЕфимСахновский)参加了俄国布拉季舍夫(В.Ф.Братишев)使团与清政府的谈判。
与此同时,传教士团利用一切机会搜集中国情报,比如利用在理藩院任翻译之职时,甚至连每月初一去理藩院领取钱粮的机会也不放过。
第6届学生阿加福诺夫(А.С.Агафонов)、巴克舍耶夫(ФедорБакшеев)和帕雷舍夫(АлексейПарышев)集体编写了《大清国1772———1782年秘密行动、企图、事件和事变录》。
从这份材料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其明显的情报性质。
它详细记述了清军平定苗人叛乱、1777年山东的暴动、1870年班禅六世进京以及土尔扈特渥巴锡汗率众返回中国等事件。
他们在文中直言不讳地声明:
“无论在什么时候,不管是满人,还是汉人,我们都与他们友好交往,时常见面,好言善语,赠送礼物,交了很多朋友。
其中有些朋友非常公开地与我们交友,透露给我们很多事关国家的机密。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团的“喇嘛”和“学生”介入中俄外交事务的情况更加频繁。
在俄国侵华过程中,传教士团向俄国政府提供了数不清的情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参谋作用。
中俄双方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几乎都离不开传教士团的帮助和策划。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成了俄国驻伊犁、塔城和天津的领事,直接参与对中国的瓜分。
在《中俄天津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巴拉第是俄国方面的主谋之一,就连条约文本,也是由第13届传教士团学生赫拉波维茨基(М.Д.Храповицкий)翻译的。
而固礼和原第12届传教士团医生塔塔里诺夫(А.А.Татаринов)则是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俄方的主要谈判代表。
1862年原第12届传教士团学生扎哈罗夫(И.И.Захаров)又被任命为全权会勘地界大臣,于1864年协助巴布科夫(И.Ф.Бабков)全权大臣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等。
结果俄国不仅同西方列强一道分享了在华的各种权益,并且独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与此同时,传教士团还承载着一定的商务功能。
根据《恰克图条约》后形成的惯例,俄国传教团只能随商队而来,除非得到中国政府的特别许可,绝对禁止随外交信使或使团前来。
18世纪上半期,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驻地南馆既是俄国商队的住所,也是其贸易的据点。
18世纪后半期虽然“京师互市”停止,但作为传教士团薪俸的俄国毛皮货物仍源源不断进京,为了获取暴利,私人与官方的货物也趁机夹杂其中。
所有这些货物都要在北京市场出售。
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商品涌入中国,俄国粗呢和毛皮等传统对华出口商品遇到英国商品的竞争和挑战,俄国在恰克图的对华贸易量下跌。
传教士团受政府之命对包括俄国商品在中国的销路、英国货物的品种和价格以及其他一切与俄国在华商业利益有关的信息给予关注,并不断写成报告寄送国内。
而自茶叶超过其他商品成为俄国从中国进口的最大宗商品之后,俄国传教士团成员非常重视搜集与茶种、茶区、茶路和茶价有关的情报。
19世纪40年代传教士团提供了有关茶叶运往恰克图路线的情报,即从福建出发,沿内河到上海,经海路到天津,转白河至通州,最后经张家口运到恰克图。
50年代巴拉第报告,为避开清政府征收高额关税,中国商人采取陆路运输的办法,海路完全被取代。
1853年巴拉第用显影墨水写的报告称:
“中国现实的动乱对贸易额的不良影响越来越明显。
从事恰克图贸易的中国商人们已遭受了2000000两(折合4310000银卢布)的损失,因为武装起义者破坏了商埠汉口,抢劫了商人们存有期票的当地商铺。
为恰克图订购的200000箱茶叶迄今运到张家口的只有一半,有关其他批茶叶的运输情况还没有一点好消息。
人们甚至认为,由于中国南部的动乱,本年只会有少数商人决定在福建订购茶叶,因此明年(?
)也未必能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所造成的恐怖,使得经过湖广地区的运输已经中断……”此外,传教士团还为俄国获取和扩大在华陆路通商特权献计出力,佟正笏于1944年建议政府在中国西部为俄国工业品开辟新的销售市场,柳比莫夫1845年到塔尔巴哈台和伊犁考察,而科瓦列夫斯基作为俄国政府全权代表最终在1851年迫使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最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也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
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始终是中俄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桥梁。
传教士团是俄国汉学的摇篮。
自传教团派出后的约二百年间,传教团成员中涌现出以罗索欣、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第9届领班)、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第12届临时差遣人员)为代表的大批汉学家。
他们从中国的哲学与宗教、语言与文学、历史与地理、社会与法律,甚至农业、天文和经济等不同角度对中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机构,中国与俄国之间才发生了教育、图书、美术、医学以及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
传教士团的教育活动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俄国留华学生教育、俄国本土满汉语教学、中国俄语教学、编写教材和词典以及在华开办教会学校等多个方面。
传教士团还将俄国图书引入中国,展示西洋绘画、西医,同时搜集中国典籍,钻研中国美术和中医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文化活动尽管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为增进中俄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发挥了作用。
“特殊”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
之所以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特殊,就是因为它在缘起与沿革、构成与换班、给养与经费、组织与管理、使命与职能等许多方面都具有与西方来华传教士完全不同的特征。
这种特殊性的产生与中俄两国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东正教的实质以及中俄两国的社会变迁都有密切的联系。
(责任编辑 陈 扬)
*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文化功能研究”。
**肖玉秋,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成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8页。
[2]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
三联书店,1982年,第11页。
[3]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
三联书店,1982年,第88页。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