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炜烨而谲诳共13页.docx
《说炜烨而谲诳共13页.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说炜烨而谲诳共13页.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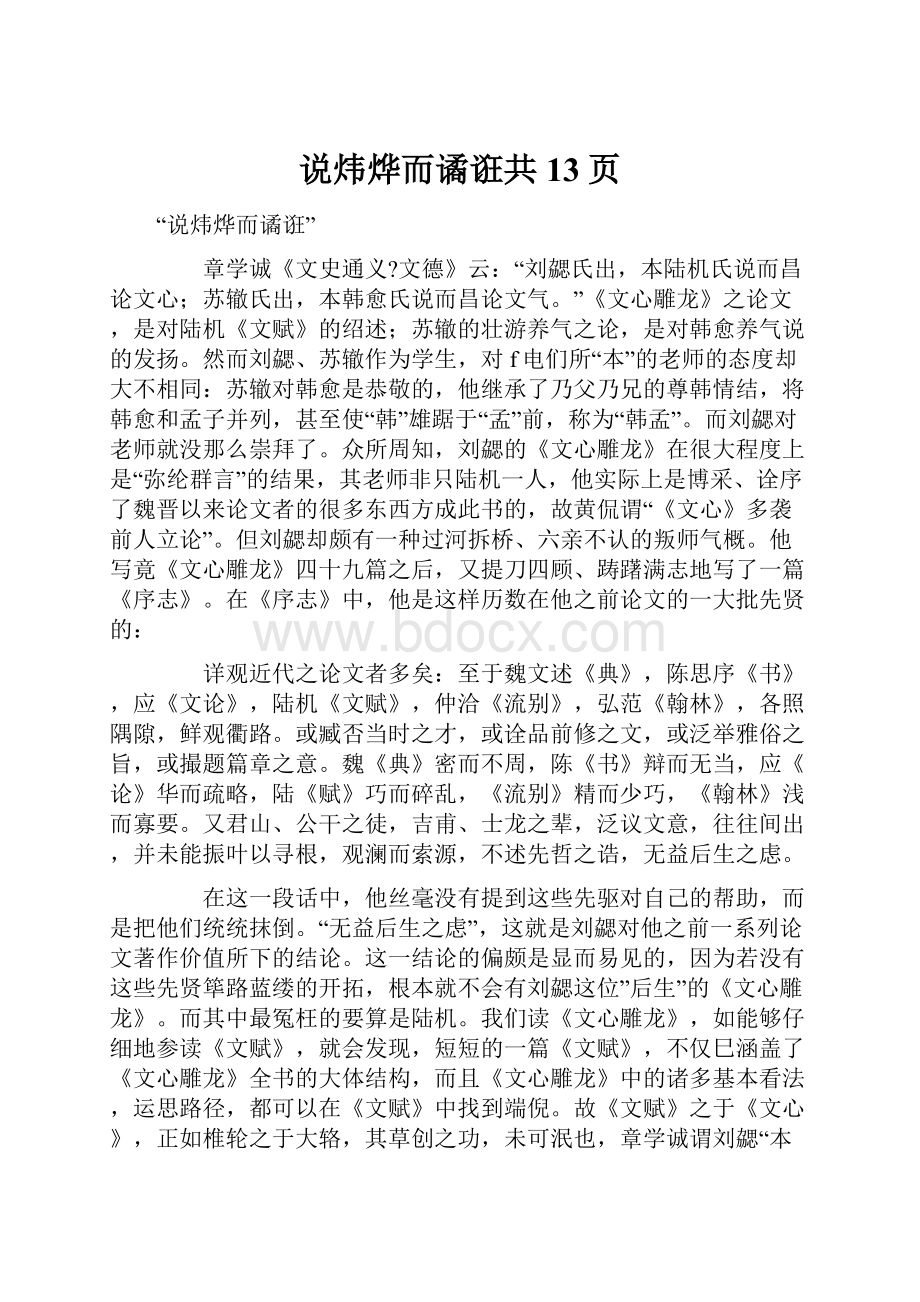
说炜烨而谲诳共13页
“说炜烨而谲诳”
章学诚《文史通义?
文德》云:
“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
”《文心雕龙》之论文,是对陆机《文赋》的绍述;苏辙的壮游养气之论,是对韩愈养气说的发扬。
然而刘勰、苏辙作为学生,对f电们所“本”的老师的态度却大不相同:
苏辙对韩愈是恭敬的,他继承了乃父乃兄的尊韩情结,将韩愈和孟子并列,甚至使“韩”雄踞于“孟”前,称为“韩孟”。
而刘勰对老师就没那么崇拜了。
众所周知,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很大程度上是“弥纶群言”的结果,其老师非只陆机一人,他实际上是博采、诠序了魏晋以来论文者的很多东西方成此书的,故黄侃谓“《文心》多袭前人立论”。
但刘勰却颇有一种过河拆桥、六亲不认的叛师气概。
他写竟《文心雕龙》四十九篇之后,又提刀四顾、踌躇满志地写了一篇《序志》。
在《序志》中,他是这样历数在他之前论文的一大批先贤的: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
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
或臧否当时之才,或诠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
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
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在这一段话中,他丝毫没有提到这些先驱对自己的帮助,而是把他们统统抹倒。
“无益后生之虑”,这就是刘勰对他之前一系列论文著作价值所下的结论。
这一结论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若没有这些先贤筚路蓝缕的开拓,根本就不会有刘勰这位”后生”的《文心雕龙》。
而其中最冤枉的要算是陆机。
我们读《文心雕龙》,如能够仔细地参读《文赋》,就会发现,短短的一篇《文赋》,不仅巳涵盖了《文心雕龙》全书的大体结构,而且《文心雕龙》中的诸多基本看法,运思路径,都可以在《文赋》中找到端倪。
故《文赋》之于《文心》,正如椎轮之于大辂,其草创之功,未可泯也,章学诚谓刘勰“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洵非虚语。
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非但讳谈所本,而且多次以批评《文赋》来显示自己的高明。
应该看到,刘勰之讳言其本、露己扬才,主要是受到了时风的习染。
魏晋六朝时代,是文人士大夫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得到极大张扬的时代。
汉末社会的惨烈丧乱与动荡,促发了士人对短暂的人生中自我价值的反思;而封建大一统的王纲解纽,使尊崇群体、压抑个性的儒学思想统治完全轰毁;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的兴起,也为人们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合适的温度。
在这种情况下,长期被囚禁在名教之下的人的鲜活的个性,也就被理直气壮地强调出来。
《世说新语?
品藻》载:
“桓温问殷浩:
‘卿何如我?
’殷答曰: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宁作我”,可以看作是魏晋士人崇尚自我、崇尚独立精神人格的宣言。
在这个时代中,那长期被汉代官方意识形态所放逐的、感性的、自然的“我”,不仅回归于士人的心中,而且,好像是对汉儒压制自我的惩罚似的,它很快地就跃居于士人的精神世界的中心,成为他们价值判断的唯―依据和思想行为的出发点。
价值判断首先是自我判断。
因为士人以“我”为核心,故在自我评价上往往有超高的自信。
“傲”,是当时士人自我崇拜的一个突出表现,葛洪在《抱朴子?
疾谬第二十五》中说当时的士林风气:
“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故让莫崇,傲慢成俗。
”“今人何其愦慢傲放如此乎!
”魏晋以还,士人中颇多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狂者。
《世说新语?
品藻》载:
“或问殷浩:
‘卿定何如裴逸民?
’良久答曰:
‘固当胜耳!
’又:
“桓大司马(温)下都,问真长(刘)曰:
‘闻会稽王(司马昱)语奇进,尔邪?
’刘曰:
‘极进。
然固是第二流人耳!
’桓曰:
‘第一流复是谁?
’刘曰:
‘正是我辈尔!
’”正是文人狂傲的例子。
这种大言不惭、理直气壮的自我矜伐之风,更突出地表现在文学创作之中。
那时的文人,“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他们“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曹丕《典论?
论文》),自矜其能,以居人下为耻。
文士们不但傲视同代,甚至肆无忌惮地藐视经典和古代圣贤。
《世说新语?
文学》:
“庾子嵩(庾鼓)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
‘了不异人意!
’”,《南史?
张融传》:
“永明二年,宗明观讲,(张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饮之。
难问既毕,乃长叹曰:
‘呜呼,仲尼独何人哉!
’”又载:
“(张)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宋武帝)日:
‘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
’答曰:
‘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
’”……
这种鼻孔撩天、睥睨千古的“狂”,便是那个时代的名士的“本色”和“风流”。
它以一种自我矜伐的形象,反映了士人的主体意识在长期受压之后的反弹与膨胀。
从历史上看,文人的自矜之风发于汉末,大煽于两晋,其余烈一直延宕于六朝,而且由豪族大腕扩展到一般文人,成为整个士林中的一种“流行性感冒”。
故颜之推《颜氏家训?
文章篇》评当时文坛:
“矜伐,故忽于操持,果于进取。
今世文士,此患弥切。
”“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
”又云:
“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
f痴符’。
”便是当时士林这种风气的写照。
所以说,刘勰的矜才扬己,可以说是一种时代性格,此病固不可不知,但于他本人却又未可深非也。
正是出于这种崇己抑人的时代流行病,刘勰一方面在《文心?
序志》中痛贬先贤的“无益”,另一方面又不厌其烦地称诩己作的登峰造极:
“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总之:
“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
这不正是善于自见、崇己抑人的矜伐之风的典型表现吗!
当然,矜伐自矜伐,今天看来,《文心》论文之淹通精审、体大虑周,确实是超乎前人的,刘勰也的确不失为深谙文学之理的巨匠,他对于陆机《文赋》的批评也并非毫无道理。
比如,他在《序志》中说《文赋》“碎乱”,在《总术》中也说《文赋》“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都还是符合事实的。
可也正因为他矜伐,其中也就有出于自己的浮躁和意气而批错露怯的地方。
作为研究者,我对他正确的批评和错误的批评都很关心。
但似乎对后者更感兴趣。
因为这一点在以往的《文新雕龙》研究中常常是被忽略的。
多年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是我们古文论研究的中心,“龙学”成了我们古文论界的“经学”。
而且由于历史的惯性,我们不少的研究者也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前代经学的研究模式。
而经学研究的最大弊病,就是预先设定被研究之经典的绝对完满,使研究者的思维以它为中轴,千方百计地阐释它的正确,从而掩盖、甚至弥纶了其中本来存在的谬误和缺陷。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拟另撰文来谈,这里不赘。
《文心雕龙》中,除了前文所举对于《文赋》的笼统否定,还有两处对《文赋》的具体论述的批驳。
遗憾得很,这两处都是批错了的。
第一处误批已为钱锺书所拈出。
《文赋》中有这样一段话:
“彼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
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
’原意是讲作家对文章的熔裁要适可而止,不能把平凡的句子全部删掉,因为凡句在文章中具有衬托警句的功能。
这就是说,陆机在《文赋》中实际上是精审地论述了警句与凡句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文章要“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
所谓“效绩”于“众辞”,讲的是警句对凡句的点化和提升作用,这用明人谭元春的话说,即“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
而另一方面,正如榛梏能使翠鸟托足,文章中凡句之存在,亦能衬得篇中的亮点更加夺目,从而可“济”其“伟”,此谭元春所谓“一篇之朴能养一句之神”也。
而刘勰则没有领会陆机的深意,他在《文心雕龙?
熔裁篇》中对陆机有这样的批评:
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
虽玩其采,不倍领袖。
巧犹难繁,况在乎拙?
而《文赋》以为“榛梏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
他认为,陆机之所以主张勿剪榛桔,乃因为他本人就为文嗦,即所谓“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故其为文,肆笔之后即率尔出手,懒于删芟也。
这显然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理解上的指责。
钱锺书对此深致感慨:
“老于文学如刘勰,则于‘济夫所伟’亦乏会心,只谓作者‘识’庸音之宜‘芟’而‘情’不忍‘芟’。
李善以下醉心于《选》学于此茗芋无知,又不足咎也。
”其实,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单纯的评论家的刘勰和注家的李善不如兼为作家的陆机之处:
陆机之《文赋》,本身就是自己写作的经验的总结,他是从他创作中的实际感受出发来谈剪裁的。
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庸音与警句的辩证关系就有深切的体会。
而刘勰等人则只是从外部简单地看待删削,故对其中的奥妙从未见也。
除此以外,《文心雕龙》中还有一处对《文赋》内容的具体批评,可惜它也和前一个批评一样,不但反映刘勰对文学“亦乏会心”,而且也是李善以下的《选》学者“茗?
J无知”的,本文想重点谈谈这个误批。
《文赋》论文,麓为十体,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
其中对于“说”的文体特点,陆机把它与“奏”相对,作了这样的界定:
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谲诳。
而在刘勰在《文心雕龙?
论说》中,对于“说”的文体特征及发展,也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末了对陆机的界定提出严厉的讦难。
为了分析的方便,姑不避繁冗,把刘勰的有关论述全部引在下面:
说者,悦也。
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
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
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
暨战国争雄,辩士云涌。
纵横参谋,长短角势。
转丸骋其巧辞,飞钳服其精术。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
至汉定秦楚,辩士弥节。
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
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嘘公卿之席。
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洄矣。
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
不专缓颊,亦在刀笔。
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并顺情入机,动言中务。
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力骋而罕遇也。
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
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
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
而陆氏直称:
“说炜烨以谲诳”,何哉?
在这一节被纪昀评为“树义甚伟”(黄叔琳《文心雕龙注》附载纪评)的议论中,刘勰首先考之以字源,取“说”字的“悦”的含义,然后将它定位于臣下对君主“言咨悦怿”的劝谏,并认为这种劝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即不但包括口说,也包括笔奏。
他先举了上古的伊尹、姜尚,战国的纵横家,秦汉之际的郦食其、蒯通,以及汉开国后的贾谊、张释之等人对君主的口头劝说为例,又举了好多谋士对君主的上书:
如范雎的《上秦昭王书》;李斯的《谏逐客书》;邹阳的《上吴王书》和《狱中上梁孝王书》等等。
最后得出一条结论,即“说”之枢要在于“时利而义贞”,亦即利于时势、旨义贞正。
基此,他强烈地攻击陆机关于“说”体“谲诳”的界定,指出:
不论是口谏还是笔奏,“说”所面对的对象都是君主而并非敌人。
既然如此,那么说者心中必当“唯忠与信”,何来“谲诳”――亦即诡诈欺诳之谈呢!
应该说,刘勰从臣下对君主的谏议的角度上来理解“说”,还是符合陆机的原意的。
因为《文赋》所立十体,其分法受《典论?
论文》的“四科八类”的影响,十体之中,每两体联举,使之相邻相对,以突出二者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
譬如诗与赋、碑与诔、铭与箴等皆是也。
奏与说亦然,它原于《典论?
论文》四科的“奏、议”并列,二者在文体上虽有区别,但它们都是面对君王的,故陆机将它们作为一组而联举之。
但如果我们稍微用心地读一下刘勰对“说”的具体论述就会发现,他关于“说”的“不专缓颊,亦在刀笔”的说法,不但与《文赋》的“奏、说”分列相违,而且也与刘勰自己在《文心雕龙》中文体分类相悖:
因为在《文心雕龙》所开列的三十三种文体中已有“奏”之一体,并专立《启奏篇》来探讨;而且,刘勰在该篇中也明确表示“上书为奏”。
而这里他又把巴上书归入“说”中,这岂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
此其一。
随之而来的是:
“说”既然涵括口谏与上书,那么它的意义也就不复是一种特定的文体形式,而是一种宽泛的“劝谏”行为了。
刘勰所谓的“时利而义贞”也好,“唯息与信”也好,都只是对这种劝谏行为所下的结论,而与文体无关。
这也就是说,“说”这个文体概念,在刘勰对陆机的讦难中预先就被偷换掉了。
需要指出,刘勰此处的偷换概念是蓄意的,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论。
另外,刘勰把陆机的“谲诳”直讲成心讲辟邪的欺诈,亦与原文?
e?
r不合。
按陆机《文赋》列举完十体的特征之后,对各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有两句原则性的要求:
“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
”可知他前文有关各体的“平彻闲雅”、“炜烨谲诳”等论述,只及形式风格而未涉内容心术,对各种风格亦一概肯定而并无轩轾。
刘勰以贬抑性的“欺诈”来释“谲诳”,貌似有理而实属歪曲。
那么,陆机的“说炜烨而谲诳”到底指什么呢?
先看“说”。
“说”在《文赋》中既是“文”之十体之一,就决非指行为,而是一种特定的文本形式。
这种文体成熟并兴盛于战国,它之所以叫“说”,首先取的是口说之义,因为这种“说”大抵为士人与谋臣向君主的口头劝谏。
秦汉诸子中,直以“说”名篇的很多,如《韩非子》中有内外《储说》和《说林》,《淮南子》中有《说山训》和《说林训》等等,皆为这种口谏之“说”之荟萃。
最古时臣下对君王的建议,还没有后来上书、奏章之类的书面形式,而只凭口舌。
古传商人有傅说者,为商王武丁之贤相。
其实,傅说之“傅”,就是相、佐之义,当是对他职务的称呼,故傅说之称,正如梓庆、轮扁、工任一类,名字只在后一字。
而再仔细考之,这后一字“说”字也并非他的真正名号,只是他所做的具体工作而已。
换言之,“说”之得名,只取他向商王的口谏。
《尚书?
说命》载,傅说曾以自己的鉴识和口才,折服了商王,于是获得了尊敬。
“傅”作为官职,“说”作为工作,工作的实绩要比官职的虚名更为重要,故傅说之后以“说”为姓(《广韵》:
“说,姓,傅说之后”)。
这就是说,古时之相,其根本职责即在于随时对君主进行口头指导,正如今天的导演和教练。
战国时代,是能说会道的辩士大显身手、争当教练的时代。
当时王纲解纽,群雄共起,天下逐鹿,过去公认的官方意识形态和规则被抛弃,人们只认实力,不读经典,故具有一条善辩的舌头,即可要众誉而得人心。
而那时辩士主要的说服对象就是统治者。
要说服他们,不需要有多高深的思想、多翔实的阐述,重要的是使自己的语言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煽动性。
治国将兵者受了煽动,他当时就能作出决策、付诸事功,从而迅速地支配国家的命运,改变天下的形势。
等到他醒过味来,事情已经办了。
故辩士之论,多非可长久消受的精神肴馔,而只是应用于一时的兴奋剂。
此李善注《文选》所谓“‘说’以感动为先”也。
说者或用譬喻,或举谚语,调动一切手段,以期“动人主之心”。
而这也就造成当时之辩说引人入胜、生动形象、奇诡恣肆的风格。
当然,要想使自己的舌头真正奏效,还要善于抓时机、揣心理、讲究说话技巧。
荀卿之《非相》,韩非之《说难》,还有《鬼谷子》等书中,都有对“说君”之艺术的专门探讨。
上文所引刘勰的论“说”,也重点提到了战国时纵横家凭“三寸之舌”而驰“说”的情况。
不过战国游说者可不止纵横家,儒、法、墨等各家都曾席不暇暖、烟不黔突,忙碌地奔走于各国之间,在统治者的耳边摇唇鼓舌。
这就是说,战国时“说”之应用范围较广。
但与这种广泛的应用相对的,是它在发表形式上的严格规定:
那就是仅止于口头言说;刘勰把秦汉以后臣下上书也归入“说”体,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古所谓“说”的范畴。
刘知?
住妒吠āぱ杂铩吩疲骸罢焦?
虎争,驰‘说’风涌。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俗尚文,时无专对,运筹进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
宰我自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
”近人章太炎亦云:
“‘说’者,古人多为口说,原非命笔之文”;“七国时游说,多取口说,而鲜上书。
上书即‘奏’也”(《国学讲演录?
文学略说》),都讲的是“说”与奏章的区别。
这种口谏的“说”,基于口谈的渠道和实用的要求所形成的生动恣肆、引人入胜等特点,也就是陆机所谓的“炜烨”。
“炜烨”者,光彩鲜明之貌,它指的是文辞的夺目移神。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动形象、吸引眼球。
孙卿在《荀子?
非相》中讲当时辩士的谈说之术,要“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
前句指用譬生动,后句指警策鲜明;《鬼谷子》谈“说”的特点:
“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人于人之心。
”“神而珍”指立言奇特而拔众,“白而分”指论理明白,“人于人之心”,则指引人人胜。
《韩诗外传》托孔子谈“说”,除了强调譬喻、鲜明和奇特,还有一句“欢忻芬芳以送之”。
所谓“欢忻芬芳”者,言其出语悦人也。
所有这些,都可归于陆机所谓的“炜烨”。
当然,“炜烨”不光牵涉到言辞,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要有一种折服人心的力量。
《庄子?
天道》中有一则故事:
齐桓公读书于堂上,堂下的制轮工人指出他所读者“乃古人之糟粕”,桓公日:
“寡人读书,轮人安敢议乎?
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说苑?
善说》载汉武帝对拂逆其意的虞丘寿王亦有此语)这里桓公向工人所逼讨的、而且关乎工人生死的“说”,一般翻成“说法”、“说道”,更陋者则翻成“理由”。
实际上,这里的“说”,用的即是战国时“说”体的本义,意谓工人必须就此立出一“说”,以服我心也。
后来轮扁从容不迫,侃侃道来,他以自己斫轮之事为例,证明凡精微之旨皆不可以喻人。
其见解出人意表,其论证足以服人。
从而充分显示了“说”在内容上的夺志移人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也属于“炜烨”的范畴。
“炜烨”的要求,是口说这―特殊渠道所决定的,但这种口头的“说”,后来也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文本形式。
因为“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口说”欲长远留存,就必须纳入文字的载体。
于是乎,人们对谋臣、辩士的“说”也就有记录、有收集。
《汉志》“纵横家”有《苏子》、《张子》,实际上就是苏秦、张仪的游说纪录。
汉初所出现的《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隋书?
经籍志》),也是谋士的谈话集丛。
当时也有些士人有意把游说要用的材料集中保存起来以备使用,此即韩非的《储说》之所缘起(《韩非子?
内储说》题下注:
“储,聚也,谓聚其所说”);“说”收集多了,于是成为“林”、成为“山”,此即《说林》、《说山》之所得名(《韩非子?
说林》题下注:
“广说其事,其多如林,故日说林”)。
汉刘向所编的《说苑》,是战国前后“说”的总集,其中所搜集的“说”,多来自秦汉前后的子、史。
子书如《孟》、《管》、《庄》、《荀》,史书如《左传》、《国语》、《史记》。
这说明,“说”在战国时就已文本化,并为诸家著述所采用。
但虽然如此,因为它的原始形态毕竟为口说,故基于这种特殊的授受渠道和时代需要所形成的“炜烨”风格,在“说”体文本中亦有鲜明的表现。
另外,为了使自己的谏说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说者往往在谏说中大量引用寓言和故事,这些寓言故事,大率为野史传闻,并无事实根据。
如《韩非子》的《说林》、《说山》和《储说》中,不特“二虱相讼”、“二蛇对话”、“滥竽充数”、“郑人买履”等等纯属寓言,即如所讲的古人的一系列故事和对话,亦为假托。
刘向《说苑》中的“说”也是这样,它们多取君臣对话的形式(也有一些是师生对话,而如果联系秦汉前后的士人争当“帝师”的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
1、世事忙忙如水流,休将名利挂心头。
粗茶淡饭随缘过,富贵荣华莫强求。
2、“我欲”是贫穷的标志。
事能常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
3、人生至恶是善谈人过;人生至愚恶闻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