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docx
《病毒.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病毒.docx(15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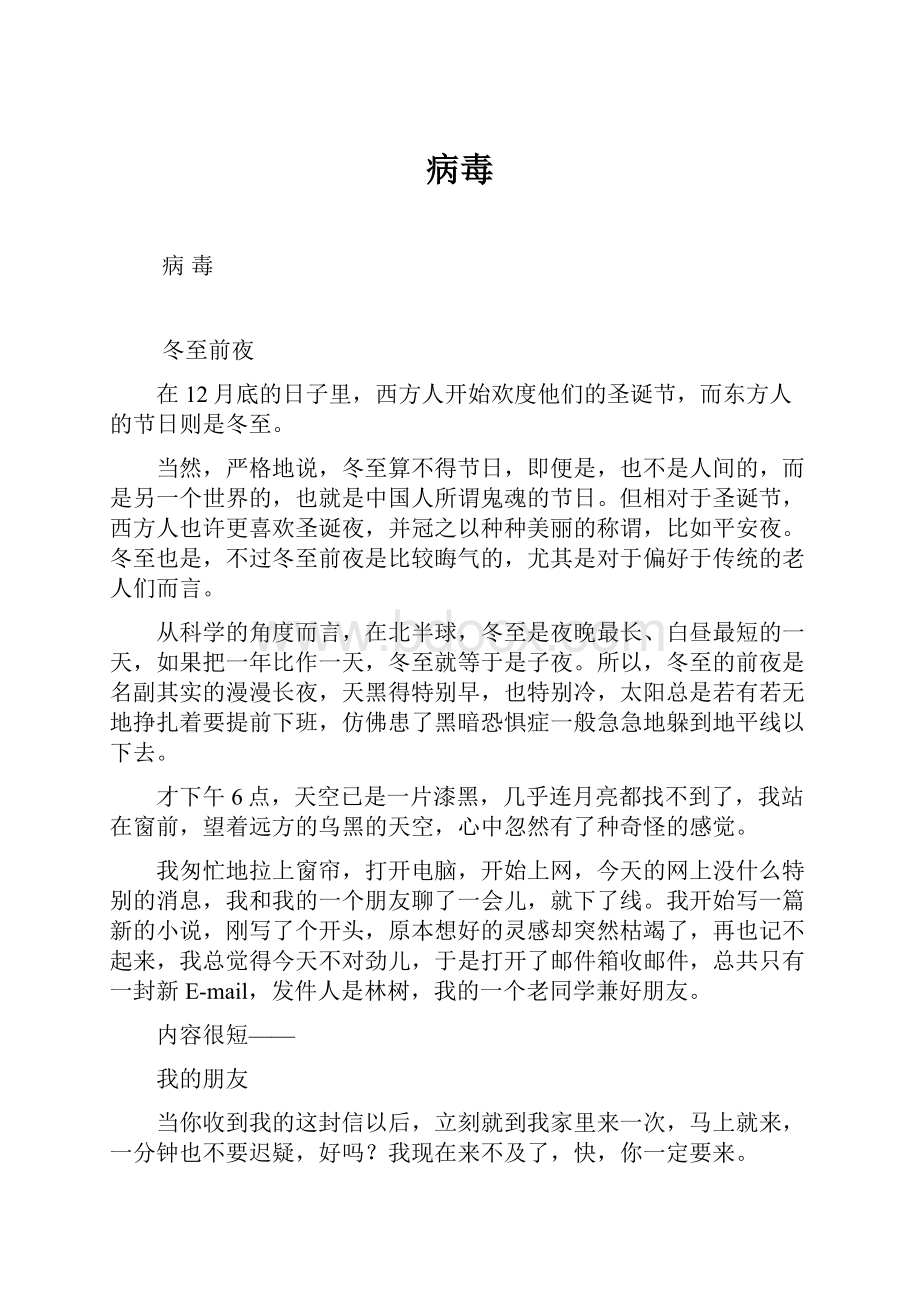
病毒
病毒
冬至前夜
在12月底的日子里,西方人开始欢度他们的圣诞节,而东方人的节日则是冬至。
当然,严格地说,冬至算不得节日,即便是,也不是人间的,而是另一个世界的,也就是中国人所谓鬼魂的节日。
但相对于圣诞节,西方人也许更喜欢圣诞夜,并冠之以种种美丽的称谓,比如平安夜。
冬至也是,不过冬至前夜是比较晦气的,尤其是对于偏好于传统的老人们而言。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在北半球,冬至是夜晚最长、白昼最短的一天,如果把一年比作一天,冬至就等于是子夜。
所以,冬至的前夜是名副其实的漫漫长夜,天黑得特别早,也特别冷,太阳总是若有若无地挣扎着要提前下班,仿佛患了黑暗恐惧症一般急急地躲到地平线以下去。
才下午6点,天空已是一片漆黑,几乎连月亮都找不到了,我站在窗前,望着远方的乌黑的天空,心中忽然有了种奇怪的感觉。
我匆忙地拉上窗帘,打开电脑,开始上网,今天的网上没什么特别的消息,我和我的一个朋友聊了一会儿,就下了线。
我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刚写了个开头,原本想好的灵感却突然枯竭了,再也记不起来,我总觉得今天不对劲儿,于是打开了邮件箱收邮件,总共只有一封新E-mail,发件人是林树,我的一个老同学兼好朋友。
内容很短——
我的朋友
当你收到我的这封信以后,立刻就到我家里来一次,马上就来,一分钟也不要迟疑,好吗?
我现在来不及了,快,你一定要来。
林树
他什么意思?
让我晚上到他那里去,这么冷的天,这么远的路,他那儿离我家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呢,这不要了我的命。
我看了看他发出的时间,距现在只有半个小时。
而现在已经快深夜11点了,难道真有这么重要的事?
会不会开我玩笑?
不过林树不是这种人,他这种比较严肃的人是不太会跟别人开玩笑的,也许真的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
我在房间里徘徊了一圈,然后看了看漆黑的窗外,最后还是决定去一次。
出了门,发现地上有好几圈黄色的灰烬,不知是谁家烧过的锡箔,我特意绕道而行。
走到马路上,才发觉天气要比我想象的还要冷,风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在半空中打着唿哨。
商店都关门了,开着的便利店也是了无生气的样子,人行道上几乎没有一个行人,就连马路上的汽车也非常少,我等出租车等了很久,清楚地数着在空旷的黑夜里回响的自己的脚步声。
终于叫到了一辆出租车。
驾驶员30多岁,挺健谈的:
“先生,今天晚上你还出去啊。
”
“有点急事。
”
“明天是冬至啊。
”
“呵呵,我不信这个的。
”
“我也不信,可是今晚这日子最好还是待在家里。
今天做完了你这笔生意,我马上就回家,每年的今晚我都是提前回家的。
”
“为什么?
”
“鬼也要叫出租车的嘛。
因为今晚和明天是鬼放假的日子。
没吓着你吧,呵呵,开玩笑的,别害怕。
”
车上了高架,我看着车窗外我们的城市,桑塔纳飞驰,两边的高层建筑向后奔跑,我如同在树林中穿行。
迷蒙的黑夜里,从无数窗户中闪烁出的灯光都有些晦暗,就连霓虹灯也仿佛卸了妆的女人一样苍白。
不知怎么,我心神不安。
车子已经开出了内环线。
林树的家在徐汇区南面靠近莘庄的一个偏僻的居民区,七楼,一百多个平方,离地铁也很远,上个月林树说他的父母到澳大利亚探亲去了,要在那儿迎接新世纪,所以现在他一个人住。
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要有点心理素质的。
我看了看四周,现在车子开在一条小马路上,虽然林树的家我常去,但从没来过这条马路,黑夜里看不清两边的路牌,只能看到远处黑黑的房子,要么就是大片大片的荒地。
车子打着大光灯,照亮了正前方,光亮的柏油路面发出刺目的反光。
而四周是一片黑暗,如同冬夜里的大海,我们的车就似大海里一叶点着灯的扁舟,行驶在迷途的航线上。
我索性闭上了眼睛,迷迷糊糊地任车子载着我在黑夜里漫游。
在半梦半醒中,车子忽然停了下来,我睁开眼睛,看到车外一栋栋黑黑的居民楼,的确到了。
我下了车,司机只收了我个整数,零头不要了。
然后他迅速掉转车头开走了。
我懵头懵脑地向前走着,不住地哆嗦,小区的弄堂里不见一个人,两边楼房里只有零星的窗户还有光线透出,可能是几个半夜上网的人。
我不断呼出的热气,像一团清烟似的向天上升去,我看了看天空,星星和月亮都无影无踪,只有几朵乌黑的云飘浮着。
风越来越大,从高空中向下猛扑而来,卷起一些细小的碎屑,在空中飞舞起来。
哪家的塑料雨棚没有安装好,在大风中危险地颤抖着,摇摇欲坠,发出巨大的声音,就像是一只拳头砸在了塑料上。
忽然我好像听到了前面有什么声音,“嘭——”那声音很闷,像是哪家的花盆敲碎了。
我加快了脚步,在林树家那栋房子下面的地上,我发现有一个人倒在地上。
我屏着呼吸靠近了几步,在楼前的一盏昏暗的路灯下,看清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的朋友林树的脸。
一滩暗红色的血正迅速地从他的后脑勺下向外涌出。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立刻抬腕看了看表——子夜12点整。
冬至到了。
冬至
林树的脸是那么清晰,白白的,一丝痛苦也没有,就像是解脱了什么。
当他想要张开嘴说话的时候,却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我对他大喊:
“你快说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我从梦中醒来了。
现在已经是中午。
我躺在床上,昨夜发生的事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我想起来了,林树发给我一份E-mail要我到他家去,当我在子夜12点赶到他家楼下的时候,他却跳楼自杀了。
我见状立刻报警,在公安局折腾了半夜,到清晨6点才回到家,然后蒙头就睡,直到现在。
我起来吃了点东西,电话铃响了,是我的同事陆白打来的,他请我平安夜晚上和他们一起出去玩,他早就说过了,但我一直没确定,因为圣诞对我的意义不大,但现在林树出了事,我的心情很紧张,于是马上就在电话里同意了。
我出门坐上一辆中巴去了嘉定乡下,一个小时以后,来到一座公墓前。
今天是冬至了,这里的人很多,上午的人应该更多。
我在门口买了一束花走进墓园。
虽然天很冷,阳光却不错,很温和,洒在墓园四周的田野上,周围有许多大树和芦苇,一些鸟在欢快地鸣叫着。
我走进最里面的一排墓碑,在一个名字前停了下来,墓碑上镶嵌着一张椭圆形的照片,一个18岁的女孩正在照片里微笑着。
我轻轻地把花放在了墓碑前,然后看着照片发了好一会儿呆。
忽然一声奇怪的鸟鸣把我从沉思里拉了出来,抬头看了看天,那只鸟扑扇着翅膀飞走了,只有冬至的阳光纠缠着我的瞳孔。
周围的一些幕碑前,人们按照传统的方式给死去的长辈磕头,也许这是他们一年中仅有的几次弯下尊贵的膝盖,另一次该是清明。
随着祭奠先人的古老仪式,四处升起许多烧冥币和锡箔的烟,那些清烟袅袅而起,如丝如缕,在空中铺展开来,仿佛已在另一个世界。
这亡魂聚集的场所,今天坟墓里的人终于放假了,我又想起昨晚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话,不知怎么,喉咙口突然痒痒的。
晚上回到家,我没有开电脑,把灯关了,一片漆黑中,我独自看着窗外冬至的夜色。
整个晚上我一直沉浸在对林树的回忆中,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选择自杀。
他这个人性格是很温和的,但也不是那种特别内向的人,家庭还算和睦,条件也不错。
他是个大网虫,一直梦想进网络公司工作,年初他好几次参加几大网站的招聘,但都没有成功,在两天前,他终于被一家财力雄厚的大网站聘用了,要知道,在现在网站纷纷裁员的时候,学历一般的林树还能应聘成功简直是个奇迹。
在他收到聘用通知书的当天晚上,就立刻请我在外面吃了一顿火锅,那时候他眉飞色舞,春风得意,谁知道第二天居然就跳楼了。
实在没理由啊。
我胡思乱想了很久,慢慢地陷进沙发中,忽然我好像看到了前面的黑暗中有一个人影,模模糊糊的,那人影靠近了我,一点光线不知从哪里亮了起来,照亮了那张脸——
“香香。
”我轻轻地叫了她一声。
那张脸平静地看着我,没有回答,然后又悄悄地隐藏回黑暗中。
我急忙从沙发里跳了起来,打开灯,房间里却只有我一个人,原来刚才我睡着了,也许做了一个梦。
现在我的精神太脆弱了,已经濒临崩溃。
我倒头就睡。
上了床却始终睡不着,直到我听见一种熟悉的声音,或远或近地飘荡着,钻到了我的心脏中。
平安夜
“多美的夜色啊。
”陆白的女朋友黄韵倚着浦东滨江大道的栏杆,她染红了的头发在风中飞扬着。
又是一个圣诞夜。
我们总共有七八个人,虽然说好了平摊,但这回陆白带着女朋友,坚持要自己请客。
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在陆家嘴,尽情地吃喝玩乐,只有我的心情比较沉重,几乎没说什么话。
陆白今年28岁,除了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以外,各方面的条件一般,但他的女朋友却非常漂亮,是个难得的美人。
他们是网上认识的,也该算是网恋的一大成果,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打得火热,但后来黄韵就对陆白不太满意了,可能是嫌陆白的相貌一般吧,看来网恋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的。
陆白常向我诉苦,说女朋友对他越来越冷淡,上个月居然提出要分手,他很痛苦,甚至到处求教让女孩子回心转意的秘诀。
在滨江大道边,我看着对岸的外滩灯火,还有身后的东方明珠,20世纪最后的一个圣诞夜,一路走来都是花花世界,我的心情却依然抑郁。
陆白忽然搂着女朋友大声地向我们说:
“我和黄韵决定结婚了,明年的春节请大家吃我们的喜酒。
”
这让我们吃了一惊,原来以为他们两个马上要分手的,没想到现在居然要结婚,太突然了。
我仔细地看着他的眼神,却什么都没看出来。
他满脸笑容,却有些僵硬,他一定是太高兴了,没错,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任何人遇到这种幸运的事都会这样的。
我看了看时间,快12点了,把这个时间让给他们的两人世界吧,于是我向陆白道别了,其他人也纷纷识趣地走了,只留下他们两个在黄浦江堤边卿卿我我。
我望了望四周,还有许多一对一对地在寒风中依偎着。
我竖着领子,沿着黄浦江走了几十步,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声。
那又高又尖的声音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划过平安夜的空气,我脆弱的心脏仿佛有瞬间被它撕裂的感觉。
我捂住胸口,自己的心简直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这时我听到许多人奔跑的声音,而女人尖厉骇人的叫声还在继续。
我回过头去,看到发出尖叫的正是陆白的女朋友黄韵。
我愣了一下,随即冲了过去,挤开人群,看到人们都在往黄浦江里张望。
我也往江里看了看,黑漆漆的江面卷起一阵寒风,一个人影在江水里扑腾挣扎着,升上一些微弱的热气,然后渐渐地消失在冰凉刺骨的滚滚波涛中。
“陆白!
”黄韵继续向黄浦江里叫喊着,“他跳到黄浦江里去了,快——快救救他——”她突然抓住了我的衣服,“救救他,快。
”
我也麻木了,我若是会游泳,说不定真的会跳下黄浦江救人的,但我不会水,一点都不会,跳下去等于自杀。
周围的人也在频频地摇头,一片叹息声,就是没有一个人敢下水。
这时,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也过来了,警察看了看黄浦江,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说自己也不会游泳,然后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话。
很快,一艘小艇驶到了江面上,他们好像不是来救人的,而是来打捞的。
我回过头去,不敢再向江中张望,浑身发着抖,抱着自己的肩膀。
黄韵的呼救声也停息了下来,她不再说话,一动不动地站立在江风中,像一尊美丽的雕塑。
一个小时以后,陆白终于被打捞上来了,惨不忍睹,我无法描述在冰冷的江水中浸泡过的他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他被装进了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拉上拉链,像一具塑料棺材,送上了一辆运尸车。
一个警察在询问着黄韵。
她断断续续地回答:
“忽然,他忽然变得神情凝重起来——像是看到了什么东西。
”
“什么东西?
”警察催促着她。
“不知道,他的眼神很奇怪,看着我后面,接着又是我左面,嗯……又移到了右面,飘忽不定,时远时近。
我看了看四周,什么东西都没有,最后,最后他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了,眼神似乎也消失了,转身翻过栏杆,就跳进了黄浦江里……”她不能再说了。
我不明白她说的话,警察也不明白,我看了看四周,除了人以外什么都没有。
那究竟是什么?
圣诞
我约了这个女孩——黄韵,我知道这是不合时宜的,但必须要这样做,以解开我心中的团团疑问。
在一个风格简洁的咖啡馆里,我独自等了很久,当我认定她不可能来,而起身要走时,她却真的来了。
一身白衣,染成红色的头发也恢复了黑色,在黄昏中远看,她就好像古时候为丈夫守丧的素衣女子。
坐在我面前,我才发现她憔悴了许多,没有化妆,素面朝天,却更有了一番风味。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她的语调很平静。
“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
“你们大概都在猜测为什么陆白会自杀吧,我也不知道,他的确没有理由去死,而且他的精神一直也很正常。
”
“正因为无缘无故,所以才可怕。
”我轻轻抿了一口咖啡,都快凉了,接着说,“而且偏偏是在宣布你们两人准备结婚的日子里,更重要的是在平安夜。
”
“你们应该知道,在上个月,我明确地告诉他我们分手了。
他很伤心,但这不能改变我的决定。
但在几天前,他发给我一个E-mail,告诉我他上个星期专门去了次普陀山,为我的妈妈上香祈求平安。
我妈妈上个月被诊断出了恶性肿瘤,就在那天晚上动手术,手术难度非常大,成功率很低,即使成功也很难完全痊愈。
他知道我妈妈是非常迷信这个的,她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去普陀山进香。
就在我收到这封E-mail的晚上,妈妈的手术成功了,而且一点后遗症都没留下来,主刀的医生也非常惊讶,连称是奇迹。
我立刻对陆白改变了看法,被他的诚意深深感动了,所以……”
“以身相许?
对不起。
”我冒昧地接话了,因为实在没想到还有这种事,陆白真的去过普陀山吗?
我不知道。
“可以这么说,我很感激他,其实我也不相信这种东西的,但至少可以知道他是真心的。
”
“有些不可思议。
”
“我很傻吧,算了,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现在想起来,我做出和他结婚的决定实在太轻率了,仅仅因为一件纯属巧合的事就决定婚姻,我实在难以理解当时的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突然变得那么迷信。
也许我不该说这些话,这是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亵渎,我对不起陆白,其实,我并不爱他,当时只是头脑发热而已,这就是我一时冲动要和他结婚的原因。
你会认为我是一个轻率、自私、麻木不仁的女人吗?
是啊,未婚夫尸骨未寒就和他生前的同事一起喝咖啡。
”她苦笑了一声,“但愿陆白能原谅我。
”
我的脸突然红了。
我知道她最后几句话的意思:
“对不起,你别误会。
”接着,我把冬至前夜我所遇到的那件可怕的事情告诉了她。
她平静地听完了我的叙述,淡淡地说:
“我认识一个心理医生,他开着一家心理诊所,很不错的,你可以去那里调整自己的心理,你需要这个,知道吗?
”她递给我一张那个心理医生的工作名片。
“忘记我吧,再见。
”然后她走出了咖啡馆。
她的背影消失在了黄昏的暮色中,我仔细地想着她的最后一句话,“忘记我吧”。
什么意思?
我又看了看周围,全是一对对的男女。
我独自坐了好一会儿,直到天色全都黑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西南角有着无数幽静的小马路,被梧桐覆盖着,夏天里是一片葱郁,树影婆娑,冬天的风情却像是在某个欧陆的城市里。
在这样一条马路里,我按照名片上心理诊所的地址拐进了一条宽阔的小巷,推开一栋小洋楼的门,门上挂着牌子——莫医生心理诊所。
那是种外面看上去很旧很老、其实内部装修得很新的房子,门厅不大,在楼梯拐角下有一张办公桌,一个20出头的女孩正在接电话。
她的语调轻快,好像在说着什么业务方面的事情,她向我瞄了一眼,给了我一个稍候的眼神。
她的脸让我想起一个人,我非常惊讶,瞬间陷入了冥想之中。
她是谁?
“欢迎你来到我们诊所。
”她的话打断了我的沉思,接着她说出了我的名字。
“怎么,你知道我的名字?
”
“有人通知过我们你要来的,请上楼,医生在等着你。
”
我在楼梯上又向下看了一眼,她正在向我自然地微笑着,我也还给她一个微笑,但我想当时自己的微笑一定显得非常僵硬,因为看到她,我的心头已升起了一团迷雾。
推开楼上的一间房门,一个30多岁的男人正坐在宽大的转椅上。
他的眉毛很浓,浓得有些夸张,虽然胡子剃得很干净,但依然可以看出他青色的两腮,与我的想象有一些距离。
“请坐。
”他自我介绍说,“我姓莫,你就叫我莫医生好了。
对了,你有我的名片的。
”
我坐了下来说:
“是黄韵告诉你我要来的?
”
“是,你是她的好朋友吗?
”
“不能算好朋友。
”
“没关系,慢慢就会变成好朋友的。
”他说这话时的神情变得很暧昧,“我听说她的男朋友跳黄浦江自杀死了,而且他们已经决定结婚了,太遗憾了。
”
“那晚我也在场,的确很奇怪。
”
“哦,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是指心理方面。
”
“你也是黄韵的好朋友吗?
”
“她一直有精神衰弱的毛病,所以常到我这来看病。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是来看病的,是不是?
”
“我没有心理方面的疾病,只是觉得最近心理上受的刺激太大了。
”我竭力要辩解,不想让别人把我看成是精神病。
“听我说,每个人都有病,有病是正常的,没有病才是不正常的。
只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病而已,生理的或是心理的。
”莫医生说完以后走到窗口把窗帘拉了起来,那是种非常少见的黑色的大窗帘,很厚实,几乎把光线全遮住了,整个房间笼罩在幽暗之中。
“你要干什么?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他不回答,回到我面前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截白蜡烛,然后点燃了蜡烛,在一点烛光之下,周围似乎更加黑暗了。
渐渐地,除了烛光以外,我什么都看不到了,眼前仿佛被蒙上了一块黑布,布幔的中心画着一块小小的白点。
这个白点在慢慢地移动着,忽左忽右,像是风,又像是一个上下左右移动着的人的眼睛,是的,我瞬间觉得这像一只眼睛,只有一只,不是一双。
我仿佛能从其中看出它长长的睫毛,还有黑色的眼球,明亮的眸子,最中间,是一个黑洞般的瞳孔。
这瞳孔深邃幽远,像个无底洞,深深的水井,没人知道它的尽头,也许通向我的心灵。
“你看到黑洞了吗?
”一个声音从我耳边响起,“黑洞——物理学意义上宇宙中的黑洞是吸收一切物质的,黑洞附近的空间和时间都是扭曲的,甚至可以说是颠倒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过去发生的事。
所以,所有的超自然现象都可以在黑洞中得到解释。
”
我说不清自己现在是闭着眼睛还是睁着,只觉得现在自己像一个盲人,什么都看不到,世界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只有那一束以光的形式出现的眼睛。
那是谁的眼睛,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
我见过这只眼睛吗?
这只眼睛已经牢牢地印在了我心里。
我还看到了这只眼睛在变化,充满了一种忧伤的眼神,它注视着我,我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独立的人,他(她)在用眼睛跟我说话,我觉得我们之间可以达成某种交流,在这个意义上,眼睛就等同于嘴巴,甚至可以说,眼睛就是人的全部。
我快被这只眼睛征服了。
我已经开始丧失了“我”的意识,我已经没有“我”了,我会和这只眼睛合而为一。
我就是它(他、她),它(他、她)就是我。
不!
我不愿意。
我猛然睁大了眼睛,大喊了一声:
“让我走。
”
忽然,那只眼睛消失了,只剩下一支点燃的蜡烛,还有拿着蜡烛的一个人影。
我摇了摇自己的头,辨清了方向,冲到窗前,拉开了那厚重的窗帘。
阳光像决堤的江水一样冲进了房间,我沐浴在阳光里喘息着,像一只野兽,我这才发现自己流了许多汗。
“你不该打断我对你的治疗。
”莫医生平静地说,但他的语气好像没有责怪我的意思。
“对不起,我承受不住你的这种治疗。
我太脆弱了。
”
“不,你是过于坚强了。
”
“我能走了吗?
付多少钱?
”我急于摆脱这家伙。
“你当然可以走,我这里一切都是自愿的。
至于钱,治疗没有结束我不收钱。
”
我“噔、噔、噔”地冲下楼梯。
楼下那个接待的女孩不见了,她的那张熟悉的脸又浮现在我心里,她去哪儿了?
我又回到了楼上,推开门,却看到那女孩正在和莫医生说话。
“还有什么事?
”医生微笑着问我。
“没,没什么。
”我木讷地回答。
“你是在找她吧。
”
我尴尬地笑了笑。
“ROSE,你还是送送这位先生吧。
”
原来她叫ROSE。
她一言不发,却面带微笑地送我下了楼,走到门外的小巷中,这时她才轻轻地说:
“你真行。
”
“为什么这么说?
”
“不为什么?
”她神秘兮兮地说。
“难道刚才他给我治疗的时候你也在房间里。
”
她抿着嘴却不回答,做了一个奇怪的眼神,那眼神刹那间让我想到了刚才在“治疗”的时候看到的那只神奇的眼睛。
难道那不是烛火,而确确实实就是她的眼睛吗?
“别胡思乱想了,下次再来吧,我等着你。
”
我向她道了别,走出几步以后,回头再看,她却已经不见了。
那只眼睛——是她的左眼还是右眼?
或者都不是?
我突然仿佛看到了我自己的眼睛。
元旦
今天是21世纪的第一天,当许多人在高楼大厦顶上或者是郊外海边顶着寒风迎接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时候,我正在床上做梦。
我这个人常常做梦,尤其是在清晨即将醒来之前。
说来不可思议,有时候我会在梦中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从而甚至会自己导演自己的梦,像指挥一部电影一样,把梦朝着自己想象的那个方向发展。
而梦自身却有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来自我意识之外的地方,常常使我在梦中遭遇意料不到的事,从而搅了计划中的好梦。
我梦见了那束烛光,烛光变成一只眼睛,飘忽不定,让我突然悟出了什么。
这回我终于战胜了意识外的自己,把自己从梦里拉了出来,我使自己醒了。
我仔细地回味着梦中的眼睛,平安夜的晚上,陆白自杀以后,警察在盘问黄韵的时候,我听得很清楚,她说陆白在跳江前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其实什么都没有,而陆白的视线却忽左忽右地飘移着,那么他看到的那个东西(假定他的确看到了什么东西)也是和我昨天在心理诊所看到的烛光(眼睛)一样是飘忽不定的。
就像风,我们虽然看不到风,但风卷起的东西却能让我们看到风的轨迹,也许这就是原理,陆白看到的东西可能真的存在,只是我们无法看到罢了。
吃完早饭我匆匆出门,才早上7点多,元旦清晨的马路上非常冷清,没什么人,我下到了地铁站。
赶到站台,一班地铁刚刚开走,四周只有五六个人,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对面的广告。
一个男人走到我旁边坐下,他大概40出头,人很高,仪表堂堂,穿一件风大衣,里面是黑色的西装,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全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也许是个高级白领,今天还上班吗?
他面无表情地坐着,直视着前方。
耳边响起了地铁过来的声音。
那男人忽然抬起了头看着天花板,然后把脸朝向了下边,接着转到我的方向,几乎与我面对着面,我可以看清他的眼睛,他的眼神似乎是模糊的,他在看什么?
我回头看看四周,没有什么,后面只有自动扶梯。
我再回过头来,却看到他站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径直向前面走去。
地铁即将进站了。
“危险!
”我站了起来。
他无动于衷,竟然真的跳下了站台。
列车进站了。
紧急制动来不及了。
一阵巨大的声响刺耳地响起,我仿佛听到了人的骨头被轧碎的声音。
地铁以其巨大的惯性,碾过了这段轨道,最后几乎和往常一样地停了下来。
在这瞬间我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好像被列车碾死的人就是我。
我抬起头,什么都看不见,我用力地抹了抹自己的眼睛,我的眼睛没问题。
他看见了什么?
一月五日
我去找叶萧。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叶萧了,他和我是远房的亲戚,我现在都没搞清楚我们这个大家族里名目繁多的亲属称呼,所以我还是习惯直呼他的名字。
他是知青子女,小时候寄居在我家里,一块儿玩大的,后来他上了北京的公安大学,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只偶尔通通电话罢了,据说这是因为他受到了某些特殊的技术训练,所以学习期间是与外界隔离的。
昨天我见到了妈妈,她告诉我叶萧已经在几个月前回到了上海,在市公安局信息中心工作。
他现在和我一样,一个人居住,他租的房子不大,但很舒适,房间里最显目的就是一台电脑。
他身体瘦长,浓浓的眉毛,眼神咄咄逼人。
但现在他有些局促不安,给我倒了些茶叶,我很奇怪,他知道我是从不喝茶叶水的。
是的,叶萧的确变了许多,他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一点都不像小时候了,那时候他非常好动,总是做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常常在半夜里装鬼吓唬别人。
“你怎么了?
”我轻轻地问他。
“没怎么,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
于是,我把最近我遭遇的所有的怪事全说给了他听。
他紧锁起了眉头,然后轻描淡写地说:
“没事的,你别管了,忘了这些事吧。
”
“不,我无法忘掉,我的精神快承受不住了。
”
“真的想知道得更多?
”叶萧问我。
“求你了。
我们从小一块儿玩大的,我从没求过你的。
”
他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轻叹了一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了张软盘,塞进了他的电脑:
“算是我违反纪律了。
”他打开了A盘里的文件,出现了一排文字和图片——
周子文,男,2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