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声慢》的外部解读和内部解读.docx
《《声声慢》的外部解读和内部解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声声慢》的外部解读和内部解读.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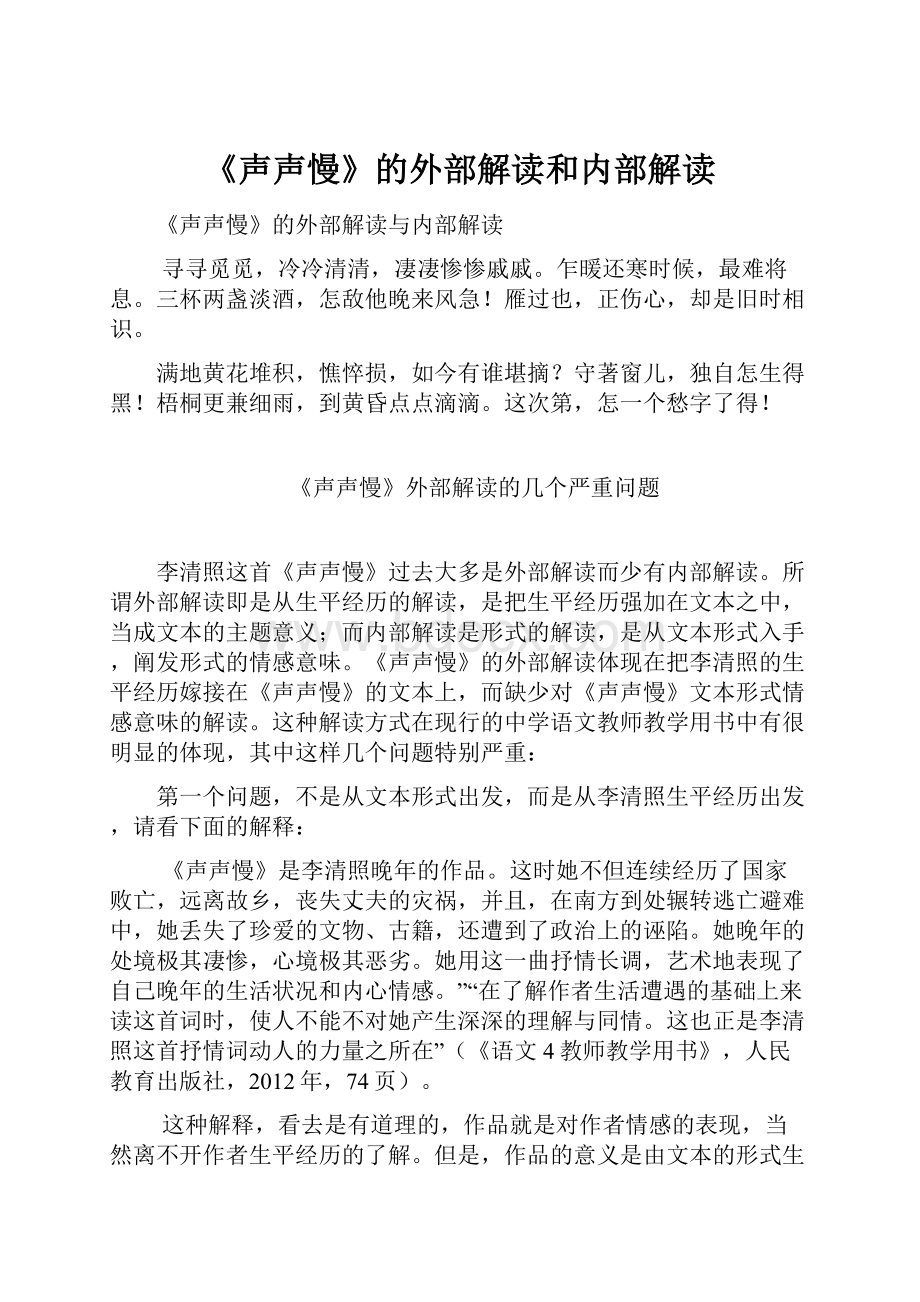
《声声慢》的外部解读和内部解读
《声声慢》的外部解读与内部解读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声声慢》外部解读的几个严重问题
李清照这首《声声慢》过去大多是外部解读而少有内部解读。
所谓外部解读即是从生平经历的解读,是把生平经历强加在文本之中,当成文本的主题意义;而内部解读是形式的解读,是从文本形式入手,阐发形式的情感意味。
《声声慢》的外部解读体现在把李清照的生平经历嫁接在《声声慢》的文本上,而缺少对《声声慢》文本形式情感意味的解读。
这种解读方式在现行的中学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中有很明显的体现,其中这样几个问题特别严重:
第一个问题,不是从文本形式出发,而是从李清照生平经历出发,请看下面的解释:
《声声慢》是李清照晚年的作品。
这时她不但连续经历了国家败亡,远离故乡,丧失丈夫的灾祸,并且,在南方到处辗转逃亡避难中,她丢失了珍爱的文物、古籍,还遭到了政治上的诬陷。
她晚年的处境极其凄惨,心境极其恶劣。
她用这一曲抒情长调,艺术地表现了自己晚年的生活状况和内心情感。
”“在了解作者生活遭遇的基础上来读这首词时,使人不能不对她产生深深的理解与同情。
这也正是李清照这首抒情词动人的力量之所在”(《语文4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74页)。
这种解释,看去是有道理的,作品就是对作者情感的表现,当然离不开作者生平经历的了解。
但是,作品的意义是由文本的形式生成的,因而,解读作品唯一的途径就是从文本出发,对文本形式的意义进行解读,而不是从作者的生平经历出发,把生平经历嫁接在文本上,当成文本的意义。
外部解读的嫁接是这样形成的:
把文本形式靠向作者生平经历进行解释,其结果是,把作者生平经历的意义当成了文本的意义,舍弃了文本形式的本来意义。
比如说“正在她凄苦无奈时,又看到了空中飞过的大雁,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旧时相识。
作者想到大雁能够按时南来北往,而自己却漂流困顿,寄寓异乡,这正是她伤心的原因。
词的上片从秋天里气候的多变,酒难御寒和北雁南飞等几个角度,写自己滞留南方的孤独生活和悲苦心情”(《语文4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74页)。
而有些解读这正是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把李清照的愁说成了失国之愁、失家之愁和失夫之愁。
而这种愁的解释是与《声声慢》形式相距甚远的解读。
生平经历为什么不能代替对文本形式的解读呢?
因为文本的形式意义不等于作者的生平经历。
文本的意义只能从形式解读出来;而在形式之外做的任何解释都是对形式意义的强加。
李清照的生平经历,即国愁、家愁和情愁等只能为李清照提供创作的素材、材料,而不能提供意义;意义是在李清照创造的形式中产生出来的,意义蕴含在李清照创造的意象和整体结构形式中。
也就是说,《声声慢》的意义只能是来自《声声慢》的形式,而不是来自李清照的生活经历(题材)。
因而,我们解读《声声慢》包括其他的作品,就只能根据《声声慢》创造的形式,而不能根据诗人比如李清照的生平经历。
艺术符号理论家苏珊·朗格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
“谁要是在读诗的时候把它当做一种心理学案卷去读,并时时地联系到作者的生平和写作背景,并以此为根据掺杂更多的个人联想,谁就是在粗暴地对诗进行践踏;因为这无疑于是强行从诗句中挤出的陈述,无疑是将诗的意义任意扩大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
这样一种作法只有对诗产生致命的后果,使它听上去毫无真实之感或令人啼笑皆非”(《艺术问题》地147页)。
朗格认为诗的意义来自于诗的幻象和意象:
在解读诗作的时候,进一步考察其人的生平及品格,或者注明诗作者成诗的环境,“对于形成那种幻象毫无裨益。
这类补充只会以不相干的信息将描述生活的意象弄得混乱不堪。
——它们之所以不相干,是因为它们并非由幻象赖以写成的有机原则喷涌而来。
这种原则是说:
情节中的每一因素也就是情节中的情感表现,因此,诗人是以心理方式编织事件,而不是把它当作一段客观的历史”(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47页)。
我们中学语文教学教师用书所出现的问题恰恰也就在这里,不是根据文本幻象——意象解读其意义,而是根据作者生平经历阐释主题。
第二个问题,把诗人对情感象征的意象当成了诗人对某些事实的陈述,从而毁灭了诗的丰富意义。
诗词表现的意象是对作者体验到和理解到的情感的象征,是情感表现的艺术符号,或者说表现性形式,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一切,都是主观现实的客观化,内部心灵的对象化,难以言说情感的符号化。
它当然与诗人的所经历的生活经历有关系,但是,它终究不是对生活经历的再现和复写,而是对生活经历产生情感的形式表现。
形式表现是意象对情感的隐喻或象征,是整体结构对隐秘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对诗人经历生活事件的陈述。
形式哲学家卡希尔曾经特别肯定瓦尔堡古代造型形式对后世的持续影响,“他并且指出了,古人在碰到某一些典型的和一再重现的情况时必定创造了某一些特定的简洁有力的表达方式。
这些表达方式不仅把某一些发自内心的激荡、张力与悬解方法紧紧地捕捉下来,更有甚者,这些内心的激荡、张力和悬解方法,其实是必须顺着这些表达方式才会走上轨道的。
每当一种相同的感触在激荡着的时候,艺术就这一种感受所创造出的图像或造型便马上会活现起来”(恩斯特·卡西尔:
《人文科学的逻辑五项研究》,关子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66—167页)。
内心激荡即内心情感是需要艺术形式来表达的,这种艺术形式或者是诗人的独自创造,或者是对传统形式的借用,但绝不会是对实际生活的模写。
如果我们按图索骥,把诗人对内心情感表现的艺术形式等作为诗人陈述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毁灭了艺术形式及其诗意。
下面的这段解释集中地表现出来这个问题:
“在词的下片又进一步推进,更具体地写自己的处境和心情。
黄花满地,当初盛开时可以插在头上,而如今花已枯萎,再也无人摘取。
这是明写花,而暗喻岁月流逝,人已衰老、憔悴!
最后,又从时间和天气上来写:
白日漫长,她独自一人要苦熬到天黑,但是带来黄昏时候,又有秋雨点滴作响,这种景象,这时的情绪,哪里是一个简单的“愁”字所能概括得尽的!
”(《语文4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74页)。
《声声慢》所表现的意象是李清照心灵世界的象征,是对她体验到和理解到的情感的造型,各种意象是对她内心难以言说孤独的强烈化、重复化的表现,而整体结构则是对她丧失生命意义的空空落落、生命孤独之苦不可解脱的表现形式。
意象和结构形式意义的这种解说可能还是不深刻不尽如人意的,但是,我们必须朝着这方面解读,即解释意象和结构形式本身的意义,而不是把意象的意义解释成生活事件。
当成生活事件的解释带来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对整首词形式结构的忽略或者无能为力。
把诗人情感的形式解说成诗人的生活事件,由来已久。
比如对李清照写的是春天还是秋天季节的争论,对写的是一天还是一个黄昏的争论,对“晚”来风急改成“晓”来风急的争论等。
把诗人表现情感的意象当成客观物象和生活事件来解释,这种解读是对文本形式的严重忽略和歪曲,这种严重的问题在《中学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中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在几乎所有的诗词的解读中都或多或少地犯有这个毛病。
比如《赤壁赋》、《再别康桥》、《雨霖铃》、《登高》等等。
有人恐怕用讲深了高中生接受不了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是,这不是一个深浅的问题,而是一个对错的问题。
这种解读是以对诗歌形式理解和对诗人怎样创作诗歌理解错误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一个文本一个文本错误的解读就交给了学生错误的文学观念和错误的欣赏方法。
外部解读的第三个问题,不是从整体结构形式上解读文本的意义,而是一句一句的解释的累加。
一个文本的意义是由整体决定的,是整体赋予了单个部分比如诗句的意义,因而,解读文本必须从整体出发、把握整体形式的意义、在整体形式意义的基础上解读各个部分,而不是相反,一句一句相加的解释,更不是翻译性的进行解释。
《声声慢》的解释大多是一句一句相加的解释,以为这样解释完了最后一句就解释完了整首词。
但是这种解释恰恰忽略了它最重要的甚至是灵魂性的内容。
一首诗词或一部其他作品,是作者一部分一部分甚至一句一句写出来的,但是,这一部分一部分或者一句一句却是由整体构思整体思想整体形式生成的。
也就是说,文本虽然是由一部分一部分或者一句一句构成的,但是,它却是在整体性的主题赋予灵魂具有生命的。
因而,文本的意义是来自于整体的把握,而不是一句一句的相加。
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正好适用于对文本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理解。
李清照是在她整体情绪之下写它的每一个意象的,她的整体情绪必然表现在整体形式结构之中,因而,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它的整体结构形式,并在整体结构形式的前提下解释每一个意象。
第四个问题,把作者提升到一种人类普遍情感完全当成了李清照个人情感的表现,缩小了《声声慢》主题的深刻性。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声声慢》对李清照个人情感的表现,没有她个人的生命遭际就没有《声声慢》的创作,《声声慢》的诗篇是由她个人生命遭际酿就而成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声声慢》完全当成是李清照个人情感的表现。
这是由这个原因决定的:
李清照是为了表达她个人情感进行写作的。
但是,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
李清照是在个人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写作的,但是,一当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客观化、对象化,成为一种形式,她就已经脱离个人性而提升到了一种普遍性。
李清照是用诗的形式对情感的表达,而诗形式是一种符号化或者说形式化的艺术,一当个人的经验被形式化之后,个人的生命体验就成了一种普遍情感的表现方式。
这种形式已经成为有着自身形式意味的诗篇,一种脱离了诗人个人性的有着独立生命主体性的客体,一种能够凭借自己的意象和结构表现自己主题意义的艺术。
这种形式表现的情感已经由诗人个人的情感变成了形式表现的普遍情感。
还有一个问题也不能忽视,那就是,李清照不仅要表达她个人生命体验失落、孤独与苦闷,李清照是一个诗人,李清照还要把她的词尽最大可能写的好一点,美一点,精致一点。
这个对词的好、美和精致的追求,也就是进一步把她的情感形式化的过程,而进一步形式化的过程,就是把个人情感提升到普遍化的过程。
朗格曾经深刻地指出:
“诗人用语言创造了一种幻象,一种纯粹的现象,它是非推论性符号的形式。
用这一形式表达的感情既非诗人的,或诗中主角的,又非我们的。
它是符号的意义。
我们领悟起来可能要花费一些时间,而符号却无时无刻不在表现着它。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首诗歌不管在什么时候呈现于我们面前,它总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并非有谁对诗人之所言做出‘某种完整的反应’之时,诗歌才存在”(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40页)。
当我们再把某些作品当做作家个人情感比如把《声声慢》当做诗人个人情感解读的时候,我们同时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既把诗词的形式当成了诗人个人经历来解读,又毁灭了文本形式本身的意味和艺术生命。
.
第五个问题,是对艺术想象和艺术创造的严重歪曲。
包括《声声慢》在内的所有的诗歌创造,都是充满想象的艺术创造,而非对现实的实录。
对《声声慢》是李清照自身生活实录性的解读,严重减损和歪曲了李清照极富艺术想象的艺术创造。
《声声慢》中的所有意象和表现,比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比如“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比如“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等,这些被人们反反复复重复的“千古”名句,都是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和包容深刻情感意象的艺术创造,还有蕴含着整体的思想情感的结构形式。
那是一个包含着是李清照根据情感精心酝酿、匠心独运、反复推敲、不断提炼、苦苦斟酌等具体创造过程,那个创作过程就是李清照把她体验和理解到的情感转化为客观意象和结构形式的过程。
而不是对一天从早到晚生活景象的实录复写,那样理解创作就变得极其简单容易信手拈来轻而易举了。
这种解读不仅严重遮蔽和忽视了诗歌创造最重要的艺术想象的成份,而且还隐含着对学生进行了错误的写作观念和文学观念教育:
这样的对文本的解读,培养了学生从写实的角度去进行文学创造,也从写实——反映论的角度理解文学,从而使学生的文学创造缺少想象力,也缺少了正确文学观念的支撑。
《声声慢》的形式解读
一首诗的意义不是一句一句解释意义的累加,也不是一个意象一个意象意味加在一起的总和,而是整体结构形式的意义,是整体结构作为一个表现性形式的意义。
我们只有把一首诗的结构形式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形式,来探讨它的意义,才能得到这首诗的真正意义;而每一句或每一个意象的意义不是由它自身生成的,而是在它的整体结构形式中生成的,一句或一个意象只有在整体结构形式中才能获得它最准确的意义。
“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
对于这种意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符号。
这种艺术符号是一种单一的有机结构体,其中的每一个成分都不能离开这个结构体而独立地存在,所以单个的成分就不能单独地去表现某种情感。
……在艺术品中,其成份总是和整体形象联系在一起组成一种全新的创造物。
谁让我们可以把其中每一个成份在整体中的贡献和作用分析出来,但离开了整体就无法单独赋予每一个成份以意味。
——艺术符号是一种单一的符号,它的意味并不是各个部分的意义相加而成。
”(苏珊·朗格:
《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29页)。
从这种整体结构形式角度来重新解读《声声慢》,我们就会获得与原来解读很大不同的意义。
从整体结构形式来看,《声声慢》是表现生命意义不可挽回地永远失落从而造成永远的孤独的主题。
开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表现的是失落和孤独的总体意象和总体情绪;“乍暖还寒时候 晚来风急句”,表现的是孤独的强烈和孤独的难以抵御;“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表现的是没有意义生活的重复、孤独的不可解决;而“满地浣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表现的是生命意义不可挽回的丧失;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表现的是孤独的永恒;“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表现的是孤独凄苦的漫长难耐;“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呼应开头的“寻寻觅觅”,表现的是生命意义丧失、生命孤独苦闷的言说不尽。
《声声慢》的整体结构形式蕴含的意义是:
生命意义的丧失和生命不可摆脱的孤独。
整首词的各个部分是被这个主题决定的,各个部分都是在表现这个主题的。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是概念的叠加性表现,但它们结构在一起是一个意象的表现。
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七个语词连缀在一起具有一种造型作用,表现了人的一种情感状态的意象;另一方面后面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在前面“寻寻觅觅”意象的影响作用下发生了形象化的表现效果,也使其向意象化方面转化。
由于“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是继“寻寻觅觅”之后的意象,因而,这个意象的意义就得在“寻寻觅觅”的意义中得到解释,是由于“寻寻觅觅”而造成了“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双声叠韵使寻寻觅觅的意象表现的极为传神。
不说寻觅,说寻寻觅觅,不说冷清,说冷冷清清,不说凄惨,说凄凄惨惨,不说悲戚,说戚戚,这就通过叠字与叠音的方法,把无着无落感、孤独冷清感渲染的极为浓重。
但是,不仅是单字的双音叠字,而且还把双音叠字叠加在一起,这就更把那种情绪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寻寻觅觅”的意象获得了更形象的表达与更深刻的内涵。
为什么要“寻寻觅觅”呢?
把这个意象与后面表现孤独的意象相联系,我们可以知道那是因为失落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寻寻觅觅”是由于弥漫、浸透和笼罩在整个生命中的失落感引起的,因而,“寻寻觅觅”是一种若有所失的精神状态,是觉得有一种东西失落了,但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失落了,因而,要寻找的也就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
也因而,“寻寻觅觅”的意象表现的就是一种在无着无落的精神状态中想要有着有落的摸索、探寻,并非是真的要寻找什么。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即可以理解成“寻寻觅觅”寻找时的精神状态,又可以理解成寻找后什么也没有寻找到的精神状态;也就说,寻找前和寻找后都是一种孤独、冷落和凄惨的精神状态。
从《声声慢》的整体结构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是整首词精神状态的总体意象表现。
为什么会出现无着无落这种精神状态呢?
“寻寻觅觅”的无着无落感导致对有着有落的追寻,但是,在不知道丢失了什么的情况下,也是不会知道寻觅什么的。
因为,对生活不能赋予意义便不能改变无着无落感,便不能获得有着有落感,便得继续“寻寻觅觅”。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对这句不能做春天还是秋天、傍晚还是早晨(季节和具体时间)的阐释,而应做生命感受的理解,是前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具体意象。
这是一个女子傍晚独酌的意象,但是,这个意象不是由外部形象表现出来,而是由内部感受表现出来的,是由内而外形成的意象。
“乍暖还寒时候”,指的是酒的“乍暖”还不能抵御“寒”的恒定感受——生活的清淡、寡淡、暗淡,使她觉得酒“淡”——倒不一定是酒的真淡;酒虽带来些暖意,但仍然不能改变她寒冷、孤独与凄凉的感受。
因为这寒冷不只是从外部侵入的,而是从内部生出的。
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浸透骨髓的悲凉感呢?
因为孤独——丧失了的那种东西使其感到了寒冷的透彻骨髓,即使饮酒也不能获得温暖。
“最难将息”,是最难应付、调整之意,“最难”和后面的“怎敌”形成呼应。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就含有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意味,是饮酒也不能改变孤独与寒冷生存状态之意的表现。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感到晚风的“急”,是因为生命力“弱”引起的,她的孤独、寂寞与凄凉使她经不起那“晚来风”的侵袭。
因而,那“晚来风”说到底并非是自然界的“风”,而是主观感受的“风”,即她失落了某种东西造成的孤独、寂寞与凄凉感。
“三杯两盏淡酒”不能使她真正“暖”起来,她也就只能依旧处在寒冷、孤独和凄凉的情绪之中。
通过这种内心的感受的表达,诗人完成了外部的意象表现,使我们仿佛看见一个孤独的女子,在傍晚独酌,但那“三杯两盏”的酒并没有带给她带来多少暖意,她仍然浸透在一种彻骨的孤独、寂寞与寒冷的感受之中。
“怎敌他晚来风急”句表现的是内心中的寒冷,但并未表现这寒冷是怎样造成的,即她在生活中究竟丧失了什么,她“寻寻觅觅”的是什么,只有与下面意象相联系才能有明确的理解。
“雁过也, 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这个意象的真实意义仍然是对孤独情感的表现,但是却透露了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雁过也,正伤心”,可以理解成“触目惊心”的意象。
听到雁的凄厉的叫声,看见南飞的雁为什么会“伤心“呢”?
;雁在这里是书信使者的符号,而书信指的是爱人的书信。
但这雁是“旧时相识”,“旧时相识”的雁过去没有带给来爱人的任何消息,现在就更不会带来爱人任何消息了。
这熟悉的大雁的凄厉的叫声唤起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和开头的“寻寻觅觅”相呼应,不仅表现了什么也没有寻觅到,而且还更加重了孤独感与凄凉感。
这个意象表现带有与其他作品“互文”的特点。
理解那个“互文”的文本对理解这个意象的意义是有帮助的。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中有“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句,表现的是与爱人远隔千山万水,音讯不通,心灵空空,愁绪满满的孤独。
这个“雁过也, 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所表现的是更加绝望的孤独,没有爱人的消息了,表现了爱人的永远的失去。
这就在暗中回答了前面丧失了的问题:
丧失的是爱。
但“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还有另一层形而上的情感意味,表现了丧失爱的孤独生活的来来去去、反反复复、重重叠叠、无休无止。
爱情曾经是有过的,但现在并不存在了;生活虽然在继续着,但生活的意义被抽空了;期待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但却还是徒劳的枉费心机。
这种生活是黯淡的、灰暗的、空洞的、没有生命的具体内容的,因而是没有意义的。
理解了这些,我们就理解了“寻寻觅觅”不是对一种具体对象的寻觅,也不是对爱的失去的寻觅,而是在绝对孤独中对一种意义的寻觅,还有生命意义丧失导致的无着无落感。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这个意象更加明显地表现着青春与爱情丧失的孤独感、悲凉感甚至绝望感,当然也就更加具体明显地表现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情绪。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是青春、生命在没有意义生活中毁灭的意象化象征。
“满地黄花”是花儿枯萎、萎谢、残败、凋落的意象表现;“满地” 和“堆积”意象则把花儿残败、凋落的状况表现得极为鲜明、强烈。
花儿本应该是在枝头燃烧般的热热烈烈绽放,但却是“憔悴损”地“满地黄花堆积”,这意象使人们想到花儿凋谢了,没有了花儿,甚至连一瓣儿花瓣也没有了,只剩下了光秃秃干枯、萧索的花枝。
隐喻的是青春、生命的流逝,是无复孑遗,再没有什么可失去了,最后只有无穷无尽、无所不在、无依无靠、无着无落、无可奈何的孤独感与飘零感。
与“红藕香残玉蕈秋“(《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表现的情感是一致的。
“满地”是一地落地的黄花,枯萎的黄花,僵死的黄花;“堆积”是表现枯萎、僵死黄花的落地之繁、之多、之厚。
“堆积”意象凸显的是花儿枯萎、凋零、败落景象的惨烈。
但它的败落不是经过了热烈开放之后的自然陨落,而是“憔悴损”,是“憔悴”使其“损”。
是什么是它“憔悴”了呢?
“这自然使人们想到了上片的“怎敌他晚来风急”,尽管它说的是词人自己而非指黄花,但是还是使人们把它和“憔悴损”联系起来:
“憔悴”是被“晚来风急”袭击、摧残、煎熬的,联系前后其他意象,那“晚来风急”其实是生命的孤独造成的。
生命孤独到“憔悴损”的程度,就是“满地黄花堆积”了。
李清照不是为了表现客观世界的“满地黄花堆积”,而是用这个意象表现主观世界的生命感受,即孤独、凋零与毁灭的悲凉生命感受。
李清照是在用“满地黄花堆积”的意象结构象征她生命凋零、陨落、毁灭、悲凉的情感结构,这样,“满地黄花堆积”与她的生命凋零、陨落、毁灭和悲凉的情感结构便具有了一种“同构”性:
“满地黄花堆积”就脱离了它的花儿凋落的自然属性,而成为李清照情感结构的隐喻形式。
“满地黄花堆积”既是指代李清照青春的丧失与毁灭的,又是指代李清照青春丧失与毁灭造成的孤独、悲哀的生命感受的。
“满地黄花堆积”与上片的“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构成了一种对应,意象化的表现使叙说性的内容获得了意义的提升: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正是生命意义丧失与毁灭内容的具体表现,而“满地黄花堆积”也成了这种具体内容的象征性形式。
“憔悴损”当然是指青春和生命意义的丧失。
是单调、重复的生活使青春和生命的意义丧失了,这种青春和生命意义的丧失,就造成了凄清、孤独、悲凉生命感受的强烈。
“满地黄花堆积”就是象征这种生命意义丧失而产生的浓重的笼罩整个身心的孤独、凄清、悲凉的情绪。
“满”和“堆积”形象地把这种情绪的浸透、胀满和弥漫整个身心程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其中的“满”也是浓郁的悲凉愁绪的表现。
正是这种生命凄清、孤独和悲凉感的“满”和“堆积”,才使李清照在上片一开始就用了“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重重叠叠的词汇来表现她的情绪状态,也才使她在上片的一开头就用了“寻寻觅觅”的寻找的意象。
她要寻找丧失了、毁灭了的生命意义,她要从那种生命意义丧失和毁灭的孤寂、悲凉感中解脱出来。
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是一个整体性的句子,是一个整体性形式,“满地黄花堆积”与“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意象,生发着新的更大的意义。
青春消逝了、生命萎顿了,如憔悴了的昨日黄花一样,现如今还有谁能够摘取这样的黄花呢?
有人解释,这是表现像她
这样“憔悴损”的女人还有哪个男人来爱的意思,我以为是不确的。
李清照仍然是在表现生命意义的缺失,而不是表现自怨自艾,自怜自叹的情绪,更不是表现希冀男人来爱的思想。
“如今有谁堪摘?
”这个句子在上、下“怎”句式构成的模式中有了不同于表面的意义。
前面的句子是“怎敌他晚来风急!
”,后面是“怎生得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