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史中日文学作品中的女性doc.docx
《日本文学史中日文学作品中的女性doc.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日本文学史中日文学作品中的女性doc.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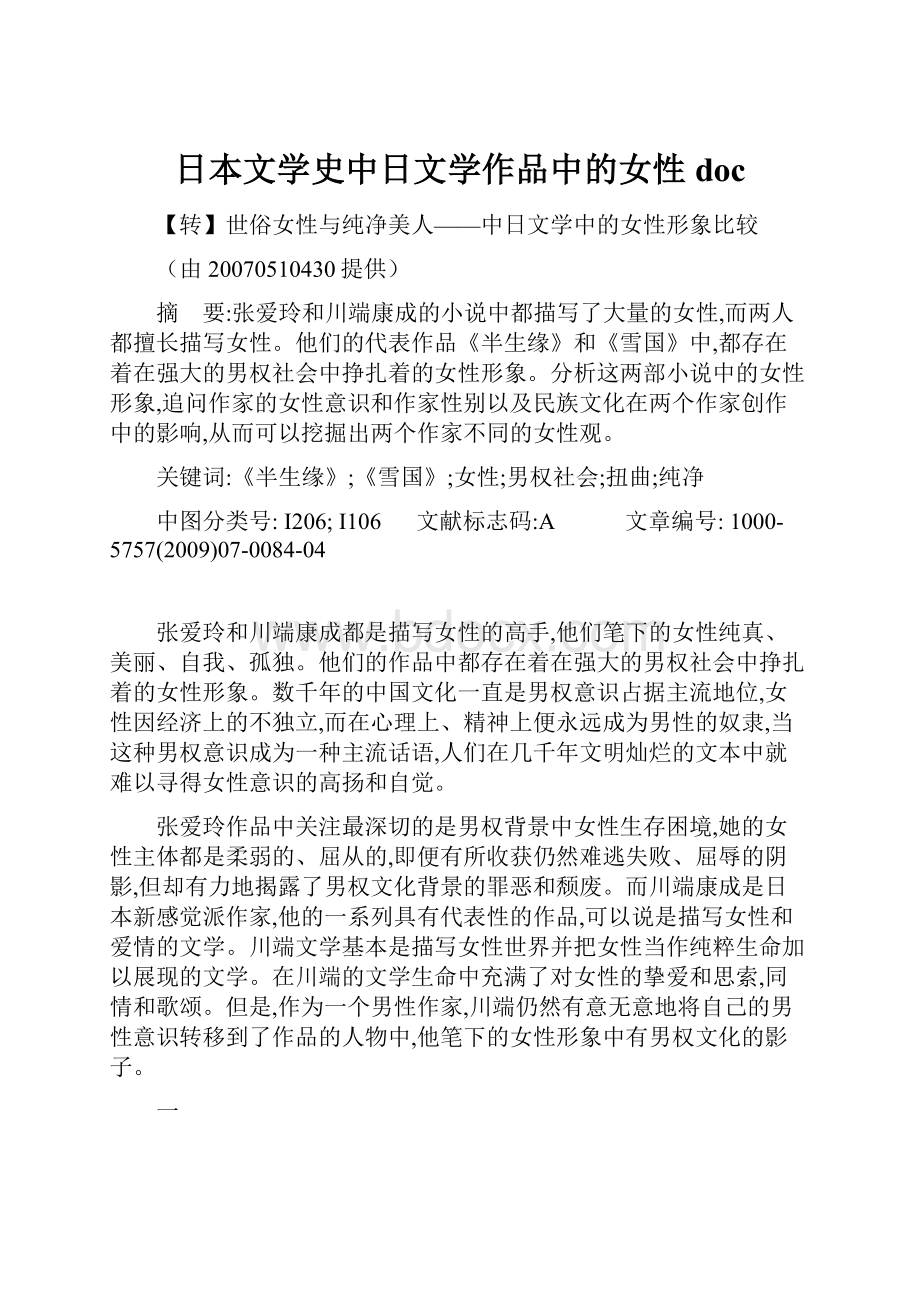
日本文学史中日文学作品中的女性doc
【转】世俗女性与纯净美人——中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由20070510430提供)
摘 要:
张爱玲和川端康成的小说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女性,而两人都擅长描写女性。
他们的代表作品《半生缘》和《雪国》中,都存在着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挣扎着的女性形象。
分析这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追问作家的女性意识和作家性别以及民族文化在两个作家创作中的影响,从而可以挖掘出两个作家不同的女性观。
关键词:
《半生缘》;《雪国》;女性;男权社会;扭曲;纯净
中图分类号:
I206;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57(2009)07-0084-04
张爱玲和川端康成都是描写女性的高手,他们笔下的女性纯真、美丽、自我、孤独。
他们的作品中都存在着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挣扎着的女性形象。
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一直是男权意识占据主流地位,女性因经济上的不独立,而在心理上、精神上便永远成为男性的奴隶,当这种男权意识成为一种主流话语,人们在几千年文明灿烂的文本中就难以寻得女性意识的高扬和自觉。
张爱玲作品中关注最深切的是男权背景中女性生存困境,她的女性主体都是柔弱的、屈从的,即便有所收获仍然难逃失败、屈辱的阴影,但却有力地揭露了男权文化背景的罪恶和颓废。
而川端康成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他的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说是描写女性和爱情的文学。
川端文学基本是描写女性世界并把女性当作纯粹生命加以展现的文学。
在川端的文学生命中充满了对女性的挚爱和思索,同情和歌颂。
但是,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川端仍然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男性意识转移到了作品的人物中,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中有男权文化的影子。
一
“自从父权制社会建立以来,人类便朝着性别统治性别依附的方向发展,五千年来的人类发展史实则是以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发展,女性从一出生就受到了来自于男权社会的各种教导,在极力将女性改造成‘谦逊、隐忍、温柔、忘我’的符合男权意识规范要求的‘大家闺秀’的同时,使女性成为了臣服于父权统治之下的逐渐失去言说权的性别。
”[1]《半生缘》作为张爱玲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中的一篇,揭示了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被“环境”所奴役,将原本纯真善良的人性扭曲成丑陋的“动物性”。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曼璐就是那个被扭曲为“动物性”的受害者。
最初的顾曼璐是个和她妹妹曼帧一样的纯真少女,可是迫于全家的生计,曼璐去当了舞女,曼璐以青春的代价换来了一家人的生计,却换不回失去的青春与贞洁。
而在男权社会里,青春美貌与贞洁是女性所有的资本。
“男才女貌”“才子佳人“的故事多鉴于中国古代戏剧和小说中,它直接将外在的美貌作为衡量女性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砝码,作为女子取得幸福爱情和美满婚姻的根本性条件。
同时,中国男人对女性容貌上的追求与要求女性贞洁是并行的,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占有欲———希望女性在身心上皆为稚嫩的,从而更能顺从地被驱使。
美貌与贞洁的不在让曼璐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难以去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
“男性把女性局限在性、生育和家庭事务中,规定了性角色的行为、姿态、态度和作风,把有利于女性受控制的特性视为女人的天性,让女人安贫乐道并维护自己所处被支配的阶级地位。
”[2]男权社会对她的压制与侮辱让她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毁灭性的力量,在疯狂毁掉自身幸福的同时更毁掉了几个人的幸福。
曼璐的“动物性”的爆发引线却是爱的缺失。
大多数的女人是在爱情中寻找自我,最后又在爱情中迷失自我,女性文学本身涉足最多最深的也是爱这个主题。
女人匮乏的是爱,虽然她们总是在付出,但收获却很少很少。
“落后和专制的社会形态对女人的压抑和摧残远甚于男人,男人尤其是知识阶层不论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多大的压迫,总还可能凭借功名利禄得到社会的承认,可以娶三妻四妾满足自己的情欲,而女人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男人找到自我。
”[3]所以曼璐把曾经的恋情看得很重。
七年后,已嫁为人妻的曼璐始终认为与豫瑾的感情是她一生中“虽凄楚,可却很有回味的”回忆,同时也成了她治疗不幸婚姻所带来伤痛的“止痛药”。
然而,再次相遇后豫瑾冷漠的态度以及与妹妹曼帧的“亲密”惹恼了敏感的她,她的情感天平一下失去了平衡。
与豫瑾不能再续前缘以及为爱求生的强烈欲望最终促使曼璐不顾伦理和亲情的约束,和祝鸿才合谋设计使其骗奸了曼桢。
张爱玲在《谈女人》里说过:
“女人在人性的发展上比较有弹性。
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而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
”对曼璐而言,她在报复让她受尽折磨受尽苦难受尽侮辱的灰暗人生!
作者充分地展示了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受压抑、被凌辱、焦虑、匮乏、悲哀、分裂,甚至疯狂的心理世界。
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生创造了无数的女性形象,他具有穿透女性心理的能力,很少有男性作家能够像他那样准确地捕捉女性的意识和情感。
女性成为川端表现“永恒的基本主题”的必由之路。
《雪国》是川端康成艺术技巧达到高峰的代表作品之一,同时也是一部女性的悲歌。
虽然雪国是一个无限梦幻的世界,里面的两个女子也被描绘得如此美丽与纯净。
虽然川端康成在极力的回避自己作为一个男性作家意识里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但是《雪国》里的驹子暴露了他的心迹。
首先驹子的身份是个艺妓。
最能代表大和民族的那种阴湿柔软性的,恐怕要属日本的艺妓了。
这是一个神秘的青春女子的世界,也是一个为上流社会男性客人服务的地。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艺妓,除了要修习琴棋书画、歌舞及茶道等艺术外,在性情上还要修炼得心静如水,没有杂念也没有野心,纯之又纯,使见了她们的客人也变得纯洁、善良。
中国清朝驻日本公使黄遵宪在《艺妓》中写到:
朝朝歌舞春风里,只说欢娱不说愁。
[4]表面看来,艺妓文化是一种美的文化,但是仔细看看,它实际是以将女性的身体与艺术出卖给男性为实质的文化,“绝大多数的卖淫是经济强大的男子购买弱小的女子的肉体,而不是相反。
那时,女子的肉体是商品,是买方———男子估价、占有、享乐的对象。
在男人看来,女人的整体大概就只能是属于这种对象。
”[5]所以艺妓文化实际上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身体与艺术被当作商品一样被买卖的文化。
其次驹子当艺妓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未婚夫治病。
日本女人学习技艺,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家庭,从小她们就被教导要牺牲自己,她们的生命不是独立的,而是依赖于男人。
日本女人为家庭奉献自身的全部,甚至去卖身卖艺被看成很正常的事情,这也是男权文化下的理所当然了。
再次,文中始终在强调一点“爱的徒劳”。
驹子爱上了一年一度来访的岛村。
驹子明明知道岛村是有家室的人,可是仍然不顾一切地在岛村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
无论驹子怎样去爱,岛村仍然觉得这只是徒劳而已。
爱的本身有种不可实现的虚无感。
岛村的形象,是灰暗、模糊的,川端康成一直在努力地替岛村辩白和解释,试图为他抹上些许光彩。
但这种种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存在于川端意识深层的对女性的鄙薄不可逆转地投影到了岛村身上。
从川端文学的爱情故事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女性观就是:
男性与女性之间是一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
故此,男性对于女性拥有自私的权力。
在创作中,川端无意识地将自己男权意识投射到了作品的人物身上,他极力保护男性的形象和地位,为此把女性的宽容、忍让乃至依附性捧为美德。
文中的岛村是个已婚男人,是游手好闲之徒,他到雪国来就是为了寻求一片洁净的世界,他在雪国里感受了两个女人的美丽,“驹子代表的是触觉的感悟,她是人生的欲念,是性的渴求和满足,是岛村品味悲剧的快感。
叶子则代表着视觉的感悟,是心灵的诉求的满足,是岛村品味活着的美感。
”[6]一个已婚男人长期逗留在外,并且和两个女子在肉体或精神上有关联,但是川端康成却并没有流露出对岛村的批判,反而是站在岛村的角度去审视和欣赏这两个女子那徒劳的爱与美,这是男权文化在他意识里留下的痕迹。
无论是《半生缘》中的曼璐、曼帧,还是《雪国》中的驹子、叶子,她们都生活在男权社会的最底层,她们都想用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美好的爱情,幸福的婚姻。
可一切都是爱的幻灭,美的徒劳。
女性作家张爱玲与男性作家川端康成在有意无意中点出了答案:
女性所面对的是一个如此强大的男权社会。
但是,在这样一个强大的男权社会中,女性从来没有停止努力。
她们默默地承受着苦难并坚强的生活,这两部作品都塑造了一个坚强的与命运抗争的底层女子的形象。
除此之外,这两部作品还透露着对女性命运的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
张爱玲对女性悲凉命运的展示与演绎,表现了她对于女性角色遭受贬压的一种无奈和对男权文化无言的控诉。
看似波澜不惊的叙述,其实是她对女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和同情。
同样,川端康成用看似不经意的叙述,透露出对善良的下层女性人物悲惨境遇的哀怜,以及自己对人生和命运的淡淡忧伤与无奈。
二
女性的挣扎与命运在不同的作家笔下被赋予了不同的色彩。
张爱玲的色彩是世俗人生,其笔下的女子是寂寞的、悲哀的甚至变态的。
而川端康成构筑的是理想世界,他笔下的女子是美丽的、纯净的极致形象。
张爱玲在《传奇》开篇中写到:
“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7]她的故事全是普通人在世俗世界里演绎的苍凉故事。
正如她说的: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张爱玲对那些新旧时代交叠下的女性的生存命运极为关注,对女性的心理挖掘也非常深刻。
张爱玲以独有的女性内审意识,探求阻碍女性自我发展的因素,并对女性生存悲剧进行透视与书写。
“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一语道破了女性心灵深处以男性为归依的“奴性意识”。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将女人逐步异化为“女奴”的历史。
自贱意识是女性自我奴化的表现之一,女性始终在寻找自身以外的依靠。
对婚的中国女人就是全部,而对于男人却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为了维护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半生缘》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男人达到一生有所依附的目的竟然伙同丈夫干出伤天害理之事,毁了妹妹曼帧一生的幸福,《金锁记》中的兰仙、《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为取悦丈夫,竟甘心忍受丈夫在外拈花惹草……她们缺乏女性为人的独立意识,掩盖不住深层意识里的依附心里,或者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或者成为父权制的帮凶。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形象是变态扭曲的;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和贬损的权力关系,表现出男权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个排他性的和单面性的价值体系。
”[8]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现代文明的外壳下,依然包裹着一颗最典型的封建式的灵魂。
她们渴望从现存的生活状态中走出来,却又被几千年积累的女奴心理所牵绊,她们在千疮百孔的感情世界里挣扎。
任何作家的创作和他的生活体验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张爱玲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但她的童年却在孤独和不幸中渡过,母亲的远离,父亲的怨恨,后母的刻薄,让她过早地尝到了人世的酸辛,早早地洞悉了世事的苍凉。
而与胡兰成飞蛾扑火般的爱情也耗尽了她一生的热情。
她的一生很少有过归属感,常感到人生是无法把握自己命运,所以她写尽了苍凉的世俗人生,小说内容也常让人感觉到压抑与无奈。
她认为“爱情是百孔千疮的”,《半生缘》少了热烈,有的只是冷静、平淡与苍凉。
“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
……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9]世钧、曼桢、叔惠、翠芝,几个普通年青人平淡如流水般轻诉的爱情,在苍凉的都市人生面前铺陈着幻灭的人生。
如果说张爱玲抒写的世俗女子在男权社会中是被扭曲的形象,那么川端康成笔下的纯美女性则是在男性视觉中被理想化的角色。
川端康成一味的在自己构筑的“雪国”世界里美化女性,与他从小的经历关系很大。
从小他的亲人相继去世,孑然一身的孤儿经历,造成了他孤僻、内向的性情。
这种“孤儿秉性”自然会使他更多地去“感悟”人生的苦短和哀怨。
自幼家中没有女性,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对女性的神秘感和向往心理。
母爱的缺乏和初恋的离去使他更加渴求女性的温柔和美丽。
“孤儿情结”和“恋爱情结”产生出川端康成“哀以思”的文学,也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观和生活观。
因此,他笔下的女性更多的呈现出来的是理想中的美。
《雪国》中的驹子被极端理想化了,明明是个艺伎和官能性的女子,却被塑造成非常洁净的美人,“女子给人的印象是出奇地洁净,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
岛村不仅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因为自己刚刚看过初夏群山的缘故。
”[10]这是岛村第一次见到驹子时候的感觉。
不仅如此,作者在描写驹子的美貌时还两次采用镜中窥人的手法,使驹子的美达到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美的意境。
“在镜中的雪里现出了女子通红的脸颊。
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纯洁的美”。
驹子除了纯净之外,艺术造诣也精湛,有着良好的审美情趣,没失去羞耻心。
在困苦的生活里驹子一直认真地记日记,学弹三弦琴,她的琴艺是雪国所有女子中最好的一个,“一个十九二十岁的乡村艺妓,理应是不会弹出一手好三弦琴的。
她虽只是在宴席上弹弹,可弹得简直跟在舞台上的一样。
”[10]性情洁净的驹子力求上进并渴望真挚的爱情,她一心一意地爱着岛村。
可是,她的爱甚至生活方式在岛村看来都是一种徒劳。
比如驹子弹琴的时候,文中这样描写“她总是以大自然的峡谷作为自己的听众,孤独的练习弹奏。
这种孤独驱散了哀愁,蕴含着一种豪放的意志……在岛村看来,驹子这种生活可以说是徒劳无益的也可以说是对未来憧憬的悲叹。
”[10]川端康成一再强调驹子的徒劳,是受了日本传统文化中“物哀”思想的影响。
“物哀”是贯穿在日本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中的一个重要观念。
“作为一个美的范畴,在日本文化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
‘物哀’产生于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化圈,又和当时日本社会的整个文化氛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最早的‘哀’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到最终形成‘物哀’这一特殊的美学范畴。
”[11]驹子对生命的憧憬和无奈,更多的是隐含着痛楚的美。
从驹子身上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内在真实的哀感,这个女性虽沦为艺妓,却洋溢着一种健康的生活情趣,有着纯朴天真的性格。
但这种美蕴藏得更多的是悲伤和哀叹,越是洁净,越是天真,她的爱便越是徒劳,艺妓身份的官能性和她自身思想上的洁净性注定了她的挣扎是徒劳。
三
不论中国女性还是日本女性,她们要面对的都是强大的男权社会,她们在其中谋生也谋爱,她们追求婚姻的幸福,勇敢地面对人生。
不同的是张爱玲笔下的女子在世俗社会中被扭曲了,而川端康成文中的则在他的幻想中化成了洁净的美人。
但相同的是二位中日作家均未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底层女性的悲剧命运将如何得与改变?
参考文献:
[1] 元程.《半生缘》中顾曼璐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J].文教资料.2008,(19).
[2]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98.
[3]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
三联书店,1993:
62-63.
[4] 姜建强.山樱花与岛国魂———日本人情绪省思[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9.
[5] 加藤周一.日本文化论[M].叶渭渠,译.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410.
[6] 陈婧,焦春艳.东西比较视阈下的《雪国》[J].现代语文:
文学研究,2008,(9).
[7] 张爱玲.传奇[M].湖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扉页.
[8] 杨永忠,周庆.浅论女性话语[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86分院学报,2004,(4).
[9] 张爱玲.张爱玲[M].上海:
文汇出版社,2001:
338.
[10] 川端康成.雪国[M].叶渭渠,唐月梅,译.天津:
天
津人民出版社,2005:
11,27,40—41,41.
[11] 刘昱.谈川端康成《雪国》中的“物哀”思想[J].沧桑,2007,(5).
《边城》与《伊豆的舞女》之比较阅读
【摘要】 以考察作品的叙事视角为中心,本文分别剖析了《边城》与《伊豆的舞女》中的叙述状况。
并在此基础上,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阅读。
具体而言,即指出不同叙事视角所造成的叙事效果的相异之处,以及探讨两者叙述所取得的某种相同的叙事效果。
【关键词】叙事分析叙述者叙事视角 叙事效果
秉着对女性美、人性美的共同追求,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几乎不约而同地分别在《边城》与《伊豆的舞女》中谱写出了哀婉的青春之歌。
笼罩于作品中的朦朦胧胧的恋情,总令人欲罢不能。
在人物塑造、小说基调、艺术风格等方面,两部作品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而从叙事视角的角度出发,对两部作品进行对比阅读,则能发现两者在叙事效果方面存在的异与同。
一、《边城》的叙事分析
《边城》讲述的是发生在湘西边境小山城里的故事。
在这个边城里,有相依为命的爷孙俩——老船夫和翠翠,有深爱翠翠的兄弟俩——天保和傩送,也有形形色色的各类“愚夫俗子”——水手、农人、兵士、商人……。
翠翠与二老傩送彼此相爱。
大老天保为了成全他们, 外出闯滩而死。
二老对此心怀愧疚,也远走他乡,只留下翠翠一人在孤苦地等待: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1]
总体而言,小说采用的叙事视角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相当于热奈特理论中的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
故事外的叙述者仿佛无所不知,居高临下地俯瞰着故事内的芸芸众生。
他时而铺陈故事发生的背景(如“茶峒”山城景色、当地风土民情等等),时而勾勒登场人物的外貌、神态及气质,时而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捕捉他/她的思想动态及情感意识,甚至时而对人物作出评价。
如在第七部分,表述了对祖父的如下看法:
“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
[2]全知叙述者所特有的权威性在此展露无遗。
然而,通过全知叙述者的中介眼光来观察事物却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作品本身的戏剧性。
《边城》的全知叙述者相当巧妙地弥补了这一不足。
首先,他不断变换对老船夫的称谓。
在第一部分,从一开始的“老人”到“老船夫”,皆为客观展示故事的称呼。
在翠翠出场之后,则迅速转变为站在翠翠立场上的称呼:
祖父或爷爷。
在这之后的叙事中,使用“祖父”称谓的情况居多,只是偶尔切换成“老船夫”的称谓。
由此,产生了通过人物(翠翠)眼光叙述的某种假象,作品的真实性也得以提高。
其次,全知叙述者在作品中“故意隐瞒”了某些人物的心理活动,在留给读者想象空间的同时,增强了情节的吸引性。
这一点在翠翠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翠翠的情窦初开,叙述者并未直接点明:
“但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3]、“翠翠同他的祖父,也看过这样的热闹,留下一个热闹的印象,但这个印象不知为什么原因,总不如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4]。
对于二老的内心活动,叙述者则完全没有展示。
读者只能通过他的言行来猜测其心中怀揣着的对翠翠的爱意以及对老船夫的误解。
热奈特将叙事分析明确划分为两个基本问题:
“谁说”(即叙述声音)和“谁看”(即叙事视角或聚焦)。
毫无疑问,在全知叙述中,叙述声音和叙事视角统一于同一主体,即故事外上帝般的叙述者身上。
《边城》的绝大部分叙事正是由这样的叙述者所掌控。
然而在作品中,全知叙述者偶尔也会短暂地换用人物的有限视角(或者称为第三人称的固定式内聚焦)。
其中的典型例子当属二老送酒葫芦到翠翠家的一幕:
“翠翠来不及向灶边走去,祖父同一个年纪青青的脸黑肩膀宽的人物,便进到屋里了。
”[5]读者透过翠翠“过滤”后的眼光,来猜测聚焦对象的真实身份,由此产生了短暂的悬念。
二、《伊豆的舞女》的叙事分析
可以认为,《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康成将其在旅途中与舞女产生恋情的自身经历加以艺术加工写就的。
当然,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作者,而只是等同于主人公的“虚构作者”。
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进行的叙述是回顾性的。
而这一类叙述通常会既涉及站在叙述当前时间点上的“叙述自我”,又涉及处在往事中的“经验自我”,从而出现两种眼光的交替:
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即“叙述自我”的眼光)和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即“经验自我”的眼光)。
《伊豆的舞女》的开篇就让人感受到了这两种眼光的互相切换。
很显然,一开始的“山路变得弯弯曲曲,快到天城岭了。
这时,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杉林,从山麓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6]是通过“经验自我”的视角来叙述的。
旋即便转为“叙述自我”事后的讲述。
“那年我二十岁,头戴高等学校的制帽,身穿藏青碎白花纹上衣和裙裤,肩挎一个学生书包。
(中略)一派秋色,实在让人目不暇接”[7]。
这一独白式的讲述也是对故事背景的一种介绍。
而接下来的部分:
“可是,我的心房却在猛烈跳动。
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
这时候,大粒的雨点开始敲打着我”[8]又明显是出自“经验自我”眼光的叙述。
如此一来,文本便穿插进行着出自“经验自我”眼光的“场景展示”与出自“叙述自我”更为成熟的眼光的“补充说明”,进一步加强了故事的戏剧性与可读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认知能力更强的“叙述自我”事后的评点,给情节的发展作出了极好的注释。
如在第四部分,提到了“我”决定跟随艺人们到大岛的家的原因:
“对她们,我不好奇,也不轻视,完全忘掉她们是巡回演出艺人了。
我这种不寻常的好意,似乎深深地渗进了她们的心”。
[9]叙述“我”在听到舞女说自己是好人的一幕之后,则插入了如下阐述:
“我已经二十岁了,再三严格自省,自己的性格被孤儿的气质扭曲了。
(中略)因此,有人根据社会上的一般看法,认为我是个好人,我真是感激不尽”。
[10]“我”与艺人们之间浓浓的互敬互爱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
由此可见,“叙述自我”适时作出的回顾性的盘点,揭示了作品的主题,使读者可以更好地从中体会到小说的内涵。
三、两部作品叙事效果之异同
全知叙事视角适用于展现宏大的叙事,因而有利于展示《边城》中湘西边境的广阔的生活画卷。
而第一人称叙述则无疑与《伊豆的舞女》自传体的性质相吻合。
其实,无论何种叙事视角都有其优缺点,难以一较高低。
然而,小说的叙事效果却属于可以比较的范畴。
3.1叙事效果的相异之处
其实,《伊豆的舞女》中“我”的视角代表的就是男性视角。
所以,女性在作品中始终是一个“被看”的“他者”。
尽管作品对舞女(“他者”)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但这也是以“我”地位的高高在上为前提的。
应该说,求知若渴的舞女对高中生“我”的感情更接近于一种仰慕之情
在男女关系方面,《边城》则有着截然不同的一番表现:
翠翠完美无暇,成为了兄弟俩共同追求的对象。
通常被认为较为冷静、客观的全知叙述者却在叙述中抬高了女性的地位,男性(兄弟俩)只能“仰视”、甚至“跪拜”女性(翠翠)。
3.2叙事效果的共同点
叙事视角的相异理所当然地会导致不同的叙事效果。
然而读者阅罢两部作品之后,却会得到相同的感受,即感到其中恋情的不透明性。
在《伊豆的舞女》中,由于第一人称视角的限制,“我”对舞女的爱慕之心有所展现。
舞女内心对于“我”的感情却无法得以剖析,只能通过他人的话来间接地表现:
“‘哟,讨厌。
这孩子有恋情哩。
瞧,瞧……’四十岁的女人吃惊地紧蹙起双眉,把手巾扔了过来”[11]所以,这段青涩初恋显得若隐若现,缥缈不定。
四、小结
综上所述,《边城》基本上采用的是全知叙述模式,只是偶尔换用第三人称的有限视角。
贯穿《伊豆的舞女》始终的则是第一人称的叙述,且该第一人称被分裂为“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
注释:
[1][2][3][4][5]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 边城》,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
446;394;387;388;407。
[6][7][8][9][10][11]川端康成.《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3;3;18;23;9。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 边城》,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10月第3次印刷。
[2]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2次印刷。
[3] 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4]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