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笛卡尔到海德格尔.docx
《从笛卡尔到海德格尔.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笛卡尔到海德格尔.docx(4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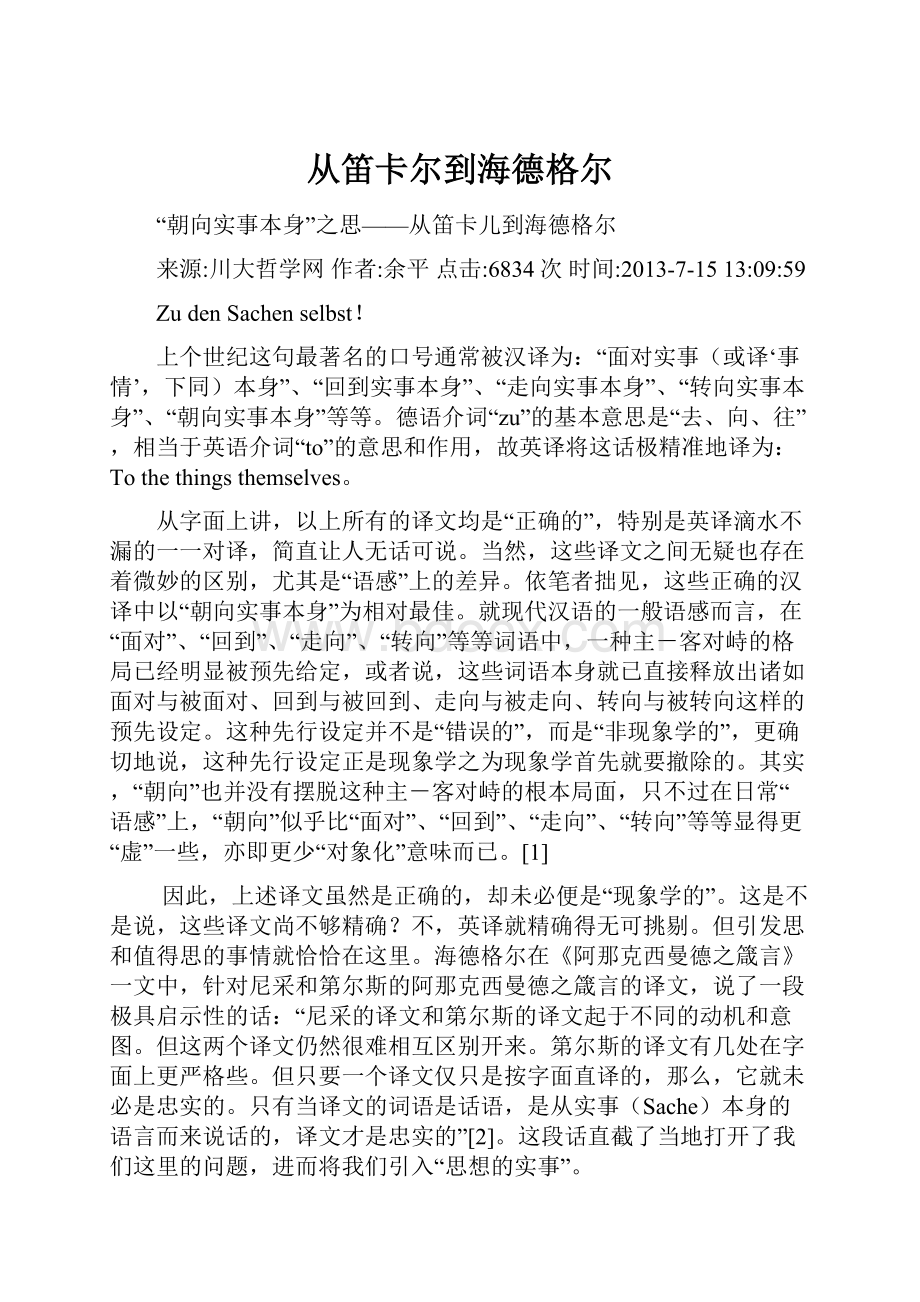
从笛卡尔到海德格尔
“朝向实事本身”之思——从笛卡儿到海德格尔
来源:
川大哲学网作者:
余平点击:
6834次时间:
2013-7-1513:
09:
59
ZudenSachenselbst!
上个世纪这句最著名的口号通常被汉译为:
“面对实事(或译‘事情’,下同)本身”、“回到实事本身”、“走向实事本身”、“转向实事本身”、“朝向实事本身”等等。
德语介词“zu”的基本意思是“去、向、往”,相当于英语介词“to”的意思和作用,故英译将这话极精准地译为:
Tothethingsthemselves。
从字面上讲,以上所有的译文均是“正确的”,特别是英译滴水不漏的一一对译,简直让人无话可说。
当然,这些译文之间无疑也存在着微妙的区别,尤其是“语感”上的差异。
依笔者拙见,这些正确的汉译中以“朝向实事本身”为相对最佳。
就现代汉语的一般语感而言,在“面对”、“回到”、“走向”、“转向”等等词语中,一种主-客对峙的格局已经明显被预先给定,或者说,这些词语本身就已直接释放出诸如面对与被面对、回到与被回到、走向与被走向、转向与被转向这样的预先设定。
这种先行设定并不是“错误的”,而是“非现象学的”,更确切地说,这种先行设定正是现象学之为现象学首先就要撤除的。
其实,“朝向”也并没有摆脱这种主-客对峙的根本局面,只不过在日常“语感”上,“朝向”似乎比“面对”、“回到”、“走向”、“转向”等等显得更“虚”一些,亦即更少“对象化”意味而已。
[1]
因此,上述译文虽然是正确的,却未必便是“现象学的”。
这是不是说,这些译文尚不够精确?
不,英译就精确得无可挑剔。
但引发思和值得思的事情就恰恰在这里。
海德格尔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一文中,针对尼采和第尔斯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译文,说了一段极具启示性的话:
“尼采的译文和第尔斯的译文起于不同的动机和意图。
但这两个译文仍然很难相互区别开来。
第尔斯的译文有几处在字面上更严格些。
但只要一个译文仅只是按字面直译的,那么,它就未必是忠实的。
只有当译文的词语是话语,是从实事(Sache)本身的语言而来说话的,译文才是忠实的”[2]。
这段话直截了当地打开了我们这里的问题,进而将我们引入“思想的实事”。
所谓正确的、无可挑剔的翻译,是就也只能是就“字面”(语法的、语义的、语用的等等)以及更深的“学术”(语文学的、历史学的、哲学史的等等)而言的,因为从根本上讲,只有与某种已然给定的东西相比照,才谈得上正确与否以及精确与否。
这就是说,当且仅当句子“ZudenSachenselbst”字面的以及学术的“原意”已经这样那样被现成地给定,我们才有可能判定:
上述汉译是正确的,而英译更是无可挑剔的。
然而,“正确的”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忠实的”吗?
一个能正确地引证甚至精确地背诵或复述黑格尔的人,就是一个“忠实的”辩证法家吗?
显然未必。
所以,纵然我们对ZudenSachenselbst的翻译从字面乃至学术上讲是正确的,也并不意味着这些译文就现象学而言一定是忠实的。
这倒不是说,译文作为译文总是有瑕疵的,毋宁说,即使是象英译那样无可挑剔的译文,由于始终处在译文与原文的“符合”关系这种先行设定的统辖下,其意义境域归根到底是实证的,就是说是一件“学术的实事”;而所谓“忠实的译文”,由于其本身是“话语”,是“从实事本身的语言而来说话”的,其“解释学处境”本质上是非实证的,并且“能够始终全新地成为当前”,[3]故而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实事”。
其实,远不单单是翻译领域才有此种区别。
在一切理解、解释、阅读、诠释、反思、对话等等之中,学术上正确的,未必就能担保其在思想上是忠实的。
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对此说得很通透:
“一如被知觉的世界之构成来自事物之间的反光、阴影、等高线、水平线——这些东西既不是物件、也不是虚无,却反过来为同一件事物和同一个世界规划出其可能的变化场域;同样,一位哲学家的整套作品及思想,亦是由已经述说的东西之间的某种接合方式构成的,对于后者而言,并没有客观的诠释与任意的诠释之间的两难,因为这些都不是思想的对象,因为一如阴影与反光,当我们对之进行分析性的观察或抽离的思考时,就会毁坏了它们,而我们能够忠实对待它们和重获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思想它们。
”[4] 若顺此而言,则对ZudenSachenselbst这句话忠实的“翻译”,便只能是不断地去重新思考它,因为ZudenSachenselbst本身乃一件彻头彻尾的“思想之实事”。
尽人皆知,ZudenSachenselbst这句口号乃公认的集中凸显现象学精神的座右铭,说它是整个现象学思潮的灵魂也不为过。
思想的口号只有在思想与口号之所说的对话中才可能被“翻译”。
这意味着,这句口号本身必须或者说只能是现象学的;这进而又意味着,只有经过重新思考,亦即与作为“话语”、作为“从实事本身的语言而来说话”的ZudenSachenselbst进行“全新当前”的历史性对答,ZudenSachenselbst这句口号的“存在性”诉说,才可能透过环绕着它的种种翻译及学术问题而“忠实地”亦即“现象学地”涌向我们。
ZudenSachenselbst作为口号,犹如所有的口号一样,其本身乃是一种召唤。
它召唤什么?
召唤那尚付阙如者或尚不在场者。
什么东西尚付阙如?
尚不在场?
“实事本身”。
如果实事本身向来就一直持续在场,那就根本不存在“zu”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所谓回到、转向、朝向、走向这样一回事,就是说,只因为尚付阙如,才需要回到、转向、朝向、走向等等。
但是这样一来,作为现象学的灵魂,ZudenSachenselbst这话要么就什么都没有说,要么便极度狂妄。
在整部哲学史上,难道有哪一个哲学家不是或者至少不认为自己起码是走向实事本身的呢?
就此而言,这话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然无容置疑的是,这个口号要召唤的恰恰就是这个“起码”的东西,而召唤这个最起码的东西等于在说:
一部哲学史甚至连“实事本身”都尚未触及,遑论它哉!
要反驳这种狂妄似乎并不难,因为我们只消说:
那只是口号呼唤者的一家之言而已。
但这种表皮的形式反驳显然解构不了上面的问题:
事情的根本不在于,每一个哲学家是否都触及到实事本身,毋宁说在于,现象学是否抵达以及如何抵达它所宣称的实事本身,因为正是现象学才使“实事本身”脱颖而出。
于是事情最终聚焦于这样一个问题:
何为“实事本身”?
我们召唤实事本身。
但“实事本身”尚付阙如,尚不在场。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用传统的定义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因为只有一本质上已然现成给予的东西才能被定义,而实事本身却尚未成形,尚未到来。
于是我们不得不返回到ZudenSachenselbst上来。
象所有的口号一样,在ZudenSachenselbst这句口号中,固然突显着“朝向实事本身”这个口号的直接意指,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句口号本身同时已经就是“话语”,即已经是在“从实事本身的语言而来说话”。
因此,在此口号中,事实上已收拢、承传和释放着哲学之“历史”,就是说,这口号本身已然就是当下的“哲学史”;更精确点说,这个作为话语而且“只有在哲学活动本身中才能得到把握”的口号,[5]召唤着哲学历史之演历作为活生生的“哲学”到来。
近代哲学发轫于笛卡儿。
被海德格尔称为“在思想上了解了思想史的唯一一位西方思想家”[6]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的近代部分(中文版第四卷)中,在讲完了培根和雅各·波墨之后,于第二篇一起首便说:
“我们现在才真正讲到了新世界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从笛卡儿开始的。
从笛卡儿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
这种哲学明白:
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象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
”。
[7]“这个人对他的时代以及对近代的影响,我们决不能以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
”[8]这是两段极具思想含量的话。
作为一种哲学史观,认笛卡儿为近代哲学的开端,并无特别之处。
出人意表的地方是黑格尔的“家园”和“陆地”之比喻。
此乃思想分量很重的“比喻”,沿着它们,我们可以探入到近代哲学的思想深处。
笛卡儿以前以及之后的哲学与笛卡儿哲学,若纯粹从“史”的层面上讲,不过是哲学的不同历史形态,说到底并没有什么优先地位。
但对辩证法家黑格尔来说,一方面“近代哲学史之所以能够存在,是靠总的哲学史,靠几千年的哲学进程;精神必须走过这一漫长的道路,才能产生近代哲学。
”[9]但另一方面,后起的哲学对其之前的哲学始终具有本质上的优先性,因为“之前”不过是“后起”的构成环节,而“后起的”总是建构在对“之前”的扬弃之上(当然这种“先后”并不等于流俗的“时间”上的先后),势必更丰富,更具体,故而更“先进”。
可是即便如此,黑格尔对笛卡儿哲学似乎也过分青睐。
难道笛卡儿以前的哲学比如培根的哲学便不是“家园”或“陆地”吗?
作为近代哲学之开端,笛卡儿哲学这种作为“家园”和“陆地”的优先性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笛卡儿哲学以方法论的怀疑著称。
这至少有三层紧密勾连的意味。
第一,作为近代哲学之开端,笛卡儿哲学决非流俗的“时间”甚至“历史”意义上的“开端”,毋宁说,这是在“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意义上之开端。
笛卡儿的“第一件事是不要作任何假定;这是一条伟大的、极其重要的原则。
”[10]其所以是“一条伟大的原则”,是因为只有首先清除掉一切成见、偏见和假定,才能重建哲学的基础,而这正是近代哲学之所以为近代哲学的真正本质。
第二,笛卡儿哲学于是便必然“怀疑一切”。
这种怀疑一切与通常所谓的怀疑论无关,因为后者以怀疑或不可知为终局,而前者是以寻求真实确定的东西为根本目标,而且这种真实确定的东西恰恰是绝对不可能被怀疑的。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
“笛卡儿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怀疑论者才怀疑,而是说,他必须变成一个怀疑论者,因为他把数学的东西确定为绝对的根据,并且为一切知识寻求与之相应的基础。
”[11]第三,按理说,一切东西都可以对象化,而一切对象化了的东西都是可以怀疑的。
故而问题便在于:
当真存在笛卡儿所说的绝对不可能再被怀疑的东西吗?
笛卡儿通过一系列怀疑的“还原”后,最终抵达了其号称作为一切怀疑之极限的“我思故我在”。
所谓我思故我在,这绝非一个推论。
笛卡儿本人对此就有无容置疑的答复:
“当我们发觉我们是在思维着的东西时,这是第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是从任何三段论式推论出来的。
当有人说:
我思维,所以我存在时,他从他的思维得出他存在这个结论并不是从什么三段论式得出来的,而是作为一个自明的事情;他是用精神的一种单纯的灵感看出它来的。
从以下的事实看,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他是从一种三段论式推论出来的,他就要事先认识这个大前提:
凡是在思维的东西都存在。
然而,相反,这是由于他自己感觉到如果他不存在他就不能思维这件事告诉他的。
”[12]这就是说,思维与存在是直接同一的,并且这种同一是在一切判断、推论之前已然先行自明地给予的,尽管“我思故我在”作为一个命题看起来很像是一种“推论性”的给予。
实际上,直接同一也好,间接同一也罢,事情的根本还不在这里。
笛卡儿哲学怀疑什么不重要,他的这种方法论的怀疑是否成功也不重要,乃至他所找到的这个“我思故我在”是否真正禀有他所说的绝对确定性也不重要。
作为近代哲学之开端,笛卡儿哲学作了如下的本质性奠基:
1、通过怀疑的方式抵达不证自明的绝对确定性;2、这种绝对确定性始终是在意识(或自我意识、理性、思维、我思、反思、精神等等)中来显现的,即始终是在“自我意识”中被给予或被占有的。
3、对这种在自我意识之意向中显现的绝对确定性之追逐,由此便构成了全部近代哲学的根本生存性朝向。
黑格尔谓之“家园”、“陆地”云云,其未曾道出的就是这种本质性奠基。
哲学之为哲学,不在于与其它非哲学相比它拥有某种由学科立场抢先决定的“哲学高度”,相反,哲学必须为自己的任何立场辩护。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近代哲学之为近代哲学,就在于它即为这种不断地重新辩护或者重新证明本身。
这意味着,“方法论”上的怀疑品格,继而追逐清楚明白、不能再怀疑的绝对前提,实乃近代哲学的基本存在方式,亦即它根本的生存论意向。
正是在这种不可遏制而又贯透一切的生存意向的强烈召唤中,才有了所谓意识之启蒙,自我意识之觉醒,精神之解放,反思之高扬,理性之张显,以及思维、我思之开敞。
而这些正是哲学之为哲学之所“是”,就是说,是哲学之为哲学活生生之释放。
一当这些启蒙、觉醒、解放、高扬、张显和开敞等等莅临之际,正如黑格尔敏锐洞察到的那样,由笛卡儿奠基的近代哲学便真正回到了哲学自在自为的“存在家园”。
非但如此。
无论被不断追逐的这种确定性是什么,由于其始终是在我思或自我意识中被给予的,就是说,由于这种确定性说到底都是“为意识”而显现的存在,因而,实质上是以还原的证明方式赢获的这种不证自明的确定性,就始终直接自身担保着自身:
作为绝对的设定者或“躺在下面的”基体的“‘我’成了出类拔萃的主体,成了那种只有与之相关,其余的物才得以规定自身的东西”。
[13]换言之,由于一切可能的存在者都是在我思或自我意识之中收拢、成形和给出自身的,所以这种我思或自我意识实质上就是作为确定性的确定性本身;这等于说,自我意识就是那照现一切从而支撑一切的确定性之“实地”,而所有在此“实地”上着落的作为这样那样“什么”的“实事本身”,故而便被绝对地担保着。
黑格尔于是有感于脚踏实地而惊呼:
“陆地!
”
的确,笛卡儿为近代哲学奠定了“内在的”家园和“踏实的”陆地,其作为近代哲学之开端及其禀有的优先性地位尽在于此。
自笛卡儿以降,哲学都栖息在此家园中,在此陆地上播种、耕耘和收获。
经过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心锤炼,这个家园或这块陆地终于赢获了自己最极端的形态:
绝对哲学。
海德格尔写到:
“思维在它自己的思维对象无可动摇的确定性中寻求绝对基础。
哲学在其中有在家之感的那块陆地,乃是知识的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
这块陆地只是逐步地得到征服和完全测量的。
当绝对基础被思考为绝对本身时,人们便完全占有了这块陆地。
对黑格尔来说,绝对就是精神:
在无条件的自我认识的确定性中寓于自身而在场的东西。
”[14]完全可以说,黑格尔哲学不过是最激进的和完成了的笛卡儿哲学。
如果只有“我思”是绝对确定无疑的,那就等于说只有“主体”是无条件确定的;然这样的主体明显是缺乏内容的,因而是形式的,空洞的。
于是黑格尔以少有的简洁斩钉截铁地说: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
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
[15]这意味着,笛卡儿的绝对确定的我思或主体,绝非一个现成给定的阿基米德点,也非一种流俗意义上的主观-客观框架中的“主体方面”;主体之为主体,是在逐步深入认识客体的过程中不断现实生成的,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在赢获作为对象的客体的过程中不断“返回”到自身亦即实现主体自身的。
“我乃是一纯粹的‘自为存在’······凡是在我的意识中的,即是为我而存在的。
我是一种接受任何事物或每一事物的空旷的收容器,一切皆为我而存在,一切皆保存其自身在我中。
每一个人都是诸多表象的整个世界,而所有这些表象皆埋葬在这个自我的黑夜中。
由此足见我是一个抽掉了一切个别事物的普遍者,但同时一切事物又潜伏于其中。
所以我不是单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包含一切的普遍性。
”[16]这样一来,主体就不再是抽象的、形式的,而客体也不再是异己的、“自在”的,两者都是具体的:
主体不过是扬弃了的客体,而客体不过是扬弃了的主体。
所以,真正现实的东西既不是抽象的客体,也不是抽象的主体,而且也不是这抽象的两者的抽象“统一”,因为具体的客体始终是向主体显现着的客体(包括抽象的“物自体”),而在此显现中,主体自身也才真正现实地显现出来。
这种始终作为主体之对象而涌向主体的客体,这种消解了客体限制或者说以客体为自身“无机的身体”的主体,从而便是无限的,绝对的,更确切点讲,就是“绝对本身”。
倘若只有以知性形而上学的命题方式来表述,我们便只能说:
主体之为主体就在于它不仅是主体也同时是实体,实体之为实体就在于它不仅是实体同时也是主体。
对黑格尔来说,意识是一条“赫拉克利特河流”,而且这条意识河流绝非一条以任何可能的经验方式给予的现成河流,毋宁说,河流之为河流的本质就在于那始终已经而又尚未着的“流”本身,若以现象学的术语更确切点说,意识之为意识的本质就在于,它是那始终作为意向性本身而先行着的“自我意识”本身。
在自我意识之河流经沿途的“两岸风光”之际,那些在自然意识那里认定为是异在于自我意识的“自在”的“风光”,由于被自我意识之光所穿透,从而蝶化成“为意识的存在”,即构成了意识自身的活生生的“内容”或显现着的诸意识之具体形态。
作为始终先行着的意向性本身,自我意识之流是弥漫着的“存在”,而两岸风光甚至河流自身泛起的种种波涛,都只是被弥漫亦即“被存在”的存在者。
这样,解除了所有异在的“风光”之限制的自我意识,便成了“在别物中即在自己中”或“在别物中返回到自己”[17]的无限性本身。
无限的就是无条件绝对的,因为包括知性的“主体”和“客体”在内的一切有条件的均被消解和吸收;绝对的就是始终显现在场的,因为哪怕只有一个异己者隐匿缺席,势必都会毁坏绝对本身;始终显现在场的就是唯一真实的,因为凡虚假的、流逝的以及隐匿的,说到底就是不能显现在场的,或者只是曾经-尚未显现在场的,而真实、真理、主体、实体等词语说的无非是:
显现在场,而且始终显现在场。
在还原掉(亦即黑格尔所谓“扬弃”)知性形而上学的种种干扰之后,我们终于通达了实事之堂奥:
真实的东西或真理,源始地就是囊括主体与客体的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
从逻辑上说,既然为统摄主-客双方、无限的或始终在场的绝对,那当然就是实事本身,全部的实事本身。
面对这样一个以不断拓进的思辩回旋而赢获“绝对”的绝对哲学,我们确已无话可说,因为只要我们以理性-概念的方式认识或反思,我们便势必葬身于思辩之绝对自在自为的十面埋伏之中。
然而,这个融实体与主体于一体的绝对精神就是实事本身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正象笛卡儿我思的自明性是经过怀疑还原后的自明性一样,黑格尔绝对的绝对性也是经过思辩扬弃还原后的绝对。
这意味着,虽然我思和绝对确乎由作为家园和陆地的自我意识担保着,但这个自我意识本身却不仅是幽暗恍惚的,而且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其“存在的意义”已被“决定性地”耽搁了[18]。
显然,这个被自我意识攫住的我思和绝对远不等于实事本身,而同样显然的是,由于实事本身被深深围困在自我意识中,从自我意识的突围因而势在必行。
这个卓越的突围是由胡塞尔启动的,其启动的契机仍然是笛卡儿。
胡塞尔对此异常清楚明确,并且直言不讳:
“在过去的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勒内·笛卡儿那样对现象学的意义产生过如此决定性的影响。
现象学必须将他作为真正的始祖来予以尊敬。
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正是对笛卡儿的沉思的研究,影响了这门成长着的现象学的新发展,赋予了现象学以现有的意义形式,并且,几乎可以允许人们将现象学称为一种新的笛卡儿主义,一种20世纪的笛卡儿主义。
”[19]之所以如此看重笛卡儿,是因为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儿的“我思”乃“是一个‘阿基米德点’,依靠这个点,真实的哲学本身才能获得一种系统的、绝对可靠的发展。
”[20] 所谓“真实的哲学”也就是胡塞尔著名的“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
为什么笛卡儿以怀疑的方式向纯粹思维着的本我的回溯,就赢获了“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之转折的阿基米德点呢?
这是因为在笛卡儿的这种朝向绝对无疑地可经验之本我的回溯中,“那种在其自足的和自为的存在中直接意识其本身、对其自身来说绝对无疑地可经验的主体性,首次被突出来了,首次在其纯粹的自为存在中、在其意识之流中被突出来了,并且被牢牢地界定起来了······那个‘纯粹主观’的领域被科学地突出来了”。
[21]这个在笛卡儿“我思”中突显出来的领域被胡塞尔誉为一个“伟大的发现,并且恰恰是一个必须首先完成的发现,借此,一种先验哲学才能起步。
这里所谓的发现也即对先验纯粹的、绝对自足的主体性的揭示,这种绝对无可置疑的主体无论何时都是它本身所能认识的。
”[22]
但是,尽管胡塞尔如此首肯笛卡儿的“我思”,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个阿基米德点上:
“这一发现的真正意义是笛卡儿本人所未能了解的。
其举世闻名的格言‘我思故我在’貌似平凡无奇,实际上在它背后开启出十分巨大和幽暗的深渊。
”[23]也就是说,在胡塞尔眼中的这个阿基米德点同在黑格尔那里一样,也绝非一个现成既定的阿基米德点,而是一个巨大的待开启的“幽暗深渊”。
根据胡塞尔,笛卡儿在这个阿基米德点上有两个根本性失误。
第一,倘若“我思”本身是幽暗的深渊,那么真正必须探入的就是这个涌动着的深渊,而决不能将这个深渊板结化为某种现成的作为出发点的“死点”。
“可惜在笛卡儿那里,那个隐约的、但却极为不幸的转折便是如此情况,它把本我变成了思维实体,变成了被分离出来的人类心灵,变成了根据因果原则推理的起点环节,简言之,通过这个转折,他成为了背谬的先验实在论之父。
”[24]第二,笛卡儿不仅仓促地掠过了作为深渊的我思本身,而且当笛卡儿由那种相比于胡塞尔的“悬搁”而显得粗糙的“怀疑”向绝对确定的“我思”回溯时,他更仓促地掠过了一个“最重要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亦即“对世界之物的悬搁丝毫不会改变这样一个实事:
经验仍然是对世界之物的经验,各种意识也仍然是关于世界之物的意识,‘本我思维’这个标题必须扩展一个环节:
每一个我思都在自身中拥有作为被意指之物的被思者”,[25]就是说,掠过了我思本身所禀有的所谓“意向性”问题。
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从笛卡儿的失误处起锚扬帆的。
笛卡儿是从怀疑一切进而向确定无疑的我思回溯而展开其哲学沉思的。
胡塞尔接受哲学必须向绝对确定的本我回溯这一点,但仅此而已。
“重新引发这些沉思的惟一有效的复兴运动并不在于接受这些沉思,而是在于,只有在向‘本我思维’的回溯中才揭示出它们极端主义的最深刻意义,并且揭示出那些由此而涌现出来的永恒价值”。
[26]笛卡儿沉思的起点是怀疑。
根据胡塞尔,这个起首处本身便是不彻底的:
“我们并不要求进行笛卡儿所做的尝试,即通过对感性经验的仓促批判来证明,虽然世界始终被经验到,但仍然可以设想它是不存在的。
”[27]换言之,笛卡儿式的怀疑无论在其方式还是内容上均是“经验的”,它由此所得到抑或删去的东西都是经验的,这意味着笛卡儿式的沉思实质上不可能真正实现“对科学进行绝对论证”,亦即抵达不了胡塞尔所说的那种绝对的给予性,那种“直接的和绝然的明见性”,那种“必然先行于所有其他明见性的明见性”。
[28]于是,胡塞尔断然改造了笛卡儿沉思的经验性开端,完全放弃了在经验层面上去纠缠诸如可疑抑或不可疑这类笛卡儿式的问题,而将包括世界之实存及其相关的经验明见性在内的整个经验世界,统统先封存起来存而不论。
这便是著名的比笛卡儿式的怀疑狠得多的“现象学悬搁”。
在悬搁掉自然世界的存在,中止了一切经验信仰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胡塞尔说:
“我的这个中止的行为还存在着”。
[29]粗看起来,这与笛卡儿的经过怀疑过滤后只剩下确定的我思简直如出一辙。
但这只是看起来如此而已。
笛卡儿的我思是形式的、抽象的和平面的,因而只能作为一个现成的外在原则来运用(如据此引入上帝的存在和真理,再进而引入客观的自然云云)。
胡塞尔的我思或“本我思维”却不是任何平面的点,而是“幽暗的深渊”,活生生喷涌着的深渊,亦即“意向性”的深渊。
胡塞尔写到:
“对于现象学来说,通过对世界存在和非存在普遍实行的悬搁,我们事实上并没有简单地丢弃这个世界,而确确实实是把它作为我思对象保留了下来。
”[30]“即使我中止对感性信仰的证实,对房屋的感知仍然像我所体验它的那样,是对这个并且恰恰是这个房屋的感知······哪怕是错误的判断也是对这个或那个被意指的实事状态的判断意指,如此等等。
我作为自我生活于其中的意识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所谓的意向性,就是对某物的各种意识到。
”[31]在括去了世界之存在及其相关的经验信仰之后剩下来的我思,由于其意向性,亦即由于我思或意识本身始终已经是关于某种“对象”的我思或意识(无论这种“对象”存在与否以及如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