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歌的河流.docx
《一条歌的河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条歌的河流.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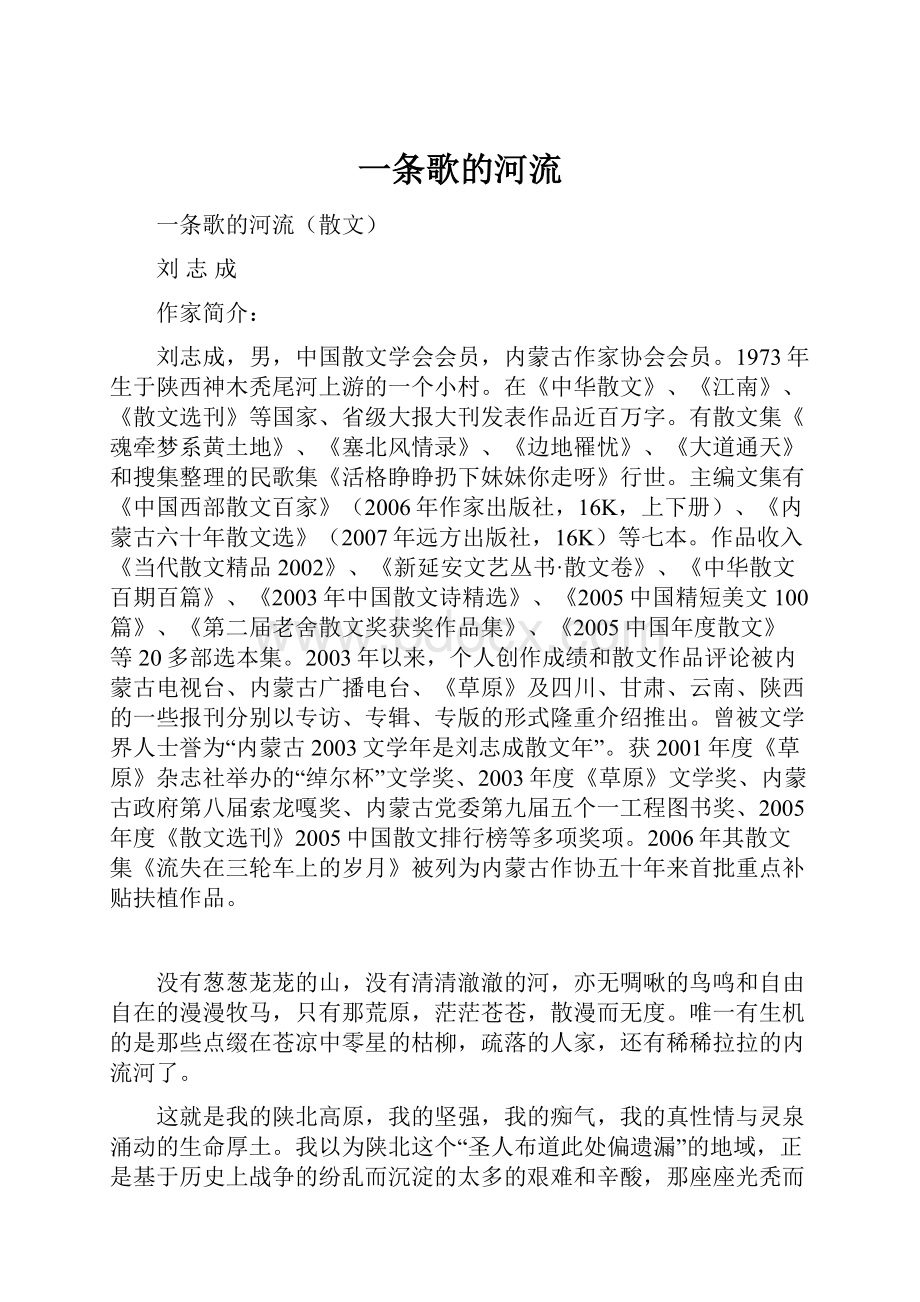
一条歌的河流
一条歌的河流(散文)
刘志成
作家简介:
刘志成,男,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
1973年生于陕西神木秃尾河上游的一个小村。
在《中华散文》、《江南》、《散文选刊》等国家、省级大报大刊发表作品近百万字。
有散文集《魂牵梦系黄土地》、《塞北风情录》、《边地罹忧》、《大道通天》和搜集整理的民歌集《活格睁睁扔下妹妹你走呀》行世。
主编文集有《中国西部散文百家》(2006年作家出版社,16K,上下册)、《内蒙古六十年散文选》(2007年远方出版社,16K)等七本。
作品收入《当代散文精品2002》、《新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中华散文百期百篇》、《2003年中国散文诗精选》、《2005中国精短美文100篇》、《第二届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集》、《2005中国年度散文》等20多部选本集。
2003年以来,个人创作成绩和散文作品评论被内蒙古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台、《草原》及四川、甘肃、云南、陕西的一些报刊分别以专访、专辑、专版的形式隆重介绍推出。
曾被文学界人士誉为“内蒙古2003文学年是刘志成散文年”。
获2001年度《草原》杂志社举办的“绰尔杯”文学奖、2003年度《草原》文学奖、内蒙古政府第八届索龙嘎奖、内蒙古党委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图书奖、2005年度《散文选刊》2005中国散文排行榜等多项奖项。
2006年其散文集《流失在三轮车上的岁月》被列为内蒙古作协五十年来首批重点补贴扶植作品。
没有葱葱茏茏的山,没有清清澈澈的河,亦无啁啾的鸟鸣和自由自在的漫漫牧马,只有那荒原,茫茫苍苍,散漫而无度。
唯一有生机的是那些点缀在苍凉中零星的枯柳,疏落的人家,还有稀稀拉拉的内流河了。
这就是我的陕北高原,我的坚强,我的痴气,我的真性情与灵泉涌动的生命厚土。
我以为陕北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域,正是基于历史上战争的纷乱而沉淀的太多的艰难和辛酸,那座座光秃而苦焦的丘梁,才揭开了令人心酸眼涩的丰厚辽远,耸起了触人肤热的文化骨架,为我们幸运地完成了一份万世的敬仰;那宛若军帐中的巾帼花木兰般美且刚烈的酒曲、和荡人心魂的野不溜溜山曲,才构成了陕北人精神的根基和记录陕北的一部浩瀚史诗。
陕北民歌生长的过程,就是高梁、糜谷们成熟的过程,它长在河洼洼,崖畔畔;长在陕北人的骨髓里。
它饱含了粮食的精华和泥土的芳香。
如果没有这些质朴无华的“音乐文学”,陕北高原浑厚的生命况味就会顿失光色,陕北人在精神田园里的耕耘就会付出更多的眼泪和心血。
我翻过有关陕北地域的各种文献,查知远在上古时的陕北,曾是一个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茂密、河流湖泊星罗棋布的地方,适宜于远古的人类居住、狩猎、采集和发展农耕。
到了公元前五至三世纪,这里先后出现了荤粥、鬼方、猃狁、默和戍、狄的氏族与部落。
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不但继承了无定河、孤山川河流域积淀下来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精髓,而且汲取了中原文化的醇厚、晋文化的精细、北方草原文化的豪放,使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成了独特的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
同时,这些氏族与部落,为扩张自己的领域,在殊死的拼杀与掠夺中,战胜者和战败者同存活了下来,并再塑出一个新的形态(这个形态也就是文化上的交融)。
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粗犷、古朴、浑厚与执着的独特文化,放射出了璀灿煊目的光彩。
公元前215年,一统六国的秦始皇为了加固他的大秦帝业,令大将蒙恬帅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失土“河南地”(今鄂尔多斯、陕北一带)。
匈奴在秦军强大的攻势下,节节败退。
秦就在匈奴的弃地设置郡县,并把中原,山西一带的民众迁移到河南地屯垦。
公元前121年,西域龟兹国归附,汉武帝迁共部族降众定居榆林一带,并在其古城滩置“属国都尉”治所。
公元前119年,“冬关东贫民徙陕西、北地、西河、上郡(今榆林一带)、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同时安置了归附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降众军屯。
公元前111年,汉庭令“上郡、朔方、西河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公元419年,攻下长安的大夏赫连氏强令一批被俘的所谓吴人定居统万城。
公元764年,唐朝将归附的党项族拓跋朝光部迁至银州(今陕北米脂县西北)、夏州(今陕北横山县西)东部居住,号平夏部。
公元1472年至1501年,明朝先后从云南、两广、福建、浙江等地清解“不服水土不肯去实边”军人和“情重罪囚”至陕北榆林一带屯垦;同时还从陕西西安、潼关、山西蒲洲、河南南阳、颖上直隶宁山抽调“轮班官军”驻守拓荒。
合上陕北触目惊心的历史巨卷,我们就会不难想到当时那些内迁来的军民,因思念故土,常邀三五好友把酒弄弦浇愁;不难想到他们将故里的“丝竹韵音”同本地在战争中孕育的豪放、率直的音乐相融合,从而唱出了一支在华夏史上独树一帜的歌。
就在那种苦难、苍凉的环境里,陕北酒曲才越来越生活艺术化,逐渐完璧无瑕成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的至纯至美:
芦花公鸡窗台台上卧
不图喝酒图红火
酒曲曲出在心里头
抖搭上几声声解忧愁
词平句淡,至纯至美的味儿会在哪里呢?
我之所以这样说这首酒曲,源自老家一个牧羊老汉的歌声。
老人老伴去世早,一个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也成了植物人。
老人后半生都在远离村子二十里地的沙地牧羊,通年难得见上上一个人。
那年,我的一个堂哥结婚,抽空回来赶亲事的老人的歌声嘶哑苍凉,像暴雨泻下岩石。
一屋划拳、嘻闹声全嘎然而止,都在静静地听。
当我穿过人丛的目光触到老人紫黑紫黑的脸庞时,我一下子愣住了.。
随即释然:
闷在心里的声音久了,爆发了能没有神性的能量吗?
而没有苦难浸泡,陕北酒曲会不会像割下来的韭菜渐至……变黄?
凝视着老人浑浊的目光,咀嚼着老人如苦瓜一样清肝润肺的歌声,我心里有一股难以抑止的酸楚在升起……
另一方面,陕北高原温差极大,素有“早晨皮袄手套,中午汗衫草帽,下午风镜口罩”那种蓄满无奈的愁苦之说。
春漫来时,风也多了,时而大了起来,在沙尘漫天频卷之后,瓷了眼了吧,大而灰蒙蒙的高原准会浮出一腔触目心惊的惨痛:
稼根裸露的吹蚀区不再是绿意的流动,禾苗埋没的堆积区也残忍地堆砌出一种粗拙的不屈。
十年九旱的高原,在冰雹蹂躏的肿胖不瓷里在寒流四月八还能冻死黑豆荚的恶劣气候里昭示着大艰难与大魅力的高原,因了这些自然因子,农作物的收成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人们只能悲苦地在一种颗粒无多的年景中剪熬。
面对泪水浸泡的日子,压抑的高原人为融解心中的圪圪瘩瘩,喝酒、放歌便成了医治神经痛楚的麻醉剂。
1996年,我在横山党岔采风。
当我听到离乡政府三十地有一个唱民歌的光棍老人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借了辆自行车一个人晃晃悠悠地骑着去了。
在老人家门口,我听见屋内嘻嘻嚷嚷,好像……正在举行宴席。
我迟疑了一下,正想敲门,有撩人的酒曲飘了出来:
安下桌子乌木呀儿红
捕来的野物味儿醇
怀抱上琵琶手抓上筝
抖起嗓子听的也是音
金盅儿斟满了竹叶青
咱放宽个心红火到大天明
那声音像山泉在岩石上淌过。
像彩蝶在花朵上翩翩。
聆听着歌声的我,忘了敲门,只觉得那歌要流进心里来。
后来进屋,发现老人是一个自娱,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半天怔怔地呆看着老人,忘了说话。
当我的思绪……触摸到遥远岁月里那悲惨的血痕和郁垒的压抑时,心被绞疼了。
我以为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才使酒曲成了先辈们苦中作乐的精神慰藉。
也许,从祖先们沙哑的嗓子里流出来的那些音符,已被残酷无情的时间给剥蚀了,可剥蚀不了陕北人那种特有的苦难情结,和子息们灵魂的净化、升华。
与现实中澎涨的欲望无缘的我渴望这种悲风千里,苦情汹涌的无奈。
我觉得只有陕北高原的荒凉、沉闷才能容得下自己一颗骚动的灵魂。
……朋友,倘若你农闲季节到陕北做客,主人会摆出丰盛的茶饭,热情地招待你,陪你大碗地喝酒。
酒至半酣,说不定谁就会杀出来这么一段助兴:
野地萝卜辣得也是葱
黄叶白菜过了时辰
人说是小葱韭菜生得也是俊
黄瓜菜绕球眼昏
芫荽菜桌儿上抖起精神
请起亲亲连喝三盅
先喝三杯竹叶青
再喝三杯状元红
人说是烧黄二酒生得也是俊
葡萄酒绕球眼昏
熏黄酒盅儿里抖起精神
请起亲亲连喝三盅
这宛如清笛悠扬、又似黄钟轰鸣的曲子,在一定程度上溶入了江浙文化的灵秀,也渗透着河套文化的粗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制。
陕北人唱酒曲,为使吐字行腔,气息控制流畅,增加曲儿的音乐色彩和力量,喜欢在曲中随口加一些诸如“哎哟”,“呼嗨”,“那个”之类的衬词。
有一年,我在靖边农村陡然听一个老汉唱这首酒曲时,猝不及防地被击中了。
老汉唱时,酒曲中的装饰音一律用“呀”来代替。
行腔润色因了这个“呀”字宛转回旋,舒展开阔。
每一声“呀”字捎带出来,咏唱速度就缓慢下来,像是朗诵在抒情,又像是心情激荡,紧张,激动情绪全含在了一个“呀”字上,一个“呀”字贯穿始终,整个曲儿因之而恬静含蓄,热烈奔放,音乐形象更加鲜明。
像春风拂过冻土,又像是泉水叮咚山涧,让我怔怔地在一种回味无穷的音乐圆润里长时间拔不出来。
为了破译那千回百转的艺术秘码,多年来,我常常一个人有意无意地将那些歌子哼出来,妄图抓住融化过我、消解过我的激越,但怎么也进不了那种如轻风掠过在心湖掀起千万层白花花细浪的感觉。
后来,我才明白,酒曲其实是一种心情的渲泄,只有恣意地唱,才能倍感舒畅。
对于主人殷殷地劝酒,你只有端起碗一饮而尽。
几碗下肚,老乡们的酒歌也多起来了,又是什么“烧酒本是糜子水,喝在肚里养身体”,又是什么“羊羔羔吃奶双膝跪,我想和朋友碰杯杯”,这曲不迷人人自迷,调不醉人人自醉,韵如阳春白雪,境似高山流水,听得你犹如肺腑里注入了一汪纯美甘泉,余韵回荡。
倘有主人的男亲家在场,这摊场会越发地热闹。
泼辣的女主人傍了亲家,白嫩嫩的绵手手端起酒盅,抛个馋人的媚眼,向亲家递去。
亲家乘势将手一捏,喜滋滋地说要听亲家老婆的奴声气呢。
女主人不免耳热心跳,面起桃红,有心戏亲家几句,可儿女在身边呢,只得故作一本正经地嗲声嗲气唱了起来:
初五十五二十五
姐弟二人磨豆腐
磨的豆腐稀糊糊
这盅盅烧酒洗屁股
静听着这意趣横生的酒歌,朋友,你的神经因长途奔波虽未松驰下来,但你的心神,你的情感,你的整个精神世界和灵魂,似乎注入了无穷无尽的欢乐。
对你的猜想,其实还不如说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不理解我怎么就叫它牢牢吸住了,仿佛自己就是一句清俊的歌词,在做一个甜蜜的梦……有时几天里听不到这种歌声,我只会觉得清寂的很。
而我们现在听到的酒曲,历经久远年代的浸泡,变得更加醇厚了,它已由单唱发展到了对唱,由围绕酒的圈子发展到了不拘格式和体裁:
什么人四岁把梨让
什么人七岁称大象
什么人十二当宰相
什么人十二领兵将
孔融四岁把梨让
曹冲七岁称大象
甘罗十二当宰相
周瑜十二领兵将
这虽是一首由古代聪明儿童的事例编成的对唱酒曲,但也渲泄出陕北人决心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远大抱负,张扬出他们骨子里内在的人性色彩与神秘无边的生命张力。
我以为这种宣泄生命的勇毅,把岁月的苦寒织成了一种扶阳正气的温暖。
它是粗犷的,像汹涌的江河激情张扬,有一种撄动人心的洒脱。
我的声音中……虽然缺乏这种亢奋,但我不会因此而自卑得低声下气。
如果还有什么积攒下的事情要我做,那就是弄清这片土地的全部。
土地的事情就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一个人默默地干下去,不因孤独而放弃,使我的孩子的声音中也缺乏这种亢奋……
我们再听听气韵同样宛然天成,可意味却相当隽永的另一类酒曲吧:
什么上来一点红
什么上来像弯弓
什么上来成双对
什么遮球了个黑洞洞
太阳上来一点红
月亮上来像弯弓
织牛星上来成双对
乌云遮球了个黑洞洞
这是陕北人对自然界丰富经验的累积,仅这足可窥见陕北人心细如发的脾性了,也更能体现酒曲是陕北人不可或缺、不可分离的一份精神食粮,那里面渗透着他们的泪水与汗水。
他们在它的透明中浸泡了自己,酿造了劳动的芬芳。
它在他们的生命里像瓷砖、钢筋、水泥装饰城市一样洗去了大自然的冷峻,让他们在凄风苦雨的攀援里回归宁静,扎稳了自己的脚跟,促成这块土地上盛产的软糜子般柔韧的性格,用玉米面酿做的黄酒般恬美的情怀。
那一年,我去神木县西部一个名叫大保当的小镇采风。
酒摊场上,主人唱了这首酒曲要我对,那天,恰主人的拜识也在场,他拿过烧酒盅子斟满接上茬口,趁机谑浪了一回:
小妹子嘴唇一点红
细细的眉毛像弯弓
年轻轻男女成双对
红缎被子遮球了个黑洞洞
那时……我的心情被调动起来了。
借着酒劲,我跟着主人忘情地唱。
第二天,那家女主人,说我那夜醉得手舞足蹈地吼喊着不睡。
而我清楚我很清醒,我是用歌声把平日里淤积在心头的压抑吐净。
这个情节,我一直无法忘掉。
我清楚在乌烟瘴气的现代都市里,这种回味是使我平静下来的唯一慰藉……
“酒曲曲好比没梁梁的斗,装在咱的心里出在咱的口”,像这样的酒曲,在陕北是随处可以听到的,即使有三五个大出版社整理,也出版不完。
它优美的旋律,精妙率真的语言,个中情味的真挚朴拙,意境的高远雄浑,无不令人心弦上紧,沉浸难拔。
古人有“三月不知肉味”词表达人沉溺于艺术氛围中的感受,我虽不能用准确的词形容,但我知道我能听到这些原汁原味的歌就足够了。
时间虽淘汰了一些酒词,但并未淘汰了它的精华。
它是父辈们用老镢头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不朽史诗。
它的痛苦欢乐都是酒,都是精血和元气,都是从水中酿浸的高梁、麦子的毛孔中飞翔出来的唐诗宋词,和柔韧而刚强的民俗民风文化作坊。
当你……刚从醉人的酒曲里醒来,朋友,你又会被那酸不溜溜甜格丝丝的山曲所勾去。
山曲就是信天游,信信然然地唱,环环复复地飘。
这种悦人的山歌,同酒曲一样,起先也与军队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载:
“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亢)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
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余在鄜延(今陕北甘泉、富县及洛川一带)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
”可见,它根植在陕北人繁衍的茫茫黄土高原之上,历经了历代人民精心的施肥,才长成了今天这种风格独特的民乐奇葩。
它是特别孤独的古典五言、七言诗,很吻合这个多山地域的大空旷。
或许因润了迭词、慕拟词、衬词等,它让人感到亲切的很,为那股泥土气息的芳香陡添激动,心时常浸在至纯至真的大山情调里平伏不下来;或许因长了赋、比、兴和连锁、双关、反复等一根根沟通人心灵回归纯朴的肋骨,它让人痴迷在朴素的风土人情里,感受到一颗颗无助的心灵,对着最亲近的大山,把自己全部交给民歌,抒发闷在胸腔里的那种凝重的悲凉和激愤;或许是因渗了乐府调的韵脚,并不用或少用角音(mi),那种悲怆的令人流泪的声音,在疾徐有致的节奏里,跳跃着一种旷世的痛苦和柔情,令人不能抑制地总想跟着抖两嗓子哪怕是跑调的音腔。
充满浓酽酽生活气息的陕北民歌,以物托情,以情赋声,高亢地张扬出艺术的雄浑热烈,沟通了无数寻找真实与纯净的心灵。
它浓浓的野味,给人的感觉不是粗俗,不会听上几遍就觉得厌烦,相反是一种永远滋养精神的艺术享受。
它只有在老实巴结的陕北人的嗓子里扎根,才能疯狂激荡地旋出一个真切悠远的艺术世界。
他们心头有爱,心底有伤,苦处唱它甜处唱它,也难表述尽他们的万千情意。
一旦……唱起来,他们往往溶溶忘我,进入天人合一要死要活的境界,令听者为之心动神摇,血澎脉涨。
余音袅袅,绕心三日。
文友马丽华在《走过西藏》序言中说:
“我之所以热衷于牧区,藏北,正是基于对那种游牧生活已往全然无知。
”我知道我不是,我的血管里流淌着陕北民歌的血浆。
我是从《东方红》里逃出来的那一句(我不知道那一时期像刘姥姥在大观园吟得诗一样纯朴、自然的陕北民歌一下子萎缩,刮起这样一股赤色的风,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悲哀和残酷)。
是由村落延伸的鬼神境界里属于激情的压抑的那一句,是合于天道,融于自然的那一句。
多少年了,每听到那些像黄土一样朴素的歌,我的灵魂就被那种神性的精神硬度给紧紧拽住——
你……听一听山坡上的蒿草丛里亦或河边的柳树林中飘漾出的一声声甜美的情歌吧:
阳婆婆出来照西墙
爱妹妹的心思一肚肚装
手拿上刀刀磨石上处
你不信我就豁开肚
歌者是一个俊格丹丹的陕北后生。
他正面对着朝阳,真诚地以生命的力量,喷射出心海里恒久、炽烈的爱火,真心真意地去煨热姑娘的芳心。
但正是这种“青杨柳树活剥皮,掏出良心爱妹妹”的感情冲动,才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陕北人那种“荞面咯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郎情妹意一辈辈,枪子儿穿心不后悔”的情爱自由性与神圣性。
我在商风熏人的城市里,就是用粗犷的信天游在一个酒摊场上挽住了我的梅。
如果没有歌声,我恐怕永远也走不进她的世界。
从此,我看到了那些音符的能量,把孤独逼出了门外,剪雪成诗……我由此而失去了衰老的理由……
小伙子大胆而爽朗的土性性歌声,也许,像我一样说不准就煨热了哪一个暗害相思的姑娘的心。
急骤而来的兴奋令她几乎昏眩,甚至连周围美丽的旷野也吞噬了。
她……抿了抿额前垂下来的几缕秀发,随之那甜丝丝、沙悠悠的音符便振荡在空旷里:
纸糊顶棚苇子绑
我也时常把你想
既想就该来
单怕我娘嚷
这些陕北姑娘们意真情实的风流野唱,系紧了男人们那颗沉甸甸的“撂下村村撂不下人”的心,使他们在这块穷困潦倒的土地上,躬耕不止,繁衍不息。
对于我来说,跑出那块盛产爱情的土地,当初孤单地站在远处眺望那些“心里有谁就有谁,哪怕狗日的跑断腿”的陕北姑娘,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让裆里的家什闲置着,真是太可惜了。
我年轻的时候,那东西肯定给面子,让人自豪不已。
到我老了,它就不肯巴结了,开始欺侮没力气的我。
从那块板结的土地上逃出来,我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哦,朋友,若说这些抒发爱恨情缘的山歌,是陕北人满腔澎湃热血酿成的甘冽的艺术之酒,那么,以独具时空的意念和心襟穿越历史迷雾的歌词,则流淌着“大江东去浪滔尽”的万丈豪情,流淌着“怒发冲冠”的悲壮美,流淌着一种能令人听之而心境拓展的无岸宽适:
杨家那个父子哟英雄将
一口刀来哪七杆杆枪
北国里有个天庆王
金沙滩前哪哈哟呀摆战场
锣鼓那齐不隆咚咣咣咣
旌旗那花花一花扬
得球得球那哈一咳忙
七郎催马哟大战那个瘟韩昌
透过这些山曲的神狂气荡,仿佛一下子又将历史拉回了那血光剑影弥漫的岁月。
这些声音告诉了我许多年前的那股渗在生活里的血腥……告诉了我什么比什么更有价值。
虽然悲愤的呐喊声已渗在了越来越远的时空里,但斩不断我敬仰的目光。
我曾绕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山峁峁,沟沟洼洼,倾听过这些声音,它虽然抽得人永远心痛……但我还是要走进去……
当然,情感质朴、乡土气息浓郁的信天游,除了风韵袭人,听之如品美酒香茗而舌苔流涎,除了具有历史、文学、美学的研究价值,对高原人还有“阴沟里的冷泉黄河里的水,人不讲义气不如个鬼”,“水由人改树由人栽,丰收全靠劳动来”的精神、思想方面的浸润,就像唐人吴道子的名画《地狱变相》的传神,令当时京都屠夫改行另谋生计,自有一种撩人心动的魅力:
歇时平地歇,不要靠崖头,恐怕崖头倒,压你崖里头。
过河坐船舱,不要坐船头,恐怕风摆浪,闪在河里头。
这是一个新婚妻子对走西口的丈夫生离死别时的痛苦叮嘱。
我最初对这首《走西口》的认识很肤浅,以为歌子只是渲染了陕北女人丝丝缕缕的深情和牵挂。
对它真正认识是从一个足可以做我祖母的陕北女人流泪的声音里开始的。
当时,我突然捕捉到从蔫蔫的快要旱死的糜地里飘出的悲苦的音符时,我吃了一惊。
当我看见穿得补丁摞补丁的老人顶着毒辣辣的日头流着泪锄地时,我的心口一痛,掂出了老人泪蛋蛋后面隐藏的是什么。
那首歌是我听过的歌声中最凝重的一首。
从那一刻起,我才知道它不是一般的情歌,它不仅表达了陕北女人对朦胧的陌生的远方的惧怕和向往,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荒睡时无法抵挡孤寂的另一种恐慌:
家园的荒芜,尚能和男人共同承受,夜晚的荒芜,一个人堵在心里,又有谁来分担呢?
年轻的时候,那种激情的把夜晚收拾的水灵嫩秀的尖叫和呻吟正旺得很,人却要分开了。
老了,即使在一起,它也蔫了,夜晚除了尴尬和干燥,还会有什么呢?
雪花打墙冰盖房
露水夫妻不久长
白云照在茅粪坑
赌搏场上没好人
这是包涵做人的道德与精神气质范畴的一首山歌,它和那个酒肉穿肠的济公游戏风尘的济世妙方有异曲同工之妙,一箭双雕地既起到传唱娱乐,又为人们荒芜的心田拔除了杂草。
更重要的是它在探示和涵盖陕北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背后,深力度地描述、揭示了陕北人重义、重情、敢作敢为、行事大器的心理、精神、性格、人格方面的磅礴大气。
这一类的山歌……既融进了哲学的辩证思考,又是祖先们另一种方式的现身说法。
它经历了时间大火的锻烧,才向我们留下了今天刚柔相济的利落老辣。
我虽远离了……这种陈列在岁月里的神性硬度,但还有一些金属的刚气泛涌在心里。
而我的孩子,失去这块土壤之后,能否抵挡得住城市里物欲横流的诱惑呢?
我真是担心极了。
而最激动人心的山歌,还当数陕北人在与民歌的对舞中找到自己旋转飘曳的影子时的那像长风一样悠远火焰一样炽热的乐曲:
正月里闹元霄,村子里好热闹,
龙灯狮子跑呀,水船后面摇。
船里边坐得二袅袅,实实生得好。
是啊,陕北人将原生、超卓之特质,朴素、清新之诗风的山歌,作为返现、完善、发展他们自己的源泉,凭着一种忍辱负重但又狂草人生的豪气傲气,在几千年后的今天,终于找到了自己旋转、飘曳的影子,找到了自己流浪的支点和这个竞争年代里对知识、思维、意志、技能、感情等方面综合竞争的坚硬与冷酷,挺起了胸膛站直了腰。
此时此刻,子孙们能不敞开胸怀,自豪地吆吆喝喝“三月三的茵陈通鼻鼻香,六月六的曲曲顺心心凉”吗?
我当初是担心让一把镢头一张铁锨的事情覆埋了一生,才逃出故土的。
可在漠然的人流中,我孤独的旗帜并未飘成什么呼啦啦的风景,吸引了什么人。
我清楚我的孤寂不适合城市与人群,只配点缀那些盛产空旷与荒凉的原野。
我虽走出了故土,但把梦永远留下了。
我明白接受苦难是心气旷达的最好决择,可我已被生活中的另一些事情永远缠住了……即使回归了那块被人改变了的土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力气拿得动生锈的铧犁去复活根的葱茏?
是否还能找到相依相随过的唢呐悲奏出大地曾经的叹息?
许多年来,我在这些歌子里穿行,揣摩着它在壮美或悲怆里所引燃的浩瀚与纯净的艺术之光,心里是一种说不出的激奋与感动,甚至梦中也萦绕着它被高山被历史孤立的生命诗性,它在现实泪影里燃烧的理想欲望和永恒的精神意念,它在大空旷大摧毁的物质世界里舐着我们的熊熊热度。
那苦难中涌动的不屈,以致我在哼着它时,不会为自已独守清贫的精神阵地感到后悔,就如冬天里围着火炉时,我们的身体不会感到寒意逼人。
我觉得每一首酒曲就是陕北人生活的一剂调味品!
每一首山曲就是生活贫困、精神富有的陕北人的一种独嘲自娱、大乐大欢的超然与人生态度之折射。
那优美的内涵,那诱人的内容,犹如陕北这块纯朴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沙打旺、沙竹一般,年年发芽年年疯长,绿油油、水嫩嫩。
它带着暴雨狂风的激越,人生的悲欢,在陕北人的口里久唱不衰,辈辈相传。
它的温暖裹紧了脚下这座绵绵的黄土高原的饥寒,它的精神支撑了一代又一代柔韧而强盛的生命。
它拍击时间的强音,已成为陕北高原之魂和当代人性灵的憩园。
记得是95年,我在神府煤田的一乡镇遇到了一位教英语的英国女孩。
她说,山隔峁阻的陕北对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但听听民歌,虽在异国,一个人一点也不觉得寂寞。
何偿不是呢?
我接触过很多时下流行的歌子,但那些刻意做作的音律对我确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痛苦。
每当苦闷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吟味起记忆里的那些原生的歌词,想放开嗓子抖出久违了的情愫。
每次坐在酒摊场上,我总要重温那渐去渐远的痴迷。
尽管我的粗燥沙哑的歌喉进不了陕北民歌的殿堂,但我依然唱得很投入,我不在乎“神经病”、“疯子”之类的雅号扣在头上。
美国记者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说:
“走向陕北,才看到一个真正的民族。
”而我想说的是:
就是这唱一声千般苦处,歌一句万种感慨的酒曲山曲,用它们史诗般的思索和记忆,在高亢而又飘逸的乐音中化作高原风,世世代代、年年月月、时时刻刻,搂抱着陕北破碎的山梁。
梳理着陕北的沟沟岔岔,把陕北的叹惜陕北的雄沉,刻在了陕北人的额头和心里。
但当我又一次走向陕北的山山峁峁,我发现陕北人的苦难在商品经济的炽热气焰中已走向了冷落。
历经了大艰难与大悲凉的陕北民歌最自由的飘弋和最响亮的吼唱也同这个世界越来越格格不入。
面对现实的物欲横流,它作着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