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史料陈丹雅走向有水的罗布泊父亲八十年前的敦煌之行.docx
《珍贵史料陈丹雅走向有水的罗布泊父亲八十年前的敦煌之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珍贵史料陈丹雅走向有水的罗布泊父亲八十年前的敦煌之行.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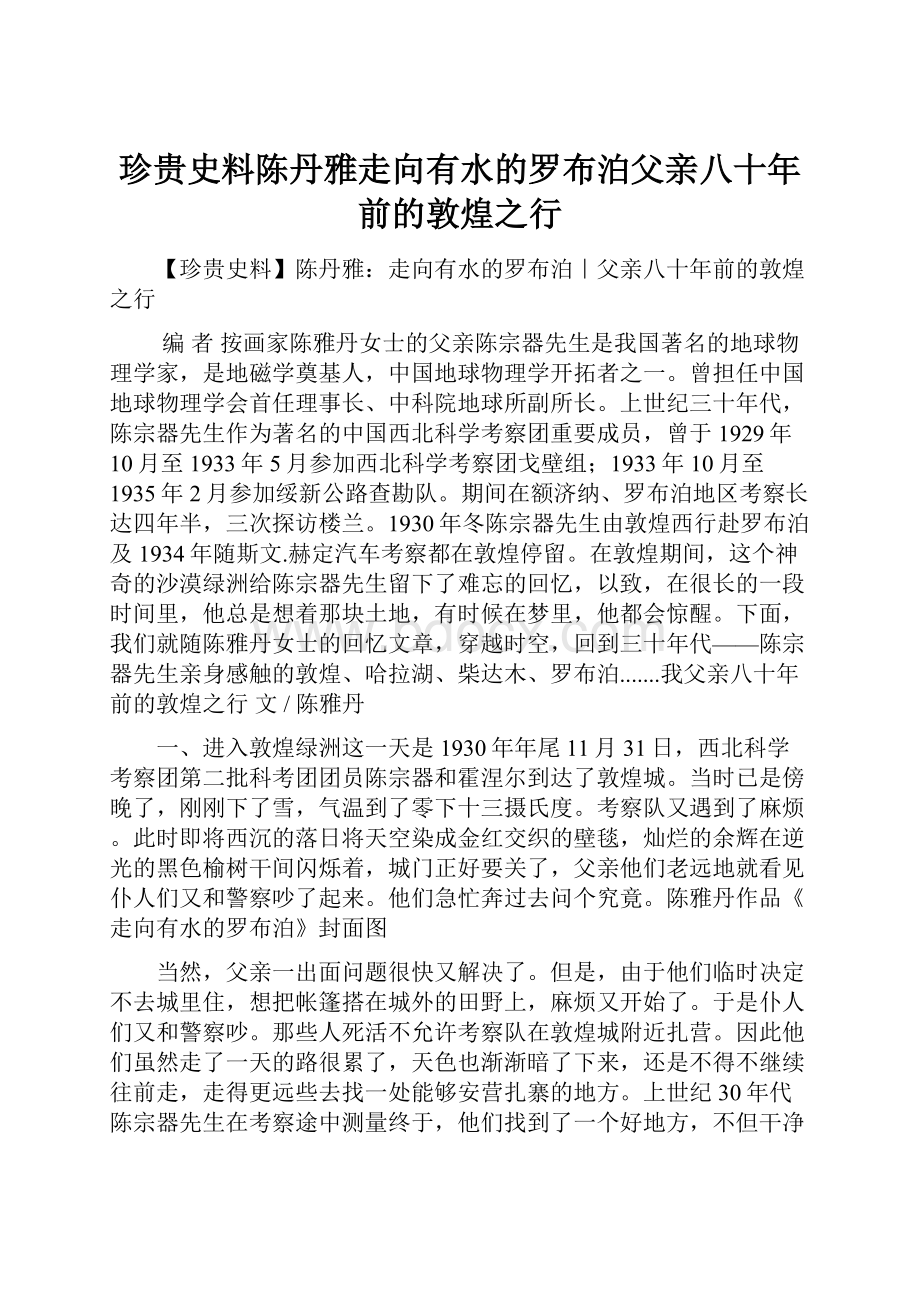
珍贵史料陈丹雅走向有水的罗布泊父亲八十年前的敦煌之行
【珍贵史料】陈丹雅:
走向有水的罗布泊|父亲八十年前的敦煌之行
编者按画家陈雅丹女士的父亲陈宗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是地磁学奠基人,中国地球物理学开拓者之一。
曾担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首任理事长、中科院地球所副所长。
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宗器先生作为著名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重要成员,曾于1929年10月至1933年5月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戈壁组;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参加绥新公路查勘队。
期间在额济纳、罗布泊地区考察长达四年半,三次探访楼兰。
1930年冬陈宗器先生由敦煌西行赴罗布泊及1934年随斯文.赫定汽车考察都在敦煌停留。
在敦煌期间,这个神奇的沙漠绿洲给陈宗器先生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以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总是想着那块土地,有时候在梦里,他都会惊醒。
下面,我们就随陈雅丹女士的回忆文章,穿越时空,回到三十年代——陈宗器先生亲身感触的敦煌、哈拉湖、柴达木、罗布泊.......我父亲八十年前的敦煌之行文/陈雅丹
一、进入敦煌绿洲这一天是1930年年尾11月31日,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二批科考团团员陈宗器和霍涅尔到达了敦煌城。
当时已是傍晚了,刚刚下了雪,气温到了零下十三摄氏度。
考察队又遇到了麻烦。
此时即将西沉的落日将天空染成金红交织的壁毯,灿烂的余辉在逆光的黑色榆树干间闪烁着,城门正好要关了,父亲他们老远地就看见仆人们又和警察吵了起来。
他们急忙奔过去问个究竟。
陈雅丹作品《走向有水的罗布泊》封面图
当然,父亲一出面问题很快又解决了。
但是,由于他们临时决定不去城里住,想把帐篷搭在城外的田野上,麻烦又开始了。
于是仆人们又和警察吵。
那些人死活不允许考察队在敦煌城附近扎营。
因此他们虽然走了一天的路很累了,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还是不得不继续往前走,走得更远些去找一处能够安营扎寨的地方。
上世纪30年代陈宗器先生在考察途中测量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不但干净而且背风,可是马上就有人跑过来喊着:
“不行!
不行!
这里撒过种子!
你们不能在这里起帐篷!
”他们只得继续往前走。
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地方,是一座打场用的场院。
主人很客气、很热情,看样子挺有钱。
他穿着丝绸的棉袄,黑色的拖到脚面的长袍,父亲和他交换了名片后,他便开始尽地主之谊忙活起来。
首先他吩咐家人给考察队送来了一捆柴火,给他们取暖,可是父亲他们习惯了晚上帐篷里不生火,于是忙把柴火送到厨师马色正在做饭的厨房去,但是,不一会又看见房子的主人亲手托着一个黄色的大铜盘,里面装了满满的烧得红红的碳送过来。
于是,许久没有生过火的帐篷开始暖和起来,父亲和霍涅尔感到好舒服,这是自入秋出发以来,第一个有火的晚上。
1934年陈宗器先生拍摄的莫高窟全景去敦煌城邮局取信的人,赶在城门关闭之前把信取回来了,父亲和霍涅尔很想马上能读到信。
要知道,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亲人一年多了,对于三十多岁血气方刚的他们,思念自己的妻子和未婚妻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是就连联系他们的惟一纽带——小小的一封信,也要采取留局待领的方式,等到他们终于走到“大”城市的时候才能去邮局领,还不知道会不会弄不好在邮路中丢失。
这不,离开酒泉半个多月了,好不容易可以看到信了,还得陪房屋的主人喝茶……雪后的夜色很美,茶很香,还有梨可以吃,父亲他们有很长时间没有吃过梨了,主人很愿意听他们讲很远很远地方的故事,也很喜欢讲自己的家乡敦煌的过去和现在,他谈到敦煌什么都有,五谷、家禽、牲畜、鸡蛋、素菜、水果什么都不缺,在这里过日子很舒服。
父亲翻译给霍涅尔听,从主人热情的款待和殷实的生活中,他们完全同意他所说的。
他们早就知道,敦煌虽是甘肃极靠西面的小县,而且出城南三公里便有沙山,然而耕地面积却达到三百平方公里之多,这全是因为党河水源丰富的缘故,这令敦煌成为嘉峪关外最富饶的地方,有着“关外桃源”的美誉。
上世纪30年代的敦煌城郊夜已经很深了,谈话还在进行。
霍涅尔礼貌的装着不经意的看了看表,已经过了晚上十二点了……12月份了,12月可是圣诞月呀,我那可爱的未婚妻会不会在信里寄来圣诞祝福呢?
霍涅尔不禁浮想连篇起来……真的,当他们回到帐篷,靠着暖融融的火盆,终于捧起那些使他们魂牵梦绕的信笺时,霍涅尔确实收到了真正的圣诞卡、圣诞信!
不过,那上面讲的是去年的圣诞节,因为信是1929年12月28日写的,而现在呢,已经是1930年12月1日了!
还有封电报也是从家乡乌布沙拉发来的,发信的日期是1929年5月,一年半他才收到!
想起来,自己离家已经很久了、很远了。
二、家书抵万金父亲何尝不急着看信呢!
他离家已经一年多了,离家时父母双亲已经年迈,妻子正怀着她的第二个孩子还没有生,怎不叫人深深想念。
可是眼下他正在热情的主人家做客,又要充当主角,又要给主人、霍涅尔当翻译,想看信,只好先忍忍了。
中国有句古语叫家书抵万金,这种感觉对于那时的父亲体会恐怕是最深的。
上世纪30年代敦煌城南门
为了防止信件的丢失,父亲给自己所有发出的信全都编了号,并要求家人的回信也要编上号。
从现在仅存的父亲进罗布泊前,1月7日至11月10日发出的编号十九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对妻子的思念:
“熙妹:
好冷落的人生!
满腔热情向谁诉?
我有两种幻想,想我爱人:
如果飞航能通,岂不甚好?
——7000里的行程,不要两天,我俩便可接吻了!
……'父亲当年正是因为家乡的种种压力才辞去新昌中学校长的职务,从家乡出走的。
当人们得知这位已经由母亲做媒包办娶了表妹靖为妻的青年,又和另一位新潮女子童在杭州正式结婚,并向前妻靖提出离婚时,这一大逆不道的举动,在家乡激起了不小的波澜,父亲的父亲和父亲的前妻靖为此还在报上发表过严正的声明。
1933陈宗器先生第一次考察归来,时年35岁虽然后来表妹在父亲与她沟通后终于同意离婚了,可是直至西北之行前这种种波澜正方兴未艾、尚未平息。
那时,父亲奔走于上海、南京、杭州,新婚的妻子则居住在绍兴一带,他们不得返回家乡,而且没有建立固定的居所。
也许是父亲考虑到当时的路途遥远,邮寄的信件极有可能丢失,于是他将全部信件编了号,这给我们后来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从编号中我们得知编号为二十三号的信,是父亲从罗布泊考察完毕胜利东返时,在途中发出的最早报平安的一封信,可惜已经找不见了。
另一封保存下来的第二十四号信,也是东返途中于1931年6月2日写的。
而中间的20-23日的四封十分珍贵的信件都非常可惜地丢失了!
这些信估计是父亲在11月14日离开酒泉时、在敦煌逗留期间、以及他们在61号营地时写的。
上世纪30年代敦煌街景
当父亲终于在罗布泊东返的归途中,距敦煌一百二十五公里的地方,收到专差从安西带回的信件时,他欣喜异常!
尽管这些信是半年或三个月前发出的迟来的消息,他却视为珍宝,因为他已经半年没有接到家人的片言只语了!
当他手捧妻子童寄来的萍儿和智儿的照片,简直爱不释手!
他回信给童说:
“很愉快地不知已细看了多少次”。
要是没有这些迟来的信件,真不知道父亲能不能支撑得这么久。
这些信是他与亲人交流的惟一途径,是他在荒野中心灵惟一的慰籍。
三、暂别敦煌12月5日父亲和霍涅尔各自给斯文·赫定发出了进入荒原前最后一封信。
父亲高兴地告诉赫定博士:
我们从酒泉到敦煌有一个愉快的旅行,现在我们即将做完各种必要的准备,立刻就要出发。
可是信发出后的第二天晚上,该带的东西还没有准备好,准备工作已经花去整整六天的时间,12月6日夜晚,他们还在忙碌。
再往西行就再也见不到人烟了,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考察途中,陈宗器先生牵着骆驼在沙漠上。
父亲他们担心骆驼会死在沙漠中,担心人吃的东西带得不够,因此他们在敦煌补充了五百公斤面粉和七百五十公斤豆子,还买了活羊。
仪器设备也得到了补充,否则到了荒天野地缺这少那可没处买。
他们还买了柴火,能带多少就带多少。
他们计划第二天一早就开始出发,因此这是劳累的一晚。
但是,好像越临近出发没做完的事越多。
月光洒满了冬日萧瑟的大地,天气很冷,望着仆人们正在吃力地往驮架上装载货物,院子里忙乱异常,父亲和霍涅尔意识到原来预计的准备时间太短了。
磨面粉和豆子需要很多的时间,只见那骡子围着磨盘整日里紧赶慢赶地走,还是有许多没磨的装着豆子、麦子的口袋堆在那里等着磨。
还有刚买的那八只羊,必须把它们看好、喂饱,他们计划一路上要赶着它们跟着大队走,如果路上没有羊吃的东西了,就把他们宰了,放在骆驼上留着慢慢吃。
1930甘肃西部绿洲的烽火台12月7号,天刚蒙蒙亮,考察队便忙碌起来,可是还是没能一大早就出发,那么多东西需要装,父亲让班彻在当地租来的驼队也不是很理想,价格太贵了,父亲发现这里面好象有问题,决定让另一个仆人马色去重新租骆驼,结果便宜了很多,只需出原来四分之一的价钱。
只是这十二峰骆驼看上去不是很强健,但是它们可以帮助父亲他们自己的二十三峰骆驼多分担些驮的东西,使自己的骆驼轻松一些,现在他们只留下班彻原来骑的那匹骆驼没装东西,准备在路上大家换着骑,别的骆驼全都装上了东西。
父亲和霍涅尔决定多用两天租来的骆驼,可驼队的主人却开始后悔,他似乎预感到从这本已荒凉的地方再向西去,恐怕是凶多吉少。
上世纪30年代敦煌街景而父亲他们深知,租来的驼队只是短期的帮忙,在以后漫长的探险时日里,真正与他们生死与共的只有他们自己的这二十三峰骆驼,必须好好的照料它们、为它们保存实力,否则它们会在沙漠里死去。
在沙漠里如果没了骆驼,他们自己也就别想活着出来。
准备工作忙忙碌碌又搞了一整天,加上骆驼和人又增加了,还需要协调,因此到这一天很晚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走。
他们将东西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带不了的就留在了敦煌,他们还计划在途径罗布荒原的东部时留下一部分东西,以备回来时物资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到那里进行补充。
临走,羊又不愿意走了,还有一只竟然逃跑啦。
大家满院子追着羊跑,眼看着这只机灵的羊冲出院子,一出溜钻进了不远处一座庙宇开着的门。
其他的主人家的羊凑热闹也跟着这头羊往庙里跑,这下可热闹啦,他们这群即将远行的人不得不耐着性子分辨哪一只羊是他们的,免得抓错了。
父亲和霍涅尔在一旁看着觉着好可笑,庙里,是个神圣的教导世人善良友爱的地方,而他们却一大群人死命追逐着一头可怜的小羊。
上世纪30年代敦煌城郊的一座寺庙
真正出发时已经是上午11点了。
这是一个比较暖和的好天,雪也化得差不多了。
天很蓝,没有一丝云彩,可以看到沙漠、逆时针打着旋的几米高的小旋风以及远方高高的白色的雪山。
这一天,他们赶了许多路。
他们的驼队出敦煌西门向西北偏西方向走了九公里之后,经过了最后一个村庄,开始踏上灰黑色细石组成的戈壁。
这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别了!
可爱的绿洲!
”父亲回头向最后的村落望了一眼,毅然勒了勒缰绳催着骆驼追赶着落日的余辉,驼道上扬起一阵细细的烟尘……戈壁的表面极软,一不小心偏离道路,便会陷下去一二尺。
要小心些,父亲不停地轻声告诫着自己。
“如果知道,这次远行要过半年才能看见人和人居住的房屋,那一天我们绝不会这样毫不在乎地离开这人、这房、这文明的世界……”霍涅尔多年后不无感慨的回忆道。
四、从敦煌去柴达木在罗布荒原完成考察后,7月5日父亲和霍涅尔回到敦煌,八个月来他们终于又回到了绿洲,见到了大片大片的湿润、丰满的绿。
原本听说甘西有穆斯林叛乱,他们还担心暂存在那位好客的农庄主家的笔记、地图、仪器受损,幸好一切安然无恙。
一到敦煌,他们便将辛苦劳碌的驼队遣往草原上去休养生息,他们自己则抓紧短暂的休整时间建起了一个简易的暗房,急不可耐的开始动手冲洗一路拍下的照片。
敦煌县城东门“迎恩门”牌坊(1907年斯坦因拍摄)
7月16日,父亲接连收到梅妹、云弟、前妻靖和梦旦校长的来信,他们详细地谈及父母双亲患病的情况。
不久弟弟、妹妹又发来了电报:
“母危速归”。
父亲得知后心里焦急万分,他不得不提笔给赫定博士写信,请求如果霍涅尔博士能够做得过来的话,请准许他回家看望重病在身的年迈父母。
当然,如果考察队的工作会因此拖延或中断,他则不做此想。
可是,此刻赫定团长远在瑞典,回信将遥遥无期,父亲只有耐心地等待。
衣服已经全部破烂不堪了,他们不得不请房东家的女主人帮忙补一补,可是她显然一向生活很粗糙,连袜子也纳不来,无奈的他们只好想出应急的办法:
自己动手用破衣服补破袜子,以便先凑合着使,等到了酒泉再去做新袄。
当然在酒泉这样落后的边远小城,所谓的“新袄”只不过是简陋的中式小褂罢了。
甘肃西部经过了叛乱很不平静,敦煌世外桃源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听说哈密一带正处于纷乱之中,所有的旅行商客都纷纷担心着旅途的安危。
但是父亲他们为了工作,并未因此迟疑片刻。
雪山
7月20日,他们启程赴南山,那正是父亲给赫定博士的信寄出后的第二天。
他们计划先和柏利一队会合,再翻越南山去柴达木盆地考察。
他们真的很有敬业精神,在罗布泊已经耗尽了精力,却不允许自己有片刻的休息。
他们乘驴马向山里进发,顿时觉得气候比平原凉爽了许多。
自荒凉的戈壁转向冰雪覆盖的高山,自然景象也有了许多的不同。
在碎石铺满的山沟行进,流水哗哗地从脚下响过,山沟的两侧时而绿树成阴,时而山体裸露,阳光越过山脊,不冷不热很舒服。
人们说大自然是可以给人疗伤的,一点也不错,在平和无言的大自然面前,父亲对父母的强烈思念之情稍稍平复了一些。
去南山陈宗器等骑骡马行进于祁连山中
8月中旬,他们来到南山一个叫铁匠沟的地方,与柏利一队会合,然后在山脚海拔两千七百米处扎营。
山的后面是党河,再往西很远的地方是敦煌莫高窟。
在这里,柏利发现了许多化石,霍涅尔则专注于研究从疏勒河带回的材料,父亲则按照霍涅尔的建议研究“雨水对土壤剥蚀的物理作用”,并抓紧时间计算孔雀河主流及支流的总流量。
不久,他们离开铁匠沟继续向南,考察队开始分为两队,柏利博士等赴托苏湖考察,父亲他们前往哈拉湖。
从这里开始父亲和霍涅尔将进入无人区。
他们顺着党河南山和洪古斯通山的峡谷朝东南方向走。
西北科考团团员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江南,这个季节只需穿毛衣就可以了,而这里晚间温度竟然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
但是冷对于吃惯了苦的父亲又算得了什么?
罗布泊又冷又饿的日子他都经历过了。
可这儿海拔高,一路上他们大多在海拔两千五百米至三千米的地方行走和工作,一开始很不习惯,父亲总觉得喘不上气,尤其是到了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地方,竟然一头倒在地上大喘不止,头痛得象要裂开,肺胞仿佛要被撕破!
要在地上喘上好一阵子,呼吸才能平缓下来。
可是那些随行的工役——当地的西藏人和那些牦牛,却在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奔跑着进退自如毫不费力,父亲真羡慕他们。
可是它们是从小生长在这里的呀,要在短时间内赶上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
渐渐地,父亲和霍涅尔掌握了高海拔反应的规律,将自己的动作放慢了节拍,这样一来就好多了。
那些西藏人穿着皮袄,却光着一只胳膊。
父亲一开始很是奇怪,但是不久他自己也体验到了,原来这里的气候变化不仅剧烈而且迅速,一天之内可以有四个季节。
在阳光下有如盛夏酷暑,要是云遮住了太阳,马上就会有秋冬的萧肃。
一次雨云袭来,雾笼罩下来将父亲他们团团围住,他们在又湿又冷的雾气中坚持前进,不一会儿下起了大雨,很快地,雨变成了雪……可是当他们湿淋淋冲出云雾抬头望去时,山顶却依然阳光灿烂。
父亲望着山坡上一道道深而无水的沟痕,知道它们正是刚才这种一过性的大雨冰雹削蚀而成的。
父亲测定的最高峰,有海拔六千三百米,大约在酒泉以南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
雪线高度则大约为五千三百米至五千五百米,这些山一到了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便是光秃秃的,山岩峥嵘陡峭,不长一棵树。
但是这里却有狼、青羊、野驴、野牦牛等野生动物出没。
1934陈宗器与赫定在额济纳木林河冰面上一路走去,可以看到不少终年积雪不消的冰山,不久他们向南面的洪古斯通山折去,气喘吁吁地爬上海拔五千米的高度,看见了天地苍茫一片的壮观的洪古斯通太立克冰山,这些冰山就象活化石,对它们的研究使得父亲他们对过去各个时代的气候变迁了如指掌。
到达哈拉湖已经是10月下旬了,这里早已下了一片白茫茫的大雪。
极目望去,雪峰苍茫,起伏绵延,像条条银色的巨龙横卧天宇。
站在因封冻而一片肃穆的哈拉湖旁,父亲的心境顿时变得清澈、豁达起来,他想到岁月的流失万物的枯荣,想到千万年来地质变迁的更替,对比之下生命是多么缈小与短暂啊,而这些亘古不变雄伟的山峦与湖泊却将永远地、无言地于天地间一直矗立下去……它们是多么的深沉、博大啊……陈雅丹大学时期木刻习作:
下乡锻炼
离开哈拉湖,越过哈拉湖西南海拔高达四千三百五十米的山口,他们折向北方,沿疏勒河谷,来到距哈拉湖约两百五十公里的昌马。
他们从昌马出山,告别了托来南山向东折去。
天气温暖了许多,然而心境却没有舒畅多少,因为逃往哈密的叛军已经返回,占据了关外的三个县,父亲他们从关外向关里走,一路上可真担了不少惊吓,好在只是虚惊一场,一行人总算平安到达了酒泉。
他们总结了一下,一年来所采集的地质、古生物、动植物等标本竟有六十箱。
于是派专人周涵生运往北平。
五、从东面进入罗布泊从东面进入罗布泊,开辟一条从敦煌至60泉的路是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乌鲁木齐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
一路上他曾问父亲、龚继成和尤寅照,不知道安西有没有足够的汽油?
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汽油,如果在安西弄不到油,他们别说去罗布泊,就是回家也不可能了。
可是真不敢相信,好事来得这么快,原来看着那么遥不可及,一下子变得唾手可得。
他们顺利地从上海欧亚航空公司那里搞到了油,而且航空公司答应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因为俄国人不愿意德国开辟这条航线,不允许他们的飞机飞越新疆与俄国的上空,所以航空公司自己要用上在安西储备的三千加仑油还早着哪!
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汽油,赫定、父亲这样一群百折不挠的人,虽然已经在艰辛困苦中走了整整一年的戈壁沙漠,现在,他们竟然又自己提出要再一次远行。
计划很快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但是由于60泉属于新疆地界,所以行动是保密的,甚至对乔格和艾非也保密,因为如果这事传出去,又会受到阻挠,新疆方面的这个盛世才他们可受够了!
因此对外,他们只说是去敦煌千佛洞。
1934年陈宗器先生拍摄的莫高窟中景实际上,父亲一直想去莫高窟千佛洞看看。
道路虽然很糟,但他们终于如愿以偿。
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虽然受到岁月无情的磨损,可是仍然挡不住光华四射的美艳。
一千八百个洞窟更显示出远古的开凿者们对信念无比的痴迷与追求。
这里汇集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处处闪烁着古代中华文明的光辉。
作为中国人,父亲深深地感到自豪,他举起相机拍下了全景和里面的壁画。
他想象着两千年前丝绸之路中道通畅时,这里一定富丽堂皇、热闹非凡。
而今,中道废弃了,人们选择了安西至哈密的北道,这使敦煌萧条了,安西繁华了。
现在他们的考察团将要试着恢复这条路,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
——要让敦煌重现昔日的辉煌!
陈雅丹为《藏经洞发现100周年藏书票》创作的敦煌壁画为主题的藏书票这一次,他们将选择比当年霍涅尔和父亲他们考察时更靠北的一条路,山间的石头路要比沙漠戈壁好走些。
他们很想找一名好的向导,但是所有的人都只知道两条路,一条从北面通往哈密,一条从南面通往若羌,从不知道有什么中间的路。
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找了一位,后来才知道是个贩大烟的走私者,经常穿行于山间小路。
11月8日,父亲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后,终于从敦煌出发了。
在斯台列尔的地图上,他们看到了有三条小路从敦煌通往哈密,在它们的西面还有一条路,那是赫定1901年绘在地图上的。
当时赫定带着驼队从吞格拉克库都克向北进入北山,一直走在北纬41度29分上,到了60泉。
虽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了,赫定博士仍清楚地记得沙丘没能阻挡住他的驼队,而且道路后来变得坚实好走起来。
车队离开了海拔一千零七十米的敦煌向北开去,渐渐离开了农庄,经过长满丰盛青草的牧场,开过干涸的疏勒河,再前行七公里便进入了软性的戈壁。
他们折向正北进入山口。
1930陈宗器的西行驼队
北山脚下的石板泉泉水甘甜味美,他们将水筒灌满,然后沿着一个个尖尖的石块堆成的路标朝着往北偏西的方向前进,翻过几个海拔一千八百米左右的隘口后,走上了一条狭窄的、见不到太阳、林阴道般的山谷。
雪花竟在太阳下扬扬洒洒地开始飞落,阳光中就像许多跳着舞的银色精灵。
父亲禁不住把手伸到车外,让几片雪花落在手上,再慢慢地融化……
“冬天来了。
”父亲他想,“这是我第六个冬天了。
”经过明水(不是哈密附近的明水,是重名),他们又翻过一座隘口,来到了水源极畅的马连井,建立了122号营地。
风越刮越大,小雪变成了暴风雪,扑打着车窗。
他们发现他们走的路离哈密至安西的公路仅六十公里。
11月12日,夜间气温降到了零下十点一摄氏度,汽车离开了去哈密的大道,穿过山谷向西北西方向行进。
已经没有路了……他们走上了自寻道路的探险旅程。
经过高低不平的十三公里原野后,他们发现了一条自东南向西北的小道。
骑骆驼的陈宗器先生第二天,父亲他们发现路边山上有一些带枪的形迹可疑的人,看样子是埋伏着准备伏击小车的,可是当他们看见又一辆卡车开来时,马上吓得甩掉皮大衣就跑,而其中有三个人好像没反应过来,仍旧呆呆地蹲在那儿。
赫定博士命令停车,他把他们叫到跟前,进行了盘问,又乘机询问了向西的路,但是他们说,超过一天路程以西的地方他们从来没去过。
到晚上,那个响导才不安地告诉他们,那几个人是有名的土匪,他本人就曾遭到过他们的袭击,当时抢走了他所有的货物。
过了骆驼井,他们发现道路向西偏南延伸,变得坚实而平坦。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父亲打开手电照着指南针继续测量着行车路线的方位。
这一天他们走了六十公里,建立了124号营地。
他们发现这几天路不好,汽油用得很费,一加仑汽油才走三公里。
于是他们在124营地埋藏了三十五加仑油,留着回来时用。
第二天,他们来到了一个峪谷的终端,走出峡谷很远以后,他们来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沙丘,原来,这就是父亲他们几年前见过的三陇沙向东北延伸的部分,是世界上最荒凉的沙漠之一——噶顺戈壁。
向西的道路又一次被切断,他们只得调头。
现在,他们必须寻找到汽车可以行走的通往罗布泊的路,他们继续向西、向南,总想绕过沙漠,却因为地面太软而失败。
他们只好返回骆驼井建立了126号营地。
这天,赫定和尤寅照再次乘小车向南面的山驶去,整整一天,还是没有找到路,崖壁间的间隙太窄,小车过不去。
晚上,赫定与父亲他们再次仔细地研究了地图,反复测量了安西到60泉的距离,发现北边西部山区除了赫定1901年标的那条线,在地图上几乎是一片空白。
这时候,油不多了,赫定决定让尤寅照带几个人开卡车回安西去搞油,大伙则在骆驼井等。
这个荒僻的地方过去除了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助手探险家罗勃罗夫斯基,没有别的西方人来过,而再往西,除了赫定就再没有第二个人去过,万一尤的车坏在了路上无法前来,他们就不能再向西了,必须立即回去救人。
一想到此,大家都十分担心。
等待真的很痛苦,需要有坚韧的心理承受力太阳一下山,气温立即下降,夜间是零下十八摄氏度。
父亲和赫定、龚继成照旧住一个帐篷,在无边寂静与寂寞的包围下,他们又一次在炉火边开始研究地图、计算距离。
陈宗器和龚继成1933.年12月中旬在绥远乌尼乌苏19日是个好天气,父亲和龚继成带上乔木查又一次出发,翻过南面的小丘去找路,他们向南走了八十公里,发现车可以继续开过去。
21日,按规定尤寅照该回来了,可是傍晚了还不见踪影。
就在大家都有了更焦急的担心的时刻,忽然父亲喊起来:
“汽车!
”他们终于按时回来了,而且带来了惊人的新闻:
新疆又开始了战争,东部的维吾尔人起义了。
大家庆幸在这之前及时逃离了新疆。
尤又说东干部队的一个师正向西朝安西、新疆移动,万一回去时碰上,那可太糟了,他们将再一次失去汽车……这些消息让父亲他们用一天时间讨论着下一步的行动。
26日,龚继成再一次出发,他将进行一次重要的勘察,气温在夜间已经降到零下二十三点八摄氏度了,在外边站一会儿刺骨的寒风就会把人冻僵。
大家呆着等消息没事干,只有父亲却忙个不停,他一会儿计算地图上的距离,一会儿进行气象观测,一分钟也不得安闲。
赫定博士则在一旁整理笔记,他也总是这样不得安闲。
28日清晨五点钟,赫定被汽车的马达声惊醒,他立刻叫醒了父亲,点燃了灯,立即看清是尤寅照和艾菲。
原来他们去看了乔格坏在半路的车后,直接去安西办事,现在又赶回来了。
11月30日,龚派仆人捎来了信,说又向西南走了一百五十公里,而且在继续向西越过一处难走的盆地后竟然还挖出了水,他们将它命名“龚井”,现在龚和三娃子在那里等候着大队跟上去。
12月1日中午父亲他们再次整装出发,沿着龚的路线边走边测量着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