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哲学系与四川大学哲学系同仁学术座谈纪要.docx
《中山大学哲学系与四川大学哲学系同仁学术座谈纪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山大学哲学系与四川大学哲学系同仁学术座谈纪要.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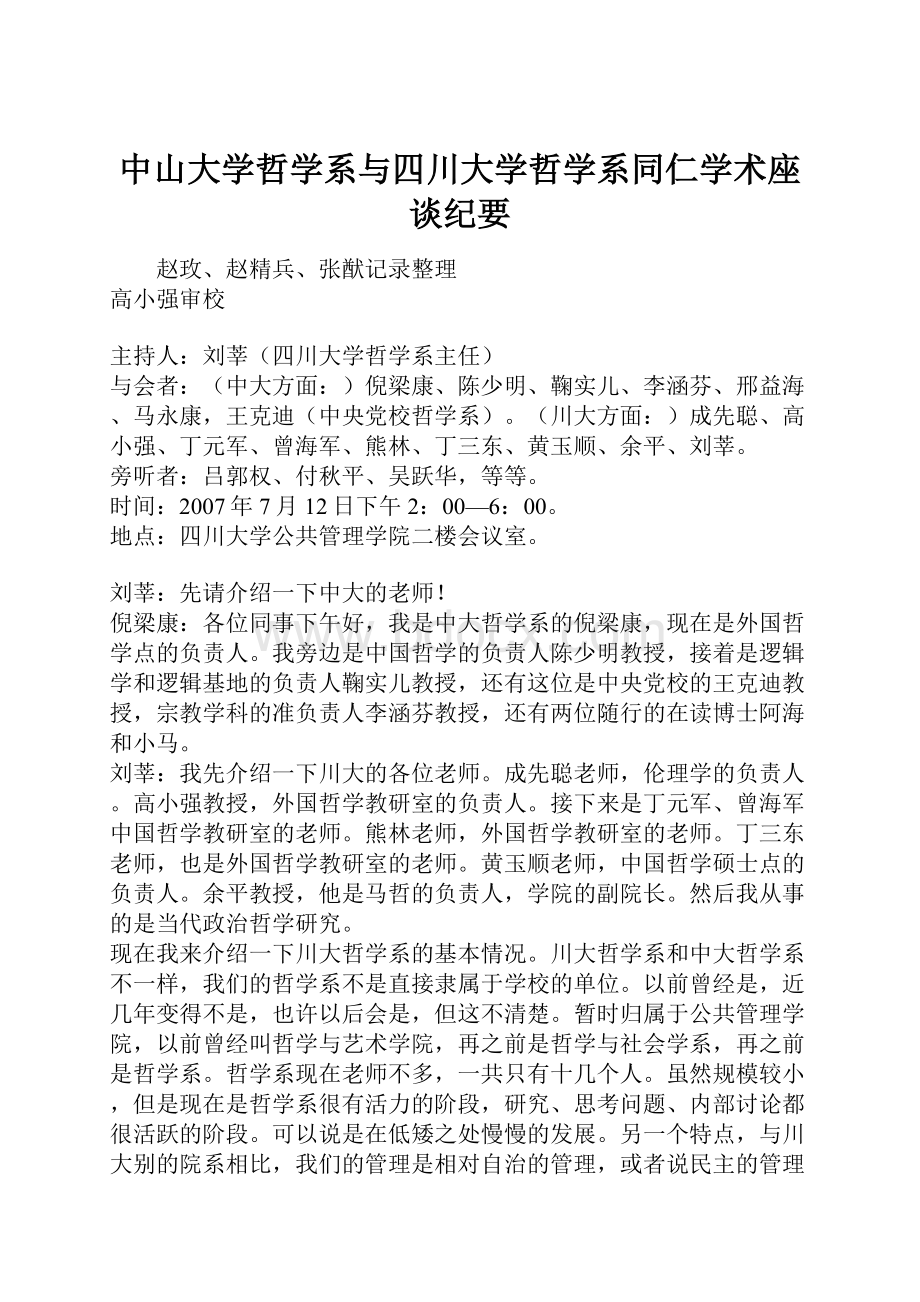
中山大学哲学系与四川大学哲学系同仁学术座谈纪要
赵玫、赵精兵、张猷记录整理
高小强审校
主持人:
刘莘(四川大学哲学系主任)
与会者:
(中大方面:
)倪梁康、陈少明、鞠实儿、李涵芬、邢益海、马永康,王克迪(中央党校哲学系)。
(川大方面:
)成先聪、高小强、丁元军、曾海军、熊林、丁三东、黄玉顺、余平、刘莘。
旁听者:
吕郭权、付秋平、吴跃华,等等。
时间:
2007年7月12日下午2:
00—6:
00。
地点: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二楼会议室。
刘莘:
先请介绍一下中大的老师!
倪梁康:
各位同事下午好,我是中大哲学系的倪梁康,现在是外国哲学点的负责人。
我旁边是中国哲学的负责人陈少明教授,接着是逻辑学和逻辑基地的负责人鞠实儿教授,还有这位是中央党校的王克迪教授,宗教学科的准负责人李涵芬教授,还有两位随行的在读博士阿海和小马。
刘莘:
我先介绍一下川大的各位老师。
成先聪老师,伦理学的负责人。
高小强教授,外国哲学教研室的负责人。
接下来是丁元军、曾海军中国哲学教研室的老师。
熊林老师,外国哲学教研室的老师。
丁三东老师,也是外国哲学教研室的老师。
黄玉顺老师,中国哲学硕士点的负责人。
余平教授,他是马哲的负责人,学院的副院长。
然后我从事的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川大哲学系的基本情况。
川大哲学系和中大哲学系不一样,我们的哲学系不是直接隶属于学校的单位。
以前曾经是,近几年变得不是,也许以后会是,但这不清楚。
暂时归属于公共管理学院,以前曾经叫哲学与艺术学院,再之前是哲学与社会学系,再之前是哲学系。
哲学系现在老师不多,一共只有十几个人。
虽然规模较小,但是现在是哲学系很有活力的阶段,研究、思考问题、内部讨论都很活跃的阶段。
可以说是在低矮之处慢慢的发展。
另一个特点,与川大别的院系相比,我们的管理是相对自治的管理,或者说民主的管理。
我们有一个系务委员会,重大事情是由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系主任由系务委员会产生,轮流坐庄,有明确的年限。
这个体制的自主性比较强,营造了相对好的气氛,与行政化的官方体制抗衡的力量相对强大些。
比如引进人才,就是由委员会无记名投票决定,投票之前充分探讨。
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学校一级的管人事的书记都没有投票权。
我和我们很多老师对这一点是相当看重的,相当自豪的。
而在研究方面,川大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各位老师之间也进行了很多交流。
今天各位教授的到来,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学习的契机。
下面能不能请作为客人的中山大学教授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描述,然后大家再来探讨,将这个会议讨论进行下去。
我们请了一些研究生来做记录,然后将会议记录发布在思问哲学网上,供更多的学界的朋友来了解交流。
首先我们还是正式地对我们的客人表示欢迎。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学术讨论。
我们的讨论可以是非常灵活的,不拘一格,而不是甲方乙方。
倪梁康:
我听前面的介绍,好像你们的老师都比较多才多艺。
比较的气氛浓一些,两位中西哲的负责人都是跨学科的。
我先介绍一下中大哲学系的情况。
先代表系主任给你们问个好。
中大哲学系的规模比较大,仅算哲学系共有50个人。
我们是一级学科,8个教研室,8个学科点,都有博士授予权。
刘森林老师是马哲的学科负责人,我是外哲的学科负责人,陈少明老师是中哲的学科负责人,鞠实儿老师是逻辑学的学科负责人,刘小枫老师是美学的学科负责人,伦理学的学科负责人由中大副校长暂带,宗教学的学科准负责人是李涵芬老师,还有张志林老师是科哲的学科负责人。
两个重点学科是逻辑学和马哲。
中哲现在正在申报。
中国哲学力量比较强,包括陈少明老师,冯达文老师,龚隽老师,还有我也作一些中西比较,主要还是外国哲学。
想做一些跟意识哲学相关的,比如中国儒家的心学,佛家的唯识学,道家的心性学等等。
就是想把意识哲学这一条线路——也不是说打通——看看有那些思想资源可以利用。
我这里还有一个小礼物。
我们刚成立了一个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
之所以想起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行内有很多人想把西方哲学理论东渐史搞清楚。
华中科技大学的黄见德老师,他本来想在武汉做这个事情,但是迟迟没有做起来。
加上北京几个朋友,包括洪汉鼎先生,还有台湾的几个朋友,他们都认为应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我后来想了一下,在中山大学作这个事情是有道理的。
因为两次对外开放,第一次包括从海上丝绸之路过来,利玛窦进到广东;第二次主动对外开放也是在广东开始的。
后来就在省政协提了一个议案,得到了一笔启动经费,去年就成立了,但是在2008年才能正式建馆。
我们想把它建成一个全国性的西学东渐文献中心,因为这个地方可以和利玛窦故居、梁启超故居、康有为故居、孙中山故居等等一系列连在一起。
以后再慢慢向研究中心迈进。
现在学校对我们哲学系很支持,我们有两个基地,马哲教学基地和逻辑学教学基地。
在03年时教育部做过一次排名,中大的总体实力排名是全国第五,科研成果是全国第二。
可以说在体制内还是有一些地位,再加上在“黑道”上我们的刘小枫老师影响比较大。
我们的周围的氛围还算可以,我的感觉是全国十所重点大学,学校支持哲学系力度最大的是中山大学。
我们科研成果总量是全校人均第一,而人均科研基金是全校第二,学校对我们的支持一直是比较大的,以至于社科处说投入产出比也不见得怎么样。
这次申请重点学科,以后还要评重点一级学科,我们就想把自己的事做好,对学校里面也有一个交代。
我看川大哲学系的内部气氛很好,各专业的老师在与会时都能聚在一起,不像有的学校,只接待自己专业的人,中哲管中哲马哲管马哲。
现在对我自己做一点介绍。
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做一点行政方面的工作和西学东渐文献馆的事情,三分之二的时间还是在做现象学,现在还在做语言哲学。
或者说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关系或意识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关系。
很想用下半生——如果还有下半生的话——来做唯识学。
功底不够,只能慢慢做。
我们这边正好有一个佛学研究中心,我和龚俊老师在做一些佛学研究。
也不能说是中西比较中外比较,因为唯识学也是西方的东西。
比较西学,因为两个都是西方来的东西。
现在我做了一些,就招来了一些批评,说是西方话语侵入佛学,需要抵制。
我就觉得很奇怪,佛学也是西方话语。
上次开会时,山东大学一个作国学的说,整个中国哲学被西方哲学话语弄的不伦不类,只有佛学还有自己的话语系统讲话。
我感觉这还是一种偏见。
我们不应该老是讲中和西,应该是探讨问题,看哪一个对我们思考和解决问题有帮助,就往那边发展。
我自己在几次讨论会上都在谈,我觉得比如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学术的自主性这些问题,我都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假问题。
我说应该还是像王国维那样,“学问不分中西”。
哪些方式对我们解决问题有帮助,就用那些方式;而不应该分东方和西方。
我就说这些,大家有不同意见我们再交流。
鞠实儿:
(略)
倪梁康:
鞠实儿是一头牵着逻辑学数学,一头牵着哲学,两边都有。
实儿刚才讲的两条线,一条像是结构主义,另一条是一个文化主义。
鞠实儿:
逻辑本来就是这样,你讲民主,讲科学,都要逻辑。
我曾经到一个法学院去讲学,问他们学不学逻辑,他们说不学逻辑。
中国的法学为什么不学逻辑还能工作,难道这是纯粹的愚蠢吗?
不是的,因为中国是允许用辩证逻辑的,一分为二呀,矛盾两方面呀。
这些辩论方法到美国是不承认的,到台湾,到香港也都是不承认的。
这说明两种不同文化讲道理的方法是不同的,这并不是错误。
陈少明:
那我来介绍一下吧,我是中国哲学的负责人。
我们中哲的历史还是比较长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真正上中国哲学这门课的老师并不多。
教本科的严格来说就只有三个人。
但是我们做中国哲学研究的老师很多,除我之外还有:
佛教哲学的龚隽、冯焕珍等人。
研究西方哲学的老师在中国哲学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可喜成就,如陈立胜老师,他近几年出的书都是关于中国哲学的。
倪梁康也做了一部分,他刚编译了一个唯识宗的一个注[1],是从外文翻译并加注的书。
所以从外面看起来我们做中国哲学的人还是很多的,但是上课的人并不多,这其实不是很要紧的。
我本人的一个工作,很难明确地说,因为很多事情是在我做过去以后,事后才知道的。
我做的跟中哲有关的工作,前后大概是这样的。
最早我对中国近现代哲学比较感兴趣。
在研究的时候,我比较重视其思想背景的研究,也研究新儒家之外的东西。
后来,我慢慢对中国古典的先秦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做的比较完整的是一本关于《齐物论》方面的书。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有了比较复杂的想法:
当我们在做近现代哲学史的时候会碰到原典与解释的哲学不一致的问题。
大家都有体会的事就是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并非是文本原来的意思,而是教科书作者本人带有的一些看法。
因此,当我们读到这些书籍时,实际上是在读教科书作者的观点,而不是在读古代思想家的观点。
这个改造是非常大的,这种改造的结果是在我们教研究生读原典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无法用在教科书上的那套东西做原始文献,或要不就是无法和教科书做得特别不一样。
这样,我们就倾向于加强对原著的阅读。
这样做就导致了我后来有一个想法,弄了一个《经典与解释》,并不是单纯研究经典,而是研究经典被解释的过程。
因为现代的教科书里收集到的是对经典的最新的解释形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同样一部经典他们前后都解释出不同的东西。
这里我们可以得出来两点启发:
1、研究每一个时代的人如何利用经典来构造他们的想法。
利用这个词可能比较强,也许他们不觉得他们是在利用,而是他们读出来的东西。
但是如果各个时代读出来的都不一样,那么,这个经典就不完全是他原本所追求的要表达的东西。
每一个时代的成功如何可能的。
2、所有的经典都是因为它开创了一个传统。
没有开创一个一个传统的经典是不存在的。
严格地说,如果一本书没有被解释它就不会是经典。
经典不是写出来的,而是通过解释一本书才能成其为经典。
那么,我们也可以研究一种思想文化的传统是怎么形成的。
后者更像是一种思想史,而前者更带有解释学的意味。
但是这两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按照这样的思路导致我写了《〈齐物论〉及其影响》的书,写作本书我出于两个目的,一方面想关照《齐物论》一文跟《庄子》一书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看《齐物论》对中国哲学的侧面影响。
我会把一个解释的流程跟每一段有创造性的解释与原典之间的方法和根据结合起来,这就是我所做的一个工作。
近来,我又有一些自觉的想法,就是关于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学界许多讨论如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价值或是方法论的问题。
我们多数的讨论都是在争论过去的做法好还是不好,但是这永远没有一个绝对的说法。
因为这个学科已经形成了这么多的影响以后,你笼统地说它行与不行——当然说是是可以的——但你很难通过逻辑的方式改变别人对它的看法。
唯一的可能性就在于,在我们建立了一个学科之后,如何理解我们的文化及其理解哲学的利与弊,进而我们要如何改进它。
按照我的理解,中国哲学这个概念是近代以来才兴起的,之前只有“理学”或者“玄学”一类。
这样一来大概有两种不同的形态:
1、如冯友兰,试图把中西方的一些概念共同构造出一个严格的体系来。
这个体系不一定包括全部的哲学,而是从古典观念中选取他本人最喜欢认为最有价值的概念,用他最熟练的方法构造成为一个系统,如他的《新理学》。
另外,有这种倾向但表现弱一些的,比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牟宗山的宋明理学的诠释,这些东西构造性弱,但诠释性强。
2、是看起来以中立的形态来叙述的,比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一些早期的书[2]等等。
这些东西表面不一样,但共同的是以西方哲学的范畴或命题为蓝本,抽取很多相关的东西来叙述。
这是现在的教科书的常态,于是就有一个问题:
所讨论的问题与原典对不上号。
这其实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是很少有人会认为读教科书胜过读原典。
这在读《庄子》原著本文时体现得最明显。
《庄子》文本里面有许多非常精彩很有意思的、不管我们叫不叫哲学,总之进不到教科书的叙述范围,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教科书即便不说失败,也是有有严重局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如何把以往两种形态做出的重要的东西,导入现在通用的哲学语言,把那个东西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做的问题。
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就是注意到经典文本中的叙述性的文本。
中国经典中论说文并不是很多,《荀子》里面有一篇,《孟子》其实是伪造成对话的论说文。
《庄子》里面有大量的故事叙述,《论语》里面也很多都是故事的片断,另外《礼记》,《韩非子》参半、《荀子》、《易传》比较像论说。
但传统的论说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的辩论,而是陈述而非论证一种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阅读不同的文本,我对那些故事性比较强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因此,我写了一篇《经典之中的人、事与物》,我们会看到《论语》中很多人物的行为人格和别人以他们为典范来表达的关于人格问题的一些观点。
另外,很多有意思的描述性的事件,在历史上启发人们对某些观点进行思考。
再有一个就是物,比如在《庄子》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些非人的东西,如石头、鸟与鱼一类,就这些问题《庄子》一个很明显的观点,就是儒家对山水、理气各个方面对世界的看法,这里没有论证,而是道德、审美的意向,并与社会的问题相互附和。
因而对于这些素材,如果我们给它一个新的论说方式,会做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出来。
我自己就尝试着做过两种:
一种以《论语》为主要的文本来讨论一些事情。
我会注意到孔子的三个学生:
颜回、子贡、子路,这三个人在《论语》里从来没有同时出现,但是两汉的传说中会让三个人同时出场。
为什么汉人专选这三个人必定有他们自己的缘由,我就是想从汉人的这个结构看出儒家对人格的一个看法。
还有一种,有一类事件其实从历史上来打量它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后来的文献一再重复这个事件,通过重复叙述这个故事来扩大它的影响。
比如说关于“孔子厄于陈蔡”的事件,如果把简帛的记载包括进去的话,一共有十个故事。
关于这类故事你会思考:
为什么同一主题,同样的人物会重复的被叙述?
这表现了一个文化上哲学上很有意思的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也很有意思,按西方的观念在中国哲学里有一些重要的内容,但是你却无法说是什么东西。
比如孔子说“四十而不惑”的“惑”字,在西方哲学里很难找到有人就此问题专题讨论。
但是有人也会提出西方讨论的“认识论”问题,就是在解决认识的问题,但是这不是同一个问题。
在中国传统中,从儒家开始讲“无耻”。
他们认为一个人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无耻。
我们一般只谈及为人的最高标准,圣人,而没有考虑限制人不成其为人的最低标准,就是有耻无耻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含了我们文化的很多问题,如果能把它们导出来的话,也是很有意义的。
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古代的叙述就不一定要像西方那样,讲一个包罗万象的认识论或本体论体系,而可以有新的尝试。
我觉得这样的尝试,这不仅与古人的生活经验,也与今人的生活经验有一个交叉。
这个交叉是一个土壤,但是我不确定我能做到什么地步。
自从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开始,大家有许多的尝试,比如黄玉顺老师提出的“生活儒学”观念,面对我们的真实生活,这些都是有价值的。
但具体的做法又是不一样的,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些尝试。
另外,如果从哲学的叙述方式上来说,是不分中西的,如果你是在讲哲学你一定要说出在讲哲学语言的人中互相能够承认的话。
我就先讲这么多吧。
鞠实儿:
我没有研究过历史,但如果一个人说“我想知道历史真相”,他说这句话有没有意义?
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比如你(指陈少明)说解释,一个经典文本在那里,我解释它。
人们会有对此不同的解释,有一个第三者标准在里边,我们可以对之提出评价。
我就想问“历史真相”的说法有没有意义?
你又如何知道历史上一个词的用法?
陈少明:
你说的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所谓的历史真相。
问题有点像分析哲学家一样,简单事实和复杂事实。
你可以把一个历史分解成简单事实,当然你可以断定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站起来了”是毛泽东说的还是周恩来说的。
如果历史学家仅仅这样理解历史,那么他们就是很肤浅的了。
如果是你要评估的一个事实,比如文化大革命,问题就很复杂了,这个问题的真实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鞠实儿:
你是不是说,某月某号几点几分某一个人说“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一个物理事实?
陈少明:
它不是一个物理事实。
一变成社会事实,问题就复杂多了。
第二个问题:
关于概念在历史上的演变——这是一个历史语言学问题——这个问题绝对是没有的。
但是,毕竟有一个接近,就像阮元在写《性命古训》的时候,每一个时代都是有一些可以验证的内容的。
李涵芬:
我是研究宗教学的,我们系做宗教研究与做哲学研究有一定的关联。
从事宗教研究的老师还要兼顾其他方面的研究,比如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
另外,一些非正统宗教研究出生的老师,由于他们研究的倾向,我们也会把他们纳入到我们的研究队伍中来。
所以,我们的队伍是比较松散的。
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有冯达文老师,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研究所,现任的所长是刘小枫老师。
相关课程的承担分为两个部分,本科与研究生的课。
基督教研究,佛教研究,从大范围来说我们有西方宗教的经典、东方宗教的经典两门必修课。
我们道教研究有个特别之处,要和外系老师联合开课,包括历史系,人类学系等。
与很多的大学一样,宗教研究一般依附于哲学系。
所以从研究的特点方面来说,偏重对观念或思想理论的研究偏多。
现在也有一些实证的研究。
我们系的研究成果最突出的就是基督教、佛学的研究。
比较宗教研究也有,但还在摸索。
接下来,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研究内容,自我作为个体的存在与那些神圣体验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实际上是把整个人的生活,把整个人的意义的追问与宗教相关联,而不去管这个人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徒。
我力图说明的是人身上的宗教性是如何体现的。
这种研究要求落实到个体案例的分析当中。
所以在基督教里我会关注到奥古斯丁,在伊斯兰教我会关注到……(?
),在佛教里我会关注太虚大师等一些人。
我注意到个体作为存在,他的生活经验、他对生活经验理性的思考以及他对神圣的信仰三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包括之间的和谐与紧张。
从更大范围上来说,我把这个问题关注到一个社群、一种文化形态,看它跟宗教的关系。
我以前还还力图做把中国宗教学科的发展历史,作思想史的分析。
它是怎么出现的,有些什么思想背景社会背景,由此引起了中国宗教学科的理解上面的问题、研究方法上面的问题,包括为什么要把宗教要放在哲学中的问题。
在大学里,宗教研究总是和哲学系相互纠缠,从而使得宗教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是非常薄弱的。
但是在理论研究上就很好吗?
恐怕不尽然。
所以,宗教研究作为一个学科要关注什么问题来是与研究者的心态相关的,很具随意性的,还没有严格的成熟的学科的意味。
我是把宗教问题看作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也和学者对其他学科有一些关系相似的。
如在“科玄论战”、“非宗教运动”和“儒教之争”等问题中,都有一些体现。
这些就是我在做的一些工作。
刘莘:
刚才中大的老师给我们谈了许多个人研究成果以及学科建设方面的内容。
接下来,我想根据自己的意愿,让我们川大的老师作一个回应或提问。
黄玉顺:
我觉得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性。
你们中大的研究我一向都特别关注,特别是倪梁康老师的现象学研究。
我对你们中大的整体印象就是经典诠释的氛围。
我个人有一些疑惑需要提出来。
我用陆象山的话头来说,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我认为都不地道。
就我个人看来,我会将它表达成为“注生我、经”。
我想说的是,一个历史的、对象性的文本和“我”这样一个“中心文本”,两者都不是先行的,都是被给出来的,我关心的是它是被什么东西给出来的?
还有倪老师介绍,你们各个学科渗透融合得相当好,我就想问,你们对何为诠释学的观念是不是有一个共识?
倪梁康:
我先讲几句,据我对刘小枫和陈少明的了解,我觉得你们是不一致的。
刘小枫会认为“解释”一词的使用是不合适的,因为“解释”是带有很多主观意念的。
用他说得斯特劳斯的方法来注柏拉图,他会说我解释的就是柏拉图他本人,而不是我的解释。
但是在中外思想史上所展现出来的脉络来看,人们都认为我解释的就是他本身而不是我的解释,但是——像少明刚才所说的——结果他们都是一种解释而已。
我自己的观点认为在整个中西方思想史上,“我注六经”的方法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不能成为随意性的解释。
鞠实儿刚才提到的历史问题,所有的历史是有真相的。
在讨论历史真相时,至少应该有两点是进行辩论前提:
1、我们都认可有一个真相的存在。
2、在诸多的解释中,要用同一种论证方式。
但我讲这两个前提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不见得有这两点就能得出真相。
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尽可能的接近实事,尽管所有的解释都是主观的。
我觉得中国的解释学派过多的夸大了主观性的合法性,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随意性。
这是我想反对的。
陈少明:
我和刘小枫没有讨论过我们关于解释是否有共同观点。
但是,没觉得就不能和对方一起工作了。
我回想一下,第一个就是我首先要强调一个文化与经典文本的重要性问题。
刘小枫认为经典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原则是压倒一切的,他很喜欢讲施特劳斯的解释学,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真实性就是原作者的一个动机(这与现代许多解释学家的看法不相容),这个动机阐释者是否猜测到了,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所以你在研究古今的历史事件,就需要大量的资料用来猜测。
而至于说解释的主观与客观的问题,除了那些经验性的物理事实(有唯一答案)之外,但是在这基础上的解释,我们都认为它不是无数的,也不是唯一的解释。
由于理智跟价值的制衡,总是那么五六种在竞争。
如何从逻辑上说明这个竞争,很复杂。
这是我对你那个问题的回应。
黄玉顺:
你说“经典是在诠释中成为经典的”,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有些经典,比如说《论语》有很多诠释,何以某些诠释就成为经典,其他的就不怎么样?
这是一个问题。
倪梁康:
现象学和解释学中间有一个连接号,实际上按照胡塞尔的观点来看,现象学的解释学就像一个木质的铁一样,也是一个语词悖论。
因为现象学按胡塞尔是要把握实事本身的,但解释学又认为事实本身是把握不了的,因为每个人的视域是有限的。
但是从现象学来说,解释学的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
比如,我们讲看这个杯子,每个人看到的都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他如何渺小,他的位置只有一个。
那么我们何以可能说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认识方式是一样的,虽然我们的认识对象可能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在找这个共同结构,即所谓哲学就是反思,无论哪种文化,无论哪种民族精神,只要有反思的能力,它都可以找到共同之处。
成先聪:
我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当代的中国人当下的生存问题。
由此进入到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此过程中就涉及到了宗教问题(我原来的专业是美学),进而还关注道德或宗教问题。
我觉得宗教问题是尤为关切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讨论存在的生存结构,这个问题也张显中西的最大分歧。
我这些年翻译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书,比如尼布尔的《人的本性与命运》,以前还翻译过蒂里希和奥托,都是西方的一些作品。
刚才诸位的谈话给我很大的启示,中西方对问题的讨论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深层结构,从表面上看有很大区别。
这一点是怎么造成的,能不能相互印合,这些都是我很关注的。
儒家是最讲道德的,现代中国的状况很让人忧心。
总体来说,我是凭借兴趣行事,而没有一个长远的固定的计划。
这次中大的同仁的到来在学科建设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很大,就是关于学科建设的一些长远架构和设想,以后要通盘考虑。
高小强:
我先来简单谈一下中大哲学系给我的印象,然后再谈一个我关注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倪梁康老师在给我们发电邮说要来访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仁们有一个很欣喜的感情。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在国内哲学界,我们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把中山大学的发展摆在第一位。
中山大学哲学系做的一些工作我们都非常的欣赏。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山大学如果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是迟早应该在大陆众多大学的哲学系里面拔头筹的,这是我们一个强烈的感受。
因此我们为您们的到来是有很强烈的欢迎和期待的。
您们在谈的时候,我心里面始终是在想一个问题。
实际上从倪老师那里就开始出来了,他引用王国维的话,说“学问不分中西”,在陈老师那个地方有一个“哲学不分中西”的说法,实际上您说他们最后的论证一定要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东西,倪老师在补充的时候又提到了,有两个前提:
一个是事实的真相、实事本身;再就是相同的,你用了相同的,后来我看你又好像是把它弱化了一点,——相近的认知与论证方式,这样我们才能讨论。
事实上,我在听的时候在鞠老师那里显然有不同的看法。
鞠老